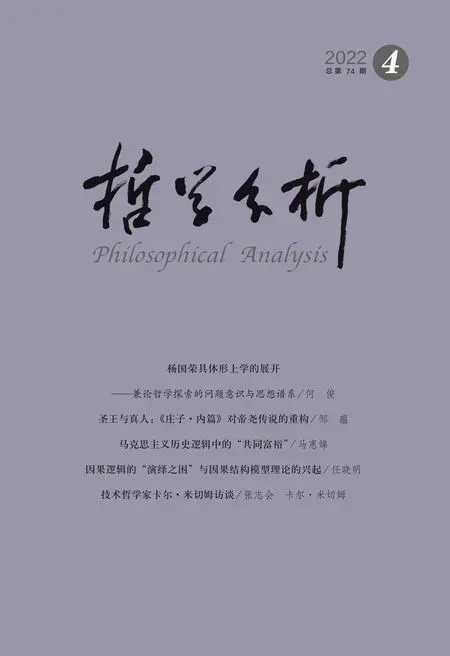楊國(guó)榮具體形上學(xué)的展開
——兼論哲學(xué)探索的問題意識(shí)與思想譜系
何 俊
純?nèi)坏目陀^世界先于人的存在,但這一純?nèi)坏目陀^世界的存在卻又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即便仍然是純?nèi)坏目陀^世界——盡管這不具有現(xiàn)實(shí)的可能性,它的存在仍然成為不同于作為純?nèi)坏目陀^世界而存在的存在。究其根本,一切因?yàn)槿恕H耸沟眉內(nèi)坏目陀^世界成為具有功能與意義的世界,并且這樣的功能與意義是呈以不斷延伸的狀態(tài)的;與此同時(shí),作為純?nèi)坏目陀^世界的組成部分,人也獲得自身存在狀態(tài)的展 開。
這原本是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但是由于人的獨(dú)特性——人是具有精神性的存在,并且其精神同樣處于不斷延伸或充實(shí)的狀態(tài),因此人對(duì)于自身從純?nèi)坏目陀^世界中分離出來(lái),進(jìn)而觀察與施為于作為對(duì)象存在的純?nèi)坏目陀^世界時(shí),人如何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guān)系,以及如何處理自身與世界的關(guān)系,就成為一個(gè)基本性的預(yù)設(shè)前提。宋儒陸九淵以他著名的兩個(gè)命題給出了一個(gè)明確的回答:第一,“宇宙內(nèi)事乃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乃宇宙內(nèi)事。”第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雖然這并不是唯一的確認(rèn),但由于這一確認(rèn)非常明確地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尤其是人作為精神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心——獲得了標(biāo)示,因此這一確認(rèn)為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的理解與處理提供了富具開放性的空 間。
只是,盡管在標(biāo)示心體存在的思想家那里,心與事幾乎是同步展開的,但是,也許是因?yàn)樾牡南蚨纫仁碌南蚨雀哂兄黧w性的特征,或者是更具有主體的自由度,事的向度總是牽扯許許多多的羈絆,有許許多多的條件,因此心的向度很容易成為思想者青睞的世界。何況,追尋自由終究是作為主體存在的人的最高理想。作為當(dāng)代中國(guó)最具創(chuàng)造性追求的哲學(xué)家,楊國(guó)榮教授的哲學(xué)探索也是由心體的打開開始 的。
一、心學(xué)的剖析
眾所周知,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宋明理學(xué)研究破冰之初,作為高考制度恢復(fù)以后的第一屆大學(xué)生,楊國(guó)榮就以他的博士論文《王學(xué)通論:從王陽(yáng)明到熊十力》贏得學(xué)界瞻目。對(duì)此書的最大特點(diǎn),楊國(guó)榮的導(dǎo)師馮契先生在序中指 出:
由對(duì)王學(xué)體系的內(nèi)在矛盾的揭露,進(jìn)而說(shuō)明王門后學(xué)的分化,著重考察了志(意)知之辯的演進(jìn),李贄把王學(xué)引向異端,黃宗羲完成對(duì)王學(xué)的自我否定,并在“歷史的余響”的標(biāo)題下討論了王學(xué)在中國(guó)哲學(xué)近代化中的雙重作用等。這一系統(tǒng)的有條不紊的考察,比較好地貫徹了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的統(tǒng)一,因此許多論斷顯得很有說(shuō)服 力。
基于這一判識(shí),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指出:將陽(yáng)明學(xué)作為一代思潮加以研究,在著眼點(diǎn)上就必須很大程度上與僅僅研究陽(yáng)明思想本身有所不同。前者的研究,必須在陽(yáng)明思想中找到一條能將陽(yáng)明思想與其后學(xué)聯(lián)貫起來(lái)的線索,而且王陽(yáng)明作為整個(gè)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中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這條線索還必須能使陽(yáng)明學(xué)可以被擺在思想史中加以解 釋。
楊著于首章“王學(xué)的興起”中首先通過(guò)對(duì)朱嘉、陸九淵思想的簡(jiǎn)要闡述,勾勒出他們各自的思想建樹及理論上的難題,從而引出陽(yáng)明學(xué)中的一貫線索乃是陽(yáng)明思想中所存在著的個(gè)體意識(shí)與普遍天理這一內(nèi)在二重性的結(jié)論。楊著以為,這一內(nèi)在二重性來(lái)自王陽(yáng)明對(duì)朱熹、陸九淵各崇天理與吾心的理論弊端的認(rèn)識(shí),而謀取此對(duì)立兩面的融通則促成王陽(yáng)明在理論上的建樹和對(duì)朱陸思想的超 越。
接著,楊著在第二章“王學(xué):王陽(yáng)明的思辯體系”里以占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詳細(xì)而縝密地闡釋、分析陽(yáng)明思想。作者指出,構(gòu)成陽(yáng)明思想的主要是良知與致良知說(shuō),其中良知是陽(yáng)明思想的基石,致良知是對(duì)良知的貫徹、落實(shí)。作為天理與吾心的合一,良知蘊(yùn)含了雙重性;良知作為先驗(yàn)之知,當(dāng)其與后天之致相聯(lián)系構(gòu)成致良知時(shí),致良知中便又有對(duì)立而求融通的兩面;陽(yáng)明一生注重“事上磨煉”,其致知工夫,具體上是展開于踐履(行)的過(guò)程之中的,因此,致知過(guò)程實(shí)際上便成了知與行的合一并進(jìn)。基于這種闡釋,楊著較前人更確切地把握住了王陽(yáng)明思想的本質(zhì),合理地揭示出其內(nèi)在矛盾,從而科學(xué)地判定了王陽(yáng)明思想的積極作用與 局 限。
由對(duì)王陽(yáng)明思想體系的闡釋,楊著分別于第三章“致良知說(shuō)的分化”、第四章“志(意)知之辯的演進(jìn)”中對(duì)陽(yáng)明后學(xué)的分化進(jìn)行了討論。由于王陽(yáng)明思想中所包含的二重性注定其演變不可能表現(xiàn)為單向的進(jìn)展,故而在才智性情歧異不一的王門后學(xué)處,陽(yáng)明思想必然遭到不同的理解而被加以詮釋。對(duì)于王門后學(xué)的分化,前人作有多種解釋,但楊著由于從王陽(yáng)明思想的內(nèi)在二重性出發(fā)來(lái)觀察王門后學(xué),因而使得他對(duì)王門后學(xué)紛爭(zhēng)的闡釋成為當(dāng)時(shí)最為細(xì)密、合理的解釋,足可備一說(shuō)。除了對(duì)王門后學(xué)的分化作出闡釋以外,楊著還在第五、六章中通過(guò)分析李贄、黃宗羲對(duì)王學(xué)的改造,從一個(gè)側(cè)面,兩個(gè)典型人物身上對(duì)晚明社會(huì)思想的發(fā)展提出了頗具說(shuō)服力的看法。總之,在闡釋陽(yáng)明學(xué)這一思潮方面,楊國(guó)榮當(dāng)時(shí)的研究實(shí)已提出了超越于前人的新釋 義。
此外,研究前人的哲學(xué)思想,闡釋是基礎(chǔ),與之相應(yīng)展開的理論上的細(xì)微分析則是不可或缺而猶見力度的工作。楊著于此方面,可謂相當(dāng)精彩。王陽(yáng)明本人立教,強(qiáng)調(diào)的是明心見性,事上磨煉,于文字甚是輕視,其思想亦即形式上的體系,要于細(xì)微處分析,研究者除了要吃透王學(xué)外,還必須具有相當(dāng)?shù)睦碚撍仞B(yǎng)。楊著的優(yōu)點(diǎn)在于:其一,所有的分析都從寬廣的理論視野出發(fā),這不僅使分析細(xì)微而深入,而且使所得論斷具有富有啟迪的理論意義。譬如在闡釋王陽(yáng)明良知(心)的雙重規(guī)定的過(guò)程中,楊著指出在王陽(yáng)明“在心稟受于天(得于天)的前提下,將吾心與理融為一體”的思辯形式中,包含著一些理論上的新建樹,“首先是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作為當(dāng)然之則的天理)與個(gè)體的道德意識(shí)的合一”。其次是“先驗(yàn)的知識(shí)條理(天賦的普遍之理)與自思合一”。再則是“一方面揚(yáng)棄了(作為主體意識(shí)的二重屬性的)個(gè)體性與普遍性的抽象同一,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二者的分離”,使二者統(tǒng)一的具體規(guī)定“以普遍觀念在主體認(rèn)知、評(píng)判過(guò)程中漸漸展開(具體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這些見解無(wú)疑是深刻 的。
其二,在借助西方哲學(xué)來(lái)分析比較陽(yáng)明學(xué)時(shí),不是以草率的態(tài)度、粗陋的手法給王學(xué)簡(jiǎn)單地貼上這樣或那樣的標(biāo)簽,而是力求通過(guò)理論上的印證加深對(duì)王學(xué)的認(rèn)識(shí)。這樣的工作在整本著作中有許多,如對(duì)陽(yáng)明良知中所含先驗(yàn)之知識(shí)條理的分析,對(duì)陽(yáng)明致知過(guò)程中的主體認(rèn)知結(jié)構(gòu)的分析,對(duì)王艮自我的分析等等。從對(duì)王學(xué)的認(rèn)識(shí)來(lái)說(shuō),這樣的工作無(wú)疑是促進(jìn)了分析上的深刻,而就中外哲學(xué)之比較研究來(lái)看,顯出相當(dāng)?shù)墓?力。
我重述楊國(guó)榮通論心學(xué)中的深入闡釋與精細(xì)分析,首先意在表達(dá),楊國(guó)榮對(duì)于心體的分析與認(rèn)知自始即在一個(gè)較高的水準(zhǔn)上展開的事實(shí);其次意在強(qiáng)調(diào),雖然他后來(lái)在心學(xué)方面有進(jìn)一步的研究,而且在哲學(xué)理論上開始進(jìn)入自覺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但其學(xué)術(shù)視野、思想方法,以及具體的分析模式(我姑且概之為“二重性分析建構(gòu)法”)可以認(rèn)為是基本一以貫之 的。
二、立心于事
不過(guò),正如楊國(guó)榮在《王學(xué)通論》中所分析與梳理的那樣,如果限于心學(xué),則即便是在陽(yáng)明本人,其心學(xué)的建構(gòu)中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nèi)在二重性,至于基于心學(xué)而展開的思想,直到熊十力,這種內(nèi)在二重性也未能消除。另一方面,我也曾通過(guò)對(duì)王門后學(xué)的討論,指出王門后學(xué)由于在良知工夫的落實(shí)上封域于意識(shí),幾無(wú)不流歸禪學(xué)。泰州學(xué)派強(qiáng)調(diào)“即事是學(xué),即事是道”,原本足以開出新境,但惜未能真正在“事”的視域作出真正的思想透視,而只是流于表象的活動(dòng),故最終沒有轉(zhuǎn)出新的思想,而只表征為“非名教之所能羈絡(luò)”而不被列入“王門”。概言之,心學(xué)不能只論心,必須有賴于事的視域打開,才能真正建立“具體的”形上學(xué),否則只是“抽象的”形上學(xué)。這里所謂的“具體”與“抽象”,乃取用黑格爾的概念,抽象意謂著貧乏與膚淺,而具體則是豐富與深刻。楊國(guó)榮在哲學(xué)上的探索,從心學(xué)開始,中經(jīng)不同論域,諸如政治哲學(xué)、倫理學(xué)等方面的思考,晚近回到事的視域,以建構(gòu)他具體的形上學(xué),這便是他在《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中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最新成 果。
《人與世界:以事觀之》除去“自序”“導(dǎo)論”與兩篇“附錄”外,共六章。首章論事與現(xiàn)實(shí)世界,揭明現(xiàn)實(shí)世界不等同于本然的存在,現(xiàn)實(shí)世界因人的活動(dòng),亦即事而形成,并因此而獲得意義,故因事而成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既是事實(shí)性的存在,又具有價(jià)值性的規(guī)定。次章論人因事而在,揭明人的本質(zhì)在于其實(shí)踐,亦即事的展開,人通過(guò)事的展開建構(gòu)了社會(huì)關(guān)系,同時(shí)賦予其意義。第三章從事的視域看存在與生成及其相互關(guān)系的問題,揭明存在與生成不是獨(dú)立的,而是相合的,這種相合性恰恰根植于事。第四、五章由事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討論,轉(zhuǎn)向心物關(guān)系以及知識(shí)論的分析。在第四章中,楊國(guó)榮指出,“僅僅囿于‘心’或限于‘物’,往往難以超越思辨之域而達(dá)到對(duì)兩者內(nèi)在意義以及相互關(guān)系的真切理解,唯有引入‘事’的視域,才能把握‘心’與‘物’的不同內(nèi)涵并揚(yáng)棄兩者的分離”。從中我們足以看到楊國(guó)榮早年開始的心學(xué)研究所形成的認(rèn)識(shí)在其中的作用與意義。心物關(guān)系自然衍生出知行關(guān)系,并聚焦于事。第五章是基于第四章的一個(gè)深入,無(wú)論是心物關(guān)系,還是知行關(guān)系,最終都導(dǎo)向事物之“理”。“事中求理”與“由理發(fā)現(xiàn)事”是此章的主旨。第六章論事與史,乃是將單個(gè)的事置于時(shí)間之流中加以討論,從史的角度理解事的意義所在,同時(shí)從事的角度理解歷史的真實(shí)性。整個(gè)討論圓滿而充分,其最終所確立起的思想邏輯,大概可由最后的兩篇附文獲得表征,即從人與世界關(guān)系中的感受出發(fā),從而在認(rèn)知、評(píng)價(jià)、規(guī)范相統(tǒng)一的意義上理解人類的認(rèn)識(shí)并落實(shí)于具體的形態(tài),即以事觀 之。
為了更進(jìn)一步凸顯楊國(guó)榮早年博士論文就開始逐漸形成的思想方法,即前文所概括的“二重性分析建構(gòu)法”,請(qǐng)舉具體的論述以為呈現(xiàn),且以最后一章,第六章“事”與“史”為例。在此章的引言中,楊國(guó)榮就非常嫻熟地通過(guò)兩句古詩(shī)將事與史的二重性挑明:孟浩然的“人事有代謝,往來(lái)成古今”,是把“事”中的“史”點(diǎn)出;李賀的“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fēng)飄”,則將“史”坐實(shí)于“事”之上。換言之,當(dāng)人們面對(duì)紛然雜陳,朝夕變化的種種事相時(shí),唯有深具歷史意識(shí),方能把握其中的意義,否則種種事不外是毫無(wú)意義的存在;而當(dāng)以歷史的眼光去透視現(xiàn)實(shí)時(shí),如果不能落實(shí)于從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領(lǐng)域到文化領(lǐng)域方方面面的具體事上時(shí),歷史雖千歲亦隨風(fēng) 飄。
在此下的“‘事’以成‘史’”一節(jié)中,為了更深入推進(jìn)“事以成史”的討論,楊國(guó)榮對(duì)“事”又進(jìn)行了“個(gè)體性的活動(dòng)”與“類的層面”的分析,即“寬泛而言,作為人之所‘作’,‘事’既表現(xiàn)為個(gè)體性的活動(dòng),也展開于類的領(lǐng)域。在個(gè)體的層面,個(gè)人所做之‘事’的延續(xù)構(gòu)成其人生過(guò)程;在類的層面,人‘事’的代謝則呈現(xiàn)為前后賡續(xù)的歷史演進(jìn)過(guò)程”(第199頁(yè))。由此,楊國(guó)榮對(duì)兩個(gè)層面的“事”逐次展開分析,并且將這種分析置于中西哲學(xué)的比較視域中進(jìn)行,一如其在早年博士論文中所呈現(xiàn)的風(fēng)格。比如,楊國(guó)榮通過(guò)舉證海德格爾關(guān)于“存在”的概念,以及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的命題(第199—200頁(yè)),指出“對(duì)個(gè)體領(lǐng)域之‘事’與類的領(lǐng)域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一些哲學(xué)家往往未能給予必要的關(guān)注”(第199—200頁(yè))。然后,楊國(guó)榮對(duì)“事”與“史”的關(guān)系作出他的充分論述,即在各種可能性的維度上,對(duì)“事”與“史”的關(guān)系進(jìn)行說(shuō)明,以表征“事以成史”的核心判斷。在這一表征的過(guò)程中,無(wú)論是涉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諸如日常言說(shuō)與網(wǎng)絡(luò)支付等等,還是關(guān)乎歷史進(jìn)程的重大事件,諸如二戰(zhàn)時(shí)期的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與愛因斯坦的相對(duì)論,“二重性分析建構(gòu)法”獲得嫻熟而一貫的使 用。
對(duì)于一個(gè)富具創(chuàng)造性探索的哲學(xué)家,他的思想成果實(shí)際上由兩方面構(gòu)成,一個(gè)自然是他的思想內(nèi)容,這往往為所有人所關(guān)注,另一個(gè)則是他的思想方法。由于思想方法常常隱遁于思想探索的過(guò)程與思想成果之中,容易被忽視,或難以獲知。所謂“鴛鴦繡好與人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既是在述說(shuō)不輕易傳授方法,但也完全存在著另一種廣泛存在的可能,即作為方法的金針,即便在原創(chuàng)者那里也未必有高度的自覺。楊國(guó)榮曾就他的哲學(xué)研究方法作有“思”與“史”并重互涵的說(shuō)明,在某種意義上,思史并重與互涵也是“二重性分析建構(gòu)法”的一種具體使用,但也因?yàn)橹皇且环N具體使用,故作為楊國(guó)榮的哲學(xué)方法論而言,我以為“二重性分析建構(gòu)法”更具有普遍的理論價(jià) 值。
三、象山心與事的印證
在闡明了楊國(guó)榮的方法以后,為了更具體地彰顯楊國(guó)榮《人與世界:以事觀之》的哲學(xué)內(nèi)涵及其意義,我試取象山心學(xué)處理心與事的關(guān)系,進(jìn)一步來(lái)佐證楊國(guó)榮的分析,同時(shí)也通過(guò)對(duì)象山心與事思想的闡釋,來(lái)補(bǔ)充楊國(guó)榮的論 述。
在本文開頭即引入的象山兩個(gè)基本命題中,除了宇宙與主體的關(guān)系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獲得確認(rèn)以外,象山心學(xué)的認(rèn)知格局中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即事與心的問題,亦即少年象山援筆所書的另一段話:“宇宙內(nèi)事乃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乃宇宙內(nèi) 事。”
依據(jù)發(fā)生認(rèn)識(shí)論的原理,人的認(rèn)知格局主要是通過(guò)人的活動(dòng)而獲得形塑的,所謂人的活動(dòng),便是象山所講的事。事實(shí)上,活動(dòng)不僅在認(rèn)知格局最初形成時(sh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在此后的認(rèn)知中始終起到持續(xù)的作用,因?yàn)檎J(rèn)知格局是在持續(xù)擴(kuò)充并得以固化的。而且憑借著“吾心即是宇宙”的開端,象山的“吾心”就把自身顯示為宇宙存在的根據(jù);不是宇宙作為矢量性存在的根據(jù),而是宇宙作為人化了的存在的根據(jù)。這意味著,宇宙既被理解和表述為客體性質(zhì)的存在,又被理解和表述為主體性質(zhì)的存在。實(shí)現(xiàn)這一理解與表述的,顯然不能限于心本身,而必須通過(guò)心所要面向的事情,亦即活動(dòng),即事。換言之,無(wú)論是理解心,還是確立心,必須使心面向事情;作為主體性表征的心體,它的存在也在于它所面向的事情本 身。
如何清楚地闡明這個(gè)問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這個(gè)問題涉及的是心的體會(huì),本身具有語(yǔ)言難詮之處;另一方面,心面向的事情雖然是具體的,但由此事情反過(guò)來(lái)表征心體,即由個(gè)體性的經(jīng)驗(yàn)求得普遍性的認(rèn)識(shí),并不是必然能夠?qū)崿F(xiàn)的。但是無(wú)論如何,象山仍然是選擇了由心面向的事情的揭明,使人對(duì)“心之體”獲得真切的理解。最經(jīng)典的案例便是象山對(duì)楊簡(jiǎn)(1141—1226)的教導(dǎo)。在《象山先生行狀》中,楊簡(jiǎn)追憶道: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jiǎn)安得而知之?惟簡(jiǎn)主富陽(yáng)簿時(shí),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yáng),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jiǎn)發(fā)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jiǎn)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wú)始末,忽省此心之無(wú)所 不通。
象山門下主要有兩部分弟子,一部分是以家鄉(xiāng)為主,即槐堂諸儒,象山學(xué)派的門庭張大主要靠他們;另一部分便是浙江為主,以甬上四先生為代表,象山心學(xué)的思想傳衍主要靠他們,楊簡(jiǎn)是甬上四先生之首。楊簡(jiǎn)小象山兩歲,卻早象山為進(jìn)士,象山舉進(jìn)士那年,楊簡(jiǎn)恰在臨安,故得與象山相識(shí),并有所討教,但真正執(zhí)弟子禮,則緣于象山回江西經(jīng)過(guò)楊簡(jiǎn)任職的富陽(yáng)時(shí)所經(jīng)歷的問學(xué),即《行狀》所述。這件事情無(wú)論對(duì)楊簡(jiǎn),還是對(duì)象山,似乎都非常重要,不僅楊簡(jiǎn)在《行狀》中專門追憶這件事,此前也是經(jīng)常舉此例,而且象山《年譜》中有更詳細(xì)的記錄,此外其他文獻(xiàn),如《宋史·楊簡(jiǎn)傳》 《宋元學(xué)案·慈湖學(xué)案》中都有述及。實(shí)際上,在象山學(xué)派內(nèi),楊簡(jiǎn)問學(xué)這件事情表征了象山心學(xué)的核心思想,即通過(guò)心面對(duì)的事情而對(duì)心體獲得確 認(rèn)。
其實(shí)對(duì)于這件事,前引《象山先生行狀》所述過(guò)于簡(jiǎn)略,并不能完全使局外人明白。前引《行狀》,主要是說(shuō)明楊簡(jiǎn)本人對(duì)此的重視。真正要討論這件事,還是以《年譜》的記載更為親切。《年譜》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34歲條 載:
四明楊敬仲時(shí)主富陽(yáng)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yáng),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guò)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duì)曰:“簡(jiǎn)兒時(shí)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shù)問,先生終不易其說(shuō),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lái)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jiǎn)發(fā)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jiǎn)忽省此心之無(wú)始末,忽省此心之無(wú)所不通。”
在這個(gè)詳盡的記錄中,可以看到,楊簡(jiǎn)數(shù)問“如何是本心”,象山總是答以孟子的四端之說(shuō)。象山的講學(xué)水準(zhǔn)非常高,不僅清晰,而且能切人心。朱子任南康守時(shí),曾邀象山至白鹿洞書院講座,象山講解“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朱子嘗以親身感受對(duì)人 曰:
這是子靜來(lái)南康,熹請(qǐng)說(shuō)書,卻說(shuō)得這義利分明,是說(shuō)得好。……說(shuō)得來(lái)痛快,至有流涕者。
但他面對(duì)楊簡(jiǎn)的數(shù)問,卻只是答以孟子的四端之說(shuō),而且楊簡(jiǎn)明確聲明,四端之說(shuō)自己“兒時(shí)已曉得”,象山仍不作任何闡釋。顯然,象山明白,本心之問不是一個(gè)語(yǔ)辭可以解決的問 題。
尤其需要指出的,楊簡(jiǎn)的問題是“如何是本心”?而不是“何為本心”?如果是后者,那么楊簡(jiǎn)的本心之問更近乎是一個(gè)對(duì)象性的客觀問題,其解答可以與主體無(wú)關(guān);而前者,則與主體密切相關(guān),因?yàn)樗^“如何是本心”,預(yù)設(shè)的追問并不是一個(gè)對(duì)象性的客觀認(rèn)識(shí)問題,而更是一個(gè)主體如何成其為主體的問題,即如何使主體確立起本心。因此,對(duì)于飽讀了經(jīng)典的楊簡(jiǎn)來(lái)說(shuō),象山任何的闡釋都只能是以往知識(shí)的重復(fù),不可能真正啟動(dòng)楊簡(jiǎn)的本心去面對(duì)事 情。
海德格爾指出,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使得主體性構(gòu)成了哲學(xué)的堅(jiān)固基地之后,“思的任務(wù)就應(yīng)該是:放棄以往的思想,而去規(guī)定思的事情”。雖然海德格爾的分析是針對(duì)著科學(xué)從哲學(xué)中分離出來(lái),致使哲學(xué)轉(zhuǎn)變?yōu)殛P(guān)于人的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從而使得哲學(xué)在展開為科學(xué)的意義上走向終結(jié),因此必須重新來(lái)思考“思”的任務(wù),完全是在現(xiàn)代語(yǔ)境中的追問;但是對(duì)于象山心學(xué)的理解仍然具有啟發(fā)。象山 曰:
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guò)依據(jù)末節(jié)細(xì)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shuō)謬悠無(wú)根之甚,……終日簸弄經(jīng)語(yǔ)以自傳益,真所謂侮圣言者矣。
在象山看來(lái),“終日簸弄經(jīng)語(yǔ)以自傳益,真所謂侮圣言者”,正仿佛海德格爾所謂的科學(xué)對(duì)哲學(xué)的終結(jié)。象山對(duì)朱子的不滿,根本原因也正在朱子熱衷于“終日簸弄經(jīng)語(yǔ)”,而不務(wù)實(shí)學(xué)。他在給朱子的信中,直言不諱地指 出:
尊兄當(dāng)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jìn)取一步,將來(lái)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jìn)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xué)術(shù),省得氣力為“無(wú)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zhì)實(shí),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shí)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者,以其事實(shí)覺其事實(shí),故事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shí)湮于意見,典訓(xùn)蕪于辨說(shuō),揣量模寫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xí)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dá),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xué)而識(shí)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wú)疑。……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
因此,回到楊簡(jiǎn)的“如何是本心”之問,象山始終沒有就孟子的四端之說(shuō)再作進(jìn)一步的闡揚(yáng),而最終因斷扇訟的判決開悟楊簡(jiǎn),決不是一種隨意的教學(xué)權(quán)宜之策,而完全是基于他的思想的抉擇。象山要使楊簡(jiǎn)的本心從經(jīng)文及其繁雜的解釋中擺脫出來(lái),讓本心直面事情本身,從而本心得以呈現(xiàn)相應(yīng)的是非判斷。楊簡(jiǎn)由斷扇訟的是非曲直判定,進(jìn)而省悟“此心之無(wú)始末”“此心之無(wú)所不通”,心之體終于獲得確 立。
這個(gè)案例表明,如何是本心的問題,與其說(shuō)是一個(gè)需要言語(yǔ)分辯的問題,毋寧說(shuō)是一個(gè)如何擺脫言語(yǔ)所帶來(lái)的遮蔽的問題。只有揭去這樣的遮蔽,本心才能面向事情本身,本心所具有的四端才能自然展開,作出判斷。象山曾就義利問題出一策問,亦可以佐證他的思想。策問 曰:
圣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凡圣人之所為,無(wú)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shí),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dāng)時(shí)首政急務(wù)。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guó)”,未有它過(guò),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辯之力?……辟土地,充府庫(kù),約與國(guó),戰(zhàn)必克,此其為國(guó)之利固亦不細(xì),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kù)之空竭,鄰國(guó)之侵陵,而不為之計(jì),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shuō)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wú)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shí),則無(wú)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茍 逃也。
歷史表明,凡圣人之所為就是為天下謀利,而孟子作義利之辯,仿佛是違背常識(shí),故“世以儒者為無(wú)用,仁義為空言”。象山以為,世俗之蔽在于對(duì)孟子之說(shuō)作了“鹵莽”理解,只有深究其實(shí),才能消除儒者無(wú)用、仁義空言的譏誚;而這個(gè)所謂的“實(shí)”,便是面向事情本 身。
不過(guò),為什么當(dāng)面向事情本身時(shí),“如何是本心”的問題就得以解答了呢?當(dāng)然,可以認(rèn)為象山對(duì)楊簡(jiǎn)四端之心的回答本身就隱含著答案,因?yàn)樗亩酥膬?nèi)含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自我判明。但是,為什么這一內(nèi)含著四端之心的本心在必須面向事情時(shí),這樣的自我判明才得以呈現(xiàn)呢?由象山對(duì)楊簡(jiǎn)的說(shuō)明,“聞適來(lái)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似乎可以推知,當(dāng)本心面向事情時(shí),事情本身具有著某種道理,足以使得本心所隱含著的是非明辯力作出判明。《語(yǔ)錄》曰:
有行古禮于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lái)請(qǐng)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于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shí)言之,則去古既遠(yuǎn),禮文不遠(yuǎn),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于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如世俗甚不經(jīng),裁之可也,其余且可從舊。”
父子發(fā)生沖突,蓋因兒子固執(zhí)于死了的古禮,而未能面向事情本身。而象山引導(dǎo)其面向事情本身時(shí),行喪禮之實(shí)重在哀而不在禮,就能使人作出合理的調(diào)適。換言之,當(dāng)本心面向事情時(shí),存于事的理與存于人的本心會(huì)相合無(wú) 間。
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象山心學(xué)的格局中,關(guān)于心與事的問題,象山是通過(guò)使本心面向事情來(lái)實(shí)現(xiàn)本心的自明與確立的,而理在事中,理與心為一,則是相應(yīng)的兩個(gè)基本思想。關(guān)于理在事中,《語(yǔ)錄》第一條 曰:
“道外無(wú)事,事外無(wú)道。”先生常言 之。
可見這是象山的核心思想。唯此,象山以為,因吾心而人化了的宇宙,無(wú)處不是道的呈現(xiàn),人只有因一己之病才會(huì)與道相隔;道總在宇宙中,也總在圣人的活動(dòng)中。《語(yǔ)錄》接著前條,續(xù) 曰: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圣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 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 理。
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zé)者,皋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范》,則居于夷狄,不食周粟。
關(guān)于理與心為一,同樣講得極清楚。在與人的書信中,象山 曰:
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dāng)歸一,精義無(wú)二,此心此理,實(shí)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nèi)此理也,外亦此理也。
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yáng),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
可以說(shuō),只有明確了道在事中,心與理為一,“宇宙內(nèi)事乃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乃宇宙內(nèi)事”,才真正獲得了落實(shí),才真正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一起,構(gòu)成為象山心學(xué)的格 局。
當(dāng)然,本心雖然必須在面向事情中獲得確立,但心并不能糾纏甚至沉溺于事情中,否則便使心失其“本”。象山 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nèi)時(shí),當(dāng)惻隱即惻隱,當(dāng)羞惡即羞惡。誰(shuí)欺得你?誰(shuí)瞞得你?見得端的后,常涵養(yǎng),是甚次第。
然而,人心往往適得其反,逐物而難返。象山 曰: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shí),如鶻孫失了樹,更無(wú)住處。
只是,這已屬于象山心學(xué)中如何發(fā)明本心所必須關(guān)心的問題,此處不再延伸開去 了。
四、問題意識(shí)與思想譜系
至此,我們足以確信楊國(guó)榮在《人與世界:以事觀之》的“自序”中所指出的:
中國(guó)哲學(xué)中“事”這一概念,可以比較好地幫助我們表述廣義的人類活動(dòng)及其結(jié)果,而在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中則似乎難以發(fā)現(xiàn)同樣的概念。……“事”這一中國(guó)哲學(xué)的概念也從一個(gè)方面表明,中國(guó)哲學(xué)中存在著其他文化傳統(tǒng)所缺乏的觀念表達(dá)形式,這些表達(dá)形式有助于推進(jìn)對(duì)世界以及人類生活更為深廣的理 解。
換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楊國(guó)榮最新的哲學(xué)探索表征了他希望從中國(guó)哲學(xué)的概念形式來(lái)推進(jìn)哲學(xué)思考,這當(dāng)然可以說(shuō)是他一直來(lái)的努力,但《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一書顯然呈現(xiàn)得更為充 分。
只是,在充分肯定與彰顯楊國(guó)榮的哲學(xué)探索的同時(shí),許多年來(lái)也不免存有內(nèi)心的疑問:哲學(xué)探索的問題意識(shí)究竟源于什么?思想新創(chuàng)如何接續(xù)學(xué)術(shù)譜系?這兩個(gè)問題側(cè)重略有不同,但彼此又具密切關(guān)聯(lián)。前者重在問題意識(shí),后者重在學(xué)術(shù)接續(xù);問題意識(shí)的發(fā)生與學(xué)術(shù)本身的知識(shí)呈現(xiàn)有時(shí)會(huì)存在一定的間隔,或顯與隱的區(qū)別,但本質(zhì)上又是具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20世紀(jì)80年代思想界曾興起過(guò)創(chuàng)造體系的熱情,但終因流于膚淺而消歇;而這種膚淺究其實(shí)質(zhì),也正是問題意識(shí)的蒼白與學(xué)術(shù)譜系的無(wú)源。90年代起,學(xué)術(shù)界漸歸趨學(xué)術(shù)本位,在知識(shí)園地上作深入耕耘,結(jié)出豐碩成果。近年來(lái),也許是以為90年代以來(lái)的知識(shí)耕耘已累積到足以有所思想突破,或不甘于知識(shí)耕耘的清寂,哲學(xué)界似乎又重興創(chuàng)造體系的熱情,使得上述問題再次凸顯。前文已述,楊國(guó)榮的哲學(xué)探索既非起于近幾年,更非追步時(shí)流,而是已經(jīng)歷年,卓多建樹。照理,我不應(yīng)以上述問題來(lái)反思他的最新研究。但是,也許正因?yàn)闂顕?guó)榮的哲學(xué)探索具有顯著的標(biāo)桿性,因此,由他的新著來(lái)提出上述問題的思考,或許更具意義,同時(shí)也是更表達(dá)對(duì)楊國(guó)榮工作的敬 意。
20世紀(jì)80年代包括陽(yáng)明心學(xué)在內(nèi)的宋明理學(xué)研究興起,對(duì)于催破固化了的學(xué)術(shù)研究與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而深遠(yuǎn)的意義,因此,這些研究雖然呈以哲學(xué)史的研究,但無(wú)疑都富涵著時(shí)代的問題意識(shí),同時(shí)又具有著學(xué)術(shù)研究自身的內(nèi)在動(dòng)力。但是,當(dāng)學(xué)界將學(xué)術(shù)研究的興奮點(diǎn)轉(zhuǎn)向所謂的體系建構(gòu)時(shí),這些建構(gòu)的問題意識(shí),以及學(xué)術(shù)研究自身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又究竟是什么呢?我在高度稱譽(yù)楊國(guó)榮的《人與世界:以事觀之》后,專辟一節(jié)來(lái)闡揚(yáng)象山哲學(xué)的相關(guān)思想,一方面是為了以古證今,彰顯古今哲思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表達(dá),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脫離了哲學(xué)史的接續(xù),這樣的共同性也意味著今人的哲學(xué)探索可能流于形式。尤其是眾所周知,當(dāng)象山在闡明他的本心面向事而確立的思想時(shí),他不僅是充滿著時(shí)代的問題意識(shí),是針對(duì)著朱子學(xué)知識(shí)主義膨脹的現(xiàn)實(shí)而展開的,而且象山的思想闡揚(yáng)始終是接續(xù)著孟子思想來(lái)進(jìn)行的,在傳承中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造,這是思想脈絡(luò)的連貫,并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嫁接。換言之,當(dāng)我們體會(huì)一種真正的哲學(xué)創(chuàng)造時(shí),我們總是能夠深切地體會(huì)到這種創(chuàng)造在現(xiàn)實(shí)的問題意識(shí)與學(xué)術(shù)的思想脈絡(luò)兩方面的綰合之力,正是這種綰合之力構(gòu)成了新的哲學(xué)創(chuàng)造的內(nèi)在動(dòng) 力。
事實(shí)上,傳統(tǒng)中國(guó)哲學(xué)如此,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也同樣如此。請(qǐng)各舉中西方哲學(xué)一例以見之。先舉哈貝馬斯為例。哈貝馬斯以他的批判理論為標(biāo)志,成為當(dāng)代最重要的哲學(xué)家之一。但是,正如研究所表明,哈貝馬斯雖然是以批判理論為標(biāo)志,但他的理論既是對(duì)當(dāng)代德國(guó)和歐洲的現(xiàn)實(shí)問題作出回應(yīng)并進(jìn)而引領(lǐng)時(shí)代潮流,從而對(duì)現(xiàn)實(shí)產(chǎn)生深刻的直接影響,又是接續(xù)著歐洲哲學(xué)的思想譜系而展開的推進(jìn)。其中,就哈貝馬斯對(duì)歐洲哲學(xué)思想譜系的接續(xù)與推進(jìn),由于批判理論是他的思想標(biāo)識(shí),因此容易被置于亞里士多德—斯賓諾沙—馬克思的序列中來(lái)加以理解;事實(shí)上,哈貝馬斯也同時(shí)接續(xù)了詹姆斯—杜威—皮爾斯的美國(guó)實(shí)用主義傳統(tǒng),以及從狄爾泰到伽達(dá)默爾的德國(guó)闡釋學(xué)傳統(tǒng),因而才通過(guò)他的《交往行為理論》提出了他的重建而非歷史的方法,向前作出巨大的推進(jìn)。再舉陳來(lái)為例。陳來(lái)的中國(guó)哲學(xué)研究一直以來(lái)定位于哲學(xué)史研究,但近年來(lái)也在哲學(xué)體系的創(chuàng)構(gòu)中有所探索,最顯見的便是他的《仁學(xué)本體論》。對(duì)于此書的具體思想,已溢出本文主題,這里只是指出,陳來(lái)提出的仁學(xué)本體論最為凸顯的問題意識(shí)是針對(duì)著李澤厚的情本論的,而其學(xué)術(shù)譜系則可以理解為是對(duì)整個(gè)孔孟程朱儒學(xué)傳統(tǒng)的接續(xù);而背后深層的現(xiàn)實(shí)回應(yīng)無(wú)疑是處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guó)哲學(xué)主體性的掘發(fā)與話語(yǔ)重 建。
以此為參照,楊國(guó)榮哲學(xué)探索的問題意識(shí)與學(xué)術(shù)譜系顯得有點(diǎn)隱晦。這并不等于說(shuō),楊國(guó)榮沒有自己相關(guān)的闡述。從淺近的角度講,他曾有意識(shí)地梳理過(guò)現(xiàn)代中國(guó)哲學(xué)中的金岳霖—馮契思想脈絡(luò),以智慧論為聚焦,從深廣的角度講,他的著作中呈以廣譜性的思想對(duì)話,不問東西古今。然而,從接受者的立場(chǎng)看,楊國(guó)榮的哲學(xué)創(chuàng)構(gòu)更近于哲思的自我展開,論題在這樣的自我展開中遷延,方法在這樣的自我展開中成熟。不僅難以在學(xué)術(shù)思想的譜系上把握到他的思想聚焦,更難以體會(huì)到他在問題意識(shí)上的針對(duì),最主要的收獲只能集中在他的思想的自洽性 上。
當(dāng)然,高度自洽的思想建構(gòu)同樣是哲學(xué)家的重要目標(biāo)之一。因此,當(dāng)我們接受到楊國(guó)榮哲學(xué)探索的這一特性時(shí),已然是一個(gè)巨大的收獲。事實(shí)上,哲學(xué)本身便是以它的獨(dú)特性而彰顯其在整個(gè)知識(shí)世界中的意義,哲學(xué)自身更當(dāng)以多樣性的探索與呈現(xiàn)來(lái)表征自己的獨(dú)特性。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上述的疑問不免有所多余,或近乎苛責(zé)。正如前文已述,由于楊國(guó)榮的哲學(xué)探索及其創(chuàng)造在當(dāng)代中國(guó)誠(chéng)為標(biāo)桿,因此從各種角度提出必要的疑問,不僅是對(duì)當(dāng)代中國(guó)哲學(xué)是有意義的,也是對(duì)楊國(guó)榮的工作深具敬意的表 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