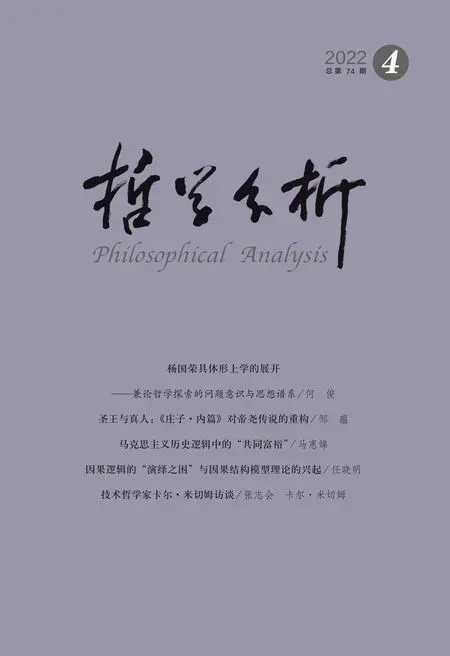事與思
——對“以事觀之”若干評(píng)論的回應(yīng)
楊國榮
在1996年完成、1997年出版的《心學(xué)之思——王陽明哲學(xué)的闡釋》一書中,我曾以“事與思”為題,專列一節(jié),討論王陽明的心學(xué)與他所作之事的關(guān)系。如以上標(biāo)題所示,該部分中的“事”被賦予了重要意義。2021年,以《人與世界:以事觀之》為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我的另一理論性著作,其中,“事”進(jìn)一步成為考察世界的廣義視域。盡管前后兩書有側(cè)重歷史與側(cè)重理論之異,但哲學(xué)進(jìn)路則大致一以貫之。2021年10月,在江西婺源舉行了《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一書的討論會(huì),學(xué)界同仁就相關(guān)的哲學(xué)思考提出了諸種問題,后續(xù)又有以此為主題的論文,這里以其中三篇論文為主作一回應(yīng),但回應(yīng)內(nèi)容不限于這三篇文 章。
自康德以來,德國古典哲學(xué)區(qū)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種認(rèn)識(shí)形態(tài)。這種區(qū)分既涉及認(rèn)識(shí)論,也有本體論或形而上學(xué)的意義。從把握世界的方式看,感性側(cè)重于經(jīng)驗(yàn)性方式;知性主要體現(xiàn)為邏輯的分辨和劃界;相對于知性而言,理性更多地以跨越界限的形上理解為進(jìn)路。從19世紀(jì)以降的哲學(xué)衍化來看,早期的實(shí)證主義比較偏重于三者之中的感性,盡管實(shí)證主義也注重邏輯分析,但是它對意義的追問首先以能否被感覺經(jīng)驗(yàn)所確證為標(biāo)準(zhǔn),從這一傾向來說,雖然實(shí)證主義不限于感性經(jīng)驗(yàn),但似乎與之有更直接的聯(lián)系。后來的分析哲學(xué)比較側(cè)重知性這一層面:從總體上說,其進(jìn)路基本不超出知性思維。分析哲學(xué)注重嚴(yán)密的邏輯分析,并趨向于以劃界的方式把握世界,在這一方面,它大致延續(xù)了康德哲學(xué)的傳統(tǒng)。比較而言,傳統(tǒng)的思辨哲學(xué)以及晚近的現(xiàn)象學(xué)更多地注重德國古典哲學(xué)意義上的理性層面以及形而上學(xué)的關(guān) 切。
在研究進(jìn)路上,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者之間的溝通,而非它們的相互并立或彼此分離。首先,包括日常經(jīng)驗(yàn)的感性層面應(yīng)給予必要的關(guān)注。眾所周知,中國哲學(xué)有“日用即道”的傳統(tǒng),生活經(jīng)驗(yàn)是中國哲人從事哲學(xué)思考的源頭之一,這一傳統(tǒng)值得關(guān)注。所謂形上與形下之間的溝通,重要的意義即體現(xiàn)于對感性經(jīng)驗(yàn)、生活世界、生活實(shí)踐的注重。其次,分析哲學(xué)所推重的邏輯分析方法,也需要加以重視,對于不同界限之間的區(qū)分亦不應(yīng)忽略,當(dāng)然,不能像分析哲學(xué)那樣,僅僅限定在劃界的層面之上而疏離不同界限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復(fù)次,對于理性的進(jìn)路,即“跨越界限而求其通”的把握世界方式,同樣不能加以拒斥,也就是說,哲學(xué)研究不宜限定在德國古典哲學(xué)意義上的感性或知性層面,而是需要接納理性。質(zhì)言之,合理的哲學(xué)研究方式在于兼容感性、知性、理性,以三者互動(dòng)的形式把握世界與人自身的存 在。
感性、知性、理性的交融體現(xiàn)于具體的哲學(xué)研究過程,涉及體系性建構(gòu)和系統(tǒng)化。寬泛而言,哲學(xué)研究需要區(qū)分體系性建構(gòu)和系統(tǒng)化的考察。體系總是追求包羅萬象的形態(tài),并常常趨向刨根問底,追問所謂最后的支點(diǎn)或原點(diǎn),從古到今,這一類體系化追求一再以多樣形式呈現(xiàn)于哲學(xué)史。分析哲學(xué)與現(xiàn)象學(xué)興起和傳入以后,受到其影響的學(xué)人每每在不同意義上追求純粹的邏輯形式,要求人們從最本源的命題出發(fā),展開層層的推論,由此建構(gòu)嚴(yán)整的體系。這種體系化進(jìn)路常常或者走向缺乏實(shí)質(zhì)內(nèi)容的空洞形式,或者陷于某種思辨哲學(xué),終究難以擺脫被解構(gòu)的命運(yùn)。事實(shí)上,歷史上各種形式的“體系”,總是無法長久延續(xù),從最初的原點(diǎn)或支點(diǎn)展開的體系化進(jìn)路,也很難被視為“做哲學(xué)”的合理方 式。
然而,盡管不應(yīng)追求體系化的建構(gòu),但是,哲學(xué)又需要系統(tǒng)化的研究。體系化和系統(tǒng)化應(yīng)當(dāng)加以區(qū)分:體系具有封閉的特點(diǎn),追求的是形式層面和思辨視域中的嚴(yán)整性,系統(tǒng)化則意味著肯定哲學(xué)觀念的多方面性及其相互關(guān)聯(lián),同時(shí)對所提出的見解和觀點(diǎn)進(jìn)行充分的論證,給出理由,提供根據(jù),使相關(guān)看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哲學(xué)領(lǐng)域的思考,不能僅僅憑借某些零星、偶然的感想,或孤立地提出某一觀念,而是需要給予相關(guān)的理論以系統(tǒng)化的考察,并對其作周密的論證,以避免流于缺乏充分根據(jù)的意 見。
歷史地看,哲學(xué)領(lǐng)域的很多概念都包含豐富、深沉的內(nèi)容,需要通過系統(tǒng)的研究,加以多方面地闡發(fā)。以“事”而言,作為哲學(xué)之域的概念,它至少在中國歷史上屬古已有之,以往思想家對其討論也綿綿不絕,直到今日,仍可看到相關(guān)的論辯。這一概念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思想界那里,也受到了不同的關(guān)注,日本學(xué)者廣松涉便先后出版了《事的世界觀的前哨》 《存在與意義——事的世界觀之奠基》等著作,如書名所示,其研究以“事”的觀念為核心。然而,綜覽其所述的實(shí)際內(nèi)容,則可注意到,廣松涉對“事”這一概念并未作實(shí)質(zhì)性的系統(tǒng)研究:他在“事”的名義之下所作的討論,似乎缺乏以事觀之的自覺意識(shí),也未能揭示“事”與人以及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內(nèi)在相關(guān)性。另外,晚近的學(xué)人對“事”雖有所注意,但對“事”的具體含義以及它在人與現(xiàn)實(shí)世界關(guān)系中的意義,卻又較少有自覺、清晰的認(rèn)識(shí):把“事”主要理解為fact,便表明了這一點(diǎn)。對“事”與fact的等量齊觀,基本上沒有超出維特根斯坦的視域:當(dāng)維特根斯坦說“世界是事實(shí)的總和,而不是物的總和”時(shí),他說的事實(shí)即指fact。以fact界定“事”,意味著將“事”主要限定在靜態(tài)的結(jié)果之上,這一理解至少在邏輯的層面,未能注意到“事”首先表現(xiàn)為人之所“為”或人之所“作”,從而,對“事”作為人的活動(dòng)及其結(jié)果的雙重涵義未能達(dá)到充分的意識(shí)。至于在更廣意義上把“事”放在“人與世界”這一寬闊的范圍作具有實(shí)質(zhì)意義的系統(tǒng)考察,相關(guān)之論則更是付諸闕如。由于缺乏系統(tǒng)的研究,“事”在把握世界中的真切意義,便無從實(shí)際地彰顯。以上思想現(xiàn)象從一個(gè)方面表明,哲學(xué)領(lǐng)域離不開系統(tǒng)性的探 索。
可以看到,哲學(xué)研究需要系統(tǒng)化,其核心觀念也應(yīng)該系統(tǒng)地展開,在哲學(xué)的探索中,不能僅僅就某一觀念提出靈光一現(xiàn)的見解,這種見解也許可以體現(xiàn)某種哲學(xué)的明智,但如果游離于系統(tǒng)性的考察,則其意義也將受到限制。如前所言,現(xiàn)時(shí)代已無需追求體系化的哲學(xué),但系統(tǒng)化的研究卻是嚴(yán)肅的哲學(xué)研究所不可或缺 的。
何俊教授的論文在追溯我哲學(xué)思考?xì)v程的同時(shí),也提出了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這里首先涉及哲學(xué)史與哲學(xué)的關(guān)系。關(guān)于這一問題,我以前也曾多次提及,總體上看,兩者難以相分。真切地理解哲學(xué)史,需要以哲學(xué)理論為背景,不然,所理解的哲學(xué)史可能只是對于以往思想材料的羅列。古往今來、幾千年中各種文獻(xiàn)和著作沒有實(shí)質(zhì)的變化,但對它們的理解和闡發(fā)卻發(fā)生了不同的變化。為什么會(huì)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這歸根到底源于解釋者的理論背景、理論視域存在差異,在這一意義上,欲讓哲學(xué)史上的文獻(xiàn)資料獲得進(jìn)一步的意義,闡釋者自身如果沒有深厚的哲學(xué)理論素養(yǎng),便很難做到。可以說,正是不同的解釋、相異的理論觀照,使對象獲得了新的思想生命 力。
另一方面,哲學(xué)理論建構(gòu)或思考也離不開哲學(xué)史:不能認(rèn)為一切都是從“我”開始,以往思維成果都可以不加理會(huì)。事實(shí)上,哲學(xué)的問題從其發(fā)生來看,總有歷史的根源,就此而言,也可以說哲學(xué)問題都是古老而常新的。按其本義,哲學(xué)問題的發(fā)生都是淵源有自,而非偶然產(chǎn)生,這一事實(shí)同時(shí)表明,要真正理解哲學(xué)問題,便必須聯(lián)系哲學(xué)史。法國哲學(xué)史家羅斑曾區(qū)分了哲學(xué)史與科學(xué)史,并認(rèn)為:“哲學(xué)史就是哲學(xué)本身”,“反之,科學(xué)史就不再是科學(xué),那是科學(xué)的過去。”換言之,與科學(xué)不同,哲學(xué)以哲學(xué)史為題中之義。進(jìn)一步看,解決哲學(xué)問題的重要資源,也來自哲學(xué)史。綜合起來,一方面,哲學(xué)問題的發(fā)生離不開哲學(xué)的歷史,另一方面,獲得解決哲學(xué)問題的資源,也需要回到哲學(xué)的歷史。哲學(xué)領(lǐng)域目前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兩個(gè)極端:或者疏離哲學(xué)理論,主要專注于文獻(xiàn)的爬梳;或者過于輕慢哲學(xué)史,對哲學(xué)史缺乏充分的敬畏。前者趨向于哲學(xué)向思想史的還原,后者則可能導(dǎo)致哲學(xué)的空疏化。離開了深厚的積淀,僅僅依靠靈光一現(xiàn),顯然難以形成真正的哲學(xué)問題:如果離開了人類文明幾千年積累的思想成果,所提出的哲學(xué)問題也許可以很精巧,但往往意義有限,更遑論切實(shí)地解決這些問 題。
具體而言,文章中提到的“哲學(xué)探索的問題意識(shí)與學(xué)術(shù)譜系”,關(guān)乎“史”和“思”之間如何溝通的問題。從哲學(xué)史上看,一些研究進(jìn)路或如文章所言,是自覺地上承某一學(xué)術(shù)脈絡(luò),接著某一學(xué)術(shù)“譜系”而說,但這并不是歷史性體現(xiàn)的唯一方式。學(xué)術(shù)脈絡(luò)或?qū)W術(shù)譜系,主要體現(xiàn)特定的學(xué)術(shù)傳承,但在哲學(xué)之域,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往往不限于這種狹義的學(xué)術(shù)譜系,而是以更廣意義上學(xué)術(shù)演化過程為背景。從哲學(xué)史上看,康德哲學(xué)固然與近代的理性主義與經(jīng)驗(yàn)論相關(guān),其理論在某種意義上以此前西方哲學(xué)的演化趨向?yàn)楸尘埃推湎到y(tǒng)本身而言,則既非表現(xiàn)為某種學(xué)術(shù)譜系的延續(xù),也難以簡單納入其中。與之類似,就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而言,馮友蘭的哲學(xué)固然可以追溯到程朱理學(xué),但同時(shí)代的金岳霖哲學(xué)則并不“接著”以往某一哲學(xué)脈絡(luò)說,從而展現(xiàn)了與馮友蘭“接著”理學(xué)說這一進(jìn)路有所不同的風(fēng)格。盡管在廣義上,金岳霖的哲學(xué)思考與中國哲學(xué)也具有相關(guān):其形而上學(xué)著作即以《論道》為題,至少在書名上可以看到他的形上之思與中國哲學(xué)的聯(lián)系,但這種相關(guān)性并不是以學(xué)術(shù)譜系的形式展現(xiàn),而是更多地表現(xiàn)為精神傳統(tǒng)的認(rèn)同。在當(dāng)代哲學(xué)中,以文章提及的李澤厚的思想而言,其哲學(xué)思考無疑獨(dú)樹一幟,盡管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儒學(xué)、康德、馬克思,但從學(xué)術(shù)譜系看,卻很難被歸入某種特定的傳承系統(tǒng)。以上事實(shí)表明,在哲學(xué)領(lǐng)域,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可以取得多重形式,并不僅僅限定于學(xué)術(shù)接續(xù)或直接承繼的模 式。
以我自身的哲學(xué)思考而言,如果要說學(xué)術(shù)脈絡(luò),則也許如論文已注意到的,我的學(xué)術(shù)進(jìn)路可以上溯到金岳霖、馮契的哲學(xué)傳統(tǒng),但在理論關(guān)切和理論研究方面,這種關(guān)聯(lián)并不單純地表現(xiàn)為狹義上的學(xué)術(shù)譜系。以人與世界的追問為指向,我的理論探索首先基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問題。在“具體形上學(xué)”系列著作的前言中,我已簡略提到這一點(diǎn):“近代以來,尤其是步入20世紀(jì)以后,隨著對形而上學(xué)的質(zhì)疑、責(zé)難、拒斥,哲學(xué)似乎越來越趨向于專業(yè)化、職業(yè)化,哲學(xué)家相應(yīng)地愈益成為‘專家’,哲學(xué)的各個(gè)領(lǐng)域之間,也漸漸界限分明甚或橫亙壁壘,哲學(xué)本身在相當(dāng)程度上由‘道’流而為‘技’、由智慧之思走向技術(shù)性的知識(shí),由此導(dǎo)致的是哲學(xué)的知識(shí)化與智慧的遺忘。重新關(guān)注形上學(xué),意味著向智慧的回歸。”這既可以視為我提出“具體形上學(xué)”的歷史前提,也體現(xiàn)了我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從更為切近的方面看,“‘具體形上學(xué)’一方面揚(yáng)棄了形而上學(xué)的抽象形態(tài),另一方面又與各種形式的‘后形而上學(xué)’保持了距離。在抽象的形態(tài)下,形而上學(xué)往往或者給人提供思辨的滿足(從柏拉圖的理念到胡塞爾的純粹意識(shí),都在不同意義上表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或者與終極的關(guān)切相聯(lián)系而使人獲得某種超驗(yàn)的慰藉。相對于此,‘后形而上學(xué)’的各種趨向在消解不同形式的超驗(yàn)存在或拒斥思辨構(gòu)造的同時(shí),又常常自限于對象世界或觀念世界的某一方面:在實(shí)證主義那里,現(xiàn)象—經(jīng)驗(yàn)被視為存在的本然內(nèi)容;對分析哲學(xué)而言,語言—邏輯構(gòu)成了主要對象;按‘基礎(chǔ)本體論’(海德格爾)的看法,‘此在’即真實(shí)的存在;在解釋學(xué)中,文本被賦予了某種優(yōu)先性;從批判理論出發(fā),文化、技術(shù)等則成為首要的關(guān)注之點(diǎn),如此等等。中國哲學(xué)曾區(qū)分‘道’與‘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系辭上》)‘道’既是存在的原理,又體現(xiàn)了存在的整體性、全面性;‘器’相對于道而言,則主要是指一個(gè)一個(gè)特定的對象。作為特定之物,“器”總是彼此各有界限,從而,在‘器’的層面,世界更多地呈現(xiàn)為相互限定的形態(tài)。從‘道’與‘器’的關(guān)系看,在肯定‘道’不離‘器’的同時(shí),又應(yīng)當(dāng)由‘器’走向‘道’,后者意味著越出事物之間的界限,達(dá)到對世界的具體理解。”不難看到,從柏拉圖以及其后的西方哲學(xué)到中國哲學(xué),從現(xiàn)代的分析哲學(xué)到現(xiàn)象學(xué),其哲學(xué)的進(jìn)路都構(gòu)成了“具體形上學(xué)”思考的廣義背景。當(dāng)然,如上所言,這種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切和哲學(xué)的傳承不同于特定的現(xiàn)象關(guān)注和譜系追溯,而是在更廣的意義上表現(xiàn)為歷史考察與現(xiàn)實(shí)回應(yīng)的交融,以此為前提,我的哲學(xué)思考既基于時(shí)代的問題,又以中國哲學(xué)的歷史發(fā)展和世界哲學(xué)背景下的多重哲學(xué)智慧為其理論之源。無論是以存在問題以及存在沉思進(jìn)路為論域的《道論》,還是以道德形上學(xué)為側(cè)重之點(diǎn)的《倫理與存在》、關(guān)注于意義領(lǐng)域的形上之維的《成己與成物——意義世界的生成》、敞開行動(dòng)及實(shí)踐形上內(nèi)涵的《人類行動(dòng)與實(shí)踐智慧》,以及從更本源的“事”這一維度理解人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人與世界:以事觀之》,都體現(xiàn)了以上特點(diǎn)。事實(shí)上,思想的現(xiàn)實(shí)之源和歷史傳承可以表現(xiàn)為多重方式,其間并無一定之 規(guī)。
相對于何俊教授對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的關(guān)注,彭國翔教授的文章更多地聚焦于“人”“事”“心”,并認(rèn)為“‘心’與‘事’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首先表現(xiàn)為‘人’與‘事’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以事觀之》一書所主張的是“事本論”,與之相對,他所持的,是“心本論”。圍繞以上幾個(gè)方面,文章作了種種討論,其中包含不少既有意義,也需要辨析的問 題。
事由人作,人因事成,人與事的關(guān)系,確實(shí)無法回避。內(nèi)格爾(Thomas Nagel)曾有the view from nowhere的表述,并以此為其一部重要著作的書名,從字面的意義上,這一觀念可以理解為“無處著眼”或“超然之見”,意謂無法從任何視域考察世界,或無法從任何角度獲得關(guān)于世界的客觀理解。人如何理解世界,是哲學(xué)領(lǐng)域一直思考的問題,與內(nèi)格爾的“無處著眼”有所不同,中國哲學(xué)比較早地形成了“以道觀之”(the view of Dao)的看法,從“道”的角度考察世界,意味著超驗(yàn)于特定的視域,比較全面地把握世界。然而,從根本上說,“以道觀之”乃是“人”以道觀之(The view from Dao by human):無論從特定角度看世界,還是以“道”為視域,都屬于人的考察。與之相近,“以事觀之”也是“人”以事觀之。從這方面看,人的視域是無法擺脫的:如后文所論,區(qū)分本然存在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也基于這一事實(shí)。進(jìn)一步考察,則可注意到,一方面,談到“事”,則“人”便在其中;另一方面,“人”又并非游離于“事”:在邏輯上,我們固然可以設(shè)定有“無所事事”的人或“無事”,但這一形態(tài)的“人”,往往并不被視為應(yīng)然之“人”,事實(shí)上,在貶義的層面,“無所事事”與“行尸走肉”常常被歸入相近類型,從而區(qū)別于人的真實(shí)形態(tài)或當(dāng)然形態(tài)。人之為人或人不同于動(dòng)物的根本規(guī)定,主要便在于:人的存在與做事、成事無法相分;可以說,人的當(dāng)然形態(tài)與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既源于“事”,也展開于事。關(guān)于這方面的內(nèi)容,《人與世界:以事觀之》已有比較具體的闡釋,這里不再贅 述。
更進(jìn)一步的問題體現(xiàn)于“心”與“事”的關(guān)系。文章寫道:“人之所以為人,究竟是因‘心’而在,還是因‘事’而在呢?”通過引孟子的相關(guān)論點(diǎn),文章肯定“人之所以為人”最為基礎(chǔ)和源始的“存在形態(tài)”是“四端之心”。歷史地看,以心立說并以體現(xiàn)道德意識(shí)的“心”為人之為人的根本規(guī)定,構(gòu)成了孟子一系儒學(xué)的基本看法,它與人是理性的動(dòng)物的觀念大致一致。世間萬物,唯有人才有道德意識(shí),這確實(shí)不錯(cuò),不過,這里的關(guān)鍵在于,作為道德意識(shí)的“心”并非如孟子所言,是先天所賦予:人固然具有形成道德意識(shí)的可能,但唯有在后天的知行過程中,這種可能才會(huì)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shí),不僅同為儒家的荀子,在其“化性起偽”等理論中已對此作了多方面的闡釋,而且孟子一系的理學(xué)也通過“變化氣質(zhì)”等理論,肯定了這一點(diǎn)。以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而言,作為道德意義上的同情心,這種“四端之心”并非人天然具有或先天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習(xí)行以及環(huán)境、教育的影響之下逐漸形成的,這種現(xiàn)象和教育(包括儒家注重的身教),便屬廣義的做事過程,由此形成的“心”,也不同于天然的趨向,而是人化或社會(huì)化的意識(shí),其中包含形成于“事”的文化負(fù)載。就此而言,“心”乃是源于“事”。當(dāng)然,從過程的角度看,“心”與“事”展開為一個(gè)互動(dòng)的過程:通過自身之“事”(習(xí)行)與社會(huì)之“事”(環(huán)境、教育以及更廣意義上的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心”,可以進(jìn)一步制約后續(xù)之“事”,后續(xù)之“事”又進(jìn)一步深化、擴(kuò)展已有之“心”,如此綿延不斷,“心”源于“事”,“事”中有“心”。如果一定要說“本源”或“基礎(chǔ)”,則如上所言,不能不追溯到人所作的“事”。
我在《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一書曾區(qū)分了“自然之人”(natural human being)與“人工之人”(artificial human being),并認(rèn)為,自然之人可以視為“事”的主體,人工之人則可以視為“事”的結(jié)果。文章對此表達(dá)了不同的看法:“當(dāng)‘人工之人’不斷從事了很多原來‘自然之人’所做之事的時(shí)候,‘人工之人’便不再只能是‘事’的結(jié)果,而完全也可以成為事的主體。就此而言,自然之人與人工之人的區(qū)別,其關(guān)鍵似乎并不能從‘事’的‘主體’和‘結(jié)果’這一角度來看。在我看來,區(qū)別二者的關(guān)鍵,恐怕在于意識(shí)尤其情感和意志的有無。而意識(shí)、情感和意志,用中國哲學(xué)的固有術(shù)語來說,恰恰就是‘心’。”這里的討論,涉及“自然之人”與“人工之人”的分梳,但其核心,仍在于以“心”為人之為人的根本規(guī)定。引申而言,“人工之人”可以視為與人工智能相關(guān)的存在,從其功能或作用看,這一意義上的“人工之人”近于機(jī)器人,歸根到底為人所用,并相應(yīng)地具有工具的性質(zhì)。與之相聯(lián)系,“人工之人”確實(shí)可以“不斷從事很多原來‘自然之人’所做之事”,但作為具有工具的性質(zhì)的存在,它在實(shí)質(zhì)上仍是“事”的結(jié)果,而不同于“事”的主體,其所涉及的,主要是一種安排之下的運(yùn)作,近于機(jī)器啟動(dòng)之后的運(yùn)轉(zhuǎn),而不同于嚴(yán)格意義上的自覺 之“事”。
在《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中,我曾提及:“從人與人的關(guān)系看,當(dāng)人僅僅在空間上彼此并存而沒有發(fā)生現(xiàn)實(shí)的交往關(guān)系之時(shí),人與人之間也就彼此無‘事’:離開了實(shí)際的交往行動(dòng),則無論是正面或積極意義上的‘事’(好事),還是負(fù)面或消極意義上的‘事’(壞事),都無從發(fā)生。”并認(rèn)為,“在疏離于‘事’(無所事事)之時(shí),人每每會(huì)有空幻或虛而不實(shí)之感,這種空虛之感既關(guān)乎對象,也涉及人自身的存在”。對此,文章以“尚友千古”為例,提出了異議:“一個(gè)通過‘尚友千古’而不斷提升和深化自己心智與精神的人,即便沒有與那些空間上與之并存的其他人發(fā)生現(xiàn)實(shí)的交往關(guān)系,過的是離群索居的生活,在實(shí)際的生活世界中所為之‘事’甚少,其內(nèi)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依然可以非常的豐富與多姿多彩。”作為寬泛意義上的隱喻,“尚友千古”可以視為某種“神交”,其具體方式是“讀書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事”包括廣義的觀念活動(dòng),“讀書思考”作為觀念之域的活動(dòng),在此意義上也屬于人所作之“事”。然而,除了觀念性的活動(dòng),“事”同時(shí)關(guān)乎人與物的交互作用與人與人的實(shí)際交往,人因事而在意義上的“事”,并不僅僅限于觀念性的活動(dòng),而是涉及多方面的知行過程,包括人與物的交互作用與人與人的實(shí)際交往,單純的“讀書思考”固然可以使人在觀念層面得到提升,但由此而“離群索居”,遠(yuǎn)離人與物的交互作用與人與人的實(shí)際交往,則人所參與之“事”便呈現(xiàn)單向度或片面的性質(zhì),以之為源,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往往容易陷于抽象和蒼白,難以真正達(dá)到“豐富與多姿多彩”的形態(tài)。以思想的衍化而言,其中既涉及觀念之流,也關(guān)乎現(xiàn)實(shí)之源,僅限于前者,無法避免思想的貧乏。“尚友千古”以過去時(shí)代的人或其思想為神交對象,往古之人具有既成性,不同時(shí)代的后人讀其書、思其義,則往往讀出不同的意義(單純的重復(fù)將導(dǎo)致思想的窒息),這種不同,便以后人所處時(shí)代、所參與之“事”的差異為前提,離開了相關(guān)的多樣之“事”(包括形成于“事”的文化成果),則思想的延續(xù)、發(fā)展、豐富便無從說起。就個(gè)體而言,如果完全“置身事外”或“無所事事”,則“逍遙”便難免成為空洞的精神受用,無法真正獲得“內(nèi)心豐盈”的意義。事實(shí)上,從歷史上看,崇尚“逍遙”的莊子、郭象,本身并非“置身事外”或“無所事事”之 輩。
在談到“心”與“事”的關(guān)系時(shí),我曾提及:“心雖可出乎其外,但更需入乎其中”。文章由“心雖可出乎其外”,推出可以有“無事之心”。并進(jìn)而反詰:“如果可以有‘無事之心’,卻不能有‘無心之事’,那么,這是不是表明‘心’較之‘事’而言仍然更為根源和優(yōu)先呢?”問題再一次涉及邏輯形態(tài)與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在邏輯的層面,可以用分析的方式看“心”與“事”,并承認(rèn)二者的相對獨(dú)立性:“心”不能還原為“事”,反之亦然,所謂“心雖可出乎其外”,亦就此而言。然而,就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而言,“心”與“事”則無法相分:既無完全離開“事”的抽象之“心”,也不存在純?nèi)坏臒o“心”之“事”。與之相關(guān),王陽明所說的“事上磨煉”,也以肯定兩者的互動(dòng)為內(nèi)涵,其中既有“心”(德性)源于“事”之意,也肯定了“事”對“心”(德性)的確證,二者在不同意義上都體現(xiàn)了“事”對“心”(德性)的制約。即使將“事上磨煉”理解為“‘心’是否切實(shí)達(dá)到凝定狀態(tài)在經(jīng)驗(yàn)層面所必需和易見的驗(yàn)證手段”,也蘊(yùn)含著“事”對“心”(德性)的制約。也許,“對陽明和孟子而言,‘心’與‘事’之間,更具優(yōu)先性的仍然是‘心’”,但從兩者的現(xiàn)實(shí)或?qū)嶋H形態(tài)來說,則不能如此單向地看待。僅僅講“事之成其為事,仍有賴于人心之運(yùn)轉(zhuǎn)”,并未把握問題的全部內(nèi)涵,在相近的意義上,同樣需要承認(rèn):“心”的內(nèi)涵受制于“事”。“心”的差異固然會(huì)影響“事”,“事”的不同,也將賦予“心”以不同內(nèi)涵:無論是心的發(fā)生,抑或心的作用和意義的確證,都無法離開事。如前所言,總體上,“心”與“事”之間展開為一個(gè)互動(dòng)過程,這種互動(dòng)最終又源于現(xiàn)實(shí)之“事”。
要而言之,“事”具有綜合性的形態(tài),既包括“心”及其活動(dòng)(觀念性的活動(dòng)),又以“人”為主體,在人、心、事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中,事因人而有,人成于事而又以事觀 之。
從總體上看,應(yīng)奇與楊超逸的《具體的形上學(xué)有多具體——“以‘事’觀之”的視域》一文對相關(guān)論題的“同情理解”似乎超越于“批判的質(zhì)疑”,不過,其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看 法。
文章提到斯特勞森的“描述形而上學(xué)”,并認(rèn)為他“揚(yáng)棄事實(shí)本體論,而倡導(dǎo)事物本體論”。盡管這里所說的“事實(shí)本體論”首先與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原子主義相聯(lián)系,但亦涉及我的若干思考。“描述的形而上學(xué)”與我提出的“具體形上學(xué)”也許確有具有某種相關(guān)性,不過,文章認(rèn)為“具體的形上學(xué)表現(xiàn)出了與描述的形上學(xué)的某種強(qiáng)烈的親和性”,則似可作一些辨析。“描述的形上學(xué)”與所謂“修正的形上學(xué)”相對,主要限于言說中的存在,其關(guān)注之點(diǎn),在于我們在討論世界時(shí)所運(yùn)用的語言的涵義。盡管它也批評(píng)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修正的形而上即被視為這一類的形而上學(xué),但這種批評(píng)似乎具有二重意義:一方面,其中包含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中抽象形態(tài)的揚(yáng)棄,另一方面,就其限定于語言的描述或分析而言,又表現(xiàn)出隔絕于真實(shí)世界的抽象性。從總的方面看,“描述的形而上學(xué)”沒有越出“以言觀之”的進(jìn)路,這與“以事觀之”體現(xiàn)的具體形上學(xué),似乎有所不 同。
“現(xiàn)實(shí)”和“現(xiàn)實(shí)存在”,是我常用的概念,《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一書也依然可以一再看到相關(guān)概念。然而,按《具體的形上學(xué)有多具體——“以‘事’觀之”的視域》一文的看法,以上概念似乎存在某種“含混”性,這里,也許有必要對此作若干澄清。從哲學(xué)的層面考察世界,便不能不注意本然存在或本然世界與現(xiàn)實(shí)存在或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區(qū)分。兩者分野的重要之點(diǎn),在于是不是與人的知行活動(dòng)相關(guān),或者說,是否關(guān)乎人的視域。人的視域是人本身無法超越的,真正有意義的存在總是相對于人而言。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人沒有出現(xiàn)之前的洪荒之世、人目前認(rèn)識(shí)未及的河外星系不存在,但即使這些對象,其意義的呈現(xiàn),也總是離不開“以人觀之”,亦即需要從人的角度去把握。從這一意義上說,離開了人的視域,對于相關(guān)的存在除了肯定其為“有”之外,我們無法說出更多的話,以射電望遠(yuǎn)鏡觀測范圍之外可能存在的河外星系而言,如果說它“沒有”或不存在,當(dāng)然未免過于獨(dú)斷,但除了說它可能“有”之外,又難以作出更多的描述,一旦說出更多東西,則該對象便開始實(shí)際地進(jìn)入我們的知行范圍之內(nèi),成為人的知行領(lǐng)域中的現(xiàn)實(shí)存在。人類出現(xiàn)之前的洪荒之世也是如此,它固然存在于人類誕生之前,但是通過研究由森林轉(zhuǎn)化而成的煤炭以及其他生物的化石,我們?nèi)钥赏ㄟ^溯源,對其意義有所了解。一旦進(jìn)入到研究視域之中,對象就不單單是人之外的本然存在,而是進(jìn)入了人的現(xiàn)實(shí)世界。
這里可以提及晚近德國哲學(xué)界的一部哲學(xué)著作《為什么世界不存在》以及其中的相關(guān)看法。如書名所示,該書作者強(qiáng)調(diào),各種事物都存在,但世界并不存在。這里所說的是世界,是指體現(xiàn)一切聯(lián)系的、作為整體的世界:“世界是包含了一切的總域。”這一看法,近于唯名論和實(shí)證主義。作者提出了“意義場”的概念,認(rèn)為“不存在外在于意義場的對象或事實(shí)。一切存在著的東西都顯現(xiàn)在某一意義場中(準(zhǔn)確地說,是顯現(xiàn)在無限多的意義場中)。‘存在’指的是某物顯現(xiàn)在某一意義場中。無限多的東西顯現(xiàn)在某一意義場中,無論是否有人曾在某時(shí)注意到這一點(diǎn)。我們?nèi)祟愂欠耋w驗(yàn)到這回事,這在存在論層面上是次要的。事物與對象不是僅僅因?yàn)樗鼈兿蛭覀冿@現(xiàn)才顯現(xiàn)著,也不是僅僅因?yàn)樗鼈兊拇嬖诒晃覀冏⒁獾搅怂鼈儾糯嬖凇4蟛糠謻|西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顯現(xiàn)著。”這一看法有見于存在與意義的關(guān)系,然而,作者對意義本身的內(nèi)涵,卻未能確切地把握。確實(shí),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意義呈現(xiàn)于人以及人的知行過程,但無論是價(jià)值—目的之維的意義,還是理解—認(rèn)知層面的意義,本身都離不開人的以上存在過程。作者的問題之一,在于雖然注意到現(xiàn)實(shí)對象是與意義相關(guān)并表現(xiàn)為進(jìn)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但卻不了解本然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區(qū)分,在肯定現(xiàn)實(shí)存在與意義相關(guān)的同時(shí),又否定了本然世界的存在,所謂“認(rèn)為存在著一個(gè)外部世界以及我們對它的表象,這完全是錯(cuò)誤的”,便表明了這一點(diǎn)。同時(shí),對意義的現(xiàn)實(shí)之源,作者也缺乏自覺地認(rèn)識(shí)。事實(shí)上,人因事而在,意義因人而有,離開人的存在,便沒有意義。人類對任何事物的追問,都可以視為對不同意義的追問,這種意義與人相關(guān),而非存在于人之外。具體形上學(xué)的涵義之一,便是聯(lián)系人自身的存在去理解這個(gè)世界。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中的自然哲學(xué)、宇宙論,完全撇開人的存在去觀照世界、追溯構(gòu)成世界的某種基質(zhì),這種還原除了滿足人思辨興趣之外,并沒有增進(jìn)我們對這個(gè)世界的真切了解。對真實(shí)世界的理解,無法完全脫離人的存 在。
人的視域并不具有抽象性,寬泛而言,人的知行、認(rèn)識(shí)和實(shí)踐領(lǐng)域都是人的視域的具體體現(xiàn)。“事”的綜合性,在于它既涵蓋人的認(rèn)識(shí),也與實(shí)踐活動(dòng)息息相關(guān),以“事”的角度了解考察世界,從一個(gè)角度體現(xiàn)了人的視域的具體 性。
現(xiàn)實(shí)存在同時(shí)關(guān)乎對象世界以及人自身存在的規(guī)定性。存在本身并非只具有一種向度,相反,它乃是由多重規(guī)定所構(gòu)成。從更廣的意義上說,事物之間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從而形成更多的規(guī)定。只要物進(jìn)入人的知行領(lǐng)域,它就不再是一種本然之物,而是展現(xiàn)多方面關(guān)聯(lián)的現(xiàn)實(shí)存在。即使是一個(gè)簡單對象,它自身所具有的屬性,它與其他事物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它與人的活動(dòng)所形成的聯(lián)系,都共同構(gòu)成了豐富的現(xiàn)實(shí)性關(guān) 聯(lián)。
文章中的另一問題,涉及對智慧的理解:“智慧概念是否同樣具有多樣性之維,統(tǒng)一性的智慧如何獲得其分殊的形態(tài)?”這一問題無疑有其意義。與知識(shí)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切入對象不同,作為哲學(xué)形態(tài)的智慧更多地以通過跨越知識(shí)的界限而把握世界為其進(jìn)路;知識(shí)的分而論之意味著其包含多樣形態(tài),相對于此,與跨越界限相關(guān)的智慧似乎主要指向統(tǒng)一性。然而,進(jìn)一步的考察表明,對智慧不能作此簡單理解。事實(shí)上,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并非僅僅囿于單一的路向,如我以前一再指出的,哲學(xué)領(lǐng)域的智慧探索本質(zhì)上具有個(gè)性化、多樣化的特點(diǎn)。從思維趨向上看,經(jīng)驗(yàn)論、唯理論、直覺主義、懷疑論,等等,一方面表現(xiàn)為不同于知識(shí)的考察方式,另一方面又呈現(xiàn)自身的多樣進(jìn)路;從言說上看,則思辨地說、詩意地說、批判地說、分析地說,等等,構(gòu)成了不同的表達(dá)方式;從學(xué)派上說,先秦有儒家、道家、名家、墨家、法家等諸之百家,古希臘也有米利都學(xué)派、伊奧尼亞學(xué)派、愛利亞學(xué)派,以及后起的犬儒學(xué)派、伊壁鳩魯學(xué)派,等等,這些學(xué)派對世界各有自身的理解;就中外歷史上眾多的哲學(xué)家而言,其智慧之思更是千差萬別。哲學(xué)的理論無法離開哲學(xué)史的歷史,哲學(xué)的形態(tài)也是如此,正是智慧的以上多樣展開,同時(shí)使其獲得了“分殊的形態(tài)”。以上事實(shí)表明,哲學(xué)以跨越界限的方式理解世界,體現(xiàn)的主要是不同于知識(shí)對特定領(lǐng)域、對象的分別把握這一特點(diǎn),而跨越界限本身又是通過多樣的形式實(shí)現(xiàn)的,求其通與多樣性、個(gè)體性,并非相互排 斥。
與以上相關(guān)的另一問題,是“智慧境界”的表述,文章認(rèn)為,在“這一表達(dá)中,‘境界’蘊(yùn)含著特定個(gè)體的限度與相對性,與智慧的跨界傾向正相矛盾”。從語義上說,“境界”可以賦予不同的內(nèi)涵,它固然具有“界限”的意義,但也可以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運(yùn)用,事實(shí)上,在“精神境界”“藝術(shù)境界”等表述中,“境界”便主要表示精神、藝術(shù)的不同層面,而非將其限定于某一界域。當(dāng)我們說“智慧境界”后“智慧之境”(我個(gè)人可能更多地運(yùn)用后一表述)時(shí),其涵義與之相近。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視域中的“境界”既非在空間意義上限定于某一界限,也非在時(shí)間意義停留于某一境域,正如精神境界的升華沒有止境一樣,智慧之境的擴(kuò)展和提升也展開為一個(gè)綿綿相續(xù)的過 程。
順便提及,文章對以上意義中的“智慧”提出了如下問題:“意義的根源與智慧的根本品質(zhì),究竟是來自人之存在的創(chuàng)造性方面,抑或是來自對諸多既有領(lǐng)域的綜合性方面?”這里涉及“創(chuàng)造性”與“綜合性”的關(guān)系,需要對此作一闡釋。按其本義,“創(chuàng)造性”與“綜合性”并非彼此相對,事實(shí)上,創(chuàng)造性總是包含綜合性:單一的規(guī)定,難以提供創(chuàng)造之源;綜合性也體現(xiàn)于創(chuàng)造性:在綜合不同方面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綜合即參與了創(chuàng) 造。
就文章評(píng)議的對象(《人與世界:以事觀之》)而言,事實(shí)、事物和事件無疑構(gòu)成了重要的方面,在以下表述中,這一點(diǎn)得到了比較清楚的表述:“無論從語義辨析還是從形上學(xué)意涵上,“以事觀之”的形上學(xué)都關(guān)乎“事實(shí)、事物和事件的本體論”。如作者所注意到的,當(dāng)代哲學(xué)對事實(shí)、事物和事件較為關(guān)注,并作了不同方面的考察。然而,如果從“以事觀之”的視域出發(fā),則理解以上問題便無法離開“事”。在《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一書中,我曾一再指出:“事”具有綜合性,關(guān)乎不同方面,這一特點(diǎn)也體現(xiàn)于事與事實(shí)、事物和事件的關(guān)系。以“事實(shí)”而言,其形態(tài)既可以表現(xiàn)為認(rèn)識(shí)論意義上的對象,也可以呈現(xiàn)為本體論意義上的人化存在;無論是何種意義的“事實(shí)”,都形成于作為人之所作的“事”。可以一提的是,文章認(rèn)為,“事實(shí)既不存在于時(shí)間中也不存在于空間中不同”,這一看法似乎需要再思考。以人之所作為內(nèi)容的“事”作為一個(gè)過程,展開于時(shí)間之中,表現(xiàn)為“事”之結(jié)果的事實(shí),同樣無法外在于時(shí)間。相對于事實(shí),事物在寬泛意義上可以看作進(jìn)入“事”的物,較之與“事”無涉的本然之物,其特點(diǎn)在于已經(jīng)打上人的某種印記。與之相近,事件作為已經(jīng)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的形態(tài),則表現(xiàn)為“事”的展開過程。從以上方面看,事實(shí)、事物、事件與“事”顯然無法相分:在實(shí)質(zhì)的層面,“事”具有本源的意義。較之當(dāng)代主流哲學(xué)(分析哲學(xué))主要從語言之域辨析事實(shí)、事物、事件,《人與世界:以事觀之》更傾向于切入人的實(shí)際存在過程,并基于“事”的現(xiàn)實(shí)展開以考察和理解以上對 象。
除了以上三篇論文,在婺源會(huì)議中,學(xué)界的其他同仁也提出了不少有意義的問題,以下對此分別略作回 應(yīng)。
(一) 一位同仁提到,雖然作為“物”的“thing”和“to do thing”的“thing”都叫作“thing”,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確實(shí)是這樣。在英文中講“事”和“物”的區(qū)分,談到“物”的時(shí)候常常用“thing”來表示,這兩種“thing”雖然形式上一樣,但二者含義并不完全重合。作為“物”的“thing”可以視作與“事”相對的“物”或存在對象;“to do thing”的“thing”是人之所“作”的對象,并與人相關(guān)聯(lián),近于王夫之所說的“境之俟用者”,從而與尚處于人之外的“物”有所不同。作為人之所“作”的對象,這一意義上的“thing”已與“事”相 關(guān)。
(二)《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中提到:“事”具有更廣的涵蓋性,它既可以涵蓋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也可以涵蓋“行”。有的學(xué)者就對此產(chǎn)生疑惑:如果只承認(rèn)知和行的統(tǒng)一,并以“事”來涵蓋兩者,那么,兩者之間的分別又該如何理解呢?對此,也許可以這樣看:知和行、認(rèn)識(shí)與實(shí)踐的區(qū)分毋庸諱言,并為一般研究所注意,但同時(shí),不能忘記:作為人類活動(dòng)的這兩個(gè)基本方面,知與行又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如果忽視其關(guān)聯(lián)而僅僅分別地執(zhí)著于知或行,那就容易引向兩者的分離。歷史上,知行脫節(jié)、認(rèn)識(shí)與實(shí)踐的分離是一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之所以如此,緣由之一就在于僅僅注意到兩者的分別。實(shí)際上,肯定兩者的差異并不難,但要內(nèi)在地把兩者溝通起來,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作為中國哲學(xué)的一個(gè)傳統(tǒng)范疇,對溝通“知”和“行”、避免兩者的截然相分可以說提供了傳統(tǒng)的資源。所謂“事”具有涵蓋“知”和“行”的意義,并不是說泯滅兩者的分別:兩者的溝通恰恰以承認(rèn)兩者的分別為前提,沒有分別,何來溝通 呢?
與前面的問題相關(guān),一些同仁提及,如何理解人的存在本身對于世界統(tǒng)一性、整體性的現(xiàn)實(shí)規(guī)定作用?這一問題也許可以從兩個(gè)方面進(jìn)行理解:一方面,人自身的存在過程,包括人的認(rèn)知和實(shí)踐。人的實(shí)踐活動(dòng)具有確證的意義,并不斷地實(shí)際肯定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從人類總體的實(shí)踐過程來看,其演進(jìn)一再確證著人和自然之間的這種相關(guān)性。另一方面,人又可以規(guī)定自然。本然的對象有自身的諸多屬性,而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活動(dòng)使得對象獲得新的屬性或規(guī)定,如森林中的樹木本來只是樹木,但人卻可以把樹木砍下來,或者制成家具,或者用作建筑材料。家具和建筑材料并不是樹木固有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它們并非注定形成家具和建筑材料所具有的屬性;正是在人作用它的過程中,樹木獲得了這些新的規(guī)定,質(zhì)言之,這些規(guī)定乃是人的活動(dòng)所創(chuàng)造 的。
(三)《人與世界:以事觀之》與“具體形上學(xué)”之間,呈現(xiàn)何種關(guān)系?這是一些學(xué)人關(guān)注的問題。前面提到,體系化的追求容易引向思辨哲學(xué),“具體形上學(xué)”總體上不同于封閉的體系,而是具有開放性,可以向多重方面展開。“以事觀之”可以看作是“具體形上學(xué)”的進(jìn)一步延續(xù),是“具體形上學(xué)”視域下理解人與世界的一種進(jìn)路,而非在它之外另起爐灶。一些學(xué)者提到,“事”是否具有形而上學(xué)的性質(zhì)?回答是肯定的:“事”當(dāng)然具有形而上學(xué)的性質(zhì)。“事”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種廣義的存在,是與人相關(guān)、表現(xiàn)為人之所“作”的存在形態(tài),從而也處于形上之域。不過,作為人之所“作”及其結(jié)果,“事”是具體形而上學(xué)視域中的存在,而不是思辨或抽象的形而上學(xué)的考察對 象。
(四) 一些學(xué)人提到“虛事”的問題,這個(gè)概念可以做些分梳。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事”,大致可以區(qū)分為兩種,其一是以實(shí)踐方式展開的事,其二是作為觀念形態(tài)或作為觀念活動(dòng)的事。帶有宗教色彩的彼岸,以及先驗(yàn)、超驗(yàn)的存在,也許可以看作是觀念領(lǐng)域的“虛事”。當(dāng)然,彼岸或超驗(yàn)的存在,實(shí)際上是人的觀念性的設(shè)定,如費(fèi)爾巴哈說,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上帝,這一意義上的設(shè)定既屬于觀念性的活動(dòng),也具有觀念性的形態(tài)。從更本源的層面上看,這種觀念形態(tài)乃是展開于人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之中,屬于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所作的設(shè)定;各種超驗(yàn)、彼岸、先驗(yàn)的規(guī)定,歸根到底都是站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大地上所作的設(shè)定。一方面,作為觀念形態(tài),這種超驗(yàn)的預(yù)設(shè)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世界中的實(shí)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們又沒有完全離開現(xiàn)實(shí)世界:哪怕是虛構(gòu)的觀念形態(tài),也是基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預(yù)設(shè)或構(gòu) 造。
關(guān)于“物”和“事”的關(guān)系,二程在一首詩中曾提到,“萬物靜觀皆自得”,依此,則似乎從萬物自身看,其生滅、變動(dòng)與人沒什么關(guān)系,所謂“自得”亦與之相關(guān)。事實(shí)上,這里涉及更廣意義上“物”與“事”或“存在”與“事”之間的關(guān)系。寬泛意義上的“存在”和“物”可以在“事”之外:沒有進(jìn)入人的實(shí)踐過程的“物”,不能說它不存在。不過,作為種自在之物,它們具有本然的性質(zhì);前面已提及,從本然和現(xiàn)實(shí)的區(qū)分看,本然的存在還沒有進(jìn)入人的存在領(lǐng)域,帶有自在的性質(zhì),一旦為人的觀念或?qū)嵺`所作用并進(jìn)入人的實(shí)踐領(lǐng)域,就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存在。本然與現(xiàn)實(shí)的區(qū)分,與是否進(jìn)入人的知行領(lǐng)域相關(guān)。“萬物靜觀皆自得”中的“萬物”如果離開人的“觀”,就只是一種自在之物,完全與人沒有任何關(guān)系的“物”不存在“自得”與否的問題,“自得”是人賦予它的意義,是“以人觀之”的結(jié)果,所謂萬物“自得”,乃是人認(rèn)為它具有“自得”的感受。這里可以引用王陽明的相關(guān)觀點(diǎn)。王陽明曾游南鎮(zhèn),其間,他的學(xué)生指著山中的花說:花自開自落,與人心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王陽明回答,當(dāng)人沒有去看它的時(shí)候,它便黯淡無光,一旦人去觀照,它就鮮亮起來。換句話說,花的審美意義離不開人:在人的觀照之外,花自開自落,并無審美意義。“自得”在某種意義上也與之類似:“自得”是人所賦予對象的意義,人觀自然對象的時(shí)候,覺得萬物或自然景象仿佛悠然自得,但這種悠然自得并不是對象本身具有的性質(zhì),而是指相對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喧鬧而言,萬物顯得悠然自得。可以看到,這種“自得”離不開物向人的呈 現(xiàn)。
在論及以上問題時(shí),“自明性”的概念曾被引入,這一概念是現(xiàn)象學(xué)所常用的。從語義角度看,“自明性”是指直接的、沒有任何中介的意識(shí)。在現(xiàn)象學(xué)中,這種“自明性”不是一開始就出現(xiàn)的,而是經(jīng)過存在的懸置、本質(zhì)還原、先驗(yàn)還原等過程而達(dá)到的,與之相關(guān)的是純粹意識(shí)或純粹自我,經(jīng)驗(yàn)性的意識(shí)并不具有“自明性”。在現(xiàn)象學(xué)中,尤其在早期胡塞爾看來,經(jīng)過還原之后達(dá)到的這種純粹意識(shí)或純粹自我是最本原、最直接的規(guī)定,也就是具有“自明性”的存在,整個(gè)哲學(xué)大廈應(yīng)建立于其上,唯有如此,哲學(xué)才能獲得作為嚴(yán)格科學(xué)的性質(zhì)。這種自明的呈現(xiàn)超越于“心”“物”之分,具有真實(shí)可靠,無可置疑的性質(zhì)。這一意義上的“自明性”,顯然帶有濃重的思辨性,具體的形而上學(xué),包括《人與世界:以事觀之》這一著作,旨在疏離對世界的這種探討方式,以解構(gòu)思辨的迷 霧。
與以事觀之相關(guān)的另一問題,涉及“求是”和“求事”之辯:應(yīng)該“求”是非之“是”還是“求”事實(shí)之“事”?這里可以作一簡單回應(yīng)。是非之“是”在最寬泛意義上可以看作對人和世界的真理性認(rèn)識(shí),這種真理性的認(rèn)識(shí)唯有通過廣義之“事”(人的知行活動(dòng))的展開才能達(dá)到。在這一意義上,“求是”和“求事”無法分開。“求是非”的“是”即敞開于“求事實(shí)”的“事”的過程中,離開了這種“求事”的過程,便很難對世界及人自身形成真切的認(rèn)識(shí)。另外,“求是非”的“是”與“求事實(shí)”的“事”在內(nèi)涵上也有不同,屬于不同的領(lǐng)域。“求是非”的“是”側(cè)重于追求真理,偏重于理論層面的認(rèn)識(shí);“求事實(shí)”的“事”既側(cè)重于做事的過程,又與“事實(shí)”相關(guān),兩者相互分別,但又并非截然對 峙。
(五) 一些同仁提到:具體形上學(xué)以中西哲學(xué)為理論之源,其中涉及對西方哲學(xué)與中國哲學(xué)的理解,那么,我們能否脫離西方視角,進(jìn)而以一種更客觀的態(tài)度來評(píng)價(jià)中國哲學(xué)?這一問題目前討論較多,也需要反思。總體而言,我們當(dāng)然不應(yīng)用西方哲學(xué)的范式來裁剪中國哲學(xué),但卻可以將西方哲學(xué)作為理解中國哲學(xué)的重要參考。從更廣的意義上說,在此需要超越狹隘的中西哲學(xué)分野的看法。實(shí)際上,中西之分在更實(shí)質(zhì)的意義上表現(xiàn)為古今之異。如眾所周知,中國哲學(xué)經(jīng)過了一個(gè)歷史的演化過程,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xué),其特點(diǎn)在于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西方哲學(xué)已進(jìn)入到了我們的哲學(xué)視野中。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哲學(xué)不能僅僅被視為外來對象,相反應(yīng)被看作我們今天思考哲學(xué)的重要背景。今天西方哲學(xué)的資源已經(jīng)融入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之中,在考察中國哲學(xué)的時(shí)候如果略去這些內(nèi)容,則意味著倒退到過去,這樣的進(jìn)路很難展現(xiàn)哲學(xué)研究的時(shí)代 性。
以上是從狹義上看,就廣義而言,作為一種文明形態(tài),哲學(xué)是人類共同的財(cái)富,而非西方所獨(dú)有,以世界哲學(xué)為視域,則中國哲學(xué)和西方哲學(xué)都是今天思考哲學(xué)問題的重要資源。事實(shí)上,西方的文化已經(jīng)滲透到生活的不同方面中,單就語言而論,現(xiàn)代漢語已經(jīng)大量地吸收了包括西語的外來語,如果略去這些外來語,現(xiàn)代漢語恐怕就不復(fù)存在了。語言不僅僅是外在符號(hào),它更內(nèi)含了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在運(yùn)用現(xiàn)代漢語的過程中,很難擺脫西方文化的影響:試圖脫離西方哲學(xué)的影響而回到“純粹”的中國哲學(xué),恐怕只能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無論從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還是“應(yīng)然”而言,西方哲學(xué)都構(gòu)成了今天理解中國哲學(xué)的重要資源和背 景。
(六) 關(guān)于“物”與“事”的關(guān)系,一些學(xué)人提到,中國人重“事”而輕“物”。事實(shí)上,也許可以說,中國人注重的是現(xiàn)實(shí)之“物”,也就是對人有意義的“物”或進(jìn)入“事”中之“物”。就此而言,或許可以說,中國人重視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物”。在人的活動(dòng)作用過程之外的“物”,則屬自在之物,后者往往處于中國人的視野之外。另外,從“事”本身看,同時(shí)涉及它與時(shí)間性的關(guān)系問題。簡單而言,“事”當(dāng)然離不開時(shí)間,真正意義上的“事”既是在空間中展開,又是在時(shí)間綿延過程中延續(xù),在這一意義上,現(xiàn)實(shí)的事與時(shí)間、空間都無法相 分。
(七) 另一問題涉及“超名言”或“超言絕知”。在從形而上的進(jìn)路把握世界的過程中,日常所用的名言確實(shí)有其限度,僅僅依據(jù)這一層面的名言,無法真正達(dá)到對形而上對象的把握。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名言都包含以上限定。形式邏輯上的名言固然有特定的含義、界限、語境,以此理解對象,常常會(huì)受到各種限制。但是,如果引入辯證的觀念、肯定概念的流動(dòng),則可不為日常的或形式邏輯層面名言所限定。如果因?yàn)槟撤N形態(tài)的名言的限定而放棄一切名言,走向所謂“超言絕知”,那便容易走向神秘主 義。
如何超越名言?中國哲學(xué)一直肯定“說”和“在”的統(tǒng)一,強(qiáng)調(diào)言說和存在不可分。真理性的認(rèn)識(shí)、人生之道的把握,不能僅僅限定于口頭的言說之上,從荀子到王陽明都注重“口耳之學(xué)”和“身心之學(xué)”的區(qū)分,對中國哲學(xué)而言,真正的認(rèn)識(shí)需要化為“身心之學(xué)”,如果僅僅停留于“口耳之學(xué)”,“入乎耳、出乎口”,那便只是在理論的辨析、抽象的名言上打轉(zhuǎn),不能認(rèn)為是真正意義上對真理的把握。“身心之學(xué)”意味著由“說”轉(zhuǎn)向“在”。這一意義上的超越名言,具有實(shí)踐的意義,與前面所述超越形式邏輯的限定、走向?qū)Ω拍畹霓q證性,有所不同。對“超絕名言”,可以從以上兩方面予以理解,由此,一方面,避免走向神秘主義,另一方面,也超越僅僅在思辨層面的觀念上打 轉(zhuǎn)。
(八) 關(guān)于“事”與宗教性進(jìn)路的關(guān)系,有的同仁提到:從“成事在天”這一層面看,“天”似乎表現(xiàn)為更具決定性、主導(dǎo)性的力量。就“成事”與“天”的關(guān)系而言,所謂“天”,首先與人或外在于人的綜合性條件相對。做事過程總是離不開人和對象之間的互動(dòng),需要充分尊重或者兼顧外部條件,而不能僅僅憑主觀意愿或主觀能力來行動(dòng)。從這一角度看,“天”可以視為人之外的綜合性條件或必然法則,與之相關(guān),“事”的成功一方面需要人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對外部條件的關(guān)注和存在法則的遵循。與之相聯(lián)系,對于“成事在天”,不必一定引向宗教性的進(jìn)路,可以從人的現(xiàn)實(shí)踐行過程加以理解:做事的過程既涉及人自身的內(nèi)在能力,也關(guān)乎外在綜合性條件,包括對象世界的法則,只有在兩者的積極互動(dòng)過程中,才能完成人所作之“事”。
(九) 有的論者對“人因事而‘在’”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人在嬰幼兒和日暮垂年階段沒有作“事”的能力,但不能說此時(shí)不屬于“人”。這里的關(guān)鍵,在于對“事”和“人”需要作動(dòng)態(tài)的理解。作為人之所作,“事”并非凝固不變,僅僅以某種現(xiàn)成的形式存在。與人自身的存在經(jīng)過一個(gè)從早年到晚年的過程一致,人所作之事也存在相應(yīng)變化。在嬰兒階段,盡管人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沒有自覺意識(shí),但并非完全游離于“事”之外。根據(jù)兒童心理學(xué)的實(shí)證研究,兒童在還不會(huì)說話時(shí),已經(jīng)開始從事各種活動(dòng),如抓取玩具、尋找食物,等等,這些活動(dòng),可以視為最初的做事過程,其中包含著皮亞杰所說的行動(dòng)邏輯,具體表現(xiàn)為在抓取等活動(dòng)中,行動(dòng)包含先后、左右的有序結(jié)構(gòu),這種行動(dòng)邏輯爾后逐漸內(nèi)化為思維的邏輯。與之類似,老年人也許不像年輕人那樣從事創(chuàng)業(yè)、勞動(dòng)等活動(dòng),但依然會(huì)做力所能及的家務(wù)事,對腦力勞動(dòng)者而言,可能還會(huì)進(jìn)行各種形式的創(chuàng)作。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看作廣義的做事過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存在形態(tài),也通過這些不同的“事”而得到確 證。
與上述看法相關(guān),有的學(xué)人對“世間本無‘事’,‘事’源于人之‘作’”這一看法表示困惑,認(rèn)為自然界每日每時(shí)都在發(fā)生這樣那樣沒有人參與的“事”,例如地震、各種自然災(zāi)害、日食月食以及疫情,它們皆不是因“人”之“作”而發(fā)生,如何能說“‘事’源于人之‘作’”?以上問題似乎對“物”與“事”有所混淆:以“地震、各種自然災(zāi)害、日食月食”為事,實(shí)際上是將自然的變化混同于人所作的事。我曾提及物理事件與人所作之事的區(qū)別:“物理事件如果發(fā)生于人的作用之外,如因云層自身互動(dòng)而形成的降雨,可視為自然現(xiàn)象;物理事件如果發(fā)生于實(shí)驗(yàn)或人工條件之下,則非純粹的自然現(xiàn)象,而是融入于‘事’并成為與人相涉的廣義事件的構(gòu)成,如人工降雨,便屬后一類事件。”至于因病毒而起的“疫情”,則需要作更具體的分析:病毒本身是自然之物或自然現(xiàn)象,但病毒之感染人、并逐漸衍化為流行之疫,則與人所作之“事”(比如與某種動(dòng)物的接觸、實(shí)驗(yàn)室的各種操作,等等,目前的溯源問題,即涉及此)相關(guān),不能籠統(tǒng)地將其歸為“物”。
(十) 一些學(xué)人對“安逸”與“做事”的關(guān)系作了考察并認(rèn)為:如果“安逸”處于事之外,則我所說的“凡人之所‘作’,均可視為‘事’”的看法便難以成立的。這里涉及的“安逸”,需要作具體分析。如果將“安逸”視為作為人的特定活動(dòng)的“休閑”方式,無疑可歸入廣義之“事”,若“安逸”僅僅表現(xiàn)為“無所事事”,則不同于作為人之所“為”或人之所“作”的“事”。論者所說的“安逸”與“事”(勞動(dòng))相對,因而不同于人所“為”之“事”。這種情況與“休閑”相近:休閑既可作為與娛樂活動(dòng)相關(guān)的“事”,也可表現(xiàn)為“無所事事”,蘇東坡所說的“閑愁最苦”,即與后一意義上的休閑相關(guān)。所謂“凡人之所‘作’,均可視為‘事’”,其中的“作”或“為”,都與有意義的活動(dòng)相關(guān),與無所事事相應(yīng)的“安逸”,則不屬于這類活動(dòng)。這里需要留意,語言的運(yùn)用并非凝固僵化,同一語詞或表述(如這里涉及的“安逸”),可以在不同意義上使用,其具體涵義的把握,則需要聯(lián)系相關(guān)語 境。
同一論者對“物不會(huì)自發(fā)地滿足人,唯有通過人作用于物的做事過程,物才能成為合乎人需要的對象”的論點(diǎn)提出疑問,其根據(jù)主要是:日光,空氣不斷地在“自發(fā)”滿足人的日用需要,根本不存在“通過人作用于物的做事過程”。此處提到的日光,空氣與人的關(guān)系,需要作具體分析。一方面,這些對象確為人所需,而且其滿足人需要的過程,似乎自然而然,無需以人之所“作”(做事)為條件;但另一方面,在“日光,空氣”滿足人的需要的過程中,人與它們的關(guān)系更多地表現(xiàn)為自然物之間的關(guān)系:作為生物,人需要空氣和陽光;換言之,此時(shí)人與對象(日光,空氣)的關(guān)系,主要表現(xiàn)為自然物之間的互動(dòng)或自然意義上的物質(zhì)能量交換:人乃是作為自然物(亦即自然中的一員),而不是自然的他者的形式,與自然相互關(guān)聯(lián)。然而,作為社會(huì)存在,人具有不同于自然的品格,其需要的滿足過程也有別于自然意義上物質(zhì)交換,從實(shí)質(zhì)的層面看,這一過程始終離不開自身所“作”或所“為”。事實(shí)上,在人的存在過程中,空氣、陽光等自然對象之滿足人的需要不僅涉及新陳代謝意義上的自然之維,而且也與人的多樣活動(dòng)相關(guān);度假時(shí)在山林和海灘呼吸新鮮空氣、享受日光之浴,與勞動(dòng)場所呼吸沉悶空氣、處于昏暗空間,便既展現(xiàn)了人做事的不同方式,也彰顯了人與世界相異的價(jià)值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