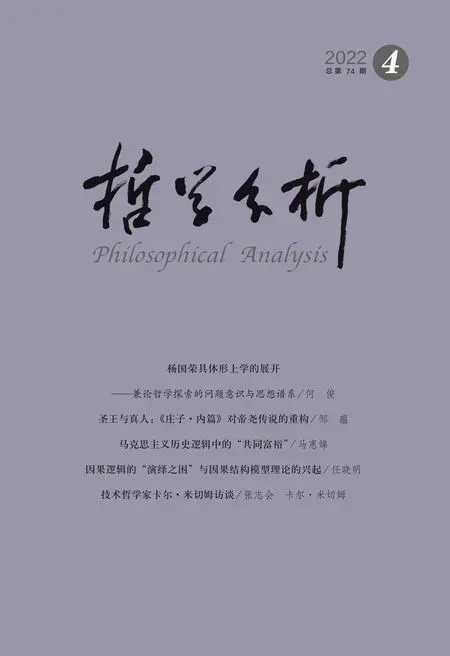生成的主體間性:雙向預測與意義建構
何 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以“計算—表征”為核心的第一代認知科學研究范式的衰落,以“具身性”(embodiment)為核心的第二代認知科學研究范式悄然發展起來。這種新的研究范式主張:認知并非大腦基于抽象符號的計算和問題的解決過程,而從本質上說是主體在與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具身行動能力。沿著這一理論思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試圖通過主體與世界間具身的、情境的動力循環來解釋不同的認知過程,如知覺、情緒和行動 等。
第二代認知科學的研究范式孕育的新觀點和新方法也深刻地影響著社會認知的研究。社會認知關注主體對自我和他者的判斷、理解和評價。歷史上,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哲學討論主要有:類比論證、歸納論證、行為主義論證和符號語言論證等。然而,這些經典的哲學論證基于理智主義的哲學傳統和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導致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無法消弭的不可通達性。近年來,第二代認知科學研究范式的支持者們一方面積極吸納現象學和社會科學中關于“交互主體性”的考察,另一方面受益于認知科學中關于社會感知的經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成果。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生成的主體間性”理論。這種理論強調社會交互過程的具身性本質,主張主體通過特定情境中的第二人稱交互過程達成了對他者的 理 解。
就研究現狀而言,生成的主體間性理論仍然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這種精細而復雜的主體間性過程背后的認知機制是什么?大腦和身體在第二人稱式的交互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主體對他者熟練的回應能力僅僅是社會性本能嗎?主體如何依據無意義的感官輸入形成對他者有意義的理解?這樣的疑問不僅是生成的主體間性理論亟待解決的理論難題,也是“他心問題”這樣古老而常新的哲學難題的核心關 切。
本文將要表明:積極吸納認知神經科學中關于預測心智(predictive mind)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引入中國哲學中關于“事”的敏銳洞見,能夠為生成的主體間性理論所遭遇的困境提供新的理論出路。一方面,預測心智的理論模型能夠為主體間的動態交互過程提供腦與神經機制的說明;另一方面,通過將由主體間性和實踐性共同擔保的“事”的維度納入社會交互過程,一種基于“事”的主體間性理論將為我們提供一種更清晰、更具說服力的社會交互理 解。
一、生成的主體間性
客觀主義將認知視為對外部世界的映射(mirroring),認為心智是自然之鏡;主觀主義將認知視為心智對外部世界的投射(projection),認為世界是心智之鏡。前者忽略了認知主體的主動性,而后者無視世界的現實存在。不過無論是客觀主義還是主觀主義,都患有“笛卡爾式的焦慮”——對確定性和客觀性的渴 望。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生成主義(enactivism)試圖將認識論從“心智—世界”之間對立的嚴格邏輯中釋放出來,以反笛卡爾的方式重新理解認知主體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它主張:主體所認知到的世界既不是心智對外部世界進行表征的結果,也不是心智的臆造之物,而是主體通過身體的知覺—行動,與特定環境中的結構特征進行耦合而生成的。簡而言之,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不是單向的表征關系,而是認知—行動的耦合關系。在這一圖景之中,主體和世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認知系統,認知是這個系統涌現的結 果。
如胡托(Daniel Hutto)所說:“生成主義認同這樣一種觀念:心智是從有機體自治的、自組織的、自我復制的行動中涌現出來的。這些行動從本質上說是有機體與環境之間嵌入的、具身的交互,并且這些交互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發生并不斷發生改變”。這種生成的認知觀是與第一代認知科學中經典的表征主義截然不同的解釋框 架。
以接拋球運動為例。按照表征主義的解釋框架,當球從對方手中飛過來的時候,我們的大腦會對球的速度和軌跡進行計算,并根據計算結果迅速向身體發出運動指令,而后身體以最有效的方式進行移動抓住球。這種表征主義的解釋將認知看作是“后—知覺”(post-perceptual)的大腦過程——認知發生在知覺過程之后,其功能是解釋知覺和指揮身體運動。
不同于表征主義的解釋進路,生成認知反對將認知看作是一個孤立的、離線的、對表征進行處理的大腦神經活動過程,而主張認知過程在本質上是一個大腦與身體的知覺—運動、具體情境進行持續的動力耦合過程。這種大腦—身體—環境之間的動力耦合過程包含了神經生物學過程、身體運動、情緒以及來自環境的調控過程等。因此,當我們看到對方手中即將拋過來的球的時候,我們的身體行動涉及大腦中的視覺皮層、前運動皮層、抓住球的欲望、對行動后果的判斷以及手與手臂運動等等。其中任何一個參數的變化,將導致知覺產生相應的變化。假如接球的主體是一個先天高度近視的人,那么他對事物距離的感知以及采取相應行動的方式便會異于他人;假如這是一場比賽中決定勝負的賽點球,那么主體將更迫切地想要贏得這個球。類似地,一個體力透支、負重前行的登山者,會比其他人覺得路程更長、崎嶇難走。這意味著,身體結構、健康狀況以及情緒等會極大地影響認知主體對外部世界的知覺體驗和行 動。
這個“外部世界”既是物理的,也是社會的。在社會情境中,主體對他者的理解過程也不是一個對他者的心智狀態進行表征和計算的過程,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包括物理環境、社會角色、文化等)依據他者運動的動力過程、姿勢、面部表情、語音語調等,與他者進行交互進而感知他者的意圖和情緒的過 程。
這意味著,在社會情境中,主體對他者的理解過程并不是主體對某個外部對象的單向表征過程,而是一個主體與另一個、主體之間進行雙向協調的動力學過程。這使得“互動過程本身的動力學在使這種行為成為可能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核心的角色。當行動主體試圖與一個無回應的搭檔進行互動時,互動無法實現……相反,其行動的成功完成根本上取決于他們在與他人的相互聯結(coupling with)中所包含的動態屬性。給予和索取、來回往復的相互過程成就了各方的行動”。在此意義上,主體間的理解就是兩個主體之間彼此定義、相互規范而達致某種一致性的過程(如兩個伐木工人一起用鋸子砍倒了一棵大樹)。然而,這種基于彼此調節而達成的一致性,并不意味著主體雙方行動的絕對同步。相反,主體雙方往往在不同步和差異之中生成對他者行動和意圖的理 解。
想象一下雙人共舞的情形。兩名舞者需要通過持續的動作協調,以呈現出渾然一體的韻律之美。當一名舞者向前邁步并伸出手的時候,另一名舞者也作出了相應的回應:向對方邁出步伐并伸出手放到對方掌心;緊接著那名舞者向后有節奏地退了兩個小快步,另一名舞者也隨之跟著節奏向前跟進兩步……舞者雙方不間斷地調節自己的身體重心和舞姿,向對方傳遞自己的身體—力量(body-weight)和行動意圖,以維護整個舞蹈的和諧與穩定。這種主體間的動作協調具有“雙向引導(bidirected)的特征,他們建構了彼此的行動方式。因此,‘協調’意味著一名舞者的運動流能夠以流暢的方式‘流入’另一名舞者并由此成為另一名舞者運動流的一部分”。如我們所見,在雙人共舞的情形中,一個主體的行動變化,引發了另一個主體行動的變化,反之亦然,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了實時的、延展的聯合運動知覺。一個主體是自身經驗的主體同時也是他者經驗的對象;主體在影響他者的同時把他者的變化帶回自 身。
這種循環往復的交互作用正是生成的主體間性所強調的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雙向規定。自我、他者以及具體的情境構成了一個結構耦合的整體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自我與他者之間持續的交互引發了系統中上行的因果作用,同時具體情境中蘊含著的規則、文化、習俗等反過來又控制和調節著自我與他者之間下行的因果作用。社會性的理解就在這種雙向作用中生成。在構成數量更大的系統中,多個主體間的多種多樣的行為(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等)依賴一定的規則相互作用,從而構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機構、組織或群體行 為。
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同于傳統的表征主義進路,生成的主體間性重新思考了大腦與身體、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間復雜的相互滲透對主體間性理解的重要作用,突出了知覺與行動之間的深刻聯結,呈現了一幅更為豐滿的社會認知圖景。不過進一步的問題在于,大腦、身體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到底是如何被徹底地整合在一起的?在社會性情境中,無意義的感官信息又如何轉變成對他者有意義的理解呢?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本文將通過神經科學中關于預測心智模型的研究以及中國哲學中關于“事”的考察,對上述問題進行探 究。
二、主體間的雙向預測
第一代認知科學中的表征主義將認知視為大腦對表征的加工過程——始于感官輸入,終于對運動系統的指令。第二代認知科學中的生成認知將認知看作是涌現自身體、大腦和世界之間持續的交互過程。在生成認知的圖景下,主體對他者的理解過程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在具體情境中與他者進行雙向協調并達致某種理解的動力學過 程。
這種生成的主體間性思想有著兩個理論硬核:具身性和情境性。具身性強調了身體的行動影響大腦如何對他者作出回應,以及他者如何通過身體行動向對方呈現自身的情緒、欲望和意圖;情境性強調了世界中的結構如何塑造并限定大腦所接受的刺激特征。因此,生成的主體間性仍然將大腦看作是認知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器官,但大腦“從主演降為聯合主演——即在認知的產生中成為與身體和世界同等的伙伴”.這意味著生成的主體間性需要在大腦—身體—世界的框架中,訴諸一種不同以往的關于大腦工作方式的理 解。
近年來,神經認知科學領域中新興的預測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理論受到了哲學家的極大關注。預測加工理論提出,大腦就好像一個推理機,基于先驗的知識和當下的感官輸入,運用貝葉斯推理對知覺信息進行解釋。這種理論的核心不是大腦對感官證據的被動接收,而是對知覺的主動預測和積極建 構。
作為一個多層級的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較低層級的大腦神經環路首先對輸入的知覺信號進行先驗預測,而后持續地將已有的預測結果與源源不斷的感官輸入進行匹配。如果結果一致,大腦就直接根據預測結果對知覺進行解釋;一旦結果有出入,較低層級的神經環路會將誤差提示傳入較高層級的神經環路,同時較高層級的神經環路通過發出身體運動指令以“改變知覺輸入或者通過改變內部狀態以調整識別密度”的方式來修正預測誤 差。
這個修正預測誤差的過程,就好像科學家不斷地將實驗數據與理論假設進行比較的過程。當預測誤差產生的時候,大腦或者像一個負責任的科學家那樣,根據數據改變預測;或者像一個有偏見的科學家那樣,堅持預測結果并挑選那些僅符合預測的實驗數據;又或者像一個偽科學家那樣,固守自己的理論而忽視真實的實驗數據。由此,著名認知科學家巴瑞特(Lisa Barrett)強調,預測和預測誤差之間的平衡決定了知覺經驗有多少來自外部世界,又有多少來自大腦。通過“頻繁的預測,你體驗到的是一個你自己創造的,經由感官世界檢驗的世界。一旦你的預測足夠正確,這些預測不僅會創造你的感知和行動,還能解釋你的感覺所代表的意義。這是你大腦的默認模式”。
舉個例子來說,當你夜晚獨自一人在公園散步的時候,突然聽到腳邊的草叢中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這時候你的已經大腦預測到“可能有蛇”。同時,大腦會根據這一預測結果啟動你的身體運動,如逃離這條蛇。這就是說,在還沒有覺察到之前,你的身體就已經不自覺地做好了逃跑的準備——如通過急促的呼吸加劇肺部和收縮,以增加血液中的葡萄糖為細胞迅速提供能量,以及肌肉釋放更多的乳酸,從而為肌肉作好拉伸和收縮的準備等。當然,你很可能也同時意識到在城市的公園中不太可能有蛇出沒,所以這可能只是風吹動干草發出的聲音。因此,為了消除可能的預測誤差,你決定將身體靠近草叢一探究竟……因此,在還未確定是否真的有蛇之前(處理來自真實世界的視覺信號輸入之前),大腦就已經完成了啟動身體的預 測。
我們看到,在此過程中,大腦的預測過程與身體行動、外部世界緊密相連。一方面,大腦中無時無刻發生著的預測,指引著我們的行動、解釋我們的知覺;另一方面,大腦根據當下的感官證據,通過采取身體行動的方式來降低預測誤差。這種“大腦—身體—世界”之間的動力循環,被稱作“積極推理”(active inference)。通過積極推理,感官輸入作為調整預測結果的參數,行動作為改變預測對象的手段,在預測加工的框架中得到了統一,并由此賦予了知覺以具身性和交互性的特 征。
正如克拉克(Andy Clark)所說,預測加工理論的核心并非大腦的表征——“某種來自大腦內部模型的信號:并且世界隱匿在知覺的面紗之后。相反,預測加工是一種高效且低成本的策略,它的執行和成功取決于行動”。大腦并不是被動地接收來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而是主動建構關于外部世界的假設。并且在無法直接與外部世界進行接觸的情況下,大腦依賴身體行動來調整預測的誤差,令我們與世界之間的持續耦合成為可 能。
正是在此意義上,預測加工所刻畫的大腦具身的和動態交互的工作方式能夠與生成認知的理論圖景相融。大腦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離線的推理機,而是作為更大有機體(鮮活的身體)的一部分,持續地與周圍環境進行耦合并最終形成關于世界的預測。在社會情境中,主體感知的對象是一個與自身有著高度相似預測模型的他者。因此,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說,主體間的交互行動和理解過程就是兩個在個體形態上相似但又存在差異的推理系統進行雙向預測的過程——在我預測你的同時,你也在預測著我。而“評價與更新我對你行動解釋的標準與理解一般意義上的行動和知覺的標準是一致的,即預測誤差的最小化”。
具體地說,大腦基于已有的社會交往經驗以及觀察到的行為或聽到的言語等感官證據,對他者的心智內容和行動進行預測:“這里的感官證據可以是我聽到的言語,從這些言語中我推斷出你試圖傳達的觀點。我不僅能夠通過預測你可能還會說什么別的來檢驗我的推斷,而且還可以通過自己說些什么,然后預測你會如何回應。同時,你將會把相同的策略用于我所說的。當我們之間的預測誤差變得足夠小時,大概就達成了對彼此的理解。”換言之,當主體間的預測模型通過相互調節和引導而達到某種一致性的時候,理解就是必然產生的結 果。
作為一種凸顯神經生物動力的理論模型,預測的心智模型從神經機制的層面將主體間性描述為兩個預測系統持續進行雙向預測的過程,為生成的主體間性提供了一種非還原的自然化說明,揭開了主體間交互過程的神秘面紗。我既是預測者又是被預測者,既是自身經驗的主體又是他者經驗的對象,他者既是我預測的一個部分又是調節我自身行動的一個原因。在預測加工的模型中,大腦不再是僅依據內部表征,而是作為更大的“自我—他者—世界”具身系統中的一個部分,與不斷變化著的他者的行動、姿態、情緒以及情境等變量進行持續耦合的預測系統;主體不再是一個對他者的行動和意圖進行觀察的旁觀者,而是通過積極推理和具身行動與他者進行動力學回應的參與 者。
三、基于“事”的共同意義建構
在腦與神經機制的層面,預測加工模型將復雜的社會交互看作是雙向的大腦預測過程,為我們理解主體間性提供了新的科學證據與理論啟示。然而,在預測加工的模型中,無論他者的行動和情緒多么富有意義,它們的給予方式和價值僅體現在與大腦預測結果的相容或背離。在此意義上,主體間的交互行動就是大腦為最小化關于他人預測誤差而衍生出來的手段。那么,在社會情境中,無意義的感官信息是如何轉變成有意義的理解呢?換言之,主體間的交互過程如何建構對他者心智和行動的理 解?
當我們看到他者憤怒的表情的時候,我們不僅基于大腦的預測加工機制將這種特定的情緒特征識別為“憤怒”,而且還不自覺地基于這種情緒所承載著的意義作出回應,如感到害怕、驚訝或憤怒等。盡管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說,這些情緒都是經由大腦的預測加工過程產生的,彼此之間并沒有顯著差別。但事實上,我們所創造的意義往往要比給定的信息豐富得多。他者的憤怒是因為被不公正地對待,還是由被人挑唆導致的?他者會因此作出過激的行為嗎?在實際情境中,我們往往會基于特定的情境和文化,賦予“憤怒”這一神經生物學的預測結果以不同的意義和功能。神經生物學模型不關注也無法解釋“意義的生成”這樣的認識論問題,而中國哲學中關于“事”的洞見則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 源。
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事”泛指主體所采取的多樣行動。這里的“事”既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不僅涉及主體與物質對象之間的互動,也涉及主體間的交往。一方面,主體對世界的認識基于所行之事。韓非子說:“事者,為也。”這里所說的“為”即主體在現實世界中所采取的行動。因此,“事”的展開就是主體作用于世界的過 程。
《爾雅》以“勞”和“績”來定義“事”,以表明“事”還包含著主體基于行動而獲得的變革世界的成果以及關于世界的理解。奧斯汀說的“以言行事”也表明“言語”和“認識”也表現為主體的所行之事。這意味著,在主體做事的過程中,外部世界中的對象才逐漸展開并由此參與主體生活世界的形 成。
另一方面,事既包括“做事”,也包括“處事”。做事首先與物打交道,處事則更多地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做事的過程中,“既需要交往雙方相互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也有賴于彼此間的默契。交流和溝通主要借助于語言層面的對話和討論,默契固然也關乎領會……默契以‘事’的參與者之間的彼此了解和互動為條件,并相應地離不開一定共同體中的社會關系”。正如加洛迪(Mattia Gallotti)和弗里斯(Chris Frith)所說,對主體間性的理解離不開對主體為何(why)、如何(how)以及何時(when)進行交互的探究,“在主體參與到特定的交互情境中去之前,那種非還原的主體間模式還只僅僅是一個潛在的模式”。這就是說,主體總是在多樣之事的磨練中,認識自己、理解他人,并通過與他人的行動的耦合而達成與他人的合 作。
由此,從神經認知科學的視角看,主體間的理解與合作以主體大腦的預測加工機制為生物學基礎;然而從更廣闊的實踐層面看,主體間性的達成始終蘊含在主體“做事”和“處事”兩個維度中。這種基于“事”的主體間性理解將我們的視域從較低層級(lower-level)的神經機制層面,帶入更寬廣的、更高層級(higher-level)的人類合作層 面。
首先,“事”表現為一種關系性(relational)存在觀。中國哲學視域中的“事”具有本源性意義——它是建構主體與世界以及主體與他者關系的主要方式。海德格爾強調,“此在”與他者的遭遇是“經由世界”發生的。也就是說,主體對他者的理解總是直接是與“事”的工具性或社會性情境聯系在一起。正是通過日常實際的情境,“此在”才遭遇了他者。這是最初的、原始的與他者遭遇的本質。主體在與他者相遇的時候,所遭遇的不是一個其他的心靈或者是作為需要進行解釋的他者,而是與自身共同參與活動的聯合行動主 體。
因此,主體首先從“事”中來理解自身與他者的共在,并由此形成了第一人稱復數的“我們—模式”。圖梅勒(Raimo Tuomela)將“我們—模式”定義為:多個(兩個及以上)個體以共同的目標為導向,通過承擔相應的角色來實現某種聯合行動或達至某種共享的心智狀態。因此,我們—模式實際上導向了一種主體間進行合作性行動的實踐承諾:“一個群體中的成員A具有某種完成X的共有意向,當且僅當:A以完成X中他應該做的事為意向;并且A具有如下信念:如果這個群體中的其他個體也能夠完成各自需要完成的任務,那么X可以通過合作而實現;并且A知道,這個集體的所有成員都相信:通過良好的合作,X可以實現。”其中,X是合作性行動,在這種合作性行動中,主體也不再是一個純粹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與其他個體緊密相連的社會性個體。由此,布萊特曼(Michael Bratman)主張我們—模式作為“一種事件狀態,存在于參與者的態度以及這些態度間的關系之中”,而無法被還原到單個主體的心智狀 態。
其次,“事”的展開過程是一個主體不斷賦予對象以意義的過程,涉及主體和他者共同生成的融合性的意義建構。基于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的“社會事實”和弗萊克(Ludwik Fleck)的“認知共同體”概念,威爾遜(Robert Wilson)主張:多個主體共同承擔的行動以及由此建構的社會情境,構成了主體認知的社會基礎。以科學家群體進行科學研究為例,威爾遜描述了個體科學家如何在科學共同體中形成融合性思考的過程。一方面,個體科學家的研究和思考總是作為更寬泛的科學共同體的組成部分而嵌入其中;另一方面,科學共同體本身卻不擁有超越個體的思考能力或心智狀態。換言之,盡管科學家的思維成果只能處于個體科學家的頭腦中,但由于它受到了其他科學家以及整個科學共同體的不斷建構,無法被還原到純粹個體的思維過程。
因此,當主體與他者“共處一事”的時候,主體和其他主體并非彼此獨立的,而是進入一個共享的社會情境之中,一個共同參與的意義建構過程。盡管一個主體無法按照控制自身的行動和意圖那樣控制其他主體,但是會將主體間或群體的信念和欲望納入自身,并通過與其他主體的意圖、語言和行動的耦合而形成的思維和行動已經超越了自身而體現出融合性的特征。例如,當我和你一起觀看音樂劇《法蘭西之光》的時候,我不僅經驗和感受了這部著名的音樂劇,而且還知道你正在和我一同觀看。我們之間的相伴隨以及互動將直接影響我對這部音樂劇進行感受的結構和質量。換言之,你參與了我關于《法蘭西之光》的經驗,這種有他者參與的經驗迥然不同于單個主體所擁有的獨立經 驗。
再次,“事”的展開過程包含了規范性的維度。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提出了三個問題:我可以知道什么?我應該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第一個問題與認知相關,而后兩個問題則更多地與評價和規范相關。與之相應,規范性一方面與認知層面的判斷——“我可以知道什么”相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實際情境中的行動選擇和展開——“我可以做什么”相連。哈貝馬斯進一步把規范看作是“普遍化了的行為期待”,多個主體共同做好一件事的有效性基礎就是“關于有關價值的共識或者基于相互理解的一種主體間性承認”。
這意味著,行事的規范不但能夠引導主體的行動取向和思維過程,起到范導性的作用,而且能夠幫助主體建立一種理解圖式,以更好地預測參與者的行為,降低自身和他者行動的不確定性。多樣之事中蘊含著多樣規范,這些規范規定了在當下事件情境中,主體應該具有何種信念和欲望,應該采取何種行動才是符合特定規范的。例如,兩個人初次見面,如果其中一人先伸出手,那么他就會期待另一人也會伸出手去握手問候;在美國,你在餐廳用餐后,餐桌服務員會期待你支付一定的小費等,這些都是社會規范的要求。當然這些社會規范并不能先天地獲得,對這些規范的理解和運用需要在“事”中不斷舉例、示范和習得。一個主體社會化的過程,就是不斷通過模仿和訓練,學習在多樣之事中如何做才是規范的過 程。
最后,在“事”的展開過程中,主體的感受構成了其重要的方面。感受不同于感覺。認知意義上的感覺主要是基于“感官與對象之間的互動,感受則不限于感官活動,而且更在于認知意義上的感覺具有分析性的特點……比較而言,感受則更多呈現綜合性的特點,情感、意欲、意愿、想象、感知、理性諸方面在感受中的相互關聯及表現為不同規定之間的互動,也體現了感受本身的綜合性”。
這種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感受盡管基于來自感官的信息,但本質上是主體在知覺外部對象和他者過程中所擁有的狀態。這就是說,感受具有意向性。一方面,它是主體對誘發情境作出某種特定的反應,因此感受往往與特定的情境中具體的他者相連。它向主體傳遞了那些在情境中對主體而言有意義的信息。例如,我因為莎士比亞戲劇中那些深沉而優美的語言而產生的愉悅感;我因為朋友獲得職位晉升而興奮不已等。另一方面,感受是對主體身體內部狀態的調節。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說,如果伴隨恐懼的身體變化被去除了,心跳仍然平穩、眼神仍然堅定、面色正常、說話堅定、思維清晰,那么恐懼還剩下些什么呢?因此,主體的感受并不是隱匿在頭腦中的神經元活動,而是能夠在表情和行動中得到表達和傳遞。而當主體感受自身的時候,感受的是自身身體的狀態,以及自身和他者在具體事務和情境中的位置。在事的展開過程中,正是這些豐富多彩的感受作為某種情感紐帶將主體和他者連接起來,達成某種統一或彼此的認 同。
四、結語
我們如何感知并理解他人的問題是社會認知的根本問題。隨著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興起,以“具身性”和“情境性”為理論核心的生成的主體間性理論,反對將社會交互看作是主體對外部世界的表征過程,而強調主體通過特定情境中的第二人稱主體間性過程達成了對他者的理 解。
然而,這種主體間性的認知機制是什么?以及那些感官信息如何構成主體對世界和他者的理解?這樣的問題成為了主體間性理論亟待解決的理論難題。預測加工模型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為生成的主體間性所強調的第二人稱式的動力交互過程提供了自然化的認知科學解釋。大腦就好像一個預測引擎,基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生成模型建構起對外部世界的預測。在此框架中,主體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就是一個基于大腦動態自組織的預測過程;主體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動就是以降低錯誤預測誤差和信息加工負荷為目的的認知參數。在此意義上,社會性理解同樣以預測加工模型為神經生物學基礎。主體間性過程從本質上說就是多個主體進行持續的雙向預測的過程。這樣一來,大腦、身體、他者、行動就構成一個相互嵌入的系統,它們為了達成降低預測誤差的目的而彼此協同、相互串 聯。
然而,這種神經科學的解釋無法解決另一個棘手的問題:主體如何形成對世界和他者的理解?梅洛—龐蒂曾經將主體在世界中的感知過程比喻為“鍵盤的游走”過程:一個鍵盤四處游走,盡管錘子的動作是單調而無意義的,但是鍵盤主動讓自己的不同按鍵接受錘子的敲打,從而形成了不同樂章。這一比喻傳遞給我們的意思是,主體所獲的來自外部世界的“輸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體主動呈現給世界的方式決定的。換言之,主體和世界實際上是彼此決定的關 系。
然而,要更好地理解這種關系,就需要我們跳出預測加工的神經科學框架,進入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的維度。因為無論預測加工的模型如何精細,我們都難以單純地通過感知的概率性信息流來解釋主體間的意義建構過程。中國哲學中關于“事”的洞見,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意義世界的窗戶。它不僅在本體論層面彰顯了主體與他者以及世界的關系性存在,而且在認識論層面強調了主體如何在實際的境遇中與他者相連,并賦予自身和他者的行動以意義。這種以主體間性和實踐性共同擔保的“事”的展開過程,為主體間的交互提供了現實的框架和結構性樣本,將主體和他者通過相互選擇和彼此規范捆綁在一起。在多樣之事中,主體間通過強有力的交互,以積累性的方式參與了彼此對世界的理解,創造了憑借一己之力絕不可能完成的人類工程(如建造金字塔、修建長城),形成了具有規范性特征的文化習俗與社會制度 等。
可以看到,這種基于“事”的共同意義建構視角,與預測加工模型對社會交互的自然主義說明高度相符。它們都反對將大腦與身體、知覺與世界割裂開來,強調大腦、身體和世界間持續的交互作用。在社會情境中,主體不再是被動接受刺激的旁觀者,而是與他者因為具體的事務而聯結的積極的參與者。只有在具體的事務中,主體才能明確自身的問題解決域以及行動規范,并以動力學的方式積極引導和調節自身的社會性行為,生成關于世界富有情感的、有意義的理解。不過,如何進一步理解文化、習俗、規范和層級神經預測間的相互作用,將是未來社會認知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 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