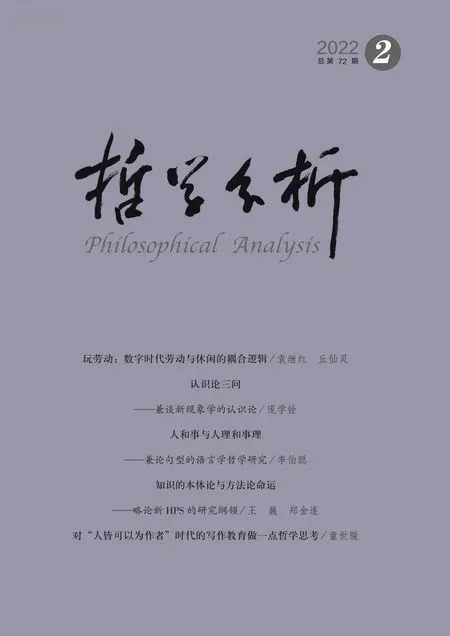人和事與人理和事理
——兼論句型的語言學哲學研究
李伯聰
本文是《哲學視野中的“物”和“器”與“物理”和“器理”》的姊妹篇。本文首先簡述21 世紀需要興起與20 世紀的“新邏輯哲學”不同的“語言學哲學”,然后運用“語言學哲學分析”方法分別對“人”“事”“人理”“事理”進行一些初步研 究。
一、 20 世紀的“新邏輯哲學”和21 世紀的“語言學哲 學”
對于歐洲哲學的發展進程,許多人認為:歐洲古代哲學重在本體論,近代哲學重在認識論,20世紀出現“語言轉向”,“語言哲學”也名重一時。可是,到了20世紀后期,有人又認為語言哲學進入了衰落階段。
對于20 世紀的“語言哲學”的內容、性質和成就,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和評論,本文無意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本文在此關注的是這個流派的“命名”問 題。
對于應該怎樣認識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分析哲學、邏輯哲學、語言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這幾個不同“名稱”的具體內容、含義和相互關系,中外學者意見紛紜,但在諸多歧異之中也有某些比較一致的意見,特別是語言轉向和語言哲學這兩個名稱,更成為了得到很大程度公認的“命名”。但本文要提出質疑:這兩個“命名”是否適當 呢?
回顧歷史,許多學者都承認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由于這里主要討論歷史開端問題,所以這里僅涉及前期維特根斯坦)三人是語言轉向和語言哲學的開山人物。雖然不可否認三人都關注了語言轉向和語言哲學研究,但如果從三人關注的首要理論關鍵和首要學術成就看,應該承認這三人關注的首要關鍵和首要主題不是“語言”和“語言哲學”而是“邏輯”和“邏輯哲學”。對于弗雷格,學術界一致把他“定性”為邏輯學家和數學家,而無人首先將其定性為語言學家。對于羅素,其在語言哲學領域聲名最顯赫的成果是摹狀詞理論,而摹狀詞理論的靈魂是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而不是運用了語言學分析方法。前期維特根斯坦的代表作是《邏輯哲學論》,這個書名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作者關注的首要重點是邏輯哲學而不是語言哲學。這就告訴我們:在20 世紀的開端期,由弗雷格、羅素和前期維特根斯坦開創的哲學新潮流的靈魂和首要關鍵是“(新)邏輯分析方法”和“(新)邏輯哲學”,而不是“語言學分析方法”和“語言哲學”。如果依據名實相符和名正言順的要求,人們應該把20 世紀初開始的哲學轉向和哲學新領域“命名”為“(新)邏輯轉向”和“(新)邏輯哲學”而不是“語言轉向”和“語言哲 學”。
由于古希臘時期以來的歐洲哲學一向重視邏輯學和邏輯方法,這就使人們不能說弗雷格、羅素發揮了“邏輯(學)轉向”的作用,但人們完全應該肯定弗雷格、羅素把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邏輯發展到“謂詞邏輯(現代邏輯)”的新階段。依據這個理由,我們可以更加名實相符地把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貢獻“命名”和“定位”為“新邏輯方法”的開端和“新邏輯哲學”的開 創。
很顯然,上述觀點在邏輯上和語義上都絕不否認在“第二重點”的意義上,應該承認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也在語言學分析方法和語言學哲學領域有前無古人的卓越貢 獻。
如果把以上兩個方面的認識和評價結合起來,就應該說:必須承認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在20 世紀之初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潮流,這個新潮流在“新邏輯分析方法”和“語言分析方法”兩個方面、在“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兩個領域都有空前重要的貢獻。但就這兩組方法和兩組領域的關系而言,無論從三位大師的主觀定位看,還是從他們的客觀學術貢獻看,我們都應該肯定,對于20 世紀之初的這個學術新潮流來說,在上述兩組方法和兩組領域的關系上,都是“前者(新邏輯方法和新邏輯哲學)為主”而“后者(語言學分析方法和語言哲學)為 輔”。
應該強調指出,以上觀點——弗雷格和羅素首重邏輯方法和新邏輯哲學——絕不是筆者的新見解,而是許多學者已經明確闡述過的“老觀點”。可是,這里卻出現了一個頗為吊詭的事情和狀況:一方面,在認識和評價這個新潮流的首要主題和基本特征時,許多學者都認識到并明確肯定這個哲學潮流的首要主題和基本特征是以“邏輯為主”而以“語言為輔”;可是,另一方面,對于這個哲學新潮流的“命名”和“名稱”,許多學者又以“顛倒主次關系”的方式將其命名為“語言轉向”和“語言哲學”,而這個顛倒主次關系的命名又難免會產生喧賓奪主的影響。在本文以下的行文中,根據敘述和分析方便,有時會把弗雷格—羅素開創的哲學新潮流“正名”為20 世紀的“新邏輯哲學”,但有時又依舊稱其為語言哲 學。
在此,還需要再談一個重要的學科史事實:就時間先后而論,弗雷格—羅素開創新邏輯哲學(通常命名的“語言哲學”)在先,而索緒爾開創現代語言學(以《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為標志)在后。這個歷史順序決定了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在開創“新邏輯哲學”(通常稱為“語言哲學”)時不可能受現代語言學的影 響。
在20 世紀20 年代及其后的幾十年中,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開創的“語言哲學”和索緒爾開創的“現代語言學”作為兩個相鄰的學科/學術領域,雖然也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但二者都作為基本獨立的學科/學術領域而不斷有新發 展。
回顧和對比現代語言學和語言哲學在20 世紀的百年發展軌跡和趨勢,人們看到:20 世紀的語言哲學如上文所言走出了一個“高開低走”的下降發展趨勢線,而現代語言學卻走了一個“后半程”急劇上升的趨勢 線。
在古代,學科尚未分化,哲學不可避免地成為學科大全,哲學家也順理成章地直接研究一切現象和一切對象。到了現代,許多自然科學學科逐漸被分化出去,現代哲學家在研究世界和研究哲學時也就“不得不”并且“樂得去”站在各門學科成就的樓頂上研究有關對象。現代哲學家不再能夠“不理睬具體學科的成就”而僅僅憑借哲學家自己的有關學科知識研究有關領域的哲學問題,這種方法論狀況使得現代學術領域出現了“科學的分支學科(物理學、生物學等)”和“與之相應的哲學分支學科(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等)”“耦合并列”的現象。在這種“耦合關系”下,哲學家研究物理哲學、生命哲學時必須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為前提和基礎,而不能“不理睬物理學、生物學知識”“單憑自己對物理現象、生物現象的理解”而研究物理哲學和生物哲 學。
可是,20 世紀卻又出現了一個明顯例外的打破耦合方法和耦合關系的哲學分支——這就是通常命名的語言哲學。雖然在20 世紀已經沒有物理哲學家認為可以脫離物理學而研究物理哲學,可是,許多“語言哲學家”卻不認為研究“語言哲學”時需要“立足語言學”。令人驚訝的是,甚至有一些語言哲學家還明確而主動地把語言學當作了“語言哲學”的局外學科。陳嘉映說:“無論在語言轉向之前還是在語言轉向之后,哲學家鮮有不關注語言現象。盡管如此,很多哲學家,包括語言哲學家,卻。這看來有點奇怪,我們會設想,不懂得數學的人很難在數學哲學上有所建樹。”“萬德勒對這個問題做了專門探討。他認為哲學家不接受語言學的主要理據是:語言學是經驗研究,而哲學處理的卻是先天問題。”
應該如何認識和評論20 世紀的語言哲學和現代語言學的相互關系 呢?
如上所述,總體而言的20 世紀語言哲學輕視和忽視了20 世紀語言學成就的內容和意義。而導致輕視和忽視的復雜原因中,最重要的主觀因素是如陳嘉映所說的在20 世紀語言哲學界存在許多語言哲學家“不認為語言學會對哲學有什么幫助”的觀點;而主要的客觀因素是在20 世紀上半葉,現代語言學還不是一門顯 學。
可是,在20 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在20 世紀末期,形勢丕變,無論從語言學中的流派紛呈和語言學分支學科的蔚為大觀看,還是從語言學應用范圍的波瀾壯闊看,語言學都成為了一門顯學,有些人更認為語言學成為了20 世紀末期社會科學領域的“帶頭學科”。
上文談到,20 世紀命名的語言哲學的首要內容和特征是著重研究“新邏輯哲學”而不是著重研究“語言學哲學”,這種狀況導致了一個嚴重后果:在20 世紀的哲學王國中“語言學哲學”成了一個缺環。更具體地說,如果以學科開創標準進行衡量,我們還不能說“語言學哲學”已經開創。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看到,20 世紀后期以來——特別是進入21 世紀之后——語言學領域(包括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語言類型學、語言獲得理論等方面)進展迅猛、成就非凡,這就導致出現了兩方面的新需求。一方面,對于現代語言學的學術新成就,急需從哲學角度進行新分析、新概括以使其有新升華。另一方面,對于現代語言學遇到的許多學術新問題(例如認知語言學、語言類型學、計算語言學都遇到一些涉及哲學思維的根本性難題),也急需哲學能夠提供新視野和新思路以促進和啟發語言學出現新突破和新開拓。這兩方面的需求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對“開創語言學哲學”的強有力的新呼喚。在這種新需求和新呼喚下,人們可以期望繼20 世紀的新邏輯轉向和開創新邏輯哲學之后,在21 世紀能夠開創和形成一門新的分支學科——語言學哲 學。
語言學哲學的開創和形成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本文希望能夠在這個新領域和新方向上有一些跬步前進的嘗 試。
二、 從專名、 通名和人稱詞進路研究關于人的哲學問題
無論從哲學理論體系看還是從哲學史看,“人”都是哲學研究的首要關鍵范 疇。
從語言學角度看,所謂人,在詞語上首先表現為每個人的專名,同時又表現為人類的通名。陳嘉映指出,專名問題是“語言哲學的核心”。對于專名問題,弗雷格有開創性研究,羅素的摹狀詞理論名噪一時;20 世紀70 年代,克里普克提出了歷史因果理論;80 年代,塞爾提出了關于專名的意向性理論。進入21 世紀后,2007年,我國學者蕢益民提出了“社會實用理論”,其后,駱傳偉博士提出了關于專名認知的社會建構論語言認知觀點。對于這些不同觀點,本文無意多加評論,這里只想指出:專名和通名是一個涉及多種對象類型的帶普遍性的語言學哲學問題,而本文關注的只是關于“人”這個特定類型的專名和通名問 題。
如果說專名和通名都屬于名詞這個詞類,那么,在研究人的哲學問題時,又遇到了另外一個詞類——代詞(特別是人稱代詞)。在詞類劃分中,與名詞并列的代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類詞 匯。
周生亞說:“從漢語語法史的角度來看,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代替說就一直在流行,至今也仍然如此。我國早期的語法著作,常常把代詞稱為‘代名字’或‘代名詞’,這其實就是pronoun 的譯名。該詞的詞根(引者按:應為前綴)pro-,就是代替的意思。代詞之所以能夠成為獨立的詞類。就是因為它的‘代替’作用,這就是代替說理論的最主要的根據。換言之,代替說認為‘代替’就是代詞的本質特 征。”
也有許多語言學家不贊成把代詞的本質特征概括為“代替名詞”。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說:“把代詞分成代詞和指別詞兩類(一部分兼屬兩類),也許更合理些。如果仍然合為一類,也是把名稱改為指代詞較好,因為指別是這類詞不同于他類詞的主要特征。”
對于代詞在詞類體系和語言體系中的作用,有些學者持比較輕視的態度。例如,有一本專門研究詞類問題的著作就認為:“嚴格地說,代詞并不是一個獨立統一的詞類,代詞實際上是從實詞各類中把一些具有專門稱代功能的詞抽出來形成的一個特殊類別,與名、動、形這樣的詞類不在一個平面上。因此代詞沒有統一的語法功能,分別屬于體詞、謂詞和飾詞。”“在43330 詞中,代詞有105 個,占0.23%。”但有更多的學者十分重視代詞問題。例如,語言學家洪堡特就認為:“在任何語言中代詞都應該是第一位的”,因為,“最初存在的當然是說話者本人”。德國語言學家策瑪克(Czermak)也強調了代詞的重大意義:“最終任何語言表達起源于空間理解的表達,即源于廣義上的代詞性詞,這些代詞性詞的最初部分轉達了原始認識‘我與非我’的對立。”
代詞中可劃分出多個子類(人稱代詞、疑問代詞、指示代詞等),而本文僅關注人稱代詞(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由于本文僅關注人類,本文也不涉及“它”和“它們”這兩個第三人稱代 詞。
對于人稱代詞,下文又稱為人稱詞。從指稱、含義、來源和用法來看,人稱詞和作為名詞的通名、專名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根本區別。所謂密切聯系,首先是指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都要在“自己的話語”中理解和使用通名、專名和人稱代詞。尤其是,在不同的語境中,每個有專名的個人在會話中都既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或“他”,沒有例外。所謂根本性區別,首先是指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雖然要在“共同”的話語中對(人的)通名和專名有“共同”的指稱和理解,可是,對于任何兩個具體的個人來說,他們卻必然對作為人稱代詞的“我”有不同的所指。更具體地說,張三話語中的“我”與李四話語中的“我”完全不同,這也沒有例 外。
從詞匯的來源和含義看,一般地說,中國人的專名(姓名)來自家族性命名,基督教家庭中來自洗禮命名,總而言之,專名的來源是“命名”的結果。可是,。與專名來源于社會性命名不同,“我”的含義和用法是每個兒童自身(language acquisition)。應該承認,語言學和哲學中對于人稱詞和人的專名的本性、區別、功能的研究目前還僅僅處于入門階段,這里還有許多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 題。
由于在涵義和語用上,“我”有許多特殊性,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將人稱代詞“我”、指示代詞“這”(以及類似的若干詞)稱為索引詞,羅素則命名了自我中心詞。索引詞和自我中心詞牽涉的問題很多,有關論著頗多,此不贅 述。
“人”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可從微觀(個體的人)、中觀(群體的人)和宏觀(類存在的人)三個尺度研究,而其語言表達就是人稱詞、(人的)專名、(人的)通名。上文簡單論及單數人稱詞,本文第四部分將涉及復數人稱詞的一些問 題。
三、 從動詞、 副詞和句型進路研究“事”的哲學問題
2021 年,楊國榮和劉陽分別出版了《人與世界:以“事”觀之》和《事件思想史》。這兩本書聚焦于“事”(event)這個哲學范疇進行闡述和研究,值得特別注 意。
以往的哲學家大都沒有把“事”當作一個哲學范疇看待,直到最近情況才有了變化。劉陽的著作從思想史角度分別介紹了尼采、海德格爾、巴赫金、拉康、列維納斯、福柯、利奧塔、德勒茲、齊澤克、德里達、蒯因等學者有關“事件”的觀點和理論。而楊國榮的著作不但更多地追溯和闡釋了中國哲學傳統中有關“事”這個哲學范疇的認識和源流,而且闡述了作者對于“事”這個范疇的許多精辟的哲學分析和哲學見 解。
從語言學角度看,“事”在漢語中早就成為了一個常見和常用的日常詞匯。例如,《論語》中就使用了“事”字56 次(根據楊伯峻《論語譯注》的統計),是《論語》中使用頻次最高的詞匯之一。《老子》中也多次使用“事”字。可是,從哲學范疇角度看,《論語》和《老子》——乃至幾乎所有中國古代論著——都沒有把“事”當作哲學范疇看 待。
《韓非子·喻老》云:“事者,為也。”可以認為,這就是事的基礎語義或定義。在這個定義中,把事解釋為“為”,也就是“做”,也就是解釋為“(人的)行動”,相當于英文動詞do。應該特別注意,這個漢語定義中,省略了兩個不言而喻的內容要素:一是省略了作為做事的主體的“人”,二是省略了“(人的)行動的對象”。在補足被省略的兩個部分之后,可以看到“事”的語言學表達或日常語義中包括了三個結構要素:一是作為行動主體也就是作為句子主語的人;二是作為揭示行動的具體含義的動詞(操作,行事;相當于英語的do,make,operate),也就是句子中的“動詞謂語”(漢語的及物動詞,英語也可為“動詞加介詞”結構);三是人之行動(操作)的對象,也就是句子的賓語。從語言學角度看,事就是上述三個要素的有機結合,這意味著,在表達(敘述)一件事時常常使用“主語—謂語動詞—賓語”或“主語—謂語動詞—賓語—補語”句型結構的句子(以下為敘述簡便,有時僅提及“主—謂—賓”句 型)。
由于遲到20 世紀,“事”才成為了一個哲學范疇,這就要求我們思考以下三個問 題。
(一) 為何“事”遲遲未能成為一個哲學范疇
對于這個問題,關鍵點和思想理論核心在于如何認識“天然/無為/天命”和“人為/有為/人力”二者的相互關系。如果在哲學理論體系中前者“壓倒”了后者,則以“人為”為核心內容之“事”就很難被上升為哲學范疇 了。
應該如何認識“天然/無為/天命”和“人為/有為/人力”的相互關系呢?中國哲學在這里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并且頗為吊詭的現象:雖然儒家和道家在許多觀點上都成為了對立的學派,但二者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難得一見的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靈犀相通。對于這個問題,道家力主“無為”而貶低“有為”;而儒家主張“天命”觀,也對“人為”大加貶斥。《論語·顏淵》云:“商(子貢)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明確指出這是“聞之夫子”。從訓詁和語境分析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出自孔子對子貢的直接教誨當無疑問。《孟子·萬章上》云:“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孟子·梁惠王下》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從上引孔子和孟子的觀點看,儒家理論體系中的“天命觀”對“人為觀”也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體現“有為”和“人為”的“(人)事”也就難以成為中國哲學體系中的重要范疇了。在歐洲哲學史上,情況有許多不同,但“事”也遲遲未成為一個哲學范 疇。
(二)“事”的哲學涉及哪些語言學哲學問題
“事”的哲學涉及的哲學問題很多,以下僅略談兩個問 題。
1. 就詞匯研究而言,必須大力開展和拓展對動詞和副詞的哲學研究。事的核心內容和語義是行動,其詞匯表現首先關聯動詞和副詞。可是,在20 世紀的語言哲學領域,正如肯尼所說:“邏輯學家已經深入地研究了專名、摹狀詞、謂詞和關系表達式,而行動動詞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針對這個薄弱環節,戴維森在20世紀下半葉撰寫了一些研究行動和事件的論文,“與同時代的分析哲學家如彼得·費雷德里克·斯特勞森等人的看法相反,戴維森認為,事件構成了一個基本的本體論范疇”。戴維森在研究行動哲學時,獨具慧眼地從詞匯和詞類哲學分析的角度空前地關注了對動詞和副詞的哲學分析。戴維森的研究具有原創性,但這里未發之覆還有很多。可以期望,21 世紀的語言學哲學有可能通過對動詞和副詞的深入研究而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新成 果。
2. 在句型研究中,必須大力開拓對“主—動—賓”句型的哲學研究。由于哲學理論體系中一向關注對“范疇”問題的研究,這反映在20 世紀的語言分析領域,就表現為語言哲學家關注了對詞匯(特別是名詞和形容詞,甚至還包括介詞)的語言學哲學研究,可是,卻很少有人關注對句型問題的語言學哲學分 析。
“事”之語言表達和哲學研究不但涉及詞匯學中的動詞和副詞,而且深刻涉及語法中的動詞句型問 題。
中國人學英語時,老師和學生往往都感受到句型問題是英語語法的突出問題。張道真說:“要掌握語言,必須掌握語言的核心。動詞句型可說是語言的核心,是骨干。綱舉則目張。”英語動詞句型(English Verb Patterns)就是英語之 綱。
英語有五種基本句型:(1)主語+不及物動詞。(2)主語+系詞+表語。(3)主語+及物動詞+賓語。(4)主語+雙賓動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5)主語+及物動詞+賓語+賓語補 語。
在歐洲哲學傳統中,本體論是一個核心問題。從語言學哲學角度看,本體論研究不但“來源于”和“扎根于”對系詞的哲學研究,而且與“主—系—表”句型有密不可分的聯 系。
在本體論研究中,中世紀哲學家提出了“God is”這個神學兼哲學本體論命題。從句型上看,“God is”不屬于“主—系—表”句型。系詞(copula,linking verb,連系動詞)的基本含義和功能是發揮“連系”主語和表語的作用,這就意味著有系詞的句子必須包括三個成分,“連系動詞”的功能才能落實。“God is”只有兩個句子成分,屬于“主語+不及物動詞”句型,這個句子不是“主—系—表”句型,從而,從詞匯屬性和語義看,“God is”中的“is”不是作為系詞的“是”,而是一個實義動詞,其語義是“存在”。許多神學家和哲學家都明確指出“God is”的含義是“上帝存在”。有人把“God is”翻譯為“上帝是”,這無論從漢語語法還是漢語語義上看,都是不通、不順 的。
從語言學角度看,不同語言——希臘語、漢語、拉丁語、英語、俄語、德語等——中的系詞涉及的詞匯學、句法學問題既有相同相通之處,也有大相徑庭之處,這就不但造成了語言學理論和一般語言翻譯中的許多復雜問題,而且造成了哲學術語翻譯和哲學理論解釋中的許多復雜問 題。
最近一段時期,我國許多哲學家關注了對本體論問題的討論,連帶地涉及對系詞的語言學哲學討論。中國當代許多哲學家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歐洲哲學本體論的研究與詞匯學上的系詞研究和“主—系—表”句型的研究有密切關聯,形成了互為因果的關系。
可是,現實語言中,除“主—系—表”句型外,還有更多的句子使用“主—動—賓(包括雙賓語)”或“主—動—賓—補”句型。如果說前者在哲學深層牽涉“關于系詞‘是’的哲學”和本體論問題,那么后者在哲學深層就牽涉“關于動詞和操作的‘事’的哲學”和實踐哲學/工程哲學/行動哲學問題。從語義、內容和對象看,所謂“事”可以泛指一切活動(包括工程之事、經濟之事、政治之事、倫理之事、軍事之事、文化之事、宗教之事,等等),尤其是,所謂“事”不但可以指作為結果之“事”,更常指“干事”,指作為操作/工程/行動之“事”。
戴維森在研究行動哲學時,關注了句型問題,沖破了以往僅僅關注“主—系—表”句型的本體論傳統,撰寫了《行動語句的邏輯形式》《行動的副詞》等重要論文,開辟了一個新方向,但未來還有更遠的路要 走。
四、 從復數人稱詞和“人類通名—人之類存在”進路研究“人理”問題
本文第二部分指出,所謂人,包括“個人之人”“人群之人”和“人類之人”。相應地,所謂“人理”也應包括“個人之理”“人群之理”和“人類之理”。本文第二部分實際上已經涉及“個人之理”的某些問題,以下簡要討論與“人群之理”和“人類之理”有關的一些問 題。
(一) 從復數人稱詞進路研究人群(集體、團體)之理
在詞匯上,不但有單數人稱詞(我/你/他),而且有復數人稱詞(我們/你們/他們)。復數人稱詞涉及的哲學問題很多,以下僅談三個問 題。
(1)對復數人稱詞語義和所指的分析
名詞和人稱詞(人稱代詞)都有單數和復數之分,應該怎樣認識這兩種詞類的“單數和復數的相互關系”呢?
應該注意,從語義和語法看,這兩種詞類中出現的“單數和復數的相互關系”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重要區別。本文第二部分已經分析了“單數人稱詞”的語義和與之有關的某些語言學哲學問題,以下再簡述“復數人稱詞”的語義和與之有關的某些語言學哲學問 題。
從語義看,雖然單數人稱詞“我”可以被千千萬萬的不同的人類個體(例如張三,李四)用于指示唯一的“(自)我”,可是對于“每個”“獨一無二”的“我”來說,卻可能并且必然存在多個“以我為其成員”的具有不同結構、含義和社會功能的“我們”。更具體地說,“自我”是“唯一含義”和“唯一所指”的,而“‘我’的‘我們’”“‘你’的‘你們’”和“‘他/她’的‘他們’”卻是有“多元含義”和“多元所指”的。
如果說單數人稱詞已經涉及許多復雜深刻的哲學問題,那么復數人稱詞就必然要涉及許多更復雜、更深刻的哲學問題了。限于篇幅,以下僅分析有關“我們”的若干問 題。
(2)關于“我們”的“語義分析”、“團體結構功能分析”和“個體與團體關系分 析”
“我”是個體,“我們”是團體。同一個“我”,在不同的情景和語境中,可以成為“不同的作為團體的‘我們’的成員”。例如,同一個“我”可以同時是“‘我們’家”的成員,又是“‘我們’企業”的成員,又是“‘我們’業余劇團”的成員。這就意味著在不同的情景和語境中,“我們”的具體所指可以是多元的,而每個群體性的“我們”又有不同的語義和“不同的團體結構功能特 征”。
對于作為“團體”(群體)的“我們”的多元含義中之“不同的具體含義”和多元所指中之“不同的具體所指”,已經在不同的具體學科中有了許多深入的研 究。
例如,從生物學的血緣關系和倫理學看,張三和李四分別屬于不同的“家”這個范疇的“我們”,換言之,二人各有不同的“我們的家”或曰“‘家’范疇的‘我們’”。在農業社會,“家”還是“農業生產單位”。現代社會學對“家”這種“人群團體的結構和功能”的各種復雜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從學校教育角度看,張三、李四會在不同時期屬于不同的“我們的學校”或曰“學校團體類型的我們”。現代社會中,張三、李四會和其他許多人被“企業”招募,這就又有了“我們的企業”或“企業組織類型的我 們”。
以上每種團體或組織類型的“我們”都有其“不同的具體語義”和“不同的團體結構與功 能”。
(3)“我們”的實在性與不同學科對不同形式的作為“制度實在”的“我們”及其“建構與解構之理”的研究
在哲學理論中,“實在性”是極其重要的問題。一般地說,“個體的自我”的“實在性”比較容易得到承認和得到辯護,而集體的“我們”是“社會建構”的結果,那么,能否承認“作為集體的‘我們’”也有“實在性”呢?
在實在論研究中,塞爾提出的“社會實在”和“制度實在”概念是重大的理論進 展。
對于復數人稱詞“我們”的含義和所指,除“家之我們”同時具有“生物實在性”和“社會實在性”外,“學校”“企業”等其他組織類型的“我們”都是通過“社會建構”而形成的團體形態的“社會實在”和“制度實在”。應該強調指出,在認識和研究“人理”時,其最基本的內容和含義就蘊含在這個形形色色的“團體的我們”的“社會建構”和“社會解構”的過程和機制之中。在現代社會中,由于不同的“團體”具有“不同的組織類型和制度形態”,它們也就成為了不同學科——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研究的對 象。
在現代社會中,企業是最常見和最重要的“團體”類型。現代法律承認企業具有“法人”地位,可以認為“法人”這個術語就是從法學角度為企業的實在性提供法學基礎。經濟學中“分工”理論分析不但涉及了企業中不同的“自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且涉及了“我”和“我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的制度主義學派、組織社會學和組織行為學分別從制度、契約、組織、管理等角度研究了企業的本性和存在方式。工程社會學對企業的本性也有新的分析。整體來看,雖然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都對作為“團體”的企業進行了許多研究,但哲學家還應該考慮如何才能借鑒這些成果而在哲學上有新認識和新升 華。
(二) 從“通名之人—人之類存在”進路研究“人類”之“理”
在研究“人理”時,不但需要研究個體層次的關于“單數人稱詞”的人理和中觀層次的關于“復數人稱詞”的人理,而且必須研究宏觀層次的與“人類”有關的人理問題。為此,就需要從“通名之人(人類)—人之類存在”進路研究“人類”之“理”。
“人類”是一個既具有生物學含義又具有社會學含義的概念。所謂人的“類存在”,不但是重大的生物學、社會學問題,更是重大的哲學問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是類存在物”,“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在研究人理時,最關鍵之點就是必須把對“人的個體”“人的‘群體’”和“人的‘類存在’”的研究貫通起 來。
五、“篇章”“事理”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
1962 年,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正式出版。奧斯汀從“行事”的角度——而不僅僅是思維和認知的角度——研究語言的哲學問題,標志著語言哲學領域的一個重大進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奧斯汀在正確地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新問題——“如何行事”時又畫蛇添足地增加了“以言(with words)”二字,把研究的對象和問題范圍“局限”在語言(“以言”)領 域。
人們要問:雖然應該承認“行事”(例如造橋、軍事活動、抓捕罪犯等)離不開“以言”這個手段,但無人能夠否認在造橋、抓捕罪犯等“行事”活動中,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非語言性的”“工具”(鋼梁、槍支等)。顯而易見,如果僅僅有“語言”這個手段(僅僅“以言”),是不可能完成造橋、抓捕罪犯等“行事”任務 的。
必須強調指出,哲學家在研究“如何行事”這個重大的哲學問題時,不但需要研究“如何‘以言’行事”,而且必須研究“如何以‘物質工具’行事”,“如何以‘團體’和‘制度’行事”,“如何依據‘操作程序’行事”,“如何應對行事中的‘風險’”等一系列問題。而這樣進行研究的結果就是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奧斯汀有意無意設置的“以言行事”的“語言哲學”的藩籬,把研究的主題擴大為“如何行事”這個屬于“工程哲學/實踐哲學/行動哲學”性質和范圍的問 題。
在研究“如何行事”時,除了必須重視“以言”這種方式外,還必須研究其他方面的許多問題,包括“行動者(agent)的能動性(agency)問題”“行事的工具問題”“行事的制度問題”,等 等。
上文談到古代哲學家一般地說都沒有把“事”當作一個哲學范疇,但中國古代的華嚴宗哲學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在華嚴宗提出的“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理論體系中,“事”是基本概念之 一。
所謂“事”,可能是“小事”也可能是“大事”。對于有些“小事”,一個句子(甚至一個單詞)即可“敘述”;對于“大事”(甚至在“仔細”地研究某些“小事”時),往往必須用“一篇(或一章)話語”進行敘述。而“篇章”所涉及的語言學問題和語言學哲學問題,無論從語義內容的復雜性看還是從語言現象的復雜性看,都要遠超“詞匯”和“句子”涉及的問 題。
20 世紀中期之前的許多語言學家往往主要關注詞匯和句子水平的語言現象和語法規律,而很少關注“篇章”水平的問題。可是,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了“篇章語言學”,把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從“句子”“擴大”到“篇章”。應該承認,目前對于“篇章語言學”的研究還僅僅處于“開題階段”,這里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可謂數不勝數,例如,如何把“篇章”和“事件”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就是一個首當其沖的問 題。
一般地說,“事件”的敘述和分析都要運用“篇章體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經濟學和管理學中興起了關于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的研究。在研究“事”和“事理”的時候,必須高度重視情景分析的方法和理 論。
再回到華嚴宗的四法界理論。華嚴宗不但把“事”看作一個基本范疇,而且獨具慧眼地提出“理事無礙”和“事事無礙”這兩個重要觀點。在20 世紀末,我國學者提出了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統方法論,在此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提出“人理—物理—器理—事理”“四理合一”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理念和境界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只能另文論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