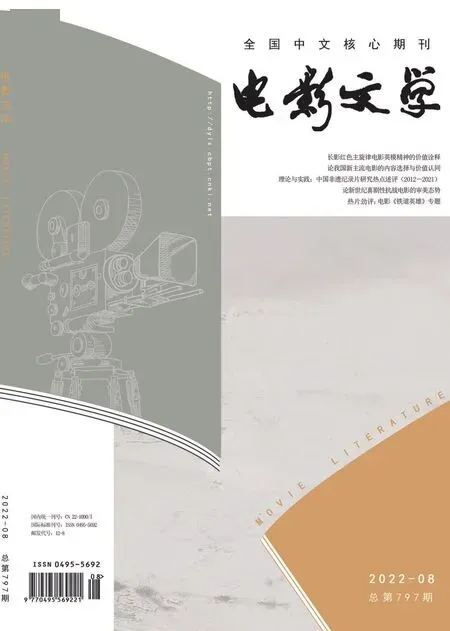從《鐵道英雄》論基于歷史事件的主旋律電影創作策略
高運榮 伊正慧
(1.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四川 雅安 625000;2.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四川 成都 610599)
從1949年開始,主旋律電影一直活躍在我國的電影銀幕之上,不論是特殊年代的“樣板戲”還是近十年的各類“獻禮片”,這些主旋律電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年代的精神側重。近些年來,我國主旋律電影的類型出現了新的變化。有以2014年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為代表的對傳統樣板戲的新編,也有將歷史進程與群像人物相結合的《1921》《革命者》;有以宏大場面、真實還原歷史真相的《金剛川》《長津湖》,也有節奏緊湊,劇情緊張,頗具現代電影工業敘事特色的《懸崖之上》《鐵道英雄》。
從這些不同側重的主旋律電影中,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主旋律電影開始根據歷史真實背景鋪展,《狙擊手》《長津湖之水門橋》《鐵道英雄》等基于歷史事實展開的主旋律故事片反映了文藝創作者對電影創作的價值取向變化,也反映出當前基于歷史事件的主旋律電影創作策略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選取《鐵道英雄》作為研究樣本,試圖從敘事策略、角色塑造、歷史價值多個維度,嘗試論析當前我國基于歷史事件的主旋律電影創作策略的更新。
一、節奏、鋪陳與鏡頭敘事:《鐵道英雄》敘事策略的更新
《鐵道英雄》取材自魯南地區鐵道游擊隊地下抵抗日本侵略者,穿鐵軌、扒火車,截取武器和物資,用膽識和智慧與敵人斗爭到底,殊死捍衛家園,為抗戰勝利做出突出貢獻的故事。電影取材自魯南地區民間抗日的一段傳奇歷史,《鐵道英雄》已經不是第一次對其進行改編了,僅僅以“鐵道游擊隊”命名的就有1956年趙明導演的《鐵道游擊隊》,1985年和2005年《鐵道游擊隊》系列電視劇。這些影視作品都取材自魯南地區民間武裝力量游擊抗日的故事。因此在分析《鐵道英雄》的敘事策略突破時,也應該與曾經出現的多個《鐵道游擊隊》版本進行對比和分析,并從這些分析比對中,探照《鐵道英雄》在敘事策略上的創新突破。
1956年版《鐵道游擊隊》講述了當地游擊隊員奇襲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從故事的表現方式來看,已經頗具后抗日英雄主義主題敘事的模板特征。身材高大、長相英俊正氣的是我方游擊隊員;而日本侵略者則被刻畫成愚蠢、遲鈍、丑陋、殘暴、惡毒的形象。在雙方的拉鋸戰中,我方游擊隊雖然在人數和武裝力量上不占據優勢,但在道德層面、智力層面、紀律層面卻遠超日本侵略者,最終通過智斗、毅力、視死如歸的精神,成功擊敗了日本侵略者。
在《鐵道游擊隊》的敘事文本中,秉持著幾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主旋律電影的敘事鐵律:我方的英雄必將打敗敵人;中國共產黨必將從相貌、人品、智力、武功等多個層面,全方位超越敵人;電影中我方力量必然緊緊擰成一股繩,對組織和國家有絕對的忠誠和信仰。這些“鐵律”也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乃至目前一些抗戰影視作品其內部一致的價值觀,即人民英雄絕對崇高、絕對偉大、絕對正確。人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形象絕對偉岸、絕對健康。不過這種“高大全”的敘事模板在大銀幕表現內容趨向復雜的當下,顯然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一些問題。首先,觀眾對故事的敘事邏輯產生了懷疑,絕對聰明的我方戰士和絕對愚蠢的敵人,消解了劇情的敘事張力,觀眾對這種絕對壓制的人民英雄史觀感到厭倦;其次,這種“高大全”的角色形象也完全脫離了歷史實際,消解了影視作品中的嚴肅部分,讓高大端正的演員扮演英雄,使得電影更多呈現出一種演繹感,觀眾無法代入劇情;最后,“高大全”敘事下,電影的藝術性存在一些缺憾,《鐵道游擊隊》是一部群像劇,統一的中景鏡頭,以時間順序展開的敘事基調,并沒有體現出敵我斗爭的驚險,也缺少在故事片敘事之外的審美意象,鏡頭內外,無一不是斗爭,無一不是英雄,這就導致電影的藝術性向電影內容的意識形態退讓,電影富有歷史價值和宣傳價值,而藝術要求退居二線。
《鐵道英雄》則反其道行之,與上述提到的《鐵道游擊隊》的“高大全”敘事有著截然相反的表現。在影片開場,電影就嘗試用下雪的氛圍、用肅殺的冬季北方環境,來暗示電影中日本人與我黨游擊隊員之間斗爭的嚴酷。陰沉、黑暗的雪天成為影片漫長的背景,游擊隊員在這種天氣之下完成暗殺、傳遞情報、截取日本軍用物資,顯得既隱蔽又困難,飄雪的天氣和肅殺的環境,構成一種敘事的雙重性。飄雪的環境氛圍和日本人虐殺游擊隊員的情節在開場相當震撼,統一的黑白紅三色基調的展開,也使得電影的主題在環境布置的一開始就得以體現。其中張涵予飾演的老洪在火車上與日本人過招的場景,電影仍然保持了與先前雪天處刑時相一致的美學風格,火車內橘黃暖光與火車外冰天雪地對比,火車內老王和日本人對峙的驚險與火車外紛亂嘈雜的搬運場的環境對比,冷暖色調的強調,凸顯出角色處境的危險與冷酷,也顯示出導演的審美取向。在電影開場,日本侵略者虐殺中國工人一節,不再將戲劇氛圍以施暴的具體過程體現,而是通過列隊的軍人、嬉笑的日本護士和整裝的狼犬多個特寫營造日據期間整體蕭索、嚴酷的社會生態氛圍。而老王與兒子相認的情節,更是其中畫龍點睛的一筆,老王與兒子的不相認是“沒到時候”,而老王和兒子最后相認時,卻是在日本人已經識破老王的秘密身份之后。因此電影的內涵維度,從民族情感、國族情仇,更細致地蔓延至個體身份與家族命運之中,人與國、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形成了雙線并行的情感敘事。這樣修改也消解了傳統抗日電影之中過度拔高英雄形象,忽略人情的一面,使得電影在肅殺的氛圍之中流露出脈脈溫情。
二、壞人、常人與英雄:主旋律人物身份與特征的變化
《鐵道游擊隊》拍攝年代獨特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氛圍給電影的角色塑造帶來了一定的要求。電影中,飾演我方英雄的大多都是長相端正、英氣,身材高大、魁梧的青年演員,而飾演日本侵略者的則被化妝成容貌丑陋、行事兇狠的壞人。觀眾在影片開場,就可以通過臉譜化的角色分辨出劇情的發展。英雄們無往不利,反派們則對英雄們的計謀后知后覺。因此,這種特殊年代的刻板角色與刻板印象流傳到現今,就有一些觀眾認為這一類扁形人物的塑造,實際上并沒有真正還原歷史中人民抗爭的真實歷程,反而從兒戲式的人物安排抹黑了抗戰時期的人民英雄。
和“鐵道游擊隊”系列電影相比,2021年上映的《鐵道英雄》對英雄主義的強調相對克制許多,與前幾部鐵道游擊隊故事一致,故事所講述的仍然是潛伏在鐵道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如何利用鐵路站這一特殊的環境,為我黨傳遞消息,奪取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物資的故事,但是敘事的重點已經出現了變化。在電影開場,觀眾能夠非常鮮明地感受到電影在風格化上做出的突破,故事發生在冬季,漫天冰雪,黑與白兩種單調色彩的重現和展示,凸顯了故事發生背景自然環境的惡劣,也間接地暗示了電影中反抗勢力與日本侵略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與爭奪。風格化還呈現在人物的服裝造型上,電影在人物穿著上依舊維持單一色調的安排設計,不論男女,鐵道游擊隊一方的角色身著黑色。服裝的樣式也相對單一單調,服道化上不斷做減法,既是為了統一故事敘事具體年代的歷史真實,也是為了將觀眾的注意力重新引回電影的故事本身。
在劇情上,《鐵道英雄》雖然還在沿用英雄主義敘事,但已經不再以塑造永不失敗的英雄,作為敘事的復調主題。張涵予所飾演的老洪雖然是個徹徹底底的民族英雄,但是在民族情結之外,又增添了更多個人形象上的復雜性。影片中段,日本人發現火車站內部的搬運工里出現了地下抵抗組織,他們買通了其中一個搬運工作為間諜,向日本人報告火車站內的動向。他既是一個漢奸,也是一個流氓無產者,在老洪與此人對峙的過程中,實際上鏡頭也包含了兩重性:一重是基于階級的共同性,即老洪與漢奸都是火車站內服務的工人,他們具有同樣的階級屬性,但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另一重則是基于國族身份與民族信念產生的一種背離性,老洪發現了漢奸的舉動。
《鐵道英雄》刻意引入了先前幾版《鐵道游擊隊》沒有引入的諜戰元素,打破了原本稍顯平庸的主旋律敘事基調,使得原本均衡的元素,一度出現了戲劇化的傾斜。諜戰元素復雜了故事敘述的路線,電影中出現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告密者,也可能是革命隊伍的背叛者。主角無時無刻不處在一種隱蔽的危險之中。在常見的歷史主義敘事中,常見的幾組形象是形成對稱結構的:人民英雄和日本侵略者;民間草莽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奸猾可笑的漢奸與英勇不屈的民族戰士;柔弱等待拯救的女子與堅強不屈的女戰士,在本電影中也有展示。電影開場濃墨重彩地表現范偉飾演的老王,頗具漢奸氣質地幾次召集工人,在值夜班的搬運工面前耀武揚威。與之平行相對的角色則是正面的英雄老洪。不過《鐵道英雄》的高明之處也在于此,電影中還暗藏著幾處身份與形象上的錯位對比,莊妍實際上就是老王的對比角色。
老王在電影前半段未揭穿身份之前,他是一個為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放棄尊嚴,討好日本人的走狗形象。從這個角色身上可以看到在當時日據環境下,普通中國人壓抑的生存狀態;小護士莊妍則是一個與老王全然相反的角色,首先她有專業的護理技術,是日本人管理的火車站的護士,她與老王賴以生存的本源是有差異的,老王依靠討好日本人生存,莊妍則利用專業技術生存。在日本人的火車站中,莊妍的世界觀發生了極大的震動:她從一個眾生平等的醫者,逐漸轉變成了地下抗日武裝力量的一分子,這個轉變本質上是一次從個人身份認同到民族身份認同的轉變。她與老王這樣以漢奸走狗身份掩護地下工作的形象是一組非常經典的身份-環境倒置的組合。從這種錯位的排列上,更豐富地展示了人性的維度,使得電影更具有歷史視角。
三、還原、創作與藝術突破:歷史原型主旋律電影的改編與創造
鐵道游擊的故事是一個已經形成敘事傳統的故事,在歷史的不同時期被反復敘說,逐漸成為中國抗日故事中的一部經典。那么對于一個這樣已經形成歷史特征的原型故事,在敘事時就需要考慮其產生的年代,民族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重社會浪潮背景下產生的特定審美區域,以及不同年代觀眾視點的落腳。從許多部歷史原型改編的主旋律電影中,都能夠看到這樣的創造,如“白毛女”故事,就著重凸顯這種階級的對立性,強調喪失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農民在時代背景下無可奈何的慘痛家庭悲劇。在1971年拍攝的電影版本,其摘取的表現向度更為復雜,這部電影既脫胎于民間的“白毛女”,又產生于一種特定年代的革命話語,有著一定特殊的審美取向,因此,在電影上則呈現了一種裝置化、布景化的象征主義傾向,在電影的敘事中,它嘗試用還原現實的方式,感召觀眾的共情,它試圖利用特殊的畫面調度、具有審美性的舞臺空間,向觀眾展示“白毛女”故事中所遭受欺壓和毀滅的對象,其自身所兼具的美好品質。1971年版本的《白毛女》中,展示的客體出現了兩個方面:其一是表意性的對舊社會“吃人”現象的展示,是對惡的揭露;其二則是來自審美客體的泯滅,當喜兒這一美好的女性形象遭受戕害時,觀眾從審美情感上感受到象征著美好的女性客體的泯滅。
與“白毛女”故事的改編相類似,《鐵道英雄》作為一部誕生于2021年的主旋律電影,在新時期的改編既要符合觀眾觀看電影的需要,也要符合歷史事實,保證電影故事的真實性與嚴肅感。這就給改編帶來了不小的挑戰,電影在還原場景上,利用了火車站這個頗具故事特點的場域進行敘說。電影中傳遞消息,利用的是鐵道交通;而搶占日軍的作戰物資,截斷日軍物資的輸送也都集中在火車上,這樣的設置為鐵道戰的敘事帶來了環境的基礎。在風格上,《鐵道英雄》大刀闊斧地做出了改良。在過去幾個版本的“鐵道游擊隊”故事中,電影的風格較為樸素、中和,缺乏極端的影像特征,地域性并不明顯。在《鐵道英雄》中,為了描繪鐵道戰激烈的斗爭環境與嚴酷的生存狀態,直接將故事發生的季節與時間拉拽到冬季最嚴酷的時刻,大雪從電影開場下到電影散場,整體帶來了一種相當嚴酷與嚴肅的氣氛。而漫天大雪的季節背景,人物清一色冬季皮帽、棉襖的裝扮也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另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林海雪原》。背景的設置在間離中喚起觀眾對經典主旋律敘事的印象與熱情,一定意義上,《鐵道英雄》的時代改編包藏了更多的同類型影視作品的記號。
《鐵道英雄》對英雄的塑造也經歷了幾重改編,首先是非僵化的原型人物改造,“鐵道游擊隊”原型故事的流傳中,由于年代久遠,真實的人物性格、人物特點比較難考察。在電影中多次進行藝術創造時,老洪除了英雄身份沒有變化之外,其他的形象符號是出現了變遷的,如《鐵道游擊隊》中形象高大健康、智勇雙全的劉洪隊長,就和《飛虎隊》(1995年,同樣以“鐵道游擊隊”故事為底本)中勇敢灑脫、不畏犧牲的洪隊長有了一定的區分;而在《鐵道英雄》中,這種形象再次更新,劉洪隊長變成了老洪,形象設計上也更偏向于真實客觀的生存環境,老洪不修邊幅,卻有智慧和魄力,面對狡猾的日本侵略者,他試圖用智慧和勇氣保護同志,為后方的抗日工作爭取更大的空間。角色的流變也意味著受眾的流變,老洪的形象也反映出不同時代觀眾的審美心理的變化。在《鐵道游擊隊》上映的年代,觀眾對英雄的訴求是超越和拯救,觀眾希望英雄在各個方面都超越常人,這是一種對更好生活、更遠未來的向往和期待;而在《飛虎隊》中,20世紀90年代市場大環境使得劇中人物塑造更具有流行特征,英雄豪杰被刻畫得樸實、粗糲,極具漫畫特點。從《飛虎隊》開始,就已經逐漸能夠看到主旋律電影在表達傾向上逐漸開始尊重觀眾、考慮市場。基于這種流變,《鐵道英雄》對畫面的風格化追求,對敘事內容嚴肅,試圖逼近真實的要求,是一次對歷史跨越時空的戲劇化重現。這種傾向可以看到在意識形態日趨復雜的當下,電影創作者嘗試借由電影這一個復雜的媒體介質,在與觀眾交流的過程中,構建一套民族身份認同。在新版《鐵道英雄》中,老洪這一角色,有常人擁有的情感,喪失了至親伙伴,會飲酒哀傷,對通敵的中國漢奸,殺伐果斷;但同樣他又是一個抽離于普通人身份建構的英雄,他對敵我形勢的洞察力,對保護同伴的責任感,使他又高于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呼應的是當下觀眾對現實存在的認同感,以及對超越現實的拯救和對英雄的真切呼喚。
從《鐵道英雄》的改編,可以看到基于歷史史實改編電影的偏移,真實歷史作為一種標尺,受眾則作為評判標準,電影的形態表現則受時代審美眼光的約束。新時代主旋律電影經歷了還原、創作與藝術突破的三重過程,突破了史實和原型故事,給主旋律的剛健敘事帶來了新的風氣,喚起了觀眾在新時代對傳奇敘事模式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