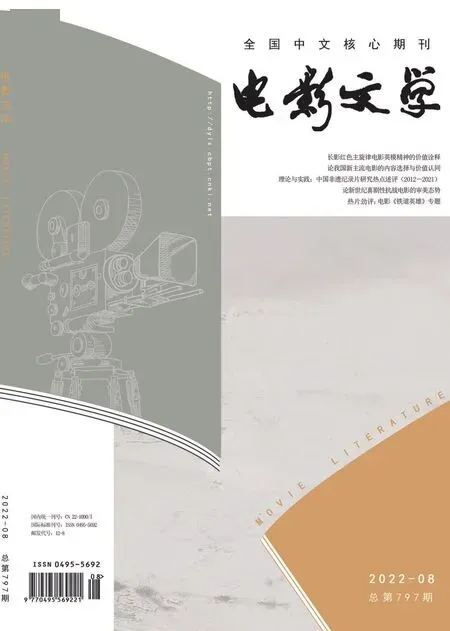《日光之下》的情感敘事機制研究
王 雪 徐 桃
(1.海南科技職業大學,海南 海口 571126;2.廣州華商學院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一、后大片時代的地域空間與多元類型片創作
中國電影市場已步入后大片時代,產業化改革推動中國電影市場持續多元化發展,雄踞票房榜首的不僅限于大制作影片,中小成本的類型片在近幾年持續爆發驚人能量,一再改寫中國影史票房紀錄。在多元化發散創作思維作用下,諸多導演將創作焦點落在地緣電影上,地緣電影自帶的視覺符號和文化景觀從根本上給予影片以藝術個性和銀幕辨識度,具有先在的受眾優勢。
在中國電影產業化發展和類型化創作逐步深化的當下,電影創作越來越朝向多元化發展,電影產量逐年增加(即便是在中國電影市場遭受疫情重創的近兩年,國內依舊保持六百余部年產量),而風格化的美學表征成為作品突出重圍的關鍵。東北電影憑借其自帶的景觀“光環”,具有強烈的視覺辨識度和銀幕吸引力,審美風格優勢的先在性使其成為諸多導演的創作熱點,如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張藝謀的《懸崖之上》、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等,都是新世紀近十年出現的東北電影中的銀幕佳作。《日光之下》是梁鳴的首部導演作品,是近年鮮少出現的東北文藝片,該片以犯罪懸疑片為“殼”,內部裹挾的是徹頭徹尾的劇情片和文藝片內核。影片集中展現了少女谷溪無果的愛情和殘酷的成長,細膩描摹了她的情感世界,谷溪身份的迷失和焦慮是推動敘事發展的動力源,也是她撕裂式成長的催化劑。
二、情感底色:東北原鄉情結與個體精神還鄉之旅
電影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通常是一次經驗主義創作,會進行一次“向內”的自我審視,即以自己的成長經歷為經驗文本創作劇本,審視自己的成長經歷和私有化的精神世界,用真實的個人經驗最大限度地與觀眾靠近,尋找共鳴,實現共情,打動觀眾,打造一部真誠的作品。而《日光之下》所呈現的并非導演梁鳴的個體經驗審視,梁鳴將故事背景定位到自己的家鄉黑龍江省伊春市,將自己的濃厚鄉愁蘊藏在極具代表性的東北地域空間當中,冬日冰凍的鄉野小路,白雪覆蓋的原野,黑黢黢的磚房,凌亂而隨意切割著天空的輸電線,等等。這些具有東北地域特色的景觀組成了記憶中的故鄉,導演借電影敘事空間(視覺空間)的塑造完成了一次個體意識下的精神還鄉,同時,這些疊加了導演梁鳴個人情緒和記憶的視覺空間也同時賦予影片以強烈的作者性。
視覺空間的建構目標是為敘事服務。導演梁鳴對故鄉視覺景觀的選擇、組合到最終呈現,是自視覺到知覺的還原和建構,視覺景觀喚起的情緒、感受和記憶被帶入故事情節的設計當中,什么樣的故事段落設計安排什么樣的視覺景觀,都受導演的個人經驗主義影響和控制。
人物形象設計同樣如此,導演梁鳴記憶中的東北人是堅強的、樂觀的,即便在東北發展遠落后于國內多數經濟發達省市的情況下,收入普遍偏低,物質生活并不豐富,東北人依舊能夠苦中作樂,在平凡的生活中尋找快樂,尋找積極生活的支撐點。谷亮兄妹只是小城鎮上最普通的居民,每天都為了溫飽、為了最基本的生活奔波,谷亮作為一家之長,四處尋找能夠賺錢的機會,每天的生活絲毫不敢懈怠。而谷溪、谷亮和慶長三人第一次見面充滿了誤會和尷尬,第二次見面的三人又相見甚歡,個性灑脫的慶長被個性靦腆的谷亮戲稱瀟灑姐,谷亮和慶長酒后的忘我舞蹈,展現了東北人樂觀和熱情的一面,無論生活再不盡如人意,一醉解千愁。
除此之外,石油泄漏導致的海洋污染的議題作為《日光之下》的敘事副線,展現了導演梁鳴對東北故鄉的人文關懷意識,石油泄漏導致的海洋污染問題不僅是一個環保議題,對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嚴重依賴自然環境生存的東北小城鎮和農村居民來說,環境污染也直接影響了生存問題,人們會因此而失業,會因為沒有收入來源而墜入底層生活的更深處,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也會發生像電影中出現的犯罪事件。即使影片《日光之下》沒能更進一步地展開這個議題,但也反映了導演梁鳴先在性的鄉愁情結對影片故事設計的導向作用,在以故鄉為敘事空間時,其記憶中關切的問題都會慢慢浮現出來,最終匯聚成影片敘事的情感底色。
三、情感結構:親情、愛情與友情交織的情感旋渦
《日光之下》是一部東北地域風格鮮明的藝術片,也是一部情感細膩的女性電影,影片既從旁觀者的視角觀察了谷溪的個人成長,也從少女谷溪的個人視角觀察了成人世界。相對于海洋污染的環保主義的敘事主旨,以及由此引發的犯罪案件,情感才是電影《日光之下》描摹的核心和主旨,也是影片敘事的主要工具。
在《日光之下》懸疑片的表層之下是多重情感交織涌動的敘事結構。只有谷溪和谷亮兄妹二人的簡單家庭單位中,親情、愛情和友情多重情感交織,兄妹、父女、朋友、愛人多重身份組合,令這個只有兩個人的家庭變得復雜又特殊,少女谷溪在看似單純的生活環境當中,經歷的卻是非同尋常的情感經歷。對于谷溪來說,谷亮如父、如兄,在沒有父親和母親角色出現的家庭成長環境中,谷亮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是照顧她生活、教育她成熟、輔助她成長的唯一的親人,谷亮撐起了谷溪的天空,在少女思春的青春期微妙情緒心理變化中,谷亮又是她潛意識里的親密愛人,是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谷亮兄妹殘缺的家庭造成了情感結構的特殊性,谷溪始終生活在一個扭曲的情感旋渦當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使她只能從哥哥谷亮身上尋找父愛和母愛的替代品,從她懂事開始,哥哥在哪兒,哪里就是家。片中家庭殘缺的女性不止谷溪一人,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家女慶長同樣家庭不幸福,她的房間只有她跟母親的合影,母親角色的缺失,父女關系的冷漠,都讓她十分羨慕谷溪能有谷亮那樣的哥哥,慶長同樣渴望親密關系。
再單純的少女終究要成長、要成熟蛻變為真正的女人。于是,影片將這場走向成熟的成長蛻變選在了這個多事的冬天,海洋被石油泄漏污染了,富家女慶長誤打誤撞地闖入了兄妹二人的生活,為了賺錢養家的谷亮參與了一場意外殺人案,谷溪的智齒也越來越頻繁地疼痛,所有事情疊加起來激蕩著少女谷溪的生活。《日光之下》架構了復雜的情感結構,谷亮、谷溪、慶長組成了三角關系,冬子作為谷亮的朋友,更像是一個入侵者,正是冬子給谷亮介紹的“工作”,才讓谷亮卷入了犯罪事件,加速了谷亮和谷溪兄妹二人的分離,也讓谷溪徹底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少女變成女人,這場成長幾乎是撕裂式的。
四、情感旨歸:自我意識覺醒、身份焦慮與分裂式成長
女性主義電影是21世紀電影的主流類型片之一,對于女性生存的人文關切深入敘事的方方面面,女性身體和心靈的成熟、兩性關系、女性職場、女性權利等諸多方面成為大銀幕主流話語,此外還有對女性精神世界、情感生活的深切關注。電影《日光之下》的敘事旨歸是多維度的,不僅有對環境保護的潛在敘述,更為突出的是將少女谷溪置于鏡頭中央,將她對哥哥谷亮畸變的“兄妹情”以及她從少女快速長大的撕裂式成長過程完整呈現。《日光之下》中少女谷溪的成長與蛻變是被動的過程,雖然她在成長焦慮中想要通過尋求信仰的方式獲得精神寄托和依靠,但最終發現哥哥谷亮已經是自己生命中的唯一信仰,她需要做出家庭關系與情感關系的兩難選擇。
(一)谷溪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谷溪從小生活在一個殘缺的家庭里,家里只有哥哥谷亮和自己兩個人,哥哥就是她的全部。谷溪從未想過要長大,她在哥哥的眼里始終是那個小姑娘,她也不需要長大,她想要的哥哥都能給予。于是,谷溪的身體發育和心智成長呈現分裂狀態。《日光之下》在敘事的推進過程中,不斷用細節交代谷溪的身體已經成熟的跡象,她早已不再是少女了。一次,谷亮想拜托李哥給谷溪上戶口,見面后對方驚訝道“還以為小女孩兒呢,都這么大了”,從旁觀者的視角塑造了谷溪的成年女性形象;也有來自谷溪身體發出的信號——來月經肚子疼,表明了她的性成熟;還有谷溪那顆越來越疼的智齒,都表明谷溪的身體早已告別青春期,發育成熟,已經長大成人。可谷溪的心智沒有和身體同步成熟,始終停留在小女孩的階段,她在谷亮面前甚至是去性別化的,兩人可以同睡一張床,現實正如二人中間的那塊將床一分為二的紗簾,它就懸在那兒,但誰都不去扯掉,不說破現實。
可以說,谷溪過去的生活并不具備促使她成長、成熟的環境因素和條件,如果不是慶長闖入了他們兄妹二人的生活,她可以一直幼稚下去、偏執下去。然而,《日光之下》并沒有將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個體成長完全歸因于男性的啟蒙,而是通過另一名更加成熟嫵媚的女性慶長激發少女谷溪女性意識的覺醒,也促使她成長,向成熟女性蛻變。谷溪在慶長身上看到了自己不具備的成熟女性特征,慶長會戴著非常女性化的耳環,舉手投足嫵媚俏皮,甚至酒后可以不顧旁人的目光當眾熱情舞蹈,她比谷溪穩重灑脫,舉手投足間透露著女人的嫵媚。當谷溪覺察到谷亮被慶長深深吸引時,慶長身上的所有細節都被放大,并與自己比對,當谷溪潛意識下開始嘗試模仿慶長,表明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
(二)谷溪家庭到社會的身份焦慮
《日光之下》對谷溪的身份背景設定為沒有戶口的“黑戶”,一方面她與谷亮缺乏基本的法律關系證明,成為“形式上”的兄妹關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谷溪在家庭身份和社會身份上的缺失,是沒有身份的個體,即她無法脫離哥哥谷亮獨立生活,變相強制了谷溪對谷亮的依附關系。因此,影片一開始就交代了谷溪的社會身份危機——工作的地方對戶口一事做出了最后表態,如果再沒有戶口就無法繼續工作,這也意味著谷溪面臨著失業危機,好不容易獲得的社會身份岌岌可危,于是谷亮四處奔走為谷溪想辦法上戶口。隨著谷溪的社會身份危機,她的身體也相應地出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隱隱作痛的牙齒潛在地隱喻著谷溪從精神到身體的焦慮和蛻變。
伴隨傳統家庭單位解體的是新家庭單位的建立,父母角色的完全缺失造成谷亮谷溪兄妹二人組建了新的家庭單位,對谷溪來說谷亮既是父親,又是兄長,也是朋友。兄妹二人經歷了漫長的共處時光以后,雖然谷溪始終是個不想長大的妹妹,但她也始終在這個只有兩個人的家庭單位中尋找著自己的位置,梳理著兩個人的關系。谷溪始終沒有正視過自己的情感,在不斷的模糊處理中,她迷失了自己的身份,慶長的出現打破了原有關系的平衡,她意識到自己正在失去谷亮,另一名女性即將剝奪自己曾經專屬的權利,甚至取代她的位置,最重要的是這一切發生在谷溪社會身份危機的當下,這也意味著她可能同時失去全部身份,某種意義上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于是,谷溪一方面與自己的老板建立聯系,尋找保留社會身份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在想辦法穩固自己的家庭身份。在原有家庭結構和情感關系被打破以后,谷溪急切地想要恢復原來的平衡。谷亮和慶長的關系日漸升溫,谷溪內心的焦慮也在不斷增加,她開始暗示慶長自己和谷亮的家庭關系的特殊和情感的和諧,“其實我倆長得也沒那么像,他說他是我哥,誰知道呢?有時候他像個爸,不過有時候我也像個媽”“慶長姐,你還回韓國嗎?”此時的慶長明白了谷溪的意思,沉默不語。
于是,谷溪的身份焦慮不斷加劇,她亟須確定自己在這個家庭中的身份、位置和權利,但她心里也很清楚她再也無法滿足于妹妹身份。同時,沒有戶口又意味著社會身份的缺失,也代表著她無法脫離家庭身份,無論從生存角度還是情感角度,谷溪都對谷亮極度依賴。谷溪渴望獲得谷亮愛人的身份,因此她假想過自己和谷亮不是親兄妹,但這層身份幻想在加速崩塌。因此,谷溪的社會身份與家庭身份的危機使她的生活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是她精神焦慮、扭曲和失常的根本原因。當她在被動中激發自我主體意識的同時,在認定自我生存價值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自我證明的過程被不斷否定,這也直接激發了矛盾和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三)“愛與成長的智齒”:從肉體到精神的分裂式成長
《日光之下》在敘事動力的積累與加速推動上是十分成功的,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谷溪在成長蛻變過程中的內心掙扎和心理變化。谷溪的身份焦慮和情感焦慮成為推動敘事發展的主要動力。當谷溪暫時保全了社會身份后,她急切地想要保住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在她的思想認知里,家就是自己和哥哥組成的,他們既是兄妹,更是愛人。
谷溪越發覺得無法阻止谷亮和慶長關系的發展,谷溪的夢境正是她壓力和焦慮增加的表現,谷溪在夢中參加了谷亮和慶長的婚禮,而所有人都看不見她,她成了透明人。睡夢中哭著醒來的谷溪扯出了作為證據的磁帶,本想與現實妥協的谷溪卻無意間撞見谷亮和慶長做愛的場景,徹底剪斷了谷溪最后繃著的神經,摧毀了她僅存的與現實妥協的念頭,也殘酷地粉碎了她的所有幻想。因為,在谷溪的潛意識里她和谷亮是兄妹也是愛人,只是在道德枷鎖下二人無法實現肉體結合,但精神早已融為一體,從她的角度來看,谷亮和慶長的性愛是對她純潔愛情的徹底背叛。
始終拒絕長大的谷溪在性的刺激下實現了分裂式成長,甚至是迫切地想要成熟起來。于是,在谷亮的生日會上,谷溪瘋狂地與身邊的男性貼身舞蹈,當眾朗讀起黃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中描述欲望和情愛的露骨段落,甚至對谷亮的朋友尋求慰藉。可以說,谷溪的情感變化完全控制了影片的敘事走向,伴隨著她情感爆發和精神崩潰,敘事也被推向了高潮。
故事最終以谷亮被捕、慶長離開、谷溪落戶結束。谷溪真正地失去了哥哥,失去了唯一的“愛人”,周圍人如潮水一樣退去,只剩下了她自己。至此,谷溪完成了精神層面的分裂式成長,而影片結尾谷溪用水果刀親手挖出了智齒,也象征著她掌控自己身體、成長和蛻變的欲望和決心,真正意義上完成了從肉體到精神的長大成人。谷溪從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家庭身份和社會身份的焦慮,到精神層面的分裂式成長,呈現出女性成長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谷溪細膩而豐沛的情感書寫了愛情命題的復雜性。
對于東北獨特的地域景觀空間,不同導演都想通過構建景觀符號,并賦予其一定的審美意義,從而借助這樣一個具有銀幕視覺辨識度的景觀進行影像表述。梁鳴在導演處女作中利用東北地域景觀空間,描摹了少女谷溪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情感成為影片敘事的全部。淺表層面以戲中人物的情感進行敘事,導演自身的情感也參與到了敘事當中,對故鄉的情感,對故鄉的眷戀,滿懷東北原鄉情結,盡情傾入影片敘事當中,匯聚成為影片的情感底色。
犯罪懸疑只是導演商業包裝與多重敘事語境中的一環,推動敘事的并非推理式破案,情節的發展完全依靠少女谷溪的心理變化來推動,最終故事走向失控也全因少女谷溪的精神世界崩塌、精神失控使然。因此,案件最終的走向更加折射出谷溪毀滅性的愛情以及割裂式的野蠻成長,她的成長蛻變深受外力作用,影片結尾谷亮被捕,留下她獨自一人,她只能與現實妥協,用刀自己挖出了智齒,用肉體的疼痛覆蓋心靈的疼痛。
很難對影片《日光之下》做一個明確的類型劃分,影片更像是國產文藝片慣用的融合類型創作與商業化設計,既有犯罪懸疑片的類型特征(犯罪劇情線),也有三角戀的愛情片特征,甚至貫穿影片始終的石油泄漏、海洋污染事件代表了影片的環保主義敘事立場,對多類型片特征的沾染使《日光之下》也表現出雜糅的藝術片特征。而影片以成熟的情感敘事體系塑造了谷溪的女性形象,架構了一場有著獨特地域韻味的情感故事,有著別樣的情感審美趣味。同時,《日光之下》作為導演梁鳴的處女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下青年導演在劇本創作上的集體問題,在商業意識滲透下,既想尋求商業利益,又想兼顧藝術理想化表達,結果往往會制造一部風格雜糅、內容混亂的作品,表現出一種商業與藝術夾縫中的集體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