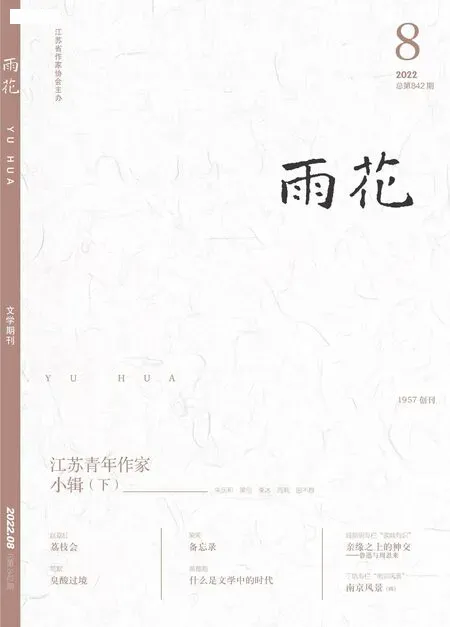北新街往事(短篇小說)
周 耗
周小舍第一次來到縣城時是在他二十二歲那年。他坐著晃晃蕩蕩的長途汽車從可蜜鎮到達縣城,用了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里,汽車停靠了六個小站,每個小站都要等上下的旅客,所以,從可蜜鎮到縣城雖然只有四五十公里路,倒也走了近兩個小時。在這段充滿了灰塵和顛簸的旅程中,坐在小舍前面的那位五十多歲的中年婦女一直在跟邊上的人喋喋不休——本來小舍想趁此機會打個盹,但那位臉上堆滿雀斑的中年婦女的嗓門確實有點大,她說到高興處還會發出可怕的大笑聲,前仰后合的,幅度確實不小。在這兩個小時里,小舍一直戰戰兢兢,他怕婦女突然轉過身來和他講話,那樣的話,小舍臉上會被噴滿唾沫,這實在是一件非常無趣的事。
車子到縣城車站的時候正好九點半,這個時間正是文化館通知的開會時間。不過從車站走到文化館至少還要十分鐘,換句話說,小舍至少要遲到十分鐘,因此他的心里稍稍有點急。小舍走出車站時,發現外面的太陽有點刺眼,雖說是初秋,但陽光白晃晃的,他在想,縣城就是縣城,連陽光好像也比可蜜鎮的強烈。因為剛下汽車,小舍的腦袋有點蒙,一下子分不清東南西北,他在車站門口站了一會兒,眼睛瞇起來往西面望去,只見馬路上人來人往,雖說文化館的許老師在信中告訴過他到文化館的路線,但第一次一個人來到縣城,他還是感到有點迷糊。突然,小舍的左臂被一個人抓住,他嚇了一跳,轉身一看,竟是剛才車上那位喋喋不休的中年婦女。
小舍有點害怕,但一想,光天化日,中年婦女不見得會干出出格的事吧?
你想干什么?小舍的聲音不響亮,但語氣很堅定,他覺得在這種時候自己不能露怯。
中年婦女仰起那張滿是雀斑的臉說,小弟弟,問一下,到蠶種場怎么走?原來婦女要問路。
小舍差點脫口而出說我也不知道,但不知為什么,他用手往南邊的馬路一指說,呶,在那里。
中年婦女馬上面露笑容說,謝謝啊!
謝什么謝!小舍在心里嘀咕一聲,他是想快點掙脫中年婦女的手,隨口說的,誰知道蠶種場在哪里呢!
看著挎著一個大竹籃的中年婦女扭著臃腫的身軀往南邊走去,小舍松了一口氣。被中年婦女一問路,小舍的腦袋頓時清醒了許多,他看到了馬路邊的路牌上寫著:北新路。對,就是北新路,許老師在信里說的,車站出來沿著北新路往西走大概十分鐘就可以看到一座灰色的建筑,門口有文化館的牌子。
小舍看了看手表,心里想,這次開會真的遲到了。
小舍步履匆匆地趕到了文化館,他看到那塊白色的牌子上寫著他要找的幾個字,是黑色的宋體字。灰色的建筑有點陳舊,門口的傳達室很小,一個干瘦的老頭坐在一把有幾個破洞的老藤椅上,眼中露出警惕的神色,而他那副黑框眼鏡的左腳是用白色膠布綁了一下的,倒有了小品里的意味。
小舍問老頭,師傅,我是來參加會議的,會議室在哪里?
老頭朝小舍上下打量一番說,你來參加會議?誰通知你的?
是許老師,許清河老師通知我來的。
老頭“哦”了一聲,用手指著里面右邊的一間房子說,從那里上樓,在二樓的第一間會議室。
小舍推開會議室的門,看到里面坐了一屋子的人,眼睛一掃,心里計算了一下,估計有三十來個人吧。他看到主席臺上有人在發言,應該是領導。門口的一位穿著鵝黃色連衣裙的女孩招呼他在一個空位子上坐下,問他叫什么名字。
周小舍,我叫周小舍。小舍輕輕地說。
女孩笑了一聲,遞給他一張簽到表,小舍在簽到表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他有點緊張,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會議室挺陳舊的,兩把吊扇在微微地轉圈。他輕聲問邊上的女孩,哪位是許清河老師?
女孩說,正在講話的就是許清河老師,中間那位胖胖的中年人是我們館長。
小舍仔細打量著許清河老師,許老師正說到興頭上,唾沫四濺。這是一位五十來歲的瘦瘦的中年人,白襯衫、黑框眼鏡,看樣子眼鏡的度數不低。這是小舍第一次見到許老師,在這之前,他們通過幾次信。
說起來,今天能夠來參加文化館的會議,全蒙許老師看得起。大概在兩年前,剛剛高中畢業的小舍偶然在可蜜鎮文化站看到一份縣文化館主辦的叫《長橋》的文學報紙,小舍在高中時曾經參加過好幾次作文競賽,也得過幾次獎,就此埋下了文學的種子,成了一名文學青年。后來可蜜鎮成立了“慈云”文學社,小舍是第一批會員,他給《長橋》報投了幾次稿,報紙的責任編輯正是許清河老師。小舍的第一首詩就發表在《長橋》報上,那是一首贊美祖國的詩歌,很幼稚,詩歌被安排在頭版上,可見許清河老師對小舍的偏愛。事實上,在這之前他們并不熟識,小舍只是一位最普通不過的文學青年。
這次文化館召開全市作者座談會,許清河老師通知小舍來參加會議,這是小舍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算是他業余文學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會議開得很熱烈,許清河老師的講話或者說是輔導,持續了將近一個半小時,接下來的作者代表交流發言很精彩,小舍顯然是一位虔誠的傾聽者,那些作者的發言對他啟發很大,有些話說到了他的心坎里。
最后是館長講話。館長畢竟是領導,講話高屋建瓴,他說,我市的文學事業迎來了黃金時期,撤縣設市給大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養分,希望大家抓住這一機會,潛心創作,寫出優秀的作品。館長顯然很興奮,他的講話有點長,后來基本上都是一些空話、套話、大話,但在小舍聽來,卻是那么令人振奮。
午餐是在一家叫“音樂餐廳”的飯店里吃的,就在文化館的對面,同在北新路上。午餐比較豐盛,還上了啤酒,許清河老師來敬酒,敬到小舍面前時,許老師說,周小舍,你的詩歌很好,以后要多寫,要多給我們投稿呀!
小舍點點頭說,希望許老師以后多多指點。
許老師說,這是肯定的,你以后也要多參加我們的活動,你們可蜜鎮的幾位文學青年中,我看你最有前途,不要放棄,好好寫下去,肯定能成功。
成功?這個小舍倒是沒有認真考慮過。
小舍端著酒杯的手微微發抖,因為激動,臉也漲得通紅,也可能是喝了啤酒的緣故吧?
剛才會議室里穿鵝黃連衣裙的女孩就坐在小舍邊上,除了許老師,其他人小舍一個也不認識,不過連衣裙女孩也算是認識的了。于是小舍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也是來參加文學座談會的代表嗎?
女孩微微一笑,說,我叫錢一蕾,是文化館的打字員,你發表在《長橋》上的詩歌就是我打的字,所以我對你的名字有印象。
哦,原來是這樣。小舍仔細打量了一下錢一蕾,她和自己年紀相仿,也許比自己大一兩歲吧?小舍想。看上去,錢一蕾不是很漂亮,但也說不上難看。她的鼻梁很挺,好像比其他的女孩子挺拔,這是一個優勢,有這樣挺拔的鼻梁的女孩子好像并不多。如此說來,周小舍到城里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錢一蕾。
周小舍再見錢一蕾是在兩年后了。那時候,周小舍已經到縣城工作,一家叫明日廣告公司的單位正好要招一名文案,在許清河老師的推薦下,周小舍進入了明日廣告公司工作。
報到那天,周小舍有了兩年前的經驗,他對縣城的街道有了初步的了解,明日廣告公司所在的紅旗路就在北新路南邊,從文化館步行到明日廣告公司大約十來分鐘,不算遠。事實上,縣城不大,也就四五條馬路、七八個紅綠燈而已。
周小舍來到明日廣告公司的那天,接待他的是一位濃妝艷抹的女士。
你是周小舍?女士公事公辦的樣子。
周小舍怯怯地說,是的,是許清河老師介紹我來找張總的。
我知道。女士臉上沒有什么表情,周小舍也搞不清她是什么角色,也不敢多問。
張總正在開一個策劃會議,你先在小會議室等一下吧。女士指了指小會議室,給周小舍接了一杯水,紙杯上印著明日廣告公司的廣告詞“把握今日,開創明日”,周小舍端詳了好一會兒,覺得這句廣告詞不咋的。不過也算湊合。當然,他一下子也想不出更好的廣告詞。
周小舍坐在小會議室里感覺有點無聊,會議室太小了,也就能坐五六個人的樣子,墻上貼著幾張KT 板,上面的內容是公司規章制度。他看到其中有一條“不準接受客戶宴請”,暗暗笑了一下,想,難道還有客戶會請廣告公司的人吃飯?也許混得好的人會經常有飯局吧!
張午成的會議開了有兩個多小時,等到會議結束,已近十二點了,好在周小舍的帆布包里帶了一本雜志,陪他熬過了這個難熬的上午。
剛才那位女士進來對周小舍說,張總會議剛結束,請你去他辦公室。女士用了一個“請”字,讓周小舍聽來有點暖意。
于是周小舍來到了總經理辦公室,見到了傳說中的張午成總經理。
張午成倒是挺客氣的,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小周,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周小舍搓搓手說,沒關系的。
張午成說,許老師都跟你說過了吧?隨著廣告業務的快速增長,我們公司要招一名文案,許老師極力推介你,我相信許老師的眼光。
張總您過獎了。周小舍不知道說什么好,畢竟是第一次跟張總見面,而且馬上要成為張總的員工,這個角色是蠻難拿捏的。
我們明日公司在本市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廣告公司,一定會讓你有用武之地的。張午成信心十足的樣子讓周小舍似乎看到了自己美好的前景。
你有沒有什么想法?張午成問周小舍。
沒什么想法,要從頭開始學習。
張午成笑笑說,跟著我們公司一起成長,我看你文質彬彬的,干文案應該能勝任。
謝謝張總信任。周小舍的內心是欣喜的,不管怎么樣,從可蜜鎮到縣城來工作,也是他一直的夢想,現在這個夢想終于要實現了。
張午成打了個電話,剛才那位女士就走了過來。張午成對周小舍說,讓蒲芳芳總助給你辦一下入職手續,安排一下辦公桌和宿舍吧。
哦,原來她是總經理助理,看起來蒲芳芳身高足有一米七,穿著高跟鞋的她顯得更高了,而她的大波浪長發又是那么的洋氣,周小舍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張午成說,小周你下午自己去安頓一下宿舍,需要什么生活用品就去買點,有什么其他事就找蒲總。
一旁的蒲芳芳朝周小舍笑笑說,以后是同事了,有什么問題盡管找我。
周小舍發現蒲芳芳笑起來真好看,如果跟錢一蕾相比,很明顯,蒲芳芳是上海大小姐,錢一蕾是鄉鎮小姑娘。他還是很滿意自己作出這樣的比較的。
明日公司的宿舍就在公司隔壁的一幢老式平房里,兩個人一間,房子帶個院子,院子里的一棵柚子樹散發出淡淡的香味。周小舍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地方,關鍵在于這里是縣城的中心,巴掌大的縣城都在周小舍的腳力范圍之內。
下午,周小舍安頓好了宿舍后決定去一趟文化館,看望一下許清河老師。去之前,周小舍用公共電話打了個電話到文化館,確認許清河老師是否在辦公室。他覺得應該好好感謝一下許老師。周小舍知道許老師喜歡抽煙,他就在商店里買了一條“紅塔山”,用報紙包了一下,放進自己那個淡藍色的帆布背包里。
這兩年里,周小舍雖然偶爾來過一兩次縣城,卻沒有去過文化館,想到這里,他感到有點奇怪,按理說,兩年前和許清河老師見面后,他們通過多次電話和信件,坐一個小時的長途車來看看許老師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這么正常的事偏偏沒有發生。
周小舍來到文化館門口,小小的傳達室里坐著的還是那位干瘦的老頭,看起來比兩年前更瘦了。老頭的眼光一如既往地警惕,不過這一次,周小舍知道他姓朱,大家喊他朱師傅,所以周小舍見了他馬上喊一聲:朱師傅好。
你是誰?你找誰?朱師傅干巴巴的臉上一副嚴肅的神情。他的眼鏡顯然已經換過了,看上去度數也增加了不少。
我叫周小舍,我來找許清河老師的。
許清河?你認識他?你跟他說好的嗎?
周小舍點點頭,他看到朱師傅的眼光變得犀利,又帶點寒意,幾乎刺進了他的胸膛,或許門衛對陌生人來訪都是這么警惕的吧。
一番盤問,朱師傅終于放周小舍上樓。上到二樓,樓梯口的第一間房是財會和文印室,周小舍在里面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不是錢一蕾嗎?
你好!周小舍走過門口的時候正好錢一蕾抬起了頭,四目對撞了一下,周小舍脫口而出打了個招呼。
哎,是你呀,周小舍。錢一蕾脫口而出,但也有點意外。
清明剛過,天氣已經很熱了,周小舍記起兩年前錢一蕾穿的是鵝黃色的連衣裙,而這次穿的是牛仔褲,倒是顯得時尚了許多。兩年不見,周小舍發現錢一蕾變漂亮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呢?一下子也說不清楚。
我來找許老師。周小舍這么一說,錢一蕾就笑了一下,這一笑讓周小舍仿佛回到了兩年前的那個會場上。
哦,是不是又來投稿了呀?錢一蕾的話讓周小舍不由自主地緊張了一下,心跳加快了起來。
周小舍“嘿嘿”一笑,朝錢一蕾揮了揮手,算是道別。
再走過兩個辦公室,就到了許清河老師的辦公室。
知道周小舍要來,許老師已經泡好了茶。看到周小舍,許老師滿是高興的神情。他還是穿著白襯衫,白襯衫外面是一件看不出顏色的夾克衫——這種天氣其實外面不穿夾克衫也是可以的,不過許老師這個年齡的人總是有點“保身價”,多穿一件似乎也是對自己負責。
坐定后,許老師笑瞇瞇地說,是不是到廣告公司報到了?
周小舍說,是呀,張總人很好很熱情。
哈哈,他是個爽直的人,也很有才,你跟著他也能學到不少東西。看起來許老師對張總贊賞有加。
我覺得明日廣告公司是一家蠻不錯的公司,我也看好廣告業的前景。周小舍這么說著,他的這些“經驗”不知道是來自哪里,總之說一些好話總歸不會錯,畢竟是許老師介紹去的。
張午成是個有想法的人,你可能不知道吧,他是我的小舅子,也就是說,我是他的姐夫,沒有這層關系我也不會介紹你去他公司。
原來是這樣呀,怪不得張總那么熱情。周小舍得知這一層關系,有點吃驚,也有點高興。
許老師說,你好好干吧,他們公司需要你這樣的筆桿子。
許老師點了根煙,繼續說,小舍,你最近在寫什么?
周小舍知道許老師是在問他文學創作方面在寫什么,其實這兩年他除了寫一些詩歌外,還寫了不少散文,也在嘗試寫小說,不過關于小說,周小舍覺得自己還是門外漢,摸不準道。周小舍回答說,還是老樣子,寫點詩歌,也寫點散文,沒什么進步。
許清河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上個月的市報副刊上不是發了你一篇寫春節的散文嗎?我看寫得不錯,當然要說不足也有,主要是角度有點普通,缺乏一些屬于個人的獨特感受。
聽許老師這樣一說,周小舍內心很是佩服,想許老師畢竟在文壇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看文章的眼光還是很犀利的。
周小舍連忙說,那篇文章寫得匆忙,也有點應景的樣子,正好春節過了不久,我就寫了篇關于過年的文章,確實遣詞造句普通了點,里面的細節也一般般。周小舍順著許老師的說法對自己的文章進行了剖析。
許老師說,你能夠看到自己的不足,說明你有進步,有的人文章沒寫好,還覺得自己的文章是天下最好的,容不得人家批評。
周小舍點點頭說,許老師說得對,我也遇到過這樣的人,牛皮很大,寫得潦草,不過他們這樣的文章能夠發表出來,說明他們還是有點本事的。
功夫在詩外嘛,哈哈哈。許老師狠狠地撳滅了煙頭,“咕咚”一下喝了一大口茶。周小舍發現許老師喝的是紅茶,再加上抽煙,所以牙齒黃黃的。
周小舍從背包里取出那條用報紙包著的香煙放到了許老師的抽屜里。
許清河說,小舍,你這是干啥?這是不正之風。
周小舍說,一條香煙也值不了多少錢,感謝許老師對我多年的關心,特別這次介紹我到明日廣告公司,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大轉折點,我也得以跳出可蜜鎮來到城里工作,真的非常感謝您。
許老師說,小舍啊,你剛剛過來,還沒有領到工資,我是受之有愧的。不過,下不為例,這次先收下,以后不能再送東西了。
周小舍松了口氣,說,這我知道,以后您還得繼續關心我,不管是文學創作上還是廣告公司里的事情,都請您掛心。
許清河說,小舍你談女朋友了嗎?
沒想到許老師會問這個問題,周小舍有點難為情地說,還沒有呀。
哦,不過你還年輕,也不急。我們文印室的小錢談了個男朋友,據說今年國慶節要訂婚了。
周小舍不知許老師說這話的意思,想,錢一蕾談男朋友和我有什么關系呢?
據說小錢男朋友的父親是機電公司的經理,家里經濟條件不錯。許老師這么一說,讓周小舍有了自卑感,畢竟自己從鄉下上來,沒有好的背景,學歷和家境也一般,到了城里才知道世界那么大,自己未知的東西還很多,就像文學創作,以前自己一個人悶頭悶腦寫了一大堆東西,如今看來,實在拿不出手。
那她運氣挺好的。周小舍不知如何接許老師的話,沒頭沒腦地說了這么一句。
許老師聽了哈哈一笑說,小舍啊,你有才能,以后肯定會找到比小錢更好的女朋友的。
怎么突然把錢一蕾作為參照物了呢?簡直是匪夷所思,周小舍心里想,如果能夠找到像錢一蕾這樣的女孩做女朋友已經非常不錯了。不過,以后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就像一年前,他哪能想到自己會到城里的廣告公司來工作呢?人生是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的。
這么一想,周小舍覺得自己的內心似乎亮了起來。
明日廣告公司的工作非常忙碌。張午成確實是個人物,在這座小城里,幾乎沒有他不認識的人,什么局長、主任、書記、鎮長,他隨口說一個名字在周小舍眼中都是一個“大人物”,周小舍對張午成很是佩服。
隨著與公司里其他同事的熟識,周小舍隱約聽到一個消息:蒲芳芳是張午成的情人。聽到這個消息的周小舍有點難以置信,又有點驚慌。確實,從蒲芳芳的行為來看,她的職務雖然是總經理助理,其實說到底就是張午成的私人秘書,張午成出去談業務,一般都會帶著蒲芳芳,在這個有二十來個人的公司里,蒲芳芳的地位僅次于張午成,而某些方面蒲芳芳甚至在張午成之上。除了周小舍,公司里所有人都清楚張午成與蒲芳芳的關系,慢慢地,周小舍也知道了他們之間的關系,而那次應酬,周小舍親眼看到了他們之間非同尋常的關系。
那天快要下班的時候,蒲芳芳過來對周小舍說,你下班時留一下,張總有點事。
周小舍點點頭算是答應了,不過他在心里想,張總找我會有什么事?難道這兩三個月來張總對我的工作不滿意?還是有其他的事情要說?周小舍思索了一下,來到明日公司的這段時間,自己一直很賣力,寫的幾個廣告文案也得到了客戶的認可,而且自己對加班也無怨無悔,這些張總和蒲芳芳應該是看在眼里的。這么一想,他心里稍稍坦然了一些。
等到公司里的其他員工走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周小舍聽到張總在關門,他知道張總離開辦公室了,一會兒,張總和蒲芳芳一起走了過來,張午成對周小舍說,走,和我們一起去拜訪一位客戶。
叫我一起去?周小舍滿臉疑惑。
對,我們要去可蜜鎮拜訪一位客戶,可蜜鎮不就是你的家鄉嗎?你和我們一起去,晚上要在可蜜鎮吃飯。
哦,好的。周小舍有點驚喜,畢竟到公司這么久,張午成還是第一次喊他一起出去應酬。
于是,三人一起來到了那輛黑色的佳美轎車邊,司機小陳已經發動了汽車在等候了,張午成對周小舍說,小周你坐前面。
周小舍有點不知所措,張午成這么一說,他就拉開了副駕駛室的門,貓腰鉆了進去。張午成和蒲芳芳坐在后排。
一路上,張午成那臺笨重的“大哥大”接到了三個電話,等他三個電話講完,車子已經來到了可蜜鎮的入口。這條路周小舍很熟悉,他幾乎每個禮拜六都要回可蜜鎮,不過這一次坐在張午成的轎車里看這條路,倒有了許多的陌生感,他心想,一定是角度的問題吧。
車子來到了騰龍酒店的門口。這個酒店周小舍是知道的,這是可蜜鎮上最好的酒店。騰龍酒店的那道醬蹄,在方圓五十公里內聲名遠揚,是真正的人間美味。
周小舍隨著張午成和蒲芳芳走入888 包廂,這個包廂是騰龍酒店最大的包廂,也可以說是可蜜鎮上最上檔次的包廂,說明今天張午成要見的客戶非同尋常。
客人們陸續到場,張午成不停地跟他們握手打招呼,周小舍站在邊上顯得有點尷尬——因為這些客人他一個也不認識,而蒲芳芳顯然和那些人都比較熟了,她的纖手不停地和他們握來握去,那些人發出歡樂的笑聲。
等到坐定,周小舍一數,正好十個人。他想,十個人至于用這么大的包廂嗎?這個包廂坐十六個人都綽綽有余,坐十個人分明是浪費。周小舍看不懂張午成的安排,心里有點疑惑。
慢慢地,周小舍知道了今天宴請的是什么人,那個為首的是可蜜鎮農工商總公司的總經理徐總,其他的什么副總、所長、主任之類的只是陪客。徐總長得很敦實,臉黑黝黝的,看上去比較正直,當然,人不可貌相。徐總是今天最大的領導,所以顯得很開心。
周小舍去給徐總敬酒的時候,張午成在邊上對徐總介紹說,這是我公司今年新進的小周,他可是你們可蜜鎮的才子哦,被我們挖過來了,他發表過好多文章,是我市為數不多的青年作家。
被張午成這么一說,周小舍有點不好意思,張午成說得有點夸大其詞,不過徐總聽了很開心,說,我最佩服作家了,我在部隊當兵時也當過連隊的通訊員,寫文章是很辛苦的,寫好文章更不容易,來來來,小周,我們干一杯!
因為已經喝了幾杯紅酒了,周小舍的臉有點燙、有點紅,不過徐總這么一說,周小舍還是很高興的,無形當中拉近了距離。張午成在邊上聽徐總這么一說,一下子來了勁,他馬上拿過來一個酒瓶往周小舍杯子里倒酒,其實張午成也并不知道周小舍的酒量如何,在這樣的場合,在領導面前,張午成可不管你酒量好不好,敬領導酒就要倒滿。周小舍沒辦法拒絕,只得硬著頭皮上,連著干了兩個滿杯后,頭腦一陣發脹,感覺血液全部沖到頭上,連頭發都像是豎了起來。
周小舍環顧四周,看到蒲芳芳正和那些人在一杯一杯地喝,看得出她的酒量了得,在喝酒的過程中,蒲芳芳也在不停地周旋,因為那些人盯著她不放,或許在美女面前,他們都有一股征服欲,表現在喝酒上就是希望對方喝醉喝倒。然而,蒲芳芳畢竟是蒲芳芳,這么多酒喝下去卻面不改色,還能反灌對方,氣氛一時熱烈無比。
張午成也喝得有點搖搖晃晃了,而徐總則穩如泰山。在敬酒喝酒的過程中,周小舍漸漸聽明白了今天這個飯局的目的:明日公司即將參與可蜜鎮老街開發的廣告策劃、形象設計等業務,這筆業務資金不是一個小數目,現在已經談得八九不離十了,今天這場酒一喝,基本上等于敲定了合同,難怪張午成要親自上門來請客,而且要在最好的酒店、最好的包廂,那些寫著英文、法文的紅酒肯定也價格不菲,反正周小舍是第一次喝這種酒,也是第一次喝這么多酒。
吃完飯將近九點鐘,這個時間不算晚也不算早,但張午成興致正高,于是一群人又去了騰龍酒店的娛樂中心。穿過一片光怪陸離的燈光,他們走進一間KTV 包廂,包廂里霓虹閃爍、音樂曖昧,周小舍是第一次走進這樣的地方,今天跟著張午成、蒲芳芳、徐總他們,周小舍算是開了一次“洋葷”。
坐定后,徐總撈起話筒,來了一首《咱當兵的人》,雖然音調不是特別準,倒也感情真摯,大家熱烈鼓掌。一首唱完,徐總有點意猶未盡,他拉起蒲芳芳,一定要合唱一首歌,蒲芳芳忸怩一番,點了首《夫妻雙雙把家還》,于是兩個人唱了起來。顯然,蒲芳芳似乎有專業功底,字正腔圓,而徐總則有點跑調,但也算過得去。徐總非常興奮,唱著唱著竟拉住了蒲芳芳的手,周小舍發現張午成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神情,不過他馬上鼓起掌來說,徐總唱得好,唱得真好!
一曲完畢,徐總好像還深陷其中。
蒲芳芳坐到了張午成的邊上,張午成遞給她一塊西瓜。那個沙發太軟了,坐在上面的人幾乎陷了進去。包廂里的氣味非常復雜,周小舍推門出去透氣,再坐下去他就要窒息了,心想,這種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可是為什么大家都趨之若鶩呢?周小舍搞不清楚。
周小舍在外面兜了一圈,吹了一陣風后,感覺酒醒了不少,一看表,已經十點半了。他們什么時候能結束呢?
周小舍回到包廂,發現張午成和蒲芳芳抱在一起,張午成有點醉了,而蒲芳芳還是蠻清醒的,他們就這樣抱著也不避嫌,邊上的人似乎也習以為常了。而周小舍則感到些許尷尬,畢竟是第一次和他們一起出來應酬,第一次發現他們這樣的舉動。
對周小舍來說,廣告公司的工作非常新鮮,他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寫文案既是周小舍的工作,也是他的愛好。雖然還稱不上得心應手,但這半年時間下來,他的工作還是得到了張午成的肯定,尤其是拿下可蜜鎮的那項大業務后,張午成心情舒暢,對公司的發展也充滿了信心。在一次公司內部的會議上,張午成對大家說,照這樣的趨勢,我們公司計劃在兩年內搬到剛剛落成的全城最高的那幢大樓里去,準備租下一層樓面,打造出自己的廣告地標。張午成的話是有一定的煽動性的,大家聽得如癡如醉,一邊的蒲芳芳頻頻點頭,她的做派倒像是老板娘。周小舍是新員工,不過他也看到了公司的快速發展,據說單單是可蜜鎮的這項業務,就相當于公司前兩年的總業務量,公司發展前景確實喜人。
周小舍的手頭一下子堆積了好幾個待寫的文案,日子就變得忙碌起來,這樣一來,自己的文學創作就無暇顧及了。時間到了將近國慶節,周小舍想,一定要去看望一下許清河老師。打了兩次電話,許老師都不在單位,那座北新街上的灰色建筑變成周小舍心里頗具分量的地方,那里不單單有個許清河老師,還有一位叫錢一蕾的女孩,不過,錢一蕾馬上要訂婚了,想到這,周小舍心里悵然若失。但轉念一想,錢一蕾跟自己又有什么相干呢?真是莫名其妙,周小舍苦笑了一下。
宿舍院子里的柚子樹上結滿了碩大的柚子,柚子正在漸漸變黃,散發出一陣陣淡淡的香味,周小舍很喜歡這種香味,也喜歡這個小院子給他的生活帶來的全新感受。從紅旗路到北新街,步行差不多十分鐘,但周小舍覺得還是有段距離的,這段距離因為有了許清河老師而變得很近,因為有了錢一蕾又變得很遠。
雖然沒打通電話,周小舍還是決定去一趟文化館,看望一下許清河老師,這次他在商店里買了一盒茶葉,他知道煙和茶是許老師的最愛。來到北新街的文化館,朱師傅已經認識周小舍了,看到周小舍走來,就說,小伙子又來找許先生呀?
周小舍“嗯”了一聲,說,對呀,許老師在不在呢?
朱師傅說,真不巧,許先生今天下鄉去了,你怎么不事先打個電話給他?
周小舍有點悻悻,嗯,我打過的,沒打通。
朱師傅滿是皺紋的臉上掠過了一絲笑意,這些皺紋就像一朵菊花——事實上,周小舍看到文化館門口正擺放著兩盆即將開放的菊花。
朱師傅,朱師傅。周小舍說,我帶了點東西給許老師,放在你這里吧,等他明天上班你幫我給他。
朱師傅搖了搖手說,他的辦公室門開著,你去放他桌上吧,下班時我會幫他關門的,你可以留個紙條在他桌上。朱師傅想得真周到。
于是周小舍一路走過去,走過了文印室——門關著,那個熟悉的身影也沒出現。他走進許清河的辦公室,把茶葉放在桌上,并匆匆留言:許老師,來看你正好你不在,送你一盒茶葉,不成敬意,再聯系!——周小舍。
往回走路過文印室的時候,周小舍又往窗戶里望了一眼,窗戶關著,整個辦公區域很安靜。到傳達室時,周小舍問朱師傅,錢一蕾今天也休息啊?
朱師傅抬起眼,笑瞇瞇地說,那個小錢呀,已經不在這里做了,離開有一個月了吧。
哦——周小舍心里有點吃驚,大概是她男朋友給她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吧?周小舍有點走神,錢一蕾,錢一蕾,他在心里默默叫了兩聲。
到臨近春節的時候,周小舍算了一下,來明日公司將近十個月,這段時間里,他對這個小城的幾條主要的街道都非常熟悉了,當然,他最熟悉的還是北新街和紅旗路,這兩條平行的東西向馬路他已經走過無數遍了。
由于公司業績不錯,張午成特地在小城最好的賓館里組織大家吃年夜飯,又給大家發了紅包。再過十幾天就是春節了,天氣冷絲絲的,但周小舍的心里熱乎乎的,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人生方向,撇開明日廣告公司不說,就是在小城的街道上漫步,那種感覺也比在可蜜鎮上要好得多。
那天,周小舍在公司的傳達室里發現了一封寄給自己的信,不知道是誰寄來的,看信封上的字也不熟悉,信封右下角也沒有留地址,只寫著“內詳”兩字,看上去字體娟秀,應該是女孩子的來信。周小舍滿腹疑惑,用美工刀慢慢打開信封,只有一張信紙,信紙折成一只紙鶴的樣子,看起來很是用心。打開信紙,周小舍先去看落款,原來是錢一蕾寄來的。周小舍的第一個反應是:她怎么會給我寫信?
信寫得很簡單,周小舍很快就讀完了,因為信并不長,就附錄在此:
讀了這封信,周小舍的心“怦怦”狂跳了一陣,他看了一下落款時間,竟然是九月份的,那么,這封信在公司傳達室默默地躺了有四個多月,而寫這封信的時候,錢一蕾還在文化館工作吧,她辭去這份工作也是寫這封信以后的事了吧。如果當時及時收到這封信的話,自己會給她回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