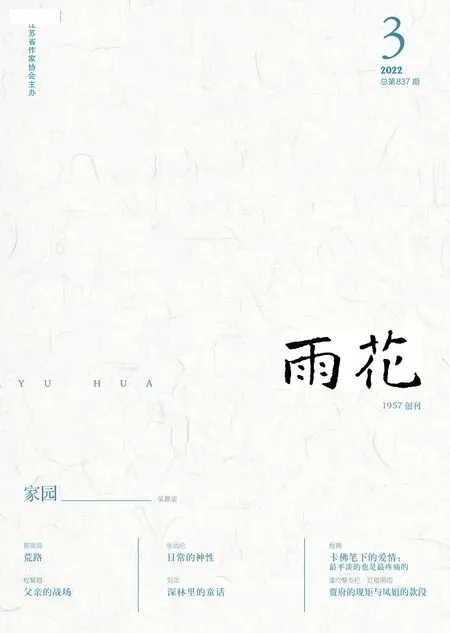絮,彌漫于我們存在之中的寓言
李海鵬
這篇小說以“我”與“絮”的相遇開篇:“我第一次見到銀白色的絮,她長了一副讓人朝思暮想的模樣,她明明沒有什么樣子,卻長了一張什么模樣都有的臉,我們思念的或者不思念的模樣全都長在她的臉上,她賦予了同一群人同一張臉,也賦予了不同的人各種各樣的臉。”讀到這樣的句子,我以為自己將會讀到一個愛情故事,或者以為這篇小說會針對人與人之間具象的交往而鋪展一場敘事。這段開場留給我的印象與期待是,“絮”似乎是一個特別的女孩,有著特別的容貌和性格,以及一個特別的名字。此外,一些閱讀經驗告訴我,在一些并不成熟的小說作者筆下,這樣“特別”的小說主人公,經常會領我們經歷一個俗套的故事、一段俗套的愛情。然而讀到稍后一點的段落,我便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伴隨著這個開頭而建立起的所有認知與預期都已失效了,通讀完全篇以后,更是覺得這篇小說所講的故事遠比我預想的要抽象和深奧:有一天,“絮”來到了“我”所生活的村莊,很快她便如柳絮一樣四處生長、彌漫,在村子里無處不在,村民們想盡辦法阻止她對自己生活的“入侵”,但都無濟于事。后來一場大火突如其來,終于讓“絮”消失,只留下她燃燒后變成的粗麻繩。正當人們為了擺脫“絮”的騷擾而開心時,一種黑色的蟲子卻悄悄潛入人們的左耳,不斷重復著那句讓村民們最煩惱的咒語:“絮,生生世世都會居住在這里。”于是村民們割掉左耳,試圖擺脫蟲子惱人的提醒,但是很快,“絮”再次返回,人們的房屋與身體上又長滿了銀白色的“絮”。與此同時,“我”的媽媽開始變得精神恍惚、錯亂,她不能接受“絮”的存在,也不能理解“絮”所做過的一切。為了徹底擺脫這種侵擾,整個村莊后來進行了兩次遷移,但不幸的是,“絮”依舊如影隨形,無論人們遷移至何處,都無濟于事。“絮,生生世世都會居住在這里”,這句咒語貫穿于小說敘事的始終,它構成了小說中村民們的生存中顛撲不破的事實,或者說一種無法掙脫的宿命。
小說家趙松在談論對一部小說的感受時曾言:“當你合上這本薄薄的書,可能會發覺,它就像一場剛散去的霧,或是剛被醒來淹沒的夢……任何時候你重新打開它,都有可能像進入一個新的夢。”我讀罷這篇小說,也感受到了一種類似的東西,就仿佛自己進入了一個細膩又費解的夢境,在這夢境中,飛“絮”彌漫,無處不在,無法擺脫。“她”在小說中被人格化,是小說的主人公,但她的身體卻又是彌散性的,不斷生長于村民們的房屋中、身體上,作者對她的處理,會讓人想到一點泛神論的意味。而且更值得玩味的是,她的存在或消失,所關涉的并不是她自身,而是村民們,或者說,作者對她的建構與談論,目的在于揭示村民們的存在狀態,她是作者思索與呈現村民們存在狀態的某種整體性、關鍵性的中介與隱喻。
這篇小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呈現出其寓言的特征與意味。當我們掩卷沉思,這彌漫在村莊中的“絮”,便會同樣彌漫在我們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思考之中。世上的人們,難道不是同這村莊中的人們一樣,也始終要面對一些不可掙脫的“絮”?對于人類來說,“絮”可以是對于什么的隱喻呢?死生之數的不可逆轉?權力意識的無處不在?存在枷鎖的如影隨形?抑或宿命論的無法破除?既然包括遷移在內的辦法都無法破除“絮”的跟隨,既然這樣的生活注定是一場煩憂、爭斗與流離,那么我們如果是小說中的村民,又將如何面對?在這個意義上講,這篇小說在讀者閱讀環節中延伸著它的未完成性與開放性,每次閱讀,我們或許都能生成一些新的思考與所得,這也正是這篇小說耐人尋味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