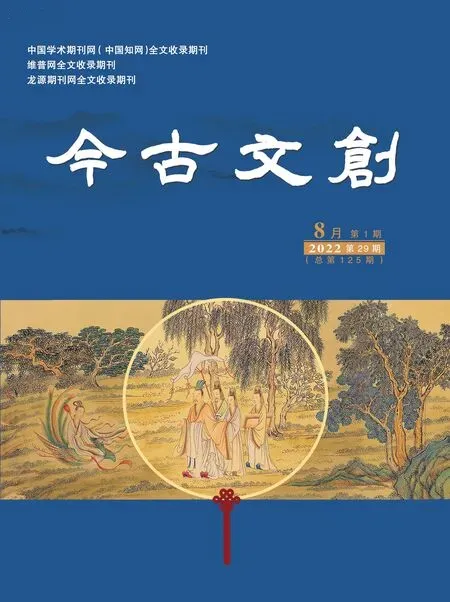《四川瀘州方言研究》中部分方言詞本字考釋
◎馮 爽
(四川大學 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四川瀘州方言研究》與瀘州方言概述
瀘州位于長江上游,地處四川省東南部、川滇黔渝結合部,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具有兩千多年歷史文化;西漢設江陽侯國;梁武帝大同年間建置瀘州;瀘州在宋代即為西南要會,明代即與成都、重慶三足鼎立,成為當時全國33個商業大都會之一。瀘州得名“瀘水說”,古稱江陽。瀘州話同四川境內的絕大多數方言一樣,屬于西南官話,與湖北、河南方言比較接近,與普通話距離也不大。《四川瀘州方言研究》是目前少有的系統描寫瀘州方言的著作之一,被納入了《瀘州全書》系列書籍。該書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瀘州方言的音系、音變,分別將瀘州方言從語音的角度同普通話語音以及中古漢語語音進行比較,從詞匯、語法的角度同普通話詞匯、語法進行比較。該書介紹,瀘州方言在語音上以保留了入聲聲調為最大特色,同時瀘州方言中的兒化音也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此外,瀘州方言在詞匯上也保留了許多古老的質素,因此瀘州方言中許多詞匯難以在現代漢語中找到對應的例字。深入考察方言詞匯本字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方言詞匯之來源及其意義之演變,同時也能在考證過程中更深刻地認識先民造字的智慧和漢字的魅力。《四川瀘州方言研究》的作者,李國正先生,在全書的最末附有上千字的詞匯表,可見先生之用心。但其中有部分方言詞匯并未找到可以匹配的本字,另對于其中部分方言詞匯所采用的例字筆者持有不同意見。故本文從其中選取共10例,按照音義結合的原則,遵循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并結合文獻例證來考證部分詞語的本字來源。
二、瀘州方言詞本字考釋
(一) ta35“達”:跌;摔
ta在書中解釋為跌,摔,是瀘州方言中十分常用的動詞詞匯,作者在書中以“達”字為之匹配。據考察,瀘州方言里這一發音為ta,意義為“跌、摔”的方言詞匯,本字確屬“達”最合理。“達”,《廣韻》他計切,足滑。《說文解字》達,逹或從大,或曰迭。足部,徒葛切。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或曰此迭字之異體也。”“迭”字在《說文解字》中記載為:“迭,更迭也。從辵失聲。一曰達。足部,徒結切。”因此,我們可以聯想到與“迭”同音,與“達”同義的“跌”字。“跌”與“迭”同為足部,徒結切;“跌”在現代漢語中表摔跤意,這與瀘州方言中“達”的意義相同。關于“跌”,在《說文解字》中有如下記載:“踼也。從足失聲。一曰越也。”在《廣韻》中,“跌”為徒結切,跌踢,又差跌也。由此可見“達”、“跌”在古漢語中有著密切的聯系。“達”本義為足滑,即現在所謂的跌、摔;而“跌”本義為踢,反倒并無摔跤意;“達”、“跌”二字本在字形和字音上就有相似以及關聯之處,也許因此便影響了二字意義之間的演變,形成了后來人們以“跌”頂替“達”來表示了摔的意義。是以,以“達”表示跌、摔的用法是中古漢語保留在瀘州方言中的印記。
(二) ia?55“央”:捱,拖延
ia?在書中解釋為捱,拖延。這是瀘州方言中常用的動詞詞匯,作者在書中以“央”字為之匹配。據考察,瀘州方言里這一發音為ia?,意義為“捱,拖延”的方言詞匯,本字確屬“央”最合理。“央”, 《廣韻》中央一日,久也。於良切。《說文解字》中央也。從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一曰久也,此一別意。”可見,據記載“央”本為會意字,原始義為“正中”;同時,“央”還有一別意為“久”,尤其是在《廣韻》中主要收錄的是“央,久也”這一義項。這正好可以與瀘州方言中的“捱,拖延”意義相聯系。因此可以推論這一方言詞的本字為“央”。
(三) t’au55“詜”:罵
t’Aau在書中解釋為罵。這是瀘州方言中常用的動詞詞匯,作者在書中以“詜”字為之匹配。據考察,瀘州方言里這一發音為t’au,意義為“罵”的方言詞匯,本字確屬“詜”最合理。“詜”,《廣韻》土刀切。詜?,言不節。可見“詜”、“?”在過去意義相近。古籍中關于“詜”的記錄較少,基本就是指向言不節以及與“?”相關。因此可以參考“?”的相關記載。“?”,《說文解字》大牢切。往來言也。一曰小兒未能正言也。一曰祝也。從言匋聲。可見,這里“?”在使用中的貶義色彩尚不明顯。有學者指出西南官話中表罵人的方言詞的本字為“?”,這有失偏頗。首先“?”經考證沒有十分強烈的貶義,同時“?”字之音的聲調與這一方言詞的發音有所出入。因此,與“?”字相關,而出現較晚、記載較少的“詜”字或許作這一方言詞匯的本字更為合適。
(四) p?n51“畚”:蘸
p?n在書中解釋為“蘸”,作者暫未匹配合適的本字。據考察,瀘州方言里的這一發音為p?n,意義為“蘸”的詞匯的本字應當為“畚”。與之相關的還有“畚菜”,即須蘸調味品吃的蔬菜。“畚”,《廣韻》布忖切,草器。《說文解字》畚,蒲器也,所以盛糧。從由,弁聲。《左傳·宣十一年》稱“畚筑”。杜預注《左傳》:“畚,盛土器。以草索爲之,蒲與草不相妨。”可見,“畚”原是用蒲、草等材料編織的盛物器具,可盛糧盛土等。《列子·湯問》有言:“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其中所謂的箕畚一物便是我們現在常用的簸箕。“畚”本是指代盛物器具的名詞,后出現活用作動詞的現象。如“他輕手輕腳來到糧房,畚一斗糯米對布袋里一灌。”《靖江寶卷》。“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這里的“畚”已經活用作了動詞,但意思是“用畚盛”。此處“用畚盛”與“蘸”之意相差甚遠,因此“畚”作“蘸”之意,或許來源于“畚菜”。《太平御覽》記載:“蒙山《高士傳》曰:‘楚王親至其門,方織畚。王去有間,其妻戴畚菜挾薪而至,問車馬跡之多。’”此一句中既有“畚”作盛物之器,亦有“畚菜”之說法,可以推論出“畚菜”即用畚簡單裝盛,且未經繁瑣烹飪調味程序的菜品。由于“畚”為蒲草等材料編織而成的器物,難以裝盛伴有湯水調料的蔬菜,因此可作此推論。是以,“畚菜”在食用時往往須另蘸調味品以為佐料,而這一蘸取調料的行為便被人們以“畚”稱之,并保留在了方言之中。
(五) t?’i?u55“煪”:煙熏
t?’i?u在書中解釋為煙熏。在該書中作者未找到合適的例字為之匹配,而瀘州地區常見是以“秋”字表示t?’i?u。如常見農家樂的招牌上寫“此處秋臘肉”,意思是這里可以提供煙熏臘肉的服務。但考察“秋”字的原始義,《說文解字》中記載為“禾谷熟也”,其后使用中也未見與煙熏、火烤有關的引申義,因此瀘州方言中有“煙熏”意的方言詞僅是與“秋”同音。據考證,這一方言詞匯本字應當是“煪”。“煪”, 《廣韻》自秋切,煪熮。《玉篇》自留切,熮也。可見在古代“煪”、“熮”二字意義相同。《說文解字》中暫未查詢到“煪”字,卻有“熮,火貌”的相關記載。“熮”, 《廣韻》余救切,火爛。《玉篇》力酒切,燒也,爛也。由此可以推論“煪”和“熮”的原始義都與“用火燒、烤”緊密相關。進一步拆分“煪”的字形,由“火”與“酋”組成。“酋”,《說文解字》繹酒也。從酉,水半見于上。凡酋之屬皆從酋。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繹之言昔也。昔、久也。多下曰。從重夕。夕者、相繹也。故重夕爲多。然則繹酒謂日久之酒。”可見,“酋”本義與烈酒、勁酒相關,而后在使用中引申出“強勁” 等意義。有學者指出“火”與“酋”聯系起來就是“用強火烘烤”,我也贊同此意。“煪”,《集韻》張流切,燥也。此處“燥”之意正好吻合了“用強火烘烤”之意。再聯系“煪臘肉”的傳統制作方式也正是以強火燒木柴,以濃煙熏烤生肉,因此瀘州方言中的“煪”這一詞匯的本字應當就是“煪”字。
(六) to?55“懂”:糊涂
to?在書中解釋為糊涂。作者在該書中以“”為例字,但經考查“懂”字實為表“糊涂”意的這一方言詞匯的本字。“懂”, 《廣韻》多動切。懵懂,心亂。《正字通》多孔切,音董。俗謂昏愚曰懜懂。《說文》有懜無懂,懜與懂音別義同。由此可見,“懂”的本義近似于我們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懵”之意,而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懂”的常用義“明白”正好相反。瀘州方言中的“懂”這一詞匯則保留了其中古漢語時期的意義。此外,“懂”在瀘州方言中的聲調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懂”字315調相差甚遠,但經查閱各大家所構擬的“懂”字中古發音,為全清上聲,如潘悟云擬音為35調,這就與瀘州方言中這一詞匯的聲調相吻合了。
(七) to?214“侗”:鼓起;努出
to?在書中解釋為鼓起,努出,大。作者在該書中以“董”為例字,但經考查“侗”字實為表“大”、“鼓起、努出”意的這一方言詞匯的本字。“侗”,《廣韻》徒紅切。《說文解字》大貌。從人同聲。《詩》曰:“神罔時侗。”他紅切。因此,“侗”之原始義就與形容詞“大”相關。與“侗”相關的詞語在現代漢語中有如“侗侗”,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長大貌。由此可以推論,在瀘州方言中表“大”、“鼓起”等意義的詞匯的本字應當是“侗”。
(八) ni55“?”:貼近;挨近
ni在書中解釋為貼近,挨近。作者在該書中以“厘”為例字,經考察在瀘州方言中表“貼近、挨近”意的方言詞匯的本字是“?”。“?”,《廣韻》尼質切,近也。《說文解字》日近也。從日匿聲。昵,暱或從尼。尼質切。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日近也。日謂日日也。”可見“?”之原始義是“接近”,同時可知“?”與“昵”是異體字,在過去往往同用。據《康熙字典》記載:“昵,親近也。”現代漢語常用詞匯中“親昵”之“昵”的“親近”之意,依然保留了核心義素“近”。雖然“昵”和“?”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少有單用的情況,但在瀘州方言中以“?”表行為“貼近”仍是十分普遍。
(九) ts’?n55“撐”:直,平展
ts’?n在書中解釋為直,平展。在該書中,作者以“伸”作為ts’?n的本字,這有失偏頗。首先“伸”與二字聲母的發音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即使“伸”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與“直、平展”之意相關,也不能勉強以“伸”作為這一方言詞的例字。經查閱相關資料,“撐”當是瀘州話中表“直,平展”意的本字。在《廣韻》中未收錄“撐”字相關內容,但《康熙字典》中有相關記載:“撐,俗撐字。手字部。”另據《正字通》記載,“撐”與“橕”音義相同,因此“撐”之音義可參考“橕”的相關記載。“橕”,《廣韻》丑庚切,撥也。又橕柱也。可見,《廣韻》中雖無“撐”的相關記載,但由以上信息可推論“撐”字之發音也同“橕”為丑庚切,其義應當與橕柱相關。橕柱,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斜柱,支柱。由“橕”所指代的“柱”之形態的“直”,我們便找到了瀘州方言中以“撐”表“直、平展”之意的由來。在現代漢語中也有收錄“橕”、“撐”二字,其中“橕”主要用作名詞,保留其原始意“支柱”;“撐”則同“撐”,主要用作動詞,有“使張開,使平展”之意。按照漢語發展規律來看,很可能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撐”的使動意義就是經由“直、平展”的形容詞用法發展而來的。瀘州方言中的“撐”則保留了其作為形容詞的意義,同時也順應語言發展規律,出現了與之相關的動詞用法,如“撐直”這一方言詞的意思就是伸直。
(十) tsai51“栽”:裝訂,縫制
tsai在書中解釋為“綴聯;裝訂;承受;實在”。將表裝訂義的“栽”和表承載義的“載”歸納為同一個漢字的兩個義項,這是不太合理的。瀘州方言里的tsai既用于書籍、紙本裝訂成冊,也用于縫制衣物等。查閱“載”的字源及其演變,很難由其以承載義為核心的語義網絡中找出與方言中所稱的“裝訂”相關的蛛絲馬跡。而查閱“栽”的字源及其演變,可以推論瀘州方言中表“裝訂”意義的方言詞匯的本字是“栽”。接下來我們將二字進行比較,便可察明其中之異。《說文解字》載,乘也。可見“載”之本義就與“車”相關。《康熙字典》中還收錄了“載”的多個引申義:“事”、“始”、“行”、“滿”、“記載”、“裝飾”等。另《廣韻》載,年也,出方言,又音再。因此,從“載”之基本義到其引申義幾乎均與“車”、“承擔”、“放置”等意相關,另又做“年歲”義,似乎與“裝訂”義的關聯不大。因此,我們再考察“栽”字,發現其中關聯。“栽”,《說文解字》筑墻長版也,又草木之殖也,另《廣韻》種也。因此,“栽”的本義是筑墻長版,后引申為種植。《漢語大字典》中收錄了“栽”作動詞時的11個義項,其中第五個義項“安上”,如“栽派”,第六個義項“使固定在豎直位置上”,如“栽電線桿子”,都與瀘州方言里所稱的“裝訂”義有所關聯。另《漢字字源》中解釋“栽,表示古代筑土墻時先打木樁夾上木板,再往里填土夯實;栽有傷義,打木樁必破土使木樁深入地下。”從其字源解釋上分析,“栽”這一行為動作與“裝訂、縫制”這一行為動作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一為“插木樁”之行為,其二為“破”之結果,無論是裝訂紙本,還是縫制衣物,必先以針“破”之,而“針”正有如“木樁”之形態與功用。因此,與原書中作者用的“載”字相比,瀘州方言中表“裝訂、縫制”之意的詞匯本字采用“栽”更加合適。
三、結語
本文以瀘州方言詞匯發音為切入點,借助方言發音和古漢語發音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演變關系,以《廣韻》為語音參照標準,梳理出古漢語中同瀘州方言詞發音相同或相近的漢字,縮小考察范圍。進而,以語義為考察的核心要素,參考《說文解字》、《漢字字源》等書籍考證例字的基本義以及語義歷時演變路徑,參考《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等字詞典籍梳理例字語義網絡,從而以詞匯語義演變規律為線索,探討瀘州方言詞匯之來源,考證方言詞之本字。以上基于音義結合的原則,采用文獻佐證的方法,對《四川瀘州方言研究》中的10個方言詞匯之本字進行了考證,其中7個字是筆者針對原書作者之觀點,提出的不同意見。但由于能查閱的文獻資料有限,加之本人能力有限,考證不足之處,有待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