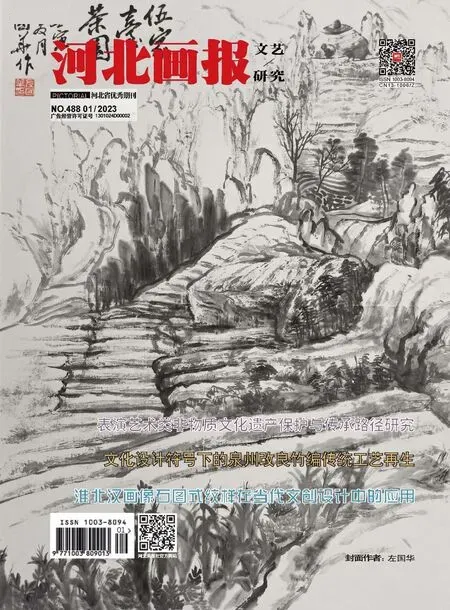語(yǔ)篇銜接下的韓漢指示詞翻譯技巧
霍雨珂
(煙臺(tái)大學(xué))
語(yǔ)篇是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語(yǔ)法約束的在一定語(yǔ)境下表示完整語(yǔ)義的自語(yǔ)言。而銜接使語(yǔ)篇的部分之間形成了連續(xù)性,是語(yǔ)篇生成的必要條件(胡壯麟,1994)。韓禮德和哈桑(1976)曾總結(jié)了五種銜接手法,分別是:照應(yīng)、省略、替代、連接、詞語(yǔ)連接。其中,照應(yīng)關(guān)系表示語(yǔ)篇中的指代成分與指稱(chēng)或所指對(duì)象之間相互解釋的關(guān)系(朱永生,2001)。對(duì)于語(yǔ)篇的生成來(lái)說(shuō),照應(yīng)關(guān)系是十分重要的。韓禮德和哈桑(1976)將照應(yīng)關(guān)系分為人稱(chēng)照應(yīng)、指示照應(yīng)、比較照應(yīng)三類(lèi)。
指示照應(yīng)是由指示詞充當(dāng)支撐詞語(yǔ)構(gòu)成的指稱(chēng)關(guān)系。指示詞表示說(shuō)話者通過(guò)空間上或時(shí)間上的遠(yuǎn)近關(guān)系來(lái)確定所指對(duì)象(胡壯麟,1994)。它可以通過(guò)指稱(chēng)或替代上文內(nèi)容。因此,指示詞對(duì)于構(gòu)成語(yǔ)篇連貫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對(duì)比韓漢兩種語(yǔ)言,不難發(fā)現(xiàn),韓漢的指示系統(tǒng)并無(wú)法一一對(duì)應(yīng)。這便意味著在韓漢互譯的過(guò)程中,如果忽略?xún)煞N語(yǔ)言使用指示詞的習(xí)慣差異,一味地按照教材,將“?”對(duì)應(yīng)成“這”,將“?”和“?”對(duì)應(yīng)成“那”的話,就很容易產(chǎn)生譯文生硬、語(yǔ)篇不連貫等問(wèn)題。
一、韓漢指示詞使用特征及差異
韓漢指示體系具有較大的共性。它們之間的共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第一,都體現(xiàn)了說(shuō)話者“自我中心”的特點(diǎn)。第二,指示功能都具有體態(tài)功能和象征功能(姜美子,2016)。然而,譯者在翻譯指示詞時(shí),也要充分考慮到兩種語(yǔ)言之間指示系統(tǒng)的不對(duì)稱(chēng)性。
(一)參照點(diǎn)不同
從基本原則來(lái)說(shuō),漢文語(yǔ)篇在選用指示詞“這”和“那”時(shí),是以說(shuō)話者的位置和時(shí)間為參照點(diǎn);而在韓文語(yǔ)篇中,除了說(shuō)話者外,參照點(diǎn)還包括聽(tīng)話者的時(shí)間和位置。但在實(shí)際的語(yǔ)篇中,選用指示詞的參照點(diǎn)也遠(yuǎn)遠(yuǎn)比上述原則要更加復(fù)雜。
在實(shí)際的漢文語(yǔ)篇中,“這”和“那”可以同指于等距的實(shí)體。例如:
[例1] 他(羅杰)怕得在那里一動(dòng)都不敢動(dòng)。……在這昏暗的角落里,她(哆玲妲)的潤(rùn)澤的臉龐上,眉眼口鼻的輪廓全部鍍上了一層光,像夜明表。——《傾城之戀》P87
例1中的“那里”和“這昏暗的角落”指的是同一地方。這也就證明了,說(shuō)話者的遠(yuǎn)近并不是選用“這”和“那”的唯一原則。從上例中可以看出,第一句在描寫(xiě)羅杰的狀態(tài),而在第二句描寫(xiě)羅杰言中的哆玲妲。這種描寫(xiě)方式如同一臺(tái)移動(dòng)的攝影機(jī),改變著讀者的視角,即從原來(lái)觀察羅杰的上帝視角,再變成觀察哆玲妲的羅杰視角。因此,雖然這里的“這”和“那”都是指的是同一地方,但由于讀者的視角在改變,所以也產(chǎn)生了由遠(yuǎn)到近的效果。
而對(duì)于韓文的指示詞而言,在實(shí)際語(yǔ)篇當(dāng)中也比較復(fù)雜。當(dāng)話者選用“?”時(shí),具有很強(qiáng)的主觀性,指示的是話者認(rèn)為離自己近的對(duì)象;當(dāng)話者選用“?”時(shí)的主觀性相對(duì)較弱,指示話者、聽(tīng)者對(duì)立范圍內(nèi)的對(duì)象;當(dāng)選用“?”時(shí),指示的對(duì)象并不是話者主觀化的對(duì)象,指示話者與聽(tīng)者對(duì)立范圍之外的對(duì)象(姜美子,2016)。
(二)功能不同
漢文與韓文的指示詞都具有回指的功能,并且當(dāng)指示詞回指上文時(shí),韓漢指示詞的使用都具有兩種形式。第一是直接使用指示詞,二是指示詞與其他名字性成分回指上文(祁陽(yáng),2021)。然而,韓漢指示詞的功能也并不能完全對(duì)等。在韓文語(yǔ)篇中“?”可以單獨(dú)使用可作為人稱(chēng)代詞,而漢文的“這”和“那”無(wú)法單獨(dú)作為人稱(chēng)代詞的,漢文指示詞實(shí)現(xiàn)人稱(chēng)代詞的功能,只能通過(guò)與其他名詞的組合的形式實(shí)現(xiàn)。例如:
[例2]?? ???? ?? ???? ? ??? ?? ???? ??? ??? ???.
譯文:接著就看到那男人走向合唱團(tuán),有幾個(gè)人匆匆拿出了電話。
——《杏仁》
例2證明,雖然漢文和韓文的指示詞都可以回指前文的對(duì)象、內(nèi)容,但兩者功能并不完全對(duì)等,因此,韓漢文篇的指示詞的使用形式上也存在差異。
除此之外,漢文中的“這”和“那”在介紹某個(gè)人或說(shuō)明、辨認(rèn)某個(gè)人的時(shí)候,是可以單獨(dú)使用指代人物的。而在這樣的句式在韓文中并不存在。當(dāng)“?、?、?”用作指示代詞而非人稱(chēng)代詞時(shí),是無(wú)法指代上述人物的。如:
[例3] 原文1:這是我的朋友
譯文1:?? ?? ????.
原文2:那是我的媽媽
譯文2:?? ?? ?????.
在例3當(dāng)中,譯文1和譯文2都是不成立的。如果要想使它們成立,則必須在指示詞后添加“??”等依存名詞。
(三)使用頻率不同
漢文的指示系統(tǒng)“這”和“那”和韓文的指示系統(tǒng)“?”、“?”、“?”都存在不對(duì)稱(chēng)性。 據(jù)《漢文詞典的統(tǒng)計(jì)與分析》的抽樣統(tǒng)計(jì),“這”的使用頻率是高于“那”的。
而在韓文的指示性統(tǒng)中,“?”是遠(yuǎn)遠(yuǎn)高于“?”和“?”的。并且與“?”、“?”之間看起來(lái)是對(duì)立關(guān)系,但在實(shí)際的語(yǔ)篇使用中,“?”和“?”并沒(méi)有形成對(duì)立結(jié)構(gòu)。除此之外,“?”在語(yǔ)篇中的使用頻率微乎其微,大多都是以“?……?……”的形式出現(xiàn)。(???,2018)。
并且,除了兩種與語(yǔ)言的指代系統(tǒng)的使用頻率自身存在差異之外,還可以發(fā)現(xiàn)韓文語(yǔ)篇的指示詞使用頻率是要高于漢文語(yǔ)篇的。???(1994)曾指出,當(dāng)漢文在沒(méi)有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對(duì)象,為了文章的簡(jiǎn)潔性,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會(huì)使用指示詞。姜美子(2016)曾表示,相較韓文的指示詞“?、?、?”而言,漢文的“這”和“那”要更簡(jiǎn)單和整齊,韓文的指示詞也有著更強(qiáng)的能產(chǎn)性。
二、韓漢文篇指示詞的翻譯技巧
韓漢兩種語(yǔ)言的指示系統(tǒng)存在的差異決定了在兩種語(yǔ)言轉(zhuǎn)換的過(guò)程中,譯者無(wú)法把所有的指示詞整齊對(duì)應(yīng)進(jìn)行翻譯。因此,本文對(duì)三部韓文原文和對(duì)譯文本中出現(xiàn)的指示詞進(jìn)行了對(duì)比分析,并總結(jié)出了以下譯者在處理指示詞時(shí)的幾點(diǎn)常用技巧。
(一)轉(zhuǎn)換
轉(zhuǎn)換表示譯者跳出“?對(duì)應(yīng)這,?、?對(duì)應(yīng)那”的框架,用另一個(gè)指示詞替換原文的指示詞。由于韓漢自身指示詞系統(tǒng)的使用頻率各自不同,并且選擇指示詞的參照點(diǎn)也不相同,所以譯者經(jīng)常將原文的指示詞進(jìn)行轉(zhuǎn)換。例如:
[例4] ??? ??? ??? ? ?? ????? ?? ???? ?? ????????…
——《82年生的金智英》
譯文 :然而,如此辛苦地一手帶大的四個(gè)兒子,最終只有金智英的父親善盡兒子的本分。
例4將表示“?”翻譯成表示近指的“此”。這里的“???”是用來(lái)形容后文的“辛苦”的程度,如果在這里將“???”直譯成“那樣”,雖然從語(yǔ)法上不算錯(cuò)誤,但其修飾“辛苦”的效果不及“如此”。這是由于韓漢指示詞的表達(dá)習(xí)慣存在差異。譯者使用這樣的處理方法,即能使譯文更加貼近原文的意思,又能使語(yǔ)篇的銜接更為自然。
[例5] ???: ?? ???? ????? ??? ?????
譯文:醫(yī)生:你有嘗試努力擺脫這樣的關(guān)系嗎?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炒年糕》
在例5中,“?? ??”是用來(lái)回指上文“我”描述的“我”與“姐姐”的關(guān)系。在這里,將“?? ??”譯成“這種關(guān)系”,顯然要比“那種關(guān)系要”更加合適。這是因?yàn)樵诖饲榫罢Z(yǔ)境中,對(duì)于作為發(fā)話者的“醫(yī)生”來(lái)說(shuō),相較聽(tīng)話者的“我”而言,“我”所描述“??”是遠(yuǎn)距離的;而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自身所描述的“這種關(guān)系”是近距離,因此,在原文用“?”會(huì)比“?”更合適。而對(duì)漢文來(lái)說(shuō),選擇指示詞無(wú)需對(duì)比發(fā)話者與聽(tīng)話者的距離,所以對(duì)于發(fā)話者的“醫(yī)生”來(lái)說(shuō),“這種關(guān)系”是發(fā)話者和聽(tīng)話者在此時(shí)此刻正在交談的重點(diǎn)對(duì)象,所以在這里用“這”會(huì)比“那”要更加合適。
(二)省略
省略表示譯者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省略了原文的指示詞。韓文語(yǔ)篇使用指示詞的頻率是高于漢文語(yǔ)篇的,所以在韓漢文言的轉(zhuǎn)化過(guò)程中,如果將韓文語(yǔ)篇的指示詞全部翻譯出來(lái),就很有可能會(huì)出現(xiàn)譯文冗長(zhǎng)的情況。因此在韓漢翻譯中,譯者會(huì)習(xí)慣性省略一些指示詞。例如:
[例6] ?? ?? ??? ???? ?? ???? ?????.
譯文:唯有“家務(wù)”始終得不到大家認(rèn)同。
——《82年生的金智英》
例6中,“??”是用來(lái)替代前文的“?? ??”,而譯者卻進(jìn)行了省略。可以發(fā)現(xiàn),原文作者利用指示詞,在一句話中反復(fù)提到“?? ??”的目的是想強(qiáng)調(diào)“?? ?? ??????? ??? ??”的這個(gè)事實(shí)。而對(duì)于譯者而言,如果把這句話直譯成“唯有對(duì)于家務(wù),那個(gè)始終得不到認(rèn)可”,不僅無(wú)法起到強(qiáng)調(diào)的效果,還會(huì)使譯文冗長(zhǎng),所以譯者對(duì)指示詞進(jìn)行了省略。
[例7] ? ?? ???? ?? ?? ?? ?? ? ?? ???…?? ?? ?? ? ????? ?? ???
譯文:他對(duì)蝴蝶做出那種事后為什么會(huì)發(fā)火?……還是對(duì)事情只做一半的自己感到生氣?——《杏仁》
在例7中,原文出現(xiàn)兩次的“?? ?”指替的是同一件事。由于韓文的指示詞要比中文更加頻繁,在原文的這個(gè)地方,如果省略指示詞,則無(wú)法銜接上文。而在漢文中,此處即便不加指示詞,讀者也能通過(guò)上下文,知道下句“事情”就是上句的“那種事”。如果在將后文的“事情”也跟上文統(tǒng)一,處理成“那種事情”,反而會(huì)有種畫(huà)蛇添足的感覺(jué)。
(三)替換
替換表示譯者在韓漢翻譯過(guò)程中,用其他的表達(dá)替換原文的指示詞。由于兩種語(yǔ)言的指示詞的功能無(wú)法完全對(duì)等,并且表達(dá)習(xí)慣不同,所以譯者有時(shí)會(huì)采用替換的方式。例如:
[例8] ??? ???? ????? ???? ???. ??? ???, ??? ??? ?? ? ????, ? ??? ??? ?????? ????????.
譯文:但是奶奶從未對(duì)爺爺有過(guò)任何怨言,她真心認(rèn)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動(dòng)手打妻子,就已經(jīng)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82年生的金智英》
例8中,作者使用指示詞“? ??”,透露出了“???”評(píng)判“??? ??”的標(biāo)準(zhǔn)之低,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于這件事的態(tài)度。因此,這里將“? ??”替換成“只要”是一個(gè)很巧妙的處理手法,譯文不僅表達(dá)出了原作者在這段話中所內(nèi)涵的態(tài)度,還使得語(yǔ)篇更加通順和流暢,這是直譯無(wú)法達(dá)到的效果。
[例 9] ??? ?? ? ?? ? ???, ??? ?? ??? ??? ?????.
譯文:上次有件事沒(méi)對(duì)您說(shuō),您說(shuō)我似乎想要變成一個(gè)機(jī)器人…….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炒年糕》
在例9中,“??”指代的上一次“我”與“醫(yī)生”的見(jiàn)面,由于上一次離發(fā)話者和聽(tīng)話者的時(shí)間相等,因此,這里使用了指示詞“?”。但在這里如果譯者按照指示詞的原則,將“??”直譯成“那次”,那么讀者就很容易產(chǎn)生“那次是哪次”的疑問(wèn)。用“上次”替代,即明確了所指的時(shí)間點(diǎn),避免了指代不清的問(wèn)題,又符合了漢文的表達(dá)方式。
三、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指示詞在語(yǔ)篇的銜接上發(fā)揮著重大的作用,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如果沒(méi)有處理好指示詞,譯文也無(wú)法自然傳遞出原文的意思,所以指示詞的翻譯是一個(gè)值得被關(guān)注的課題。
本文總結(jié)出了韓文與漢文之間指示系統(tǒng)的三點(diǎn)差異。這些差異也決定了譯者在進(jìn)行韓漢互譯的過(guò)程中,不能將指示詞一一對(duì)譯。因此,本文也通過(guò)對(duì)比分析韓文作品以及它們的漢文譯文中所出現(xiàn)的指示詞,對(duì)譯者處理指示詞的技巧進(jìn)行了分析與總結(jié)。并發(fā)現(xiàn)譯者在進(jìn)行韓漢指示詞的轉(zhuǎn)換時(shí),經(jīng)常使用轉(zhuǎn)換、省略替代的處理技巧。
同時(shí),本研究的分析結(jié)果也表明,當(dāng)指示詞用來(lái)回指,形成照應(yīng)性時(shí),我們無(wú)法通過(guò)指示詞本身確定其所指的對(duì)象,而是必須要根據(jù)語(yǔ)境進(jìn)行判斷。因此,譯者在處理指示詞時(shí),應(yīng)該充分注意到兩種語(yǔ)言知識(shí)系統(tǒng)的差異,并結(jié)合上下文及情境語(yǔ)境和語(yǔ)篇語(yǔ)境。
- 河北畫(huà)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從繪本看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
- 師范認(rèn)證背景下的版畫(huà)“金課”構(gòu)建研究
——以《版畫(huà)創(chuàng)作》課程為例 - 群眾舞蹈作品創(chuàng)編分析
——以第十四屆江蘇省五星工程獎(jiǎng)舞蹈類(lèi)獲獎(jiǎng)作品為例 - 試論二十世紀(jì)藝術(shù)哲學(xué)對(duì)偶然音樂(lè)的影響
——以約翰·凱奇音樂(lè)作品為例 - 淺析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造型藝術(shù)對(duì)現(xiàn)代雕塑設(shè)計(jì)的影響
- 博物館展示空間視覺(jué)語(yǔ)言的整合設(shè)計(j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