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辨識工具的初步探析
曾祥榮 趙偉 王榮田 陳強龍 孫繼高 何海軍 譚彪 奚向宇 陳衛衡*
1.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北京 100029 2.貴州中醫藥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5 3.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北京 100102 4.北京市西城區廣外醫院,北京 100080 5.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北京 100078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一種以骨代謝失衡、骨量減少、骨折風險增加為特征的全身性代謝性骨疾病,常見于絕經后的婦女和老年男性[1-2]。骨質疏松導致骨折的發生率為7.31 %~12.2 %,然而將近一半的脆性骨折發生在骨量減少者中[3]。骨量減少作為骨量正常向骨質疏松癥發展的過渡階段,通常被患者和臨床醫生忽視,未采取有效的手段干預,直至發展成骨質疏松狀態,或進一步引起骨折,不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增加死亡風險,還給家庭和社會帶來高額的醫療支出。2019年調查結果顯示,我國40~49歲人群骨量減少率達到32.9 %,50歲以上人群骨量減少率為46.4 %[4]。本課題組前期基于德爾菲法建立了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辨識問卷[5],旨在通過具有中醫特色的篩查條目篩檢骨量減少的人群,以期為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中醫辨識提供臨床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于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和北京市西城區廣外醫院等多中心招募的接受“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辨識問卷”調查的315例受試者的問卷結果。本研究已獲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件號:WJEC-YJS-2020-025-P001)和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件號:BZYSY-KYKTPJ-22)。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年齡≥40歲,性別不限;②無意識障礙,有一定的語言表達及文字閱讀能力,與人溝通無障礙;③在充分理解研究目的和方法后,本人愿意接受問卷調查及骨密度檢測,簽署知情同意書者。
排除標準:①既往已被診斷為原發性或繼發性骨質疏松癥者;②正在服用或長期服用影響骨代謝藥物者或服用激素者;③合并有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造血系統等嚴重內科疾病者;④肝腎功能檢查結果高于正常值上限者;⑤正在妊娠階段、準備妊娠及哺乳期婦女;⑥有精神類病患者。
1.3 分組依據及診斷標準
骨密度診斷標準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標準[6]和《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治指南(2011 年)》[7]。骨量正常:T值>-1;骨量減少:-2.5 本課題組在上述3家醫院及相應區域的社區服務中心開展受試者招募以及問卷調查。問卷設計參考課題組前期運用德爾菲法建立的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辨識工具[5],中醫癥狀按“有”“無”二分類統計。所有受試者均采用雙能X線吸收檢測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進行骨密度檢測,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及北京市西城區廣外醫院使用雙能X線骨密度儀GE Lunar iDXA檢測儀,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使用GE Lunar Progidy檢測儀。檢測前需對儀器進行校正,符合質控要求后再使用,同時為了減少操作者不同而引起差異,3家醫院的BMD檢測均分別由同一名醫師操作。 本研究共收集了315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22份,最終納入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辨識問卷的受試問卷293份。293例受試者包括男性94例,女性199例,年齡在41歲至86歲之間,基線情況見表1。 表1 納入分析的293例受試者一般資料 從中醫癥狀分布頻次來看,在32個中醫癥狀中,骨量正常組中腰痛、身高變矮、健忘、畏寒4個癥狀條目出現頻率超過了30 %;骨量減少組有包括骨量正常組中出現的所有癥狀的14個癥狀條目的頻率超過了30 %,包括視物模糊、目睛干澀、腰膝酸軟、口燥咽干、遇寒痛甚、背痛、失眠、下肢拘攣、下肢困重、耳鳴。 骨量減少組中腰膝酸軟、身高變矮、下肢拘攣、倦怠乏力、多夢易驚、失眠、耳鳴、健忘、口燥咽干、視物模糊、目睛干澀中11個中醫癥狀出現頻率較骨量正常組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背痛、氣短、頭暈、腰痛、畏寒、遇寒痛甚、下肢困重、目眩、易怒、肢體麻木、駝背、足跟痛、發脫齒搖、夜尿多、脅肋脹痛、體重減輕、手足煩熱、面黃肌瘦等18個中醫癥狀的發生率也高于骨量正常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見,骨量減少組的中醫癥狀在頻數和頻率上均高于骨量正常組,其中腰膝酸軟、身高變矮、下肢拘攣等11個中醫癥狀條目可作為骨量正常人群和骨量減少人群的鑒別點。具體見表2。 表2 骨量減少組與骨量正常組中醫癥狀條目比較 調查結果顯示,骨質疏松癥組中醫癥狀出現頻率大于30 %的達到了21個,包括了骨量減少組中出現的14個中醫癥狀,還出現了氣短、發脫齒搖、多夢易驚、目眩、夜尿多、易怒、頭暈,其中腰痛、腰膝酸軟、畏寒、目睛干澀、健忘5個癥狀條目出現頻率超過50 %,而骨量減少組僅健忘和身高變矮超過50 %。氣短的發生頻率低于骨質疏松癥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骨量減少組中腰膝酸軟、畏寒、耳鳴、腰痛、目眩、發脫齒搖、多夢易驚、目睛干澀、夜尿多、納呆、足跟痛、手足煩熱、毛發枯槁、周身痛、易怒、體重減輕、背痛、遇寒痛甚、頭暈、下肢拘攣、下肢困重、健忘、面黃肌瘦、肢體麻木共25個中醫癥狀出現頻率較骨質疏松癥組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見,骨量減少組中醫癥狀在頻數和頻率上均低于骨質疏松癥組。具體見表3。 表3 骨量減少組與骨質疏松癥組中醫癥狀條目比較 我國骨量減少人群龐大[4],如果能在骨量減少階段,通過一些相關的癥狀和體征及時發現并且干預,使骨質疏松發病進程延緩,降低發病率、致殘率及醫藥費用。及早準確地篩查出骨量減少的人群顯得十分重要,然而目前臨床上篩檢骨量減少人群的相關研究報道較少,主要存在的篩查工具多側重于對骨質疏松癥的診斷,忽略了處于骨量減少的高風險人群,尤其是未見到有關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中醫篩選標準。因此,本研究采用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辨識問卷,幫助識別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可疑患者,爭取在其骨質疏松癥還未確切形成之前,積極干預,將“關口前移”,有效防止骨質疏松癥的發生。 骨骼在人的一生中總體呈現“正常-減少-疏松”的發展趨勢,人體自35~40歲開始骨量水平開始下降,在《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 年)》中,針對40歲以上人群,骨密度檢測項目已被納入了常規體檢內容[8]。根據中醫治未病理論,當存在骨質疏松危險因素或者已是骨量減少者屬于中醫“未病”范疇,在此階段早期識別及時干預即為治未病[9]。中醫癥狀的辨識過程實際也是由內而外統一的過程,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會表現出某些特有的中醫癥狀或體征。通過這些癥狀和體征,可以及早辨識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所以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防治除了重視傳統的危險因素以外,不應忽視中醫癥狀辨識。充分識別該人群的特征性中醫癥狀,并進行早期干預可達到預防骨質疏松發生的目的。有發現,下肢拘攣、身高變矮、腰背痛、腰膝酸軟可作為辨識骨質疏松癥高危因素中醫癥狀[10-12]。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所有骨量減少組中,腰膝酸軟、腰痛、畏寒、遇寒痛甚、發脫齒搖出現的頻率為40.32 %、48.39 %、40.32 %、37.90 %、29.84 %,而在骨量正常組中出現的頻率為26.27 %、38.69 %、30.66 %、28.47 %、27.01 %,發脫齒搖在兩組出現的頻率較低而且差異不大,可能尚未出現腎精不足證的相關癥狀,但腰膝酸軟、腰痛、畏寒、遇寒痛甚、在兩組中出現的頻率較大,而且隨著骨量的降低,其出現的頻率增高,可以推斷骨量正常向骨量減少過渡階段就出現了與腎虛相關的一些癥狀,“骨者,腎之合也”,腎與骨代謝密切相關、影響顯著[13],這與現代醫學認識一致[14]。 在所有骨量減少組中,下肢拘攣、目睛干澀、視物模糊出現的比例分別為35.48 %、43.55 %、45.16 %,而在骨量正常組中出現的比例僅為17.52 %、27.74 %、29.93 %,且隨著骨量的降低,出現的頻率也隨之升高。肝主筋,“肝虛則無以養筋,而筋骨攣急”,故出現下肢拘攣。腎虛日久必損及肝;而“肝開竅于目”故而出現目睛干澀、視物模糊。 在所有骨量減少組中,健忘、失眠、多夢易驚出現的比例分別為54.03 %、37.10 %、27.42 %,而在骨量正常中出現的比例僅為32.85 %、21.90 %、14.60 %,隨著骨量的減少,出現的頻率也隨著增高。由此可得,腎虛的同時也會導致心虛癥狀的在出現,因此在區分骨量正常人群和骨量減少人群時,健忘、失眠、多夢易驚著3個中醫癥狀具有一定意義。腦為髓之海,元神之府,人到中年,因臟腑功能減退,腎中精氣不足[15],無以生髓,髓海空虛,且“心之精依于腎……精髓之海,實記憶所憑也”,腎精不足則無以養心精,故而出現健忘、失眠、多夢易驚等癥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處于骨量減少組中在腰膝酸軟、身高變矮、下肢拘攣、倦怠乏力、多夢易驚、失眠、耳鳴、健忘、口燥咽干、視物模糊、目睛干澀中醫癥狀的發生頻率會高于骨量正常的人群(P<0.05),表明這些中醫癥狀可以應用于那些正處于骨量減少階段而又尚未確診骨質疏松人群的篩查中。中醫癥狀的出現可在骨密度等指標改變之前出現[16],所以監測中醫癥狀的變化可以早期識別骨量正常人群和骨量減少人群。 在本次調查中發現,骨量減少組中出現腰膝酸軟、畏寒、耳鳴、腰痛、發脫齒搖、夜尿多、毛發枯槁、遇寒痛甚的比例分別為40.32 %、40.32 %、31.45 %、48.39 %、29.84 %、21.77 %、6.45 %、37.9 %,然而骨質疏松癥組中出現的比例分別為56.25 %、56.25 %、46.88 %、62.5 %、43.75 %、34.85 %、15.63 %、43.75 %。其中骨質疏松癥組中腰痛的出現率最高為62.5 %。骨質疏松屬中醫學“骨痿”、“骨痹”、“骨枯”、“骨極”、“骨蝕”等范疇[17]。腎主骨生髓,與腎虛相關的中醫癥狀在骨量減少組中明顯低于骨質疏松癥中出現的頻率,并隨著骨量的減少而升高。腎虛是骨質疏松癥的基礎[18],根據“腰為腎之府”,故在骨質疏松癥人群腰痛的出現率為最高。 在所有的骨量減少組中,下肢拘攣、下肢困重、肢體麻木、目眩、目睛干澀的出現率分別為35.48 %、33.06 %、17.74 %、23.39 %、43.55 %,然而在骨質疏松癥組中出現的比例為40.63 %、37.5 %、18.75 %、37.5 %、56.25 %。骨量減少組中出現的下肢拘攣、下肢困重、肢體麻木、目眩、目睛干澀癥狀頻率明顯低于骨質疏松癥組,同時也是隨著骨量的減少而出現的頻率升高。另外,由于“腎為氣之根”,主氣機,行水液,并且腎主封藏固攝,腎氣足則可保持呼吸深度,不易氣短;在本次調查研究中還發現,骨量減少組在氣短的發生頻率上低于骨質疏松癥組(P<0.05)。 本研究結果顯示,處于骨量減少組在腰膝酸軟、畏寒、耳鳴、腰痛、目眩、發脫齒搖、多夢易驚、目睛干澀、夜尿多、納呆、足跟痛、手足煩熱、毛發枯槁、周身痛、易怒、體重減輕、背痛、遇寒痛甚、頭暈、下肢拘攣、下肢困重、健忘、面黃肌瘦、肢體麻木等中醫癥狀的發生頻率會低于骨質疏松癥組,表明這些中醫癥狀隨著骨量減少而增高。從中醫理論分析,這些癥狀涉及臟腑較多,特別與腎肝的關系密切,本病以腎精虧虛、骨枯髓減為本,以瘀血痹阻、骨絡失榮為標[19-20]。所以監測中醫癥狀的變化在骨量減少人群和骨質疏松癥人群也有意義。 表2結果顯示,在骨量正常人群中也存在諸多中醫癥狀,但本研究遵循嚴格的納排標準,在受試者納入本研究時,就已排除了具有明確基礎疾病或體檢異常狀態的人群,可能骨量正常組部分受試者存在著亞健康狀態[21]。亞健康狀態是指存在明顯不適和能力下降的狀態,然而未發現存在器質性病變。研究[22]表明,在亞健康人群中疲倦、目澀、頭暈、咽干、胸悶、心悸、不寐、自汗、腰部困乏、健忘出現的癥狀頻率較高,與本研究結果中骨量正常人群出現的中醫癥狀基本類似。因此在骨量正常人群中也存在中醫癥狀。本次調查研究,是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癥狀調查問卷的初步應用,旨在區分骨量正常人群與骨量減少人群,因此在調查過程中骨質疏松癥樣本量偏少,僅僅只有32例;同時本次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總體樣本量及男性比例較少,受性別偏態分布影響,未將男女分開統計;以上都是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闡明骨量不同人群的中醫癥狀發生頻率不同,中醫癥狀可以識別骨量減少人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臨床價值,調查研究的地域分布以及總體的樣本量可進一步擴大,以期更大的骨質疏松癥樣本量和更大的數據支持,值得進一步推廣。1.4 問卷調查及骨密度檢測
1.5 統計學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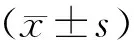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2.2 中醫癥狀在骨量減少組與骨量正常組之間分布規律

2.3 中醫癥狀在骨量減少組與骨質疏松癥組之間分布規律

3 討論
3.1 中醫癥狀辨識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必要性和意義
3.2 骨量減少人群中醫癥狀發生的頻數與頻率高于骨量正常人群
3.3 骨量減少人群中醫癥狀發生的頻數與頻率低于骨質疏松癥人群
4 不足與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