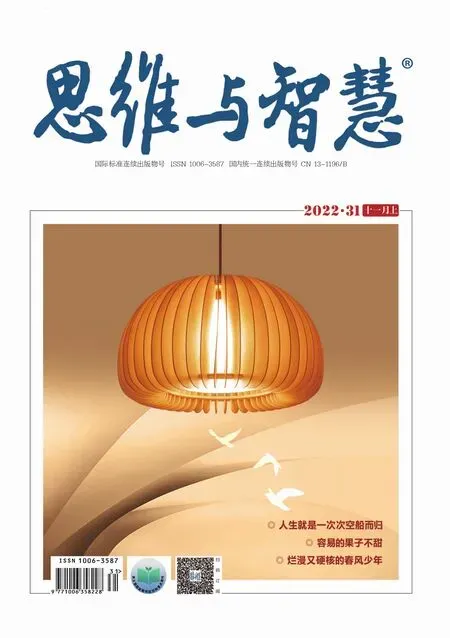生活場
◎ 姚文冬

那年去太原旅行,精神狀態、身體狀況都不錯,但下午忽然腸胃不適,晚上開始低燒。莫非中午的面不干凈?就開始服藥,飲食也倍加小心,但還是持續燒了三天。接下來雖離開山西,去了寧夏、甘肅、青海,腸胃卻一直沒有好轉。而回家的當天,癥狀戛然而止。這才意識到,我患了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原因很多,通常認為與飲食、氣候有關,令人驚奇的是,外鄉的口音也會造成水土不服。秘魯有位女作家,隨父母遷來北京,她說母親每天給花澆水,要自言自語地說一堆西班牙語,母親說,這些花只懂西班牙語,聽了不會水土不服,那些花草是隨她們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
實際上,我們的生活始終被一個氣場所籠罩,氣候、環境、飲食、風俗、口音、生活方式,等等,構成了這個氣場。我把這個氣場叫作“生活場”。生活場以自我為中心,呈放射狀,其范圍大小取決于一個人的生活半徑。這個范圍內的人、建筑、草木、街道乃至氣候、風俗,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活場,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在一座居住多年的城市,大到商場影院、街道胡同,小到常去的超市,甚至那滑梯的扶手、收銀員嘴角的一顆痣,都深深烙進我們的生活。還有小區似熟非熟的那些面孔,好聽或不好聽的聲音,撒歡的寵物狗、進出的車輛,都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通,借助時間和空間,與我們的肉體相融、與精神相通,構成了我們的生活場。居住在這個生活場,有一種自然的舒適感,即使宅在家里,不與這些事物接觸,也沒有脫離它的滋養。而一旦離開這個場,精神與肉體便會產生激烈反應。
再縮小到家庭內部,在一棟住久了的房子里,布局、家具、電器都十分熟悉,哪怕有了包漿的墩布的木柄,沙發上被煙燒掉的一個洞,還有愛人的鼾聲,孩子上學出門進門的時間點,都會讓人感到親切。在這樣的房子里生活,一進門就會自然放松。難怪工作一天的人,都愿意回家舒緩身心。人是房子的主人,也是房子跳動的心臟,人的體味、氣息、意識在屋內飄揚,養活著一座房子的精神。而在異地他鄉,即便住在豪華舒適的房子里,也不會產生這種感覺。我有個做生意的鄉親,在城里買了房子,偶爾居住,但每次都住不長,就開始想鄉村的家。按說,城里的房子也是他的家,怎么就覺得不自在呢?他說,他在城里很窒息,寂寞得要發瘋,就像胎兒失去了羊水。只因他的生活場在鄉村,在左鄰右舍的鄉音里,在泥濘的街巷里,被棗樹、榆樹和廣闊的田野籠罩著。
還有那些多年的鄰里、朋友或同事,更是我們生活場里的要素。和這些人在一起,彼此一個眼神就能會意,一句貌似普通的對話,就可能引起捧腹大笑——因為這句話里藏著一個省略掉的鋪墊,這鋪墊里有共同的記憶,所以才能引爆成一個笑話。這是一種默契,生活場以外的人則不會有感應。
那年送兒子去青島上大學,夜間在賓館,兒子忽然說:“我怎么有點想家了?”我很納悶,對他來說,家不就是父母嗎?一家人在一起,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想家從何談起?我當時以為,他是看到要離開我們了,以此表達不舍吧。后來恍然大悟,兒子說的想家,的確就是那個我們生活多年的小城,是那幢房子,還有他熟悉的街道、學校和伙伴。他驟然離開了生活17年的生活場,已經感到不適了。在自己的生活場里,有一張看不見的網把我們與周圍的一切聯系在一起,離開家鄉,是失去了這種暗物質。怪不得,后來我們去青島看他,他雖然也很欣喜,但程度卻遜于寒暑假回家。回到他曾日夜生活的房子里,即使我們不在家陪他,他依然很歡快,就像魚跳入了水里。
在一個地方遭受重創的人,比如失戀、事業失敗、人際關系惡化,都想要換一個環境,因為他的生活場遭到了破壞,短時間內不好修復,甚至永遠不能修復。為什么我們要與人為善呢?對人有禮貌,經常幫助人,每天做一件善事,當這些善意傳達出去,自我就會感覺生活被友好籠罩,被許多看不見的笑臉包圍著,那其實是在優化自己的生活場,就像給房間里布置了鮮花,人會感覺很舒服。相反,一個四面楚歌的人,會感到焦慮、煩躁,他只能去換個環境,重新開始,營造和諧的生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