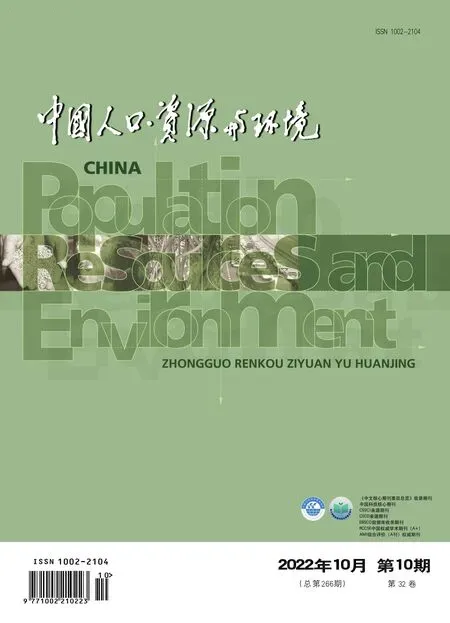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測度(2010—2019年)
王宏新,邵俊霖,,李繼霞,徐孟志,王英杰,,平澤宇,
(1.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北京 100875;2.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 100875)
自2013年起,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被世界經濟論壇連續9年列入全球五大風險之一[1]。近年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高溫熱浪、洪澇、干旱等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更是頻頻發生。未來人類面臨的將不再是小概率的“黑天鵝”式風險,而是更大概率、更大影響的“灰犀牛”式氣候風險[2]。減緩與適應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兩大主要路徑。由于氣候變化具有巨大慣性,減緩行動難以短期內消除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3];同時,目前全球“國家自主貢獻”(The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s)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各國亟須在適應領域取得進展[4]。
“適應”是系統針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化及其影響進行調整的過程[5],是氣候臨界點(Tipping Points)爆發后能夠減輕危害或利用有利機會的唯一選擇。適應和發展之間存在復雜相互作用,二者相互促進可共同推動人類社會螺旋式演進。然而,自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以來,許多部門和區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良適應(Maladaptation)和適應極限(Adaptation Limits)。不良適應是指由于計劃不周、實施不力、過于追求短期效果給目標或群體造成更大脆弱性或暴露度;適應極限即為無法通過適應行動來規避風險。不良適應和適應極限二者將打破適應和發展之間的正向互動,不僅使得適應目標面臨失敗風險[6],人類社會發展成果甚至會隨之破滅。適應必須與發展融合,在氣候變化適應過程中保障發展成果、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發展過程中避免適應不良、不斷推進適應極限。在此背景下,“適應性發展”概念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發展領域前沿熱點,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個新發展理論框架[7]。中國已在政策實踐中凸顯這一理論內涵,《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高度重視適應氣候變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部署有機銜接的重要性,將系統適應視為中國適應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該研究在闡述適應性發展內涵的基礎上,基于三個維度構建中國適應性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CRITIC法對2010—2019年間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Adaptive Development Index,ADI)進行測度,并通過Moran指數、差異系數和Theil指數方法,探究其時空特征及區域差異;結合實證分析結果,提出加快推進適應性發展政策,全面提高適應性發展水平的政策建議。
1 理論基礎
1.1 “適應性發展”的提出
適應(Adaptation)最早廣泛應用于生物學領域,泛指組織或系統為了更好地生存繁殖而不斷適應周邊環境的過程,涵蓋有機個體、單個種群及整個生態系統等不同層級[8-9]。后經不斷演化,“適應”一詞逐漸進入人類學、政治學及管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10-11]。在氣候變化應對方面,學界已從氣候變化適應類別、主體、內容、目的及特征等不同視角進行了探討[12-15]。隨著適應在氣候變化應對中的重要性逐步被認可,適應對象涉及發展中國家數十億人,而這些人本身又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捐助者制定發展政策時考慮的主要目標群體,支持發展中國家的適應往往被視為支持其發展。至此,適應與發展的關系開始引起學界關注,并形成三種觀點:第一,適應與發展相互獨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用不同資金支持氣候適應與發展項目,適應只是發展的外生變量[16]。第二,適應與發展相交疊。氣候變化適應可以增進發展,解決干旱和洪水造成的饑餓、預防和治療氣候變化帶來的病媒傳染病,有助于減少“發展成本”[17]。第三,適應即發展。對于深陷環境污染、災難頻發、資源枯竭和土地退化泥潭的窮人而言,適應問題完全是發展問題;在此情形下,適應與傳統的發展完全重合,強化資源稟賦、提升社區韌性等適應措施即是發展手段[18]。
近十年來,“適應性發展”概念逐漸走向清晰。Lemos等[19]在討論氣候變化適應如何影響發展時,首次提出了“適應性發展”(Adaptive Development,AD)的概念,認為著眼于短期的發展目標具有局限性,不切實際的適應行動有可能面臨失敗,應在發揮適應與發展二者優勢的基礎上,同步解決正在產生甚至未知的發展問題,尤其是氣候問題,實現適應性發展。Agrawal等[7]認為,氣候變化造成的風險愈加顯著,提升弱勢群體風險應對能力是“適應性發展”的應有之義。他們又進一步豐富了“適應性發展”的內涵,指出適應性發展與早期發展范式的不同之處,在于強調化解氣候變化以及不良適應能力所導致的風險,從而將風險置于適應性發展核心。Eakin等[20]、Sherman等[21]提出了同時實現適應和發展目標的路徑,即有效結合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必需的特殊能力以及實現人類發展基礎目標的一般能力。
在明確適應性發展概念基礎上,近年來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以下方面展開。一是深化適應性發展路徑研究。Tian等[22]對鄱陽湖的氣候適應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展開分析,提出適應和發展交互過程中,社會、自然與技術系統的良性互動是保障其正向協同的方式之一。Erbaugh等[23]提出混合治理,即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的參與者共同定義和實施干預是實現適應性發展的措施之一,并通過赤道地區可持續農業展開分析。Struthers[24]基于比較政治制度理論,結合智利官員對2010—2015極端干旱事件的回應策略,闡明了適應政策實現受到政黨制度、行政立法安排和選舉規則影響,政治環境是某些適應不良的直接因素,改進制度安排而不僅是更新適應技術,將有助于實現適應性發展。二是細化適應性發展領域研究。Liao等[25]細化研究了畜牧業的適應性發展策略,通過埃塞俄比亞氣候適應案例,指出種植牧草可進一步轉變牧民畜牧對象,緩解草原生態系統風險暴露的同時,保障畜牧業發展和牧民生計。Liao等[26]研究了中國新疆北部的牧民定居計劃。通過大規模調查,發現“定居”前后,家庭收入和資產持有量出現明顯下降,影響了牧民生計,未來應基于適應性發展制定有助于福祉提升的政策。Lemos等[27]建立了涵蓋水安全治理、適應能力和發展三者互動的模型,強調基于動態和不確定性進行規劃,得出不同風險組合結果可幫助決策者更好面對未來。三是在適應性發展理念指導下展開應用性研究,主要涉及指數編制。適應性發展強調在各項政策中納入應對氣候風險考量,基于此,Neder等[28]編制的城市適應指數(UAI)、Singh等[29]編制的氣候韌性農業指數(CRA),均衡量了經濟社會、制度環境等方面的基本發展要素是否可達適應目標。
目前,關于適應性發展的研究已超越學術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開始引入,適應性農業、適應性環境管理等具體實踐也大量使用[30]。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提出了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 Pathways(CRDP)概念,以描述實現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雙重目標的路徑。該報告同時指出,應強化適應與發展二者間的相互關系,通過低悔適應(Low-regret Adaptation)產生發展協同效益,通過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發展政策降低適應赤字(Adaptation Deficit)[6],這一觀點與Cannon定義高度契合。《巴黎協定》也提出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CRD,氣候適應型發展)的概念,指出“資金流動應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31]。本質上,氣候適應型發展(CRD)與該研究的適應性發展(AD)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前者強調目的和結果,面對氣候變化風險發展應該具有韌性;后者強調過程和方法,即通過適應和發展的有效結合來應對越來越大的氣候變化風險。總之,“適應性發展”對這些實踐經驗和本土知識進行了理論提升,是指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國家適應戰略)和方案設計(如基于自然的適應方案),綜合運用財政、金融、信息、技術等政策,既有效提升氣候韌性,又降低發展風險。
1.2 適應性發展內涵
人類對發展理念的認識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前,發展基本等同于經濟增長。1990年,聯合國提出“人類發展”的概念,認為人類發展不僅是收入、財富的增加,還是自身需求的不斷擴大,即獲得健康生活水平、獲得文化知識以及提高生活品質的三個基本需求[32]。人類發展的概念突破了經濟增長的桎梏,但尚未關注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發展概念的進一步提升,強調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能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33]。2015年聯合國提出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涉及169個具體目標,涵蓋經濟增長、社會包容和環境保護三大維度[34],并提出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這些目標。然而,迄今為止,世界仍未步入實現2030年目標和指標的軌道[35]。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適應性發展通過對適應與發展關系的把握,以風險管理為視角,運用系統耦合理論,可以更好地實現應對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的協同。準確把握適應性發展的內涵,需從以下四方面著手。
第一,正確認識適應與發展之間的復雜交互。一般而言,適應與發展可以相互促進。例如,通過改進水文氣象服務,中、低收入國家每年可挽救2.3萬人,帶來至少1620億美元的潛在經濟社會收益[36]。但需注意的是,發展并非一定意味著適應能力的提升,適應策略也有可能損害發展。例如,如果當地居民沒有投資于正確的風險管理策略,減貧成效顯著的地區脆弱性就未必會降低[37]。若采取激進的適應策略忽視原住民生計的“土地掠奪”,則將加劇社會矛盾[38]。這種復雜交互為適應性發展概念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第二,適應性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在目標上具有同構性,且適應性發展更具動態性。聯合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目標13”直接表達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除此之外,適應性發展還有助于實現其他12個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目標[39]。反之,“優質教育”(目標4)、“性別平等”(目標5)、“減少不平等”(目標10)、“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目標16)等可持續發展目標又是實現適應性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可持續發展的所有目標都能找到與適應性發展的對應。同時,由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以過去和現在的氣候背景為基礎,較少考慮未來幾十年到一百年全球變化的趨勢,因而難以突破其靜態局限性[40]。相比之下,適應性發展含義本身卻具有動態演化的特征,可以讓人們更加聚焦未來變化,從而采取更具戰略性和靈活性的發展舉措。
第三,適應性發展的核心視角是風險管理,根本方法在于系統耦合。以往的發展政策往往與具體目標聯系在一起,如通過經濟增長實現減貧、通過再分配促進平等、通過可持續資源利用保護環境。適應性發展概念則將風險管理作為核心目標,在適應過程中實現增長、公平和可持續,在發展中緩解氣候變化風險[11]。要充分實現氣候變化適應與發展的協同,必須借助系統耦合相關理論和方法[41],重視不同部門、層級、地區及不同時空尺度間的相互影響,開展整合性規劃、管理。
第四,適應性發展既有局域性,又有全局性,因而必須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實施路徑。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兩種方式中,人們往往因減緩針對整個地球氣候系統而認為其具有全局性,適應只針對具體地區、部門,則將其框定在局域范圍[42]。事實上并非如此,適應性發展兼具局域性和全局性兩種屬性,某一具體地區乃至全球,某一具體領域乃至所有行業系統,都可以實現適應性發展。因此,適應性發展的實施路徑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宏觀把控,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創新政策:前者從整體出發制定適應性發展戰略目標和藍圖,減少不同部門、層級或時空尺度的權衡取舍,防止政策沖突;后者則從基層實踐者出發,充分結合本土知識和區域實際,避免政策在地方層面產生適應不良。
1.3 指數測度
發展指數測度問題一直是各界關注的核心。聯合國從預期壽命、教育水準和生活質量三個維度設計了人類發展指數(HDI)[43];李曉西等[44]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兩大維度、12個綠色發展領域對各國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算;Xu等[45]度量了2000—2015年中國及各省份可持續發展指數并研究了其時空差異;此外,民生發展以及其他分領域發展指數也都可為測度適應性發展指數提供借鑒[46-49]。
適應性發展指數測度相關研究,尤其暴露性、脆弱性、復原力等適應性發展關聯要素的量化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如Monterroso等[49]運用風險暴露指數(Risk Exposure Index,REI)測量墨西哥地區的暴露性水平;Summers等[50]從自然環境、社會、建筑環境、治理、風險五個維度提出氣候韌性篩選指數(Climate Resilience Screening Index,CRSI);Azam等[51]參考IPCC脆弱性框架和可持續生計框架計算生計脆弱性指數(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LVI);吳紹洪等[52]認為適應是氣候變化風險管理的主要目的,從致險因子的危險性、承險體的暴露度與脆弱度出發,構建突發氣候事件和漸變氣候事件風險定量評估方法;葛詠等[53]基于“危險性-暴露度-脆弱性”風險評估框架,構建多尺度極端氣候風險評估技術體系,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極端干旱、極端降水、高溫熱浪、風暴潮4類代表性極端氣候風險進行了評估。當前尚無適應性發展指數的測度研究,集中于發展指數或氣候變化適應測度,無法反映適應與發展的復雜相互作用,且在適應能力的指標選擇上僅從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層面著手(一般能力),未考慮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特殊能力。該研究在充分借鑒已有研究基礎上,從適應性發展內涵出發,創新構建中國適應性發展測度指數,為豐富適應性發展理論和應用研究提供參考。
2 評估框架
2.1 研究區域概況
該研究以中國31個省份為研究區域。限于數據可得性等原因,研究未涉及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中國跨緯度較廣(近50°),距海遠近差距較大,加之地勢高低不同,地形類型及山脈走向多樣,形成了復雜多樣的氣候類型,孕育了豐富的農作物與動植物資源,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然而,復雜多樣的氣候類型也存在諸多不利方面,特別是近年來,頻發的高溫、寒潮、熱浪、干旱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正越來越危及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該研究除了對中國31個省份適應性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外,還將對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區域進行進一步研究(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0省份;東北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2省份)。
2.2 指標體系構建及解釋
科學構建適應性發展指標體系,應考慮省域氣候條件、發展方式、治理能力等要素間作用機制,關注指標的系統性與邏輯性。適應性發展水平測度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以氣候變化適應為中心點展開。依據IPCC[54]歷次評估報告、殷永元等[55]和Polsky等[56]的相關研究,ADI應從暴露度、敏感性和適應能力三個一級指標著手。每個一級指標下都包含氣候變化及其適應相關指標和發展相關指標,以充分反映適應與發展的相互關系,體現適應性發展內涵。暴露度下設“氣候系統”和“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兩個二級指標,從主客體兩方面反映氣候系統本身變化及其作用對象暴露于氣候變化的全貌;敏感性下設“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兩個二級指標,從氣候變化對人類發展物質基礎和發展成果兩方面的影響表征敏感性;適應能力下設“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兩個二級指標,全面涵蓋適應性發展能力指標[54]。在上述三個一級指標下,按照科學性、系統性、可量化性與可比性的原則并結合中國省級發展實際,構建出6個二級指標、33個三級指標(表1)。

表1 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評估指標體系及權重
2.2.1 暴露度
暴露度(Exposure)是系統暴露于顯著氣候變化的性質和程度,即人員、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統、環境功能和服務以及各種資源、基礎設施或經濟、社會或文化資產處在有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位置,如有多少人生活在可能被海平面上升淹沒或受到沿海風暴變化影響的地區。暴露度設立“氣候系統”和“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兩個二級指標。其中,“氣候系統”的量化指標通常包含溫度、降水、風速、極端氣候頻次和強度。當氣候變化達到或超過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的承受能力時,將催化氣候災害產生[57]。一般來說,氣候變化越快,強度越大、頻率越高,則地區暴露度越高。年平均氣溫、年降水量、風速、極端氣候發生頻次及強度應當納入氣候系統暴露度指標。考慮到各省風速、極端氣候發生頻次及強度不可獲取,該研究以年平均氣溫與年降水量2個三級指標表征氣候系統暴露度。“經濟-社會-生態系統”是人類及其活動所在的社會與各種資源的集合,是氣候變化作用的對象[58]。氣候變化尤其是極端氣候對經濟-社會-生態系統的影響表現在經濟損失、人口傷亡和物種滅絕等[59]。一般來說,地區燈光指數高、人口撫養比高,則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員范圍更廣,社會經濟損失也更大。此外,植被覆蓋率增加能降低氣候變化對地區的影響[60]。因此,該研究采用地區燈光指數、人口撫養比、NDVI指數(植被歸一化指數)3個三級指標評價經濟-社會-生態系統暴露度。
2.2.2 敏感性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不同人類系統和部門受到氣候相關災害的影響程度,強調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如作物產量或徑流的變化[50]。敏感性通過氣候變化影響和災害導致系統變化兩方面體現[61]。參考人類綠色發展指數指標體系并結合中國實際[40],確定“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2個二級指標。其中,“資源環境”考慮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環境和森林系統的影響,以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空氣質量指數、林業有害生物發生率3個三級指標表征;“經濟社會”考慮氣候變化對經濟、人口、農業和健康的影響以及極端氣候造成的人、財、物損失[62],以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自然災害受災人口占比、農作物受災面積占比3個三級指標表征。慢性病發病率(心血管疾病)、蟲媒傳染病發病率、氣候災害導致停工停產/停課數(天)、停電/氣/水的次數/時長/影響范圍與道路毀壞面積占比等數據納入“經濟社會”二級指標,由于數據可得性限制,暫未納入核算。
2.2.3 適應能力
適應能力(Adaptive Capacity)是決定適應性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19]。IPCC將適應能力定義為某個系統、機構、人類及其他生物針對潛在的損害、機遇或后果進行調整、利用和應對的能力[26]。Eakin等[20]認為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有兩種形式,即與基本人類發展目標相關的能力(一般能力)和與管理氣候變化風險所必需的能力(特殊能力),并指出適應性發展就是要在不同時空尺度實現一般適應能力和特殊適應能力的結合。其中,“一般能力”表現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構成適應氣候變化的社會基礎,包含節能環保財政支出占比、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建成區綠地覆蓋率、自然保護區面積占比、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技術人員、養老保險參保率、就業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互聯網普及率、R&D經費投入強度、R&D人員全時當量等11個三級指標;“特殊能力”反映預防、響應、恢復氣候災害和長期變化的直接措施,包含水土流失治理面積占比、林業有害生物防治率、堤防保護人口占比、每百萬人救災儲備機構數、節水灌溉面積占比、氣象觀測站密度、氣候預測產品得分、萬人氣象科研課題、氣候科技經費占比等9個三級指標。應急避難場所密度、農作物多樣化指數(綜合指數)、慢性病治愈率、蟲媒傳染病治愈率納入特殊能力二級指標,因數據可得性限制,暫未納入核算。
2.3 計算方法
2.3.1 適應性發展水平測算
該研究采用Diakoulaki等提出的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為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評估指標體系各級指標進行賦權,并計算綜合得分。CRITIC法根據指標間對比強度和沖突性的乘積客觀確定權重。其中,對比強度是指同一指標在不同評價對象間取值波動程度,以變異系數表示,變異系數越大,對比強度則越大;沖突性則以指標間相關性為基礎,在數據正向標準化前提下,引入指標間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越大,沖突性則越低。
對于多指標綜合評價體系而言,指標間不可避免存在相關關系,該研究在構建指標體系時已對強相關關系的指標進行剔除處理。同時,CRITIC法引入了沖突性的概念(在變異系數一定時,指標間沖突性越小,權重越小;沖突性越大,權重越大),進一步糾正了指標相關性對評價結果造成的影響。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1)指標標準化。各項指標單位不同,無法進行統一計算,因此采用Min-Max方法對所有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使評估結果處于[0,1]區間內。

其中:Sqc是第c個省份第q個二級指標進行Max-Min歸一化的值,Zqc是第c個省份第q個二級指標的z值得分,maxZq、minZq分別代表所有省份第q個三級指標z值得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計算第q個指標的對比強度dq:

其中:σq為第q個指標取值的標準差,Xˉq為第q個指標取值的均值。
(3)計算指標間沖突性Cq:

其中:rtq為第t和q個指標間相關系數。
(4)計算指標權重Wq,得出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各級指標權重見表1。

(5)計算綜合指數。采用線性綜合方式計算ADI得分。

2.3.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為探索ADI指數的空間相關關系,該研究使用Moran指數(Moran’sI)進行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ESDA是指在不對數據進行任何先驗判斷或前提假設的背景下,將地圖、圖表、圖形等可視化技術與空間統計學理論相結合來診斷所計算的數據結果是否具有空間相關特征,也即用于檢驗地理空間中某一現象和其相鄰單元的屬性值是否存在顯著性關聯或呈現為某種空間分布模式[63]。Moran指數計算方式如下[64]。

其中:n為空間單元數量,xi和xj分別代表空間要素x在空間單元i和j中的值,xˉ為要素x的均值,wij為空間權重矩陣。Moran’sI∈[-1,1],當Moran’sI>0時表示各地區呈正相關,當Moran’sI=0或者接近0時表示各地區空間上不相關,當Moran’sI<0時表示各地區呈負相關。
2.3.3 區域差異測度
(1)變異系數。為了初步考察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的差異及變動趨勢,計算各區域適應性發展指數的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簡稱CV),公式如下:

式中:ADIn,t表示n省在t年的適應性發展指數,ADIt表示所有省份適應性發展指數平均值,CV反映適應性發展指數的相對差異程度:CV值越大,說明不同區域間適應性發展指數差距越大;若CV值呈下降趨勢,則說明不同區域間適應性發展指數差距在縮小。
(2)Theil指數。該研究用Theil指數衡量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ADI)的區域差異。由于Theil指數具有可加性,區域整體差異可分解為區域間差異和區域內差異。具體步驟如下。
①總體Theil指數(TL)衡量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區域整體差異:

②以區域間Theil指數衡量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的區域間差異:

③以區域內Theil指數衡量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的區域內差異:

其中:y表示各省適應性發展水平,n為省份數量,nk為k區域內省份的數量。
④用區域間Theil指數與區域整體Theil指數的比值,即(10)/(9)表示區域間差異對區域整體差異的貢獻度;同樣,用區域內Theil指數與區域整體Theil指數的比值,即(11)/(9)表示區域內差異對區域整體差異的貢獻。
為保障數據科學、準確,該研究采用數據全部源自中國公開出版的年鑒或者相關部門公布的權威數據。原始數據主要源自《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氣象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水利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林業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其中,個別年份、個別省份缺失數據,均采用TREND函數法進行補齊處理。
3 測度結果與分析
3.1 ADI時間演變
采用CRITIC法測算2010—2019年中國ADI狀況以及維度水平(圖1),呈現出如下特征。

圖1 2010—2019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及維度水平
(1)ADI整體較低,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10—2019年中國ADI均處于<0.5的較低水平,適應性發展水平尚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具體來看:2010—2013年,中國ADI增長較快(2.9%),波動性較為明顯;自2014年起,中國ADI呈現增長趨勢(2016和2019年除外),增速較為平緩。經濟社會發展提升了整個社會應對氣候風險能力,但也促使更多人員財產暴露于氣候災害之下。
(2)ADI三大維度發展趨勢差異顯著。具體來看,暴露度得分從2010年的0.1355下降至2019年的0.1309,暴露度增加3.39%,氣候變化致災風險提升;敏感性得分從2010年0.1210下降至2019年的0.1197,敏感性增加1.07%,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受氣候變化影響程度擴大;適應能力從2010年的0.4718上升至2019年的0.4755,上升了0.7%,呈穩步發展態勢。總體上,中國氣候變化適應能力雖有所提升,但其提升速度明顯低于氣候變化程度。
3.2 ADI空間特征
3.2.1 區域特征
適應性發展水平呈“東部>中部>東北>西部”特征,且區域差距在縮小(圖2)。2010年ADI區域差距主要是東部(0.5399)和西部(0.4205)造成,差距達0.1194;2013年東西部差距達到頂峰(0.1324);2013年后差距不斷縮小,2019年差距最小(0.0906)。從區域內部變化趨勢來看,東部地區ADI較為穩定,十年間無明顯變化;東北和中部地區ADI基本呈現波動下降趨勢,東北下降幅度更顯著;西部ADI雖然整體較低,但呈現出穩步增長趨勢。

圖2 2010—2019年中國四大區域適應性發展指數
ADI三大維度發展水平區域差異較大(圖3)。2010、2015和2019年四大區域暴露度水平都呈現“西部>東部>東北>中部”特征,且暴露度略有增加。西部地區暴露度水平整體高于其他三個區域,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區氣候條件較為惡劣。2010、2015和2019年四大區域敏感性水平基本呈現“中部>西部>東北>東部”特征。中部地區敏感性整體相對較高,且呈波動上升趨勢,氣候變化不斷加劇帶來的影響逐漸加重。2010、2015和2019年四大區域適應能力水平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的特征。東部地區適應能力顯著高于其他區域,主要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基礎設施完善、災害應急體系完整,能較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影響。
3.2.2 省份特征
進一步探究各省份ADI時空集聚特征,將各份ADI分為高水平(ADI>0.5)、中等水平(0.5≥ADI>0.45)、低水平(ADI≤0.45)3個 梯 隊。利 用ArcGIS 10.8軟 件 繪 制 了2010、2015及2019年中國省級ADI的時空分布圖,分別代表該研究起始、“十三五”收官以及該研究結束之年的各級ADI空間分布情況(圖4)。

圖4 2010、2015和2019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及維度得分空間分布
2010年,各省份ADI一、二、三梯隊數量為“9、10、12”。第一梯隊的9個省份,除中部河南省外,其余8個省份均位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較為發達,為應對氣候變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二梯隊的10個省份,東、中、西部數量分別為3、3、4,分布較為均勻。第三梯隊的12省,集中分布于西北和西南等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地區。這些地區本身易受氣候災害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條件進一步限制了其適應能力,導致ADI整體水平較低。2015年,各省份ADI一、二、三梯隊數量為“12、7、12”。第一梯隊省份的數量擴展到了12個,重慶、四川、陜西、海南和福建進入第一梯隊,原第一梯隊的河南和河北則退居第二梯隊,第三梯隊數量及省份分布整體變化不大。2019年,三個梯隊數量為“9、10、12”,梯隊分布與2010年一致。其中,重慶、四川和陜西回歸第二梯隊,海南退居第三梯隊。
為深入探究不同ADI水平的維度特征,根據前文測度的2010—2019年31個省份共310個變量的暴露度(E)、敏感性(S)、適應能力(AC)以及氣候風險(暴露度+敏感性,E+S)數據,繪制pairplot圖(圖5)。
位于對角線的四個曲線子圖顯示了三種適應性發展水平在暴露度、敏感性、氣候風險、適應能力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高、中ADI在暴露度、風險維度上具有相似分布,E(H)與E(M)均集中于0.15左右,E+S(H)與E+S(M)均集中于0.29左右,低ADI在這兩個維度均具有兩個峰值,分布也較高、中ADI更加廣泛(圖5-1.1和3.3);中、低ADI在敏感性上具有相似分布,S(M)與S(L)均集中于0.13左右(圖5-2.2);高、中、低ADI在適應能力維度分布差異顯著,AC(H)、AC(M)、AC(L)峰值分別出現在0.15、0.21和0.3附近(圖5-4.4)。
進一步分析圖5-4.3,高、中ADI面臨風險都較低,但高ADI普遍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適應能力與風險的相對影響則決定了中、低ADI的劃分。因此,適應能力是造成省級適應性發展水平差異的主要原因,提高適應性發展水平必須努力提高適應能力。此外,暴露度、敏感性、適應能力兩兩之間的線性相關程度都不顯著(圖5-2.1、4.1和4.2),進一步印證了維度設置的科學性。

圖5 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三種等級pairplot關系圖
3.2.3 空間相關關系
2010—2019年31省份ADI的Moran指數均大于零,且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其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適應性發展在空間分布上并不是隨機的,而是呈現出一定的集聚效應,即ADI較高的省份被其他ADI較高的省份所包圍,相對較低ADI的省份被較低ADI的省份所包圍。同時,一個省份ADI不但會受到自身環境影響,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圍其他省份輻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科技發達程度、產業空間布局和環境政策等都會進一步增強各省份適應性發展之間的空間相關性。
2010—2019年31省份ADI的Moran指數整體呈現波動趨勢。具體而言,由2010年0.1418下降到2012年的0.1132;2013年出現了增長到了0.1912;2014—2018年出現持續下降;2019年又出現上升趨勢且高于2010年(表2)。

表2 2010—2019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的Moran指數
在空間分布上在創建鄰接權重矩陣后,Geoda軟件自動生成Moran散點圖,Moran散點圖主要分為“高-高(HH)、低-低(L-L)、高-低(H-L)、低-高(L-H)”四個象限(圖6)。“高-高”和“低-低”分別表示ADI高(低)的省份其周邊省份ADI也較高(低),“高-低”和“低-高”表示ADI較高(低)的省份其周邊省份的ADI較低(高),從而表征相鄰省份ADI具有差異性。運用Geoda軟件計算2019年中國ADI的Moran指數(0.1587),輸出其Moran散點圖(圖6)。可以看出,中國各省份ADI存在空間正相關關系。

圖6 2019年中國省際適應性發展指數Moran散點圖
3.2.4 區域差異及其分解
利用變異系數、Theil指數模型可測度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區域總體差異、區域間差異和區域內差異(圖7、表3)。

表3 2010—2019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Theil指數及其分解
從全國層面看,適應性發展指數的變異系數較大,整體變化較小(圖7)。2017年差異最大(0.0725),2018—2019年逐漸回落到0.0632的最低水平。全國ADI變異系數較大,可能由于各區域間ADI差異較大。東部適應性發展指數的變異系數最大,呈現波動上升趨勢;西部適應性發展指數變異系數較大,呈下降趨勢;東北適應性發展指數中等,呈現波動上升趨勢;中部地區適應性發展指數變異系數最小,近年來呈穩步上升趨勢。整體而言四大區域適應性發展呈現出“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發展態勢。此外,區域內部差異也可能是成因之一,需進一步探討四大區域適應性發展指數區域差異。

圖7 2010—2019年中國四大區域適應性發展水平變異系數
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總體區域差異呈現波動變化趨勢(表3)。2010—2014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總體區域差異基本呈現增長趨勢;2015年出現較大下降,總體區域差異僅為0.0093;2015—2017年又繼續呈現上升趨勢,2017年差異達到最大0.0111;2017—2019年出現下降趨勢,且2019年區域總體差異降到最低,僅為0.0086。將總體差異進行分解,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區域間差異整體呈現縮小趨勢,而區域內部差異則與總體區域差異一致,呈現波動變化趨勢,但其對區域總體差異貢獻率不斷提升。具體而言,2010—2015年基本處于區域間差異大于區域內差異的階段(2014年除外),區域間差異對區域整體差異起主導作用;2016—2017年區域內差異開始不斷增加,并超過區域間差異;2018年區域間差異再次超過區域內差異;2019年區域間差異小于區域內差異,區域內差異逐步成為區域整體差異的關鍵。
進一步分解區域內差異,四大區域內部差異基本呈現“西部>東部>東北>中部”的排序。具體而言,西部地區除2019年外,區域內部差異均位于四大區域之首;中部地區除2010年和2015年外,區域內部差異均位于四大區域之尾;東部和東北部區域內部差異變化較大,且整體呈現擴大趨勢。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該研究基于2010—2019年31省份統計數據,從暴露度、敏感性和適應能力3個維度詮釋適應性發展理念,在此基礎上構建了適應性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CRITIC綜合評價和Moran指數、差異系數和Theil指數方法,探究了中國適應性發展指數(ADI)的時空特征及區域差異。研究發現:①ADI整體較低,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10—2019年ADI綜合得分均低于0.5的較低水平。其中,2010—2013年ADI雖實現了較快增長(2.9%),但波動性較為明顯;2014年起,適應性發展指數呈現增長趨勢(2016和2019年除外),但增速較為平緩。②與2010年相比,2019年暴露度提高3.39%、敏感性提高1.07%、適應能力增強0.7%,適應能力提升較慢。③適應能力是造成ADI水平差異的主要因素。④四大區域ADI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特征,差距在縮小。Moran指數測算結果也表明,31省份適應性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全局空間正相關關系。
提高適應性發展整體水平以及各一級指標水平,推進中國區域適應性發展水平協同提升,是實現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保證綠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基于生態文明建設系統工程論,樹立復雜系統理念,推進中國適應性發展頂層設計。當前,中國適應性發展綜合得分處于低位,近10年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均位于0.5以下,且2019年僅比2010年上升0.78%,仍處于較低水平。2019年仍有70%以上的省份處于中低水平,亟須從國家戰略高度予以重視。適應性發展是一個涉及多領域、多主體的復雜的系統工程。一方面,應加快推進國家氣候變化適應戰略制定,以生態文明建設系統工程論為指導,統籌目標系統、空間系統、時間系統、合作系統,以整體論思維實現氣候變化適應與高質量發展系統耦合。建議兼顧多領域、多主體,成立國家適應智庫,為適應戰略制定提供專業科學理論,定期評估國家適應性發展進展,向決策部門和社會發布專業咨詢報告。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中,完善氣候變化適應法律體系建設。健全完善生態文明建設質量目標責任體系,尤其明確各職能部門的氣候適應權責,進一步細化政策領域和責任部門,明確定期考核指標。另一方面,注重氣候適應科技研發與成果轉化,加大適應性發展領域的相關知識、技術和資金支持力度,實現創新驅動適應性發展。具體地:加快多渠道適應科學普及和知識共享,高效宣傳適應性發展理念;分行業、分區域、分類別地建立健全適應技術體系和標準;實施稅收減免和多樣化的適應金融手段,形成多資本協同發力。此外,應推動適應性發展國際合作納入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格局,踐行生態環境全球治理觀,在綠色“一帶一路”和“南南合作”框架下,通過國家間科研單位、企業、NGO等主體間合作,提升中國在適應性發展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第二,發揮優勢補齊短板,關注適應行動關鍵領域。中國適應性發展的暴露性、敏感性和適應能力3個一級指標的發展并不均衡。當前中國適應性發展的優勢在是中國幅員遼闊、氣候條件復雜多樣、氣候災害多發基本特征的體現。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宏觀政策制定和實施中,要著力建立健全氣候變化影響關鍵領域的防災減災體系建設,如農業、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和衛生健康等。其中,農業領域受氣候影響較大,開展適應行動容易取得成效。結合鄉村振興戰略,一方面,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為綠色農業、智慧農業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將抗逆品種的培育轉化作為重點之一,促進農作物多樣化種植。水資源領域也是適應性發展的核心領域之一。中國不僅嚴重缺水,水資源污染也相當嚴重,應加快節水和排污技術發展,合理利用雨水,淡化海水,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此外,生物多樣性、衛生健康等領域也亟須開展相關適應行動,以減輕脆弱群體暴露度,提高地區適應性發展水平。
第三,積極推動適應性發展融入區域重大發展戰略和協調發展戰略。當前中國區域適應性發展水平,除東部多個省份處于第一梯隊外,中西部及東北地區都位于二、三梯隊的中低水平。適應性發展區域間差異出現縮小趨勢,但區域內部差異變化不一(東部基本穩定、東北和中部地區下降、西部上升),制約了中國整體適應性發展水平提升。建議將區域適應能力協同提升、適應性發展水平協同增長作為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的關鍵目標,在深入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區域重大戰略的過程中,全力推動區域發展與氣候變化適應實現良性互動。具體來說,東部地區應在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同時,進一步發揮地區適應性能力較高的優勢,推動適應性發展效果外溢,優化資源配置,形成可借鑒的發展模式,充分體現東部地區的動力源作用;東北地區適應性發展的突出短板在于適應能力不高,應利用東北振興戰略機遇,轉變發展模式,提升地區發展質量,提升一般適應能力和特殊適應能力;中部地區敏感性較高,氣候災害對于地區經濟、社會和生態發展影響嚴重,應做好災害預測與監控、普及農業保險等,以實現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開創中部崛起新局面;西部地區暴露度、敏感性均較高,且適應能力不足,應結合當地自然地理特征,抓住國家深入實施一批重大生態工程的契機,加強氣候變化影響觀測評估,優化生態產品供給,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在發展中提升適應能力。
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65]。在2021年“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習近平強調,“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66]。將氣候變化適應與發展相結合,是新時代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抉擇。在邁向“30·60”目標、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疊加鄉村振興、地區協同發展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立足中國測度適應性發展水平,將為中國提高氣候韌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合作引領全球氣候治理、推動全球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構建提供借鑒。該研究深化了適應性發展理論研究,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國家重大戰略要求相結合,為科學制定中國各地區適應性發展政策提供了決策依據。文章從暴露度、敏感性和適應能力三個維度測度了中國適應性發展水平,由于部分數據缺乏,指標選取受限,ADI評估指標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縱橫交錯的經濟、社會、生態等系統性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國ADI時空演變特征,對于其因果機制,將開展專門研究以挖掘適應性發展時空分布機理。由于不同地區適應目標、評價標準不同,跟蹤適應性進展是一個世界級難題,將于下一步研究中,探索推廣本評價指標體系到全球尺度、推動適應性發展理論和應用研究在國際層面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