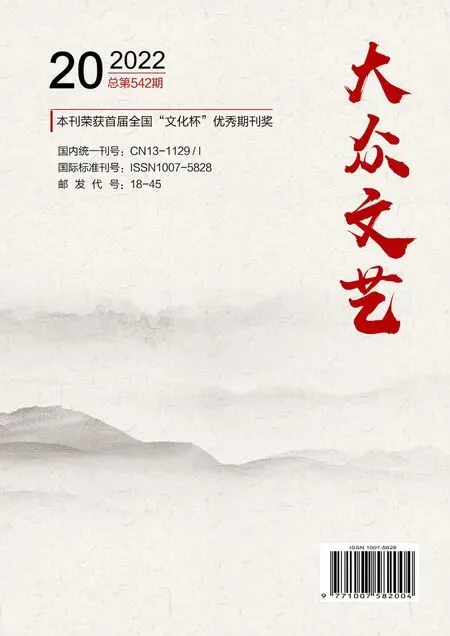靜止、循環(huán)與裂變:當代性視域下美術館影像中的時間性
劉佳郡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1331)
美術館以時間為基礎的影像藝術(Movingimage Art),在對時間的處理上顯示出與電影很大的不同。相較于電影以“進步觀”為導向的線性時間,對時間的消極處理成為人們對影像藝術的普遍印象。在媒介屬性上,克里斯·米安德魯斯以“臨時性”“瞬間性”與“非永久性”概括了影像藝術難以保存的媒介特性;而在對時間的確切表達上,漢斯·貝爾廷亦指出影像藝術“艱澀的記錄性”給傳統(tǒng)藝術史工作帶來的障礙;在大衛(wèi)·安提因那里,影像藝術對敘事時間薄弱的控制能力,“使即使是最短小的錄像作品,也總被人們描述為‘冗長或者無聊’”。然而,影像藝術這種消極的時間性卻在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藝術實踐中被視為一種優(yōu)勢,大衛(wèi)·A·羅斯將其視為一種“純粹的快樂”,相較于被學院標準束縛的古典藝術和背負著未來烏托邦宏大愿景的現(xiàn)代藝術,“視頻沒有任何正式的責任需要承擔。”
正如吉爾·德勒茲試圖在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電影中尋找具有生命時間之異質(zhì)性、非時序性和生成性的時間-影像,對美術館影像時間性的考察,不能在現(xiàn)代敘事對時間的線性構想中進行,必須引入另一種“當代性”的視角。本文將從對“現(xiàn)代線性時間”的反思出發(fā),對美術館影像區(qū)別于電影的三種時間策略進行檢視和梳理,在一個“當代性”的視野中考察這種“消極”的時間策略對“現(xiàn)代線性時間”的重審。在“現(xiàn)代線性時間”的慣性之外構建對時間的當代性思考。
一、“當下”的重思:從運動到靜止
現(xiàn)代性的核心在于運動,電影作為一種典型的現(xiàn)代化產(chǎn)物,從一開始就與運動聯(lián)系在一起:它捕捉一切運動中的事物,通過圖像的運動呈現(xiàn)自身。在好萊塢的電影敘事中,“世界必須處于時間中并經(jīng)歷顯著改變。”電影將現(xiàn)代性關于變化與行動的意識根植在人們心中,對一個典型的現(xiàn)代人來說,靜默地等待是難以忍受的。然而,正如鮑里斯·格羅伊斯在《時代的同志》里指出的,“和傳統(tǒng)藝術形式相比,正當電影是對運動的褒揚時,它也矛盾地把觀眾推向生理靜態(tài)的新極端。”面對圖像的更迭,人們什么也不用做,意識所經(jīng)歷的時間完全被圖像的運動所取代。
在道格·艾特肯的《電子化地球》中,鏡頭跟隨一位黑人男孩夢游般的舞蹈,呈現(xiàn)了一個由自動技術所驅使的現(xiàn)代社會。在這里,馬路上的信號燈、自助洗衣房的洗衣機、超級市場的自動結算機都在一個電子信號均質(zhì)化的節(jié)奏中井然有序地運轉。與這種持續(xù)的運動狀態(tài)相對的是,城市的空間空無一人,被一種無生命的靜止籠罩。夢游男孩在電子節(jié)奏機械的滴答聲中麻木的舞蹈,如同被某種程序所驅動。正如運動本身是包含著靜止的運動,永恒的同質(zhì)運動只會使意識陷入自動化的靜止當中。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談到,在波德萊爾論康斯坦丁·蓋伊的文章《現(xiàn)代生活的畫家》中,現(xiàn)代性是同凝固于僵化傳統(tǒng)中、意味著無生命靜止的過去相反的,對轉瞬即逝的感官現(xiàn)實的企圖,是用變化的人的思考代替靜止的神的意志,即從“靜止”到“運動”。然而,當大眾媒體鋪天蓋地的運動圖像將“變化”固化為一種永恒狀態(tài)時,“變化”便又成為對“靜止”的回歸。
美術館影像在大眾媒體無休止的圖像運動中引入靜止,促發(fā)對時間運動的重新考量。作為影史中探索極端靜止的案例,居伊·德波的《為薩德疾呼》用影像的純粹靜止打斷了觀眾對運動圖像的迷戀,質(zhì)疑執(zhí)意“求新求變”的現(xiàn)代時間觀念。當觀眾帶著對電影的傳統(tǒng)理解進入放映廳,期待由流暢的圖像運動喚起的心靈之旅,等來的卻是全程靜止的空白畫面,他的期待落空了,認知也土崩瓦解。通過“靜止”,德波在以運動為基礎的影像中制造了利奧塔所說的“事件的時間”,在這里,影像飛速運作的“機械時間”冷卻下來,觀眾附著在影像上的“意識時間”也冷卻下來,作為運動最陌異的形式,打斷了現(xiàn)代性對運動與變化不假思索的習慣。
居伊·德波以“事件”方式制造的突然靜止在現(xiàn)代觀看者中產(chǎn)生了一種驚異效果,雖然這個短暫的停頓在大眾媒體飛速更迭的圖像中被迅速淹沒,但由停頓觸發(fā)的反思卻影響了一批批60年代的影像創(chuàng)作者。在白南準由一臺家用閉路電視和一尊古董佛像構成的錄像裝置《電視佛》中,攝像機捕捉了佛像的實時影像并同步到電視上,使佛像透過電視屏幕凝視靜坐中的自己。佛像與電視形構了日常生活中觀眾的觀看行為,但不同于通常狀態(tài)下“運動的影像”和“靜止的觀眾”,電視機以秒為單位的運動圖像被佛像的“靜觀”吸收了,被固定在座位上靜止的觀眾卻悠閑漫步在美術館中。這種“運動”與“靜止”關系的對調(diào)迫使靜止的影像不得不面對由觀眾的運動構建的全新觀看關系。觀眾的意識不再被影像的運動完全吸納,而是在斷斷續(xù)續(xù)的線索中將影像作為意識的提詞器,促發(fā)自我反思的發(fā)生。在這里,對“純粹靜止”的引入并非對古典神學中無生命靜止的回歸,而是當代性對曾經(jīng)構建現(xiàn)代性的那個笛卡爾式“懷疑”時刻的重新開啟。作為運動的變量,靜止成為重思“當下”的一個契機,將觀眾被文化工業(yè)平滑的圖像運動所同化的意識重新引入異質(zhì)性的思考當中。在更廣泛的影像實踐中,對“當下”的重思亦在“循環(huán)”的時間中展開。
二、“當下”的懸置:從線性到循環(huán)
現(xiàn)代性以“線性”方式展開的時間,使時間呈現(xiàn)為朝向特定方向的單向運動,在經(jīng)典的好萊塢電影與商業(yè)電視中,作為“有目的的行動,由可識別的目標和計劃所驅使。”現(xiàn)代線性時間從一開始就承載著未來烏托邦的宏大愿景,以產(chǎn)出有價值的結果為導向。正如中世紀對永恒的時間感興趣,文藝復興對過去的時間感興趣,以結果為導向的現(xiàn)代時間是一種關于未來的時間。對于現(xiàn)代性的支持者來說,這種以未來為導向的時間給時間運動一種明晰的方向感,讓它能夠以進步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而對于另一部分現(xiàn)代觀察者來說,被未來操控的時間是不自由的,人為設定的烏托邦未來限定了時間在當下的可能,是一種強加在生命之上的外部時間。
美術館影像以“循環(huán)”的結構扭轉時間的“線性”,將時間留置于“當下”。在70年代那些基于電影、電視的挪用素材創(chuàng)作的影像中,藝術家通常以“重復的剪輯”循環(huán)電影中的特定動作。以達拉·伯恩鮑姆的《技術/轉型:神奇女俠》為例,女演員琳達·卡特由辦公室女孩向神奇女俠變身的旋轉動作和爆炸特效被循環(huán)了30多次。對奇幻特效的反復強調(diào),禁錮了銀幕偶像“超能力”的發(fā)揮。通過將大眾媒體塑造電視偶像的技術暴露出來,藝術家以“重復的剪輯”拆解了現(xiàn)代性敘事服務于意識形態(tài)的最終目的,神話時刻的到來變得不再可能。
相比之下,90年代的行為藝術家用影像記錄的“重復的行動”則專注于對無意義時間的生產(chǎn)。在中國錄像藝術家張培力的早期創(chuàng)作中,打碎鏡子、清洗活雞、一遍遍轉著圈的舞蹈,這些無聊的重復活動以難以忍受的長度占據(jù)著電視服務于娛樂的時長。然而,嚴肅的勞動卻拒絕任何特定成果的產(chǎn)出。在《30cmX30cm》中,張培力窮盡一卷錄像帶的時長,拍攝他戴著乳膠手套的雙手反復打碎一面鏡子,然后將碎片粘起來,繼而再次打碎,再次黏合。打碎與黏合這組相互抵消的動作以一種存在主義的姿態(tài)拒絕了未來產(chǎn)品的生成。每當時間靠近即將產(chǎn)出成果的那個當口,都會在下一個抵消式的動作中折返至行動的起點。現(xiàn)代性敘事許諾當下付諸勞動的時間會在未來伴隨產(chǎn)品的生成被加倍感知。然而,對于專注重復行動的當代藝術家來說,那個現(xiàn)代性許諾中終將抵達的烏托邦未來是一種外置于生命的時間。相比之下,重復的行動通過對無意義時間的主動生產(chǎn),將時間留在“當下”并指向存在本身。它生成阿甘本口中那個當代性的“剩余時間”,表明鮮活的生命不可被任何特定產(chǎn)品的產(chǎn)出所取代,是生命超越了政治與經(jīng)濟框架后的剩余。
這種拒絕未來、“懸置”當下的存在主義姿態(tài)構建了惰性的時間結構,但循環(huán)的最終目的并非時間自困于當下的機械復制,對目標的消解意味著過程中多重可能性的生成。2022年,弗朗西斯·埃利斯的系列影像《兒童游戲》代表比利時參加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其中,名為《卡拉科爾》的第一部影像記錄了一個小男孩一邊沿城市陡峭的上坡路行走,一邊用腳踢一只裝有半瓶水的礦泉水瓶,他不斷調(diào)整力度和方向,控制水瓶跟隨自己向坡上運動,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上坡后,瓶子在路的最高處滾下“山坡”,小男孩的努力化為烏有。乍一看,小男孩似乎復制了埃利斯以往那些西弗斯式的徒勞行動,然而,這個重復行動的目的卻被藝術家通過游戲的方式轉移了。游戲在一個預設的規(guī)則中展開,卻不以輸贏為最高法則。重復的“玩”的動作雖然無法導出任何有價值的結果,卻是對純粹時間的生成。在這里,“為玩而玩”的“重復”作為存在對當下的創(chuàng)造,是對“現(xiàn)代時間觀中以犧牲當下而可預期、可操控的烏托邦未來”的移除,也是對當代“有著多元維度和多重可能的開放式未來”的敞開。在美術館影像最后一種時間策略中,這個包含多重可能性的未來在“差異”的自我裂解中產(chǎn)生。
三、“當下”的重組:從連貫到裂變
連貫的現(xiàn)代敘事通過對時間的總體化組織,將時間運動描述為不間斷的連續(xù)性過程。在電影中,敘事者會圍繞影片的總體意義,對現(xiàn)實中的事件作出選擇,吸收同一性的部分,排除差異性的部分,繼而將真實世界的時間兌換為虛擬的敘事時間。這種被同一性統(tǒng)籌的時間通過排除差異來進行,然而,生命時間的展開是非常復雜的,它由差異驅動,包含時間運動中復雜的相互關系和分散變化的多樣性,是偶然與差異的擴散。現(xiàn)代性的連貫時間剔除時間變化中異質(zhì)性的部分,是對時間本身的畸變,是敘事學意義上的時間而非人的時間。
美術館影像通過多屏投影或分屏技術,將“差異”引入連貫的敘事。以加拿大藝術家斯坦·道格拉斯為例,他的多屏影像裝置揭示被現(xiàn)代性連貫的歷史敘事所遮蔽的異質(zhì)性時間。在《鏡頭之外》中,四名非裔美國音樂人的自由爵士表演被剪輯成兩個版本,在一塊屏幕的正反兩面同時放映。正面的版本以當時法國音樂制品嚴絲合縫的工作室風格剪輯,展示演出中所有精彩的獨奏與高潮部分的合唱;背面則是樂隊成員在進入和聲之前的耐心等待和聆聽——是“標準版本”中通常被剪輯掉的部分。作為非裔美國人創(chuàng)作的音樂形式,“自由爵士”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流行文化中大放異彩,然而,一如那些被剪輯掉的等待鏡頭,這種音樂形式對美國文化的貢獻卻始終隱沒于璀璨的群星背后。阿甘本在《何為同時代?》一文中提及觀察夜空時環(huán)繞于群星周圍的黑暗。他說,“黑暗不是一個剝奪性的概念……感知這種黑暗并非某種形式的惰性或消極性,而是,更確切地說,意味著一種活力或奇異的能力。”而同時代人,恰恰是“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的人。”道格拉斯通過尋回那些在連貫歷史中被刻意忽視的個人敘事,書寫了一部由差異所彌合的另類歷史。
相比之下,皮埃爾·于熱則關注差異對時間與意義的生產(chǎn)。在他早年那些聚焦于影視作品的配音、翻譯、翻拍等過程的作品中,對原作與再現(xiàn)版本的差異化并置構成影像意義的主要來源。其雙屏影像裝置《第三記憶》的靈感源自西德尼·呂美特的電影《熱天午后》對1972年發(fā)生于布魯克林一起真實的銀行搶劫案的改編。在影片上映的25年后,于熱找到當年搶劫案的故事原型約翰·沃伊托維奇,在被重建的布魯克林銀行重述事件的經(jīng)過。有趣的是,當年邁的沃伊托維奇指導演員重新排演當時的場景,試圖揭開那些被好萊塢電影所混淆的真相時,他的記憶卻遭到電影敘事的同化。被媒體強大的敘事功能所填平的差異在這里以缺席的方式向觀眾敞開,新的故事在觀眾的頭腦中被調(diào)和。如果說現(xiàn)代性的連貫敘事在“同一性”的統(tǒng)籌下消滅時間,被差異所驅動的時間則在自我裂解中催生新的時間。在于熱的并置中,關于事件的第一記憶、電影改編后的第二記憶以及沃伊托維奇被扭曲的第三記憶交織在一起,它們在不斷錯位中激活了差異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一種時間對自身的產(chǎn)出。
差異的裂變最終生成的是不斷重組的當下,通過將美術館播放環(huán)境的實時畫面引入作品當中,加里·希爾將影像轉化為“當下”的捕獲器。在全息影像裝置《捕夢網(wǎng)》中,一只鋁制捕夢網(wǎng)被懸掛在展廳中央,在觀眾圍繞捕夢網(wǎng)參觀的同時,現(xiàn)場的實時畫面會被隱藏其中的31臺微型攝像機捕獲,并同步投射在展廳中央。全息投影使這些影像彼此交疊的懸浮在空中,以或放大或縮小或倒置或滑行的方式將“當下”裂解為30個不同的碎片,伴隨人群的流動不斷變換。觀眾連貫、穩(wěn)定的時空感瓦解了,不得不面對時間支離破碎的本質(zhì)。以這樣的方式,美術館影像在具體時空中呈現(xiàn)著一個個不斷重組的當下,它們不同于電影再現(xiàn)系統(tǒng)中在觀看時已逝去的創(chuàng)作者的當下,而是觀眾此時此刻身處其中的當下。正如在波德萊爾那里“剝離了描述功能”,“不再是一種給定狀態(tài)”的現(xiàn)代性,這個“當下”拒絕將自身凝固為某種可描述的確切形態(tài),它變動不居,是時間對自身的不斷重組,一種真正內(nèi)在于生命的時間的綿延。
結語
當現(xiàn)代性由目的論驅使的連貫敘事將時間固化為運動的永恒狀態(tài),一種“當代性”的時間則以靜止、循環(huán)與裂變的“消極”姿態(tài)重啟了笛卡爾那個“懷疑”的時刻。不同于被“過去”與“未來”附著的“古典”與“現(xiàn)代”,在美術館影像中,一種“當代性”是時間與“當下”的緊密聯(lián)系:作為對當下的重思,它將靜止引入運動,將停頓寫進時間,中斷現(xiàn)代性不假思索的變化習慣;通過對當下的懸置,它以循環(huán)逆轉導向未來的時間,讓時間指向存在本身;在對當下的重組中,它不以產(chǎn)出確切的“當代性”結果為目的,在差異的自我裂解中成為“不斷使自己變得當代”的時間機器。至此,美術館影像“對時間的消極處理”不應該被看作某種惰性的時間結構,在一個當代性的視域中,它是時間“于當下對存在自身的反復創(chuàng)造”,意味著時間本身是關于人的時間,一種始終鮮活顫動著的當下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