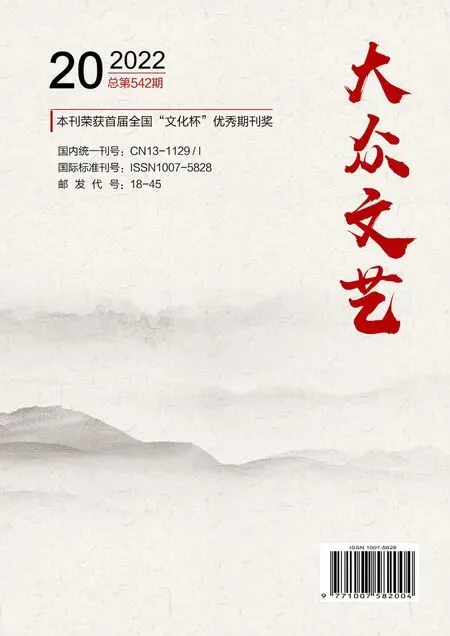從《兄妹開荒》看延安時期人民戲劇理論中的黨性教育*
宋 珊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19;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延安 716000)
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最早使用了“黨性”這一概念,他說“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 ”在列寧看來,作家只有嚴格接受黨的監督,才是黨性合格的革命作家。毛澤東認為:“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沒有黨性,或叫作黨性不完全。”劉少奇從理論上對黨性做了闡釋:“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陜甘寧邊區政府長期在農村開展工作,尤其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急需民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文藝作為展開黨性教育、提高生產、發展經濟、繁榮文化的工具,延安地區的新秧歌劇就成了這場教育的主力軍。《兄妹開荒》成了當時這場教育中“最初的、也最具典范意義的文本。”
一、《兄妹開荒》中人民戲劇理論進行黨性教育的歷史邏輯
囿于抗戰的環境,黨員及群眾的黨性都被重視,并得到了提升。《兄妹開荒》這部秧歌劇的誕生過程,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思想等問題的認識,黨性教育貫穿始終。
從文藝發展的方向看,《兄妹開荒》成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黨性教育,實踐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成果。毛澤東指出“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那么,要怎么去親近,怎么實現?《兄妹開荒》誕生之前,毛澤東對魯藝“關門提高”的藝術態度提出過批評,對此,魯藝學員主動走入群眾、深入群眾,從群眾藝術中發掘藝術因子,依靠群眾最終完成了這部秧歌劇的創作。關于怎么實現?王大化曾說:“一個黨的文化宣傳工作者,不但是指你的作品,而最主要的,你這個人就是黨的最具體的宣傳品。”這句話說明了演員本身就是黨的思想的宣傳者,也應該完成宣傳者的責任。《兄妹開荒》以馬丕恩一家,響應政府移民號召,從米脂移居延安三十里鋪開荒種地,實現了邊區政府提出的“耕二余一”的目標,成了生產模范,邊區政府授予他們“父女勞動英雄”稱號。1943年初,王大化、李波、路由、安波根據馬丕恩父女的事跡,創作了《兄妹開荒》這部新秧歌劇。該劇是當時社會歷史的反映,符合群眾戰斗生活的事實,無論是演員,還是演員在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方面,都做了真實的反映,這是黨性自覺的一種體現。
從思想上看,《兄妹開荒》一改之前“大戲”與陜甘寧邊區現實生活聯系不緊密的狀況,尤其對《講話》所要求的文藝內容有了具體響應。毛澤東指出:“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斗爭。”據此,文藝配合政治宣傳,文藝如何反映社會生活,并能教育民眾,團結民眾,成為此時創作與表演要完成的任務。與《兄妹開荒》同時期的《動員起來》,這部秧歌劇中借張栓婆姨的口,把群眾的一些疑慮提了出來,讓村長進行解釋,群眾與干部直接對話,對消除疑慮有積極作用,“可見他們觀劇時的心理,已不是欣賞技術而在聽取變工問題的辯論會”。新秧歌劇簡單明了地傳達邊區政府的各種思想,通俗易懂,群眾易于接受,這是黨性貼合社會的具體體現。
秧歌劇《兄妹開荒》的出現,是一種偶然,更是一種必然,它是演創人員無意中選擇的一個劇本,它更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團結民眾、教育民眾、傳遞思想的有力武器,誠如艾青所說“整個秧歌隊的工作,是為了演出,為了宣傳工作的順利完成。一切工作朝向一個目標:宣傳。”
二、《兄妹開荒》中人民戲劇理論開展黨性教育的現實路徑
《兄妹開荒》從文本內容、演員表演及其形式等多個角度如實反映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黨性教育的現實路徑,同時也反映了新秧歌劇在實踐《講話》、教育民眾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從《兄妹開荒》的劇本內容來看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黨性教育的現實路徑,主要包括了語言規勸、政策引導、行為指引三個方面。《兄妹開荒》劇本的語言基本全部使用群眾的語言表達方式,運用大白話、大實話讓群眾聽懂,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易于傳播黨的政策思想。比如在劇本中,妹妹看見哥哥沒記住區長的話,專門給哥哥重復了一遍:“區長講的話呀,句句有道理,大家學習勞動英雄,馬家兩父女呀,……深耕勤鋤草呀,又快又認真,別家一坰地打六斗,他們打八斗零呀……”劇本的語言,沒有故作高深的道理,將哥哥的“不勤快”與馬家兩父女作為勞動模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區長的聲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既有特定的身份,又借妹妹之口傳遞了正確的思想。《兄妹開荒》中的政策引導,基本上是通過兄妹對話來完成的。比如:“加緊生產,不分男女,……邊區的人民吃得好來,穿也穿的暖,豐衣足食,趕走了日本鬼呀,建設新中國。”生產、開荒、男女平等、建設新中國等意識全由兄妹對話、合唱傳遞出來,這是深入社會生活之后發自內心的吶喊,群眾也在觀看的過程中,被這種情緒所感染。《兄妹開荒》中镢頭的設置十分巧妙。撅頭既作為開荒的工具,又成了劇中兄妹勞動與不勞動的推手,兩個人不斷放下又拿起撅頭,最終一起用撅頭勞動,全劇一直圍繞撅頭這個具體物件展開人物動作,勞動成為全劇的核心問題,自然勞動的動作、物件本身也就成了勞動必須要言說的全部,將邊區政府勞動教育精神傳遞給群眾。
從《兄妹開荒》表演及其形式來看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黨性教育的現實路徑。首先,《兄妹開荒》屬于集體創作,這種創作方式能集思廣益,創作出相較于個體而言高水平的藝術作品,這在陜甘寧邊區的文藝創作中也是常見的形式。其次,《兄妹開荒》從民間藝術中進行普及和提高。這部秧歌劇保留了傳統秧歌一男一女表演的形式,但這對男女已經從夫妻變成了兄妹,從男女打情罵俏變成了先進改造落后,表演上依然是秧歌本身,認識上則成了教育民眾、改造民眾的方式。《兄妹開荒》中不乏陜北方言俚語,“爾刻”“麻達”“哪搭”“一滿解不下”等隨處可見,生活化的語言生動質樸,易于群眾感知,并認同演員所傳遞的思想。新秧歌劇的“新”,一方面是通過先進人物幫助落后分子進行改造,或者通過勞動競賽,最終共同進步;一方面通過劇中能代表權威的村主任、區長、婦女主任這樣的角色來進行教育,以期達到教育目的的最終實現。《兄妹開荒》基本也是圍繞這樣的模式,只是這部劇設置了一個哥哥故意不勞動的環節,代替了以往秧歌劇中“打情罵俏”的情節,秧歌劇的這種設置滿足了邊區群眾獲取政府政策知識、理解政治任務的實際需求,對他們來說,新秧歌劇稱得上形象化的宣傳冊和教科書,總之,“他們過去從舞臺上接觸的盡是前朝往代的歷史和傳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如今卻看見了現代的中國人,殘暴的敵寇,狡猾的漢奸,自己的同伴,乃至他們自己。”
總體來說,以《兄妹開荒》為標志的新秧歌劇,開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最廣泛意義上的人民黨性宣傳教育工作,用艾青的話:“在新的政治環境和新的經濟條件下,群眾要求著自己的文化藝術......這就是說,秧歌劇是群眾的歌舞劇,從劇本的內容到形式,從秧歌隊的組織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眾性的東西。”
三、《兄妹開荒》開展人民黨性教育的經驗性意義
1943年7月5日,重慶《新華日報》以《一個秧歌劇演員的創作經驗談》為題,轉載了王大化1943年4月26日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從演員本人自述演出的經歷與經驗,再到報紙轉載,能看見這部劇全方位的影響,是從演出者到傳播者、再到群眾這一接受群體全民性的一次“經驗之談”。
首先,《兄妹開荒》是《講話》后關于文藝方向最直接、最成功的一次實踐,一次有意義的“經驗之談”。李波曾回憶:“我們深深地為陜甘寧邊區人民響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在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的英雄事跡所感動,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們感到應該讓這些英雄事跡再現出來,鼓舞群眾,教育群眾也教育自己。于是,我們把接觸到的群眾戰斗生活中的人和事,編寫了《兄妹開荒》這個小秧歌劇。”在這個表述中,李波首先是被教育者、被感動者,然后全身心進入了《兄妹開荒》的創作和演出,李波是讓自己的感知去感化未被受益的群眾,這是發自肺腑的一個文藝工作者從思想認知到行動實踐的典型代表,文藝的思想教育與傳播就是從自我再到他人,從自我的內化再到外在的展現,通過《兄妹開荒》也的確達到了教育民眾的效果,這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自覺的黨性體現,也是對文藝政策最自覺的履行。
其次,《兄妹開荒》這部秧歌劇能獲得巨大成功,得益于這部劇最大限度地群眾基礎,即從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展開群眾最為熟悉的日常生活,解決群眾最為迫切的矛盾沖突,簡單來說這部秧歌劇體現了關于群眾的“經驗之談”。毛澤東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以此為邏輯出發點,中國共產黨代表著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根本階級屬性決定了文藝事業的黨性和人民性。以《兄妹開荒》為代表的秧歌劇,與前期“大戲”相比,《兄妹開荒》開始關注群眾的勞動生活、家庭倫理、知識普及、識字情況等等,將百姓圖景作為了藝術表達的全部內容。對以群眾為基礎的文藝創作與發展,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這也成為當下文藝再次依循的主體,這也是黨的文藝工作者堅定不移堅持的創作原則與方向。
最后,對《兄妹開荒》這部秧歌劇而言,它是抗日救亡時期文藝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吸收文藝政策到自我的大膽創新,藝術的革新也成了“經驗之談”。秧歌是一種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一直處于群眾自發演出,純屬民間娛樂,多伴有調侃戲謔引人發笑的藝術效果,難登大雅之堂。但也就是這種民間藝術形式,獲得最廣大群眾的喜愛,如何讓就有的秧歌劇形式注入新的時代內容,這就是延安時期這場如火如荼的秧歌劇運動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文藝工作者們大膽地運用秧歌劇的藝術形式,加入了社會生活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內容,基本上采取一劇一個問題的內容設置,保留一定的幽默元素,采用“小團圓”的解決方式,在普及中提高群眾的認識,在提升民眾的社會認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兄妹開荒》作為延安時期秧歌劇的典型代表,這是《講話》后文藝工作者利用民間藝術試驗和探索工農兵大眾方向戲劇的一次成功的實踐。在面對陜甘寧邊區近乎全是文盲的群眾,用這種通俗易懂、自然親切的表演方式,融入了全新的教育內容,能調動觀眾的參與感,寓教于樂。《兄妹開荒》獲得成功后,文藝工作者同時也發現,秧歌劇單一的表達模式,不夠豐富的藝術形式,不能有更高的藝術水準,隨后推出了一大批新劇目,秧歌劇的形式也已由簡單到復雜、由小型到大型,內容更加豐富,反映社會生活也更加廣闊,之后的《周子山》等秧歌劇開始了題材容量與藝術質量的提升嘗試,這也為新歌劇《白毛女》的最終出現鋪墊了基礎。不管怎樣,《兄妹開荒》所代表的藝術方向性、藝術創作原則、藝術工作者應該持有的工作態度,是從陜甘寧邊區政府黨性要求與實踐的路徑上來進行嘗試的,無疑,這也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從文藝的角度為全黨黨員自覺按黨性要求鍛煉自己指明了方向,誠如任弼時同志在中央黨校作《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的報告時指出:“這個決定加上《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其他決定的發出,引起了全黨對于思想問題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學習,展開了今天這樣廣大的全延安全黨的學習運動。”今天看來,提升黨性依然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文藝工作順利推進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