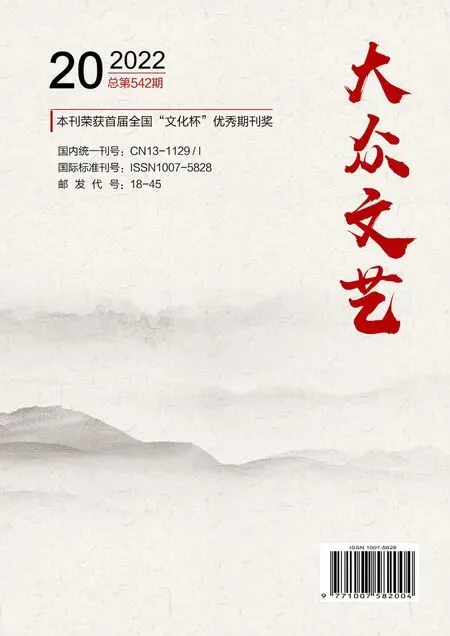論懷素狂草藝術中的“自由”創作精神及其現實意義
李欣娜
(河北大學藝術學院,河北保定 071000)
初唐書壇長期以來都以法度森嚴、端莊典雅的理性主義楷書書風特征為典范,至盛中唐時期隨著賀知章、張旭及懷素等人書風的轉型,逐漸開創出酣暢淋漓、奔放不羈的浪漫主義狂草風格。而懷素作為唐代狂草藝術的推動者,與張旭并稱為“顛張醉素”。懷素雖為一介僧人,但他在其書法實踐中追求新奇,借助酒后大大增強的創作欲望書寫著自身超然灑脫的精神世界。此外,懷素引禪學入書,并將個體主觀意識與自我精神貫穿于創作過程,以其獨特的創作精神將傳統草書的實用性與審美性十分巧妙地進行了協調融合。
一、懷素“自由放逸”狂草書風的成因分析
(一)時代背景:盛中唐書家注重主體性情的抒發
唐書“法度”之尚是唐代書壇中審美取向的直接體現,唐人主張追求書法本身的主體性靈與生命精神。而這一“森嚴法度”發展到盛中唐時期則產生了一系列具有爆發性的浪漫主義書風,這種追求個性,自由灑脫的書法風格夸張但不張揚,反叛但不反動,使整個書壇呈現出一派熱情奔放的豪邁正大氣象。
狂草藝術新潮流的出現,是受盛唐社會、政治文化外在因素的決定性影響。唐開元年間,統治者勵精圖治舉國繁榮,內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頻繁,儒釋道三教兼并共存開創了盛唐社會群起激昂的思想盛典。而這一激情昂揚的社會文化反映在書法創作領域內則是一眾書家注重創作中情感的抒發,重視書家個人內心重“意”主“情”的顯現。書家的精神、風度和氣質滲透在其實踐的各個維度,心性情感的抒發和表達是此時藝術領域內中高揚主體論的體現。盛唐狂草藝術以其獨特的藝術語言宣泄情感,以期用情動人,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實用性,成為夸大風格與情感表達交叉在一起的抒情藝術。唐代書家通過在藝術創作過程中表現主體性格,傳達個人感情,形成了一種更加樂觀豪邁的鮮明時代特色,深刻體現著一種雄壯、崇高之美,書壇中倡揚著感性而有力的風貌。盛中唐以張旭、懷素為代表書家所開啟的浪漫主義寫意書風,使書家高揚主體精神的抒情與寫意,十分重視將其性格和情感融入至藝術創作中,形成自身獨特的藝術風格。張旭打破傳統書法理性內蘊的束縛,創造出以超然的道家思想和酒神型文化為基調的狂草書法,酒打亂了張旭對于理性的控制,讓其在創作中得以釋放、得以酣暢淋漓的表現自我。而此后中唐懷素受此風氣影響,逐漸呈現出具有抒情性的狂草書風,表現出浪漫主義書風抽象玄奧的意蘊形式臻于極致。
(二)個人經歷:學書環境與取法方面對其書風的影響
“素睹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據宋人王象之所載,懷素長久以來正是將先賢的書跡以及學書規范視作楷模并極力推崇,“夫草稿之作,起于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模精法詳,特為真正。”懷素在其《自敘帖》中收錄了顏真卿的書論作序,由此可以看出懷素十分認可和主張顏真卿所論述的草書發展歷程,認為習草必然奠基于漢魏,上追王二、張芝,近承張旭,其自身習書過程及風格的形成也主要遵循這條正統途徑。受唐統治者所尚書風的影響,崇王風尚在此時蔚然成風。而懷素秉承“二王”筆墨精髓,在突破章草和今草格式規范的基礎上,把線條的書寫性發揮到了極致,更將張旭、賀知章等人的酣暢浪漫寫意書風推向至新的高度。懷素曾受到鄔肜的傾囊點撥,對其早期的書法創作筆法及審美觀念產生了極為關鍵的影響。《僧懷素傳》曾記載:“肜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樹葉。’張長史又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吾師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圣盡于此。”據此可推斷出懷素在師從鄔肜之時,亦間接受到其師張長史草書實踐中的獨到見解。唐人對鄔肜的草書風格評價極高,如“寒鴉棲林,平岡走兔”般縱橫瘦挺、奇崛古樸。懷素追隨鄔肜領悟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的筆法內蘊,在其后來的草書創作中更是將筆法的奔縱與變幻的空間相交映形成了懷素草書中獨特的放逸氣勢。而后顏真卿啟發懷素學書還需“自得”,從自然內汲取營養,以追求自然之美中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鄔肜與顏真卿同師承于張旭,二人對于懷素創作的熏染沒有使其滯留在一味追尋仿效古人的屏障中,而是給予他從自然事物中自悟筆法、意會書勢的方法。總體來看,上溯漢魏傳統,近師同代書賢的取法經歷構成了懷素的縱橫兩路吸收創作中精華真知的學書之路。
二、“自由”創作精神在懷素草書中的體現
懷素遠承漢魏,近追鄔肜、顏真卿,在古今賢人的傳教與指引下,懷素結合其自身性格與經歷便有意識地開始追求獨辟蹊徑的風格面貌。這種在傳習古人傳統基礎之上的創新求變,是一種大膽新奇且別開生面的自由創新精神,而懷素狂草書風中所內含的“自由”創作精神正是其追求新奇藝術創作與表達自我情感的直接顯現,主要體現在創作心理、創作觀念以及書寫材料幾個方面。
(一)醉后創作中情感的自由表達
盛中唐所狂熱興起的狂草藝術以期通過草書創作中情感的投入喚起人們心靈的觸動。狂草藝術作為最能體現書家本人情感與心境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會由于創作者性情的差異性而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
清人劉熙載曾指出懷素習草時悲喜雙遣,強調懷素在書寫過程中能夠自由地把握悲喜情緒,自然流露出他的超然心態與奔放情懷。懷素自幼皈依佛門出家為僧,佛教極重視對于個人內心的洗禮與放空,要求人們摒棄“我執”與“法執”,努力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懷素作為孑然一身的僧侶遠離廟堂,自然不會受到封建權力階層的強力約束,通常可以更充分的沖破束縛,在創作中乘興展現“自由”精神的逸興與灑落。懷素有“醉僧”之名,嗜酒沉醉這種行為似乎在懷素周圍的僧人群體中比較格格不入,但也正因如此,他突出封建禮法所帶來的桎梏,開創了浪漫主義新書風的典型。“懷素疏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于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倡志。時酒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由于酒精的刺激與促進,使懷素的創作欲望大大增強,隨之而形成的則是超越理性的狂逸草書風格。懷素的《自敘帖》是其代表作中最能體現他的情感迸發之作,此作的放浪形骸之態正是懷素草書狂放超然生命力最直接的體現,給予觀者十分狂熱的生命情感體驗。此作墨色變化極其豐富,受書家創作習慣原因影響,墨色通常從濃到淡,從濕潤重筆到淡墨渴筆,燥中帶潤且柔中見剛,產生較為強烈的筆墨情趣與視覺沖擊力,是懷素狂逸奔放、縱情恣意本真心態的自由流露。其次在結體與章法方面,此作中的結體往往較能反映懷素的藝術趣味與特色,懷素乘興而作大膽地針對某些字形結體作出調整,如“懷”“胸”“承”等字,因時而異的結體特點體現了作品整篇布局的情感變動,增加了此作中偶然性與不確定性的審美意蘊。懷素在酒醉狀態下激情揮灑,“醉來信手三兩行,醒后卻書書不得”,醉后創作日益成為懷素張揚個性,自由宣泄的重要精神載體。
(二)引禪入書的自由頓悟
唐代的狂禪風氣是此時期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統治者十分重視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禪宗流派,故而以“以心印心”為特點原則的禪宗直接影響到了此時書法藝術的發展。盛中唐時期自由奔放、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是禪宗在此時扎根發展的主要因素,禪宗中所蘊含的自性、頓悟思想使書家進行創作時不斷追求物我兩忘的至高境界,使之不受世俗羈絆進而釋放天性。書家只有悟得自身心性,感受生命無窮的靈氣與本真才會盡得自由、自然的禪意境界。
懷素籍貫為唐永州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市),而懷素之鄉正是唐代禪宗主要盛行之處,“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懷素自幼生長于佛僧世家,其幼年皈依佛門也深受到惠融禪師的影響,此后“經禪之暇,頗好筆翰”成為懷素引禪入書的一大契機。懷素借助禪宗的“參悟”之法激發創作靈感并一改戒律世俗為其帶來的束縛。當我們一覽其作時,從中所滲透出獨具懷素特色的超然灑脫,自由飄逸之感秉持了禪宗所尊崇的“無物無我”“明心見性”的思想主張。懷素晚年所書《小草千字文》一作較于《自敘帖》更凸顯復歸平淡后的自由天真之感,除卻晚年垂垂老矣的身體健康狀況等次要的外部原因,更主要的應為懷素經過時間沉淀對禪宗思想更加頓悟深入后的自然書寫。在《小草千字文》中,大幅度的情感擺動減少,整體風格都呈現出率性任心的風格特點,即是從禪意中感化而來,若靠自身參悟,則需排斥濃烈的自身濁氣并以忘懷遣慮的心境追求自由真如的域度。此作用筆含蓄自如,幾乎是以中鋒貫穿全篇,未見極明顯的情緒波動。通體來看,《小草千字文》緩急有序,簡淡臻至,從而體現出書家作者“參禪”的自性解放。懷素融書法創作、忘懷、心性等禪宗思想為一體從而妙悟升華到自由爛漫、恬憺逸意的創作境界,亦為唐末書僧群體中“以書參禪”的風氣開拓了借鑒思路與傳承觀點。
(三)書寫方式與材料的自由選擇
通過上文對懷素引禪入書這一創作行為的梳理,我們可了解到懷素的書法精神正是佛教禪宗“出世超逸”自由思想的顯現。懷素所修的禪宗并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打坐誦經之上,禪宗“念在于心,不在于言”的自由思想精神為懷素進行書法創作提供了十分寬泛靈活的時間。在唐代論書詩中,稱贊懷素草書的詩歌約占十五首之多。其中“吾師醉后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李白《草書歌行》)“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以上均為唐代頗負盛名的詩人觀懷素揮毫后乘興而作的詩歌,其中竇冀所言“滿壁縱橫千萬字”則還原了懷素當時所喜愛的題壁書寫方式,懷素為了規避“局促兒童戲”的書寫形式,而大膽地選擇在寺廟內的墻壁上自由攘臂揮灑。懷素通常為了書寫及觀賞效果更佳還會選擇在連綿數十米的長廊墻壁上進行創作,憑借其強烈的感性意識和激蕩的創作欲望實現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自由宣泄。此外《僧懷素傳》中所記載了“懷素書蕉”的行為:“(懷素)貧無紙可書,嘗于故里種芭蕉萬余株,以供揮灑。”這則廣傳于世的典故為我們展現了懷素重勤學的刻苦行為,同時也向我們傳達出他對于書寫材料的自由擇取。
懷素書法創作中隨性灑脫的自由創作精神向觀者傳遞出他所追求的真如本性至高境界,結合其創作風格、方式及思想幾個方面來看,懷素對于草書藝術的推動在于他向其中灌輸了個人的性情與頓悟,通過禪宗的熏染摒棄了內心阻礙從而更好地將參禪與草書高度融合,為其草書藝術增添了更充分的自覺性與可塑性。懷素在洋溢著正大氣象的盛中唐書壇內求新求變,逐漸從法度森嚴,氣勢宏大的楷書書風中開拓創新理念,極力追求乘興發揮,個性張揚的“自由”創作精神。
三、懷素書法實踐中“自由”創作精神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
盛中唐時期出現的以張旭、懷素及顏真卿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書風與法度森嚴的楷書書風形成了兼容并存的形式。懷素狂草中所秉持著禪的自性與妙悟,主張個性張揚表現自身性情,沖出封建禮教的束縛從而高舉狂逸的“自由”精神。今有學者指出懷素創作中所具備的神采氣勢:“我讀《自敘帖》二十年,初則驚奇莫名,嘆為觀止,繼而又覺簡單粗糙,點畫無形,有失雅麗;再之,便覺浩浩茫茫,神秘莫測,筆意縱橫,氣勢恢宏,境界升騰,不知其所止,不可望其向背。”懷素極快的用筆速度使整體布局不拘成法,看似下意識的表現其主觀內心世界,實則深刻地傳達了他“志在新奇無定則”的創作態度。此外懷素傳世書帖《苦筍帖》這類晚年代表書作,用筆圓潤勁健,結體簡淡枯健不作狂態。明人項元汴評其曰:“藏正于奇,蘊真于草,含巧于樸,露筋于骨,觀其以懷素稱名,藏真為號,無不心會神解。”懷素在其草書實踐中融入傳統楷書,并以此為字號時刻勉勵自己,并在學習經典感受傳統的同時超越法度,追求書法創作中筋骨精神與自由精神并進兼容的藝術創造力。
懷素以其對傳統書法精神的把握,順應時代發展而標榜壯美雄渾的書法審美追求,其守正出新所呈現出的猖狂灑脫之風正是反映了具有強大生命感染力的風格取向。這一新風尚不僅影響宋人在創作中所追求的強烈文人自尊意識,形成尚意趣的時代新書風,還直接喚起了晚明時期又一浪漫主義書風的革新浪潮。若以懷素的書法風尚反觀當下,隨著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的斷裂缺失,象征著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強大自信心也逐漸削弱,反映在藝術創作中即總是缺乏一種博大豪邁且古拙正大的創作風氣,相反出現了一路妍美流俗的時尚書風。從懷素創作實踐及學書經歷來看,他十分注重自身素質及學書體系二者相融合的修煉升華。早期“書蕉”及“筆冢墨池”的學書典故闡釋了懷素個人勤學苦練、刻苦習字的行為。而其后遠近取法,師承古今書賢,從而視野開闊思想活躍,實現了融禪入書的完美契合,使其自由的生命主體精神得以揮灑。通過對懷素狂草藝術創作中“自由”創作精神的闡釋也正是對當下健康書法風格的呼喚,秉承古人經典之跡,師法傳統并推陳出新,成為當下書法創作保持良好發展的必經之路。
結語
在盛唐寬博大氣書風的籠罩下,狂草這類高度抽象的書寫藝術需要書家始終秉持著自由放任、恬憺空靈的個體本性。懷素在承繼前人傳統基礎之上積極進取,力求創新,將唐代狂草藝術推向更加繁盛的高峰。懷素狂草書風中所透露“自由”之態是他寄情于書法,是他借書法創作去參悟簡淡玄遠的真如本性以及表達信仰的精神體現。縱觀懷素的學書之路,從遠追漢魏經典及近賢,到超然物外、漫游山水,在山川中吸收可以啟發自身的自然靈感。懷素作為禪僧,他在草書中踐行對禪意的參悟,將狂草與禪宗思想融合發展成一種具有“自由頓悟”特性的禪意創作觀念。因此我們要宣揚懷素在草書實踐中的強大創造力和積極進取的守正出新精神,使書法藝術在雄渾壯美的文化氣象中繼續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