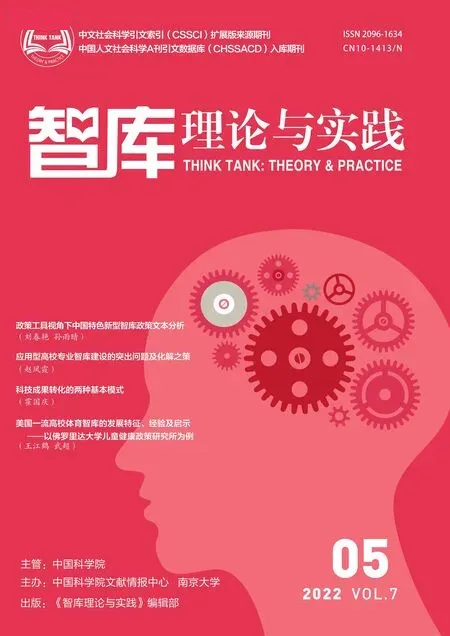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構成與特點*
——從利益附屬到思想附庸
■ 翟石磊 許善品
1 中國礦業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網絡風險治理研究中心 徐州 221116
2 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湘潭 411105
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在南海問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新疆問題、人權問題、5G 通訊等方面緊隨美國,對中國進行訛詐、攻擊,抹黑中國的發展成就,妖魔化中國國家形象。這些動作的背后,始終可以看到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為代表的極右派反華“智庫”的身影。其鼓吹抗衡中國,以所謂學術研究之名掩蓋政策工具的本質,推高國際反華情緒。從資源配置方面來看,這一類智庫通常擁有官方、軍方甚至外部力量的支持,包括資金、人員、技術、信息等支持,成為政策建議、輿論動員的旗手。
然而,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偏好美國、英國、德國等傳統大國智庫研究,對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關注不夠,這對研究、預判和制定涉澳政策不利。本文以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麥甘(James McCann)團隊所發布的歷年《全球智庫報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為參照,以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歷程、分布區域、領域、基本特點和國際影響力為分析問題,對其構成、特點、政治傾向等方面進行梳理分析,從而對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形成更加全面的認識和評價。
1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概況
在聯邦政府成立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外交議題始終未被納入澳大利亞政策制定的優先層面。在二戰以前,澳大利亞在外交事務和安全防務領域全面依賴英國。二戰爆發以后,英國國力驟降,世界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澳大利亞在外交與安全防衛方面逐步轉向美國,并充當美國推行國際霸權的助手。近年來,澳大利亞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有所提升,對“中等強國”和南太平洋地區大國的身份認同意識也在逐漸強化,因此,謀求地區、甚至全球影響力開始成為澳大利亞政府在外交領域新的目標。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智庫在政策制定、輿論引導等方面發揮著獨特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所分析的國際問題研究智庫是指以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涉外議題為研究對象的智庫。此類智庫在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早期就已出現,并在過去近百年間有了顯著的發展。其在促進澳大利亞外交決策科學化的同時,也將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訴求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各類政策游說之中,甚至以所謂理性化的方式來對極端化思想進行包裝和宣傳,助推澳大利亞政府對抗中國,干預他國事務,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發展。
1.1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的歷史分期
自1901 年以后,新獨立的澳大利亞聯邦需要借助“外腦”促進國家建設和發展,這一需求直接促成了各類智庫的成立,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4 年成立)、澳大利亞經濟學會(The Economic Society of Australia,1925 年成立)、澳大利亞教育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1930 年成立)等智庫均誕生于這一時期,該階段可被視為澳大利亞智庫發展的奠基時期。然而,彼時的澳大利亞并未實現外交獨立,外交傳統也尚未形成。因此,當時的澳大利亞智庫更多的是聚焦國內發展議題,國際問題研究并未真正走進智庫研究視野。
20 世紀70 年代以后,隨著國際意識和外交主體意識逐漸增強,澳大利亞對開展獨立外交的意愿逐漸強化,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這一轉變促成了包括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0 年成立)在內的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設立。1972 年是澳大利亞決策咨詢體系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之前,咨詢機構在政府的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由于惠特拉姆(Whitlam)政府對政策咨詢的重視,政府的大量決策均是基于公共調查,并廣泛征求政府外部的意見后進行制定的。智庫在此時期得以充分發展,并在其后持續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20 世紀90 年代,冷戰的結束帶來了國際秩序的調整,國際格局日益多元化。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 年的“9·11 事件”的相繼爆發,使得澳大利亞產生了新的安全焦慮。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不穩定性因素逐漸增加,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干涉行為以及恐怖主義威脅加深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澳大利亞愈加關注安全與防御、國內與國際協調發展等問題。在此期間,包括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以下簡稱:羅伊研究所)、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內的智庫先后成立,成為日后影響澳大利亞外交決策的重要力量。
新世紀以來,澳大利亞智庫發展進入成熟期,專業化、協同化和國際化是該時期的典型特征。地區局勢相對穩定,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給澳大利亞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利好,中澳經貿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穩步提升。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制定對華政策,一批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國的智庫或課題組得以設立,例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所(China Institute-ANU)、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澳中“一帶一路”倡議(Australia-China Belt &Road Initiative)、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1]、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China in the World)等[2]。這些智庫研究議題更加聚焦,研究團隊更加多元化,體現出該時期澳大利亞智庫研究的專業性、精準性和實踐導向的新特點。
當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國的研究僅僅是澳大利亞國別與區域研究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亞洲、東南亞、南太平洋地區、美國等地區和國家也進入了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視野。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院(Griffith Asia Institute-Griffith University)、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US Studies Centre,Sydney University)等一批國別與區域研究中心的設立,將早期廣義的國際問題研究向具體的區域研究轉換,建立起澳大利亞對全球主要大國和關鍵區域研究的智庫體系。研究結果顯示,這一時期智庫對澳大利亞政策發展的影響力越來越大[3],這些智庫依附于不同機構,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制定發揮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1.2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區域分布
從智庫分布區域來看,首都堪培拉是澳大利亞的智庫中心。根據2016 年《全球智庫研究報告》公布的結果,澳大利亞在亞洲地區排名前20 位的智庫主要集中在堪培拉,這里既有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The Strategic&Defense Studies Centre)、澳大利亞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等成立于20 世紀的老牌智庫,也有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Security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er)、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院(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等新興智庫。這些智庫位居國家行政中樞,接近權力和決策中心,更容易獲取關鍵信息,發揮智庫影響力。
悉尼和墨爾本是澳大利亞重要的經濟、金融中心,同樣聚集著大量智庫,屬于澳大利亞智庫體系的次中心區域。在悉尼,具有代表性的智庫包括獨立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羅伊研究所、經濟學與和平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①該智庫在全球5 個國家設立辦公室,分別為美國(紐約)、比利時(布魯塞爾)、津巴布韋(哈拉雷),墨西哥(墨西哥城)以及荷蘭(海牙)。、國際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澳中關系研究院(Australian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悉尼研究所(The Sydney Institute)等,這些智庫以經濟、安全和國際關系為研究特色,服務地方、聯邦政府和國際客戶的決策需求。
布里斯班、黃金海岸、珀斯、阿德萊德等城市屬于澳大利亞智庫的外圍區域,擁有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院、布里斯班研究院(Brisbane Institute)、邦德大學全球化與發展中心(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Bond University)、澳大利亞研究所、澳大利亞亞太經合組織研究中心(Australian APEC Studies Centre)等智庫。這些智庫大部分都是依附于高校設立的,與所在城市發展特色和高校學科特長相結合,側重于全球貿易治理和亞太地區研究,與首都地區和中心城市地區智庫的研究形成互補。
1.3 學界對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評價
整體來看,澳大利亞智庫通常以亞太研究、商業機構與發展戰略、經濟政策與企業關系、國際事務與防衛、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等為特色[4],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在部分領域走在世界的前列,成為地區智庫大國。根據2010 年的《全球智庫報告》,羅伊研究所位列全球智庫50 強(不含美國),排名第27 位。在地區智庫排名方面,羅伊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分別位列當年亞洲智庫第8 位和第9 位。至2020 年,澳大利亞有10 家智庫入選全球頂尖智庫名單,其中羅伊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分別位列世界頂尖智庫榜單(共計150 家,不包括美國)的第57 位和第66 位。在2020 年南亞和南太地區110 家入圍該榜單的智庫中,共有10 家智庫來自澳大利亞,其中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位列第10 位,與歷史上的排名相比呈現下降趨勢。這與該時期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智庫的迅速崛起不無關系。
可以說,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建設歷程與澳大利亞國家意識和外交獨立意識強化同步發展,并且其在澳大利亞國際戰略制定和外交政策調整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國內學界對于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構成體系、內在特質、政治立場等缺乏系統性認識,也尚未對這些智庫建設得失做出全面評價,這不利于對澳大利亞智庫運行機制和政策影響進行評估。從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來看,《澳大利亞國防安全智庫對華認知的轉變》[5]《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網絡安全領域研究及對中國智庫的啟示》[6]等均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對華認知、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域的研究成果。此外,部分學者以澳大利亞智庫產品為分析基礎,分析智庫研究對政策制定和公共輿論影響問題。江璐在《精英的合謀——澳大利亞對華民意研究(2014—2018)》中以羅伊研究所等機構的13 份民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從經濟、安全、中澳關系/對華情感3 個維度勾勒出澳對華民意呈現的特點和變化[7]。張亮通過對澳大利亞智庫等對中國加強與太平洋島國關系的評論進行研究,對澳大利亞對華認知和態度做出分析[8]。這些研究既是對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構成和運行機制的初步探討,更是據此類智庫充當反華急先鋒而做出的應對。從當前國際局勢及發展趨勢來看,全面了解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構成體系和運行特點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體系的構成
雖然智庫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但是如何定義智庫,學界尚未形成共識。有學者[9]認為,“智庫”通常是指以公共政策研究為核心、以影響政府政策選擇為目標的研究機構,一個國家(地區)著名智庫的數量和影響力通常會在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發展和對輿論陣地的爭奪中體現出來。也有學者將智庫定義為“模糊不清、善變的、充滿爭議”的機構[10]。該定義更多的是揭露智庫內在的問題,具有批判意義。詹姆斯·麥甘團隊采取較為寬泛的定義,其認為智庫是“開展與公共政策相關的研究與分析,為國內和國際問題提供建議,讓政策決策者和公眾獲得有關公共政策決策的充分信息”[11]。在詹姆斯·麥甘看來,智庫開展的政策研究涵蓋國內和國際兩個領域,針對的對象是政策決策者和公眾,這一觀點也被大部分學者所接受。但是,學者對于政策研究主體的界定卻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一切從事政策研究并且與政府和決策層保持某種聯系的研究主體均可以納入智庫序列[12];也有學者認為智庫提供的必須是“高質量思想產品”,且具有超前意識,能夠提出從長遠來看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的建構[13]。本文認為,世界各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決定了各國政策決策過程的差異,也導致了對智庫認識的不同。但基本上不會否認這樣一些共識性元素,例如:智庫是為決策過程提供思想產品的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獨立智庫和依附于政府、政黨和高校的附屬型智庫;智庫可大可小,其服務對象既包括社會精英也包括社會公眾;同時一般智庫均宣稱自己具有無黨派傾向和非營利導向。
對于智庫類型的劃分,學界也存在不同的標準。智庫一般被劃分為獨立型智庫、隸屬型智庫和混合型智庫。保羅·哈特(Paul Hart)和阿里亞德尼·維羅門(Ariadne Vromen)將澳大利亞智庫劃分為學術型智庫、政府智庫、合約型智庫和政策宣導型智庫等4 種類型[14]。王莉麗從智庫資金來源、機構歸屬等角度分析,提出智庫主要分為官方智庫、大學智庫和獨立智庫3 種類型[15]。本文更加傾向于王莉麗對智庫類型劃分的標準。與世界智庫大國相比,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體系的體量并不算大,但從大洋洲地區智庫分布格局來看,澳大利亞無疑屬于地區智庫大國。近些年來,澳大利亞政府逐漸形成了一套內部決策咨詢體系和外部咨詢體系。其中,內部咨詢體系包括政府內部咨詢機構、專門的政策研究機構、由國會立法確認的政策咨詢機構、政府間機構以及議會調查和公眾調查(public inquires)等咨詢渠道。政府外部咨詢體系包括隸屬于大學的研究咨詢機構、政黨政治研究機構、利益團體、游說團體等,也包括狹義的智庫部門,例如,知名的獨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悉尼研究所(Sydney Institute)、公共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羅伊研究所、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等[16]。澳大利亞智庫既包括廣義上的政府內部咨詢機構,也包括狹義上的智庫部門。為了能夠合理地使用國際智庫研究數據,更加清晰地進行國際比較。本文所考察的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是指不包括政府內部政策咨詢部門在內的其他研究機構,即官方智庫、大學智庫和獨立智庫。
2.1 官方智庫
官方智庫是指由政府發起并提供主要資金支持的智庫。根據《全球智庫報告》,自2010 年以來,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等智庫先后上榜,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官方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就是由政府發起成立的較為知名的官方智庫[17],該機構成立于2001 年,歷任領導人履歷表見表1[5]。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對自己有如下描述: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是一家獨立、無黨派利益傾向的智庫,為澳大利亞戰略和防御提供政策建議,注重對亞太地區戰略議題的研討提供支持[17],研究領域涵蓋澳大利亞本國與國際范圍內的防衛、和平與安全等。自成立以來,該智庫高調反華,倡導對華實施遏制和打壓政策,充當澳美反華勢力急先鋒,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傳播中國威脅論。

表1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歷任領導人履歷表Table 1 List of executive directors,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近年來,雖然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名聲大噪,但并不被公眾歡迎。據調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臉書(Facebook)大概擁有24,595(2021 年)名支持者,低于澳大利亞智庫的平均數(29,607),也低于全球智庫平均數(31,049)。在推特上,關注該智庫的人數呈現遞增趨勢,分別為14,898(2017 年)、22,563(2019 年)以及37,467(2021 年)人,這些數據均高于澳大利亞智庫關注人數(8,544)[17]。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在南海航行安全、新冠病毒溯源、新疆問題、香港問題等層面指手畫腳,發表偏離事實的言論,渲染反華輿論,配合美澳政府干涉中國內政,這與其資金來源有著密切關聯。國防部是其第一大資助方,且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也通過大使館等渠道對該機構輸送大量經費,委托其以智庫的名義對第三方開展調查研究或制造輿論。另外,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rup Grumman)、雷神公司(Raytheon)、法國泰雷茲集團(Thales)、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以及英國宇航系統公司(BAE Systems)等所謂國防企業也通過各種活動形式向其提供資助[18]。以2018 年為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經費收入為530 萬澳元,國防部的資助是其主要資金來源,占總經費的37%,委托收入占總經費的32%,會員贊助和訂閱占總經費的25%,其他占總經費的6%[6]。
作為一家官方背景濃厚的機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還扮演著“旋轉門”的角色,在政府、軍方、財團和知識界之間搭建起身份轉換和人員流動的平臺。自成立以來,該機構主要圍繞兩個研究議題展開,即國防與戰略計劃、國家安全項目,歷任領導人均具有軍方及政府背景。
2.2 高校智庫
高校智庫是澳大利亞智庫體系的一個特色,在國際智庫領域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傳統意義上,高校的功能主要包括人才培養、文化傳承等,社會服務和咨政建言并未納入其中。21 世紀以來,越來越多高校設立了研究機構,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跟蹤研究,并提供政策咨詢服務。澳大利亞擁有較為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和國際化人才儲備,這為高校智庫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保障。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各高校紛紛成立高校智庫,并逐漸打開局面,形成一定的研究特色和影響力。綜合近些年的《全球智庫報告》數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邦德大學全球化與發展中心、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等智庫蟬聯全球最具影響力智庫。與其他智庫不同,高校智庫所開展的政策研究一般注重長時段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是同行評議的公開發表作品;智庫研究經費也是通過競爭性方式從大學、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以及企業和基金會那里獲得[19]。
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亞典型的高校智庫,且具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力。該中心成立于1966 年,隸屬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是澳大利亞歷史最長、規模最大、排名最高的從事戰略研究、教育和評論的研究機構。該智庫聚焦亞洲戰略環境、澳大利亞與亞洲關系以及國際事務中的武裝力量應用問題[20]。該中心在軍事戰略研究方面更加關注澳大利亞國防、軍事問題研究以及亞太安全問題。歷年的《全球智庫報告》顯示,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一直位列澳大利亞最佳高校智庫榜首,全球排名也屬于前20%~30%之間。
2.3 獨立智庫
獨立智庫一般是指由企業、個人和信托基金發起成立的政策研究機構。這類機構一般自稱具有獨立研究、無黨派傾向、非營利等屬性。根據《全球智庫報告》歷年排名結果,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羅伊研究所、超越零排放機構(Beyond Zero Emissions)、獨立研究中心等被認為是澳大利亞最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問題研究獨立智庫。雖然此類智庫的設立并非由政府直接發起和資助,但是作為營銷政策和思想產品的機構,其并非真正的中立。事實上,許多獨立智庫由于接受了大公司或財團甚至政府變向的資金支持,其研究選題和咨政建議也自然難以維持所謂的“中立”性。以羅伊研究所為例,該智庫于2003 年由企業家弗蘭克·羅伊(Frank Lowy)出資和發起成立,作為一家全國性和綜合性智庫,總部設在悉尼,其成立之初,弗蘭克·羅伊提出“開展澳大利亞視野下的國際政治、戰略和經濟議題研究,這些研究需具有原創性和政策相關性”的發展定位。2012年,該研究所與澳大利亞慈善與非營利委員會(The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t-for-profit Commission)合作注冊,注冊名稱為“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簡稱羅伊研究所。
羅伊研究所的運轉除了依靠最初設立的研究基金,還接受來自包括澳大利亞國內外管理咨詢公司、外交部門的捐助。此外,可口可樂公司(The Coca-Cola Company)、瓦倫堡家族(the Wallenberg family)、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力拓集團(RioTinto)、必和必拓(BHP Group)等企業也是羅伊研究所重要的資助方。在政治立場上,羅伊研究所通常被歸入新自由主義、中右派的保守型智庫序列,以影響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為主要使命。雖然羅伊研究所宣稱其政策研究沒有黨派傾向和利益關聯,但是在實際工作中,該研究所研究議題的選定、政策產品的營銷、政策游說和媒體宣傳等通常會夾雜著智庫的態度和價值傾向,其對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國家的態度與對中國等國家的態度具有顯著的差別。澳大利亞政府也是羅伊研究所的捐助方之一,尤其是澳大利亞秘密情報局(The Australian Intelligence Service)、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澳大利亞總檢察長辦公室(Australian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國防部和國家評估辦公室(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等特殊政府機構對羅伊研究所的研究產生直接影響。因此,羅伊研究所在“中國南海問題”“新疆問題”“中東反恐問題”等方面與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外交戰略相呼應,甚至大肆鼓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攪動國際反華情緒。
羅伊研究所在公共關系和政策宣導方面具有較高的行業認可度,并在東亞研究、國際安全、太平洋島國研究、西亞研究、國際經濟研究、外交與民調等業務領域取得了一定成績,也因此受到了政客官員的關注。例如,在研究所成立初期(2003 年),澳大利亞時任總理霍華德在該智庫就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發表講話,可見澳政府對該智庫的重視程度。此外,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英國前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北約秘書長以及澳大利亞和各國外交部高官都曾訪問該智庫。名人的到訪既提升了智庫的知名度,也利用智庫為其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形成了政治利益共同體網絡。
2.4 智庫的政治哲學傾向
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角度來看,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雖彼此相互區別,但本質上卻是趨同的。與大多數英美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相似,那些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研究機構(有些甚至是更加保守傾向的)往往更容易獲得企業慷慨解囊。智庫為引起政府、社會精英和公眾的關注,通常會對具有所謂共識性的問題提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觀點。在部分智庫研究者看來,其使命不是順應公眾的思維,而是引導甚至超越公眾認識來對未來社會走勢提出預警。因此,一般保守派智庫更容易獲得各方的注意和支持。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最著名的保守派智庫包括獨立研究中心、公共事務研究所及其分支機構悉尼研究所。整體而言,澳大利亞智庫的政治傾向大致劃分為保守派、自由派、中間派、進步派和開明派,還有一些智庫的政治傾向難以界定。據研究顯示,2015 年澳大利亞43%的智庫具有右翼傾向,34%的智庫具有左翼傾向,23%的智庫屬于獨立的高校智庫[19]。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還包括非黨派利益傾向的保守型智庫。此類智庫持保守主義立場,但并不公開承認有政黨利益傾向,羅伊研究所就屬于此類智庫。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作為另一家典型的保守型智庫,其更加關注青年政治精英和大學生引導,培養具有保守主義理念的青年政治骨干作為澳大利亞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傳承人。
在澳大利亞,智庫并不總是享有正面的公眾形象,許多人將智庫描述為存在于陰暗世界從事暗箱政治的尖刻、腐敗、詭異的組織[21]。無論是公開承認智庫存在政治立場傾向還是將其隱藏,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研究通常與大眾思潮相背離,為中右思想提供智力支撐。因此,有時候這些智庫也被稱為“文化衛士”,其捍衛本國利益,說出一些其他人不愿意表達的觀點[22]。無論承認或不承認,智庫對政府決策的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專欄作家米里亞姆·羅賓(Myriam Robin)提出,近年來,堪培拉地區的智庫日益主導澳大利亞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澳大利亞國防部支持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成為“瓦解北京共識的引爆點”[23]。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尤其是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 年“基地”組織對美國發起的恐怖襲擊以來,對于決策者來說,信息時代革命包括數碼通訊、個人計算機、移動電話等都強化了經濟全球化[3]。國際局勢和信息技術的變化推動澳大利亞智庫崛起。同時,在社會變革趨勢之下,為了確立與政府之間的內在聯系,高校智庫紛紛得以成立,并實現教學、研究與公共影響的融合[3]。
3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特點
澳大利亞致力于打造與“中等強國”和區域大國身份相適應的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體系,體現了智庫發展的國家意志性。2019 年,澳大利亞《新日報》(The New Daily)曾以“影響澳大利亞的智庫”為主題,分別介紹了包括羅伊研究所、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公共事務研究所、澳大利亞研究所以及澳中關系研究院在內的澳大利亞最具政策影響力的智庫。這5 家智庫雖然發展歷史不長,但是卻產生了廣泛的政策和社會影響力。這些智庫的成立與發展既與其智庫成員的研究有關,又與幕后的資助方密切相關。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開展針對國家安全政策、外交事務、國際發展戰略等研究議題折射出澳大利亞自身的安全焦慮。長期以來,澳大利亞的發展戰略在依靠西方與融入東方之間搖擺,外交政策在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轉變,以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謀求更多的話語權,并藉此來實現其作為在東方的西方大國的價值。為了整合國內外資源方面,提升智庫在決策建議和輿論引導方面的作用,發揮旋轉門效應,澳大利亞政客、富商等紛紛為智庫站臺。例如,羅伊研究所研究者的成果常常呈現新自由主義和反華的傾向(neoliberal and anti-China leanings)[24]。這些所謂的政策成果受到包括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前外交部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首席國際通訊編輯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等積極的評價。近40 年來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異軍突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特點。
3.1 整體實力一般,但是特色鮮明,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智庫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智庫產品對政策制定、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等方面的實際作用。影響力是決定智庫建設質量的關鍵性指標,也是智庫政策產品發揮公共效用的體現。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是澳大利亞依然算不上智庫大國。根據麥甘團隊推出的《全球智庫報告》,在2010—2021 年間,澳大利亞上榜智庫數量維持在29~63 家之間。其中,羅伊研究所、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以及獨立研究中心等三家智庫躋身世界頂尖智庫陣營。2010—2011 年,麥甘團隊曾將澳大利亞作為亞洲區域國家進行智庫評價,研究結果顯示,羅伊研究所分別位列第8(共25家上榜)和第5(共30 家上榜),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位列第19(共25 家上榜)和第7(共30 家上榜)。自2012 年開始,麥甘團隊對評比規則做出調整,將澳大利亞與東南亞、大洋洲地區國家智庫并列評比,羅伊研究所、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獨立研究中心、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澳中關系研究院、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等智庫躋身地區頂尖智庫序列。其中,羅伊研究所、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獨立研究中心、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排名長期保持領先位置。
一直以來,澳大利亞有著深刻的安全憂慮,并逐漸陷入了所謂的“安全困境”。為了維護其國家安全,澳大利亞政府先后與英國和美國結成安全同盟,以西方國家成員定義國家身份,以西方大國為安全盟友,并在印度洋、南中國海、太平洋等地區劃定安全防線,積極配合、參與美國等國家主導的國際軍事行動。這些防務領域的政策出臺與澳大利亞智庫在防務和安全領域的研究特色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全球智庫報告》中,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等智庫擁有較好的全球排名。其中,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更是躋身全球防御與國家安全研究智庫的前10%(2020 年)。
近年來,澳大利亞對國際事務話語權一直懷有強烈的渴望,并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地區和全球事務,試圖提升澳大利亞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在此過程中,先后成立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羅伊研究所、戰略與防御研究中心、澳大利亞區域安全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ecurity)、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院、獨立研究中心和澳中關系研究院等智庫機構。其中,澳中關系研究院入選全球最佳高校區域研究智庫,澳大利亞區域安全研究所作為獨立智庫連續5 年(2016—2020)入選全球最佳智庫,位列前10%左右,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院全球排名也基本維持在前60%左右。
3.2 密切追蹤熱點前沿問題,推崇跨學科研究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在保持既有研究特色的同時,密切關注國際熱點問題,以跨學科研究方法開展特色化研究。例如,羅伊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長期深耕安全防務、外交等領域。近年來,國際發展開始成為這兩家智庫的新興領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同時,羅伊研究所向科學技術政策等領域研究滲透,形成了新的特色研究領域。隨著氣候變化成為熱點話題,包括羅伊研究所在內的智庫開始關注這一領域,并持續發聲,意圖樹立澳大利亞國際新形象。
為謀求區域大國地位,澳大利亞對亞太地區事務參與程度和廣度日益增強,對外交政策的需求也更加迫切,這也為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當前,澳大利亞智庫在防務安全與國際事務、國際發展、國際經濟等方面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研究與咨詢體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其諸多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國際同行的肯定,并躋身于世界頂尖智庫行列。
3.3 注重形象宣傳,擁有較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
根據《全球智庫報告》,羅伊研究所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被認為是能夠最有效利用社會網絡的智庫。其中,羅伊研究所在構建外部公共關系、引導公眾參與研究項目方面走在全國智庫的前列。羅伊研究所在國際民調、地區國家力量數據庫建設、政策宣導等方面也頗有建樹,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此,該智庫連續多年被評選為最佳網絡公關智庫(分別為2010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9 年 以及2020 年)。羅伊研究所在媒體利用(印刷媒體和電子媒體)、公共政策影響、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多年入選全球最佳智庫,在澳大利亞位居榜首。
近年來,澳大利亞國際問題智庫在宣傳倡導、跨機構合作、跨學科研究、高校智庫建設、獨立性、媒體使用、政策影響、區域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例如,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作為一家官方智庫,自2015 年以來連續六年入選全球最佳機構合作智庫;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獨立研究中心、超越零排放機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羅伊研究所自2015 年以來連續入選最佳獨立智庫。
4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存在的問題
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在本質上依然循著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傳統路徑,在研究議題、理論依據、話語體系、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一致性。綜合澳大利亞智庫發展歷程、體系構成和運行特點,可發現其中存在諸多問題。
第一,與國內外政府、企業和基金會形成利益共同體,成為利益集團的思想附庸。澳大利亞智庫與游說團體往往相互配合,鼓吹新自由主義。由于這些理念符合統治集團的利益,統治集團也會因此而給予其持續的資助,繼而構成了一個周期性的循環系統[24]。這極大地削弱了智庫的獨立性,使之偏離了智庫行業的行為準則。例如,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曾經從美國國務院獲得450,000 美元的資助(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稱實際額度不到230,000 美元),用于調查與中國保持科研合作的澳大利亞大學[25]。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接受國防部、外國政府、反華基金會等資助,發表缺乏理性和客觀性的言論,誤導公眾輿論,為保守勢力和利益集團代言,甚至不惜通過編造中國威脅論來回報其資助方,換取持續的資助,因此,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也毫無獨立性可言。
第二,研究議題簡單化,智庫產品的全面性和客觀性不夠。作為非政府行為體,智庫在澳大利亞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6]。然而,部分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為了回報資助方,提高自身在澳大利亞決策權和政策市場的影響力,常常對本身具有高度復雜性的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以是否能夠迎合資助方需求作為政策研究的標準,失去智庫研究的客觀性和全面原則。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溯源問題、中國新疆問題、中國南海問題等諸多涉華議題上,羅伊研究所、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等機構常常以澳美政府主張為政策研究出發點,以所謂學術研究之名將上述問題簡單化,以“二元對立”的分析思維解讀對華關系,鼓吹對抗和遏制戰略,延續“冷戰”思維,助推地區局勢緊張態勢。
第三,政策研究泛政治化,戰略定力不夠。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研究領域雖然相對寬泛,但主要是圍繞安全、經濟、外交等議題展開研究,在“政治正確”原則之下,部分智庫常常將非政治問題政治化,將一般問題嚴重化,將地區問題國際化,其目的依舊是呼應澳大利亞國防部以及美國等國家政府部門和利益集團的主張。由于澳大利亞長期依賴英美等盟友參與國際治理,缺乏獨立外交的傳統,因此,無論是政府的外交政策穩定性還是國際問題智庫的研究定力均存在問題。例如,2018 年以前的相當長時間內,中澳關系整體穩定,澳大利亞智庫的涉華研究也大體較為客觀;然而,自2018 年以后,包括羅伊研究所在內的研究機構所發布的涉華言論明顯傾向于負面,部分機構甚至將教育、移民、經濟、人文交流等問題政治化,鼓吹中國戰略滲透,從而配合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
5 結語
本文對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的發展歷程、體系構成和運行特點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有利于形成關于澳大利亞智庫體系的整體性認知。同時,本文對智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判性地分析,指出澳大利亞智庫在獨立性、客觀性和戰略性方面的不足,形成在智庫獨立性與利益集團依附性之間游走的發展模式。在諸多全球和地區問題上,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往往遵循贊助人和利益資助集團的訴求,為營造特定輿論氛圍,推行特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成為利益集團的思想附庸。這一特質對全面評價澳大利亞智庫及其與外交政策制定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我國解讀澳大利亞智庫報告、政府決策機制提供了依據。
當然,《全球智庫報告》的客觀性和全面性也存在諸多問題,在實踐中需要以批判的態度參考使用。在針對該報告涉及澳大利亞智庫內容的分析過程中,本文發現該報告未充分考慮不同國家政治體制這一因素,其智庫發揮政策影響的渠道也存在差異。《全球智庫報告》更多的是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智庫體系為標準,衡量全球不同國家智庫體系,存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麥甘智庫評價報告存在的爭議性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智庫遴選標準、對智庫影響力評價體系、對區域智庫分類、內部不同評價項目之間的協調性等方面均存在問題;對智庫評定的過程(參評人員的傾向性)、智庫影響力的顯性問題與隱性問題,尤其是隱性層面的不可觀測性,智庫對政策影響的直接性與間接性也有諸多問題存在。因此,國內智庫研究學界要做到謙虛謹慎,立足中國國情,加快構建符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要求的評價體系和科學標準[27],以提高我國智庫研究的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