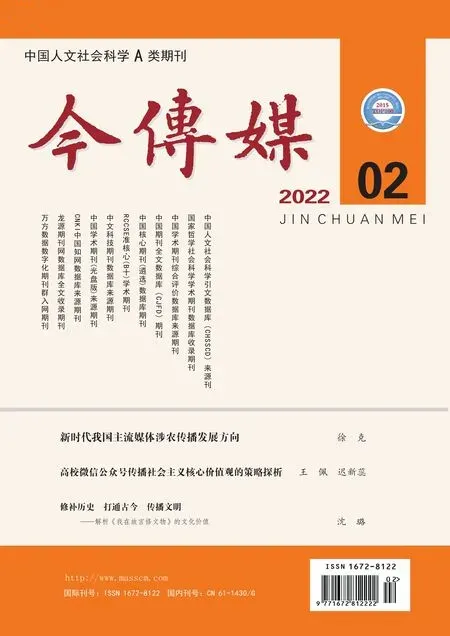論近年來主旋律電視劇的敘事策略
季 靜
(南京郵電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2021年初,由正午陽光出品的扶貧劇 《山海情》引發了一波主旋律電視劇熱潮。該劇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在村干部馬得福的帶領下,貧瘠的寧夏西海固地區涌泉村村民,憑借自己的艱苦奮斗和福建省的援助幫扶,最終脫貧致富、建設新家園的故事。不同于以往主旋律電視劇“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遇,《山海情》一經播出便受到觀眾的廣泛好評,豆瓣評分達9.4,在愛奇藝、優酷、優騰等視頻播放平臺的評分也高達9.5,成為近五年來評分最高的國產劇。在2021年的上海電視節上,《山海情》以九項提名領跑,并最終獲得了包括“最佳電視劇”在內的四個獎項。《山海情》為主旋律電視劇如何打破刻板、宣教的藩籬,在內容蘊涵和形式表達上有所創新,成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優秀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一、宏大敘事下的精深細節刻畫
主旋律電視劇承載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對塑造國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肩負傳遞時代聲音、詮釋時代主題的重要職責。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布:“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山海情》這部主旋律電視劇正是以宏大的敘事視野,講述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脫貧攻堅事業,不僅成為脫貧攻堅歷史的縮影,也是時代大潮下波瀾壯闊的史詩。在如此宏大的主題之下,《山海情》的創作者們沒有一味煽情和說教,而是在宏大敘事的框架下從個體角色出發詮釋脫貧攻堅的困難與成效,進行精深的細節刻畫。脫貧攻堅的主題被嵌入在這些看似碎片化、日常化的敘事中,非但沒有遮掩主題的嚴肅性,反而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在觀眾的感動與共鳴中實現了價值創造。
(一)用人物經歷召喚集體記憶
影視作品可以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表征,在對集體記憶的捕捉和召喚中產生集體凝聚力。尤其是對年輕觀眾來說,他們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年代,貧困對于他們來說是難以感同身受的體驗,宏大主題下的扶貧故事只有通過描述具體人物的具體經歷,才能夠被觀眾理解和接受,進而成為共享的集體記憶。
《山海情》以冷靜、克制的敘事態度,通過不同人物的經歷將現實的殘酷與脫貧的不易展現得淋漓盡致。熱依扎飾演的水花因為貧困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又被父親嫁給了鄰村的村民換取物資。女子的自由與幸福在極度的貧困面前敵不過一口水窖、一頭驢,“將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并非為了夸張或者煽情,而是更加深刻地表達貧困的悲哀與無奈。馬得寶去新疆尋找尕娃卻被人賣到黑煤礦強制勞動,是對“黑工廠”存在歷史的還原與殘酷刻畫。麥苗遠離家鄉到福建工廠務工,從聽不懂福建話、學不會流水線操作,到成為廠里的業務骨干、救火英雄,是20世紀90年代“打工潮”的縮影和真實寫照。背井離鄉的不舍、留守孩童的思念、創業打拼的艱辛,總有某種情感能牽動觀眾的情緒,引起觀眾的共鳴。這些故事與細節的相互交織,為 《山海情》注入了多維度的視野與多元的歷史背景,將“大歷史”落在“小人物”身上,既真實可感,又真切動人。
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說:“凡是通過感觀印象儲存起來的記憶,都比通過語言重復這種媒體儲存起來的記憶更加具有無與倫比的直接性和真實性。”中國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正是透過水花隱忍的淚水、得寶額頭上的傷疤、金灘村種出的第一茬雙孢菇這一樁樁小事傳遞給觀眾的,以一種具象化的、帶有情感溫度的方式被觀眾感知、理解和記憶。正因如此,《山海情》的整體敘事非但沒有說教意味,反而更顯真實質樸、饒有趣味,關于貧困與脫貧攻堅的集體記憶在人物故事的講述中被刻畫和記憶。
(二)用精良制作增強藝術真實
主旋律電視劇向來不乏鴻篇巨制,但高昂的投入并不一定代表著制作精良。《山海情》在制作方面擁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使整部劇呈現出一種匠心獨運的精致感。首先,眾多演技精湛的優秀演員貢獻了杰出的表演。從主要演員到配角,沒有一個讓觀眾出戲的角色,演員和角色融為一體,甚至讓觀眾忘記了演員的表演只看到了角色,熱依扎飾演的水花、張嘉譯飾演的馬喊水、尤勇飾演的李大有在劇集播出期間都曾因為精湛的表演成為網絡熱門話題。方言對話雖然對演員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卻通過聲音元素營造了真實的熒屏空間,讓觀眾仿佛置身在貧瘠的寧夏西海固地區。
其次,考究的服飾、化妝和道具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與可信度。演員臉上的“高原紅”、干裂的嘴唇、干枯打結的頭發、沾滿黃土的破布鞋都在無聲地訴說著西海固的貧瘠與生活的艱難。無論從劇情的時間維度還是空間維度上看, 《山海情》都是經得起推敲的,更是被觀眾稱為“細節控”“良心劇”。搪瓷水杯、二八大杠自行車、尼龍襪等道具精準地契合了故事的年代背景,以物的方式塑造著故事空間的真實感,通過物的再現喚醒觀眾的記憶,從而和觀眾產生情感共鳴。
再次,相比動輒五六十集的長篇電視劇,二十三集的 《山海情》顯得短小精煉,敘事節奏緊湊,主題集中不渙散。所有情節、人物緊緊圍繞脫貧攻堅的主題,僅有的幾段感情戲也是隱忍克制的,沒有刻意渲染和煽情。水花和得福兩人美好的初戀在貧困面前不堪重負、難以為繼;麥苗和得寶為了擺脫貧困各自歷經艱苦終于修成正果。感情戲的存在不僅沒有分散主題,反而為劇集注入了溫度,以脫貧攻堅奮斗過程中愛情的苦澀與甜蜜增強劇中情節的感染力。
二、打造價值內涵豐富的視聽符號體系
隨著數字媒介和電子媒介的興起與普及,形成了一種以圖像為主導的文化景觀,包括電影、電視、廣告等在內的視聽藝術紛紛運用具象的意指符號來展現日常生活圖景。法國結構主義代表人物羅蘭·巴特認為,“圖像符號比文字符號更易被大眾接受,因為圖像符號與文字符號相比,圖像的特征與日常對象比較接近,觀眾解讀圖像符號的方式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現實世界的方式類似。”因而相較于文學作品,影視劇的圖像化特征更具有普遍的受眾基礎。真實記錄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運用影像傳遞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這類現實題材主旋律電視劇的歷史價值。
(一)精準的視聽符號選擇
《山海情》通過多元的視聽符號再現涌泉村的脫貧故事,以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視聽符號體系感染和啟迪觀眾。例如第一集中,政府給涌泉村的81只珍珠雞,本意是想讓村民通過發展養殖業從而實現脫貧,然而卻被村民吃得僅剩1只。僅有幾個鏡頭的珍珠雞把涌泉村貧困、艱難的生活生動刻畫了出來,這種收效甚微的物質扶貧與之后的技術扶貧、產業扶貧形成鮮明對比。第十九集中,白校長帶領小學生們在歌唱比賽上唱的 《春天在哪里》,通過歌曲傳遞出孩子們心中的向往和憧憬,這首歌頌春天的歌曲也象征著閩寧村村民對多年脫貧攻堅成果的贊許,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更多期待。通過熟悉的旋律召喚共同記憶,與觀眾共情,精準的視聽符號既能準確傳達敘事信息、引發情感共鳴、啟迪觀眾思考,同時也能夠確保“短平快”的敘事節奏,避免拖沓冗長。
(二)鄉土情懷與時代精神的碰撞和融合
西海固地區惡劣的自然條件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當人們走出大山,依靠自己的艱苦奮斗過上好日子的時候,卻沒有忘卻故土。劇情中當政府決定讓涌泉村整村搬遷離開貧瘠的西海固時,老一輩的村民說“根在這里”“先祖在這里,死也要死在這里”。這里的“根”代表了一種傳統的價值主張,一種深切的鄉土情懷。雖與年輕一輩認同的現代觀念和時代精神有差距,但兩者并不沖突對立,正如劇中臺詞所言“涌泉村的根有兩頭,一頭在過去,一頭在將來”。這些符號所代表的就是“面向未來,但不要忘記過去”,這也是對既往扶貧事業以及未來生活的一種告誡:既不能忘記曾經的艱苦生活,更要通過不斷奮斗創造未來。最后一集中,黃茫茫的山坡在視聽符號的互動中變成了綠水青山,大大拓展了全篇視聽符號的內涵,給觀眾創造了想象空間。新一代的子孫們從城市回到綠意盎然的西海固,代表著未來對過去的回望,象征著鄉土情懷的傳承與延續。
三、以真實事件改編,與觀眾真誠對話
巴赫金指出“對話是存在于主體間自我意識中的意義建構。”基于對話理論,巴赫金又提出復調小說的概念,“認為復調由各自獨立、具有自身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眾多主人公及其聲音都有相對的自由和獨立性,每個人真正的個性都得到保留。”用對話理論來考察影視作品,我們會發現一些影視作品也具備類似復調小說的特點。《山海情》中的主要角色都擁有自己獨立的故事線,這些故事線之間有交叉重合也有對立沖突,其作用在于“發展對話”,即推動情節發展。
(一)具有真實原型的代表性人物
《山海情》扎根現實的土壤進行藝術創作,多數情節和主要人物是在現實原型的基礎上再創作的,為與觀眾真誠對話提供了基礎與可能。閔寧鎮真實存在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張樹成的原型是閔寧鎮書記李雙成,他在完成寧夏西海固地區整村搬遷工作后遭遇車禍去世;福建菌草專家凌一農教授的原型是林占熺教授,他長期奮斗在科研、扶貧、援外第一線。這些基于現實原型的創作與西海固地區勞動人民的形象相呼應,為該劇增添了真實的質感。
不同于以往主旋律電視劇直接以真實人物原名呈現的模式,如 《焦裕祿》 《任長霞》等,《山海情》雖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卻不完全還原真實,而是通過更多的藝術創作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更強的可塑性。在劇集播出的過程中,觀眾通過新聞資訊、社交媒體等渠道獲知劇集中人物有其相對應的真實原型,既豐富了該劇的信息量,又使得真人真事在劇集的鋪墊和渲染之下擁有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
《山海情》還打造了很多生動的配角。這些配角雖然沒有現實中對應的真實原型,但在真實感、生動性上絲毫不遜色于主角。筆者認為其中最出彩的人物是李大有,這個有些小心機、目光短淺、刺頭、脾氣暴躁的農村大爺令觀眾“又愛又恨”。這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他市井、貪便宜、短視,經常做出一些令人生氣的事情,但人們又會因為他的滑稽、可愛和骨子里的淳樸而原諒他。這種“有缺點的小人物”讓觀眾有極強的親切感,“李大有”雖是一個虛構人物,但又確實是某一類人的真實寫照,似乎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身邊都存在“李大有”這樣的人,進而與觀眾的生活經驗、真實經歷形成了“對話”。
(二)能被觀眾理解的共通性情感
《山海情》沒有刻意渲染、烘托人物的崇高,而是從能被觀眾理解的共通性情感入手,在看似平實、質樸的講述中,逐步積累好感,最終打動觀眾。張樹成因為涌泉村幾個吊莊戶的逃跑而被女縣長訓話,縣長下了必須把人勸回的命令。沒有過多的鋪墊和渲染,脫貧攻堅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到了涌泉村以后,張樹成面臨著諸多困難:吊莊戶的抵觸、村民們的不配合,接二連三的意外導致工作難以開展。但上級的命令像一個緊箍咒,不論多么艱難,張樹成也要完成任務。《山海情》沒有渲染刻畫人物行為的內在動力,比如理想信念、信仰使命等,而是給出了直觀可見的外在動因,比如上級命令,張樹成完不成涌泉村吊莊任務就無法向縣長復命。這是一個能被所有觀眾理解、甚至感同身受的理由,不由得聯想到自己在接到棘手工作時的心情,因而使觀眾產生了強烈的共情。馬得福作為村干部,和第一批金灘村移民在戈壁灘上艱苦奮斗了幾年,可金灘村依然沒通上電、用不了灌溉水,他還經常吃力不討好、受到村民的埋怨。馬得福說:“是我把你們勸來的,你們過不上好日子,我咋向你們交代嘛!”一句話就讓觀眾理解了馬得福,理解了他為什么甘愿把自己的青春揮灑在戈壁灘上,理解了他為什么寧愿忍受憋屈、誤解也要堅持自己的工作。
正是因為人物的情感和動機能被觀眾所理解、能讓觀眾產生共鳴, 《山海情》才能夠切實地打動觀眾。不去“拔高”人物,讓觀眾以平視的視角來觀察人物,用共通的情感、相似的經歷和觀眾“對話”,讓觀眾從理解到相信再到感動,在情感的遞進中實現價值創造和意義傳遞。創作者們完全不必擔心主要人物的“祛崇高化”會削弱主題的教育性、宣傳性;相反,有血有肉、甚至有小缺點的人物更受觀眾喜愛,并且隨著劇情的開展,觀眾會自然而然地被打動,主題的宣傳教育性和感染力也就“潤物細無聲”地實現了。
四、結 語
《山海情》作為2021年最受歡迎的主旋律電視劇之一,在宏大的敘事脈絡之下進行了精深的細節刻畫,細膩真實地反映了寧夏西海固地區人民的脫貧歷史;在視聽符號選擇上精準簡練,引起觀眾共鳴、引發觀眾思考,打造了價值蘊含豐富的視聽符號體系;通過對真實故事的改編,以共通性情感為切入點,實現與觀眾的真誠對話,使得劇集擁有了能夠令觀眾為之動容的質樸與溫情。《山海情》為主旋律電視劇樹立了一個范本,期待未來有更多優秀的主旋律作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