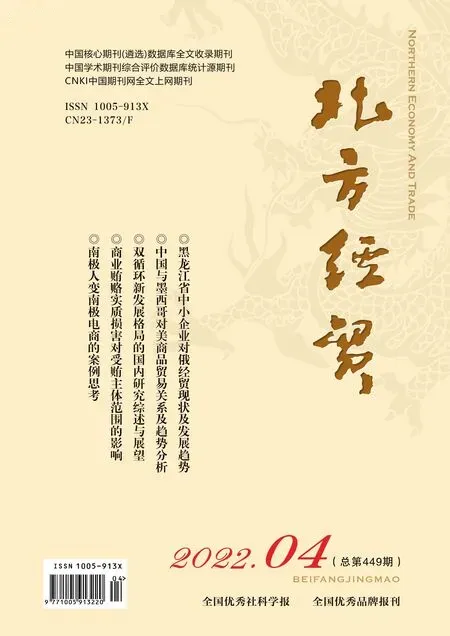商業(yè)賄賂實質(zhì)損害對受賄主體范圍的影響
文 弘
(山東大學(xué) 法學(xué)院,濟南 250100)
一、商業(yè)賄賂受賄主體的發(fā)展與矛盾
我國對于商業(yè)賄賂的規(guī)定最早出現(xiàn)在1993年實施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以下簡稱老反法)第八條,該條款以行賄人和受賄人的賄賂關(guān)系為切入點,重點關(guān)注收受回扣這一行為方式,條款內(nèi)容相對粗略與單一,但對于立法之際的市場競爭環(huán)境而言,其規(guī)制效果差強人意。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市場競爭關(guān)系日趨復(fù)雜,該商業(yè)賄賂規(guī)制條款在調(diào)整對象、構(gòu)成要件、法律責(zé)任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弊端與缺陷,無法應(yīng)對層出不窮的商業(yè)賄賂問題,其規(guī)制力度與效果均有不足。因此,2017年新修訂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以下簡稱新反法)對商業(yè)賄賂條款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變動與調(diào)整,其中最為突出的變化在于跳出了原來賄賂關(guān)系中行賄者與受賄者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相比于老反法將受賄主體籠統(tǒng)規(guī)定為“對方單位或者個人”,新反法通過列舉的形式極大地擴充了受賄主體的范圍,具體包括交易相對方的工作人員、受交易相對方委托辦理相關(guān)事務(wù)的單位或者個人以及利用職權(quán)或者影響力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共三類,這為商業(yè)賄賂的法律認(rèn)定提供了更為具體與明確的指引。
新反法對于商業(yè)賄賂的規(guī)定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豐富,但修訂前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仍然沒有對商業(yè)賄賂的內(nèi)涵進行明確的界定,也未給出行為規(guī)制的原則性規(guī)定。從前后兩個版本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來看,對于商業(yè)賄賂的認(rèn)定更多地是從法律條文給出的行為主體、行為方式、行為目的等因素進行逐一匹配,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即為商業(yè)賄賂。通過比對修訂前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新反法雖將老反法規(guī)定的受賄主體“單位或者個人”具體細(xì)化為三類,但在擴充的同時卻也略去了交易相對人本身。從文義解釋來看,老反法所指的“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必然包括交易相對人本身,但新反法第七條第一款第一項只規(guī)定了交易相對方的工作人員,而非交易相對方或其工作人員,顯然已將交易相對方排除在外。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根據(jù)法律的歷史解釋與體系解釋,交易相對方應(yīng)然成為受賄主體之一,新反法的規(guī)定確有瑕疵,但卻不影響最終受賄主體的認(rèn)定。但結(jié)合整個第七條的規(guī)定來看,其第一款第二項與第三項兩項內(nèi)容均以“單位或者個人”結(jié)尾,唯獨第一款缺失了“單位”,并不像是因疏忽而導(dǎo)致的漏寫。
通過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彈性的一般條款使得法律調(diào)整的范圍具有開放性,而相對明確卻無兜底條款式的列舉行為,則使得法律的適用范圍受到限制。因此,交易相對人是否作為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這在學(xué)術(shù)界中存在一定的爭議。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在設(shè)計商業(yè)賄賂規(guī)制條款,尤其是采用列舉式規(guī)范時,自然而然應(yīng)當(dāng)將重心置于行為之上而非主體方面,但主體要件作為商業(yè)賄賂構(gòu)成要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此爭議置于“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并不利于對商業(yè)賄賂行為的規(guī)制。此外,商業(yè)賄賂受賄主體的爭議或許能夠上升為更深層次的以下問題:決定某類主體能否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受賄主體的因素是什么?立法中的三類主體是對實踐中的總結(jié)歸納亦或是法理上的涵括列舉?這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其不同的回應(yīng)都將影響對于商業(yè)賄賂更深層次的認(rèn)識。
二、商業(yè)賄賂對競爭秩序的損害事實
(一)商業(yè)賄賂的顯性損害
商業(yè)賄賂的顯性損害是指實施商業(yè)賄賂該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所展現(xiàn)出直接的、外在的損害事實,該損害事實雖能造成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最終結(jié)果,但卻無法將商業(yè)賄賂與其他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進行區(qū)分。競爭行為正當(dāng)性的判斷一直是司法案件的判斷焦點,商業(yè)賄賂的顯性損害是背離競爭行為正當(dāng)性的直接體現(xiàn),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兩方面:
其一是對市場的信用體系的破壞。《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二條規(guī)定了經(jīng)營者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中,應(yīng)當(dāng)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信用在經(jīng)濟學(xué)中是指在市場交易之時依附在個人、單位所形成的一種相互信任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社會關(guān)系。對于一個經(jīng)營者而言,信用既是一種無形資產(chǎn),也是一種重要的競爭優(yōu)勢,消費者等其他交易相對人都愿意與具有良好信用的經(jīng)營者進行反復(fù)、長久的交易。市場秩序的有效維護與市場規(guī)律的穩(wěn)定運作都離不開一個完整良好的市場信用體系,但商業(yè)賄賂這種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卻通過非公開、非正當(dāng)?shù)呢斘锝灰钻P(guān)系,嚴(yán)重地削弱了信用因素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造成市場信用體系的破壞,進而導(dǎo)致市場的混亂與無序。在信用體系無法有效發(fā)揮作用的市場環(huán)境下,交易雙方的經(jīng)濟活動增加了無意義且本可避免的交易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都將均攤至該市場的每一位主體之中,造成公眾福利的削弱。經(jīng)營者所實施的商業(yè)賄賂行為在對市場信用體系造成破壞的同時,同樣會受到來自于市場秩序的反作用,極大地降低了經(jīng)營者自身的信用價值,成為一種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的互換行為。
其二是不利于市場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中,價格機制是引導(dǎo)市場主體作出相應(yīng)經(jīng)濟活動的有效工具。價格既反映商品的社會價值,又反映商品的社會成本。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經(jīng)營者能夠根據(jù)現(xiàn)有市場所反饋的信息,對生產(chǎn)內(nèi)容、生產(chǎn)數(shù)量、生產(chǎn)時機作出有效判斷,以最終實現(xiàn)資源的有效配置。商業(yè)賄賂這一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容易導(dǎo)致價格機制失靈,使得經(jīng)營者所創(chuàng)造的社會資源不自覺地向行賄方聚攏,最終導(dǎo)致社會資源無法流向正確的地方,造成資源配置不平衡不合理,甚至阻礙資源合理配置情況下的科技進步與技術(shù)革新。
(二)商業(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
商業(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是指實施商業(yè)賄賂該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所具有的內(nèi)在性與實質(zhì)性的損害事實,該損害事實是使商業(yè)賄賂能夠直接造成市場競爭秩序受到破壞這一最終結(jié)果的關(guān)鍵因素,同時也能夠?qū)⑸虡I(yè)賄賂與其他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進行有效區(qū)分。
商業(yè)賄賂這一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對市場信用體系和資源配置同時造成了一定的負(fù)面影響,但這些危害效果在其他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中都有一定程度體現(xiàn),因此,商業(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不在于此。經(jīng)營者作為市場最主要的構(gòu)成主體,在進行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擁有獨立的人格和意志。經(jīng)營者試圖通過商業(yè)賄賂這一不正當(dāng)競爭手段來爭奪交易機會或競爭優(yōu)勢,但交易行為的達成與否最終還是取決于交易雙方獨立的交易意志。以經(jīng)營者中最常見的企業(yè)為例,企業(yè)具有自己的決策機構(gòu)和執(zhí)行機構(gòu),能夠在法律意義上形成企業(yè)的整體意志并通過自己的運營機構(gòu)付諸實施。作為一個理性的經(jīng)濟人,企業(yè)總會根據(jù)其所掌握的市場信息從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決策,這是經(jīng)濟人趨利避害的本質(zhì)使然。企業(yè)人格獨立是公司法乃至整個商法體系的基石,對市場秩序的正常運轉(zhuǎn)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正常的市場競爭模型下,企業(yè)甲選擇與企業(yè)乙達成交易,而非選擇企業(yè)丙或其他企業(yè),這是由于與企業(yè)乙進行交易的這一項決策是企業(yè)甲在其所掌握的市場信息后所作出的最優(yōu)選擇。若是企業(yè)丙通過商業(yè)賄賂的手段對企業(yè)甲內(nèi)部的員工進行行賄,以謀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yōu)勢,導(dǎo)致企業(yè)甲選擇與企業(yè)丙進行交易的結(jié)果,此時企業(yè)甲所作出的交易行為,并非是一種最優(yōu)的經(jīng)濟活動決策,也并非符合企業(yè)甲獨立自主的決策意志。企業(yè)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獨立自主地作出市場決策與該決策最終是由具體的自然人所作出的這一事實兩者之間并無矛盾,但企業(yè)員工為謀求自身的不當(dāng)利益,而影響企業(yè)獨立自主做出決策的行為,則需要為法律所規(guī)制。若對該行為放之任之,企業(yè)的獨立人格將會淪為空談,企業(yè)制度也將會成為個人謀求不正當(dāng)利益的重要手段。
競爭行為天生攜帶著威脅他人利益的基因,通過簡單的交易模型分析,企業(yè)丙實行的商業(yè)賄賂行為,其實質(zhì)損害并不在于該行為損害了企業(yè)丙與企業(yè)乙在競爭過程中對企業(yè)乙的不正當(dāng)影響,而是最終影響了企業(yè)甲,即交易相對人的決策自由。因此,商業(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在于該行為破壞了經(jīng)營者獨立自主的經(jīng)營人格,對經(jīng)營者的決策自由造成了不良影響或具有造成不良影響的風(fēng)險。值得注意的是,交易相對人的概念比經(jīng)營者更為廣泛,還應(yīng)包括消費者等能夠獨立參與市場經(jīng)濟活動的相關(guān)主體。商業(yè)賄賂通過對交易相對人獨立人格的蠶食,影響交易相對人在經(jīng)濟活動中自主的決策,繼而嚴(yán)重破壞自由的、正常的市場秩序,這便是商業(yè)賄賂對競爭秩序的損害路徑。
(三)損害路徑對受賄主體范圍的影響
商業(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已經(jīng)明晰,特定主體能否通過收受賄賂的方式,繼而達到對經(jīng)營者決策自由的影響,便是受賄主體與非受賄主體的界限所在。
通過分析新反法的第七條第一款,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三類主體均能對經(jīng)營者的自由決策產(chǎn)生影響。其一,交易相對人的內(nèi)部員工:經(jīng)營者的決策機構(gòu)本身就是由其內(nèi)部工作人員所構(gòu)成,因此內(nèi)部員工在利益的驅(qū)使下能夠偏離經(jīng)營者的整體意志對某項決策的作出造成有效且直接的影響;其二,受交易相對方委托辦理相關(guān)事務(wù)的單位或者個人:鑒于兩者之間存在的委托關(guān)系,受托人為謀求不當(dāng)?shù)睦妫耆茉谑帐苜V賂的情況下,影響甚至直接代表委托人進行商業(yè)活動決策;其三,利用職權(quán)或者影響力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該條文使用“影響交易”的直接表述更為明確地體現(xiàn)了此類主體對交易相對人決策的影響力。
回歸“交易相對人”能否作為受賄主體的問題。交易相對人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市場地位,在市場經(jīng)濟活動中能夠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一方經(jīng)營者向交易相對人給予非公開、非正當(dāng)?shù)呢斘镆灾\求交易機會,雙方最終達成交易,在此過程中,交易相對人在市場經(jīng)濟活動中的獨立地位和自主決策的能力是否受到影響?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市場主體在進行經(jīng)濟活動的過程中,其決策行為須符合自身的利益且基于其所掌握的市場信息,由于潛在的交易相對人是不計其數(shù)的,忽略所掌握市場信息的這一前提,便無法探討何為最佳的決策。企業(yè)乙與企業(yè)丙作為市場競爭對手,都渴望與企業(yè)甲達成交易,假設(shè)企業(yè)甲根據(jù)其所掌握的市場信息,通過比較企業(yè)乙與企業(yè)丙的各方因素,認(rèn)為選擇與企業(yè)乙進行交易是當(dāng)下最佳的決策行為。若企業(yè)丙向企業(yè)甲實施商業(yè)賄賂,此時企業(yè)甲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必將考慮接受賄賂所能帶來利益的這一因素,最終轉(zhuǎn)向與企業(yè)丙進行交易,該決策轉(zhuǎn)變更為深層次的制度機理在于,理性的行為人能夠根據(jù)某種標(biāo)準(zhǔn)對自己希望獲得的東西進行排序。因此,企業(yè)甲所作出的最終決定并非是由于企業(yè)甲的決策自由受到商業(yè)賄賂的影響,相反,該行為恰恰是企業(yè)甲獨立自主決策行為的體現(xiàn)。從邏輯上來看,不存在“自己受到自己的影響”與“自己影響了自己”的這種情況,它與受到第三方主體的影響并不相同。因此,通過對交易相對人予以非公開、非正當(dāng)?shù)呢斘锝灰撞⒉荒軌蛟斐缮虡I(yè)賄賂的實質(zhì)損害后果,即它對交易相對人獨立自主的決策能力并無影響,也正因如此,新反法未將交易相對人納入受賄主體之列,并非是一項立法疏忽,而正是基于對商業(yè)賄賂損害實質(zhì)的考量,最終將其排除在外。
三、商業(yè)賄賂受賄主體的實踐印證
(一)我國商業(yè)賄賂案件的實踐情況
截至2021年12月,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中以“商業(yè)賄賂”作為關(guān)鍵詞,并選擇“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競爭糾紛”的案由選項,共顯示出相關(guān)文書105篇。排除裁定書以及案件內(nèi)容與商業(yè)賄賂無關(guān)的判決書,最終符合要求的商業(yè)賄賂案件僅有18件。在此其中,以新反法的實施年份2018年為界,根據(jù)這18件案件的終審時間進行分類,在2018年1月1日之前的商業(yè)賄賂案件共有兩件,而201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則有16件;根據(jù)案件當(dāng)中的受賄主體進行分類,受賄主體為交易相對人員工的案件共有16件,剩下兩件案件分別是中國聯(lián)通昭通市分公司訴中國移動昭通市分公司商業(yè)賄賂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案,以及濮陽縣巨鑫商貿(mào)有限公司與耿瑞芬、杜海波商業(yè)賄賂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案。從這兩個案件的受賄主體和案件結(jié)果來看,前一案件的受賄主體為交易相對人本身,但法院最終并未將其認(rèn)定為商業(yè)賄賂;后一案件雖然被認(rèn)定為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但該案件受賄主體的類型有待商榷,將在后文論述。
在中國聯(lián)通昭通市分公司(以下簡稱昭通聯(lián)通)訴中國移動昭通市分公司(以下簡稱昭通移動)商業(yè)賄賂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案中,昭通聯(lián)通與昭通移動均是昭通市電信服務(wù)領(lǐng)域內(nèi)的同類經(jīng)營者。為爭奪當(dāng)?shù)氐碾娦欧?wù)市場,提高市場用戶占有率,昭通移動在昭通學(xué)院開學(xué)之際舉辦了“我的青春要移動”的宣傳活動,向昭通學(xué)院的大學(xué)生發(fā)放充電寶、藍牙耳機等禮品,推廣其運營商的手機卡。昭通聯(lián)通認(rèn)為,昭通移動直接向消費者派送禮品的行為導(dǎo)致部分聯(lián)通用戶轉(zhuǎn)向使用移動手機卡,造成聯(lián)通用戶客源的減少,屬于不正當(dāng)競爭的商業(yè)賄賂行為。對于昭通聯(lián)通的指控,昭通市昭陽區(qū)人民法院最終以昭通聯(lián)通所提交的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其訴訟的事實主張為由駁回了聯(lián)通公司的訴訟請求,即昭通移動的行為不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雖然該案件的判決文書并未對昭通移動的行為不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的理由進行具體闡述,但該案的案件事實相對清楚,能夠為“交易相對人”無法納入至商業(yè)賄賂受賄主體的觀點提供了很好的司法實踐支持。回歸到本案中,誠然,在昭通聯(lián)通與昭通移動相互競爭的電信服務(wù)市場中,每一個具體消費者均是“交易相對人”本身,消費者們在選擇何種電信服務(wù)運營商之時,將會對每個電信服務(wù)運營商所提供的服務(wù)質(zhì)量以及其他相關(guān)因素進行綜合考量,而昭通移動所派送的充電寶、藍牙耳機等禮品,都將成為消費者在選擇何種電信服務(wù)運營商之時的重要因素。這些消費者最終選擇了昭通移動,并非是由于收受“賄賂”導(dǎo)致個人判斷受到了影響,反而正是在消費者自身獨立意識的基礎(chǔ)上所作出的選擇。該案件很好地詮釋了本文如上論述的理論模型,通過司法實踐的方式證明了“交易相對人”不能成為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
(二)域外商業(yè)賄賂的立法規(guī)定
商業(yè)賄賂的外觀形式雖然在古代也曾出現(xiàn),但作為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概念,商業(yè)賄賂實質(zhì)上還是一種在市場經(jīng)濟體制背景下所衍生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其在定義上也未有統(tǒng)一的國際標(biāo)準(zhǔn)。以德國為例,其1909年實施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當(dāng)中就對商業(yè)賄賂進行了如下規(guī)定:“在商業(yè)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向企業(yè)的職員或受托人提供、允諾或給予某種利益,以使其在采購商品或服務(wù)時以不正當(dāng)方式優(yōu)待自己或某個第三人。”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在該法條中的表述是“企業(yè)的職員或受托人”,并未將“交易相對人”納入受賄主體。對于市場經(jīng)濟最為發(fā)達、市場競爭最為激烈的國家——美國,其對于商業(yè)賄賂的規(guī)制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學(xué)、系統(tǒng)的法律體系。為了打擊商業(yè)賄略犯罪,美國先后制定并頒布了《虛假索取法》《克萊頓法》《反回扣法》《魯濱遜——帕特曼法》《海外反腐敗法》《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禁止海外賄賂法》等法津規(guī)范,通過這些法律規(guī)范,絕大多數(shù)的商業(yè)賄賂行為都能被加以管制,賄賂關(guān)系中主體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充。美國《布萊克法律詞典》對商業(yè)賄賂作出如下定義:“商業(yè)賄賂是指賄賂的一種形式,是競爭者通過秘密收買交易對方的雇員或代理人的方式,獲取優(yōu)于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優(yōu)勢”。從該定義來看,對于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依然限于“交易對方的雇員或代理人”,與德國的法律表述在“交易相對人”能夠作為受賄主體的這一問題上具有一致性。
從德國與美國的法律規(guī)定來看,雖然西方發(fā)達國家對于商業(yè)賄賂的法律規(guī)定較于我國更為成熟,但在受賄主體的選擇上與我國的法律規(guī)定具有共性,均未將“交易相對人”考慮在內(nèi),這也進一步地印證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不應(yīng)包括“交易相對人”。
四、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
商業(yè)賄賂的受賄主體不包括交易相對人,因此對交易相對人進行賄賂的行為不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只是一種具有商業(yè)賄賂的行為外觀,卻不具備商業(yè)賄賂實質(zhì)損害的“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但經(jīng)營者直接向交易相對人通過非公開、非正當(dāng)?shù)男问浇o付財物以謀取競爭優(yōu)勢的行為同樣具有商業(yè)賄賂的顯性危害,因此,在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不能適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情況下,需要另尋規(guī)制出路,具體可從以下兩類規(guī)制路徑著手:
(一)財稅管理制度對“賬外暗中”的破解
回扣是商業(yè)賄賂中比較典型與常見的行為手段,一般是指賣方從買方支付的商品款項中按一定比例,通過賬外暗中的方式返還給買方的價款。對于此類行為的規(guī)制,關(guān)鍵在于破解“賬外暗中”,或?qū)Α百~外暗中”予以追責(zé);或使“賬外暗中”轉(zhuǎn)為“賬內(nèi)明示”。目前我國涉及財賬內(nèi)容的法律包括《公司法》《企業(yè)所得稅法》《會計法》《企業(yè)會計準(zhǔn)則》等法律規(guī)范,這些法律規(guī)范已經(jīng)初步構(gòu)建起一套相對完整的經(jīng)營者財務(wù)、稅務(wù)法律體系。通過對經(jīng)營者財務(wù)、稅務(wù)的嚴(yán)格管理,要求經(jīng)營者認(rèn)真履行財稅管理義務(wù),能夠使得經(jīng)營者的財務(wù)報表、收支數(shù)據(jù)等財賬信息真實有效。首先,建立會計領(lǐng)域?qū)?zhǔn)商業(yè)賄賂的專項審計職能,建立和完善法務(wù)會計相關(guān)體系,結(jié)合企業(yè)的微觀操作,以賬外回扣和賬內(nèi)回扣的形式,做好商業(yè)賄賂資金的登記、結(jié)合企業(yè)的財務(wù)管理,做好入賬登記,迫使經(jīng)營者將“賬外暗中”的回扣主動入賬,削弱回扣行為的危害性;其次,加強對經(jīng)營者的財務(wù)、稅務(wù)審查,嚴(yán)格追究財務(wù)造假、偷稅漏稅的法律責(zé)任,發(fā)揮法律的指引作用和教育作用,規(guī)范經(jīng)營者的財務(wù)行為;最后,從交易相對人的角度出發(fā),發(fā)揮企業(yè)自身的作用,加強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體系建設(shè),樹立誠信經(jīng)營理念,主動拒絕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所帶來的不良誘惑,并以合法正規(guī)的經(jīng)營模式推動自身營利。
(二)實現(xiàn)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的轉(zhuǎn)化
公司法領(lǐng)域內(nèi)有一項特殊的法律制度——公司人格否認(rèn)制度。該制度是指為了阻止公司獨立法人人格的濫用和保護公司債權(quán)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根據(jù)具體法律關(guān)系中的特定事實,責(zé)令公司的股東對公司的債務(wù)或公共利益直接負(fù)責(zé)。在“刺破公司面紗”的情況下,公司股東的個人行為與公司根據(jù)其獨立、整體意志作出的行為決策并不一致,其行為純粹為了自身的非法利益,而非公司的獨立人格利益,因此才需要由其最終承受相關(guān)的法律責(zé)任。該制度的內(nèi)在邏輯可供商業(yè)賄賂借鑒,以實現(xiàn)對準(zhǔn)商業(yè)賄賂的轉(zhuǎn)化。在現(xiàn)實的市場競爭活動中,經(jīng)營者內(nèi)部的自然人借單位之名以謀個人受賄之實的情況并不少見,這種賄賂行為所轉(zhuǎn)受的財物最終也并未用于經(jīng)營者本身,而是為該內(nèi)部自然人所享用。由于此時的受賄主體表明為交易相對人,從商業(yè)賄賂的構(gòu)成要件上并不能將其認(rèn)定為商業(yè)賄賂并以《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進行規(guī)制,但在實質(zhì)上,這種情況與公司人格否認(rèn)制度所適用的情況別無二致,因此,在對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的進行轉(zhuǎn)化之時,同樣需要將經(jīng)營者內(nèi)部的自然人與經(jīng)營者本身作為兩類獨立主體加以區(qū)分,從而避免借單位之名,謀個人之實的行為無法得到有效規(guī)制。
濮陽縣巨鑫商貿(mào)有限公司與耿瑞芬、杜海波商業(yè)賄賂不正當(dāng)競爭糾紛案為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的轉(zhuǎn)化提供了一定的司法經(jīng)驗。該案件的原告巨鑫公司與被告耿瑞芬、杜海波分別代理了不同品牌的白酒,均負(fù)責(zé)濮陽地區(qū)的總經(jīng)銷。被告耿瑞芬、杜海波通過向濮陽地區(qū)的部分餐飲店贈送海爾洗衣機、愛瑪電動車的方式,要求這些餐飲店銷售被告所代理的白酒,且禁止銷售原告所代理的白酒。濮陽縣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實之后,最終認(rèn)定被告耿瑞芬與杜海波的行為構(gòu)成商業(yè)賄賂。在該商業(yè)賄賂關(guān)系下,行賄人為被告耿瑞芬與杜海波,而受賄人是濮陽縣的部分餐飲店,似乎符合“交易相對人”的身份外觀,但法院在判決書中并未對受賄人進行深入的論述。事實上,本案的受賄主體在性質(zhì)上屬于個體工商戶,根據(jù)《個體工商戶條例》第二條的規(guī)定,個體工商戶是指有經(jīng)營能力并經(jīng)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從事工商業(yè)經(jīng)營的公民。在此情況下,交易相對人和交易相對人內(nèi)部的個人已經(jīng)混為一體。此外,就該賄賂關(guān)系的涉案財物來看,洗衣機、電動車等物品與餐飲店經(jīng)營范圍的相關(guān)度較低,最終還是由餐飲店內(nèi)部的個人所享用,而非由餐飲店本身所使用。因此,基于交易相對人與交易相對人內(nèi)部的個人已經(jīng)高度混同,結(jié)合賄賂財物的實際使用情況來看,該受賄主體應(yīng)將其認(rèn)定其為交易相對人的內(nèi)部個人,而非是外觀上的交易相對人本身,這也在邏輯上滿足了商業(yè)賄賂的構(gòu)成要件,繼而使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七條來對被告的行為進行規(guī)制。
因此,借鑒“公司人格否認(rèn)”制度,將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轉(zhuǎn)化為商業(yè)賄賂行為,然后再適用《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關(guān)于商業(yè)賄賂的規(guī)制條款,繼而完成對人格混同或是假借經(jīng)營者之名等情況下的不正當(dāng)受賄行為的規(guī)制,這既符合《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七條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不違背受賄主體的限定范圍,同時也能避免準(zhǔn)商業(yè)賄賂行為逃脫法律的監(jiān)管,填補了相應(yīng)的制度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