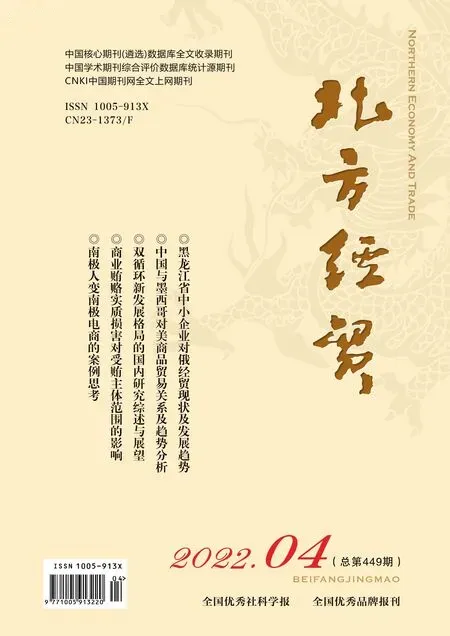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研究述評
何照琦
(湖南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國內外學者對于企業資本結構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F.Modigliani和M.H.Miller教授提出了MM理論,學者們從多種角度在對資本結構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通過不斷放寬對MM理論的假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如Booth等(2001)搜集了10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數據進行資本結構的對比分析,根據靜態權衡、融資順序及代理理論闡明了其存在的差別,最后得出決定的影響因素有:稅率、商業風險、規模、資產收益率和國別等。
資本結構不僅會影響企業績效與價值,還會對企業治理結構、成長性等產生深遠影響,主板市場的上市公司多為大型成熟企業,因此,研究其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具有較大的理論和指導意義。本文將從微觀的公司特征、資本成本、股權融資因素以及宏觀的行業差異性、法律環境、宏觀經濟環境方面,歸納總結近年國內相關研究,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關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微觀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和發展,以證券市場為代表的資本市場不斷壯大,我國企業選擇資金來源時的方式和范圍更為廣泛。國內最早對資本結構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也可追溯至此,從搜集的大量文獻研究中得出,文獻對公司各項特征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的研究占比較大,直至21世紀初期,幾乎均為從微觀層面進行的研究。
(一)公司特征因素
一是從公司整體的規模、成長能力及經營水平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陸正飛(1998)進行了行業間資產負債率比較,發現這些企業的資本結構由于行業不一致有較大的區別,而后深入研究了以35家制造業數據為樣本的企業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發現企業的獲利能力存在明顯的負向影響,而其規模、資產擔保價值以及成長性的影響不大。而袁衛秋(2004)對不同行業分析得出,企業的成長能力、規模及業績等原因的差別會影響其自身的資本結構。李遠慧等(2007)也得出企業的規模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是眾多學者在研究微觀因素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中,通常考慮將公司特征因素相關指標呈正相關和負相關變化。根據施東輝(2000)、洪錫熙和沈藝峰(2000)、肖作平和吳世農(2002)等人對滬深兩地的所選樣本進行分析,通過多元化統計回歸模型的估計,發現在微觀因素中:非債務稅盾、盈利能力、成長性與債務水平呈負相關,公司規模、資產擔保價值、國有股股本、財務困境成本與債務水平呈正相關。孫良(2014)選取的研究樣本分布在五種行業之中,包含了在中小板上市的約500家公司的財務及其他相關數據,采取構造回歸方程的方式,與自己在文章提出的假設進行對比,發現公司規模、成長性、資產擔保價值與資本結構呈正向相關,另外其盈利性、非債務稅盾、產品獨特性與資本結構表現出的是呈反向相關。
(二)資本成本因素
資本是企業正常運營的基礎,企業最重要的資本來源有兩種,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但從眾多研究表明,企業大多都有股權融資偏好。黃少安、張崗(2001)在研究了我國的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特點后,由于其股權融資比債務融資的成本要低一些,發現特別是處于我國如今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時,股權融資偏好是較為突出的。而在閻達五(2001)實證分析我國的上市企業配股融資的行為中可以看出,很多公司的配股動機較為強烈,產生通過配股價要比每股凈資產更高來實現籌集資金的目的。齊寅峰(2005)通過問卷調查,將國內公司的投融資行為采取了較深的研究,發現公司最常用且必不可少的融資途徑是銀行貸款,但融資時也會受到政府調控政策的約束。黃少安(2012)對我國企業的股權融資偏好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由于股權融資成本的影響因素多,所以導致股權融資的債權要高于成本,而根據我國的體制情況,企業高管幾乎不會受到股東的影響,根據偏好使自身效用達到最大化來進行股權融資。近三年來,從辛琳等(2017)在對中國上市公司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公司如果能夠運用更多的社會資本,那么外部的融資需求就會更小;而公司的外部社會資本與資本結構呈負相關。
其實,合理利用債務資本,能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但如果債務比率過高則很有可能會給企業帶來破產的風險。所以公司需要很好地調整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的結構,形成有利于本公司發展的資本結構,才是不斷提升公司價值,促進公司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
(三)股權結構因素
股權結構因素同樣在一定程度上也約束了企業的資本結構決策。姜付秀、黃繼承(2013)通過雙重差分模型法,尋找曾經出現過CEO變更事件的我國上市企業當作此次研究的樣本,發現只有出現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比較低的情形時,CEO與財務相關的從業經歷才會對資本結構決策有重大影響。另外,洪正(2005)更是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均衡度以及集中度三種指標進行了實證研究,來衡量股東控股情況和股東之間的相互制約情況,表明在股權結構中,只有國家相對控股才對資本結構具有顯著影響。因此可以看出,資本結構是國家控制權主導下的產權多元化與各主體間博弈的產物。
二、關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宏觀研究
近十年來,國內學者將分析角度逐漸擴大,一些研究從宏觀上的不同角度如行業差異性、法律環境及宏觀經濟環境分析了企業資本結構的相關問題,這些研究都表明,企業要想長久維持其穩定發展,就必須全面掌握宏觀經濟市場的發展規律,預測宏觀經濟的周期變化,把握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力度與方向,根據經濟、金融政策及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有針對性地制定風險應對措施。
(一)行業差異性
行業差異性是研究和分析資本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沈雅芳(2020)分析發現了中國上市企業各行業間資本結構差異較大,這并非因為個別異常值導致,也并非由于不同行業的公司間的差異,這就是普遍存在的。陳家淳、胡哲帥(2015)通過2011至2012年深滬兩市的84家新興產業上市企業的數據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所選因素中盈利能力的影響是最大的,企業的規模對自身的資本結構也有明顯影響,而成長性、資產流動性的影響程度較小,資產有形性、產品獨特性、股權集中度和非債務稅盾對新興產業的資本結構影響并不明顯。與此同時,邱永輝、石先進(2017)選取2003-2014年287家上市公司面板數據對企業最優資本結構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現資本結構具有明顯的行業差異性,稅盾效應以及信貸供給對資本結構存在顯著的影響,相反債務成本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則并不明顯。由此可以得出行業差異性是影響其因素之一的結論。
(二)法律環境
對資本結構實際影響因素背后的制度環境作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企業也會隨著法律環境的變化對企業的資本結構進行一個相應的調整。伍中信等(2013)收集了846家中國上市公司2001年起十年的數據為研究的樣本,構造了企業資本結構的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的分析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信貸政策會明顯對公司自身的資本結構產生影響,另外對流動負債的影響要比對長期負債的影響程度更加顯著。另外,黃繼承等(2014)以滬深兩市證券交易所1998-2009年的A股上市企業作為研究樣本,認為法律環境能夠根據影響債務融資的方式改變企業自身的資本結構,其提升后,公司會對自身的債務規模進行相應的調整,而權益資本并不會被調整。
(三)宏觀經濟環境
宏觀經濟環境是融資的基本環境,是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Nejadmalayers(2001)根據Probit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一個公司融資方式決策的影響,發現其可以部分解釋企業融資選擇的原因。而由于企業的金融服務會受到外部種種條件約束,任何宏觀經濟方面的變動都會對企業的資本結構造成嚴重影響。何靖(2010)選擇了我國378家企業1998年起十年的平衡面板數據,根據G MM模型,把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內化于模型中估計,得出其會直接影響企業對目標資本結構的選擇和動態的調整速度,使宏觀經濟環境與其資本結構的調整速度呈正相關。李勇(2014)以我國820家2001-2011年的數據為觀測樣本,選用實際GDP增長率、信貸規模、股權擴容規模、債券發行規模和實際貸款利率衡量宏觀經濟環境,運用實際GDP增長率把宏觀經濟周期劃為四個階段,并作為其啞變量,構建了資本結構動態調整模型,發現其調整呈順周期特征。
三、文獻評述
通過對上述國內外文獻的回顧,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分析,總體上是從靜態視角轉變為動態模型為主,也逐步發展為從微觀到宏觀的全面性研究。雖然學者們對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結論還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可能是由于樣本選擇、研究方法等的不同而造成的。但總體來說,公司特征、資本成本以及股權結構因素都一定程度地約束了企業對資本結構的選擇,而在宏觀上的行業差異性、法律及經濟環境也制約著其調整。
雖然我國學者對于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微觀層面的研究已較為完善,但在宏觀層面上的研究也才剛剛起步,而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仍然會隨著各種因素不斷變化。因此,只有不斷完善對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才能為企業在調整資本結構時提供思路,從而實現長遠穩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