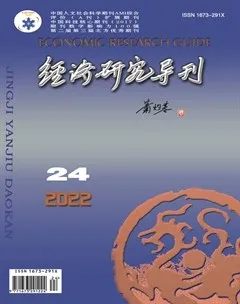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勞動力回流現象
——基于推拉理論視角
洪 潔
(貴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貴陽 550025)
引言
近年來鄉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鄉村空心化、無產化、老齡化加劇,城鎮和鄉村的勞動力差距明顯擴大。以這些現象為依據的“鄉村衰落論”十分盛行,從“鄉村衰落”的判斷出發不斷有聲音呼吁加大對鄉村的投資和扶持力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展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活動,也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總要求,制定了清晰明確的鄉村振興任務書和路線圖。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人力資源的配置,要合理引導鄉村勞動力回流。只有讓鄉村勞動力充裕起來,才能發展好鄉村,鄉村發展得好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需著力打造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的新格局,而勞動力回流正是一個契機。因此,本文對勞動力回流進行研究分析,以探討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勞動力回流現象及其成因。
一、鄉村振興與農村勞動力回流之間的關系
對于農村地區而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就需要優先發展農村和農業,有效利用農村回流勞動力,提高農民參與農村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促進“三農”高質量發展。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返鄉勞動力相關的研究數量呈增加趨勢,隨著各種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推動,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開始選擇“歸巢”,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外流的農民工也逐漸回流到農村,迎來了較大規模的返鄉潮。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曾出現過由于政策原因促使勞動力回流的現象,1950—1952年,國家全面推行土地改革,農民生活壓力降低,農村生活相對安定,農民工主動返鄉;1961—1963年,國家制定了明確的城鄉分離制度和相關政策促使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大規模返鄉,嚴控鄉城人口遷移,農民工被迫返鄉;1997—1999年,由于改革開放后鄉城遷移的第二次高潮導致城鎮剩余農民工數量激增,農民工因就業機會減少而主動返鄉;2012年,由于鄉村建設的發展,大部分勞動力留在鄉村,外流的勞動力也逐漸回流。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大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服務型產業等中小企業因疫情影響而受到沖擊,就業壓力和疫情防控政策都促使大量農民工返鄉。
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特別是國家鄉村政策的出臺,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勞動力回流。勞動力回流是一個“被動回流”和“主動回流”的結合。而鄉村振興戰略與勞動力回流的關系也是相互的,鄉村振興戰略吸引勞動力回流,而勞動力回流也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因而我們從這兩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鄉村振興戰略吸引勞動力回流
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可圍繞“生態、產業、文化、人口、組織”五大方面進行研討。
就生態而言,鄉村振興通過加強農村居民對自然環境的全面認識,發展出一條農村建設的新道路。通過對農村自然環境的改造,使農村的產業更加多元化,同時也能夠極大地改善農村居住條件,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這增強了居民的留鄉居住意愿;就鄉村產業而言,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結合當地的資源進行發展各類服務業、旅游業等,除了促進當地產業的發展,也能為回流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文化而言,鄉村振興戰略中,大力扶持基層文化建設,積極推動基層群眾的文化素養的提高,在保證生活水平的同時,也能夠有精神上的滿足;就人口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防止人口返貧化,建立健全脫貧人口防返貧監測機制、脫貧效果鞏固核查機制、返貧人口響應機制、返貧人口響應機制、邊緣人口幫扶機制、脫貧人口防返貧保險機制、脫貧人口激勵機制等;就組織而言,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行,能促使當地農村基層黨建工作質量的提升,能讓當地黨組織更具凝聚力,充分發揮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二)勞動力回流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
勞動力回流會在各方面推進鄉村的發展,從而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就資源而言,在外就業會拓寬自己的人脈資源、技術資源、資金資源等,結合鄉村振興的產業政策,他們回鄉后進行農業開發經營,形成一批新型的農業經營大戶,并通過示范效應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提高了農民收入,增加了當地的就業率;就人才發展而言,勞動力外流的過程中對于勞動力而言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這一過程中外出務工者的交際能力、自我能力、技術能力、適應能力等都有所提高,由于在城鎮生活時間久,他們會在思想上、生活上更加現代化,這也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減少城鎮和農村的隔閡,改變當地社會生活的方式;就創新精神而言,回流勞動力返鄉后大部分會進行創業,由于接受城鎮的現代化產業的熏陶,大部分年輕群體會進行發揮創新精神,如開辦企業、進行農業投資、從事服務行業等,最顯著的就是結合互聯網來發展當地的農產品,這些都促進了農村創業活動的開展,也為農村發展帶來了很好的示范效應;就制度意識而言,外流勞動力在外出就業期間,會受到相對嚴格的規章制度,不論是所在產業的公司制度還是所暫住地區的區域制度,都會使得這些民工的制度意識加強,當他們返鄉時,他們在遵守制度方面的自覺性會增加,從而會推進政府工作的順利開展,也會帶動身邊人主動配合政府工作。
二、推拉理論背景下的分析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根據當前外流勞動力回鄉發展狀況,將這種回流現象視為推力和拉力以及現實條件的共同作用。為深入分析勞動力回流的機制,本文從推力—拉力—中介力的角度,分析影響勞動力回流的因素。
(一)輸出地對勞動力的拉力
對于勞動回流的拉力,主要體現在輸出地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可以從政策因素和自身因素兩個方面進行淺析。
從政策方面考慮,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各地政府積極制定政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第一,產業興旺建設推動了鄉村第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吸引了很多返鄉勞動力利用自身資源進行創業。第二,在生態宜居建設下,鄉村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逐漸完善,退耕還林、保護農田等措施也使得鄉村的生態環境越來越好,有效改善了以前落后的生態環境,使得人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第三,鄉風文明建設下,主要體現在文化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地政府開展了多樣化的文化活動,開設了各種文化綜合站,提高當地村民的文化建設,增加了村民的文化素養。第四,在治理建設下,治理的關鍵在于人,各地政府發揮黨員的帶頭作用,深入基層帶動村民進行有效治理。第五,在生活富裕建設下,鄉村振興的目標就是實現村民的生活富裕,當人們一直與以前的生活進行比較時,就會滿足于現狀,外出的意愿反而會降低。
從自身因素方面考慮,大部分勞動力回流現象會與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自然資本相關,它們之間呈現一種遞進的關系。對于人力資本而言,分為年齡和文化教育兩個方面,年齡越大,回鄉意愿越強烈,并且隨著自身文化教育的限制,在當今信息技術發展下已經不具備就業優勢,年齡和文化教育與回流意愿呈負相關關系,但是由于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政策的影響,這種負相關關系越來越不明顯,更多的勞動力會選擇結合政策在當地進行發展自我;在社會資本中,由于自身在當地的發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即能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增加當地就業,因此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具有一定的提升,這滿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在經濟資本中,外出務工主要還是為了滿足家庭需要,由于相關政策減輕了生活的壓力,使得留鄉發展也能保障家庭生活,因此留鄉的意愿也會增強;在自然資本中,擁有宅基地的鄉村勞動力回流意愿更強,除了城市的房價昂貴外,傳統的“落葉歸根”思想使得外流勞動力會愿意將自己的資本投入到宅基地中,會增強自己的回鄉意愿。
(二)輸入地對勞動力的推力
對于勞動力輸入地而言,過多勞動力的輸入會導致城市發展出現問題。在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而使城市中的成年勞動力大量地從農村向城市遷移。但是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不合理性,也給城市的就業市場和就業環境帶來了諸多困擾和問題。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這給人口管理帶來了難度,也給社會的安全帶來了許多未知的問題。其次,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城市勞動力與農村勞動力之間的社會保障存在差異,使得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更加困難。最后,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農村勞動力不能相應地轉移到二、三產業,這就造成了我國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的困境。城市發展不足以及由此引起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門路變得十分狹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給城市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從而影響了城市的就業環境。
在這種推動力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的數量不斷增加,由于其自主意識較強,數量較多,在選擇遷移到城市后,對社會的基本秩序產生影響,在住房、交通、醫療等方面增加了較大的壓力,不利于城市的發展,影響了城市原有的第三產業。此外,轉移到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就業崗位、工資待遇、社會保障待遇等方面都與城市居民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種勞動力供求的差異以及農村勞動力的知識技術水平與城市就業崗位之間的不匹配,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城市就業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這些問題的凸顯都促使勞動力留城意愿降低,側面上也推動勞動力回流。
三、“新冠肺炎疫情”中介力的影響
自2020年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我國經濟與就業都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中,經濟增長與就業率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而短期內發生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在長期內對經濟造成難以修復、持久的創傷。外流勞動力的工作場所大部分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這些行業由于疫情的影響受到沖擊,也一定程度增加了農民工的失業率。因此,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在對勞動力回流過程中的影響。
(一)收入與支出導致的失業率增加
根據經濟學中收入與消費的關系可知,消費與可支配收入存在著一種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疫情的影響造成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速下滑,這也使得居民的收入下降,因此消費的動機也隨之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訂單需求的減少,給企業帶來經營壓力,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會在其他方面減少支出以保證成本最小化,就會實行裁員減負,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失業的幾率。2021年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疫情沖擊下,農民工的失業率為3.63%,較2018年上升了1.48%。
(二)就業格局發生變化
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外流工作于小型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疫情使得這些企業被迫縮減甚至倒閉,從而導致農民工失業的比率增大。此外,在疫情的影響下,平臺就業、靈活就業等新興工作方式隨之發展,大部分企業將工作模式調整為網絡辦公,將自己的定位變成線上企業。這些調整對于員工的知識技術要求較高,而部分農民工存在自身知識能力的限制,加之農民工就業穩定性較低,疫情下所需的靈活就業人員比例高,進而導致大部分農民工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三)農民工返崗受阻,生活壓力增大
各地區為了加強疫情防控,大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都推遲了復工復產的時間,加之部分地區疫情的出現,也使得許多人員居家隔離不能外出,這導致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不能按期返崗就業。長時間的隔離會導致待業無業甚至失業,家庭收入隨之減少,從而增加生活的壓力。因此,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了滿足基本的需求,外流勞動力就要回歸農村進行自給自足以及增加家庭收入。
結語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勞動力回流的規模逐漸在擴大,這對于勞動力輸入地和輸出地來說具有雙重的影響,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殊群體,也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當勞動力回流時也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比如如何將農村勞動力回流現象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經濟平衡發展結合起來,如何保障回流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如何促使回流勞動力投身于鄉村建設發展中等,這些問題也是需要進一步進行考慮并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