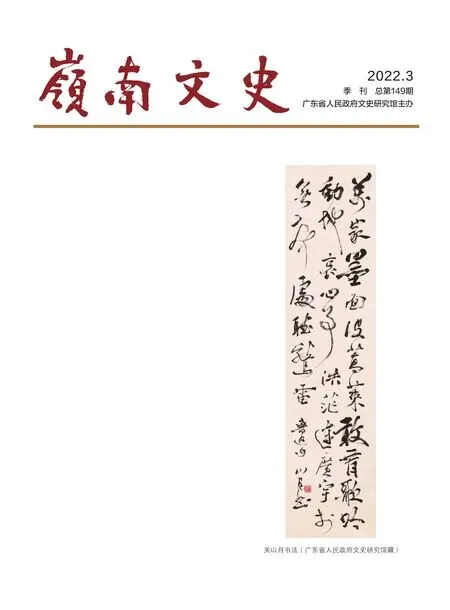華南教育歷史時期內遷粵北學校的黨建工作
王麗 廖鋼青
抗日戰爭期間,珠三角及港澳地區眾多學校遷至以韶關為主的粵北地區,在戰火中堅持辦學,這段特殊的時期稱之為華南教育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內遷粵北學校的黨建工作,圍繞思想入黨、社會實踐、隊伍建設等方面,推進馬克思主義在粵北地區的大眾化和時代化,為粵北地區及至廣東革命和建設培養了大量人才,促進了黨組織在粵北地區的發展和壯大。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學校黨建工作,培養了大批革命人才,為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華南教育歷史時期內遷粵北學校這一特殊群體,分析中國共產黨開展黨建工作的方式與特點,以此闡釋學校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和歷史作用。
一、在內遷粵北學校中開展黨建工作概況
1938年10月,日軍侵占廣州。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倉皇遷至粵北重鎮——韶關,將其作為臨時省會。為保存力量,中共廣東省委也遷至韶關,積極開展戰時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人民進行武裝斗爭,抵抗日本侵略。在當時,眾多粵港澳中高等院校為賡續華南教育火種,紛紛遷往以韶關、連州為主的粵北等地區,在戰火中堅持辦學,這一特殊時期稱為“華南教育歷史時期”。據統計,從1938年10月廣州被日軍占領始,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止,粵港澳地區遷至韶關辦學的中高等學校共計有38所,其中高等學校11所,中等職業、師范、專科學校7所,中學20所;遷往云浮縣、羅定縣、郁南縣辦學的高校、職校、中學共20所。如中山大學及附中先期遷往云南澄江,1940年6月又從云南澄江回廣東,落址韶關坪石。中山大學前身之一,私立嶺南大學及附中于1941年6月從香港遷至韶關湞江大村。華南師范大學的前身,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于1939年8月從廣西容縣遷至韶關乳源侯公渡,1939年冬搬到連縣東陂,1942年春又遷回韶關曲江桂頭。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附中隨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遷到連縣東陂,后又遷至學院舊址江夏村,改名為粵秀中學,是為惠州學院前身。廣東省立法商學院于1941年秋遷至韶關曲江桂頭。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院于1940年秋遷往韶關曲江西河黃塱壩,后搬至連縣鷺鶿。廣東省立仲元中學于1939年秋遷至韶關曲江南郊鶴沖坪,后遷往連縣星子鎮,1940年1月又遷回韶關。
華南教育歷史時期,不少內遷粵北學校具有濃厚的紅色底蘊,其中尤以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為甚。中山大學在1923年就有藍裕業等5位黨員,是首批建立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的學校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中山大學(時稱廣東大學)建設,不僅派李大釗、毛澤東、阮嘯仙、惲代英、黃日葵等十多位黨的領導人到學校任教,還將其作為黨員干部培訓的重要陣地,“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此時的廣東大學已成了中共的一所特殊黨校”。1926年,中山大學建立了中共總支委員會。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常年由進步教育家林礪儒擔任院長、校長。1936年10月,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時稱勷勤大學)陳能興等6人成立“中共勷勤大學第一個學生黨支部,由中共廣州市地下黨指派王均予負責聯系并直接領導”。陳能興后來成為廣東青年運動領導人,抗戰期間擔任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隊組織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青年部部長,直接領導和參與了內遷粵北學校黨的建設。
廣東黨組織伴隨著蓬勃興起的青年運動孕育而生。“廣東的黨可以說大部分是在青年運動的工作發展起來的。”抗戰之前,廣州一直是華南地區青年運動的中心。抗戰爆發以后,隨著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和中共廣東省委遷至韶關,特別是多所粵港澳大中院校遷到以韶關為主的粵北地區后,青年運動的重心也隨之由廣州轉移至韶關。鑒于內遷粵北多所學校擁有濃厚的革命傳統和紅色屬性,中共十分重視內遷粵北學校的黨建工作,為推動粵北乃至廣東黨建工作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在內遷粵北學校開展黨建工作的主要內容
由于土地革命時期學校黨建工作被邊緣化,學校黨組織建設一度比較薄弱。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黨組織開始意識到學校黨建的重要性,青年運動和學校黨建逐漸承擔起在黨內的先鋒和橋梁作用。1941年1月,朱醒良代表廣東省青委作《廣東青年工作報告——廣東青年運動的概況及黨的領導方針》,總結了1940年之前廣東的青年工作,指出了黨建方面的不足:“廣東青年工作對于黨的工作檢查得非常不夠,所以說對于這方面沒有注意到,所以材料很少。因為我們過去的了解認為青年工作就只管青年群眾運動,而黨的工作是屬于黨的組織工作,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念。”因此,中共開始有意識地強化學校黨建工作,“在各類高校中大多建立了牢固的基礎”。聚焦到華南教育歷史時期內遷粵北學校,主要體現在思想錘煉、社會實踐、隊伍建設等方面。
(一)解決知識分子入黨問題
雖然中國共產黨由知識分子創立,但如何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建設工人階級的政黨,一直是學校黨建的難點,也是決定學校黨建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如何讓知識分子真正從思想上入黨。“在這一時期,中共確實為知識分子的入黨打開了方便之門,并且在實踐中確立起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基本原則。”
華南教育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內遷粵北學校中著重從黨內黨外多個層次著手,較好地解決了知識分子入黨的問題。
對于黨員,一是通過秘密過組織生活的方式,組織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最新政策。“青年學生接受革命思想的重要途徑是通過聽講、閱讀革命書籍……當時,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等,以及我黨出版的報刊如《新華日報》《解放》《群眾》等,共訂了四十多份,全國各地進步書籍刊物,也都能交流暢通。我們因勢利導,建立各種形式的學習組織,包括公開的,秘密的,學術性的形式,組織他們學習,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二是舉辦黨員培訓班。國民黨當局兩次反共逆流期間,廣東黨組織于1941年和1942年在樂昌和坪石舉辦了兩次面向所有內遷粵北學校的黨員培訓班,為期一個月左右。由中共廣東省委各部長圍繞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政策、統一戰線、青年學生工作等進行系統的闡述,提升黨員在特殊時期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提高了黨組織的戰斗力。
對于非黨員的進步分子,黨組織首先引導他們選修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當時內遷粵北的學校中,聚集了一大批黨員教師和進步教師,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資本論》翻譯者王亞南、進步戲劇家洪深、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李達、因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被國民黨政府解聘的前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中國共產黨情報界抗戰三杰之一梅龔彬等人。他們開設了一系列馬克思基本理論相關課程,如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高等經濟學》,李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洪深的《戲劇評論》等,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親自講授辯證唯物主義等課程,并支持學生撰寫研究蘇聯的相關論文。黨組織引導進步學生和積極分子選修這些課程,為思想上入黨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二是成立讀書班、研究會等各類進步團體,并將其作為解決思想入黨、吸納黨員的重要陣地之一。如中山大學嶺風文藝社、文藝研究社,粵秀中學文苗社、勵志讀書會、春雷讀書社等社團,不僅處在黨的領導下,而且在校內影響很大,吸引了大批進步學生和積極分子參加。方法是先組織他們閱讀抗戰書籍、演唱抗戰歌曲,然后學習進步刊物,待時機成熟后,再宣傳黨的政策和理論主張。通過這種營造氛圍、由淺入深、逐層遞進的方式,將大量進步學生和積極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直至發展入黨。
(二)通過社會實踐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時代化
除在校園內強化理論學習外,黨組織還注重校園外的社會實踐,通過實踐深化對理論的認識和理解,促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時代化。“抗戰時期也是中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關鍵時期。在其中,高校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戰爆發后,隨著大批粵港澳學校向粵北轉移,廣東學校黨建工作的主戰場也由以廣州為主的中心城市轉向粵北廣大城鄉。黨組織不僅在校園內強化理論研究和學習,還注重帶領黨員和進步青年走出校園,從實踐中探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在廣袤的農村大地上,他們或是進行鄉野社會調查,深入了解中國農村現狀,或是舉辦面向當地農民的識字班、民眾夜校等,提升農民文化知識水平,宣傳抗日救亡主張,傳播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學生——農村——農民的循環互動中,學生以農村為媒介,切身體會到農民被壓迫被剝削的社會現實,拉近了同農民大眾的距離,進一步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黨的方針政策的認同和理解。農民受到學生宣傳教育的熏陶,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不斷進步,不少人走上了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思想和黨的主張,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時代化的宣傳者和實踐者,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為粵北地區及至廣東革命和建設培養了大量人才
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學校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人才的重要來源。在內遷粵北學校中,黨組織有意識地強化隊伍建設、人才培養,為粵北地區和廣東革命與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
一是注重培養本地干部,為鞏固粵北當地黨建工作扎下根基。針對學校遷至粵北后,本地學生大量增加的特點,黨組織尤其注重對本地學生的團結教育、鍛煉培養。實踐證明,黨的這一舉措不僅在校園內培養了黨的骨干,也為粵北本地的革命建設培育了大量干部,使黨的工作能夠在基層黨組織中落地生根。以粵秀中學為例,“在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建立粵北革命根據地、發動連陽起義等各項斗爭中,大批革命骨干是來自粵秀中學的本地同學。”
二是注重人才輸出,為廣東革命和建設輸送了大量優秀干部。這一時期,黨組織以粵北為中心,為全省乃至省外的抗日武裝和解放戰爭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學校不僅是掩護黨組織的據點,也是開辟城鄉抗日工作的陣地,同時又是進行革命教育,培養革命人才和發展黨組織的搖籃。廣東許多革命和建設的人才,特別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廣東游擊隊,許多指導員都來自這些學校的。”1945年,日軍南下入侵廣東,為保存力量,黨組織以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粵秀中學、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為主,選送了600多名學生參加東江縱隊,其中中山大學有200多名。粵秀中學除有90多名學生參加東江縱隊外,還有26人參加解放戰爭,27人(一說32人)參加清遠、英德地區的武裝斗爭,4人參加大別山游擊隊,6人參加中原軍區和華東軍區武裝斗爭,19人參加連縣東陂、星子武裝起義,24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犧牲。
三、在內遷粵北學校開展黨建工作的成效和影響
華南教育歷史時期,中共在內遷粵北學校除注重從思想、隊伍上加強建黨工作外,還根據廣東學校黨建、廣東戰時特點和廣東政治環境采取了一系列組織制度建設,大大促進了校內及校外黨組織的蓬勃發展,擴大了黨組織在粵北地區的影響力。
(一)完善領導和組織聯絡制度,推進黨組織在校內扎穩根基
領導體制方面,內遷粵北各學校黨的工作在中共廣東省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具體由省委青年部直接聯系,省委青年部部長陳能興主管全面工作,副部長張江明抓青年學生工作。張江明常年駐在韶關坪石老街,每個月到連州東陂一次,全面負責中山大學及附中、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粵秀中學、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等學校黨的工作。這一專人負責、集中領導的工作體制,便于黨內統一協調內遷粵北各學校黨的工作。如在領導學生運動、發展學生社團、政治理論學習培訓、組織學生參加抗日武裝斗爭時,能更好地調配各學校開展工作,便于校際間的相互呼應和支持。
組織聯絡制度方面,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黨組織在這些學校中采取單線聯系的工作制度。具體表現在:這些學校的黨務工作統一由張江明負責聯系,各學校內設立若干支部,支委分工聯系黨員。如中山大學分別在法學院、文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師范學院、理學院、醫學院設立獨立支部,支部之間不橫向聯系,張江明直接和支部書記聯系。單線聯系工作制度不僅能有效避免黨組織被破壞后遭受重大損失,也為在嚴峻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隱蔽埋伏積蓄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大幅增加黨員人數,增強校內黨的力量
土地革命前期,受“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影響,黨內流行唯成分論的錯誤思潮,大量知識分子被擋在黨組織之外。一二·九運動以后,黨逐步突破唯成分論的束縛,強調從思想上入黨。華南教育歷史時期,黨組織通過強化思想建設,強調思想入黨,吸收了大量新黨員,黨員人數明顯增加,黨員質量不斷提高,黨的戰斗力顯著增強,促進了黨組織在粵北學校中的發展壯大。如中山大學1940年秋搬遷到坪石時,只有黨員12人。經過短短兩年的培養發展,至1942年秋,因中共廣東省委遭到國民黨嚴重破壞、黨組織被迫停止活動時,黨員已經激增至116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1939年搬到東陂時,只有黨員3人,至1942年8月黨組織停止活動時,發展到42人,占全院學生總數的30%多,建立了2個黨支部和1個中心支部。粵秀中學剛到東陂時,全校只有3名黨員,建立黨小組1個。至1942年8月,已有學生黨員80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幾,且建立了學生黨支部。嶺南大學在這一時期共有4名黨員,5位進步分子,對于這所學生以港澳華僑弟子為主的私立教會學校,是非常突出的。
(三)以“種子黨員”和“中心據點”為突破口,促進粵北地區黨組織的發展壯大
中國共產黨在內遷粵北學校中不僅強化校園黨組織建設,也利用校園黨組織的力量,通過“雙帶動”方式,不斷在校外開拓建設新的黨組織,促進了粵北地區黨的發展壯大。一是以高校帶動中學,通過“種子黨員”積極拓展和壯大學校黨組織建設,擴大黨在粵北地區教育戰線的覆蓋面。黨組織重視將畢業的學生黨員作為“種子黨員”,選派到還未建立黨組織的學校任教,在校內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如“1941年夏,中大文學院黨支部書記盧熾輝畢業后通過陽山縣長介紹,任陽山中學校長,中大法學院黨支部書記林之純任教務主任。同年10月,陽中成立了黨支部,先后調來一批黨員任教師,樹立了良好的學風,迅速提高了教學質量。”二是以校園帶動農村,圍繞校園這一“中心據點”,向校園周邊農村地區輻射。如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粵秀中學等學校的學生黨員為學校附近的農民辦夜校,開展宣傳工作,培養農民骨干,發展農民黨員,逐步在農村建立黨組織。通過這種“高校—中學”“校園—農村”的雙帶動方式,以星火燎原之勢,逐步在粵北地區建立了一批黨的基層組織,為粵北地區開展抗日武裝斗爭和解放戰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1][6][8]周良書:《中國高校共產黨建設史(1921—1949)》[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06。
[2]顏澤賢:《華南師范大學校史(1933.8-2003.8)》[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0頁,2003。
[3]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5[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第350頁,2022。
[4]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1輯[M]。第185頁,1991。
[5]周良書:《1937—1945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設》[J]。《北京黨史》,2006年第4期,第29頁。
[7]林敬文,劉渭章,鄭彥文:《崢嶸歲月,堅持斗爭——廣東文理學院學生運動概況》[M]//廣東省政協文史委:《廣東文史資料》第36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19頁,1982。
[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26頁,1991。
[10]鐘國祥,麥楊,戴江,張文藻:《抗戰時期粵秀中學的青年運動》[M]//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中共韶關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清遠市委黨史研究室:《抗戰時期粵北青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58頁,1991。
[11][12]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廣東青年運動史》[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98、303頁,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