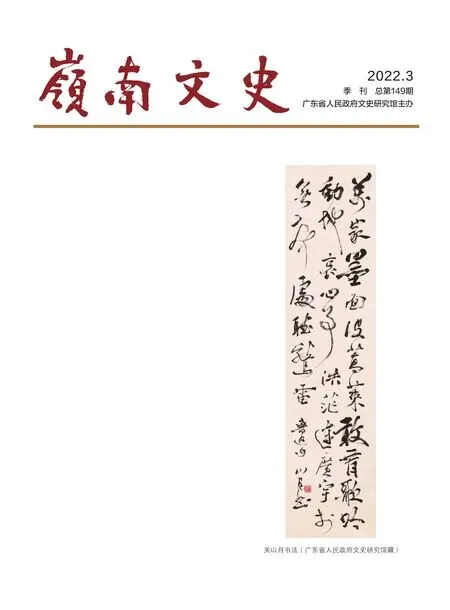積極推動粵港澳人文灣區中外交流互鑒
王元林
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在第八章“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積極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文化、旅游、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務優質、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其中第二節“共建人文灣區”,包括: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強調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迄今為止粵港澳嶺南文化的特色與優勢。如何理解與實現這一“發展規劃”,應該深入研究與穩步落實。
一、人文大灣區的中西文化長期交匯共存
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由于地理相近,文脈相通,中西文化在此交匯共存。大灣區所在的珠江口江海交匯處,早期的百越人群在此生活繁衍,中原地區的禮制與國家相關的文化制度逐漸通過嶺嶠五道:靈渠道(湘漓道)、瀟賀道、連江道、武水道、湞水道(梅關道)傳播到嶺南,嶺南民眾逐步改變了過去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禮樂教化在此初步推行。中國禮制文化傳播的過程,不是單純的移植,而是一個不斷與嶺南南越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優勢互鑒的過程。物質生活的變遷,必然會引起文化質素的變遷。一種文化傳入新的區域后,原來的質素自然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中原文化傳播到嶺南,催生了嶺南文化,國家觀念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倫理觀等逐漸在嶺南民眾中被接受并加以發揚光大。從宋代開始,嶺南出現了眾多忠君報國的義士與名宦,在南宋末期表現尤為突出。明代黃淳編纂的《厓山志》記載眾多嶺南志士為追求氣節,義無反顧地加入到保衛南宋流亡王朝的行列,極具代表性。由此說明,嶺南文化作為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一部分,其實質內容與精髓仍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而嶺南文化吸取由中原傳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進行創新,誕生了明代陳獻章、湛若水等儒學大家,開創了明代心學先河。歷史上,在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中,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嶺南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起著重要作用,居于重要地位。
嶺南文化以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特點,采中原之精粹,納南海之新風,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嶺南地近南海,海內外交流源遠流長。先秦時期,嶺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開辟了以陶瓷為紐帶的“交流圈”“交易圈”,海上絲綢之路把嶺南、域外物質都匯聚于此。南海航線,又稱南海絲綢之路,起點主要是廣州,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東南亞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達十數個國家和地區。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使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全長1.4萬千米。商船從廣州起航,將絲綢、瓷器、茶葉等帶往世界各地的同時,也帶去了農耕及手工業技術、造紙術和指南針,搭乘商船來來往往的高僧、科學家、畫師、譯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發達,技術與市場、原料與商品、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思想與藝術等彼此交流、相互影響,從嶺南到東南亞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灣和東非各港口,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全球化”的活躍海絲貿易網絡。明清時期,大帆船貿易,南海絲路從中國經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動了沿線各國共同發展。隨著葡萄牙殖民者租借澳門,澳門成為明末與清代中外經濟、文化會聚地。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國與世界貿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傳播東方文明。近代,嶺南開風氣之先,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孕育出以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為代表的近代中國的一代先進人物。嶺南的文學、嶺南畫派、粵劇等藝術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中國電影最先從嶺南傳入,嶺南教育近代更領教育革命之先。而香港在鴉片戰爭后被英國占據,近代成為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香港市民最普遍娛樂的粵曲,仍是早年普及的大眾娛樂,1930年代是粵曲的黃金時代。1950年代之后,香港吸取上海普及文化,加上歐美多年影響,自20世紀70年代起,許冠杰等創造的香港口語演繹法,帶動了中文歌潮流,對“粵語流行曲”的推行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由此可見,中外文化在此的交流與會聚。
從大灣區的人文發展進程看,大灣區也都不同程度上受域外文化影響,中外文化在此交流會聚,形成以中國傳統的嶺南文化為主,兼具不同特色的域外文化因素的特色。故今文化交流互鑒,仍然需要從發揮大灣區中西文化長期交會共存等綜合優勢,促進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創新人文交流方式,豐富文化交流內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
二、人文大灣區嶺南文化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一是根基
粵港澳大灣區地理上仍然是南中國最具活力的地方,灣區的民眾歷史上不斷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不斷會聚、碰撞、交流、融通。而今天,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領導下,族群一樣、語言相通、文脈相同,更呈現出中華傳統優秀地域文化之一——嶺南文化的不同特色,但其本質的主體仍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缺少了這一根基,人文灣區就會成為無本之末。
因為澳門、香港興起較晚,此前長時期都是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的優秀文化。這一傳統文化是通過歷史上不同的文化形態來表示的各種民族文明、風俗、精神的總稱。其特征世代相傳、民族特色、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儒家、佛家、道家彼此共存共榮,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從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描述嶺南各地文化風俗可以看出,各地文化都差別不大,都是與中華文化為一體的風俗特征。各地州縣的書院教育,是以官方推行教化的重要渠道。宋元明時期,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體的理學思想學說流行,陳獻章、湛若水等心學在嶺南有深刻的影響。陳獻章以“自然為宗”“學貴自得”的哲學主張,形成“白沙學派”,西樵山成為當時全國知名的“理學名山”。湛若水、方獻夫、霍韜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創建了大科書院、石泉書院、四峰書院、云谷書院四大書院,在此切磋學問、講學,藏修10多年,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名儒,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中心之一。但萬變不離其宗,理學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其根本就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文學、書法、繪畫、戲曲等無不受其影響。
清代,廣東的書院發展空前,廣州書院在數量上據全國之首。學堂書院不僅數量眾多,形式齊全,而且分布集中。當時,省級的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與府級的羊城書院并稱“廣東三大書院”,縣級的西湖書院、禺山書院同樣不遑多讓,還有肇慶端溪書院等。其后在粵秀山的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等掀起了廣東書院的改革風氣,廣東也一躍而成為全國樸學研究的重地。而廣州民間書院(宗族祠)同樣發展迅速,鼎盛時期達數百間,在廣州的大小馬站、流水井一帶連成了壯觀的書院群。而西樵山有三湖書院(思想家康有為出自此書院)、云溪書院和云瀛書院。傳統書院教育培養了眾多的人才,為維護清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
鴉片戰爭后,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容閎等力主變法強國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學校,培育出一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巨大能量。1864年,清政府在廣州創辦廣州同文館,是廣州最早的一所外語學校。1898年,梁肇敏、鄧家仁、陳芝昌等人就在廣州西關創立了時敏學堂,開設修身、國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現代標志的課程。隨著社會各界“教育興國”的呼聲不斷,迫于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布了“興學詔”,要求將各地的書院改為小學堂、中等學堂和高等學堂,推行西式教育,廣東廣雅書院、越華書院、禺山書院、格致書院等相繼改為廣東高等學堂、廣府中學堂、番禺初級師范學堂、嶺南學堂。后來,許多新式學堂的學生都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近代西方的科技、思想與文化隨著新式學堂傳入中國,對啟迪人們思想與豐富嶺南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
16世紀中葉以后的嶺南文化與澳門文化是相互促進、雙向互動的。在西方政治與法制文化的影響下,澳門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與特點,即開放多元,中西合璧。即便如此,澳門文化仍然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嶺南文化的特色長期在澳門得到保留和發揚,并占據著主體地位。同時,由于澳門長期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橋梁,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宗教藝術、價值觀念以及教育制度等,通過澳門傳入廣東,繼而擴散到內地,使嶺南文化“得風氣之先”又“開風氣之先”,在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1820年馬禮遜在澳門開設一家中式診所,聘請中西醫師,以免費醫療服務作為傳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設一家眼科醫院。六年以后,又在廣州開設一家眼科醫院,眼科醫生聘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師擔當。1839年,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布朗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課程設置有漢語、英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等,學制三至四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容閎曾就讀于該校,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大學畢業生、第一代西醫黃寬也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才生。澳門不僅是中國維新運動和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據點和策源地,而且是一批又一批有識之士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橋梁,而文化精英們在澳門的活動,又大大提升了澳門的文化品格,催化澳門愛國進步文化的成長和發展。澳門與嶺南文化的雙向互動關系再次得到體現。總之,中華文化與澳門文化之間,從文化屬性角度分析,澳門文化也是以中華文化為分類,同時又有澳門特色。從文化的構成角度看,也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
香港從秦代到清代的2000多年中都在中央王朝的管轄下,香港地區越族土著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很深的影響。1841年英軍侵占香港島時,島上只有幾千名居民。后來英國殖民主義者又陸續占領九龍半島和強迫租借新界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多是祖籍東莞、新安等縣的本地人和來自嶺南各地的移民,他們的文化主要是嶺南文化。這些情況表明香港文化的根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香港植根很深,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東方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和民間風化習俗三方面交錯融合而成。而英帝國主義在1841年侵占香港后,除對這一“殖民地”進行軍事征服、政治控制和經濟掠奪外,還通過宗教活動、奴化教育、新聞傳媒以至日常生活多種途徑,對香港輸入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一百多年來,在香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同英國殖民主義文化以及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既互相碰撞、沖擊,又互相滲透、融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當代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和傳統與現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體,目前以商業性流行文化為主流,但老百姓的主流文化仍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
三、發揮人文灣區不同城市的定位與職能,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
粵港澳人文灣區無論是從歷史上、地緣上,還是文化上,都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血脈相連,休戚與共。而在文化合作方面,粵港澳三地亦早已建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交流合作機制——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這一合作機制自香港、澳門回歸以后建立并持續至今,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合作機制切實推動了三地在演藝、文化資訊、文博、公共圖書館、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等領域的合作,真正做到了精誠團結、彼此尊重、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有力地促進了區域文化建設與發展。至2019年6月,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已經舉辦了20次,三方就創新合作繁榮大灣區文化分享構思和意見。“一國兩制”體現在三地文化交流互通互鑒方面,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不動搖,發揮不同城市文化優勢,在文化交流中互通互鑒,扎實做好人文灣區的文章。
在人文灣區粵地,做好九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品牌影響力、輻射力,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嶺南文化的特色與精神實質挖掘與展現出來,具有重要意義。由于歷史上廣州一直是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中心,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一直繁榮的港口所在,所以支持廣州在人文灣區中建設嶺南文化中心和對外文化交流門戶,擴大嶺南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而中山市一直是香山文化中心與孫中山先生故里,支持中山市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把中山先生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作為統一祖國,聯系海外華僑華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江門五邑地區也是中國重要的華僑華人祖籍地,支持江門建設華僑華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臺,做好僑刊、僑情、僑鄉文化,做好華僑華人文化交流的新融合與互通。
作為人文灣區最具特色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應成為開展“一國兩制”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根據歷史發展與特殊時期形成的文化特征,支持澳門發揮東西方多元文化長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和文化旅游,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心。鼓勵香港發揮中西方文化交流平臺作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港澳地區,深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發揮兩地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與“橋頭堡”的作用,內聯外接,促進內外、中外文化互鑒互通。
四、繼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好人文灣區的文化交流
2020年底,文化和旅游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加強政策研究和頂層設計的指引。規劃提出,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繁榮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加強人文灣區建設,首先要開展各種文化遺產的系統性研究與保護,把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以文化遺產為抓手,以海上絲綢之路為突破點,在大灣區三地文化遺產普查基礎上,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聯合實施重要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專項計劃,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數字信息共享平臺,共同推進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聯合申遺工作。
加強人文灣區建設,其次要強化內地和港澳地區青少年愛國教育,加強憲法和基本法、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豐富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文化培育和交流計劃,為粵港澳青年在文化和旅游領域創業、就業、實習搭建平臺,提供便利。
加強人文灣區建設,還要建立大灣區各地影劇院、博物館、美術館、公共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聯盟,推進互相間的數字化共建共享,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群眾藝術交流合作,培育群眾文藝人才和團隊,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群眾文化活動品牌。
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從這里了解與感悟中國,讀懂中國;從這里展示當下中國發展的模式,與世界進行文明交流。人文灣區發展愿景是嶺南文化發展的主要內容,也代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標桿。粵港澳大灣區經過十數年建設,已經具有一定基礎,發展前景喜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遠期展望至2035年。屆時,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事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中華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世界級旅游目的地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一個新高度。
[1]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書院與南海士大夫集團》。《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2]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第17-264頁,2001。
[3]陸昌萍:《國外漢學概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32頁,2017。
[4]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第274頁,1999。
[5]周毅之:《從香港文化的發展歷程看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關系》。《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