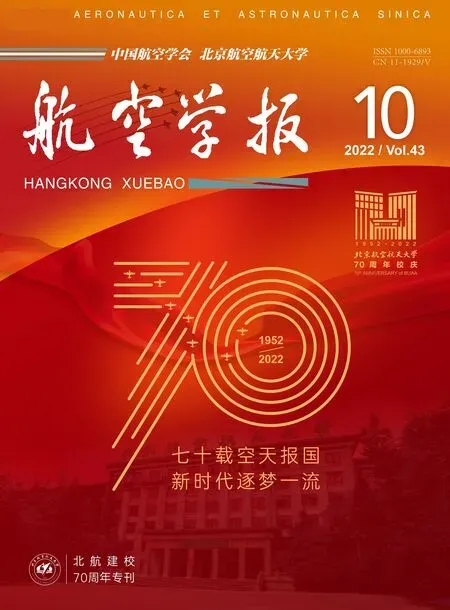航空CFD四十年的成就與困境綜述
閻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教育部流體力學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91
航空領域是CFD發展主要的推動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CFD對航空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具有革命性或者根本性的影響。
一般認為CFD起始于1910—1917年[1]:英國氣象學家Richardson通過用有限差分法求解Laplace方程的方法來計算圓柱繞流和大氣流動,試圖以此來預報天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數值求解 Euler/RANS方程為基本特征的現代CFD進入了實用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原因主要包括2個方面:① 新型CFD計算格式和湍流模型的爆發式發展;② 計算機性能的迅速提高和市場化普及。計算格式方面:1980年后的2年時間里,連續出現了Jameson顯式中心差分有限體積格式[2]、Roe的FDS格式[3]和van Leer的FVS格式[4],這些格式此后被大量應用于航空飛行器的CFD計算和研究,其中Roe格式至今仍然是使用最廣、綜合性能最好并且表現最穩定的計算格式。
湍流模型方面,1968年第一次Stanford湍流會議(1968 AFOSR-IFP Stanford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 of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國際上第一次對二維邊界層湍流等經典算例進行了系統詳盡的模擬、評估后認為:當時所有湍流模型都是不完備的,倡導發展完整、實用化的模型。這促進了此后兩方程模型等的爆發,如1972年后分別出現了k-ε[5]、k-ω[6]、SA[7]、SST[8]等完備模型,這些模型奠定了CFD快速發展的基礎,形成了今天CFD的主力。
遺憾的是,此后的許多年CFD在計算方法和湍流模型等核心理論方法方面,幾乎陷入了停頓。雖然借助于對上述方法、模型的不斷修補完善,尤其借助近40年計算能力的飛速發展和大眾化普及,可以用更精細的網格計算更復雜、更多的飛行器構型,畫出更絢麗的流動圖像,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和更高的評價,但不得不說:CFD陷入了困境。
為了便于全文閱讀,作者根據自己40年的CFD研究經歷,就航空CFD的發展給出一個簡明的路線圖:20世紀80年代前后,由于CFD計算格式和湍流模型爆發式的創新,航空CFD得到了迅速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航空CFD快速進入了RANS時代,超過預期的發展盛況使大家對CFD寄予很大的熱情和期待,但此后,CFD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被專家形容為緩慢、停滯甚至“死亡”的時期[9]。此時,DPW[10]等國際合作系列會議的公開及豐富的結果使大家清醒地認識到航空CFD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存在很多的不足和挑戰。一些關鍵難題如分離模擬,甚至陷入了至今還走不出的困境。
本文試圖梳理航空CFD近40年來的輝煌成就和仍面臨的艱難困境,以期拋磚引玉,共同努力走出困境。作者從事CFD研究及應用也剛好近40年,本文的基本觀點和實例主要來自2個方面:① 作者及其研究團隊多年來的研究結果,尤其是綜述性論文[11-12]、個人感悟和反思,其中一些觀點可能會引起爭論甚至駁斥,希望這些爭論能夠推動中國航空CFD的發展;② 歐美CFD研究,尤其是NASA[13-15]、波音[16-18]和空客[19-20]等在航空CFD方面的論文、報告等。第一時間靜心閱讀和思考這些文獻一直是作者最享受的時光。
1 航空CFD的成就
CFD的主要優勢是經濟,快速靈活,便于多學科協同耦合,提供數字化、精細全面的流動物理的理解和洞察。
近40年來CFD發展迅速,從根本上改變了航空航天飛行器研究、設計流程。CFD有效減少了地面試驗和飛行試驗需求,節省了研制費用,降低了設計風險,顯著縮短了研發周期,并能夠深入揭示流動物理機理以便進行分析診斷、性能改進和優化設計,開拓飛行器設計及飛行器性能方面的新領域。CFD通常配合或部分取代試驗,減少試驗次數和時間,但在一些特定、復雜或極端條件下,CFD是唯一可以依賴的研究手段或設計數據來源。
CFD在航空領域的具體應用主要包括:飛行器氣動性能計算、流動分析診斷、流動控制或改進設計、氣動布局設計或最優化設計、載荷計算、飛行(動、靜)穩定性分析、氣動彈性計算、結冰模擬、機載武器/副油箱等掛載的多體分離與運動仿真。其他方面還有:氣動聲學和噪聲控制、發動機燃燒及推力計算、氣動熱和熱防護模擬、力/熱/結構/運動等多場耦合計算和協同設計、氣動光學、機艙通風/溫控/滅火等。
由于CFD在節省研制費用、縮短研制周期、提高飛行器性能、降低設計風險、實現研制數字化自動化等方面的優勢,在航空航天等領域,它革命性地改變了傳統的氣動研究和設計方法,推動了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未來飛行器性能的確定,將依賴于在“虛擬風洞(CFD)”數據基礎上產生的“虛擬飛行”,這將是飛行器研制的主要發展方向。
波音公司的Tinoco說[17]:“在現代商業飛機的成功設計中,CFD的有效應用是一個關鍵因素。CFD在商業飛機設計中的應用革命化地改變了氣動設計方法……。”在飛機發展中,CFD的應用越來越多,這并不是因為它本身技術上的推動,而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現在,CFD是氣動設計過程的主要部分,另外還包括風洞和飛行試驗。在顯著縮短飛機研發周期方面,CFD是主要保證因素。如果希望保持競爭力,別無選擇。
Lockheed Martin公司的Raj指出[21]:“CFD將在飛行器氣動設計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并在飛機設計的每一階段發揮核心作用,之所以聚焦CFD,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飛機設計的每一個階段,CFD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 Stanford大學的Chapman認為[22]:“對于高超聲速飛行問題,風洞和激波管在模擬高溫和真實氣體效應方面的基本能力不足這一情況非常嚴重,以至雷諾平均Navier-Stokes的CFD,即便不具有大渦模擬能力,也能提供遠比試驗真實的模擬。因此,在今天的高超聲速飛行器設計中,計算機已變成主要的、風洞和激波管已變成次要的流動模擬數據的提供者。”對比一下Northrop 的YF-17戰斗機和Northrop/McDonne Douglas的YF-23戰斗機的發展歷程:YF-17設計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歷時8年,用了13 500 h的風洞試驗,幾乎沒有使用CFD輔助設計;更加復雜的YF-23設計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歷時8年,用了5 500 h的風洞試驗,用了15 000 CPU小時的CFD輔助設計。研制人員說:CFD減少了花費、降低了風險、提供了更優質的設計方案。
在中國,航空航天領域CFD也得到普遍認可,成為型號設計部門的常規手段:CFD作為主要的氣動設計手段,風洞試驗成為后期的確認性工作;計算周期大大縮短,常規CFD任務可以在數日至數周內完成,復雜任務可以在數周至數月內完成。
下面,分別論述CFD在民用航空和軍用航空方面的成就。
1.1 民用航空CFD成就與實例
以波音和空客為主線,論述民用航空CFD的發展歷程和成就,最后介紹一個代表未來CFD發展和應用的方向:德國DLR Digital-X研究的基于數值技術的虛擬飛行器設計和虛擬飛行試驗。
1.1.1 波音公司
美國波音公司在CFD理論和方法研究、CFD軟件開發及其航空工程應用等領域全周期、多方位地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有效推動了CFD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效益。波音公司的CFD歷史,可以認為是一部濃縮的CFD發展史。因此,這里詳細論述波音公司的CFD情況[16-18]。
首先,簡述一下其發展歷史:20世紀60年代末至1973年之前,主要使用線化超聲速流動代碼;1973—1983年,面元法占據了中心地位,它可以模擬復雜幾何構型中同時存在線性亞聲速和超聲速的復雜流動。非線性勢流/耦合邊界層代碼在1983—1993年達到了全盛時期,其對應的歐拉版本在那個時段后期也開始使用。1993—2003年,開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RANS代碼,顯然,導致這些代碼廣泛使用的許多開發和演示工作,發生在比這些時間早5~10年的時候。
1998年,波音公司有超過20 000次CFD運行,以支持各種產品線。其中超過85%的運行是由CFD研究小組之外的生產工程師完成的。CFD方法可以在數小時或數天內提供及時的結果,而不是數周或數月。對這些方法的充分經驗使管理層對其結果有信心。這意味著,計算結果是可信的,無需進一步比較試驗和計算結果。
自20世紀70年代末波音757和767的開發期間起,CFD方法開始進入生產應用。波音757駕駛室允許使用與波音767相同的座艙和執照機型,完全采用CFD設計,只在最后進行風洞試驗。在波音757和波音767中,CFD影響了發動機/吊掛安裝,機翼設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CFD方法廣泛應用于新型波音777的高速構型設計,以及派生的下一代波音737的設計和開發進度縮減。多年來計算技術的進步使得CFD能夠影響與飛機設計更多的相關設計問題,如圖1所示。使用這些方法可以在開發的早期進行更周密的空氣動力學設計,從而更專注于與操作和安全相關的功能。
波音777作為一種新設計的機型,允許設計師充分利用CFD和空氣動力學進步的成果。高速巡航機翼設計和推進/機身集成消耗了CFD應用的大部分時間。飛機設計的許多其他特征點也深受CFD影響。CFD在機身設計中發揮了作用,一旦機身直徑確定,就可以利用CFD設計駕駛艙;設計完成后,風洞試驗表明,CFD設計良好,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改動。因此,在未來的駕駛艙設計中,無需再進行風洞試驗。針對后機身和機翼/機身整流罩形狀設計,CFD通過壓力分布和流線,提供了流動理解并指導了這個設計過程,CFD擴展了相關的風洞試驗。對于襟翼支撐整流罩的設計,CFD也發揮了類似的作用。CFD用來確定空氣數據系統的靜態源、側滑口和攻角葉片的主要位置。CFD用于設計環境控制系統、ECS、進排氣口,機艙(增壓)出口閥使用CFD進行定位。盡管CFD在高升力設計方面仍處于起步階段,但它確實為高升力概念提供了見解,并被用于評估平面形狀的影響。然而,大部分高升力設計工作是在風洞中完成的,需要使用CFD確定和完善由于風洞壁、模型安裝和雷諾數等試驗數據的修正。
作為早期波音737的衍生產品,下一代波音737-700/600/800/900,提出了一個更受約束的設計問題。CFD的大部分工作還是集中在巡航機翼設計和發動機/機身集成上。雖然是新的機翼,但它的設計仍然受到現有機翼/機體相交以及液壓完全失效時需要保持副翼手動控制等限制。同波音777類似,CFD與風洞一起用于機翼-機體整流罩的設計、后體的修改、襟翼軌跡整流罩和高升力系統的設計等。
在機翼設計方面,CFD可以充分考慮機翼、機艙和發動機的相互作用,設計出最佳性能的機翼,并通過多點設計實現具有可接受的非設計特性。
CFD也變革了機翼的設計方法,傳統的、依賴經驗和大量風洞試驗的“試錯法(Cut-and-try)”已經被依賴CFD模擬的“反設計法”和“多點優化法”所取代。這些新方法更快、更經濟,更重要的是這些新方法設計出的機翼性能比傳統機翼有了顯著的改進。傳統的試錯法需要設計幾十個機翼(最多77個)進行大量風洞試驗,而新的CFD設計方法,只需要設計出2~3個性能最好的機翼,再放到風洞里進行試驗驗證和最終選型。
波音777和787同樣做了大量的風洞試驗,但相對之前型號,已經大幅減少了風洞試驗的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CFD技術的應用,它實現了更智能的試驗,減少了獲取關鍵空氣動力學數據所需的試驗車次,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無需進行試驗。CFD在波音787中的應用情況如圖2所示。
在波音777的空氣動力學設計中,通過CFD分析發現了由于發動機排氣而產生的顯著干擾阻力的風險。傳統的風洞試驗(沒有模擬排氣)無法檢測到這個潛在的問題,只有非常昂貴的動力機艙測試技術才能評估這些干擾效應。這種新飛機考慮了3種不同制造商的發動機,使用動力測試技術來開發發動機安裝將增加相當大的費用,此外,這種基于風洞的開發將需要太多的時間和不可接受的設計流程時間。CFD使得解決這些安裝問題變得切實可行,包括及時解決發動機排氣流的影響。如果這些問題直到飛機開發的后期才被發現,也就是通常完成動力測試的時候,任何修復措施的實施都將是極其昂貴的。
但是,用知名CFD軟件OVERFLOW計算波音777的升力特性時,出現了大攻角α下升力系數CL誤差很大的現象[23],如圖3所示,這是由于大攻角時分離預測不正確造成的,也就是大攻角時CFD模擬會提前分離,導致失速攻角提前。這個“升力塌陷”現象在航空CFD中很普遍,也成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難題,此問題將在后面展開討論。
作為航空CFD早期最成功、最有效的應用之一,在此詳細論述一下CFD在發動機/機體集成設計方面的應用實例。
早期CFD的成功之一,是提高了對機翼下吊掛式發動機短艙的干擾阻力的認識水平。風洞試驗揭示了存在有害的干擾阻力,但干擾的物理機制仍然未知。為了避免干擾阻力,通常的做法是將發動機從機翼上移遠一些,這導致了更長的發動機吊桿,由此產生了額外重量和阻力,這時必須權衡如果發動機向更靠近機翼移動時潛在的干擾阻力。
CFD模擬以及專門的風洞試驗,提供了對造成干擾的流動機制的必要洞察。波音757、767、777、737-300/400/500系列、下一代737/600/700/800/900系列和KC-135R都是在不產生明顯阻力的情況下,實現了非常緊密的短艙安裝。
如果波音737系列要繼續生產的話,來自麥道MD-80的競爭壓力要求在運行效率和能力方面有很大的改進。此外,新的聯邦法規要求在未來幾年內大幅降低噪聲。如果能在不增加過多的干擾阻力、重量或成本的情況下,安裝現代渦扇發動機,就能滿足這一需求。在機艙安裝上,為了避免干擾阻力,傳統的做法是加長起落架,以提供適當的地面間隙。然而,增加起落架長度,將導致額外的重量和過高的成本來修改飛機結構。最終的解決方案,允許一個更大直徑的發動機適配在機翼下而不增加主起落架的長度,如圖4所示。CFD所提供的知識使原始737的主要衍生品非常成功,CFD的作用在這里促成了歷史上最成功的商用噴氣飛機系列。
CFD也被越來越多的應用于噪聲預測和設計,例如,自2004年以來,波音737在機頭上安裝了成對的小型渦流發生器,目的是減少擋風玻璃底部折角處的分離,以及由此誘導的玻璃上的壓力波動尤其是駕駛艙內的噪聲水平。雖然是由CFD設計的,沒有進行氣動試驗,但在飛行過程中測試了駕駛員耳旁的噪聲降低,驗證了降噪設計的有效性[24]。
1.1.2 空客公司
空客公司[19-20]認為:在過去的50年里,數值模擬在物理模型的準確性、求解算法的穩健性和效率以及整體預測方法的可靠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目前,數值模擬被大多數的飛機公司(空客、波音、達索等) 在設計鏈中經常使用,減少了需要在風洞中試驗的設計方案數量。這一趨勢,盡管目前有局限性,但在未來十年中將繼續增長。最終,數值模擬將大大改變飛機的設計過程和工作方式,并可以顯著減少開發時間,同時將越來越多的學科納入到概念設計的早期階段,以找到整體的最佳方案。CFD在A380上的應用如圖5所示。
2011年,空客給出了在飛行包線里CFD可信度的示意圖,如圖6所示。由圖可見,在巡航點附近的飛行區域,CFD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隨著從巡航點向飛行包線邊緣的移動,CFD的可信度逐漸下降。這是因為巡航狀態下的流動分離最小,CFD精度最高,因此可以高度依賴CFD。距巡航狀態越遠,飛機上的分離流、非定常等復雜流動現象越嚴重,目前物理模型對這些現象的模擬精度和可靠性均不足,這個問題將在后面展開討論。
值得強調的是,巡航狀態的設計工作占整個飛機研制空氣動力學相關工作總量的不到20%。也就是說,可以高可信度的依賴CFD的工作總量并不大。
目前的數值模擬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來分析詳細的飛機結構周圍的流動,但有許多明顯的技術限制。這些限制包括:主要由中等和大規模分離主導的非設計條件、飛行雷諾數效應、控制面間隙效應、控制面效能、動力系統等。同時,用于大型航空問題的工業仿真工具,仍然未能充分利用新興的高性能計算架構的最佳性能。最先進的工業求解器使用的是20年前的算法和思維方式。
它們沒有利用新硬件架構的巨大新功能:主流加速器或多核平臺。近年來,計算世界發生了變化,處理器時鐘速度的提高已經停止,多核/異構平臺現在占據主導地位。只有聚焦于將算法和高性能計算聯合研究,才有可能開發和形成更成熟的仿真工具,達到歐洲航空工業需要的水平。
空客公司計劃從2個主要方面徹底改善現有的模擬能力:
1) 精度(通過物理建模和算法)。
2) 效率(通過數值算法和先進計算機)。
總體來說,空客的CFD研究和應用同波音類似。但同波音相比,空客CFD的發展歷史、應用深度和廣度稍有差距。
1.1.3 德國DLR
近年來,航空工業已經建立了流動數值模擬手段作為氣動設計過程中的關鍵元素,并與風洞和飛行試驗相輔相成。物理模型和數值方法的不斷發展以及日益強大的計算機,使用數值模擬的范圍要比過去大得多,這將從根本上改變未來飛行器的設計方式。除了加快和改進產品設計周期,數值模擬還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用數學模型表達所設計產品的所有性能及其相互作用并確定在現實操作條件下的飛行器行為。DLR在2012—2016年開展的Digital-X研究[25]就是以這種思想為指導,以實現飛行器的虛擬設計和虛擬飛行試驗,其流程原理見圖7。它采用高保真多學科仿真方法,通過數值計算確定飛行器的飛行特性,并在真實的首次飛行前進行虛擬飛行。在虛擬計算機環境中,實現飛行器首飛的愿景,降低開發風險,通過逐步認證,顯著降低開發成本。
Digital-X項目的主要目標是開發和部署一個靈活的、并行的、基于各學科高保真數值方法的軟件平臺,用于飛機和直升機的多學科分析和優化。DLR的幾個研究所都參與其中,包括空氣動力學與流動技術研究所、空氣彈性研究所、推進技術研究所、結構與設計研究所、復合材料結構與自適應系統研究所、飛行系統研究所、航空運輸系統研究所、系統動力學與控制研究所,仿真與軟件技術研究所等。
圖8顯示了XRF-1機翼/機身構型的多學科優化結果,燃料消耗降低了3.6%。這個結果是用多學科優化鏈在詳細的層次上實現的,采用高保真CFD計算機翼/機身的空氣動力學,結合機翼結構的有限元分析,確定靜態氣動彈性平衡。此外,在每個優化步驟中,機翼結構使用了兩個預定義的載荷情況。在保持平面面積不變的情況下,采用5個幾何參數(扭轉、展弦比和后掠等)對機翼進行參數化。
1.2 軍用航空CFD成就與實例
這里主要以美國近40年來,不同時期軍用飛機研制中的CFD應用為主線,論述軍用航空CFD的發展歷程和成就。之所以選擇以美國為例,一是因為其高水平的CFD,二是因為豐富的參考文獻。
1.2.1 F-18、F-16掛載分離
如圖9所示,20世紀后期,為了獲得前視紅外瞄準器(TFLIR)的預先許可,美國海軍在F-18C戰斗機上進行了77次掛載分離飛行試驗[26],時間超過4年,花費超過600萬美元。1998年12月,戰斗機掛架下MK-82炸彈投放時尾部與TFLIR相撞。此后進行了多次飛行試驗,仍然無法確定事故原因,為避免事故再次發生,只好對掛載投放條件作出限制和妥協,對機載武器的戰斗力造成了影響。后來再次開展研究,改用CFD、風洞試驗和飛行試驗相結合的方法,用了不到2年的時間,進行了7次飛行試驗,總成本不到200萬美元,并且CFD計算結果清晰的解釋了炸彈和瞄準器相撞的原因:TFLIR后體激波打到了炸彈尾部,使炸彈產生了較大的俯仰及偏航力矩,從而導致相撞。最后基于相撞原因的清晰解釋給出了解決方案,這個CFD解釋被制造商稱為“無價的收益”。為了便于對比,這里將這2次的試驗情況匯制成表1。

表1 試驗研究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test research
由此可見CFD的顯著特點:時間短,費用低,可以給出詳細具體的機理性描述,這也是CFD受到廣泛歡迎的主要原因。
Baum等[27]使用非結構網格CFD方法模擬了F-16C/D拋撒370加侖副油箱運動過程,馬赫數Ma=0.851,攻角α=2°。圖10給出了CFD、風洞和飛行試驗的結果對比。可見,同實際飛行結果相比,CFD計算結果比風洞試驗更接近飛行結果。實際上,對于航空航天飛行器常見的多體分離運動問題,由于風洞試驗技術困難、飛行試驗風險較大,CFD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
1.2.2 F-22 消除垂尾抖振
這里敘述F-22研制時,利用CFD探索使用氣動固定裝置來緩解或消除垂尾抖振[28]的一個實例。
F-22的高機動能力很強,但它作為雙垂翼戰斗機,在一定飛行條件下,其垂尾會受到由于前體渦運動尤其是渦破裂而導致的抖振,這對飛行安全、穩定和控制、結構動態載荷和應變都構成了危害。F-22的早期飛行測試也證實了由于非定常渦運動而發生的垂尾抖振。
如圖11所示,通過CFD計算(Ma=0.5,Re=5.26×10-7,α=22°和26°)發現:在機身前緣和發動機進氣口上唇的交界處形成了強渦流,其后的非定常渦破裂導致了垂尾抖振。通過CFD計算和分析,設計了梯形隔板。CFD計算結果見圖12,可見由于梯形隔板的作用,渦破裂及垂尾抖振都被消除了。后來專門安排了風洞試驗驗證CFD結果,表明CFD給出的幾種方案都可以延遲或消除渦破裂,從而顯著降低或衰減垂尾抖振,可用迎角高達約32°。
CFD還分析預測了F-22馬赫數、發動機入口質量流量和尺度對抖振起始的顯著影響。
1.2.3 F-35 減阻優化設計
F-35研制時CFD發揮了很大作用,日常氣動設計約使用了超過6 000次的CFD作業。尤其是由于F-35有3個型號且被多國采用,其掛載的武器種類非常多,掛載分離的風洞和飛行試驗都比較昂貴、困難,因此CFD被大量的應用于掛載分離仿真。這里,僅給出F-35利用CFD進行減阻優化設計的例子[29],因為這個例子簡單易用且很有實用價值和借鑒意義。
F-35曾經遇到整機阻力偏大的難題,工程師們利用CFD的特點,設計了一種非常簡單有效的減阻優化方法,其步驟是:
1) 用CFD完成F-35的全機計算。
2) 通過第1)步計算結果畫出壓力系數Cp梯度圖,據此圖直觀的找出阻力增量較大的各個部位,并研究確定潛在的改進部位。
3) 對這些部位進行外形修改以進行減阻優化,并針對修改后的外形進行網格調整和CFD計算。
4) 分析計算結果,評估性能影響。
5) 結束優化設計或返回進入下一輪優化設計循環。
這樣的一個優化設計周期僅需要4天時間,最后選用的優化結果再進行風洞驗證。顯然,這種基于CFD的優點設計具有簡單、快速、直觀、高效、數字化、易評估的優點。
1.2.4 V-22魚鷹旋翼機旋翼模擬
直升機旋翼[15]的CFD計算是航空CFD中最具挑戰性的難題之一。這不僅因為旋轉槳葉同機身高速的相對運動、強烈的相互干擾,還因為槳葉尤其是槳尖高速運動時同自由來流的相對姿態、流動條件等一直在快速變化,產生了非常復雜的非定常強剪切流動,誘導了多種尺度的渦結構,這些渦不斷向下游運動演化,它們對旋翼氣動性能、飛行穩定性、直升機噪聲等影響很大。用目前的RANS CFD模擬這種多尺度、非定常渦運動存在先天理論上的不足(雷諾平均)以及技術上的困難。
圖13是用CFD軟件OVERFLOW計算V-22魚鷹旋翼機三葉片&輪轂的分離流和渦運動情況[30]。使用的計算機是NASA的 Pleiades超算系統,該計算機有20萬核、峰值2.9 pFLOP/s,當時世界排名19位,計算時實用16 384核。使用的計算網格有4套,網格數從1 400萬~30億,這也是迄今為止RANS已知的最大計算網格。計算時間:30億網格時、4萬時間步,20 h(由于通訊瓶頸,求解器只用了計算機峰值速度的約10%~15%)。
從圖13可見:隨著網格從約1 400萬不斷細化至30億,計算出的渦核直徑逐漸靠近試驗值,但仍有差距。RANS使用30億網格可較精確模擬槳渦,用世界最先進的計算機約1天可完成。但上述計算僅是3個葉片&輪轂,不難推斷:對直升機等復雜構型飛行器的CFD精確計算將更加困難。另外,這個算例使用了當時世界排名19的最先進的超級計算機,一般航空領域通常沒有或難以使用如此性能的計算機。因此,精細、精確的RANS模擬仍然非常困難。
作者課題組徐培敏計算了V-22魚鷹旋翼全機的懸停/傾轉流場[31]。使用的計算方法是:空間格式ROE+WENO5,時間格式LU-SGS雙時間步格式,湍流模型SA模型,采用384核并行計算,使用重疊網格技術,網格總量約8 910萬。計算結果見圖14[31],圖中渦量圖由Q準則計算,用馬赫數著色。分析可見,由于使用了高階格式和較大網格量,全機的渦結構捕捉清晰,尾跡渦向下發展到遠離機身較遠的距離;槳尖渦發展軌跡隨著向下的距離增加逐漸向前移動,向對稱面靠近。這樣復雜、精細的CFD計算,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這自然意味著CFD應用的不斷進步。這個CFD計算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工作,這里說明一下它的4個難點:V-22全機幾何構型非常復雜;需要同時考慮旋翼旋轉+傾轉效應;生成近9 000萬的全機重疊網格;復雜的計算結果處理和流動機理分析。這4點對任何一個經驗豐富的高手都是不小的挑戰。
對比圖13(NASA模擬)和圖14(北航模擬):2009年的NASA模擬使用了1 400萬~30億的網格且計算區域只有三葉片&輪轂,2020年的北航模擬使用了僅9 000萬的網格,但計算區域包含了V-22全機。對比計算結果可見,北航模擬的流動更加精細、渦結構更加豐富、流動尺度從大到小范圍更廣、流動結構時空演化的耗散更低更慢,也就是說結果更好。對比兩個模擬可知,所使用的重疊網格技術和湍流模型都是相同的,作者分析認為導致上述模擬結果差異的主要因素是:空間格式和網格質量。NASA使用了3階中心差分格式,北航使用了5階WENO格式,5階格式的分辨率等性能優于3階中心差分。從論文附圖的網格上判斷,北航網格對流場的適應性匹配、網格正交性和過渡光滑性等有優勢,這可能是北航模擬結果更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1.3 CFD的優勢及其在飛行器研發中的作用
目前航空領域可以利用的CFD主要優點是:
1) 經濟性。CFD僅使用軟件和計算機,一般情況下,比風洞試驗和飛行試驗等更省錢。
2) 快速、靈活。可以在數天或數周內,快速完成CFD的建模、計算和結果處理;可以方便通過改變輸入參數,實現飛行器幾何變化或流動條件的調整。CFD可以實現其他方法無法實現(時間周期或流動條件限制、流動物理理解困難等)的設計、改進或優化。如上述F-35的優化設計周期只有4天。
3) 打破了學科之間的障礙,容易實現多學科協同耦合。如通過同最優化方法的結合,在設計中實現真正全局最優化[14];通過同飛行器運動、控制的耦合實現虛擬飛行等。
4) CFD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提供全息數據,從而提供對飛行器研制非常必要的流動物理的理解和洞察。CFD可以提供飛行器及其任意部件上完整、詳細的流動細節和力/力矩,以及數字化、圖形化的流動物理,提供對流場認識、分析、診斷、改進設計、優化設計等直接支持。目前的風洞無法提供這種級別的細節和數字化信息[15]。
在飛行器研制中,CFD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應用包括:
1) 巡航條件下,目前CFD模擬水平是足夠的,可以通過CFD精確預測飛行器的絕對空氣動力學性能,其精度高于風洞測量后經飛行雷諾數修正的數據。這些CFD預測包括全機跨聲速巡航構型、高速(巡航)機翼設計、配平到指定的重心位置、推阻平衡的動力效應、真實彎曲的氣動彈性變形等。
2) 巡航之外的飛行狀態下,尤其是大分離流動、邊界層轉捩等,CFD的可信度較低。盡管如此,CFD仍有限的應用于低速(高升力系統)分析,內部流動,穩定性和控制(S&C),振動和噪聲預測等。如進行性能變化和比較分析,排除一些不合適的構型,并減少風洞試驗。
3)目前,CFD最重要的應用之一是飛行器研發的概念設計和早期分析設計階段,如用于確定初始結構尺寸等。即使在早期設計階段,淘汰那些表現出良好巡航性能但可能具有無法通過認證的操縱特性的構型也是很有意義的。這些不可接受的操縱特性通常發生在以明顯流動分離為主的飛行狀態。例如,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法規對飛機俯仰力矩特性的非線性進行了限制。
4) 使用CFD對風洞數據庫進行修正,如雷諾數效應(飛行雷諾數)、風洞壁效應、測量儀器和安裝系統的干擾修正、氣彈效應等;并幫助將風洞數據庫擴展到飛行條件。
5) 飛行器研制中,風洞有可能無法提供所有必要的數據。此時,CFD會用來增加數據集以滿足要求。有些情況下,CFD是必不可少的,如線負載、大飛行雷諾數(高達約10億)和羽流效應等[15]。
目前,航空CFD還在不斷發展、完善之中。NASA認為[15],CFD在飛行器設計中有4個階段:
1) CFD通常不是產品開發過程的一部分,但產品開發團隊正在密切關注CFD能力的發展。在這一階段,CFD被用于探索飛行包線的一部分,此部分的問題預計會出現在穩定性和控制(S&C)或載荷方面,但這與建立一個完整的空氣動力性能數據庫不同。
2) CFD作為試驗的補充或深化進入工程過程。這時,風洞是主要數據源,CFD是作為補充的第2個獨立的數據源,它在風險管理上非常重要。該階段同下一階段的界限并不明確。
3) CFD的不斷發展使其成為首要的數據源,風洞試驗作為降低風險和驗證確認的獨立數據源。這階段,風洞試驗越來越少、時序上也越來越靠后。
4) 完全放棄風洞僅使用CFD,這要求在全包線中對CFD結果的正確性有充分的信任,并要求此前有足夠的經驗,以便工程團隊確信在預期的代價和周期內,CFD可以完成計劃的工作。
經驗表明,CFD正處于飛行器設計的第3階段,即僅使用CFD進行設計開發和成熟完善,在項目接近尾聲時僅對優勢的構型或者可能只對一兩個優勢的構型進行風洞測試確認。今天,這基本上是常規構型跨聲速空氣動力學性能工作的規范。
風洞試驗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獨立于風險管理的數據確認手段。CFD還不能提供所需的精度(在各種條件下,具有低個位數百分比的精度)和吞吐量,這是取代廣泛的風洞測試所必需的,這種情況反映了對CFD預測的高度但不完全信任。
需要強調的是[18]:現在越來越多的將CFD結果直接與飛行試驗進行比較,而不是同風洞試驗比較,這兩種信息來源在工程過程和公司文化中的地位正在慢慢改變。因為正確的理由而從風洞過渡到CFD是很重要的,如因為壁效應、雷諾數和氣彈等,但僅僅為了速度和成本優勢這樣做是有危險的。本文對CFD過度自信的傾向,甚至到了忽略眾所周知的錯誤來源的程度,可能導致CFD被指責為“一種錯誤的設計方法”,而這種錯誤帶來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如不得不對飛行器重新設計。因此需要謹慎的增加對CFD的信賴,避免過度信賴帶來的危害。
1.4 航空CFD應用現狀
1.4.1 氣動數據
目前,用于創建飛行器設計所需的空氣動力學數據庫,需要風洞產生數十萬至數百萬數據點,且必須覆蓋整個飛行包線。現在越來越多的認證要求、機動負載減輕、包絡保護、電傳操縱等的出現,增加了飛行器開發所需的載荷、S&C和模擬器數據庫等的規模。
首先,CFD減少了開發低阻力高速巡航構型所需的試驗;其次,飛行特性和空氣動力載荷必須在首飛前以非常高的精度進行預測,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飛行測試中出現的意外情況和所需的變化。通常的做法是使用CFD對風洞數據庫進行修正,以考慮雷諾數效應、風洞壁和安裝系統的干擾,以及飛行器與風洞模型之間的幾何差異等;另外,在一些情況下,還要利用CFD加強或填補沒有風洞數據的數據庫。
在商用運輸機的發展中,最終氣動飛行載荷的確定要求很高的精度。載荷預測中過于保守會導致不可接受的結構超重。低估飛行載荷可能會導致飛機無法獲得認證,或認證為較低的起飛總重,在結構改進之前,性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都對CFD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
1.4.2 設計周期
一個典型的飛機開發項目要經過2個或3個設計周期,每個設計周期都需要大量的CFD和重要的風洞試驗[32]。對于飛機制造商來說,其目標是將飛機開發過程減少到一個設計周期。這需要CFD和風洞的重大改進。例如,新的設計理念推動了對更高雷諾數試驗的需求,現有低溫、高雷諾數風洞的生產力需要至少提高一個數量級。
CFD可以貢獻的潛在新領域是飛機開發的各個階段的認證,以及航空公司的客戶支持。除了與權威機構溝通,使之確認CFD有能力產生可信任的結果,以滿足特定需求,CFD過程變得可跟蹤和可重復是必要的。目前正在努力爭取在特定情況下使用CFD進行認證,比如構型的微小變化。實際上,分析認證是指通過理論、飛機模型比較和地面試驗來建立信息,而不僅僅是通過CFD建立。爭取在特定情況下使用CFD進行認證的目的是減少一些飛行試驗。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降低成本、縮減設計時間以及在飛行測試期間避免危險。
Spalart曾經激動地說[18]:“通過分析,主要是通過CFD,廣泛接受認證,將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對我們來說是一項鼓舞人心的使命”。通過逐步認證,顯著降低開發成本。
1.4.3 風險防控
一般說來,飛機制造商都是非常保守的公司,首先是因為他們對安全的關注,也因為任何設計錯誤都會導致極端的工業后果。在新型號的組裝或飛行測試中發現的缺陷會對進入服役造成相當大的干擾。
很明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設計缺陷,因為在項目后期對其進行糾正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可能予以糾正。為了在環境、經濟、安全、性能和操作參數之間找到最佳平衡,在非常早期階段,就需要對飛機遵守的不同要求進行數字化建模。數值模擬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為了實現這一點,飛機在早期階段就進行了建模,以表征物理飛行行為以及不同飛機結構和系統(包括動力裝置)的行為。然后,設計團隊將不同的改進計劃和研究應用到這個模型中,這允許快速分析任何修改或優化建議的結果。由于現在執行得越來越詳細,在越來越短的時間框架里,需要大量的高性能計算能力。
1.4.4 CFD和風洞試驗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地面試驗設施的利用率和需求都在穩步下降,而對CFD的依賴則在穩步上升。核心問題是: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嗎?在未來20年內,風洞試驗的作用會減弱嗎?
飛行器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性能改進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就需要更大的數據量和更高的精度。因此,并不認為風洞試驗在未來20年內會被淘汰,但確實看到隨著計算模擬和實驗能力的發展,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會持續演變。
在航空領域,即使是現在,用于高升力系統、S&C、載荷、故障條件、結冰和噪聲的風洞努力都是相當大的。總的來說,對于一個新機翼,包括它的高升力和控制系統,以及無數的構型和姿態組合,這樣的試驗需要一年的全天候風洞使用。它也顯示了CFD在處理飛行器全部復雜情況時的相對弱點。這個弱點包括精度和生產周期。
對于戰術軍用飛機,存在巨大的數據庫用于S&C、掛載分離和高升力系統性能,目前的CFD代碼無法準確地模擬這些。對于飛行包線的主要部分,RANS幾乎肯定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因此,在簡單流動情況下,CFD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風洞試驗,但要在航空領域取得重要進展,風洞是必要的,除非CFD可以克服上述的不足。航空航天工業將繼續廣泛使用風洞試驗,而且由于目前CFD物理模型的不足,預計這一趨勢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下去。產品的復雜性、飛行包絡的擴展、風險規避和大量的飛行控制系統是繼續使用風洞的額外動力。
在可預見的未來,計算技術不會消除對試驗設施的需求,CFD完全能夠取代風洞試驗的時間框架估計在幾十年左右。CFD的適用性范圍只有通過穩定的技術投資才能擴大,驗證過程也將需要精心設計的風洞試驗。
目前的挑戰是如何將CFD與風洞試驗最佳結合,以改善氣動飛行載荷的預測,同時減少開發周期時間。
2 航空CFD的困境
2.1 DPW及對航空CFD困境的認識
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初期開始,基于RANS/Euler方程的航空CFD無論是在計算方法和湍流模型等核心理論和方法,還是在工業應用上都發展迅速、成效斐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發達國家的航空CFD進入RANS廣泛應用的時代,成就輝煌,可以計算的飛行器構型越來越復雜、網格越來越多、計算效率越來越高(尤其是1988年LU-SGS無條件穩定隱式格式出現[33]后)、流動圖譜越來越絢麗、計算結果同試驗結果越來越吻合,航空CFD的模擬范圍也在不斷的迅速拓展:從定常到非定常、從附著流動到分離流動、從單體到多體甚至多體分離……,大家信心十足,越來越相信“網格決定一切(Grids Are Everything)”“只要網格足夠,一切不是問題”。[34]
此后,沿這個方向的CFD研究基本沒有大的突破,甚至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有人質疑:CFD死亡了(CFD Is Dead)[35],當然,這句話的本意是CFD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科學、一個研究和發展領域結束了,正如尋求二次方程一般解的努力已經過去了一樣。
文獻[36]表示“這是一個CFD成熟的時期,人們沉醉在能用CFD處理復雜的機體結構和復雜的物理現象的想象中。這一時期進行了產品創新,被認為是繁榮時期”。現在仍有人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想說這方面努力的重要性在90年代早期就大體結束了,那時我們已獲得了基本的CFD方法去解決各方面的空氣動力學問題。
文獻[15]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CFD的能力在過去的10~15年里已經趨于穩定。20世紀70—90年代,從位勢方法過渡到歐拉方法再到RANS方法,非結構化網格技術被廣泛采用。然而,在過去的十年中,RANS方法的發展停滯不前,LES和其他更先進的技術(例如混合RANS/LES方法)并沒有對設計過程產生顯著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這些先進方法的計算成本和缺乏魯棒性。”
隨著CFD計算和分析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在模擬航空飛行器普遍存在的分離等復雜流動時,逐漸發現了CFD越來越多的缺陷、困惑,如即便對一些幾何非常簡單的物體繞流,CFD始終無法給出正確的結果,這其中著名的例子有翼型大迎角升力曲線、三角翼和雙三角翼上的旋渦流、超聲速底部流動等[34]。大量的計算實例也表明:對于航空飛行器的CFD計算僅在一些流動條件(如巡航時的附著流動)下,其結果高度可信。
CFD失敗案例使CFD界面臨越來越多的困惑、質疑。在這種背景下,系統評估當時航空CFD的能力和不足,成為理所當然的焦點話題,始于會議走廊聊天的DPW (the Drag Prediction Workshop)就這樣應運而生[10,12]。DPW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國際合作和系列會議,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清醒地認識了真正的CFD:外表強大、內核虛弱。外表強大是指當時被認為幾乎無所不能,內核虛弱是指由于湍流模型等核心方法的嚴重缺陷,其可信的范圍不足。
DPW對航空CFD最大的貢獻也許就是:通過大量、廣泛、公正、公開、長期、深入地計算、研究和分析,使大家清醒地認識到:
1) 當大家沉醉在CFD超出想象的發展速度和成功應用時,DPW使人們第一次普遍對CFD結果失望,這主要表現在不同代碼的CFD結果散布較大,超出了預期。經過DPW歷經20年的不懈努力,結果有所改善但沒有最終解決,很多疑點、問題等沒有澄清,如DPW最關心的網格效應和收斂性等。
2) CFD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包括分離的復雜湍流計算,CFD模擬分離的能力嚴重不足,同時也深刻認識到分離流對飛行器氣動性能影響的重要性。
3) DPW出人意料的成功,也促發了航空領域其他方面的CFD評估活動,如HiLiftPW(High Lift Prediction Workshop)系列會議等。這些公正公開、廣泛國際化的CFD驗證確認活動,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也逐漸形成了影響至今的基本觀念:對CFD預測的高度但不完全信任。
為了全面了解和評估航空航天中CFD的現狀,梳理存在的問題,美國、歐洲的政府部門、科研機構、企業、高校等開展了很多的國際合作、項目研究、專題討論、系列研討會,除了上述的DPW和HiLiftPW,比較有名的還有:The European Research Community on Flow, Turbulence, and Combustion (ERCOFTAC)、Workshops on CFD Uncertainty Analysis、CFDVAL2004 Workshop、A European Proj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Higher-Order Variational Methods for Aerospace Applications(ADIGMA)、Advanced Turbulence Simulation for Aerodynamic Application Challenges(ATAAC)。其中DPW影響最大,DPW參與者幾乎包含了國際上所有知名航空航天機構,其產生的大量CFD結果的數據統計、分類歸納和物理分析等成果非常珍貴、意義非凡,由于本文的部分觀點也基于這些成果,因此這里先簡單介紹DPW[37-42]。
DPW源于1998—1999年的AIAA會議,于2000年1月正式成立了第一屆DPW組織委員會。此后,經過20年的持續努力舉辦了6次國際研討會,DPW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CFD界普遍認為DPW是絕對的成功,因為它是CFD研究者、代碼開發者、航空領域CFD使用者等“基層草根”集體努力的計算分析、公開透明的交流討論。DPW通過長期、廣泛、充分、公開、多層次、多角度、針對性的國際合作和研討,評估CFD的實用性能尤其是阻力計算精度,對比和公正評價CFD代碼的有效性,揭示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并探索解決方法。因為DPW空前的歷時、廣泛的參與和豐富的成果,它成為國際上航空航天CFD領域影響最大的會議。會議發布了非常豐富的幾何構型、各類網格、數據統計、結果分析及對比、意見和建議等,這些均發布在公開的網站上,包括數據庫、會議文檔、論文、出版物和演示文稿等。
DPW發布的成果過于豐富,這里作者只能根據自己多年來的跟蹤閱讀和理解,濃縮其要點如下(以下用DPW加數字N表示第N次DPW會議,如DPW2表示第2次DPW會議)[12,43]:
1) 對CFD結果普遍失望,主要表現在不同軟件的CFD結果散布范圍較大,也就是誤差帶較寬,超出了預期。盡管后來通過不斷努力提高網格質量和數量、強化收斂性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散布范圍,但仍然大于飛機設計者對CFD的期望,并且俯仰力矩等并沒有顯示出隨著網格分辨率的提高而趨于收斂的明顯趨勢。總體說來,CFD置信度仍然沒有降到可與實驗相競爭的水平。
2) 網格問題(包括網格質量和數量、網格分辨率、網格收斂性等)一直是DPW研究的中心議題,CFD結果的數據統計也證實了網格質量和網格分辨率的重要性。網格數量從最初的250萬平均基準網格到后來最大高達24億網格。但最終仍然沒有給出明確或具有指導性的結論,CFD結果散布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如:相似的網格分辨率下,DPW6結果的變化一般比DPW5更高,DPW6俯仰力矩的變化甚至高于DPW3的結果。
3) 為盡可能消除網格因素對計算結果的影響,組織者刻意設計了各種獨特的網格集合。但統計數據仍然存在較大的散布,所以會議普遍認為湍流模型、軟件、邊界條件和計算格式等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但因為組織工作量大、協調困難等原因,對這些問題沒有進行有效的研究。
4) DPW2統計分析了計算結果,在網格、代碼、湍流模型、轉捩模型、黏性模型等影響CFD計算結果的5個因素中,發現湍流模型、轉捩模型和網格對計算結果的影響位居前3位,分別約為:15%、11%和11%,這是世界上第一次量化統計和認識了CFD結果的影響因素。
5) 自DPW2開始,就有一個共識,即分離區的準確預測是成功預測阻力的關鍵,關鍵區域的分離流動使得很難對網格收斂性和阻力預測得到有意義的結論。雖然后來的多次會議針對此問題設計了多種方案,但最終這一共識也沒有得到確認或否定,這是因為影響因素多且復雜。比如,網格細化后分離區變大還是變少?對于這一貌似簡單的問題,即便是世界知名的CFD軟件,也給出了令人困惑的結論:變小(CFL3D、OVERFLOW等),變大(UPACS、TAS、FUN3D、ONERA-elsA、BCFD),不變(Edge、DLR-TAU)。
6) DPW的統計分析表明,CFD的阻力誤差約為十幾至幾十個阻力單位(1個阻力單位=0.000 1),而風洞試驗的誤差僅有4個阻力單位。飛機設計者們更愿意所預測的阻力誤差在1個阻力單位以內,這一誤差對于亞聲速運輸機(如A320或B737)來說意味著增加或減少一名乘客[44]。
7) 總的來說,DPW系列會議提供了豐富的信息,雖然從某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幾乎是完美的CFD結果,但將大量的計算結果放到一起,會發現CFD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8) 在評估了所有結果后,一個普遍的看法是: 有一組CFD代碼,其計算結果比較一致,并且在跨越不同DPW會議序列的所有測試案例中都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組核心代碼是由基于所有類型網格的求解器組成的,包括結構網格、非結構網格和混合網格。可以由此推知:一些非結構和混合網格的求解器已經足夠成熟,可以作為CFD工具進行精確的阻力預測。這是DPW為數不多讓人興奮、很有意義和應用價值的結論之一。
實際上,HiLiftPW和國內組織的“第一屆航空CFD可信度研討會”[45],也有同上述DPW相似的結論,如:網格規模的增加沒有明顯改善計算結果之間的數據散布程度;應該加強CFD方法、湍流模型和可信度分析方法研究等。
CFD在應用上迅速進步但理論上步履蹣跚,促使業界認真地審視它的現狀,籌劃它的未來。事實上,近些年來歐美等都陸續發表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報告。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或者說最精彩的是:2014年,NASA組織了185名CFD有關領域的資深專家,進行了150多次各類調查和研討,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CFD Vision 2030 Study: A Path to Revolutionary Computational Aerosciences”(CFD2030)[13],它系統、深入地評估了航空航天領域CFD的成就與不足、需求與差距,對CFD在2030年應該具有的能力進行了規劃并給出了實現的具體建議。這份長篇研究報告是CFD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指導性文件。
2.2 航空CFD主要問題
目前,航空CFD存在3個限制其廣泛應用的主要缺點:計算周期過長、一些情況下解的精度或可靠性不足、CFD用戶的技能水平差異很大。前者成為限制CFD在氣動數據庫建設、優化設計、多學科耦合等應用的主要因素;后者的問題要嚴酷的多,它直接決定了CFD的可用與否、可信與否,如航空飛行器廣泛存在的分離流問題。
首先,討論CFD的計算時間或計算效率問題[15,17,20]。
與直覺相反,CFD同風洞試驗相比,隨著模擬次數的增加,其成本也在增加,會超過風洞成本。CFD的初始成本(時間、花費等)可以大大低于風洞試驗的初始成本(模型制作、安裝等), 但是當需要數百種以上工況時,成本比較就會轉向風洞。風洞的主要問題是雷諾數限制(需要根據飛行條件調整)、風洞壁效應、模型支撐、測試技術以及無法準確反映氣彈效應等。
在風洞運行幾分鐘的時間里,可以完成迎角或其他一些參數的掃描,而使用RANS需要數萬到數百萬CPU小時才能復現 (還存在精度問題)。一旦有了試驗模型,風洞仍然比CFD便宜得多,見圖15。
考慮到目前的飛行器設計需要大約數十萬至數百萬個模擬,在整個設計過程中最先進的CFD方法仍然沒有競爭力。CFD還需要數量級的性能提升以提高這些數據的生產率,這包括改進幾何建模和網格生成、湍流建模以及算法和硬件性能等方面。
其次,討論CFD的計算精度和可靠性問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2002年11月,NASA和國防部在弗吉尼亞州主辦了一個關于空氣動力學飛行預測的研討會,與會者來自大小航空公司、NASA、美國海軍和美國空軍。在現有的設計方法中,缺少可靠、準確的氣動S&C預測方法被認為是一個主要的缺陷。本次研討會得出的結論之一是:預測全速度內分離流動的起始(伴隨的問題有轉捩預測、湍流建模、非定常流等),以及分離流動的特征和對飛機性能的影響,是唯一需要解決的最關鍵的基本問題,在空氣動力學研發計劃中應該得到非常高的優先級。在2003年9月舉行的關于S&C計算方法的后續研討會上[46],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因此,之前關于CFD缺點的討論與廣大空氣動力學界的集體意見完全符合。
分離流是大雷諾數流動的普遍現象。航空飛行器普遍存在大量的分離流動,例如,展開的前緣和后緣襟翼、擾流板偏轉、控制面偏轉、大迎角、大側滑角、高(跨聲速)馬赫數、發動機排放條件、結冰、飛行中遇到顛簸使其處于正常飛行條件的包線之外的速度和/或攻角條件下等[15]。
最重要的是,分離流是決定飛行器許多關鍵設計點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這些分離流主導著飛行器的許多關鍵設計點,如最大升力、非定常脈動、噪聲等,是影響飛行器安全、經濟性、舒適性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飛行性能、飛行包線等的主要因素。而且,分離形態的微小變化可能導致一些力/力矩的非線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操縱特性是否可以接受。一般情況下,線性范圍內的導數等可以得到充分的預測,但最關鍵的還是在這些非線性范圍里[15,20]。
如前所述,CFD的分離流模擬能力不佳,成為制約CFD在航空中大量使用的“瓶頸”難題和可信度不足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成為RANS長期以來走不出的困境、難以逾越的障礙。
例如,考慮模擬一架客機的著陸動作,包括高升力裝置、起落架、擾流板、移動控制面、地面效應、反推力和持續許多秒的不穩定。到今天為止,即使使用成本最低的湍流模型,RANS也無法為這個著陸動作模擬出達到行業要求精度的結果[18]。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風洞試驗對于分離流動的模擬也受到一些限制。如對于典型的低雷諾數風洞來說,也無法充分捕捉分離形態及其變化,這也可能是高雷諾數(飛行)風洞試驗的一個問題。其結果是,這些問題必須在飛行試驗中識別和解決。
除了分離流動,邊界層轉捩也是CFD最具挑戰性的難題之一,但轉捩僅在相對較小的區域和一些特殊應用中具有重要作用,限于篇幅,本文不深入討論轉捩預測,有興趣者建議閱讀文獻[12]。
另一個限制因素是CFD用戶的技能水平[18]。CFD用戶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熟練掌握CFD的各個階段:幾何準備、網格劃分、求解方案設置、計算結果后期處理和流動物理分析。其他限制還包括CFD中與數值計算、物理建模(尤其是轉捩和湍流)相關的各種不確定性,以及為進行網格生成和氣動分析而準備幾何體所需的時間。這其中,網格生成是一項困難、枯燥而又非常重要的技巧性人工工作,需要嚴格訓練和經驗積累;計算結果分析需要扎實的流動力學基礎和對流動物理敏銳的洞察力,這一點對用戶的要求更高。
2.3 湍流模型40年的艱難困境
通過上述論述,可以看到,航空CFD 40年來的主要困境在于分離流等復雜湍流的模擬能力不足,而分離流模擬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湍流模型。因此,這里對湍流模型進行較深入的剖析。
目前的CFD方法主要分為3大類,即DNS(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LES(Large Eddy Simulation)和RANS(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另外還有近20多年來發展迅速的RANS/LES混合方法。目前航空CFD廣泛使用的是基于湍流模型的RANS方法,RANS方法使用的湍流模型分為2大類,即:雷諾應力模型(Reynolds-Stress Model, RSM)和渦黏性模型(Eddy Viscosity Model, EVM),見圖16。
雷諾應力模型(RSM):它通過求解由Navier-Stokes方程嚴格推導來的、完整的輸運方程,從而給出額外的湍流動量通量。在RANS框架下,它是對湍流最全面的描述,因此一直被認為是最自然最符合邏輯的模型,可以克服EVM模型的一些嚴重缺陷,如各向同性。但由于后面將要論述的多種原因,目前RSM模型在國內外都沒有得到有效應用。
目前航空領域廣泛使用的湍流模型都是線性EVM模型,包括零方程、一方程、兩方程模型,雖然它有一些“致命的弱點”。這其中,航空CFD應用最多的是一方程和兩方程模型。廣泛使用線性EVM模型的主要原因是:簡單、經濟、魯棒性好、容易實現、歷史悠久、性能特點了解較多、使用者眾多等。
在CFD長期的發展、研究和應用中,越來越認識到湍流模型的重要性。Spalart[47]指出“湍流模型是CFD的決定因素”;2018年, Durbin[48]明確“湍流模型是大量應用CFD的核心”。
即便在新興的RANS/LES混合類方法中,湍流模型仍然具有基石般的重要地位:航空湍流主要是由近壁產生、發展以及分離再附等,混合方法強烈依賴近壁湍流模擬的準確性,這些都是由湍流模型決定的。
需要強調,湍流模型一般被認為是CFD中最大的誤差源、最薄弱的環節、最不靠譜的部分,是現代CFD的Achilles heel(Achilles heel,原指荷馬史詩中英雄阿喀琉斯的腳跟,現在一般指致命的弱點、要害),成為CFD結果不佳的“替罪羊”。[12,49-51]
事實上,前述DPW2的統計分析結果已經清楚地表明:湍流模型對CFD計算精度的影響最大。因此,湍流模型成為制約CFD發展和應用的瓶頸難題。
圖17表示:過去50年中,商業飛機設計一個循環中所需的試驗模型數量隨時間的變化[52]。藍色軸線表示在過去50年中,飛機設計一個循環中所需的試驗模型數量隨時間的變化,紅色是常用湍流模型發展的時間軸。由圖可見,近20多年中,湍流模型沒有取得顯著的進展。結合紅色的常用湍流模型發展時間軸來看,湍流模型發展之初,在應用中成效斐然,試驗模型數量顯著下降。但近20多來,該數據沒有明顯變化,導致這一瓶頸的主要困難是湍流模型的預測精度不足。下面將就湍流模型預測精度不足這一核心困難,從機理出發逐步展開討論。
首先討論線性EVM的基本原理,也就是Boussinesq(1877年)采用比擬法提出的渦黏性假設:他將流體微團的湍流脈動比擬為分子的熱運動,將湍流脈動量的平均動量輸運比擬為分子熱運動的平均動量輸運,即湍流脈動的雷諾應力比擬為分子熱運動的黏性應力。因此參照黏性應力的表達式,引入渦黏性系數將雷諾應力與平均速度應變率聯系起來,建立了線性渦黏性模型的本構關系:
(1)
由式(1)可推知:
1) 渦黏性項只考慮了正應力與其平均值2/3k的偏差,即正應力偏置部分。
2)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應力考慮了湍流的非局部過程(因為k方程有對流、擴散、耗散等效應)。
顯然,Boussinesq假設是錯誤的,因為分子黏性是“流體”的屬性,而渦黏性取決于“湍流脈動”情況,兩者不可比擬。即便拋開這個原則性錯誤的假設,從式(1)也可以直接導出渦黏性模型固有的本構缺陷或者說“致命弱點”:
1) 各向同性。渦黏性系數的標量特性或各向同性,k是標量。
2) 雷諾應力和平均應變率間的瞬時平衡、雷諾應力與平均場應變率方向相同。
3) 坐標不變性。雷諾應力依賴于應變率張量。
4) 雷諾應力——平均速度應變率之間的線性關系。
上述問題導致了諸多后果,如無法準確預測分離流、角區二次流、旋轉、曲率、高速流動、轉捩、大逆壓梯度流動等。大量的理論分析和數值實驗也表明:一般說來,EVM只有對二維剪切主導、正應力不重要的簡單流動才能給出可靠的結果。
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現這個本構關系的其他一些固有缺陷。這里僅討論一個航空航天領域最常見也是最關心的湍流問題也就是邊界層湍流。由式(1)可知:如果沒有正應變,所有的正應力分量都是相同的2/3k,也就是說對純剪切應變流動(包括邊界層、射流或自由剪切層等),本構關系給出了正應力各向同性的結論。實際上,由于壁面法向湍流脈動的抑制效應等,剪切流中3個方向上的正應力差別很大,也正是這種差別,導致了邊界層湍流的不斷發展和演化,尤其是渦拉伸和各個方向的能量傳遞。
為了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這里講述一個與此相關的、解決航空CFD實際困惑的真實故事,這是作者課題組成員周玲、劉宏康博士完成的一個研究項目。某無人機的CFD計算和試驗結果的比較如圖18所示,0°和10°攻角兩者相差較大,其他情況吻合很好,多次改進計算和試驗,沒有改善,為什么?如前所述,同試驗相比,大攻角時CFD模擬會提前分離,導致失速攻角提前,這個現象已在1.1.1節中作了介紹,這一特性也已廣為人知,因此10°攻角的誤差可以解釋。但小攻角時基本是附著流動,CFD精度理應很好,為什么0°攻角的CFD結果這么差?通過分部件力積分等深入研究發現:0°攻角力矩的非線性主要來垂尾和機身連接處的角區,該區計算結果有逆壓梯度誘導的分離結構:分離區是低壓,導致抬頭力矩。那么,計算和試驗的誤差是由這個分離區造成的嗎?DPW會議有一個重要結論:EVM模型會高估角區分離區大小。
如圖19所示,高估的機理分析如下:角區流有兩個邊界層,各向異性特征強,除沿流向的主流外,一般還有垂直于主流的二次流,這個二次流產生的機理是: 壁法向湍流脈動弱,因此法向和橫向雷諾正應力不同,兩方向雷諾正應力之差產生二次流。二次流將邊界層外的動量等輸運到邊界層內,從而延遲、減小甚至消除角區分離,但EVM假設3個方向的脈動相同即正應力相同,因此無法捕捉角區二次流,導致預測的分離區偏大。
雷諾應力模型(RSM)沒有各向同性假設,可以正確預測出二次流等分離區大小。本算例使用RSM模型后,0°攻角計算同試驗吻合很好。因此,可以推知:0°攻角時,EVM錯誤地模擬出了垂尾和機身連接處的角區分離,分離區是低壓,導致抬頭力矩,而實際沒有這個角區分離。也就是說,由于湍流模型本身的缺陷導致角區分離區大小被高估,較大的角區分離改變了垂尾和機身連接處壓力分布,進而計算出了錯誤的俯仰力矩特性。
那么,為什么其他攻角沒有使用RSM模型,計算結果依然很好呢?這是因為攻角增大后,垂尾和機身連接處的壓力梯度由逆壓梯度變為順壓梯度,順壓梯度不能誘導分離,也就是此時沒有分離,CFD計算結果正確。
需要說明的是,有多種形態和結構的分離流動,其中CFD最難處理的是光滑壁面上的分離,也就是本實例中的分離。
了解航空CFD常用湍流模型的發展過程和性能特點尤其是近些年來的新認識新觀點,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就此進行一些歸納總結。
將湍流模型的發展劃分為3個時期:
1) 基本概念時期。以Boussinesq (1877年) 的渦黏性概念和Reynolds (1895年)的RANS方程為代表。
2) 理論探索時期。其代表是Prandtl(1925年)的混合長概念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一方程模型[53],Kolmogorov (1942年)的k-ω模型[54],周培源(1945年)的k-ε模型[55],Rotta(1951年)的k-l模型[56]。
3) 完備、實用化時期。1968年第一次Stanford湍流會議上,通過對2D邊界層等模型評估后認為:當時所有模型都是“不完備”的,倡導發展完整的模型,促進了此后兩方程模型的爆發和發展,出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實用化的兩方程模型:k-ε模型。1980—1981年第二次Stanford湍流會議評估后認為,湍流模型進步很大,如k-ε、k-ω等完備模型,但結果不是很好。其中代表性湍流模型如下:Jones & Launder、Launder & Spalding的k-ε模型[5,57],Wilcox的k-ω模型[5,58-60],Spalart和Allmaras的SA模型[7],Menter的k-ωSST模型[8,61]。
準確、全面認識湍流模型的性能是研究者和使用者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也是CFD長期以來的研究熱點問題。但是,雖然這方面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直到今天,即便對于最簡單或最常用的湍流模型,也無法給出嚴格、明確的性能結論。當然,經過幾十年的不斷實踐、總結和摸索,對各種湍流模型的性能還是有了一些粗略的認識。這里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給出航空航天領域常用湍流模型的性能、特點:
1) SA模型。這是一個參照盡可能多的試驗結果和經驗積累,通過實用化、啟發式方法建立起來的模型:精心設計、不斷修正、多方標定和優化。其特點是速度快,魯棒性好,通過大量實用化標定,故簡單實用,對中、小逆壓梯度等附著邊界層性能優秀,對小分離等邊界層流動表現良好,一直是航空領域最受歡迎的模型之一。但由于其經驗性、實用化、修補式的構造思路,常被批評不嚴謹、不透明,同傳統模型原則不一致、僅定性成立等。
2)k-ε模型。該模型是第一個實用化的兩方程模型,歷史悠久,后來也發展了很多針對性的變種k-ε模型,以及大量的近壁處理方法等。它曾經是航空CFD使用最廣泛的湍流模型,但由于ε相關物理基礎和實驗數據的嚴重缺乏,ε方程的模化被廣泛批評為大膽無畏、惡作劇、胡鬧、騙人的把戲、超出認知的外科手術……[59]。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k-ω和SSTk-ω異軍突起后,質疑k-ε模型的聲音越來越多,使用者也越來越少,例如:在一些重要的CFD評估中,這個模型甚至沒有出現在候選名單里。目前一般認為這個模型的缺陷較多,主要包括:①ε在壁面無物理邊界條件,壁面ε方程有高級關聯項——導致穩定性、精度、剛性等一些嚴重問題;② 一般近壁的ε值過低,會導致模擬出的分離延遲、分離區短、熱流和表面摩擦系數過高等;③ 近壁需要各種壁阻尼、修正項等[60,62]。
3)k-ω模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發展了很多種k-ω模型,其中航空CFD應用最多的是Wilcox的k-ω模型[60]。越來越多的算例也證明了其優勢,尤其是該模型的2006版性能優越。一般認為這是一個性能出色的全能型RANS湍流模型,近年來的評價越來越高。這主要是因為ω方程模化時的物理機制較明確、量綱分析容易可行,不像ε方程模化時的諸多硬傷。該模型的特點是:① 魯棒性很好,對逆壓梯度、中小分離等性能好、精度高;② 對低Re數流動、轉捩、粗糙壁、高超等流動模擬優勢明顯;③ 不需要或不嚴重依賴阻尼函數,壁修正甚至可以不用壁函數等,這些特點非常有吸引力,也令人驚訝,其原理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缺點是:ω無壁面物理邊界條件,理論上是無窮大,實際處理時一般是給一個充分大的值,但這會帶來近壁網格敏感性問題;近壁漸進特性不正確其結果有歪打正著之嫌;對ω邊值過度敏感,這點已在逐漸改進中,2006版已經基本完善了。
4)k-ωSST模型。剪切應力輸運(Shear-Stress Transport,SST) 模型,是一個性能出色的全能型RANS模型,也是目前廣泛使用的EVM模型中性能評價最好的一個,因此一般推薦為首選,無論是模型研究者還是有經驗的實戰使用者對它都比較推崇。SST的基本原理是:在近壁處采用k-ω模型、在邊界層外區和自由剪切層采用k-ε模型,并通過Bradshaw假設(剪應力正比于湍動能τ=ca1k)引入了雷諾剪切應力輸運的影響。它巧妙結合了k-ε、k-ω和JK模型的優點、規避了它們的缺點。因此,除了具有上述k-ω的穩定性好、精度高等優點外,還可以較好地處理湍流剪切應力在逆壓梯度和分離邊界層內的輸運,故SST模型能更好地預測逆壓梯度和邊界層分離等較復雜的流動情況。SST模型以其精度高、魯棒性好、適用性較廣而成為航空航天領域應用最廣的湍流模型之一。其缺點有:近壁使用k-ω模型,存在上述ω近壁漸近特性等問題;經驗性函數和常數過多、高超聲速特性不如k-ω模型。
近十多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尤其是k-ω類(包括k-ωSST)模型的異軍突起,出現了一些關于k-ε和k-ω模型性能差異及其原理的研究,其主要觀點是湍流尺度和湍流模型閉合不一致等問題,這里簡單討論如下:
1)k-ε模型。k適用于大渦(低波數)、ε適用于小渦(高波數),k基于L尺度、ε基于η尺度,兩者相差很大,相應的它們的時間尺度也顯著不同, 湍流輸運特征也不同。另外,大渦和小渦所在的主要區域不同,湍流特征也不同。因為數學原因,將兩者生硬的耦合,有先天缺陷。
2)k-ω模型:k表示占全部湍能超過80%的較大的渦,而ω表示大渦(以及小渦)的湍能耗散,它們在湍流輸運特性(各種尺度、區域)上是匹配的、一致的。因此,k-ω模型是自洽的。
文獻[63]也證明: 對于逆壓梯度流動,ω是最優選擇,這同Wilcox觀點類似[60]。
湍流模型給使用者帶來的困難不僅是理論上的缺陷,還包括認識上的困惑。這些困惑一方面來自湍流模型本身的種類很多、假設條件和適用范圍復雜、各種經驗性系數繁多等,另一方面來自湍流模型本身性能表現的模糊不清甚至是自相矛盾。關于這些困惑,分類總結如下:
1) 理論上的困惑。 Boussinesq的錯誤假設;本構關系的固有缺陷;方程模化缺乏理論支持;參數標定局限性和經驗性很強、普適性不足等。
2) 認識上的困惑。模型種類很多、假設條件和適用范圍復雜;邊界層湍流近壁處理方法的長期困擾;模型性能的模糊不清甚至是自相矛盾。
3) 表現上的困惑。同一模型在不同算例中表現不一,甚至同一模型在不同軟件上得出的結論也常不一致,包括一些知名軟件[50]。
4) 使用上的困惑。模型中包含很多種經驗性系數、參數、函數等,如何選擇?有些參數的微小改變可能會導致模型性能的顯著改善或惡化。近年來的不確定度量化分析也證實了這一結論。
如前所述:RSM基本方程是由Navier-Stokes方程嚴格推導的完備傳輸方程,在RANS框架下是對湍流最全面的描述,因此是最自然、最符合邏輯的模型,它可以克服EVM模型的一些嚴重缺陷,如各向同性等。雖然很多算例證明了RSM對比EVM的明顯優勢,如分離流、二次流、曲率和旋渦運動等復雜流動的模擬。但令人困惑的是,有一些算例表明,RSM模型并未顯示出對EVM模型的全面優勢。
RSM模型的主要困難包括:
1) 建模問題,尤其是壓力應變項。
2) 數值剛性,這導致其魯棒性較差。
3) 計算量較大。
4) 模型更復雜、更難校準,且缺乏校準所需要的相關理論、數據等資源。
但近些年來,RSM模型在建模和計算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模型精度進步較大,數值方法進步較明顯,計算量已不是大問題,剛性、魯棒性得到一定改善。
一個實例:用近壁二階矩模型計算幾個復雜的渦輪流動,計算時間與k-ε模型相比僅多了30%[64]。
很遺憾,至今愿意使用RSM模型的人仍然很少,原因可能是:普遍對RSM模型的進展認識不夠、了解不多;使用者的習慣或者慣性,不愿意嘗試新的模型;相比EVM,雖然RSM的性能有改善,但并沒有顯示出普遍性、壓倒性的優勢。
為了更直觀地認識湍流模型的在航空CFD領域的表現,尤其是印證上述關于不同湍流模型的性能評估,也為了對比分析EVM和RSM的性能表現,這里給出幾個比較嚴謹的湍流模型性能比較研究實例。
在DPW一節中曾經強調:分離流預測成為DPW的主要困難之一,圖20給出了第二次DPW會議使用的DLR-F6 WBNP模型、ONERA的試驗結果,以及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湍流模型的計算結果[65]。對比分析可見,SA和SST模型等EVM模型預測的分離區太大,顯式代數雷諾應力模型EARSMk-ω則給出了同試驗接近的結果,這顯示了RSM模型的優勢。
文獻[66]使用多個經典標模系統深入地對比研究了4個經典湍流模型:EVM(SA、SST)和RSM(SSG/LRR-ω、JHh-v2)。這些湍流模型是目前CFD界公認的具有代表性的優秀湍流模型。計算結果和分析表明:對于簡單標模,如小壓力梯度平板邊界層等,4個模型計算結果非常一致;但隨著標模復雜程度的增加,一般而言,RSM表現出了更大的適用性和更高的精度,但這種結果的改善常常不是很明顯也不是很普遍。
這里詳細的討論一個計算結果改善較明顯的標模算例:ONERA M6機翼。M6機翼是一個經典的湍流模型驗證標模,一般用來檢驗湍流模型的跨聲速性能尤其是激波誘導分離的模擬能力。使用的CFD軟件是德國DLR TAU,流動參數為:Ma=0.84,Re=11.72×106,α=0.03°~6.06°。
計算結果表明:α=3.06°之前,不同湍流模型的預測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差異,但α=4.08°時,在機翼外側,RSM模型的計算結果同EVM模型的結果差別很大。圖21顯示了機翼外側展向截面站位分別為80%和95%的壓力分布。由圖可見,SA和SST模型的預測與試驗結果差異明顯,但SSG/LRR-ω模型預測的壓力分布與試驗結果非常吻合,JHh-v2 RSM模型預測的激波位置在80%展向截面同試驗更加吻合,但在95%展向截面偏差很大。圖22顯示了機翼上表面的摩擦線,由圖可見,SST模型預測的機翼外半部有很大的分離區,而SSG/LRR-ω模型預測的分離區僅限于激波根部后面的小區域,由壓力分布分析,這個結果與試驗吻合的更好,JHh-v2 模型預測的分離區展向延伸的更小。
在上例計算網格的基礎上,保持網格總量基本不變但重點在激波附近區域加密網格,此時計算表明:4個湍流模型都給出了非常好的結果,見圖23。對比圖21和圖23,網格效應很明顯。顯然,這是一個非常不希望的研究結論[67]:除了SSG/LRR-ω模型外,其他3個模型都顯示出了對網格質量的高度敏感性,只有SSG/LRR-ω模型在兩套網格上都與試驗結果一致吻合,沒有變化。
作為一個與航空應用相關的亞聲速試驗實例,這里用2D水平尾翼研究翼型HGR-01來驗證湍流模型。試驗Ma=0.073,雷諾數為Re=656 500,試驗顯示了既有前緣層流分離又有后緣湍流分離的混合失速特征。攻角增大至大約α=12°后,流動逐漸被后緣分離所支配,這是研究的重點。圖24顯示了數值模擬的升力曲線與試驗數據的比較。所有4個模型都高估了大攻角下的升力系數,且只有JHh-v2 近似達到了升力極值平臺。
顯然,這4個被認為是性能最優秀的EVM和RSM湍流模型,都無法滿足此類飛機設計的要求。
其他較復雜的經典標模的計算結果表明:在翼尖渦旋、彎管流動等算例中,RSM的優勢更明顯,這是因為線性渦黏性模型無法考慮流線曲率等效應。
2.4 CFD計算方法的困境
關于CFD計算格式,文獻 [12]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這里再做簡單的總結和補充。
目前,由于上風格式具有計算精度高、效率高、魯棒性好、自由參數少或無自由參數等優點,在航空航天CFD得到廣泛應用,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絕對主力格式。上風格式中,Roe的FDS格式歷經40年的考驗,在航空CFD中得到了普遍的信任,成為應用更廣的計算格式。相比較HLLC、AUSM系列等其他性能良好的上風格式而言,Roe的主要特點是:對激波和滑移間斷(這是邊界層等黏性作用區域的主要特點之一)都具有優秀的分辨率,在復雜流動情況下表現穩定;它的主要缺點是激波異常問題,這是一個從Roe誕生就一直伴隨它的難題,目前尚無好的解決辦法,一般采用熵修正等方法改善。但熵修正方法很多、性能各異,可以毫不夸張的說,Roe格式的實際性能表現主要取決于各種熵修正的正確使用,這里有很多經驗因素。HLLC、AUSM系列等上風格式也在航空CFD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得到了較好的評價,但在總體性能穩定性、計算精度等方面,同Roe格式相比還有差距。在30多年的實際使用中,作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些較復雜流動的模擬中,Roe格式的性能基本穩定、計算精度高,而HLLC、AUSM系列格式等有時會模擬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流動結構或者不收斂。
關于上風格式的性能認識,可能因人而異、存在爭議。這里,作者講述一個真實的事情:某重大科技工程專項,組織了一個歷時十多年至今仍在進行的CFD精度評估活動,國內先后有10個CFD優勢單位參與了這個項目,作者一直參與其中。這個項目計算過不少于20種復雜的、實際工程中遇到的空氣動力學難題。項目開始時,大家使用的計算格式各式各樣,后來越來越多的使用Roe格式,近幾年,變成了清一色的使用Roe格式、無一例外。因為這個項目經常針對一些未知的、復雜流動模擬及其機理進行深入、細致的剖析、探索,對于CFD格式性能的認識值得大家信賴。
作者認為,“完美”的CFD通量計算格式應該具備這樣的特點:
1) 間斷分辨率高。
2) 黏性分辨率高。
3) 高馬赫數流動模擬時無激波異常現象(如“粉刺”)。
4) 可以在同一流場中,高精度高效率地求解高速激波流動、低速不可壓流動,也就是所謂的全速域格式(避免使用預處理矩陣:依賴人工經驗參數、不適用全速域流動)。
5) 避免“Overheating”現象。
6) 計算過程無需經驗性人工參數的設置。
雖然已經取得很大的進展,CFD計算格式在上述方面仍然有改進的空間。
目前的2階CFD格式主要以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上風格式為核心,當時的CFD主要強調高速時激波的穩定捕捉,對其他因素不太重視,普遍耗散較高且不可控,因此精度和適應性較差,尤其是在低速、小尺度流動結構時,以及高速時激波異常導致氣動熱計算困難等。CFD發展到現在,更加關注復雜流動結構的正確描述和精細刻畫,這些復雜流動結構常常是高低速同在、多尺度共存、互相干擾,如高速流動的分離區、激波/邊界層干擾區域等。因此,發展和研究低耗散格式、激波穩定格式和全速域格式,以應對迎風格式在低速和高速共存時遇到的困難,為精細化湍流模擬、高超聲速氣動熱預測等提供更加優秀可靠的數值求解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針對上述需求,陳樹生等新發展了LD-Roe2格式[68],其基本思想是:在通量求解方面,一般通量格式在低速時精度惡化,采用新型低馬赫數分裂,以提高低速求解精度;在重構方面,常用重構方法在低速時耗散過大,導致慣性子區湍動能精度損失,采用Thornber重構,以提高分離流等分辨率。
這里給出計算實例:串列雙圓柱繞流。來流速度為44 m/s,基于圓柱直徑的雷諾數ReD=1.66×105。本算例著重驗證原始Roe格式和LD-Roe2格式的表現。時間格式為雙時間步LU-SGS;湍流模型為SA-DDES模型。試驗結果取自美國NASA Langley研究中心在QFF(Quiet Flow Facility)靜音風洞獲得的數據。
圖25給出了瞬時展向渦量圖。在低階格式下,Roe格式的計算結果僅捕捉到了大尺度的渦結構,相比之下LD-Roe2格式則解析出大量的小尺度結構,與試驗得到的瞬時渦結構分布接近。顯然,對Roe格式的改進極大提升了渦結構捕捉能力,能夠更好地模擬低速區的分離流動。Q準則描述的瞬態流場結構也反映了這個特點,從圖26中可以看出LD-Roe2格式在剪切層和尾跡區捕捉到大量的小尺度渦結構,這是原始Roe格式在3階精度下無法獲得的。
由圖27可知,LD-Roe2很好預測了前圓柱的壁面壓力脈動,而Roe得到的結果則過大,這是因為Roe格式只能捕捉到大尺度二維渦結構,與單圓柱有相似的特點。展示對稱面后圓柱45°位置監測點壓力系數脈動的功率譜密度如圖28所示。Roe格式和LD-Roe2格式測得的主頻與對應的PSD值均與試驗較為接近,而LD-Roe2格式相比之下稍微準確一些。在高頻區域改進格式有更多的能譜分布,代表小尺度結構的脈動影響。
從ENO格式出現后的近40年來,高階格式一直是CFD計算方法的研究熱點之一。高階CFD方法具有提高預測精度或降低計算成本的潛力,對其優缺點也有了較系統深入的認識[69]。但由于其尚未在航空中得到有效的應用,因此本文不詳細論述這方面的進展。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歐洲倡導的、歷時多年的2個關于高階格式的國際合作項目:面向工業空氣動力學應用的自適應高階變分方法(ADIGMA)[70]和高階方法的工業化(IDIHOM)。ADIGMA項目的一個研究結論是:網格適應和誤差估計是提高高階方法整體效率的關鍵因素,在求解效率、魯棒性、激波捕獲和高Re湍流的計算方面需要取得重大進展。IDIHOM項目歷時4年,參與機構21個,項目的基本結論之一是:其CFD代碼仍然不應該被認為是航空工業常規應用中的通用工具[71]。因此,高階格式的廣泛實際應用仍然需要時日。
但是,目前普遍的共識是:與采用同樣網格分辨率的二階格式相比,無論是對于定常RANS計算還是多尺度求解問題,高階格式的計算精度都會獲得顯著的提升。圖29對比了在有限差分框架下、典型高超聲速飛行器繞流二階格式和五階格式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到二階格式得到的二次渦結構等清晰程度明顯弱于五階格式,二階格式過高的數值耗散抑制了邊界層的不穩定發展,一定程度上抹平了流場中的細節結構或小尺度結構。對于定常氣動力/熱計算,盡管湍流模型的誤差常常對計算結果起主導作用,高階格式也表現出了顯著的優勢。
在時間計算格式方面,因為計算穩定性和計算效率等原因,目前航空CFD主要使用隱式時間格式,如廣泛使用的LU-SGS格式。模擬非定常流動時,一般使用雙時間步迭代法。但是,雙時間步迭代法由于內迭代常常無法在短時間內收斂甚至根本不收斂,一般需要通過設定內迭代步數來限制計算量,這必然引入過大的截斷誤差甚至可能導致非定常流動的模擬失真。另外,由于隱式邊界條件處理非常困難、計算節點間數據交換量大等原因,隱式格式在大規模并行計算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因此,近些年來顯示格式得到了很多的關注和發展,其突出優點是時間精度高、大規模并行計算易行、程序簡單、存儲量較少、不存在隱式邊界條件困難等,錢戰森在此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72]。
3 討論和建議
CFD的誤差主要包括數值誤差和物理建模誤差2大類。隨著計算機能力的不斷提高,數值誤差可能最終在空間和時間上都降低到可控水平[15],另外隨著高階格式在未來可能變得實用,數值誤差將會進一步減小。但降低物理建模誤差,卻與計算能力的提高沒有多少關系。因此,航空CFD必須思考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什么是未來可以依賴的湍流模擬技術?
3.1 什么是未來的湍流模擬
湍流已經困擾人類一個多世紀了。如前所述,CFD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復雜湍流模擬,而且它也是未來最不可控、最不可預見的難題,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十年內,它也不會成為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對傳統湍流模型還是LES,對湍流突破性進展的期望都很低,因此包括分離在內的非設計條件下的流動物理將繼續構成巨大挑戰,層流-湍流轉捩也是如此[18]。
3.1.1 RANS、LES或DNS
在RANS方法之后,在計算機可負擔的條件下,航空CFD最有可能實現的方法是RANS/LES混合方法和LES方法。它們都被寄予很大的希望,普遍認為是未來代替RANS方法的主流方法。
在航空CFD中使用LES方法,理論上最大的困難來自近壁處理方法。因為近壁湍流雷諾數較低,是非充分發展湍流, 很難區分慣性子區和耗散區,其脈動尺度正比于壁面距離, 愈靠近壁面尺度愈小,近壁區亞格子尺度也許包含某些重要的雷諾應力產生機制,因此需要采用解析方法,可是這將導致巨大的網格和計算量要求。
目前,根據近壁處理方法的不同,一般把LES分為2大類:壁解析LES(Wall-Resolved LES,WRLES)和壁模化LES(Wall Modeled LES,WMLES)。對于高Re流動,WRLES需要的網格和計算量同DNS差別不明顯,因此,計算量太大。WMLES本質上是RANS/LES混合方法的一種,是一種需要模化但又不存在普適精確的近壁建模方法,因此是近似的LES方法。
CFD Vision 2030報告認為[13]:RANS/LES和WMLES是預測外部空氣動力學高雷諾數下真實流動的最可行方法。確實,目前RANS/LES混合方法在航空領域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功應用,尤其是對大分離、非定常等復雜湍流的模擬,比RANS方法具有明顯的優勢。如清華大學符松課題組[73]使用混合方法成功模擬了噴流噪聲,以及其他一些非定常分離流動等復雜湍流。那么,RANS/LES混合方法或 WMLES會是明天CFD的主流嗎?
2017年在密歇根安娜堡,NASA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召開了為期3天的湍流建模研討會(Turbulence Modeling Symposium),會議匯集了近90位來自學術界、政府和工業界的專家,討論了湍流建模的現狀、新興的想法,以及圍繞其未來的問題[74]。會議認為:WMLES和混合RANS / LES將會繼續受到關注,但是即使對于至少20年后的常規實際使用而言,這些方法也可能過于昂貴。而且,這些方法也有各自的失敗和爭議。
文獻[44]也認為:盡管RANS/LES混合方法將導致更高水平的湍流物理描述,它們的計算成本仍然比穩態RANS模擬高2~3個數量級。這個代價對于大多數用戶來說過于昂貴。
2021年,MIT和Stanford 大學的Lozano-Durn等用WMLES方法模擬了NASA Juncture Flow模型后認為[75]: WMLES仍遠遠不能提供CBA所需的穩健性和嚴格的準確性,特別是在分離區域和機翼-機身接合處。這再次說明,混合類方法對分離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完善。
確實, RANS/LES混合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應用日益廣泛。但在航空CFD中廣泛使用RANS/LES混合方法可能還需要很長的等待。
關于LES方法,嚴格說是WRLES,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可以用于航空工程的可能性。對于這個觀點可能持有較大的爭議,不妨回顧一下CFD的發展歷史,從中不難發現,人們幾乎都是過于樂觀的預測了未來,例如:如圖30所示,1979年,Chapman[76]曾預測LES將于20世紀90年代應用飛機全機的計算,可事實是這個預言至今也沒有實現,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實現的可能性。
NASA2030分析認為[13]:當時(2014年)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2號,其理論峰值是55 PFLOP/s。在此計算機上,WMLES用約一天的時間可以完成百萬量級Re的流動計算。展望2030年,預期頂級計算機的理論峰值約30 ExaFLOP/s,那時WMLES就可以完成億量級Re的計算,這個Re量級基本就是真實飛行器的Re了。
問題是,即便這一天到來了,用戶真的可以用LES解決航空實際問題嗎?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拷問:用戶有條件使用這樣頂級的超級計算機嗎?一般用戶用得起嗎?實際模擬的計算周期可接受嗎?做得出LES需要的至少數百億的網格嗎?具備LES要求的高技能嗎?
這里給出一個實例:2020年,Terracol和Manoha用WRLES模擬了一個三段翼型[77]:如圖31所示,流動條件Ma= 0.178,Re=1 230 000。計算網格約26億,包括10 688個子塊。使用的是法國CINES的超級計算機,實際使用其4 096個核。計算時間為600萬CPU小時(折合約61天)。如圖32所示,WRLES結果很精細,同相應的PIV以及LDV精細測量結果吻合很好。
這個航空WRLES應用實例僅是一個百萬量級Re、構型簡單的3段翼型,對于三維高Re真實飛行器構型來說,WRLES或者真正LES的計算代價可想而知。
2000年,Spalart[47]曾經做過一個關于CFD的知名預測,如表2所示。事實證明,這個預測過于樂觀。實際上,2016年Spalart對此又做了一個補充說明[18]。

表2 策略總結Table 2 Summary of strategies
1) 關于LES:在2000年預測,LES將在約2045年流行,這是以壁模化和其他一些慷慨的假設為前提的。因此,沒有理由做出任何更樂觀的預測,特別是在這個后摩爾定律時代,RANS建模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高度優先事項。
2) 關于DNS: 2000年,曾大膽地預測這將在2080年左右發生,但現在對21世紀是否會發生這一點沒有信心,甚至對它是否會發生也沒有信心。
NASA預言[15]:如果沒有發展出精確的湍流模型,那么再過幾十年,摩爾定律的進步或者量子計算宣稱的計算模式的轉變,可能導致最終成功計算湍流。
如上所述,DNS的應用有些過于遙遠,不確定因素也過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討論。
3.1.2 湍流模型的發展完善
目前普遍使用的、基于線性渦黏性關系的一方程和兩方程等EVM模型受到了很大的挑戰。那么,很自然,大家都很關心問題是:湍流模型下一步該如何走?
CFD2030 給出了湍流模擬方面的發展規劃[13]:在2020年前應決策是否繼續進行RSM研究,不行就轉向RANS/LES混合方法。但這一觀點受到廣泛的非議,NASA后來也認為需要修正。2019年,在針對NASA2030的研討會上,Bush等[78]認為:CFD2030建議在2020年左右做出放棄RANS研究的決定,這樣的放棄還為時過早。
2010年AIAA下屬的湍流模型基準測試工作小組針對湍流模型的應用和未來發展進行了深刻的討論[79],結論之一是:盡管對于許多工程流動的模擬不盡完美,RANS將在未來20~50年內依舊得到廣泛的使用。
目前,一般的、普遍的觀點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或者說至少在未來的20~50年內,基于湍流模型的RANS仍將是航空航天的主流CFD方法,同時,RANS/LES混合方法將得到一定的發展和應用,未來混合方法也許會逐漸壓縮RANS區域直至使其減小到邊界層最靠近壁面的薄區域。至于LES、DNS走入應用的時機,是一個難以確定的話題。
近20多年來,關于湍流模型的話題很多,爭議也很多,如:湍流模型的精度沒有取得明顯進展;投入減少、研發人員減少、使用者動力不足、現有軟件開發者利益……;質疑湍流模型存在“性能天花板”、已經到了極限……[18,58-59]。
NASA和現已解散的科學與工程計算機應用研究所(ICASE)在2001年舉辦了一個湍流建模研討會,當時與會的湍流模型專家建議:NASA應該支持代數應力模型和雷諾應力模型的長期研究。重點應放在改進長度尺度方程上,因為它是最不容易理解的,而且是兩方程和更高模型的關鍵組成部分。其次,應優先發展改進的近壁模型。DNS和LES將為開發和驗證新的RANS模型提供寶貴的指導。這個建議得到普遍的認可和支持[15,80]。
2017年密歇根Turbulence Modeling Symposium會上[59], 就湍流模型的未來繼續發展問題,與會專家充分討論后,認為近期應該開展2個方面的研究:①不確定度量化(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UQ)分析;② 數據驅動建模(Data-driven Modeling)。
近年來,湍流模型的UQ分析引起了CFD界的高度重視。這是因為由于湍流模型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會對模型的預測精度產生較大影響。所以,對湍流模型進行不確定性分析,量化并降低模型的不確定度,對于提高模型預測精度,改進模型的預測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也因此,UQ成為近年來改進和發展湍流模型的有力手段和新途徑,用來提高模型預測精度、改進模型預測能力。
目前,基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建模方法很流行。湍流建模將涉及數據(校準)、推理(直覺/試驗和錯誤測試)和基本機器學習(用簡單函數進行曲線擬合)。因此,湍流建模可以很自然地利用大型和多樣化的數據集,并采用形式推理和學習方法。利用數據科學來改進湍流建模并不是新的理念。相反,數據驅動建模引入了一組新的工具,允許更形式和全面地使用數據。
在雷諾應力建模方面,歐洲逐漸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尤其是以DLR的TAU軟件為代表的RSM模型在航空中的成功應用[81],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受到CFD界的關注,有理由相信RSM模型具有值得期待的潛力。在此方面,一般認為,主要的機會在于改進長度尺度方程、壓力-應變建模方法、近壁處理技術、壓縮性修正等。
湍流建模的主要困難之一是缺乏輸運方程模化時所必須的理論依據和數據支撐,目前的試驗測試技術無法提供建模要求的細致、精確、可方便分解的湍流數據,如脈動高階關聯關系等。但是,DNS正在逐漸接近這種可能,因為其越來越精確的結果、越來越高的Re等。這方面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
3.2 航空CFD的現狀與發展建議
首先,總結一下航空CFD的現狀[13,15,18]:
CFD在過去40年中對飛行器設計過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同一時期風洞試驗數量的減少。由于預計計算機速度將繼續提高,CFD將繼續蠶食物理試驗的需求,如果在湍流建模等方面的進展能夠有信心地預測湍流等復雜流動物理現象,CFD將最終取代風洞。
對于附著流或分離流最小的巡航狀態(這只是飛行包線的一小部分),CFD將很快能夠取代風洞試驗。對于其他飛行條件,如包括復雜的分離流動,基于當前和預測的計算機在復雜分離湍流方面的不足,仍然需要風洞。事實上,還需要進行額外的風洞試驗,以充分促進發展合適的湍流模型,然后對這些模型建立信心。未來將關閉更多的風洞,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利用率的降低和整體成本/基礎設施驅動因素的組合,而不是由于通過建模和模擬完全消除對風洞的需求。
如前所述,CFD缺乏在合理的時間范圍內產生足夠多數據的計算能力,對分離流相關的復雜湍流缺乏足夠精確的模擬能力。另外,CFD的一個重要缺陷是無法回答誤差或者可信度是多少?因此,與CFD相關的不確定性水平需要被量化并得到認可。這種不確定性將與飛行試驗測量中的固有噪聲進行比較。風洞有其誤差,但它們非常穩定(只有少數相對較新的低溫設施可以達到大型商業運輸機的全尺寸雷諾數)。
不幸的是,正如風洞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種種原因一直在關閉一樣,NASA的3個航空研究中心(Ames、Glenn、Langley)對CFD研究的支持也一直在穩步下降。在20世紀80年代及以前,Langley的許多分支機構都積極地從事CFD研究,但現在這些努力已經減少到一個分支機構的一小部分。Langley成立了ICASE,專注于數值算法和湍流建模,并引進了獨特的、世界級的人才,但ICASE于2003年關閉。NASA迫切需要重振計算科學和工程研究,并向NASA科學家提供最先進的計算機硬件。
其次,規劃一下航空CFD的未來。作者很贊同NASA2030中關于CFD在2030年應具有的能力[13]:
1) 基于物理的預測模型。對轉捩、湍流、分離、化學反應流動、輻射、傳熱等,模型應更多反映物理機理。
2) 誤差及不確定度管理。包括物理模型、網格及離散的缺陷,以及偶然誤差、認知缺乏等。
3) 全分析流程的高度自動化。幾何創建、網格生成及自適應、計算結果處理、海量數據中大量信息的提取和理解。
4) 能夠高效利用大規模并行、異構和容錯的HPC架構。
5) 靈活使用HPC系統。具有工業(大量數據)和科研(深入研究)的雙重能力。
6) 與多學科分析無縫連接。高保真CFD工具、接口、耦合方法等。
當然,航空CFD所面臨的挑戰(如非定常分離、邊界層轉捩)是不能僅依靠更快的計算機來解決的。需要研究發展更精確的數值格式、先進的求解器技術、網格自適應、誤差估計、物理建模,以及有效利用未來大規模并行機器能力的方法。
為此,必須沿著多條路徑爭取進展甚至突破,建議應重點包括如下方面:
1) 大力支持EVM模型和RSM模型的不斷發展、改進、完善和推廣應用,尤其是針對提高大分離模擬能力方面的不懈努力。
2) RANS和LES之間精確可靠的接口方法或模型。
3) 適用面廣、精確魯棒的LES近壁建模方法。
4) 各種轉捩預測方法的發展和應用,尤其是基于轉捩模型的預測方法。
5) 具有優秀的激波和黏性分辨率、無各類異常、無可調參數的全速域通量計算格式。
6) 實用化的高階格式(低耗散/低色散、高魯棒性格式)。
7) 快速、魯棒的求解器技術。
8) 誤差分析及不確定度管理。
9) 實用化的網格自適應技術。
10) 靈活方便、功能強大的多學科耦合能力。
11) 開發充分利用目前高性能計算硬件架構潛力的策略。
12) 精心設計的精細試驗,以幫助發展物理模型和CFD驗證。
4 展 望
過去的40年里,航空CFD從萌芽逐漸成長為今天航空人可以高度信賴的、離不開的支撐,雖然它還有許多的不足,未來它終將成為航空人可以完全依賴的支柱。對未來CFD在航空中越來越多、越來越成功的應用應充滿信心:
1) 航空CFD高可信度區域將從飛行包線的中心逐漸向外擴展直到超越包線的邊界,其可以信賴的應用也將從單一的計算到多學科耦合,從被動仿真到開拓設計。CFD將使飛行器研制的周期更短、代價更低、性能更好、風險更低。
2) 基于CFD和最優化理論相結合的氣動最優化設計、CFD/運動/控制等多學科耦合的虛擬飛行,將是航空CFD在可預見未來成就空間最大的2個應用方向,前者將代替工程師實現數字化、自動化、最優化的飛行器設計,后者將代替試飛員成為可以突破各種極限、無畏任何風險、評估更為客觀全面且精確系統的數字化試飛員。目前,這2個方向尚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嘗試應用的初期階段。
3) 未來,航空CFD有望從一個被動的模擬手段、逐漸轉變為一個主動的探索工具,甚至成為一個完整的飛行物理生產方法。也就是說,它不僅能提高傳統飛行器的性能,還能從流動模擬擴展到概念探索、將新的思維引入空中,比如,設計出具有可接受的燃燒和音爆性能的超聲速運輸機[18,35]。
4) 就像DLR的Digital-X項目所期待的那樣,未來CFD同其他多學科的耦合可以進行飛行器的虛擬設計和虛擬飛行試驗,實現飛行器在計算機上首飛的愿望。也許未來的某一天,只要在計算機上輸入期望的飛行器性能,通過基于CFD/結構/控制/運動/動力等耦合的多學科優化設計和虛擬飛行,一杯熱咖啡之后,就可以坐在虛擬機上親身感受新飛行器的方方面面了。
致 謝
感謝我的學生白睿潔、王英審閱了初稿,提出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感謝劉再接、路嘉晨幫助排版和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