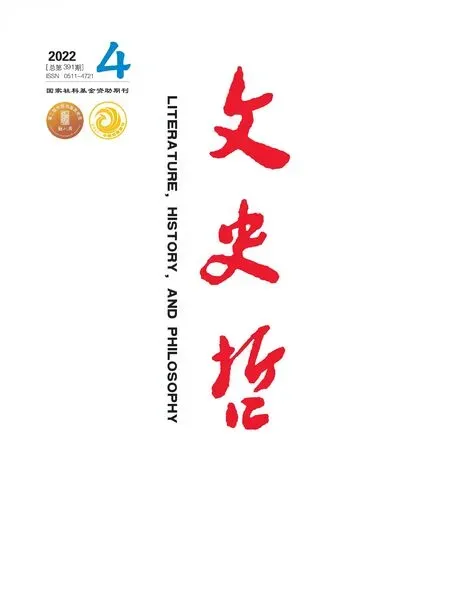如何生活:一個廣義的哲學問題
楊國榮
羅蒂曾認為,西方哲學最初是從追問“好的生活是什么”這一問題發端的,威廉姆斯則把蘇格拉底所理解的倫理問題概括為“人應該如何生活(how should one live)”,兩者都涉及人的生活。從本源的層面看,人之“在”與人的生活無法相分,這里的“生活”不限于蘇格拉底所理解的倫理之域,而是具有更廣的哲學內涵,需要從形而上等層面加以考察,“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也相應地包含多重意義。
一、人的生活與人的存在
以人的存在為關注之點,生活涵蓋不同的方面,既關乎人的存在狀況,也涉及人的存在方式。這一論域中的生活不同于生存:生存主要表現為活著,生活則不僅以活著為前提,而且包含更廣層面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創造。動物只有生存,沒有前述意義上的生活;唯有人,才擁有多樣的生活,并且能夠追求更好的生活。日常生活可以視為生活的基本形式,在外在的方面,日常生活主要表現為日用常行,從飲食起居,到灑掃應對,日常生活呈現不同的形態;就內在或實質的方面而言,日常生活則以人自身的生產或再生產為內容,后者的實際指向是個體生命的維系和前后延續。作為個體生命維系和延續的形式,日用常行首先展開于家庭之域,無論是農耕時期的擔水砍柴,還是不同歷史時代家庭成員的衣食住行,都構成了基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之具體內容。家庭成員之間多樣的相處和交往形式,往往表征著人的存在的不同形態: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作為權威主義背景中的存在方式,主要體現了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品格;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彼此尊重、相互關切,則具有更廣的歷史涵蓋性,其中彰顯了人類由“野”而“文”的歷史衍化,展示了人區別于其他存在的文明特征;二者既有歷史重合的一面(體現了社會的演進),又彰顯了人之“在”的多方面性(包括文明形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與日用常行相關的,是廣義的生活世界。除了家庭生活,生活世界還涉及人的存在的其他維度。儒家曾提及“里仁為美”“朋友有信”,其中便關乎生活世界的多樣關系。“里仁”已超乎家庭的生活空間,指向寬泛意義上鄰里之間的相處,朋友則關涉更廣領域的人際交往,作為廣義“公共空間”的存在方式,兩者不僅與前現代的人類狀況相關,而且構成了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以日用常行為內容,公共空間中的以上交往呈現多維的形態:它可以表現為守望相助的實際作為或踐行,也可以取得對話、交流等語言溝通的形式。日常生活的這一方面不僅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而且有助于形成和諧的社會形態。相對于生命維系或延續的自然之維,生活世界的以上內容更多地展現了存在的文化意義。
從社會文化的層面看,人的生活體現于更廣的領域。事實上,生活世界本身涉及多重方面,并與社會生活的相關領域彼此互動。這里可以簡略考察近代以來歐洲(首先是英國)糖類的日常消費以及其中關涉的歷史變遷。以生活取向而言,人每每具有愛好甜味的特點,在歐洲,蔗糖的消費是滿足這種需要的重要方式。當然,最初糖被視為上等之品,只有貴族能夠享用。隨著社會等級關系的變遷,平民和勞動階層中也開始獲得消費糖類的權利,蔗糖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尋常之物,這里同時蘊含著生活方式的某種變化。消費蔗糖的生活過程,也在更廣的層面影響了社會生活。英國人在1650年之前,主要通過攝入碳水化合物(淀粉)來果腹,其獲得營養和能量的方式,也與之關聯。相形之下,蔗糖是更為高效的熱量來源。17世紀以后,在蔗糖從奢侈品成為必需品的轉換中,蔗糖為英國人的日常飲食里提供了相當數量的熱量,其消費量也不斷增長,從1650年到1800年的150年間,英國人的蔗糖消費增加了25倍。這種生活方式不僅改變了英國人食物的構成,而且節省了家庭主婦下廚房烹調食物的時間,使之可以參與其他形式的勞動或生產活動。同時,蔗糖消費的增加,既推動了殖民地的規模化生產活動(包括甘蔗、甜菜的種植和開辦企業),并使這種活動本身成為掠奪殖民地人民財富的重要手段,也使歐洲本土的機器制造、船舶工業等發展獲得了動力,而蔗糖從南美等地向歐洲的運輸,則推進了航海運輸的繁榮。以上事實表明:生活方式不僅以自身變化為內容,而且往往廣泛地制約著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
不難注意到,生活世界并不囿于日用常行,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費、朋友交往之外,人所從事的多樣活動,也屬于廣義的生活過程。生命的維系和延續離不開生活資源,后者的獲得則基于人的勞作;同時,人的存在也并非限于休閑消費,而是以勞動和工作為其重要內容。廣而言之,人的日常生活既涉及狹義的生產勞動,也關乎各種形式的文化創造,從社會治理、政治運作,到科學研究、藝術創作,與人的存在相關的生活,展開于多重方面。概要來說,人的生活不僅與自然層面的生命活動相關,而且體現于文化之域的諸種活動,后者既賦予生活以多樣的內涵,也使之獲得了更為深沉的意義。
綜合而論,人的生活既有日常的形式,又不限于日常存在。作為生命維系與延續的日常生活每每呈現自在和非反思的形態,其中的活動一般發生于已然之境,具有依循往復的趨向。相對而言,社會文化層面的生活形態,則更多地包含自覺的創造性內容。“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中的“生活”不僅具有本源性,而且關乎更為內在的存在形態;與之相關,以上追問的意義顯然不限于日用常行,而是同時以人的自覺活動及其創造內容為指向。以日常生活之中與日常生活之外的活動為相異形態,生活既涵蓋了人之“在”的各個方面,又賦予這種存在以自發(非反思)和自覺的不同向度。
寬泛地看,人的存在形成何種方式、人的生活取得怎樣的形態,涉及多重方面。首先需要關注的是歷史制約。人的生活過程并非抽象空乏,相反,作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其內容豐富而多樣,后者與歷史衍化的不同形態息息相關。前述與糖的消費相關的生活方式,便基于歐洲近代以來的社會結構的衍化,包括貴族與平民關系的變遷。生活樣式植根于歷史的發展這一事實,決定了人如何生活無法由個體隨意決定。當歷史還處于農耕之世時,信息時代的生活方式顯然難以呈現;在權威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候,民主社會中的生活和交往形式,也缺乏可行性。前者展現了人“如何生活”與科技、經濟的發展之間的關聯,后者則折射了政治結構、價值觀念的演化對人“如何生活”的影響,兩者從不同方面表現了歷史衍化過程對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的制約。在日常生活之域,也可以注意到歷史的變遷與交往過程的相關性。以家庭關系而言,在父為子綱的背景之下,子對父的無條件順從,構成了親子關系的主導方面,即使父已逝,子也常被要求“無改于父之道”。在近代以來的社會人倫關系中,父子之間則不再以單向服從為交往原則,而更多地側重于相互尊重、彼此關切。這種歷史變遷同樣體現于日常生活之外的領域。從政治實踐的過程看,在君權至上的條件下,臣民對君主的效忠,構成了君臣之間交往的基本形式,然而,以民主為政治結構的基本形態,人與人(包括領導人物與一般民眾)之間,更多地呈現平等的關系而非等級差序。可以看到,無論是生活世界中的彼此相處,抑或政治領域中的相互交往,都涉及如何生活的問題,而其具體方式,則與歷史的衍化過程無法分離。
與歷史制約相輔相成的,是個體的選擇。生活的承擔者總是一個一個的個體,人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存在歸根到底也與個體相關。個體存在于世,常常面臨多重生活方式,如何生活、怎樣在世,不僅以歷史的衍化為背景,而且離不開個體自身的權衡和抉擇。從社會的層面看,既需要對個體做必要的引導,又應尊重和維護個體選擇的權利,而非代個體“作主”或強制個體作某種選擇。個體的生活固然包含普遍、必然的一面,但也呈現多樣性并受到運氣的制約,荀子所說的節遇、王充所注重的遭命,都與運氣相關。生活中的這種運氣,主要表現為偶然性,后者展開于日用常行的各個方面,同時也為個體的選擇提供了多重可能:如果生活中沒有偶然的變動,一切都被預定或命定,則個體的自主選擇便失去了前提。寬泛而言,人的生活過程既涉及人與物的互動,也關乎人與人的交往。從人與物的互動看,在自然經濟的背景下,個體與類可以在既成的生活環境中主要依據已有的自然資源而生存,基于采集和狩獵的存在方式便體現了這一點;也可以從“制天命而用之”的觀念出發,不斷化“天之天”為“人之天”,使本然的對象合乎人的不同需要,農耕和游牧的存在方式即與之相關。步入近代以后,在天與人、人與物的關系方面,個體與人類群體有了更廣的選擇空間,隨著技術的發展,人作用于自然的方式也愈來愈多樣。就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言,從傳統社會中的克己復禮、仁以待人,到近代以來維護權利、尊重契約,個體之間的交往取得了相異的形式。以成就自己和成就世界為指向,個體對價值目標的選擇與如何生活緊密相關,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則具體地落實于成己與成物的過程。事實上,如果離開了成就自我與成就世界的實踐活動,“應該如何生活”這一追問便失去了其實際的價值意義。
個體應該如何生活,同時關乎內在的情感世界。從社會的層面看,個體的生活首先源于親子之間,后者既涉及生,也指向死。按先秦的禮制,父母去世后應實行三年之喪,孔子曾就三年之喪與門人宰予展開了一場對話,宰予以為守喪三年時間太久,并對此提出質疑。孔子則反詰:不行三年之喪,“于女(汝)安乎?”(《論語·陽貨》)這里的“安”即心安,它所關涉的是內在情感,孔子的反詰主要由宰予缺乏本應具有的哀思之情而發,其中既滲入了子(子女)對親(父母)從生到死都應事之以禮這一價值要求,也肯定了如何生活(如何交往)的過程中蘊含著內在的情感規定。歷史地看,仁人志士在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上,往往涉及生與死的抉擇,提出“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的蘇格拉底,最終選擇飲鴆而亡,便體現了這一點。從如何生活的角度看,生與死的抉擇無疑具有嚴峻性,在這一方面,歷史上既可以看到慷慨赴死的悲壯情懷,也不難注意到從容就義的浩然之氣。就如何生活或如何存在的情感之維而言,如果說,慷慨赴死主要彰顯了歷史曲折演進的沉重性并展示了個體選擇的凜然之志,那么,從容就義則更多地隱含了對未來的樂觀信念以及個體的理想情懷: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便體現了這一點。
可以看到,就個體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而言,一方面,個體生活有其獨特的一面,從外在的行為方式到內在的情感世界,這種獨特性具有多樣形態,需要加以尊重;另一方面,個體又并非游離于群體,其生活總是受到社會的多方面影響,無論是行為的規范,還是健全情感趨向的培養,多離不開社會的引導。質言之,個體的生活展開于社會群體之中,社會生活則體現于多樣的個體活動,兩者呈現相互作用的形態。
與“如何生活”相關的是“何為好的生活”,前述羅蒂對西方哲學的回溯,便涉及后一問題。對“好的生活”的向往,具有普遍性,即使是似乎向往彼岸世界(the other world)的宗教,也在實質上體現了對此岸世界(this world)中更好生活的追求。就“好的生活”的確認而言,其中的“好”既關乎現實準則,也涉及一般的價值內涵,前者引向實際境域,后者與主體的判斷以及主體的感受相關。對什么是“好”的理解,在個體之間無疑存在差異,但不能由此引向“怎么都行”的相對主義,也不應將關于這一問題的見解都視為強加于人的獨斷看法。事實上,在這方面,盡管觀點可能不盡相同,但人與人之間依然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從終極的層面看,可以從“合乎人性”這一角度理解“好”:好的生活,也就是合乎人性的生活。合乎人性與合乎仁道和自由具有一致性:真正意義上的合乎人性,最終體現于仁道的原則與自由的走向,后者的具體內涵,表現為對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的肯定和以自由為指向的價值理想的確認,兩者構成了人區別于其他存在的根本規定。仁道原則表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自由的走向則是判斷歷史發展的基本準則。歷史地看,人類的衍化,以自由之境的深化和擴展為現實的內容,這一趨向的最終旨趣,在于達到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里同時需要肯定好的生活的形態與生活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選擇之間的統一。對何為好的生活的判定,與確認生活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并非截然對立。一方面,需要確認正當、健全的價值取向,培養價值創造的多方面能力,使人能夠在合法則與合目的統一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選擇和踐行,另一方面,如后文將更深入討論的,應當承認不僅好的物質生活形態可以有多樣形態,而且精神層面的合理追求也可以取得不同的實現方式。合乎人性的生活,本質上具有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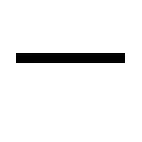
要而言之,“好的生活”一方面允許個人的參與,并蘊含著多樣趨向:如果生活變得千篇一律,便會顯得十分乏味;另一方面,具有正面價值意義的這種生活又有相通的方面,后者體現于后文將具體論述的至善或生活的完整性。“如何生活”也與之類似,一方面,如上文所論及的,生活的主體乃是一個一個的個體,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也是由不同的個體自身所決定;另一方面,這種生活方式并沒有離開廣義上的社會制約(包括前述歷史制約)。從個體性與社會性、歷史性與階段性的互動來說,“如何生活”和“何為好的生活”之間既相互關聯,又彼此互動。
二、生活的兩重形態及其意義
“人應該如何生活”與“何為好的生活”,都以人的生活為指向。如果對生活本身做進一步的考察,則如上文已論及的,其中既涉及物質的層面,也包含精神之維,可以說,人的生活呈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重規定,兩者關乎生活的不同意義。亞里士多德曾將人的生活主要區分為三種類型,即享受的生活(the life of enjoyment),政治生活(the politic life),沉思的生活( the contemplative life),其中,第一種主要與物質生活相關,第三種涉及精神生活,第二種(政治生活)則既有物質之維,也包含精神的方面,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分屬以上兩種生活形態。馬克思在談到人類生活時,也區分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并肯定了兩者在人的存在過程中的獨特地位。當然,在兩者之間,馬克思還論及“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不過,寬泛而言,“政治生活”既如前述,兼涉物質與精神,又可歸屬于“社會生活”;同樣,“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構成了廣義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面。盡管對社會生活的具體分析可以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活動的其他領域,但從比較實質的層面看,這些不同領域的社會活動,都不僅包括物質的層面,而且涉及精神之維,就此而言,“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無疑可以視為人類生活的一般表征。需要指出的是,無論“物質生活”,抑或“精神生活”,都不同于僅僅以生存或活著為內容的自然形態,如后文將進一步闡釋的,兩者雖與個體相關但又有別于單純的個體性活動,從這方面看,似乎也可以將其視為廣義的社會生活。
生活的承擔者,首先是具有感性生命的主體,與之相關的個體生命維系和延續,離不開物質層面的生活過程。感性意義上的生命,構成了人的基本存在價值之一,人的現實性和具體性,無法略去這一規定。告子認為“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固然過于強化了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屬性,但就其注意到感性的生命是人之為人不可或缺的方面而言,顯然不無所見。承認人的感性生命,是考察人如何生活的出發點。注重感性層面的生命存在及其發展,則構成了好的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離開了感性的生命存在,如何生活便失去了基本的依托,同時,對人來說,豐衣足食的存在形態,總是比饑寒交迫的境遇更實際地體現生命存在的價值以及生活的意義。從這方面看,人的生存權利在人的生活過程中無疑具有優先性:如果生存權利得不到保障,則如何生活便無從談起。
生活的承擔者同時又是精神生命的主體:人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對象,而且還是具有多重精神規定的存在,這種規定構成了精神生命的具體內容。與之相應,應該如何生活與何為好的生活的追問同時關乎精神生命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充實。寬泛意義上的精神生活涉及意識或心理的不同領域,包括理性、情感、意志、想象、直覺等多重層面的活動,其中既有喜、怒、哀、樂等情緒變動,也內含條分縷析的邏輯之思;既交織著個體在心理層面的權衡和抉擇,也指向自我意識的反省與體驗。從價值的維度看,精神生活則與真、善、美的追求以及人的文化創造活動相聯系,并體現于相關過程。人作為現實的存在,包含物質與精神多方面的需要,物質需要的滿足和感性境域的改善,固然為好的生活提供了必要前提,但認知的擴展、趣味的提升、仁善的向往、終極的關切等精神層面的取向和活動,同樣也構成了生活的重要內容,應該如何生活,同時指向以上方面。進一步看,精神層面的存在還涉及德性的培養、品格的形成,其中關乎不同層面的境界。綜合而言,認知的擴展、審美趣味的提升、仁道的關切、精神慰藉和依托的尋求與品格和德性的完善,等等,構成了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相關規定,好的生活既受到精神世界的制約,也以精神世界領域的多樣追求以及與之相關的精神活動為其內容。
從歷史的層面看,倫理學領域曾形成了多樣的流派,諸如后果論、德性論、道義論等等,這些不同學派一方面都在某種意義上關注應該如何生活與何為好的生活等問題,另一方面又分別側重于生活的相異維度。后果論(包括其中的功利主義)注重行為的結果,并以是不是產生有益的行為結果,作為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道德性質的根據。有益的行為結果,首先與感性的物質形態相聯系:好的結果,常常在于能夠從物質層面滿足人的需要。盡管功利主義并非完全不談精神需要,但其所追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在實質的層面又以物質需要的滿足為首要或優先的關切之點。從這一角度看,后果論的關注重心似乎在于生活的物質之維:對后果論而言,好的生活主要便以好的物質生活為具體形態。比較而言,德性論與道義論的價值取向與后果論有所不同。就理論旨趣而言,德性論與道義論對倫理生活無疑存在相異的理解:德性論注重成就人格,并試圖以人格的完美擔保行為的道德性質;道義論則關切成就行為,要求通過普遍道德原則的規范和引導,使行為合乎道德準則。然而,兩者又存在共同之點或相通的價值觀念,后者主要體現在對精神生活的關注。德性理論,包括對美德即知識的肯定,意味著確認存在好的品格以及與之相一致的好的生活,這里所謂“好的生活”,主要便指好的精神生活。對德性倫理而言,德性的意義首先在于通過人格境界的提升,使人在精神層面追求并走向更好的生活。同樣,道義論注重道德法則或準則的普遍規范意義,以合乎普遍規范為判斷行為具有正當性的依據,將行為結果的考慮完全置于倫理領域之外,其實質的價值指向,也是人在精神生活層面的完美:基于道德法則的行為,不以促進人的物質生活境域為目標,而以行為本身在精神上趨于崇高之境為旨趣。
前文已論及,按威廉姆斯對蘇格拉底問題的概括,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首先與倫理學相聯系。就倫理學而言,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仁愛為形態的行為和側重于克己的道德踐行。基于仁愛的道德行為主要以關懷、行善為取向,相對于此,克己之行首先表現為自我限定,在涉及重大或劇烈的利害沖突背景下,它意味著舍己或自我犧牲。不過,盡管在表現形態上有所不同,但作為道德行為,兩者的共同特點在于“給予”或“付出”,后者有別于“獲得”:仁愛以關懷他人的方式“給予”他人以幫助,克己則以自我抑制的方式為他人或社會“付出”自身。正是這種“給予”或“付出”,賦予以上行為以道德的性質:按其實質,道德行為不同于其他活動(如功利活動)的主要之點,即在于不求利益的獲得,只重身心的付出。
從以上方面考察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便不難注意到,人的生活的兩個方面,即物質層面的生活和精神層面的生活,具有不同的價值意義。內格爾在談到功利主義時,曾認為:“功利主義是一種關于何謂正當地活著的理論。”如前面所述,功利主義主要關注物質層面好的生活,這種生活在如何達到(以什么方式實現生活目標)等方面,也有正當與否的問題。廣而言之,盡管關切人的物質境遇、以仁愛或克己的方式讓人過上好的物質生活具有道德意義,但物質生活本身主要與人的感性生命相關,并以滿足人在物質層面的需要為指向,后者很難歸入道德之域,事實上,飲食起居、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方式固然可以呈現貧富之分,但并沒有善惡之別:盡管生活資源的獲取手段和形式,包括對待自然的取向(尊重自然或單向掠奪),也存在是否正當的問題,但衣食住行作為物質生活的特定內容,本身卻無法以道德原則加以評判;以飲食而言,以粗茶淡飯還是粱肉之類果腹,確實表現了生活狀況的差異,不過,兩者與道德上的高下并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與之相對,精神層面的生活,則具有不同的道德意義。寬泛意義上的觀念定勢、品格內涵關乎人在精神領域的生活取向,其中包含對錯與否的分別;行為的根據和理由既涉及普遍的法則,也指向人的內在動機,與之相涉的活動同樣構成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并體現了精神境界的不同層次,如此等等。精神生活的以上方面,展現了多樣的價值內涵與道德性質。人總是追求好的生活,其中既內含好的物質生活,也關乎好的精神生活,包括品格與德性的完善;前者不涉及道德層面的對錯、善惡,后者則關乎道德領域的正當與否等問題。從以上角度看,后果論(包括功利主義)主要以好的物質生活為關注之點,其理論顯然無法納入嚴格意義上的道德領域。這里需要區分非道德(nonmoral)與不道德(immoral),非道德意味著不屬于道德之域,無關道德上的善惡,不道德則表現為與完善的道德品格相對立或不合乎道德規范和道德準則,并相應地呈現道德意義的負面性質(惡)。后果論(功利主義)不能視為不道德,但在一定意義上可歸之于非道德,康德在倫理學上拒斥功利主義,似乎亦有見于此。比較而言,德性論、道義論以精神層面的品格提升和合乎普遍道德法則為指向,并懸置特定的行為結果,這一進路既體現了對精神生活的注重,也突顯了其中的道德意義。
盡管威廉姆斯將蘇格拉底所理解的倫理問題概括為人應該如何生活,但他自身則認為,人的生活并不限于倫理之域,與之相應,人應該怎樣生活也不僅僅意味著人應當怎樣道德地生活。這一看法注意到人的生活與道德的生活不能簡單等同,然而,廣義的生活無疑包含了道德生活,也就是說,盡管人的生活不能與道德生活等量齊觀,但道德生活應包含在人的生活之中,當內格爾肯定“道德的生活至少是善的生活的一部分”時,也多少有見于此:這里所說的“善的生活”,也就是寬泛意義上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與之相近,對儒家而言,好的生活便是合乎仁與義的生活:“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粗食淡飯,主要涉及物質生活,“義”則與道德領域的當然之則相關(《中庸》“義者,宜也”),從如何生活的角度看,物質生活(首先是物質境遇)并非儒家追求的目標,是否合乎道德規范(“義”)則構成了其首先關切的問題。引申而言,“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如前所述,“克己”屬道德行為的形態之一,在儒家看來,如果每一個體都能以“克己”的方式生活,則天下便可普遍地形成合乎仁道的存在形態。在這里,生活的道德之維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這種生活形態不同于追求物質境遇的活動,而是體現了生活的精神之維。
物質生活層面的“好”,常常與幸福相聯系。就其本來形態而言,幸福既涉及物質境遇,也與人的感受(所謂幸福感)相關,幸福的感受(幸福感)固然關涉精神層面的取向和精神的追求,從而,其內容也包含價值旨趣和道德意義上的境界,但物質境遇層面的幸福,則主要關乎物質生活,并不直接涉及道德的問題。康德認為:“自身幸福的原則將道德建立于激勵(incentive)之上,這是損害道德而非建構道德,它完全破壞了道德的崇高性。”這一看法注意到了幸福與道德的差異,其中強調的是僅僅關注自我物質境遇意義上的幸福,往往將遠離道德。以上觀點也有見于物質生活(包括物質境遇層面的幸福)與道德的不同,它與康德否定主要關注行為結果的功利主義,在理論上具有一致性。當然,康德將道德與幸福視為不相容的兩個方面,似乎忽視了幸福并不單純地限于物質境遇,而是同時包含精神層面的幸福感,后者同樣可以具有道德的性質;當亞里士多德肯定幸福包含“靈魂的德性活動”時,便肯定了這一點。邏輯地看,康德的以上觀點與后文將論及的德福統一的至善追求之間,也存在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問題。
作為人的生活的兩重向度,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構成了好的生活的相關方面,后者(好的生活)的實現,則需要不同的條件,前文所論及的歷史制約,已涉及這一方面。更具體地看,這里首先關乎外在前提:無論是物質生活,抑或精神生活,其展開都需要現實條件,這種條件既涉及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積累,也與政治體制的完善、社會秩序(包括公正的社會分配形態)的合理建構相聯系。相關條件和前提的形成,當然將展開為一個過程,其具體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取得相異的形態,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缺乏以上方面,則所謂“好的生活”將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洞和抽象。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內在前提,這一層面主要關乎個體自身能力、品格的提升。亞里士多德曾認為,好的東西可以區分為三類,即外部事物(the external goods),以及分別與靈魂或身體相關的其他規定(others as relating to soul or to body),如果說,前者(外部事物)屬外在條件,那么,后者(與靈魂或身體相關的規定)則可以視為內在條件。從后一方面看,好的生活與個體自身的努力顯然無法相分,這種努力本身又基于個體身、心等方面的內在品格和能力的發展。廣而言之,生活的物質之維與精神趨向本身并非彼此懸隔,好的生活的現實前提與內在條件的互動,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這一點。如后文將進一步論及的,盡管物質生活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道德意義,但卻受到與道德實踐相關的精神生活的影響并作為外部條件制約精神生活的變遷;同樣,精神生活對物質生活也具有類似的作用。
三、生活的完整與人的完整:走向至善
以上考察表明,人的生活既有物質之維,也關乎精神的面向,好的生活不僅指向物質或感性需要的滿足,而且以精神層面的提升為旨趣;考察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則需要同時關注以上兩個方面。
人的生活與人的存在無法相分,生活的多重性,源于存在本身的多方面性,人的存在既以感性生命以及與之相關的不同規定為形態,也包含精神層面的多重品格和多樣追求。前文提及,倫理學上的后果論(包括功利主義)以行為的實際結果為關注之點,其中所側重的首先是人在感性生命層面的規定性(包括物質需要的滿足)。先秦具有功利主義趨向的哲學家墨子便認為,“功,利民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此所謂“功”,即行為的結果,“喜”“惡”,表現為感性的情感,“福祿”“禍祟”則關乎實際的物質境遇。對墨子而言,行為的結果最終需要體現于“福祿”這一類物質境域,墨子之主張“節用”“節葬”“非樂”,也基于與之類似的考慮。盡管墨子亦關注“義”,但在他那里,“義”的實際內涵又與物質的境域難以相分:“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墨子·天志上》)這里的“生死”“貧富”,關乎人的感性生命與物質存在狀況,以此為指向,人的生活主要便以物質之維的追求為內容,與之相關的人,本身也更多地呈現為感性的存在。
相對于后果論,道義論與德性論首先以人的精神生活為關注之點。如前文所論,盡管在突出普遍的理性規范和側重于人的內在德性方面,道義論與德性論呈現不同趨向,但在超越物質層面的行為結果而指向精神層面的規定這一點上,兩者又有相通之處。與后者相聯系,在道義論與德性論那里,人的感性之維逐漸趨于邊緣化,從理學的理論旨趣中,便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作為儒學在宋明時期的衍化形態,理學既具有道義論的取向,又內含德性論的觀念:就其強調天理對人欲的制約而言,其理論近于道義論;從它主張成就醇儒或“尊德性”這一方面看,又表現出認同德性論的趨向。然而,在以天理拒斥人欲、以道心消解人心等要求中,人的理性精神似乎被置于至上的地位,感性的生命存在以及與之相關的物質生活,則多少被忽略或漠視:對理學來說,相對于精神境界的提升,物質境遇的改善似乎顯得無足輕重。在物質生活層面的規定被凈化或剔除后,人或多或少呈現為普遍之理的化身。
不難注意到,后果論主要承諾人的感性存在,道義論和德性論則或者將人理解為規范的服從者,或者更多地指向人的精神品格。在以上理解中,人都呈現為單向度或片面的形態。與之相對,在談到人的存在時,諾齊克曾指出:應當關注“我們存在的完整性”(the whole of our being),其人生哲學的討論,也以人的“完整存在”(whole being)為對象。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存在的完整性”或“完整存在”這一觀念。以現實的人為指向,“存在的完整性”或“完整存在”既蘊含克服人的片面性這一要求,也意味著避免在理解人的生活過程時偏向一端。一方面,人的完整存在不同于感性存在,與“完整存在”相應的“好的生活”,也有別于僅僅以感性層面物欲的滿足為準則:單純地限定于此,往往容易引發物對人的支配,甚而導向人的物化和異化。另一方面,精神層面的人格并非人的全部存在規定,完整的人生不能等同于精神之域的道德人生,如果無視人的物質生活,僅僅強調精神意義或追求所謂醇儒,往往將引向偽道學或禁欲主義。
在人的完整與生活的完整這一層面,問題同時涉及自我與群體或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前文已提及,生活的主體首先是自我或個體,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需要滿足,抑或精神層面的境界追求,都以個體為承擔者。但在現實的存在過程中,個體又非離群索居、孤懸于群體之外,事實上,從物質生活資源的獲取,到精神領域的互動、交往,個體與社會共同體都無法各自相分。就此而言,人的生活又如上文所言,具有社會性。與之相聯系,一方面,個體不僅需要融入群體,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合乎社會要求并為社會所接納,而且應成為共同體中自覺履行不同義務并承擔多樣責任的成員;另一方面,社會共同體又需要通過日常禮俗、公正的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形式,為個體生活的合理展開提供社會保障。以上兩者的統一,既從一個方面確證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又構成了好的生活展開的價值背景。當然,這種統一難以一勞永逸地完成于人的某一發展階段,其實現本質上展開為一個過程,后者從另一方面賦予存在的完整和生活的完整以歷史的品格。
要而言之,以現實存在為視域,人本質上應當是完整的對象,人的生活也同樣以完整性為其題中之義。好的生活既有物質之維,也包含精神的內涵,從而,既不能將人片面地限定于物質的形態,也不宜把人單向地精神化。完整的人與完整的生活呈現一致性,其中,物質的規定與精神之維構成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物質需要的合理滿足,是人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的提升,則體現了人生另一無法忽略的規定,對應該如何生活的追問,無法回避以上兩者。作為人的存在的相關方面,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在展現人的完整性的同時,也使好的生活獲得了形而上的深沉內涵。
康德曾提出并討論了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問題,并以德福統一為其內容:“德性與幸福一起在個人之中構成了對至善的擁有。”這一論域中的至善可以加以引申和擴展,并賦予更廣的含義,在引申和轉換之后,至善的內容可以超越單純的道德之善而包含更為深沉的價值內涵,這一意義上的至善與人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完整性也可以形成更為實質的關聯:作為人的內在品格的體現,“德”首先與人的精神形態相聯系,“福”則更多地關乎人的物質生活,兩者的統一既與完整的人相應,也體現了生活的完整性。以上視域中的完整存在和完整生活,同時指向人的存在過程的正當性與人生的健全性,正是后者,使之具有廣義的至善性質。
以人的存在與生活的完整性為具體內容,至善既不同于既定或現成的存在形態,也難以完成于人生的某一終點,其實現本質上具有歷史性和過程性。從這一角度看,康德的相關見解顯然無法加以認同。對康德而言,“只有假定靈魂不滅,至善在實踐上才是可能”。“靈魂不滅”意味著精神的永恒,它與上帝存在的理念相互關聯,并由此在形而上的層面預設了現實生命終結之后的來世。以靈魂不滅與上帝存在為至善的前提,也就是強調唯有來世才能實現至善,這一看法對至善的理解未免顯得抽象和思辨。就其現實性而言,無論是人走向完整的存在,抑或生活本身的完整性,都是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實現的。如上所言,作為康德觀念的轉換和引申,以人的存在和生活的完整性為指向的至善,已揚棄了康德語境中的抽象形態,這一視域中的至善誠然不同于已經完成的形態,而是具有過程的品格,但其過程性并非基于虛幻的來世。質言之,一方面,不能認為好的物質生活與好的精神生活的統一已經當下實現,而是應當承諾其歷史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斷創造條件,使兩者的統一獲得現實的社會前提,這種統一同時意味著經過轉換之后的至善理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不斷實現。從以上角度理解好的生活,便不難注意到,其真實的形態體現于存在的完整性與過程性的統一。
好的生活或至善的現實前提,具體表現在多重方面,好的物質生活與好的精神生活之間的互動是其中之一。物質境域的提升或廣義上好的物質生活,可以推進好的精神生活。如前所述,道德行為表征著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其實施則與物質生活的狀況存在不同的關聯。以仁愛行為而言,物質生活境域的改善,有助于促發關懷人的善行:對收入較高、物質境遇較好者來說,以捐款等方式幫助災區,較之在物質生活方面自身難保、處境艱難者,顯然更為容易。同樣,前面已提及,克己的行為常常伴隨著自我的某種犧牲,通過設立見義勇為基金、改善救助條件(如提升消防、醫療等服務設施)等方式,無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舍身救人者的后顧之憂,并激勵人們勇于躍入洶涌的洪流、沖進熊熊的大火以解救被困者,或不顧個人安危以制止歹徒行兇,等等。盡管道德行為的形成離不開主體的內在精神境界,外在條件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引發這一類行為,但以上前提對激發克己等道德行為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看到,物質境遇的提升、各種社會保障的完善,既可以視為好的物質生活的延伸,又為好的精神生活(包括道德行為的展開)提供了現實的社會條件。
在更廣的意義上,以好的物質生活與好的精神生活的交互融合為實質指向,前述至善的達到涉及寬泛的社會背景。首先是人的自由,此所謂自由不僅僅關乎觀念,而是以勞動時間的縮短為現實前提。就人類的歷史演進而言,早期人類為獲取生存資源而從事的勞動幾乎涵蓋其全部活動,與之相應,生活時間與勞動時間往往處于重合的狀態。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動不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內容,人開始從主要以生存資源的獲取為指向的勞動中抽身而出,擁有了不同尺度的自由時間,盡管不同的成員所享有的自由時間并不相同,在相當長的時期中,獲得并運用這種自由時間主要表現為社會部分成員的特權,但就整個社會范圍而言,自由時間的這種歷史變動又賦予文化的多方面發展以現實前提。在歷史的進一步演進中,人享有的自由時間也越來越多,生活的內容和方式則愈益多樣,后者的核心方面,表現為物質生活的豐富與精神生活的升華。從以上方面看,基于社會發展的自由時間,構成了好的物質生活與好的精神生活共同發展、相互統一的前提。自由時間的形成、擴展與延伸,本身展開為一個歷史過程,這既體現于以往的歷史發展,也將存在于未來的歷史演進。以上現實過程使廣義至善的實現既非基于虛幻的“靈魂不滅”,也不同于一蹴而就。
在談到社會自身的結構和演化時,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城邦的組成以追求“完善而自足的生活”為指向,這里所說的“城邦”,關乎社會自身的系統。具體地看,社會系統主要從公正、均衡的發展這一層面構成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彼此協調的條件。此所謂公正,以社會成員平等地擁有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源和機會為內容,均衡則意味著生活的物質之維與精神形態的彼此兼顧以及文化的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協調。唯有一方面,社會成員公正地獲得多樣的社會資源和發展機會,另一方面,社會系統中的不同方面都得到均衡的關注,好的物質生活和好的精神生活才能逐漸趨向統一。當然,社會的這種公正、均衡發展,同樣將經歷一個過程,而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也會獲得不同的內容。公正、均衡發展的社會形態,與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協調統一具有一致性;前者的過程性,規定了后者也總是面向動態的過程。
從生活主體的角度看,實現存在的完整性和好的生活又涉及不同視域的交融。這里可以關注“以我觀之”(the view of oneself)與“以人觀之”(the view of others)二重視域。就如何生活而言,“以我觀之”關乎自我的獲得,“以人觀之”則同時涉及自我的給予或付出。在“獲得”這一層面上,“以我觀之”與自我的物質境域具有更為切近的關聯;以“給予”或“付出”為關注之點,“以人觀之”則首先體現了精神世界的品格。當然,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以上視域與中國哲學中的成己與成人之說相關。對中國哲學來說,成己意味著成就自己,其中包含精神層面的提升;成人則既表現為對他人物質境域的注重,又以“己欲立而立人”的方式關切他人的精神完善。從以上方面考察,“以我觀之”與“以人觀之”的二重視域顯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區分。不過,以人的具體存在為關注之點,則可以注意到,自我成就并非僅僅指向抽象的觀念,而是以身心的多方面發展為現實內容;成就他人則如上所言,首先以他人在精神生活層面的提升為指向。與之相聯系,在引申的意義上,可以著重從與身相關的物質生活層面規定“以我觀之”的內涵、從“己欲立而立人”的人格關切的角度理解“以人觀之”。就個體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的運用而言,“以我觀之”側重于讓這種資源服務于自己在物質領域的生活;“以人觀之”則以設身處地地考慮和幫助他人為指向,包括通過以仁愛關懷的方式助人解困、以克己安人等形式讓人免于傷害,等等,后者體現了精神層面的高尚追求。單純注重“以我觀之”,常常更多地考慮自身的境遇,并容易由此限定自我;與之相對的“以人觀之”,則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意義上超越自我、關切他人,兩者體現了不同的價值關切。以上二重視域的交融,最終以好的物質生活與好的精神生活的統一為指向,后者意味著既走向存在的完整性,又實現生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