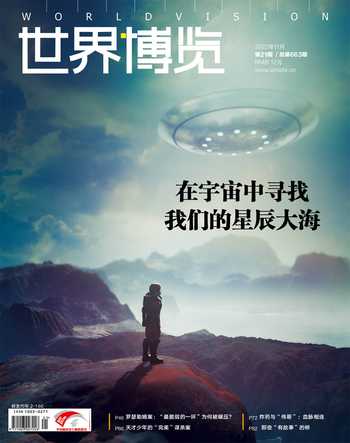科幻文學(xué)中的“太空圖景”
大海

被稱為“美國現(xiàn)代科幻小說之父”的羅伯特·海因萊因。
自古以來,“天上到底有什么”就是一個可以充分調(diào)動人類好奇心的問題。從世界各地的古代神話中都可以看到,天上一直是各路神仙的領(lǐng)地。對于無法理解和探索的事物,人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安排“超級人類”在上面,這不光是一種想象,也是人類希望變成“超人類”以探索和進(jìn)入這些領(lǐng)地的美好愿景。
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天上都有巨大的樓宇和宮殿,它們要么建在白云之上,要么飄在白云之間,而名為“神仙”“天使”的超級人類居住在里面,他們大多和普通人長相類似,而普通人也可以通過“修煉”或“行善”變成他們,從而去未知的地方過上無法想象的美好生活。除了天空,作為人們在夜晚看到的最亮的天體,月亮也一直是人類想象中可以探索和生存的地方,除了大家耳熟能詳?shù)逆隙鸷驮聦m,世界上許多地方的神話也有著神仙在月亮上生活的場景。只不過同樣作為人類熟知的天體,太陽往往就沒有這個待遇,可能祖先也知道太陽特別熱,連神仙都受不了那個地方。如今,對于更多的未知,人們依然利用無盡的想象力來描繪,只不過這次人類有了另一個重要的工具——科學(xué),而這也是科幻作品的來源。
雖然科幻作品的種類五花八門,至今都沒有一個完整的分類,但對于宇宙的探索和描述永遠(yuǎn)是科幻作品的重頭戲。不管是比較注重科學(xué)根據(jù)、對科幻因素的描述與解釋較為詳盡的硬科幻,還是天馬行空、更注重故事和文學(xué)技巧的軟科幻;不管是作為人類探索世界理想的延續(xù)、被稱為“未來大航海時代”的太空歌劇,還是描繪在宇宙格局下人類文明歷程和社會發(fā)展的未來史詩;不管是描述人類文明與其他文明相互交流與沖突的文明倫理,還是描繪星際間不同種族以宇宙為尺度的太空戰(zhàn)爭……歸根結(jié)底,關(guān)于宇宙的科幻文學(xué)都在思考兩個問題:宇宙是什么樣的?人類如果進(jìn)入宇宙之后會發(fā)生什么?而這兩個問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技術(shù)背景和不同的思想下,得到了眾多不同的答案。
在“神話時代”之后,其實(shí)很多作家也描述過以太空為背景的故事,法國文豪伏爾泰就在他的短篇小說《小大人》中描寫了一個天狼星人分別來到土星和地球并與這兩個星球上的智慧生物交流的故事。這篇充滿想象力和哲學(xué)思考的作品與現(xiàn)代科幻小說唯一的區(qū)別,也許僅僅只是那輛穿梭于星球之間的馬車。進(jìn)入20世紀(jì)后,人類文明的飛速發(fā)展讓人類對宇宙有了前所未有的認(rèn)知:1915年,愛因斯坦完成了廣義相對論,在牛頓之后為人類描述了一個新的宇宙圖景;接著,量子力學(xué)也漸漸進(jìn)入了人們的視野;1939年,G·雷伯通過射電望遠(yuǎn)鏡,接收到了來自銀河系中心的無線電波;借助射電天文學(xué),人們對自己所處的銀河系,對于整個宇宙的認(rèn)知又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1946年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jì)算機(jī)“ENIAC”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誕生,機(jī)器人的概念開始不斷被人提起;1961年蘇聯(lián)宇航員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宇宙飛船繞地球飛行一圈,成為首位進(jìn)入太空的人類;1969年,人類首次登上了地球唯一的衛(wèi)星,這是阿姆斯特朗個人的一小步,也是人類的一大步,很難想象萊特兄弟發(fā)明的簡陋飛行器和登月的宇宙飛船僅僅相隔了60年……而放眼地球,兩次世界大戰(zhàn)讓人類付出了數(shù)以億計(jì)的生命,而冷戰(zhàn)的陰云卻依然籠罩在人類文明上空。就在這樣一個時代里,誕生了科幻文學(xué)的三大巨匠——艾薩克·阿西莫夫、亞瑟·克拉克和羅伯特·海因萊因,科幻文學(xué)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銀河帝國已有12000年的悠久歷史,一位心理史學(xué)家卻作出驚人的預(yù)言:帝國即將土崩瓦解,整個銀河注定化作一片廢墟,黑暗時期將會持續(xù)整整3萬年!這是阿西莫夫描繪的宇宙圖景——一個跨越了數(shù)萬年歷史的星際帝國的興衰。1951年,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基地》出版,直到今天這部作品依然被認(rèn)為是科幻小說的經(jīng)典之作。《基地》講述了人類蝸居在銀河系的一個小角落——太陽系,在圍繞太陽旋轉(zhuǎn)的第3顆行星上,生活了10多萬年。人類在這個小小的行星上建立了200多個不同的國家,直到地球上誕生了第一個會思考的機(jī)器人。在機(jī)器人的幫助下,人類迅速掌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術(shù),開啟了恢弘的星際殖民運(yùn)動。人類在銀河系如蝗蟲般繁衍擴(kuò)張,帶著他們永不磨滅的愚昧與智慧、貪婪與良知,登上了一個個荒涼的星球,并將銀河系卷入漫長的星際戰(zhàn)國時代,直至整個銀河被統(tǒng)一,一個統(tǒng)治超過2500萬個住人行星、疆域橫跨10萬光年、總計(jì)數(shù)兆億人口的龐大帝國崛起——這就是銀河帝國。
一個微妙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銀河帝國建國后的12020年。哈里·謝頓,這個剛滿32歲的年輕數(shù)學(xué)家,開創(chuàng)了“心理史學(xué)”。這門學(xué)科能用數(shù)學(xué)公式準(zhǔn)確推演全人類的未來——“預(yù)言”從此成為一門可以信任的科學(xué),人類由此可以看見未來。謝頓的第一個預(yù)言是:雖然毫無征兆,但已存在12000年之久的銀河帝國即將滅亡。一時間,銀河震動,帝國飄搖,皇帝、宰相、奪權(quán)者、反叛的星球,各方勢力立刻劍拔弩張激烈爭斗的故事。其實(shí),嚴(yán)格地說,這部作品更像是一個披著科幻外衣的歷史寓言。而阿西莫夫也承認(rèn),《基地》系列作品的靈感來源于《羅馬帝國興衰史》。銀河帝國實(shí)際上就是羅馬帝國,偉大的“心理史學(xué)家”哈里·謝頓則是耶穌,也是活躍在帝國的末期,耶穌預(yù)言了人類的命運(yùn),而謝頓預(yù)言了帝國的黃昏。謝頓起初也是遭到帝國的審問和囚禁,就像耶穌和他的門徒遭到了羅馬的逮捕和封禁。但謝頓根據(jù)所謂科學(xué)的“心理史學(xué)”的計(jì)算,驚人地準(zhǔn)確預(yù)言了帝國對他的逮捕,精準(zhǔn)地預(yù)言出了對策,預(yù)言到應(yīng)該找一個帝國邊緣沒有人要的荒蠻星球,在那上面建立了為帝國保留科學(xué)、知識、技術(shù)火種的組織——“基地”。帝國將要?dú)缌耍貐s按照預(yù)言,像長庚星一樣在黃昏中冉冉升起,并受到帝國的庇佑。這完全就是基督教一開始被羅馬帝國禁絕、后又變?yōu)榈蹏鴩痰臍v史。不僅如此,隨后的情節(jié)基本也是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和近代歐洲崛起史。

科幻界的“三巨頭”。

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基地》、《銀河帝國三部曲》和《機(jī)器人》三大系列被譽(yù)為“ 科幻圣經(jīng)”,他曾獲代表科幻界最高榮譽(yù)的雨果獎和星云終身成就大師獎。

《基地》最近還被翻拍成劇集播出。
這種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故事,特別是政治、社會、宗教、倫理等較為宏大的背景,放到太空的架空背景里面的作品,在后來被人們稱為“太空歌劇”。這個詞在誕生的時候可不是什么褒義,在最初的定義里,太空歌劇就是太空背景的“肥皂劇”。不過《基地》通過一個個精彩的故事將太空歌劇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其中許多的科幻設(shè)想也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哲學(xué)性,比如貫穿整個故事的“心理史學(xué)”,就是以對銀河系中超過2000萬顆星球上的百億億居民為研究對象,用歷史上大規(guī)模人群的活動產(chǎn)生的一系列經(jīng)濟(jì)社會政治效應(yīng)進(jìn)行分析,試圖得出普遍的規(guī)律,用此規(guī)律來預(yù)測人類社會的發(fā)展。
在大多數(shù)的科幻作品中,就算將人類放到宇宙的尺度當(dāng)中,人類的社會結(jié)構(gòu)依然是“帝國”或者“共和國”,掌權(quán)者不是“國王”就是“貴族議會”,雖然《基地》系列作品也沒有能脫離這種局限性,但故事中也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文明形態(tài),比如共享信息、共同決策、共同思維的蓋婭文明,又比如獨(dú)居發(fā)展出來的索拉利文明,他們?nèi)丝谙∩佟⒖萍及l(fā)達(dá),長達(dá)幾百年的壽命里幾乎從不與他人交流,到后來還把自己的基因改造成了雌雄同體,只用心靈感應(yīng)交流,不再需要婚配,也不再需要養(yǎng)育后代,而是依靠統(tǒng)一規(guī)劃延續(xù)種族;當(dāng)一個索拉利人死后,會有一名新的小索拉利人被指定來繼承他的遺產(chǎn)……不管是銀河帝國還是各種形態(tài)文明的設(shè)定,都在激發(fā)著人們的思考,如果將人類文明的尺度放到足夠大,那么人類還能算是人類嗎?就像后來劉慈欣在《三體》中寫道的,“我沒有太多可說的,只有一個警告:生命從海洋登上陸地是地球生物進(jìn)化的一個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魚再也不是魚了;同樣,真正進(jìn)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對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2018年11月,在獲得“2018克拉克獎”時,劉慈欣又激動地回憶起自己讀《2001太空漫游》的那個夜晚:“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門仰望星空,那時中國的天空還沒有太多的污染,能夠看到銀河,在我的眼中,星空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我第一次對宇宙的宏大與神秘產(chǎn)生了敬畏感,這是一種宗教般的感覺。而后來讀到的《與拉瑪相會》,也讓我驚嘆如何可以用想象力構(gòu)造一個栩栩如生的想象世界。正是克拉克帶給我的這些感受,讓我后來成為一名科幻作家。”
如果說阿西莫夫描繪的宇宙是人類的擴(kuò)張,那么阿瑟·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則描繪了宇宙的另一面:神秘、深邃、宏大。在阿瑟·克拉克的筆下,人類變成了對宇宙沒有絲毫了解的孩子,在神秘文明一次次地指引下,憑借著強(qiáng)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進(jìn)化”。故事從史前階段開始,某天,一群生活在饑餓和死亡邊緣的人猿,在外出的途中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人造體”,這個人造體是純黑的立方體,作用不明,但明顯是智慧生物的手筆。人猿雖然不知道什么智慧不智慧,但立方體的出現(xiàn)卻在它們混沌的心智里觸動漣漪。人猿的首領(lǐng)偶然揮舞了一下手里的棒骨,“發(fā)現(xiàn)”它是一件趁手的工具,人猿們紛紛開始狩獵小動物,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他們甚至擊殺了一頭獵豹,史無前例地站在了進(jìn)化鏈的最高端。隨后故事跳躍到了人類進(jìn)入太空時代,人們在月球上發(fā)掘出了一塊埋于地底的黑色立方體,這個立方體遠(yuǎn)遠(yuǎn)超過人類的理解范疇,證明了地球之外存在遠(yuǎn)高于人類文明的智慧生命,而這個黑色立方體用電磁信號引導(dǎo)著人們前往土星的衛(wèi)星。人們駕駛飛船前往土星尋找信號指引的信息,經(jīng)歷了人工智能的叛變危機(jī),最終只剩下鮑曼一個人來到土星軌道,發(fā)現(xiàn)了又一塊黑色石板,接近石板之后鮑曼突然高速穿過一條五彩斑斕的隧道,最終置身于一間風(fēng)格古樸華麗的臥室。鮑曼迅速老去,在垂死之際,第四塊石板出現(xiàn)在床邊,石板將他變成透明光團(tuán)中的胎兒——星孩。星孩凝視著浩瀚的宇宙,等待未知新生的到來。

如今影視作品中經(jīng)常能看到的蟲族。

羅伯特·海因萊因的幾部科幻小說作品。

由科幻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星船傘兵》,這部影片對以后的科幻題材的電影、游戲等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人類在探索宇宙的過程中究竟會不會與外星文明產(chǎn)生聯(lián)系,外星文明到底是什么樣子?這是科幻作品經(jīng)常會討論的問題,有些作品中外星文明有些親和友善,有些殘暴好戰(zhàn),但在阿瑟·克拉克的筆下,根本就沒有外星文明的形態(tài)。人們通過描寫,只知道他們的文明程度遠(yuǎn)高于人類,關(guān)于外星文明的所有了解與想象全部來源于一塊黑石板,這塊黑石板“極致的黑中,看不到任何痕跡,任何不勻。這是純?nèi)坏囊梗Y(jié)的夜”。黑石是人類可以見得到、摸得到的,但是黑石背后的完美科技人類無法理解,黑石在外星文明中的用途也無法確定,因此,黑石背后神秘的設(shè)計(jì)者——外星文明在人類的想象中變得格外強(qiáng)大。而這個強(qiáng)大的文明引領(lǐng)著人類一次又一次地進(jìn)化,只是這種進(jìn)化過程永遠(yuǎn)伴隨著強(qiáng)者對弱者的毀滅。這種描寫為人類對外星文明的幻想開啟了新的大門,這種強(qiáng)大到人類無法觸及的太空人形象還引發(fā)了人們對于宇宙探索和與外星文明接觸的新的思考。在寫作《2001太空漫游》小說的同時,阿瑟·克拉克還與著名導(dǎo)演斯坦利·庫布里克一同編寫了同名電影的劇本,而這部電影被稱為“現(xiàn)代科幻電影技術(shù)的里程碑”,同時也被譽(yù)為最偉大的科幻電影之一。
許多科幻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向人們描述著不同的宇宙圖景:被稱為“美國現(xiàn)代科幻小說之父”的羅伯特·海因萊因在《星船傘兵》中首次引入了蟲族的概念,這個瘋狂擴(kuò)張的恐怖種族成為了人們仰望星空時揮之不去的噩夢;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構(gòu)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完整宇宙體系,將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宗教、生態(tài)學(xué)甚至人性、人的本質(zhì)、人的目的放在一個宇宙的尺度上進(jìn)行思考;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也通過《三體》將宇宙描繪成一個充滿爭斗與毀滅的黑暗森林……如今,隨著人類對宇宙的不斷探索,人們對宇宙的幻想也更加豐富立體。也許正是這種不斷豐富的幻想激發(fā)著人類對宇宙更多的好奇心,而這種好奇心也終將帶領(lǐng)人類走向更深的太空。
(責(zé)編:昭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