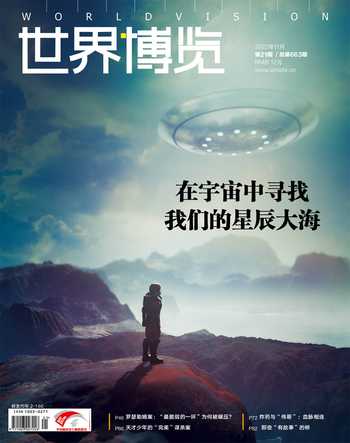天才少年的“完美”謀殺案
付杰

兩個堪稱“高富帥” 的天才少年——18歲的理查德·勒伯和19歲的內森·利奧波德,卻成了殘忍的殺人兇手。
死刑是最為嚴厲的刑罰,以直接剝奪罪犯的生命為目的,故被稱為極刑。人類歷史上一直用死刑來懲罰那些罪大惡極的人,從而達到刑罰的威懾效果。但隨著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啟蒙思想家重新審視死刑制度,出現了越來越多廢除死刑的聲音。近代刑法學鼻祖貝卡利亞的經典著作《論犯罪與刑罰》的“橫空出世”,更是將廢除死刑推向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權運動。
如今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而美國作為最發達的經濟體依然保留著死刑,不過關于是否廢除死刑的討論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是在發生重大惡性案件時,對死刑的態度將民眾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
美國歷史上曾發生一樁融合天才少年、完美犯罪與謀殺藝術3個吸睛元素的轟動案件。本來兩名罪犯被判處死刑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但律師的精彩辯護不僅扭轉了兩人的命運,還引發了人們對死刑的深刻反思,這就是發生于上世紀20年代的伊利諾伊州訴利奧波德與勒伯謀殺案(以下簡稱利奧波德案)。
1924年5月21日晚上,弗蘭克斯夫婦在芝加哥的家中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自稱為“喬治·約翰遜”的男子說已將他們的兒子羅伯特·弗蘭克斯綁架,但并沒有傷害他,要求他們明天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其實在當天早些時候,見羅伯特久久不歸,父親雅各布·弗蘭克斯已經給芝加哥警方打了電話,請求警方幫助尋找他的兒子。
5月22日上午,他們收到了一封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盡管其內容言辭考究、彬彬有禮,弗蘭克斯夫婦卻感受不到絲毫溫情。綁匪要求他們支付1萬美元的贖金,并對支付方式也提出詳細要求,比如必須是不帶記號的舊鈔,而且要把這些錢放入白紙包裝、用蠟封口的盒子。信里讓他們等待下步指示行事。他們當天又接到了綁匪的電話,說會有一輛出租車接雅各布去一個雜貨鋪。
正當焦急萬分的弗蘭克斯夫婦準備贖金之時,警方打來電話稱在芝加哥南部的沃夫湖附近發現了一個孩子的尸體,并讓他們前去確認是否為羅伯特。盡管尸體赤身裸體,外貌還被鹽酸所毀,弗蘭克斯夫婦仍悲痛地發現這就是他們的兒子。警方很快就鎖定了犯罪嫌疑人,他們是兩個堪稱“高富帥”的天才少年——18歲的理查德·勒伯和19歲的內森·利奧波德。
理查德·勒伯(Richard Leob)是密歇根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畢業生,畢業后繼續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其父為美國第二大零售商西爾斯·羅巴克公司副總裁。勒伯特別喜歡閱讀偵探小說,沉迷于犯罪故事,這個愛好也深刻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他認為只要使用天才的作案方法,肯定存在世上任何人也破解不了的“完美”犯罪。
內森·利奧波德(Nathan Leopard)同樣出身于富人家庭,他通曉15種語言,15歲就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法律,當時已經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是個公認的天才少年。他還是個鳥類學家,對鳥類懷有濃厚興趣,在核心期刊上發表過研究論文。除此之外,他還是尼采的狂熱粉絲,尤其癡迷尼采的“超人”哲學。尼采眼中的“超人”,絕非生活中的平庸之輩,而是超越了自我與他人,是絕對的強者和天生的統治者;“超人”不受現行法律和習俗的約束,他本身即是價值體系的創造者,是真理的尺度和道德的準繩。
在利奧波德眼中,他和勒伯都是尼采哲學中的“超人”,“超人”可以“合法”地殺人,尤其是殺掉那些“懦弱、平庸”的普通人。“超人”即法律,可以審判世人的生死。他們還認為謀殺對大多數人是犯罪,對少數人是特權,而且上等人可以“合理地”殺死下等人,“超人”無疑是“少數人”和“上等人”。他們之前干過幾起盜竊和縱火案,沒有被發現。但這樣的小案件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超人”人設,于是就想實踐“把謀殺作為藝術、把死者作為作品”的瘋狂設想。
從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來看,兩人皆是含著金鑰匙出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擁有超高的智商。勒伯外向活潑,利奧波德則內斂沉靜,但兩人相識后很快就成為了好朋友,甚至有證據顯示他們還是一對同性戀人。
1924年5月21日下午,兩人開著租來的車在大街上搜尋目標,正巧遇上了勒伯的遠房表弟——14歲的羅伯特。羅伯特是一個網球迷,他們以鑒定網球拍為借口把羅伯特引上車。勒伯先是用鑿子重重擊傷了他,然后將破布和膠帶塞入他口中令其窒息而死。殺死羅伯特之后,兩人把尸體丟棄在了芝加哥南部一個下水道的排水口,并帶走了他的衣服,毀壞了他的外貌,還將車上的血跡清洗干凈。
兩人在作案的時候,并無目擊證人在場,那么,警方怎么發現他們兩個就是兇手的呢?
5月22日上午,一位鐵道維修工經過拋尸的下水道附近,發現一具尸體后立即報了警。警方勘察現場時發現了一副角質框架的眼鏡。正是這副眼鏡令警方按圖索驥,確認了利奧波德有作案嫌疑。原來,兩人拋尸時利奧波德的眼鏡不慎掉落現場,這副眼鏡上有一種十分昂貴的鉸鏈裝置,當時全芝加哥只有3人擁有這種眼鏡。警方根據這個線索迅速鎖定了3人,在確定了另外2人的不在場證明后,利奧波德就成了最大也是唯一的嫌疑。
警方來到利奧波德的家中,向他詢問關于眼鏡的事情,恰巧勒伯也在。利奧波德謊稱他前段時間曾在尸體被發現的地區觀察鳥類,而且在下水道附近拍過照片。利奧波德并沒意識到自己丟失了眼鏡,就說眼鏡在家里放著,可佯裝一番尋找之后自然是找不到。警方懷疑兩人與這宗謀殺案有關,就將他們帶回警局拘留審訊。
警方又詢問了兩人在案發當天的活動。利奧波德說他倆上午先是開著自家的車出去兜風,中午去了市區吃飯,然后去南部觀察鳥類,晚上由于喝多了沒有回家,就去了公園玩。兩人事先肯定已經串供,勒伯也證實了利奧波德的說法。
這條線索暫時找不到突破口,但警方還手握另一個重要證據,就是那封寄給弗蘭克斯夫婦的綁架信。經專家辨認,這封信是用安德伍德牌手提式打字機打出來的。警方了解到,利奧波德和他的同學曾用這臺打字機打印考試資料。警方把綁架信和考試資料仔細對照,確認它們來自同一部打字機,利奧波德家的仆人也說家中有這樣一臺打字機。但利奧波德矢口否認自己有這樣的打字機,警方搜查了利奧波德家,也沒有找到打字機。
這時警方又發現了一個重大線索:利奧波德的司機說案發那天把車送去維修了。兩人開車出去兜風的謊言不攻自破。警方順藤摸瓜,找到了兩人租來的汽車,并發現了汽車上沒有被清洗干凈的血跡。在鐵證如山的事實面前,兩人不得不認罪,并供認了殺害羅伯特的詳細過程。
這件案子十分具有新聞效應,經過媒體大肆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轟動,公眾對利奧波德和勒伯毫無動機且異常殘忍的謀殺行為感到震驚和憤慨,主流民意紛紛要求判處兩人死刑。檢察官也聲稱這是“有史以來大小陪審團遇到的情節最完整的案件”,信誓旦旦要將兩人送上絞刑架。
案件被起訴后,利奧波德和勒伯的家人深知兩人生機渺茫,因此聘請了當時美國最優秀的律師之一克拉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丹諾被后世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是美國律師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不僅具有高超的演講才華和嫻熟的辯護技巧,還是弱勢群體的“守護神”,堅決捍衛社會底層人士的基本權利。但利奧波德和勒伯顯然不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家人之所以選擇丹諾,還因為他是堅定的死刑廢除主義者。丹諾認為,死刑源自原始、落后的同態復仇思想,在20世紀的世界顯然是極不人道的野蠻刑罰,應該予以廢除。鑒于利奧波德案的轟動程度,丹諾可以借此宣揚其反對死刑的主張,大概這也是他接下此案的深層考量吧。
不過,即使是丹諾這樣偉大的律師,也深知此案十分棘手。利奧波德和勒伯已經認罪,而且證據鏈真實完整,想要推翻兩人的供認也不可能,何況他也沒有想過這樣做。因為丹諾十分清楚,想為兩人作無罪辯護無異于天方夜譚,只能想辦法讓法庭判決兩人免于死刑。
丹諾首先申請無陪審團審判,這樣只需面向法官展開辯護,因為在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中,陪審員通過認定案件事實問題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法官則要處理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并在被告人有罪時負責具體量刑工作。在這個案件中,既然無法作無罪辯護,陪審團也就沒必要設置了,而且12位陪審員在場的情況下,兩名被告人的行為可能更容易引起眾怒,進一步惡化兩人的輿論處境。法官由于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且有豐富的法律實踐,因此更為冷靜理性,不會受到民眾情緒的過多干擾。

在利奧波德眼中,他和勒伯都是尼采哲學中的“超人”,可以“合法”地殺掉那些“懦弱、平庸”的普通人。

當地時間2017年1月17日,美國華盛頓,民眾聚集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組織反死刑游行。美國已有23個州廢除死刑,美國聯邦政府和27個州依然保留死刑。


一副眼鏡令警方按圖索驥,確認了利奧波德有作案嫌疑。
1924年8月22日,案件正式審判。盡管控辯雙方也有激烈的交鋒,但是到了丹諾發表最終辯護的環節,整個法庭幾乎成了丹諾的獨角戲。為了能夠說服法官,丹諾將法庭當作個人布道的講臺,發表了長篇大論的演講。整篇演講既神采飛揚、鏗鏘有力,梳理了案件的來龍去脈和關鍵要點;又聲情并茂、感人至深,不禁讓人對兩名被告生發惻隱之情。俗話說,刑事辯護律師總是讓人看到壞人最好的一面,離婚訴訟律師總是讓人看到好人最壞的一面,丹諾通過其雄辯的表達讓法官看到了案件背后更多應當納入考量的復雜因素,有學者就曾評論道:“很少有審判能夠像1924年這起利奧波德與勒伯謀殺案那樣催人淚下。”
首先,丹諾指明了被告的財富與年齡不應被忽略。“如果我們在這個案子中失敗,那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因為有錢的緣故。我們所碰到的最嚴重的障礙就是金錢。有時,貧窮反而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說,兩名被告的家庭背景反而激發了公眾的仇富心態,進而匯成一股要求判處他們死刑的聲浪。如果是因為被告父母的富有而判處被告死刑,這顯然是不公正的。
丹諾還專門查詢了伊利諾伊州的死刑記錄,歷史上共有90人以絞刑的方式被執行死刑。在這些死刑犯中,沒有一人是23歲以下的,而2名被告分別為18歲和19歲。如果法官不遵照先例,堅持判處被告死刑,丹諾用混雜著請求和質問的語氣說道:“您將不得不置過去的所有判例于不顧,您將不得不置世界的進步于不顧,您將不得不置所有人類的情感和同情心于不顧。但我知道,本法庭充滿著這些人類情感。”


根據利奧波德案改編的電影《朱門孽種》(1959年)和《奪魂索》(1948年)劇照。利奧波德案被改編成了小說、電影、音樂劇等多種文藝作品。
其次,丹諾懇請法官不要判處兩人死刑。他說判處兩人死刑既不能讓羅伯特起死回生,也不能發現真正的正義,反而“殘酷只能孵育出殘酷”“仇恨只能導致仇恨”,只有用仁慈、博愛和理解才能化解這種無休止的殘酷和仇恨。“如果兩人被判處了死刑”,丹諾反問道,“難道這就是芝加哥的光榮之日嗎?難道這就是本州檢察官的光榮勝利嗎?難道這就是美國公正的偉大勝利嗎?難道這就是基督教精神、仁慈和寬容的光榮體現嗎?”因此他向法庭發出祈求:“與其說我是在為這兩個孩子祈求,還不如說我是在為那些不可計數的后代祈求。那些后代也許不會受到如同這兩個孩子一樣好的保護,他們也許會在狂風大浪中無助地倒下。就是為了他們,我在思索,而且就是為了他們,我才向本法庭祈求,不要再退回到那殘酷、野蠻的過去。”
最后,丹諾詳細分析了兩名被告的心智狀況,說明兩人其實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這才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慘無人道的罪行。他先提到了精神病醫生的診斷,發現兩名被告不同于常人的一點是沒有“情感反應”,即使談及那些十分恐怖的事情,他們的表情也不會有絲毫變化。他們還缺乏“道德上的震驚感”,這顯然是極不尋常的。接下來丹諾又敘述了兩人的童年經歷對他們造成的心理影響。
勒伯在兒童時期受到了家庭教師的嚴厲管教,當時這位女教師強迫勒伯努力學習,“就像非要把植物放進溫室里一樣”,希望他能達到最高的完美境界。勒伯在這種強壓性的環境下成長,喪失了兒童本應享有的自由天性。為了擺脫家庭教師的控制,他學會了撒謊和逃學,甚至癡迷上了偵探小說,終日沉浸在犯罪故事中,這也導致他形成了一個固執的想法:“世界上總有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偵破的完美無缺的案子,總有一個讓偵探們無從下手的案子。”丹諾還指出勒伯曾對查利·羅斯被綁架的故事產生過濃厚興趣,這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他要實施一樁天衣無縫的綁架和謀殺案。
丹諾總結道,他們兩人的行為可以從童年中找到解釋,他們殺人就像是一種本能,只是為了追求新奇的體驗和刺激,“當童年的夢想、童年的幻覺還在一個人身上徘徊不去時,當一個人生理上正在逐漸長成大人,心理上還是個孩子,還具有孩子一樣的情感、感受和幻覺時,你就可以說,正是這些童年的夢想和幻覺應當對這個人的行為負責。”
丹諾的精彩辯護顯然打動了法官。1924年9月10日法庭宣布了判決,勒伯和利奧波德分別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和99年有期徒刑。兩人的后續命運也很有戲劇性,勒伯于1936年服刑期間被獄友殺死,利奧波德則于1958年被假釋出獄,搬到波多黎各,繼續接受教育并從事鳥類研究工作,他還與當地一名寡婦結婚成家,最終于1971年因心臟病發作而離世。
被稱為“世紀大案”的利奧波德案已經過去了近百年,但在案件內外,有2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思考與探討,并且這種討論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案件之內,是死刑是否應當被廢除的問題。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律實踐的深入展開,死刑廢除已經成為一場蔚為大觀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越來越多的國家廢除了死刑。開頭提到的貝卡利亞對死刑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加繆也在《思索死刑》中認為死刑是一種“可憎的示范”,其威懾效果十分有限。
當然,每個國家的國情、社情、民情都存在很大差異,是否廢除死刑應因地制宜、因時而動,如美國和日本至今仍保留死刑,但毫無疑問的是,廢除死刑將是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丹諾在最終辯護中也曾深情展望道:“我祈求生命、理解、仁慈、友好以及體諒所有人類的無限慈悲,我祈求我們能用仁慈去征服殘酷,能用愛去征服仇恨。我知道,未來在我這一邊。”如今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廢除了死刑,也驗證了他所說的“未來在我這一邊”。
案件之外,是律師是否應當為“壞人”辯護的問題。在利奧波德案中,兩名被告在沒有任何動機的前提下殘忍地殺害了一名14歲的兒童,丹諾無疑是在為所謂的“壞人”辯護,這種做法肯定讓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強烈反對。律師的天職,到底是主持正義、成為天使的化身,還是履職盡責,哪怕有時不得不去做魔鬼的代言人?在筆者看來,在法律這一場域,替天行道、伸張正義并非律師的唯一天職,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盡心盡力為委托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務,只有這樣,在與檢察官、法官等角色的“合作”中,才能促成理想的結果。法庭是實現正義的地方,但正義無法自我實現,只有控辯雙方在對峙與博弈的過程中才能發現真相。當然,這種真相是法律事實上的真相,而非客觀事實上的真實,兩者有時一致,有時卻有較大差別甚至迥然有異。
況且,很多案件往往沒有那么明晰,當事人也并非黑白分明。此時,控辯雙方各司其職,傾盡全力擊敗對方,才是對彼此、對法庭,也是對法律最好的尊重。這與曼德維爾悖論和亞當·斯密的自私人理論所揭橥的道理異曲同工。也即,只有私人的“惡德”才能成就公眾的利益。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審視,個人自私自利、企業唯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和市場制度當然不具備道德合法性,但指望以“公共精神”為基礎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大同社會,試圖在地上建立天國,無疑是“浪漫的奇想”。
(責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