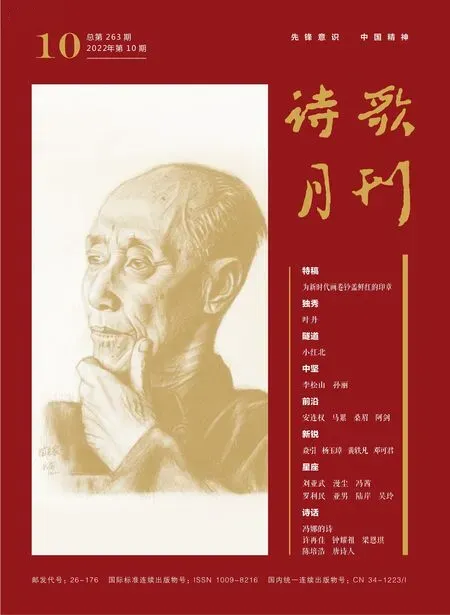矛盾詩學的矛盾
唐詩人
馮娜近幾年的詩歌越來越哲學化,視野變得開闊,主題更為宏大,表達風格也趨于穩(wěn)定,似乎在著力建構自己的詩學體系。像其2021 年的新作《心靈》《螺旋星云》《白茅海》《雙河溶洞》等等,或探討一些本體性的詩學問題,或探尋生命、自然、時間等一類玄奧主題,讀來不能不感嘆詩人的知識之廣博和思考之深沉。但是,近來我也聽到一些聲音,說他們更喜歡馮娜早期的詩歌,現(xiàn)在的作品比較難進入,那種使人振奮、予人心靈共鳴的元素少了,起碼不再容易感受到。這似乎是一個悖論:詩人逐漸成熟的詩學技藝,與讀者通常情況下所期待的詩性體驗,形成了一種創(chuàng)作追求與接受習性的沖突。這或許是很多詩人都要遭遇的考驗,像北島、翟永明等等,早期出名的詩作攜帶著多數(shù)讀者都能夠直接領會的激動人心的品質(zhì),但要進入他們更多的,尤其后期的詩作,卻不再那么容易。當然,具體到每個詩人,內(nèi)在的問題也不同。
是什么原因?qū)е铝笋T娜詩歌走向深刻卻不再親切?可以從《魔術》《勞作》《短歌》這幾首新作來具體闡述。這四首詩歌,不知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都有一種矛盾性的結構特征。所謂“矛盾性”,是詩人對一些主題的詩學探討,借助的是語義或意象的矛盾結構。比如《魔術》里說的“魔術技藝”,女人與母豹、困頓旅途與迷人的蜃樓海市、聲音與沉默、你和我,這些有著矛盾內(nèi)涵的意象、詞語,很輕捷地說出了詩所謂“魔術技藝”的所指,指向的是人、物、世界的復雜性、辯證性內(nèi)涵。再如《勞作》,“我”和蜜蜂、螞蟻、桉樹的對比,尤其是“我”與“農(nóng)夫”的對比,所形成的矛盾性結構,揭示詩人與世界、與其他人的內(nèi)在關聯(lián)。還如《短歌》,南方與北方、果實的安慰與事實上的衰老、酸澀與甜蜜等,這些表達所構成的語義上的矛盾性,幫助詩人完成了自然與人生的思索。這些詩作,題材雖小,但牽涉的主題極廣,對生命、自然與人生的思考也抵及了很深的維度。但是,詩人借助矛盾性結構來完成的思想探詢,也局限著詩歌的親切感和生命力,這是一種“矛盾性詩學”的矛盾。
呈現(xiàn)問題的矛盾性本質(zhì),這是創(chuàng)作者思辨性思維的一種表現(xiàn)。但矛盾性、思辨性所關聯(lián)的,通常是哲學思維。哲學思維與詩學思維有很大不同,歷史上的哲學與詩之爭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說明這兩種思維很難分辨清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馮娜的“詩學”有逐漸向“哲學”靠攏的傾向,這或許帶來了深刻,但也帶來了感性的缺失。詩學邏輯不等于哲學邏輯,其中最主要一點就是詩歌不能過于理性。《魔術》《勞作》《一種聲音》等等,理性的聲音大于感性的聲音,我們看到了詩人關于人生和自然萬物的“理”,卻難以被詩的語言、意象本身所刺激、所感動。或者說,馮娜的詩歌創(chuàng)作,到了一個新的轉(zhuǎn)型階段,她需要更多的意象、更新的語言,以及更豐富的精神形式,以擺脫這些理性化的矛盾性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