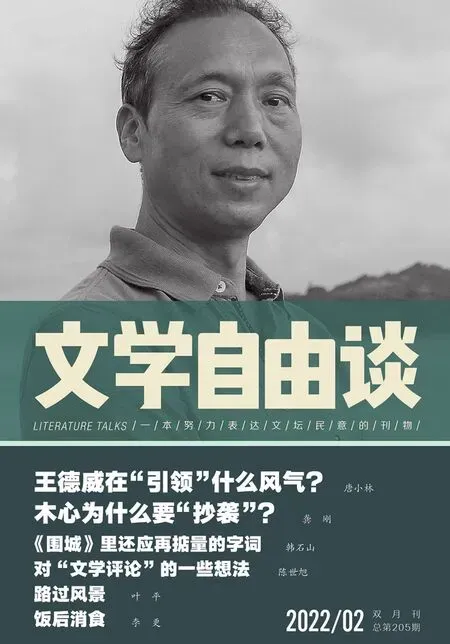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中國新詩
□丁 魯
首先要說明,我談這些問題,針對的是詩歌界,不是針對社會上愛好詩歌的朋友們。大家喜歡詩,愿意寫一寫,那是怎么寫都行的。但涉及詩歌界,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詩人的寫作是面向讀者的。進入信息社會之后,部分人,甚至個別人的欣賞趣味開始受到重視,出現了“小眾”和“分眾”的說法,但這是給詩歌作者提出更高要求,而不是否定受眾的大多數(即“大眾”和“群眾”)。其次,詩歌界不能沒有經典。一個時代留不下經典,通過什么來了解這個時代?——光憑這兩個原因,就值得對新詩做點兒研究了。
我曾經說過,中國新詩的問題癥結,在于基本理論的缺失。有的朋友對我批評得很尖銳。其實,如果不先解決理論問題,一開始就從作品和作者來討論,我估計會爭論得更加激烈。新詩百年,這樣的爭論還少嗎?效果怎樣,回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們還是先別談具體的作品和作者吧。
一、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中國新詩
中國是一個詩歌大國,先天的詩歌資源非常豐富。可是,“五四”以來,中國詩歌忽視基本理論,迷信“內容決定形式”的觀念,因而問題不斷。到了當代,新詩對古典詩歌遺產的繼承,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話。原因何在?我以為首先得從“五四”時期的語體突變去尋找。
語言屬性,是詩歌最重要的屬性。“五四”時期語體突變,法定的書面語言在短時期內由文言(古漢語)變為現代白話(現代漢語),使中國詩歌出現了一個斷層,即語體的斷層。中國的白話新詩,基本上是借鑒西洋詩而建立的。借鑒并非移植,新詩的語言母體仍舊是漢語,但語體從文言變成了白話,怎樣繼承古典詩歌的遺產呢?這個問題短期內沒有很好解決,遺留至今。
其原因,客觀的自然不少,如日本侵華戰爭;但更重要的還是主觀原因。“五四”時期,守舊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攻擊,常針對尚未成熟的白話詩。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保衛白話詩的時候,往往強調它的內容之“新”。胡適把白話詩命名為“新詩”,就是針對內容而言的。至于其形式方面,百年來始終重視不夠,而且只是把詩歌形式的研究和實踐當作一種流派活動。雖有以聞一多為代表的白話格律詩倡導,但理論上的開拓并不多,還出現了一些毛病(比如提倡所謂的“建筑美”)。我這里說的“形式”,也包括自由詩在內。自由詩只是詩歌的一體,它也需要研究形式。以為它沒有形式或不需要形式,或以為它窮盡了一切形式,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由于語言屬性是詩歌的第一屬性,我們說到詩歌形式,指的主要就是詩歌的語言形式,特別是它的語音形式,因為詩歌這種文體和文學樣式是極為重視語音美感的。文學教材提到詩歌的特點時,總是要說到“韻律”之類。我把那些說法歸結為“語音美感”,是因為“語音美感”比其他說法更寬泛,更有包容性,可以涵蓋自由詩。
過去對新詩形式方面的不夠重視,特別表現于將“形式”等同于“藝術性”。其實,形式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給事物“賦形”的根本條件,涉及事物的定性。如果事物沒有一定的形式,一個事物就不能和別的事物區別開來。比如詩歌,如果沒有一定的外部形式,我們怎么能把它和散文加以區別呢?
不研究詩歌的形式,就無法確定詩學中一系列重要術語的名稱和定義,甚至連什么是詩歌、什么是中國新詩等等詩學中最重要的議題都無法解決,因此也就無法完成構建中國詩學的任務。
說到詩歌的外部形式,當代的中國人常以為分行排列就是新詩的唯一標志。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由此引出的“會敲回車鍵就會寫詩”的說法,不過是個笑話罷了。中國古典詩歌就從來不分行,因為它的文句和詩句基本一致,沒有分行的需要。西洋詩分行,是由于印歐語的單詞長度不如漢語整齊,再加上使用“跨行法”,不分行看不清詩歌的結構。至于利用分行作為藝術手段,那是以后的事了。新詩從西方學來了分行,使詩歌的眉目更清楚,這是好事,但不應影響到我們對詩歌本質的認識。
西方由研究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已經發展到了研究非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我們可以讀讀馬克思的著作,比如《共產黨宣言》,里面許多句子就具有詩歌的美。有些中國人以為只要把它們分行排列就是詩,西方人卻并非這樣認識,因為這些著作是用散文語言而不是詩的語言寫的。詩的語言不光內容具有文學性或者說“詩性”,而且首先有它的外部語音形式,像節奏、韻腳等等都是。以為有了詩性就是詩,和以為有了詩歌形式就是詩一樣,都是片面的。完全否定傳統詩歌形式的觀點出現之后,詩歌語言和散文就真的沒有區別了。所以自由詩在西方又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而“回歸”也成了一個議題。
中國詩歌界人士可以提倡自由詩,但不能不如實地了解外國人自己的詩歌習慣,也不能不了解中外詩歌的歷史,特別是中國格律詩,包括古典格律詩和成長中的白話格律詩(或者叫格律體新詩)的歷史。這種知識本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文化素養;對詩歌界人士而言,更是一種基本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我們的詩歌界至今對此重視極為不夠。
這種忽視也影響到我們的西方詩歌研究。外國詩歌研究的物質基礎是詩歌譯本,這是全世界的共識。西洋詩其實和中國古典詩歌一樣,是極為重視詩歌形式的。印歐語用于詩歌翻譯遠不如現代漢語好用。他們譯格律詩往往像改寫一樣,就是為了照顧譯文的詩歌形式。這一點,是我們詩歌界許多人士所不了解的,或不愿了解,或了解而不愿提及的。過去我們詩歌翻譯的對象,主要是西洋格律詩。由于白話新詩的格律研究滯后,西洋詩的翻譯質量就一直不穩定,往往只傳達了詞句內容方面,沒有力求傳達詩歌的形式方面,有些人甚至認為“以格律詩譯格律詩”是多此一舉。而詩歌的美感卻主要是靠形式方面來傳達的。人家的是格律詩,念起來瑯瑯上口;如果譯成中文磕磕巴巴,用這樣的譯文怎么去分析作品的特點呢?這特點不光是指藝術方面,連它的基本特征(比如是格律詩還是自由詩)也包括在內。不首先解決翻譯問題,許多重要的名詞術語就難確定,中國的現代詩學也就無法構建。
總之,由于忽視了詩歌的形式方面,新詩難以吸收中國古典詩歌的營養,顯得先天不足。至于說它后天失調,也包括對西方的吸收囫圇吞棗,食洋不化,而且同樣主要表現在詩歌形式方面。所以,想要構建中國的現代詩學,詩歌形式是不能繞過的環節。
“五四”時期,中國文人是普遍具有古典詩歌修養的。到了現在,許多人,包括詩歌界人士,對古典詩歌文化已經陌生了。從他們的詩歌論著和詩歌作品,都可以看出這種情況。比如有的論者不通平仄,卻力圖分析古典詩歌,這就很容易穿幫。至于對西洋詩,由于忽視詩歌形式,同樣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即使想要吸收西方現代主義,如果缺少這些知識,那也是不行的。這雖然是從形式談起,但已經遠遠超出形式問題了。
二、說說“自由”
中國新詩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和中國自由詩的興起有很大關系。中國古典詩歌本來沒有自由詩,發展到近體詩和詞、曲等形式之后,格律嚴格,常有要求解放的議論。“五四”時期,漢語語體由文言變為白話,詩歌在客觀上有了使用白話寫作的要求,卻一時又拿不出一定的形式;主觀上則國內有熱火朝天的思想解放運動,國外有新興的自由詩作為借鑒,中國的白話新詩就以自由詩為主要形式發展起來了。
于是詩歌界熱衷于強調詩歌可以自由寫,應該自由寫。到了當代,一些人更加強調詩的自由。在他們看來,所謂自由,就是絕對的無拘無束。他們總是把內容和形式混在一起來談,一張嘴就說詩是不能受拘束的。說到形式的時候,他們不理解自由和規律的辯證關系,也不理解自由的詩思要在詩歌形式的制約下實現,而這是許多詩歌界大人物曾經談過的。一定的形式,是詩思自由的保證。即使是自由詩,也要有它的定義和外部形式,不然就無法和格律詩加以區別。所謂詩歌的絕對自由,如果不是在相對自由中逐步實現,那就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罷了。
讓我在這里引用俄羅斯詩人丘特切夫的一首作品來說明。丘特切夫在俄羅斯是一位大詩人,所獲評價極高,只不過在中國介紹的很晚,許多人不知道。他的作品富于哲理,常將哲理通過具象加以表達。他是十九世紀的人,但二十世紀白銀時代的俄羅斯詩人認他為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的鼻祖。
以下是他的《噴泉》一詩(拙譯):
你看那股活潑的噴泉,/冒著云煙,像一根光柱,/在太陽下迸出閃閃的火花,/又化成一團潮濕的塵霧。/它那道光華直射天宇,/一觸及朝夕思慕的高空,/又注定要像火紅的灰燼,/重新落到下面的土層。
啊——人間思想的噴泉!/你永不停息,無休無止!/你盡情噴射,搖曳不安——/是受什么神秘的法則驅使?/你多么急切地向天噴射!……/——惡運的巨掌卻變幻莫測,/老把你那股頑強的光流/擊成水珠——從高空飛落。
這首詩通過噴泉,表現了自由和必然的深刻哲理:人永遠是不自由的,但總是在追求自由;人總是在追求自由,但永遠是不自由的。詩不也是如此嗎?既然你要的是無限自由,還要寫成文字干嘛?還要出版干嘛?
這里不能不涉及“解構”問題。既然西方已經到了要解構的階段,我們為什么還要研究結構問題呢?
“五四”提倡自由詩,似乎實現了詩體的徹底解放。其實這種解構的快樂,伴隨著的卻是解構的痛苦。由于文言改白話,中國的現代詩學還沒有建構,詩歌實踐還無所依據,這時片面提倡自由書寫,結果成為百年來中國詩歌問題不斷的根源。
中國的白話詩歌由于建構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出現了許多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光說名詞術語和定義吧:“中國新詩”究竟是什么?它是所謂的“現代詩”嗎?什么是格律詩和自由詩?它們之間的界限在哪里?“自由體”這個說法科學嗎?所謂“自由體”究竟如何定義?為什么“格律詩”和“格律體”是同一回事兒,“自由詩”和“自由體”卻不是同一回事兒?所謂“現代格律詩”究竟是什么?所謂“馬雅可夫斯基詩體”究竟是什么?“馬體”就是“樓梯詩”嗎?它是自由詩或者所謂“自由體”嗎?這件事鬧了多大的笑話?等等等等。
說到這里,我們不能忘記,二十世紀的文學現代主義是從俄羅斯形式主義開始的,而這個流派提倡的恰恰是結構主義,參加者也都是一些語言學者。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的說法雖然影響很大,但其影響實際上是俄羅斯形式主義的一種異化。對于一首短詩來說,處處陌生化,而且是表面上的陌生化,那是很難搞下去的。
所以,為了解決中國詩歌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補上建構這一課。欲速則不達,寄希望于跨越,寄希望于省去詩歌發展的這一必要環節,只會拖延解決問題的時間。因此,對建構的一切抵觸情緒,都是需要克服的。
三、說說所謂“現代詩”
我們的討論遇到的阻力,往往和所謂“現代詩”這個說法分不開。
如今許多人喜歡說“現代”。我寫的是“現代詩”呀,因此理所當然應該是當代的代表性詩歌呀——這是當前詩歌界一些人士的心態。
他們所說的“現代”指的是什么呢?是“現代的”詩歌(modern poetry),還是“現代主義的”詩歌(modernist poetry)?如果是前者,“現代”應該是指時間;如果是后者,應該是指一種詩歌潮流。這絕不能混淆。認為自己的現代主義作品就等于這段時間的所有作品或者這段時間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不正確的。除了詩歌界,當代其他文學領域的人士都不會這樣看問題。
“現代”(modern)一詞,理所當然應該是指時間。所以modern poetry這個說法,外國人會以為是指中國現代所有的詩歌作品。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現代的中國詩歌有各種流派,也有自由詩以外的其他形式(成長中的白話格律詩),還有白話以外其他語體的作品(文言詩)。
實際上,他們說“現代詩”,往往指現代主義詩歌。這里的所謂“現代”,明顯不是指時間。不然為什么又有“后現代”的說法?豈不是穿越到未來去了?而且,不是白話詩,不是現代主義作品,也是可以有現代性的。比如說,魯迅的文言詩就沒有現代性嗎?
由此可見,“現代詩”這個名詞,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提法,企圖以某個流派的作品暗暗取代整個時間段所有作品,包含著偷換概念的嚴重邏輯錯誤和詭辯手法。
“這個名詞已經用慣了!”“中國詩歌已經是這樣了!”——這是詩歌界某些人士用來抗拒批評的借口。他們用“習慣成自然”和“約定俗成”來為自己做擋箭牌。不錯,約定俗成在語言現象中是有的。但對于一個學科來說,正規的名詞術就不能這么隨便了。你搞錯了,就不許別人撥亂反正嗎?這不是什么約定俗成,而是指鹿為馬。你能把中國詩歌“發展”成什么樣子,別人就不能向別的方面發展發展嗎?你把外國人那本經念歪了,就不許別人按原樣兒念一念嗎?
在實踐中,“現代詩”這個名詞體現了一種唯我獨尊的派性。一些詩歌界人士容不得不同意見,動輒將不同觀點的討論視為零和游戲,根子正在于這種派性。他們忘了,包容,是這個多極化和多元化的世界所要求的;而絕對觀念和激化矛盾,都不符合當前的時代精神。
因此,如果把中國的白話詩歌改為“現代詩”這個似是而非的術語,詩歌作品的百花齊放和詩歌理論的百家爭鳴就難以實現。這不僅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而且是當前的現實問題。
除了片面強調創作的絕對自由,甚至還有人在出了一點名氣之后,認為讀者需要提高水平來理解他,或者認為不需要別人理解。這種作風,很難說是體現了現代主義精神的積極方面。
我在這里要不厭其煩地強調一點:“讀者”這個詞兒是什么意思?讀者就是人民!一個作者,對讀者是應該敬畏的。不尊重讀者,談什么文學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不是什么大帽子。
四、說說文明辯論
最后,我想談談關于討論(或辯論、論戰)本身的一點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多。要有探討真理的精神呀,不要將討論視為“零和游戲”呀,要將結論的取得視作雙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不是“誰打倒誰”呀,要尊重對方、尊重廣大的“旁觀者”(也就是讀者)呀……似乎都談過了。我特別想說的是:尊重對方,還表現在客觀地談問題。結論的得出,應該是在討論之后,而不是討論之前。應該承認討論的雙方都有可能在共同的結論中做出貢獻,也都可能會有需要修正的錯誤。
尊重對方,還表現在充分研究對方的論點、論據。如果不同意,應該提出來,并說明自己的看法。對別人文章中已經批評了的某種說法照用不誤,卻不談理由,就說明并沒有認真讀人家的文章。
人人都做文明人,反對語言暴力,尊重對方,特別是尊重少數,倡導善意和愛心,這代表了社會的精神面貌,也是符合現代精神的。因此我在這里說了這么多。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