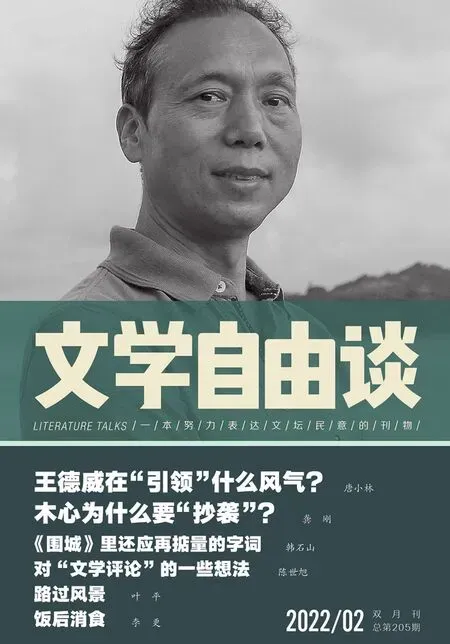筆名的尷尬與榮耀
□井 崗
一
談筆名之前,先講個用筆名取不出稿費的尷尬事。
稿費,對寫作者來說,是對辛苦勞動的獎賞,即使面額很小,觸手便感溫暖。疫情防控期間,出入小區大門,去商場超市,進公園休閑場所,甚至爬山活動一下筋骨,在入口處都要出示證件或實名登記。實名認證,對疫情管控無可厚非確有必要,但如郵政部門,拿著匯款單卻取不出辛苦費來,卻要當事者一趟趟地去有關部門“實名認證”,不知其他使用筆名的文友是否也遇到過同樣的尷尬處境?
最近我去取稿費,辦理匯兌的小姐姐和藹地說,你經常來取款,我也知道這是你的筆名,但新裝的電腦系統不認,匯單上姓井,你的身份證上姓張,取不了款。除非在匯款單沒有過期之前,去派出所開個證明,能表明筆名與身份證上的人名是同一個人才行。如此三番,每取一次稿費都要去開證明。幾次周折后,便時時提醒自己,在投稿時,除注明郵編地址聯系電話,最后特意寫上身份證上那個法定的名字。報刊雜志習慣了用筆名發表,這是尊重作者的署名權,寄稿費時卻常常順手寫上筆名。
按現行的稿費標準,一小筆稿費,就如一根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有時,數額較小的匯款單便作了書簽,算是對自己使用筆名的執拗與自信。當下依靠寫作維持生計甚至發家致富的,畢竟少數!更何況自己的寫作只是業余愛好,寫得稍稍滿意時心里必萌生一點小自豪小榮耀,也不在乎那幾個小錢,關鍵是找到了一個宣泄情感的出口。取個筆名,寫點小文,也是一種精神寄托。至于能否得到稿費,已不重要了。
二
中國文人取筆名,自古有之。古代文學大家的堂號、齋名、字號等實質上就起著筆名的作用,如青蓮居士、河東先生、東坡居士、易安居士、醉翁、放翁等。
筆名涵蓋的內容極其豐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筆名就如文人的潛水服,可以護佑文人寫出一些正常身份下不便寫出的文字。有些筆名就意味深長,比如那位《金瓶梅詞話》的作者,恐怕就是因為視小說為小道,且有些風月文字,羞于用真名發表引來非議,所以才小心署名“蘭陵笑笑生”。
筆名的使用,在中國近代逐漸增多。柳如是,明末清初的詩人,原名楊愛,是秦淮八艷之一,才藝雙全。楊愛在辛棄疾的《賀新郎》中讀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從此改名柳如是。
脂評《石頭記》中,常出現一個胭脂齋,這也應該算是個筆名吧,而且是個最懂《石頭記》的評論家。紅學家們對神秘的胭脂齋,是男是女說法不一,其身世確實撲朔迷離。
《老殘游記》署為“洪都百煉生”著,當為劉鶚的筆名。
以上可說是較早出現的一批筆名。其中重要一個原因是,“小說”在當時難登大雅之堂,取個筆名以隱身,免受方家譏笑。
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家對筆名的態度已有很大改觀,甚至有人慎之又慎,仔細斟酌,力求取出一個寓意豐富的筆名來。不過,絕大多數人卻抱著比較隨意的態度。畢竟,筆名的好壞與文章的高下關系不大。但也有不少筆名來歷非凡,耐人尋味,引人遐思。
現代文壇曾大興筆名之風,幾乎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筆名。有的多達十幾個乃至上百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文壇大家魯、郭、茅、巴、老、曹,他們最響亮的名字就是筆名。
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旗手,其筆名傳播和影響最為深遠。在用“魯迅”這一名字之前,他曾有過阿張、周樟壽、豫山、周樹人等名字。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首次使用筆名“魯迅”。這個廣為人知的筆名,“魯”是他母親的姓氏,取“魯”在于紀念感懷母親養育教誨之恩,“迅”原是他幼時乳名,又含迅捷進取之意,表明他誓與反動腐朽的舊時代徹底決裂,積極進取的鴻鵠之志。魯迅先后使用的筆名共計一百八十一個,二字筆名有一百一十六個,三字筆名有三十七個,四字筆名有五個,五字筆名有七個,六字筆名有一個。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號尚武。他的筆名、化名很多,有郭鼎堂、麥克昂、羊易之、楊伯勉、白圭等,而用得最多的是“郭沫若”。因為他家鄉四川樂山的兩條河,一條是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條是若水,他少年時飲二水長大,所以他后來發表新詩時,就用了“沫若”這一筆名。
茅盾原名沈德鴻,字雁冰。他用過的筆名除茅盾外,還有郎損、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當然“茅盾”影響最大。取這個筆名起因于內心的矛盾和思想沖突。1927年大革命失敗,沈雁冰被迫隱居上海,郁郁不得志的他開始用筆來宣泄心中的情感,于是創作了小說《幻滅》。小說完成后投稿給多家報社卻不用,這使得他內心十分矛盾,于是他在手稿上署名“矛盾”。稿子最后交給了《小說月報》的編輯葉圣陶,葉圣陶認為小說很好,但是看到這個名字覺得欠妥,并提出修改意見,認為這個名字是個哲學名詞,不像一個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尤其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使用如此尖銳的筆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張在“矛”字上加了一個草字頭,改作“茅盾”。沈雁冰對這一改動也很滿意,此后就常用這個筆名發表作品。
巴金原名李堯棠,在法國留學時,他有一個姓巴的友人自殺了。為了懷念這位友人便以“巴”作姓,“金”字則是《倫理學》作者克魯泡特金的最后一個字,于是“巴金”這筆名就誕生了。他寫成小說《滅亡》發表時正式使用筆名巴金。他著作等身,是二十世紀中國杰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現代文壇巨匠。
老舍先生原名舒慶春。他把“舒”字拆成“舍”“予”兩字,取名“舒舍予”,后來干脆叫起“老舍”來。之所以這樣,是習慣于北方的朋友會面時親熱的叫法,如“老王”、“老馬”等。另外,又有舍己為人、奮發勵志、“舍我其誰”之意。
劇作家曹禺原名萬家寶,有人問起他的筆名有何含義?他回答說:“我姓萬(繁體字萬)。這個‘萬’字草字頭下是一個禺。寫文章總得有個筆名,我便將‘萬’字拆為‘草禺’,但‘草’不像一個姓,就取其諧音曹。”
三
筆名畢竟是文人的小把戲、小愛好,有自己獨特的情調,文化氣息較重,而這又大都與作者的教養學識有關。尤其受到中國古典詩詞的濡染,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心儀的字眼兒,隨手拈來,用作筆名的不在少數。聞名已久的如張恨水、戴望舒、冰心、瓊瑤等。
張恨水原名張心遠,“恨水”一名是他十七歲那年,在蘇州第一次投稿時取的筆名,是從南唐后主李煜《相見歡》詞“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東去”中截取出來的。張恨水幼年酷愛詞章,讀了李后主這首詞,想到人生有限,不能讓光陰如流水一樣白白流逝,就取了這個獨特的筆名。
戴望舒原名戴朝宗。筆名“望舒”取自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望舒,即神話中驅月駕車的神,后成為月的代稱。月在古詩詞中可作為愛情的象征,戴望舒詩歌的朦朧婉約與月光的朦朧相吻合,筆名暗示了詩人的詩歌內容和詩風。
冰心原名謝婉瑩。她小時候就接觸中國古典文字,特別喜歡唐詩。她對唐代詩人王昌齡作的《芙蓉樓送辛漸》一詩特別欣賞,對“一片冰心在玉壺”情有獨鐘,遂取“冰心”為筆名。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在《新晚報》副刊發表“新派武俠小說”時,一時想不出用什么筆名,后索性把名字最后一個字分為兩半,從此“金庸”的筆名風靡香港。
瓊瑤本名陳喆,筆名出自《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這是一首甜美的愛情詩,筆名正是瓊瑤言情作家身份的絕好體現。除瓊瑤外,她還曾用過鳳凰、心如。
三毛本名陳平,她起初使用這個筆名,是因為這個名字很不起眼,另有一個原因是自謙作品一般,只值三毛錢。她婚后定居西屬撒哈拉加那利群島,并以當地的生活為背景,寫出一連串膾炙人口的作品。
四
中國人有筆名,外國人也有筆名。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原名是塞莫爾·朗菏恩·克萊門斯。他取筆名馬克·吐溫,是為了懷念青少年時期在密西西比河上做水手和領航員的一段生活經歷,那時他經常聽到測水員的叫喊聲:“水深兩噚(MARK TWO等于六英尺),航船可以小心通過。”“馬克·吐溫”就是這個意思。
歐·亨利這個筆名來自一家酒吧老板的“呼名”。他經常到這家酒館喝酒,有一天他請兩位記者來這里做客,大聲招呼道:“歐·亨利,再來一杯!”接著詢問兩位記者:“我寫了一篇小說,不想用真名發表,你們看用什么筆名好呢?”他剛才招呼“歐·亨利”的叫聲因為與眾不同,引起了其中一位記者的好奇。這位記者開玩笑說:“你剛才喊叫的‘歐·亨利’不是很好嗎?”結果,他竟把這玩笑當真,在小說上簽上了“歐·亨利”作為筆名。小說發表后,就一直沿用這個筆名。歐·亨利的真名是威廉·雪德雷·波特。
蘇聯作家高爾基的原名是阿歷克塞·瑪克西姆維奇·彼什柯夫。看高爾基創作的自傳體小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可以得知,作者的筆名是為了永志苦難艱辛的生活歷程。“高爾基”在俄文中有“痛苦”的意思。那他又為何取這個名字呢?原來他從小父母雙亡,讀了兩年書就開始在社會上謀生了,遭受了很多的人間苦難,為了紀念自己的經歷,所以取了“高爾基”這個筆名。
司湯達是法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小說《紅與黑》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原名是亨利·貝爾,“司湯達”本是普魯士的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的名字,作者很喜愛這個獨具特色的小村莊,便以此為筆名,首次署于1817年出版的《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著作中。
五
筆名主要用于作品的署名,每個人的文化背景、出身經歷、文化素養、心理特質以及其他種種個人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筆名的啟用。
當今文壇也有一些影響力比較大的筆名,如莫言,原名為管謨業。用莫言自己的話說,他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孩子,在農村叫做“炮孩子”。莫言因為喜歡說話,喜歡說真話,給家里帶來了很多麻煩。所以過了幾十年以后,當莫言要寫小說準備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叫“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
進入本世紀后,一批新銳作家脫穎而出,也受到網絡的巨大推力,一批極具個性的筆名應運而生,如唐家三少,幾乎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原名張威了。像安妮寶貝、當年明月、十年砍柴、天蠶土豆、淺羽薰、南宮莫塵、薇珞等筆名亦可以理解為網名,不過其作者的真實意圖與筆名相同,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后宮·甄嬛傳》的作者流瀲紫,是一名叫吳雪嵐的小學教師。她的筆名取得更隨緣,據說她寫小說時正在使用一款叫流瀲紫的化妝品,于是就有了這個特別隨意的筆名,但并不影響她對作品的高品質要求。
現在是網絡時代,取個網名、微信名如家常便飯。有的大神級網絡作家如辰東(楊振東)、貓膩(曉峰)、柳下揮(黃衛)、我吃西紅柿(朱洪志)、天蠶土豆(李虎)、憤怒的香蕉(曾登科)、烽火戲諸侯(陳政華)、夢入神機(王鐘)、月關(魏立軍)、耳根(劉勇)、血紅(劉煒)、蝴蝶藍(王冬)、煙雨江南(丘曉華)、魚人二代(林晗)、隕落星辰(徐靖杰)、鴻蒙樹(王斌)等,都穿著“馬甲”,神秘莫測,倒更像是一些有趣的物件,或幾名食客、幾只鳥蟲,或一抹色彩一道光影幾縷思緒。有的甚至如今還處在潛水狀態,尚且不以真面目示人,如風凌天下、純情犀利哥、愛潛水的烏賊等,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作品已經風靡網絡,本尊卻神出鬼沒。
這種隱身寫作,為作者本人解除了很多顧忌。既然作家不想透露真實姓名,那就由他去吧,我們能吃上雞蛋,就不必追問那只下蛋的雞是誰了。
如今,隨著社會環境的改善,寫作發表的多元選擇,筆名已非寫作的必要條件。不過,筆名在文化圈中,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筆名使用中的尷尬狀況畢竟占少數,帶來更多的是精神榮耀與文化自信。隱去真實姓名所署的別名(筆名或網名),并非全是初始寫作者不自信的代名詞,它往往寄托了寫作者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境界,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值得大家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