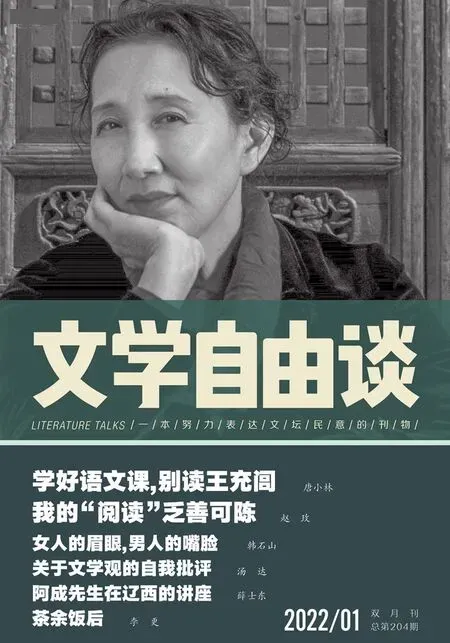文學場域:從教堂到賣場
□朱斌峰
2014年諾獎獲得者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曾發出這樣的詰問:“為何舊時代的文學家們能夠建立起那種類似天主教教堂一樣宏偉壯麗的文學大廈,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問世?”——在我看來,這個發問對作家的要求有些苛責了。當文字從金石、磚瓦變成松散的沙子后,當下作家要從時代語境中超拔出來,用文字堆起沙塔,談何容易!
目光穿過歷史云煙,我們不難看出文字一步步祛魅,從祭壇走向煙火人間:從刻在龜甲殼上的占卜禱詞、鐫在青銅器上的記功鑄史,到印刷術彌漫的油墨,再到網絡時代的爽文,文字的質地越來越松軟了——仿佛是天上的星星變成隕石落入人間,又由鐵和瓷變成了鹽和沙——無論多么高妙的建筑師,想用鹽和沙作為材料建造起宏偉壯麗的大廈,都是紙上談兵吧?而文學存在的場域從莊嚴肅穆的廟堂、教堂走向熙熙攘攘的劇場和賣場,作家的角色也隨之從大祭師、書記官、說書人嬗變為消費品制造商,來不及“華麗轉身”便陷入了尷尬的窘境甚至困境——畢竟他們不是能拎著自己頭發跳舞的人。
面對時代的流變,作家或許只能有兩種姿勢:后撤堅守和隨波逐流,除此無處遁身。
起初的文學高居于神殿和教堂,那是靈魂與上神、靈魂和靈魂對話的場所,是用神性與博愛等精神條石構筑的場域。
神話是文學的母體,見證了初民對宇宙萬物的敬畏和創世的想象,隨后的古希臘悲劇對英雄傳說時代充滿著懷想。文藝復興以降,雖然人本主義開始抬頭,但文學并沒有立刻放棄載道傳統,一批批文學的傳教士和苦修者仍居住在教堂里,悲天憫人,度人度己。英國意識流小說家伍爾夫在《現代小說》中說:“在每一個偉大的俄國作家身上,我們都仿佛看到了圣徒的特征——如果對于他人苦難的同情,對于他人的愛,以及為了達到某種要對人的精神進行嚴酷考驗的目標而奮斗,即構成為圣徒性格的話,那么正是他們的這種圣徒精神使我們感到惶惑,覺得我們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淺薄無聊”……這樣的作家顯然是在建筑宏大敘事的樓宇,并在穹頂上高懸著兩件東西:“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標準,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康德)
到了二十世紀,尤其是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時期,文學的神殿開始瓦解,但堅守者仍不乏其人。加西亞·馬爾克斯以《百年孤獨》逆歷史潮流而動,演繹了一部經典神話:從馬孔多的創立和布恩蒂亞家族的繁衍,到洪水和世界末日的降臨,神和人相生相克、人和鬼相濡以沫,小鎮和家族的命運與《圣經》之類的古老神話、英雄傳說時代的神奇故事互文,一如古希臘悲劇《奧狄浦斯王》所昭示的那樣,以“上神天諭——逃避命運——預言靈驗”,構建了拉丁美洲民族乃至整個美洲的宏偉寓言。而在當下的中國新疆,劉亮程也在回望著神跡。他在《散文之散》中說:中國人很早就建立了觀察和表達萬物的體系,《詩經》中就有三百多種動植物,在給它們命名的同時把它們喚醒,讓萬物回到人類關注的視野。天上有神靈有耳朵,散文就是向上表達,就是對萬物言說,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我們最早的詩歌就是巫師的祈禱詞,也是朝天上說的,朝天地間的萬物說的,那聲音朝上走,天聽過了落回來又被人聽到。因而,對天地說話,與天地精神獨往來,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隱秘傳統。
與神靈對話,在教堂寫作,這樣的文學姿態往往與懺悔、拯救有關。
從教堂走出后,有人就流離失所了。
二十世紀奧地利小說家弗朗茨·卡夫卡,或許是個被神拒絕的人。他的小說《城堡》說的是土地測量員K為進入城堡而徒然努力的事兒,是“迷宮似的令人暈頭轉向的小說”。這個“城堡”未必不是神殿的象征,K尋找城堡入口,卻得不到神的恩典,不能進入城堡而成了局外人。他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孤立、異化而絕望,對社會的陌生感、孤獨感與恐懼感成了他書寫的永恒主題:《變形記》中,沉重的肉體和精神的壓迫,使人失去了自我的本質,異化為非人;《饑餓藝術家》中,絕食表演者被關在鐵籠內進行表演,時間長達四十天,表演結束時已經骨瘦如柴不能支撐起自己,又被馬戲團聘去關進籠子,放在離獸場很近的道口,讓游客觀看野獸時能順便看到他。可是人們忘了更換記日牌,絕食者無限期地絕食下去,終于餓死;而在《萬里長城建造時》中,龐大工程與帝國機構同構,傳遞諭令的使者一直奮力穿越在內宮的殿堂里而不得出。如果說建造長城是設圍,那么傳遞諭令則是突圍,兩者之間形成的悖論式的糾纏讓人無所適從——也許“城堡”和“迷宮”是同構物,“不得入”和“不得出”均指向同一種精神上的困境。
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也有屬于他的《長城》,小說以戍邊明將宋督察與蒙古蠻夷勇士庫特盧克兩個視角,分別對中國長城進行了獨白式的思索——那是疆土與心理的對峙。最后來自明朝廷教坊司的人卻揭示了長城修復的真相:“中國修建長城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游牧部落的侵襲,但是已經過去這么久了……如今我們就處在這樣的時候,蠻夷懼怕天朝,那就是他們堅決要求重修長城的原因……它的宮殿,它那里的女人,它那里的絲綢。在他們(蠻夷)的眼里,那所有的一切都意味著死亡”——卡達萊的“長城”是不是也是一種歷史、文化和心理上的“迷宮”?
而阿根廷作家豪·路·博爾赫斯,就走進了“迷宮”。他以超于常人的視野,從希臘文學、希伯來文學、中世紀哲學、東方佛教道教典籍、巫術星相等龐大駁雜的體系中,提煉出自己對于宇宙、生命本質的理解,讓象征著時間的《小徑分岔的花園》成了作家離開教堂后的棲身之處。他不斷地編織一個又一個精巧、詭異、無盡的迷宮——關于自我、空間、時間的困惑。
用文字構筑的“迷宮”里有著歷史、人性的秘密,而作家在這樣的文學場域中或許只是猜謎者。
從教堂走向市井,街頭就成了劇場。
劇場作為人跟人交流的場所,是回歸世俗后的作家的棲身地。此時文學中的人物完成了從神祗、英雄到凡人的“矮化”過程,作家進入日常生活領域,成為可觸可感的平常人乃至畸零人。極簡主義者雷蒙德·卡佛的小說《大教堂》中,主人公的妻子多年一直與盲人朋友保持著聯系。這天盲人朋友前來拜訪,主人公心懷敵意和鄙夷,后又放下內心的抵觸,在盲人的指觸下閉上眼感覺起大教堂——這是在書寫人們內心冷漠的陷阱,還是救贖的殿堂?有人說,卡佛善于從生活瑣事中展現人物內心的細微變化,一段無頭緒的對話都被賦予了特定的意義。也有人說,卡佛用普通但準確的語言寫普通事物,卻賦予它們廣闊而驚人的力量。還有人說,卡佛的作品中隱藏著超越日常的奇妙意外、讓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現實感——而他的極簡主義,絕不僅僅是一個修辭上的簡化,而是表達在人的真實生活處境中,存在著巨大的沉默,一種包藏著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傷痛的沉默——這樣的“大教堂”是怎樣的教堂呢?
在劇場,作家以平民的姿態,尋找著生活中自己的影子。
文學走進賣場,成為一場場虛擬的游戲,不知是淪落還是高蹈。
或許當下時代有了“新神”:電影《美國眾神》中,各民族的人們移民來到美國,帶來了各自的神祗,但是這些舊神正日漸衰落。隨著新型信仰的確立,一些新神如媒體女神、高科技小子日漸壯大,引發了一場新舊兩神的爭斗——這是關于時代之“神”的寓言。從事大眾傳媒研究的學者戴錦華,在《數碼轉型時代的文化與社會》中說:我們正置身于現代文明轉型臨界點的大時代,數碼轉型和生物科技革命沖擊了人類的知識生產和接受方式,改變了人類社會生態。2012年奧斯卡頒獎儀式上有一個不可見的變化,頒獎典禮上最重要的角色——柯達膠片公司破產了,這標志著“數碼轉型”。這對電影行業的沖擊非常直接,那就是膠片死亡,電影正在死亡。如果說以前“電影院在取代教堂”,那么當下的虛擬電影院正在取代著實體電影院,這意味著人們社群關系將被改變。電影是公眾空間的藝術,數碼技術讓人類擁有了虛擬的生活,讓我們進入了充滿幻象、有圖沒有真相的時代。
反觀文學場域,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文學的需求、創作方式、傳播方式和消費方式。當下文學閱讀已陷入危機,人們對紙質書的閱讀量逐年減少,閱讀方式正在網絡化,閱讀耐心正被鋪天蓋地的信息消殆。文學閱讀需要品味,需要對細微的、深層的東西進行體悟,但是電子刷屏追求的是一目十行的速度,這必然會忽略文學最為深層和本質的東西。因此,這種閱讀危機必然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文學審美能力和文學判斷能力的下降。可就在此時,一種名叫劇本殺的社交聚會類游戲,正在年輕人之間風行,玩家拿到各自的劇本后,就能扮演特定角色,通過與其他玩家的交流、推理,還原出故事的全貌和真相——當然那未必是文學的真相,而更像是海市蜃樓。
我只是有些擔心:在這種消費式的文學場域中,作家是否會成為販賣致幻劑的老板?
我相信過:文學是紙上的建筑群,是精神的避難所。
我不知道:文學場域從教堂到賣場,是人性的勝利,還是流俗的狂歡。
當下的文學,不是我們在建構著世界,而是我們被世界虛擬著,文字暗淡而又喧囂。美國的馬爾科姆·考利在《流放者歸來》中說:“這是一個輕松、極速、冒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度過青春歲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這個時代卻讓人感到欣慰,就像從一間人擠的太多、講話聲音太嘈雜的房間里走出來到冬日街道上的陽光中一樣”——我想從這個時代偷偷跑出去,像大江健三郎那樣做一個“跑來給你報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