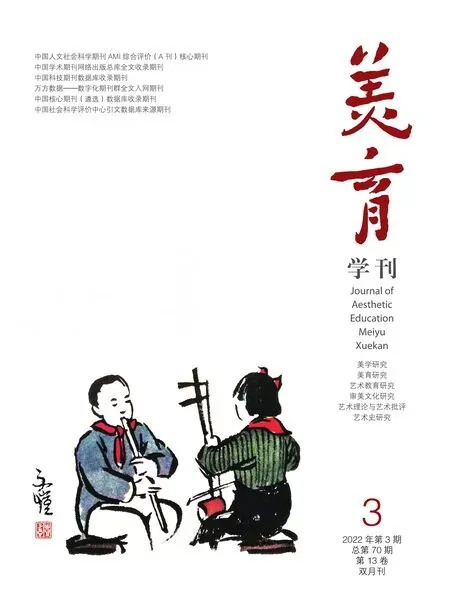中國20世紀現代派美術的美學探索與論爭
楊向榮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關于現代藝術的美學探索與建構是20世紀中國美學史建構的重要一維。這里的“現代”并不是傳統意義上作為歷史分期的時間概念,“現代藝術”亦不同于20世紀流行于歐美的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流派,而是一個概括中國現代藝術發展情境的概念,特指這一時期探索和學習國外現代藝術的藝術家群體創作的藝術。具體而言,是指20世紀上半葉一批受西方現代美學思潮和先鋒藝術探索精神影響的藝術家,在創作中融合西方現代美學和藝術觀,并自覺進行本土化的轉換吸收。中國現代藝術家群體的創作涵蓋了文學、戲劇、電影、美術和音樂等各種藝術形式,雖然創作主體多元,創作類型多樣,且具有不同的美學和藝術探索方向,但總體上是在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基礎上對西方現代美學思潮和先鋒藝術理念的借鑒。
在中國現代派藝術家群體中,隨著西方美術繪畫理論的引入,美術家群體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們在傳統美術思想與外來思潮的影響下探索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劉海粟提倡在發展東方藝術的同時研究西方藝術。林風眠偏愛中國古典素材,同時對西方表現主義、象征派藝術手法等相當熟稔,呈現出強烈的現代先鋒探索意識。徐悲鴻向西洋畫學習,融合東西方繪畫技藝和審美實踐。鄧以蟄以黑格爾美學思想為基礎,在書畫藝術中探索形式和意境的關系。李叔同吸收西洋技法,同時堅守中國繪畫傳統。豐子愷以超越功利的審美心態去觀照審美對象。潘天壽堅持藝術的獨立性,認為獨特的風格是保持藝術審美價值的關鍵。上述藝術家通過對西方繪畫藝術的考察與反思,對比東西方美術差異,進而探索中國現代繪畫藝術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現代性探索意義。在對中國現代美術的美學探索中,一部分藝術家主張將東西方的繪畫理論和技藝結合起來,引進西方現代美術思想來改革中國美術;另一部分藝術家雖然也受到西方現代美術思想的影響,但更多致力于傳統美術基礎上的創新。這兩部分藝術家都受到了西方現代前衛美術思想的影響,只是受影響的程度不同罷了。
一、革新派的美學探索
在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中,一直存在著革新派與傳統派的論爭。革新派看到西洋畫法的先進性,認可西方美術技法,主張接受西方美術思想,將東西方藝術融合起來,創造出符合時代發展的新美術藝術,如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和鄧以蟄等藝術家都提倡東西方美術的融合。
劉海粟是中國近代美術教育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是提倡中國新美術的開山之人。在美術思想上,劉海粟提倡發展東方藝術,研究西方藝術。劉海粟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正規的美術學府——上海圖畫美術院,反對束縛藝術個性,認為青年學生應實現思想上的解放。劉海粟以超越常人的勇氣和力量去深刻考察中國和西方的繪畫藝術,他對東西方的繪畫潮流有著深刻的研究。在《國畫苑》中,劉海粟認為:“故近數十年來,雖西學東漸之潮流日甚,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藝術上亦開始容納外來情調,惟無鑒別、無抉發,本末不具,派別不明,一味妄從,故少新機運。愚生于此種‘藝術饑荒’之時代,其思苦索,發愿一面盡力發掘吾國藝術史固有之寶藏,一面盡量吸收外來之新藝術,所以轉旋歷史之機運,冀將來拓一新局面。”如何對待東西方藝術,劉海粟提倡“窮古今東西各派名家之畫,而又努力沖決其樊籬,將一切樊籬沖決矣”。他一方面認為要發掘本國藝術的精華;另一方面也強調借鑒吸收西方現代前衛藝術經驗,將東西方繪畫藝術融合起來。
劉海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女性人體模特的人。在當時的藝術家眼中,人的身體是不可向外人展示的。1920年7月20日,劉海粟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人體畫室,他對真善美的追求都反映在他對人體的喜愛上。在他看來,只有人體的美感才能真正體現形式與內容上美的一致。劉海粟看到了人體之美,強調人體的張力美和生命力。在他看來,人體創造了生命,也能體現美的真正意義所在。人體模特的出現可以引導國人高尚純真的人格,并從中感悟出美好的事物從而達到自我救亡的目的。但當時國人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不能完全接受人體模特,而劉海粟對人體美的追求也引起了社會的爭議,并長達十年之久。
劉海粟追求人體美,其主要目的在于推進當時美術教育的革新。劉海粟一生都在為美術教育而奮斗,他認為真正的審美趣味是在寫生中不斷發現美的事物,強調在表現日常生活時要加入自己的主觀情感。可以說,劉海粟對美的追求、理解和感悟,推動了中國美術的進步。此外,劉海粟對待東西方美術文化,而是不是簡單地拋棄其中一種而選擇另外一種,他將東西方藝術的精華結合起來,將國畫和西洋畫的研究結合起來。劉海粟看到了西方美術的審美價值,主張吸收外來精髓為之所用。他將東西方藝術思想融會貫通,具有強烈的革新性。
與劉海粟一樣,林風眠也深受西方現代藝術思想的影響。林風眠在歐洲留學時受到西方繪畫藝術的熏陶和影響,并因此確立了自己的藝術發展方向。留學期間,林風眠將中西繪畫理論結合在一起,呈現出既有中國畫特色,又有西方繪畫風格的藝術新風格。在北京國立藝專和杭州國立藝專任校長時,林風眠在探索西方現代藝術經驗時大力提倡新美術思想,推動藝術運動和藝術教育。林風眠有著較為自覺的現代性意識,主張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經驗來促進和發展中國現代新美術。他強調藝術創作中的自由精神,主張在中西藝術精神相互溝通的前提下,建構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國新藝術。在林風眠看來,繪畫藝術并沒有中西之分,只要回歸到繪畫本身,就是真正的藝術。林風眠不僅強調技藝上的進步,也強調藝術需突顯其審美本質。在他看來,要了解藝術品傳達出來的情感,必須有豐富的主觀情感投入,而不能是單純的技藝提升,美術改革并不要“無為”的藝術。
林風眠關注藝術情感,他的藝術表現形式更接近于凡·高和蒙克。在林風眠的藝術作品中,他注重自我情感的表現:“中國現代藝術,因構成之方法不發達,結果不能自由表現其情緒上之希求;因此當極力輸入西方之所長,而期形式上之發達,調和吾人內部情緒上的需求,而實現中國藝術之復興。”林風眠具有強烈的藝術先鋒意識,他在創作材料上不斷創新,大膽運用新型材料,在中國畫創作中不再局限于水墨與丹青,而加入了節奏、風格等西方元素和藝術形式。他反思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試圖融合西方現代藝術風格來調和中國現代藝術。
林風眠受西方象征派藝術的影響較大,他采用象征化的形象語言,通過美與丑的沖突,彰顯崇高的審美意象。在《人道》《人類的痛苦》《死》《悲哀》等作品中,這種傾向尤為明顯。《人類的痛苦》擠滿了受苦受難的人體,“從正、背、站、俯、仰、欹、側各個角度,表現出各種內心強烈痛苦的情狀。色彩以灰黑為主,有的女人體作了綠色”。林風眠選擇一系列怪誕詭異的意象,通過美和丑的對比與沖突,揭露殘酷的社會現實,表現內心的痛苦情緒。林風眠在繪畫藝術中表現出的“以丑為美”和李金發詩歌創作中的“以丑為美”有著共通的性質。二者的題材來源均是生活中的殘酷和黑暗面。這種看似反叛的美學觀,實際是作者對現實的揭露和反抗。在林風眠看來,表現丑陋并不是最終目的,而是通過丑所帶來的反差,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進而讓人們去追求美和善。
林風眠的作品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他在創作中將西方現代藝術元素,與陶瓷、壁畫、皮影、剪紙、戲曲等中國傳統藝術融合在一起,豐富了中國現代派藝術的創作風格,如潘公凱所言,林風眠“流連于中國銅器、漆器、漢磚、皮影、剪紙、磁州窯、壁畫、青花瓷之間,在豐富的形式因素中尋覓表現符號,同時糅進塞尚式的風景、馬蒂斯式的背景、莫迪里阿尼式的人體、畢加索式的立體分割處理”。林風眠對美術的責任感使他在繪畫表現形式上不斷創新,他的藝術實踐也為中國畫的發展引領了新的方向。
林風眠對中國美術所作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創新,不斷嘗試新的元素和材料來豐富中國美術。在他看來,美術改革始終要回到繪畫本身中去,繪畫作品不僅要表達創作者的主觀思想,也要體現出繪畫本身的審美性。林風眠一生致力于美術教育事業的發展,他用畫家之眼傳遞審美,在西方繪畫與中國傳統藝術的結合道路上開創了新的方向。趙無極、吳冠中、朱德群等一大批藝術家,正是沿著林風眠開創的現代派藝術風格,在中西融合的基礎上致力于民族繪畫的探索和創新。
徐悲鴻受過系統的西方繪畫藝術訓練,他主張融合東西方藝術,既吸收中國傳統畫的精髓和精神,也學習西方繪畫的科學技法。徐悲鴻認為中國畫和西方畫均是文明的產物,具有各自的價值,但由于中國畫技藝逐漸衰敗,因此向西洋畫學習,融合東西方技藝是很有必要的。徐悲鴻倡導寫實,認為藝術與生活有密切關聯。藝術要以生活為題材,不能脫離生活而存在。徐悲鴻認為應該仔細觀察自然,觀察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神態。在談到中國近代藝術時,徐悲鴻說:“從古昔到現在我國畫家都忽略了表現生活的描寫,只專注意山水、人物、鳥獸、花卉等,抽象理想,或模仿古人的作品,只是專講唯美主義。當然藝術最重要的原質是美,可是不能單獨講求美而忽略了真和善,這恐怕是中國藝術界犯的通病吧。……要把藝術推廣到大眾里去。”在徐悲鴻眼中,藝術不是簡單地摹仿生活的外部形態,更應當表現生活的內在精神。藝術應該是大眾的藝術,藝術要進入大眾,就得表現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縮小藝術與大眾的距離,體現大眾的美好精神品質。
雖然強調藝術的寫實性,但徐悲鴻也認為,過于強調真實也會使繪畫作品喪失美感,不符合自然境界。“吾所謂藝者,乃盡人力使造物無遁形;吾所謂美者,乃以最敏之感覺支配,增減,創造一自然境界,憑藝以傳出之。藝可不借美而立(如寫風俗、寫像之逼真者)。美必不可離藝而存。藝僅足供人參考,而美方足令人耽玩也。”在徐悲鴻眼里,美不能離開藝而單獨存在,美和藝要達到一定的和諧與平衡。美離不開藝,美和藝結合,才能達到藝術的最高境界。基于寫實的美學觀,徐悲鴻提倡要改良中國畫。“畫之目的,曰‘惟妙惟肖’,妙屬于美,肖屬于藝。故作物必須憑實寫,乃能惟肖。待心手相應之時,或無須憑實寫,而下筆未嘗違背真實景象,易以渾和生動逸雅之神致,而構成造化。偶然一現之新景象,乃至惟妙。然肖或不妙,未有妙而不肖者也(前曾作《美與藝》可參閱之)。妙之不肖者,乃至肖者也。故妙之肖為尤難。故學畫者,宜屏棄妙襲古人之惡習(非謂盡棄其法),一一按現世已發明之術。則以規模真景物,形有不盡,色有不盡,態有不盡,趣有不盡,均深究之。”在徐悲鴻看來,繪畫要達到惟妙惟肖的效果,既要呈現出美感,又要表現出藝術真實。一方面,作為繪畫藝術的摹仿要以客觀自然為表現對象,而惟妙惟肖和摹仿說均要求藝術品與原物有一定的相似性,只不過惟妙惟肖更注重神態表現上的形神兼備;另一方面,藝術內在的審美屬性也不可少,藝術品應當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
除了寫實性,徐悲鴻的繪畫還體現出很強的時代性風格。徐悲鴻擅長采用顏色拼接,并通過對色塊的層次過渡來突破中國畫的固有表現形態和豐富中國畫的表現內容。徐悲鴻提倡美術改革,認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歐洲之寫實主義”,“美術應以寫實主義為主,雖然不一定為最后目的,但必須用寫實主義為出發點”。徐悲鴻是學院派寫實主義的捍衛者,在他的作品中不僅能看到他的寫實功底,還可以看到畫中形象所要表達的意境。他的作品并不是純粹技法上的追求,而寄寓著那個時代的精神追求。
徐悲鴻對真善美的要求是源于他對社會和時代的責任感,以及對繪畫和美術教育的熱愛。徐悲鴻追求真,追求寫實主義,但并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簡單拷貝和復制,而是強調形神兼備,強調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徐悲鴻對中國畫的改良做了很多貢獻,他不僅將寫實主義與中國現有的繪畫技法相結合,還在創作題材上加入了現實問題,把美術和革命真正融合在一起。潘公凱曾評價說:“徐悲鴻推出新七法作為其改良中國畫的具體方法,并意欲取代謝赫六法。這七法為:一、位置得宜;二、比例正確;三、黑白分明;四、動態天然;五、輕重和諧;六、性格畢現;七、傳神阿堵。新七法立足于西方古典造型系統的基本功訓練法,徐悲鴻視其為培養健全之畫家,尤其是健全之中國畫家的準繩。”可以說,“新七法”在今天的美術教育中仍有著廣泛的適用性。
徐悲鴻是中國現代藝術的先鋒探索者,他改良中國畫,不僅用西方寫實畫法進行創作,同時在細節上保留了中國畫中工筆畫的邊線和構圖留白。在徐悲鴻大量的素描作品和油畫作品中,都能發現中國畫的筆墨韻味。徐悲鴻主張從西方繪畫藝術中汲取養分,用一種科學寫生和寫實的方式,拯救中國早已衰落的繪畫藝術。在他看來,國畫只有在保留舊的形式的同時加入新的精神,才會彰顯時代性和民族性。
在力主革新的現代美術家當中,還有一個人的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鄧以蟄。鄧以蟄早年留學日本和美國,其代表作有《藝術家的難關》《書法之欣賞》和《畫理探微》等。鄧以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擁護者和新藝術思想的傳播者,他受黑格爾影響較大,同時對中國傳統書畫美學也有深入研究。《藝術家的難關》以黑格爾的美學思想為基礎。在鄧以蟄看來,藝術家的難關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他肯定藝術存在的價值,認為藝術有一種力量,這股力量能夠讓人超脫自然,獲得圓滿安寧的心境,藝術并非像柏拉圖所說的只是自然的影子。鄧以蟄認為,藝術只有攻克這一被誤解的難關,為藝術的真實身份正名,才能有良性的發展。
在鄧以蟄看來,藝術與人生的關系很近,藝術很容易與生活混淆,從而使藝術的表現力受到影響。藝術家要竭盡全力去對抗生活中的常規和習慣,創造出有特色的藝術,“藝術正要與一般人的舒服暢快的感覺相對筑壘的呢!它的先鋒隊,就是繪畫與雕刻(音樂有時也靠近),因為這兩種藝術最易得同人類的舒服暢快的感覺與膚泛平庸的知識交綏的。……但是人事上的情理,放乎四海而皆準的知識,百世而不移的本能,都是一切藝術的共同的敵陣,也就是藝術家誓必沖過的難關”。鄧以蟄認為,有的藝術有很高的造詣,但是因為沒能引起情感的愉悅,價值因而被抹殺掉。因此,藝術的價值不能簡單按照這個標準去評判,這是藝術家需要攻克的難題。藝術家如果被情理和本能包圍,便會陷入生活的藩籬,不自覺地去表現本能性的事物,因而缺乏創造性。
鄧以蟄集中研究了書體和書法,認為書體可以歸納為形式和意境兩種。鄧以蟄發現,魏晉之時,承載書法的工具主要為紙墨,書法進入了美術領域,講求入神。在他看來,飄逸的行草書體是書法形式意境美的代表。在論及書體的意境時,鄧以蟄認為“意境出自性靈,美為性靈之表現,若除卻介在之憑借,則意境美為表現之最直接者。……擺脫一切拘束,憑借,保得天真,然后下筆;使其人俗也則其書必俗,使其人去俗已盡則其書必韻。書者如也,至此乃可謂真如”。在鄧以蟄看來,意境來源于人的性靈,是性情和心靈之物的結晶,美即是性靈之物外化的結果。藝術品和人本身有很大的相連,創作者的人品和藝術作品的風格有著內在一致性。在他看來,風格即人,一個俗人是難以創作出高雅的作品的。
鄧以蟄認為,書法的形式和意境不可分離。書法不僅需要具備字的形式,還需要一種美的成分,即所謂的意境。“意境亦必托形式以顯。意境美之書體至草書而極;然草書若無篆筆之筋骨,八分之波勢,飛白之輕散,真書之八法,諸種已成之形式導之于前,則不能使之達于運轉自如,變化無方之境界,亦無疑也。故曰,形式與意境,自書法言之,乃不能分開也。”在鄧以蟄眼里,書法是意境和形式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的表現需要一定的形式作為載體,如草書的飄逸變幻就能將書法的意境闡釋得淋漓盡致。
“氣韻生動”最早出現在南朝畫家謝赫的《古畫品錄》中。所謂“氣韻”,不僅表現出人的精神面貌和品格,還同外部的環境息息相關,關涉宇宙的元氣以及藝術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鄧以蟄從藝術發展的角度考察“氣韻生動”,論述了“氣韻生動”與藝術的關系及其哲理價值。鄧以蟄認為,心本來是沒有形跡的,胸襟、意境、詩意等通過一定方式表現出來,即氣韻或者神韻。神韻來源于生動,沒有生動的描寫,神韻便難以表現出來,“生動”將本是無形跡的事物在繪畫藝術中體現出來。“神韻出于生動……生動尚有形跡可狀,神韻在心,無形跡可狀也。然形跡非全為有生動者,如無生命之圖案花紋或初唐以前之山水畫;生動亦非全有神韻,如僅得禽獸飛動之形似者。但形跡既可有生動,則生動亦可有神韻。有神韻之生動,謂之人物。神韻為無形跡可見之物而可托生動以見,則凡無形跡可見之胸襟、意境、詩意、古意、逸格、人格之得表出于畫者,皆屬于神韻及生動矣。”鄧以蟄認為,氣韻與物體外在形式的關系不大。如果藝術作品符合氣韻生動的要求,形式上也應當符合形似的特點,但若只有形式的相似,這并不意味具備了內在的神韻。鄧以蟄將氣韻歸結到“理”的層面,“藝術不因與氣韻不相容而失其存在,而氣韻則超過一切藝術,即形超乎體,神或意出于形,而歸乎一‘理’之精微。此其所以為氣韻生動之理,而為吾國畫理造境之高之所在也”。
鄧以蟄認為,“氣韻”與藝術家的創作也有著密切關系。作家在進行藝術創造時,需要充分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去表現宇宙的內在生氣,探求宇宙人生的奧妙和玄理。“人為飛動之倫,能觀天地之大,豈曰以大觀小?以大觀小仍就藝術之規律與義法而言,若乃畫理,則當立于藝術之外觀吾人之明賞、妙得可也。賞者何?得者何?曰:氣韻而已矣。”“氣韻”著眼的是整個宇宙、人生和歷史大境界,更多是表現整個宇宙和人生,強調藝術品要蘊含宇宙元氣。如果說西方的摹仿說強調的是對外部客觀自然的觀照,那么氣韻不僅需要對客觀自然的認真觀察,更需要內在情感的表現,藝術創作者的元氣要和整個宇宙的元氣達到和諧統一的狀態。
二、傳統派的美學探索
與革新派不同,在中國現代美學史上,有一批堅持傳統藝術審美風格的藝術家。他們堅守傳統,宣傳中國古典美術的風格和價值,如李叔同、豐子愷和潘天壽等。他們雖然也受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但更多在堅守和維護著中國傳統的藝術精髓,在現代美學的探索中發出了自己的獨特聲音。
豐子愷將東方和西方的美學思想融會貫通,引進西方美學思想來實現其本土化的目標,并以此來推動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豐子愷的美學探索主要體現在對情趣、苦悶和絕緣等范疇的提出與闡釋上。豐子愷曾留學日本,他的“情趣說”受到了日本夏目漱石的“余裕說”影響。“余裕說”強調的是一種對生活的觀察和反應態度,它反對灰暗瑣碎地描寫生活,主張以一種新的態度去觀照人生,給人一種美的感覺。豐子愷主張藝術創作要有情感投入,藝術的作用就是書寫和排遣感情。豐子愷認為,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對象身上,與自己的對象共喜共悲,暫時進入“無我”之境。豐子愷的觀點與立普斯的移情說有所相似,也與康德的審美非功利性思想大致相同。在豐子愷看來,藝術家應該具有感性情懷,要去感受對象身上的趣味,然后把這種情趣表現出來。
豐子愷認為,趣味屬于畫家感興的范疇,“趣味即畫家之感興也。一畫家之感興,不當與凡眾相同……所謂中國之洋畫家者,皆逞其模仿之本領,負依賴之性質,不識獨立之趣味為何物,直一照相器耳(有遠近法、位置法等都不顧到者,則反不如照相器),豈可謂之畫家哉!予不敢自命畫家,但自信未入歧途”。在豐子愷看來,趣味獨立是畫家的一個重要的素質。繪畫藝術中不能缺少獨立的趣味,獨立的趣味能夠帶來意志、身體和時間的自由,如果在繪畫藝術中缺少趣味,便會墜入粗鄙。豐子愷批評西洋畫照相機似的畫法,認為這只是追求藝術品與原物摹仿的相似程度,使繪畫失去了藝術應有的獨立趣味,因而不是真正的繪畫藝術。豐子愷反對這種照相機似的繪畫藝術,提倡捕捉和表現趣味。豐子愷對兒童教育十分關注,認為兒童的天真爛漫是極其美好的,童真和童心在大人眼里便是一種趣味。在豐子愷看來,藝術家也應該具有孩童般的趣味,在對現實和自然進行審美觀照和藝術創作時,應有博大的胸襟,不要受到現實功利因素的困擾。趣味是藝術審美內涵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是藝術區別于他物的重要特征,藝術家通過對趣味的表現創作真正的藝術。
豐子愷提出“苦悶說”,其理論主要來源于廚川白村。豐子愷受廚川白村影響,認為“生命力受抑壓而生的苦悶懊惱便是文藝底根柢,又文藝底表現法是廣義的象征主義”。豐子愷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孩童時期的自由奔放的情感被壓制,年紀的增長所帶來的是人生的苦悶和對現實的無奈。“孩子漸漸長大起來,碰的釘子也漸漸多起來,心知這世間是不能應付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的,于是漸漸變成馴服的大人。……我們雖然由兒童變成大人,然而我們這心靈是始終一貫的心靈,即依然是兒時的心靈,不過經過許久的壓抑,所有的怒放的熾盛的感情的萌芽,屢被磨折,不敢再發生罷了。這種感情的根,依舊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們的心靈中。這就是‘人生的苦悶’的根源。”在豐子愷看來,苦悶的根源是被壓制的自由感情,當情感得不到疏泄,便會導致人生的苦悶和抑郁。
對于人生的苦悶,豐子愷認為并非不可消解。在他看來,藝術具有排遣苦悶的作用和效果,能將心中郁結的感情通過一定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的身體被束縛于現實,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爛。然而我們在藝術的生活中,可以瞥見生的崇高、不朽,而發現生的意義與價值了。”豐子愷認為,藝術具有永恒的價值,能引導人走出人生的苦悶和彷徨,由此可以看出藝術對人生的教化作用。豐子愷充分認同藝術的教育作用,強調通過藝術引導個體走出人生苦悶。在這個意義上,“苦悶”的疏泄和亞里士多德的“凈化說”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即都強調藝術具有排遣壓抑的功效。
豐子愷還提出“絕緣說”,“所謂絕緣,就是對一種事物的時候,解除事物在世間的一切關系、因果,而孤零地觀看……絕緣的眼,可以看出事物的本身的美,可以發現奇妙的比擬”。豐子愷認為,天真爛漫的兒童對人生自然所采取的態度具有絕緣的性質。“絕緣”不同于實用的或者是科學的態度,它要求用一種純粹的眼光去欣賞藝術,強調審美的非功利性態度。在豐子愷看來,注重事物本身審美經驗和注重實用功利的日常經驗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審美經驗應當是一種絕緣的態度,即以超越功利的審美心態去看事物,斷絕各種實用的功利的聯系,即“絕緣”。“絕緣”要求破除一切相關的利害關系,直接用直覺去感受形象,獲得最真切的審美感受。審美主體要排除功利實際的占有欲,用一種超功利的審美態度去觀照審美對象,如此才能獲得最本真的審美體驗。
豐子愷在《藝術教育的原理》中指出:“科學是有關系的,藝術是絕緣的,這絕緣便是美的境地——吾人達到哲學論究的最高點,因此可以認出知的世界和美的世界來。”對藝術家而言,如果要對事物進行審美觀照,一方面需要去除實用的功利方法,另一方面需要破除科學上的求真和求實方法。在豐子愷看來,只有拋棄世俗功利的感知方式和科學求真的認知方式,不執著于求利和求真,才能進入到對人和事物等的審美觀照中。要達到這種絕緣的藝術效果,關鍵是要擁有一顆兒童般的超凡脫俗的心。保持純粹之心,在看待事物時便會“絕緣”,便不再因為世俗的功利化而喪失藝術本質。顯然,豐子愷所論及的“絕緣”其實是一種審美非功利性態度,即強調藝術的純粹性和自主性。
李叔同是豐子愷的老師,他與另一位學生潘天壽及其他一些藝術家也立足于中國美術傳統,對現代美術的發展進行了積極探索。李叔同肯定藝術的審美作用和功能,認為藝術不僅能陶冶人的情操,也具有實際的功用性。在《圖畫修得法》中,李叔同肯定圖畫的效用和力量,認為圖畫能夠彌補語言文字窮盡的遺憾,對于文化的傳承有著重大意義。李叔同特別提到圖畫的優勢,“圖畫者,為物之簡單,為狀至明確。舉人世至復雜之思想感情,可以一覽得之。挽近以還,若書籍、若報章、若講義,非不佐以圖畫,匡文字語言之不逮。效力所及,蓋有如此”。此外,李叔同在《音樂小雜志》的序中,專門論述了音樂對人情感的陶冶作用,充分肯定了音樂藝術的審美價值:“繄夫音樂,肇自古初……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情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矣。”
李叔同主張在吸收西洋技法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美學觀。在談中西繪畫比較時,李叔同談到中國畫和西洋畫由于文化傳統等各方面的差異,認為西洋畫在一些方面比國畫具有優越性,中國畫需要吸收西洋畫的優秀之處,“中畫雖不拘泥于形似,但必須從形似到不拘形似方好;西畫從形似到形神一致,更到出神入化……觀察事物與社會現象作描寫技術的進修,還須與時俱進,多吸收新學科,多學些新技法,有機會不可放過”。不難看出,在李叔同對現代美術的美學探索中,他不僅受到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西方現代藝術思想的影響。
潘天壽認為,藝術創作必須有獨特的風格,藝術應保持其獨特性,不可失去自身的原則,一味地復制和模仿也不是長久之計。對于繪畫藝術來說,東西方繪畫體系可以相互吸收對方的長處以供學習,但不能漫無原則。“漫無原則的隨便吸收,絕不是一種有理的進取。中國繪畫應該有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中國繪畫如果畫得同西洋繪畫差不多,實無異于中國繪畫的自我取消。”在潘天壽眼里,真正優秀的藝術家應該是民族風格的體現者。民族風格需要不斷繼承與發展,才不會脫離時代的精神和要求。潘天壽強調,獨特的風格應當具有以下三點:“一要不同于西方繪畫而有民族風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創獲,三要經得起社會的評判和歷史的考驗而非一時嘩眾取寵。”潘天壽追求繪畫藝術的獨特風格,實際上是對藝術獨立性的堅持與追求。在他看來,只有獨特的風格才能使繪畫藝術保持真正的審美價值和意義。
三、革新派與傳統派的美學論爭
20世紀初,西方藝術和美學理論的傳入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派選擇堅守傳統的陣營,力求將傳統的藝術精髓發揚光大。革新派在接受西方先進理論之后,強調借用西方理論探索和構建中國藝術。傳統派關注中國傳統,強調發展傳統藝術精華的理念;革新派更多關注西方繪畫理念,強調以此來激發中國傳統繪畫精華。
繪畫中傳統派與革新派的論爭,更多源于西洋畫引入時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失衡。面對西方的技術和文化的沖擊,如何去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成了一個問題,也因而產生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優劣比較。在繪畫領域,產生了中國畫和西洋畫哪一個更為優秀的論爭。在中國繪畫現代轉型的歷史時期,革新派看到了西洋繪畫的優勢,認為西洋畫注重求真求實,是一種講求科學的藝術。倡導改革者開始對中國傳統繪畫提出批評和否定,倡導學習科學畫法的西洋畫。在這種情形下,不少人對中國傳統繪畫產生質疑,進而否定中國傳統繪畫的價值。
在論爭中,劉海粟提倡在發展東方藝術的同時研究西方藝術;林風眠偏愛中國古典素材,同時對西方表現主義、象征派藝術手法等相當熟稔,呈現出強烈的現代先鋒探索意識;徐悲鴻向西洋畫學習,融合東西方繪畫技藝和藝術實踐;鄧以蟄以黑格爾美學思想為基礎,在書畫藝術中探索形式和意境的關系;豐子愷以超功利的審美心態去觀照審美對象;李叔同吸收西洋技法,同時堅守中國繪畫傳統;潘天壽堅持藝術獨立性,認為獨特的風格是保持藝術審美性的關鍵。這些藝術家們通過對西方繪畫藝術的考察與反思,對比中西美術差異,進而探索中國現代繪畫藝術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現代性先鋒探索意義。
在革新派與傳統派的美學論爭中,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徐悲鴻等都紛紛表達自己的觀點。一部分人否定中國傳統的文人畫,批評中國傳統文人畫不求形似的特點,主張學習西洋畫求真求實的精神;還有一部分人反對學習西洋畫的求真求實,提倡保留傳統畫,如金城就充分肯定文人畫的價值。在這場論爭中,傳統派與革新派畫家雖然都主張學習西方繪畫理論,但是對待繪畫的具體態度有所區別。傳統派堅持中國傳統藝術審美品格,堅守傳統,如豐子愷就堅守中國傳統的藝術精髓,強調情趣、苦悶、絕緣等美學觀。豐子愷擅長將東方和西方的美學思想融會貫通,他引進西方美學思想主要是為了實現其本土化目標,以此來推動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和進步。此外,李叔同和潘天壽也主張藝術創作要有自己的鮮明風格,不應該為了復制和摹仿而失去藝術創作的原則。
與傳統派不同,革新派要求融合西方的繪畫理念去革新中國的傳統繪畫,革新派關注西方繪畫藝術,希望實現中西融合的效果。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鄧以蟄等。劉海粟主張學習西方繪畫藝術,發展中國繪畫藝術。林風眠介紹了西方的藝術,在整理中國藝術的基礎上,創造出新時代的藝術。受過系統西畫教育的徐悲鴻,主張中西融合的繪畫藝術。徐悲鴻倡導建立一種寫實的美學觀,認為藝術應該去表現生活,藝術的表現從生活中觀察取材。徐悲鴻認為應該去仔細觀察自然,觀察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神態,以此作為繪畫的表現對象。徐悲鴻認為中國近代藝術普遍存在的問題便是因求美而失去了對真的追求,“從古昔到現在我國畫家都忽略了表現生活的描寫,只專注意山水、人物、鳥獸、花卉等,抽象理想,或模仿古人的作品,只是專講唯美主義。當然藝術最重要的原質是美,可是不能單獨講求美而忽略了真和善,這恐怕是中國藝術界犯的通病吧”。因此,徐悲鴻主張學習西洋繪畫的那種寫實主義精神,充分吸收西洋畫的科學技法。
革新派和傳統派論爭的復雜性和雜糅性,究其根源,是現代藝術家群體既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先鋒探索寄予厚望,同時又質疑其是否能夠實現其理論承諾,繼而多方探索尋覓,多維審視而糾結的結果。這種異于西方現代派藝術的創作,事實上卻是中國藝術自身發展對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一種本土化操作。客觀上講,西方現代藝術的理論主張和藝術技法,因其生成語境和形式上的異質性,未必能夠完美契合中國藝術的現實發展,必須要加以甄別和選擇。現代藝術家群體以一種主動選擇的姿態尋求中國藝術的生存發展策略,他們將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主張作為主要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通過對中國古典藝術和西方不同藝術流派的美學理論和創作技巧的吸收借鑒,進而探索出適合中國藝術發展現實的藝術理論和創作技法。
無論是革新派還是傳統派,他們都希望為中國繪畫的發展謀求出路,改良或創新都是希望借鑒西方的繪畫藝術理論,促進中國繪畫理論和繪畫藝術的發展,推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兩個派別的側重點不同,傳統派更多傾向于立足中國傳統,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試圖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革新派則強調立足于中西融合來發展中國現代藝術。二者的論爭,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所采取的態度的區分。
在這場論爭中,隨著西方繪畫理論的引入,現代美術學家在傳統國粹與外來思潮的雙重影響下尋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空間。西方的繪畫理論給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血液,面對西方繪畫藝術,中國現代繪畫藝術應持一種開放的心態,不要閉關自守。但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同時,中國現代繪畫藝術也要對自身實際情況有清醒認識,不能盲目借鑒和吸引。中國繪畫藝術應該在借鑒的基礎上,自主選擇與建構,而不是在西方現代派思潮的沖擊下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