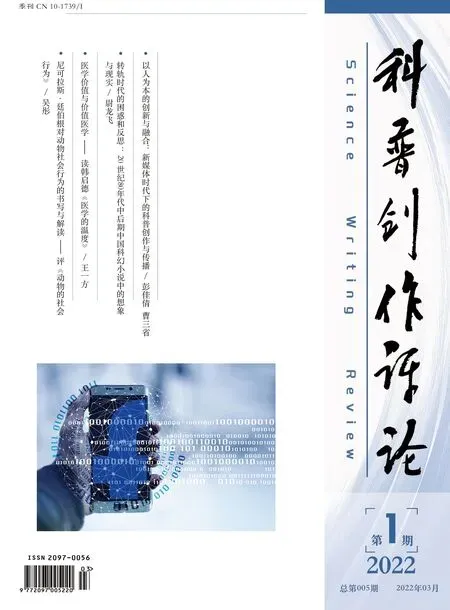關(guān)于科普創(chuàng)作及其評論的一種評論
劉 兵
(山東中醫(yī)藥大學(xué)中醫(yī)文獻(xiàn)與文化研究院,濟(jì)南 250355)1
(中國科協(xié)—清華大學(xué)科技傳播與普及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2
就《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這份刊物來說,對于刊名的解讀也可做做文章。因?yàn)椋@里涉及何為科普,何為科普創(chuàng)作,也涉及何為“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這樣幾個(gè)基本概念。而且,說起這些概念,也并非毫無異議,對于其內(nèi)涵和外延,有著很大的可討論空間、不同的理解和多樣的選擇。針對不同的理解和選擇,為之所撰寫的文章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自然也會有很大的差別。當(dāng)然,就可能存在的不同理解和多樣選擇來說,本文也只是個(gè)人觀點(diǎn),或許尚有可供他人思考借鑒的些許價(jià)值。
為了邏輯清晰和討論方便,也許首先需要界定一下本人所理解和定義的“科普”概念。2019年,筆者曾在《科普研究》雜志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對科普相關(guān)概念研究的簡要回顧與討論”的文章。其實(shí),在那篇文章中,我只是討論了“科普”“公眾理解科學(xué)”和“科學(xué)傳播”這幾個(gè)概念,以及它們彼此的差別和關(guān)系,對其中的“科普”并沒有給出一個(gè)總體的定義,只是簡要地回顧了這一概念及背后的諸多承載的演變歷程。不過,在這里,也許按我對《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的想象,還是可以給出一個(gè)更籠統(tǒng)的定義:科普,就是指在正規(guī)的學(xué)校教育之外,在社會上,面向非專業(yè)人士(也即公眾)和在對內(nèi)容的了解上非本專業(yè)的其他專業(yè)人士(例如,這里可以是指其普及的內(nèi)容并非本專業(yè)研究領(lǐng)域的科學(xué)家或?qū)I(yè)科學(xué)史家等)的對與科學(xué)有關(guān)的各種內(nèi)容,采用各種形式的有意識的普及傳播。這可以說是一個(gè)涵蓋范圍很廣泛,但又有一定約束性的定義。
以上觀點(diǎn)作為一種科普的定義,雖然仍可進(jìn)行討論,不過其至少在形式上應(yīng)該沒有太多的問題,而更多細(xì)節(jié)的說明,后文也還會有涉及。但在這個(gè)定義中,卻包含和隱藏著一個(gè)爭議非常大的概念,即在“與科學(xué)有關(guān)”這一說法中的“科學(xué)”。眾所周知,關(guān)于“科學(xué)是什么”,或者說,對科學(xué)的定義,長期以來一直是沒有特別的共識而且充滿爭議的。如果不對在此定義中涉及的“科學(xué)”再給出界定,這個(gè)科普定義在操作的意義上就依然是不明確的,還是沒法劃定邊界。
在科學(xué)哲學(xué)這個(gè)已經(jīng)非常成熟的學(xué)科中,科學(xué)的定義問題,或者說是將科學(xué)與非科學(xué)分開的“劃界問題”,一直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研究問題。許多年來,眾多的科學(xué)哲學(xué)家對之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例如實(shí)證主義的“證實(shí)原則”,或證偽主義的“證偽原則”等。相關(guān)的研究,像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綱領(lǐng)方法論”,或者像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范式學(xué)說”等,各種或是規(guī)范性的,或是描述性的方案層出不窮,但卻都沒有得到所有學(xué)者的一致認(rèn)可,以至于有人甚至提出了無法對科學(xué)給出一個(gè)精確定義的說法。
但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傳統(tǒng)中,這些科學(xué)哲學(xué)家們研究的“科學(xué)”對象,基本上都是西方科學(xué),這說明,即使在范圍較小的西方科學(xué)的范圍內(nèi),想要以簡單的劃界標(biāo)準(zhǔn)來統(tǒng)一地定義科學(xué),也是非常困難的。而在超出西方科學(xué)時(shí),問題就更大了。在眾多的科學(xué)史著作中,對西方科學(xué)之外的其他類型的“科學(xué)”,也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尤其是隨著科學(xué)史學(xué)科的發(fā)展,對“非西方科學(xué)”的關(guān)注更是在不斷增多。這也就對我們考慮科普的內(nèi)容提出了問題,即科普中的“科學(xué)”是否應(yīng)僅限于西方科學(xué)嗎?除了歷史上的“非西方科學(xué)”,在現(xiàn)實(shí)中也同樣存在著沒有被劃歸到西方科學(xué)范疇的“非西方科學(xué)”。例如,科技部頒布的《中國公民科學(xué)素養(yǎng)基準(zhǔn)》,就曾因其中包括了一些在標(biāo)準(zhǔn)的西方科學(xué)之外的中國內(nèi)容而被有些人質(zhì)疑,這至少說明,在這個(gè)問題上,還是存在爭議的。
以醫(yī)學(xué)科普為例。在今天的圖書市場上,健康醫(yī)學(xué)普及性書籍為數(shù)眾多,也經(jīng)常在分類上被歸屬于科學(xué)普及類。其實(shí),按照最嚴(yán)格的科學(xué)劃界理論,醫(yī)學(xué)又是有其獨(dú)特性的,與近現(xiàn)代主流的西方數(shù)理科學(xué)差異很大,尤其是在臨床醫(yī)學(xué)領(lǐng)域,以致曾有著名科學(xué)史和醫(yī)學(xué)史家將之歸為“仁術(shù)”,以區(qū)別于狹義的西方科學(xué)。但這種以西醫(yī)為基礎(chǔ)的普及性圖書,說它們不是“科普圖書”,則似乎又與現(xiàn)實(shí)中人們的認(rèn)識大有沖突。但在這類圖書中,另一個(gè)明顯的事實(shí)則是,以中醫(yī)為基礎(chǔ)的醫(yī)療、保健、養(yǎng)生類圖書所占的比例更大。它們是否屬于科普圖書呢?同樣,雖然目前人們普遍將西醫(yī)視為“科學(xué)”,但中醫(yī)是否是“科學(xué)”,卻在社會上有著激烈的爭論,盡管衛(wèi)生部中醫(yī)研究院早已更名為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但在西方科學(xué)的意識形態(tài)傳播的影響下,不認(rèn)為中醫(yī)是科學(xué)的人比例也非常大。那么,這類中醫(yī)保健養(yǎng)生類圖書是否屬于“科普圖書”呢?如果不屬于,它們應(yīng)歸到什么類別里?
如果放眼到更前沿的科學(xué)哲學(xué)、科學(xué)史、科學(xué)文化和科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我們還可以注意到,通俗地講,關(guān)于科學(xué)的范圍,存在著分類上的“寬面條”和“窄面條”之爭。前者,將西方科學(xué)之外的許多學(xué)說也包括在“科學(xué)”之中;而后者,則只將西方科學(xué)作為科學(xué)。另外,在這些領(lǐng)域中,如果采用以“地方性知識”為基礎(chǔ)的“多元科學(xué)”的概念,也會帶來更包容的分類,在這樣的分類中,其他許多非西方科學(xué)同樣可以納入“科學(xué)”的范疇。
因此,在這種包容性最強(qiáng)的分類中,我們或許可以將科學(xué)定義為:人類各種對自然的認(rèn)識的合理的系統(tǒng)化知識。這也是筆者在前文的科普定義中所想采用的“科學(xué)”的定義。
對于這種“多元科學(xué)”的定義,有人會質(zhì)疑或提出關(guān)于“偽科學(xué)”的問題。盡管科普法中也明確要反對傳播偽科學(xué),不過,從嚴(yán)格的學(xué)術(shù)角度看,偽科學(xué)是一個(gè)非常難以明確而且爭議頗多的概念。按某種科學(xué)的劃界標(biāo)準(zhǔn),也只能說是要區(qū)分科學(xué)和非科學(xué)。在邏輯上,雖然可以把偽科學(xué)看作是打著科學(xué)的旗號而按某種劃界標(biāo)準(zhǔn)不是科學(xué)的東西,但因沒有統(tǒng)一的劃界標(biāo)準(zhǔn),這樣對偽科學(xué)的指稱又不唯一。因此,作者在前文的定義中采用了“合理的”這一形容詞。不過,這也還是留下了關(guān)于究竟何為“合理”的討論空間,但在此先不展開討論。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科學(xué)定義中,至少表明了“科學(xué)”并不只有單一的“科學(xué)知識系統(tǒng)”。
面對我國的“科普”,除了前面討論的“科學(xué)”的定義,還存在一個(gè)同樣有爭議的問題,就是技術(shù)。因?yàn)樵趪?yán)格的分類中,科學(xué)和技術(shù)的差距同樣不可忽視,盡管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處于變化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技術(shù)推廣”是面向公眾進(jìn)行技術(shù)普及的重要內(nèi)容,尤其是面向農(nóng)村的技術(shù)推廣,也是極有意義和中國特色的普及活動。當(dāng)然,如果嚴(yán)格地區(qū)分科學(xué)和技術(shù),那么“技術(shù)推廣”類的普及活動肯定就不屬于“科普”的范疇。但實(shí)際上,在人們習(xí)慣使用的中文表達(dá)中,“科技”是一個(gè)常見的用詞,甚至在談?wù)摗翱茖W(xué)”時(shí),實(shí)際含義中也經(jīng)常將技術(shù)包括在內(nèi)。所以,如果不去進(jìn)行學(xué)究式的較真,我們同樣可以把這類活動也包括在廣義的“大科普”的范疇中。
在筆者前文對科普的定義中,“對與科學(xué)有關(guān)的各種內(nèi)容,采用各種形式的有意識的普及傳播”這種說法,也是在廣義上包括了所有可能的科普內(nèi)容和形式。傳統(tǒng)科普中主要關(guān)注科學(xué)知識,在后來的科普說法中又將科學(xué)方法、科學(xué)精神和科學(xué)思想涵蓋了進(jìn)去。而來自科學(xué)哲學(xué)和科學(xué)史等領(lǐng)域的材料,不僅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都與“四科”有關(guān),自身與科學(xué)也具有其他相關(guān)性,所以當(dāng)然也是合法的科普內(nèi)容。在形式上,人們會想到如科學(xué)小說、科幻、科學(xué)家傳記等科學(xué)文藝,也會想到科學(xué)史、科普展教具器材(或稱科普產(chǎn)品)等,這些自然也都在這“各種”的說法所包括的定義范圍內(nèi)。尤其是長期以來關(guān)于科幻是否屬于科普的爭議,在這種“大科普”的定義中,自然也可消解,即科幻也應(yīng)包括在科普之內(nèi)。
但要說明的是,在本文對“科學(xué)”的定義中“對自然的認(rèn)識”這一限定,似乎是將對人文社會科學(xué)的普及排除在了科普之外,不過對于科普中的科學(xué)是否包括社會科學(xué),還是存在著爭議的。如果將社會科學(xué)排除在外,也是一種選擇,而目前在科普中融入人文因素是人們關(guān)注的一個(gè)重點(diǎn),也體現(xiàn)了在這兩者間很難截然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最新而且尚未完整出版的八卷本《劍橋科學(xué)史》的第七卷(),標(biāo)題即為“現(xiàn)代社會科學(xué)”,表明科學(xué)史家也介入了社會科學(xué)史的研究。但實(shí)際上,在人們習(xí)慣使用的中文表達(dá)中,在與自然科學(xué)相關(guān)的意義上關(guān)注的社會科學(xué),以及就社會科學(xué)本身關(guān)注的社會科學(xué),這兩者還是有區(qū)別的。我們也可以看到,至少在現(xiàn)實(shí)中,絕大部分的“科普”,還是以自然科學(xué)作為中心的。
討論完“科普”的概念,我們再來討論“科普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的概念。其實(shí)如果詳細(xì)分析的話,在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中,也大有可說之處。
在《漢語大詞典》中,對“創(chuàng)作”一詞的釋義是:1.制造,建造;2.始創(chuàng)。而現(xiàn)在在人們一般的理解中,創(chuàng)作更多地特指創(chuàng)作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刊物《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英文刊名翻譯是Science Writing Review,也即將“創(chuàng)作”譯成了英文的“寫作”。當(dāng)然,這種譯法可能是有益于對外交流的,但如果反譯回來,或許也可能造成某種誤解。在人們?nèi)粘UZ言的應(yīng)用中,“創(chuàng)作”一詞的所指顯然不止于對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是可以有更寬泛的所指,可以用于各種文字產(chǎn)品的和物質(zhì)產(chǎn)品的創(chuàng)造性的完成。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完成”,暗含了某種“原創(chuàng)”的意味,帶有creation 的意思,排除了對于那種非原創(chuàng)性的、復(fù)制式的生產(chǎn)和制作。當(dāng)然,對于一本“評論”科普創(chuàng)作的刊物,只要是與科普創(chuàng)作相關(guān)的內(nèi)容(例如科普出版),自然也可以是屬于可評論的內(nèi)容。
這樣,結(jié)合前面對科學(xué)的定義、對科普的定義以及對“創(chuàng)作”的說明,“科普創(chuàng)作”的概念就應(yīng)該具有了比較清晰但又范圍廣泛的邊界所指和限定了。
最后,針對刊名,再簡單地講一下對“評論”的理解。在文學(xué)領(lǐng)域,有文學(xué)評論或文學(xué)批評,那本來也是獨(dú)立和成熟的學(xué)科,是不同于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以文學(xué)作品和作者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學(xué)科。類似地,其他領(lǐng)域也有相似的情況。因而,總結(jié)起來可以說,這是一種“二階”的研究。就比如說,科學(xué)以自然為研究對象,如果把這定義為一階研究的話,那么,科學(xué)史以科學(xué)作為研究對象,這就是二階的研究。在這樣的意義上,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就是指在以前述的各種類型的一階的科普創(chuàng)作作品為對象的一種二階的研究。
由于多種原因,有時(shí)人們會對二階的研究帶有一些偏見,會覺得其價(jià)值低于一階的研究。例如,文學(xué)家有時(shí)便會不太看得起文學(xué)批評研究,科學(xué)家有時(shí)也會不太看得起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研究。但這其實(shí)是一種偏見。階數(shù)不同的研究只是因研究對象不同而分工不同。有著自己直接研究對象的二階研究,同樣有著不同的指向、不同的價(jià)值,有著上一階研究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以科普創(chuàng)作為對象的研究,同樣具有和科普創(chuàng)作本身同樣重要的價(jià)值,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普創(chuàng)作本身,也會有助于更好地開展科普創(chuàng)作。
這里將“評論”理解為“研究”,也帶有某種理想化的意思,也即這樣的“評論”在二階的意義上,仍然是一種“原創(chuàng)”的“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