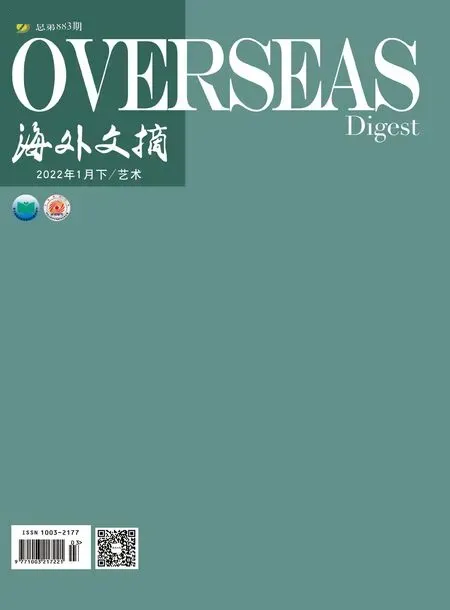說服的藝術: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海報中的多模態隱喻分析
□阮氏梅鴛/文
競選海報作為政治說服的手段在選舉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基于Kress &Van Leeuwen的視覺語法理論框架對2020年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海報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旨在研究海報中的視覺符號的政治隱喻以及如何塑造候選人的形象,有利于加深對美國總統選舉政治的理解。其次,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Kress &Van Leeuwen的多模態語篇分析理論在競選海報中的適用性和可行性。
今天的政治交流是建立在視覺基礎上的,圖像是居于主要地位的,而文本則處于次要的位置(Grabe&Bucy ,2009)。競選海報是美國選舉中歷史最為悠久的視覺政治傳播媒介。從19世紀初到如今競選海報從未缺席,每一張競選海報或多或少都能體現當下的競選政治生態。作為選舉宣傳的利器,競選海報具有尋求關注和動員功能,塑造候選人形象和宣揚議題立場功能,甚至還能增強民眾對選舉的政治興趣。
可見,競選海報作為候選人最常使用的競爭選民的戰略溝通工具在當代政治話語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塑造候選人形象方面可謂功不可沒。競選海報上的各個視覺元素的選取以及組合布局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隱喻,因此本文試圖通過2020年的競選海報探索海報中的視覺符號如何建構意義以及塑造了候選人的何種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們對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有進一步認識和了解。
1 理論概述
1.1 克瑞斯(Kress)和 凡·勒文(Van Leeuwen)的視覺語法理論
鑒于競選海報屬于多模態的視覺語篇,所謂多模態話語指的是運用聽覺、視覺、觸覺等多種感官模式,通過語言、圖像、動作、聲音等多種手段和符號資源進行交際的現象。簡單來說,可以認為多模態話語分析不僅僅關注語言符號,而是將非語言符號如圖像、色彩、聲音等其他符號類型也納入到分析范疇。
1996年,克瑞斯和凡·勒文在其代表作Reading Images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較為系統的多模態視覺語法分析框架,該視覺語法理論由再現意義、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三大維度組成。這三大意義的理論來源是基于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Halliday)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所提出的三大元功能,分別是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其中再現意義對應的是概念功能,其含義為視覺圖像像語言一樣,能夠如實的再現客觀事件中的人、地點和事物以及人類內心世界的活動;互動意義則對應的是人際功能,它代表了圖像生產者、圖像與圖像觀看者之間的特殊互動關系,作者提到這里面至少有三種互動形式存在,圖像內部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圖像內部參與者與觀看者之間的互動以及圖像制作者與觀看者之間的互動;構圖意義對應的功能理論中的語篇功能,即在一張圖像中的布局安排,不同的布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主要是通過信息值、顯著性和取景三個子項目來進行解構。基于這一理論,國內已有三篇針對于美國競選海報的研究,裴曉娜和甘青的研究對象為奧巴馬的競選海報,而李碩則對特朗普的競選海報進行了專門的研究,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證實了視覺語法理論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視覺隱喻對2020年候選人的競選海報進行更加深入的比較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挖掘競選海報所要表達的更深層次內涵。
1.2 視覺隱喻
隱喻通常被認為是最常見的也是最重要的修辭方法之一,因此談及隱喻必先追根溯源談談何為修辭。“修辭”(rhetoric)起源于古希臘,指的是采用巧妙的語言來說服別人認同自己的觀點,因此被稱之為“說服的藝術”。最早的修辭研究發軔于語言符號系統,而最早對隱喻的解釋亦是從文字符號角度出發,公元前300年亞里士多德對隱喻作出解釋:“用一個表示某物的詞借喻它物,這個詞便成了隱喻詞,并認為隱喻就是詞匯間的轉義現象。關于喻體與本體之間的轉義如何成為可能,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轉義生成的基礎是源域(喻體)和目標域(主體)在認知意義上的相似性,即隱喻意味著不同意義系統在相似性基礎上的轉義生成關系,因此相似性是隱喻發生的認知基礎。
但是相較于語言隱喻“A(喻體)是B(本體)”這樣明顯的語言結構,視覺隱喻的重要特點即是本體和喻體并不總是同時“在場”,故劉濤進一步依據此“在場”方式將視覺隱喻區分為構成性視覺隱喻和概念性視覺隱喻。構成性視覺隱喻意味著本體和喻體在視覺結構中同時“在場”,我們可以借助一定的類比邏輯或聯想方式提煉出“A 是 B”這樣的隱喻結構。
而概念性的視覺隱喻概念性視覺隱喻的顯著特點是喻體“在場”而本體“離場”——喻體體現為“在場”的視覺元素與內容,而本體則指向某種抽象的概念圖式。2008年奧巴馬的海報“進步”則是一個典型的概念式視覺隱喻在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之下,選民急切需要一個能夠帶領他們走出經濟危機,給予他們希望的候選人。可見,競選海報作為典型的政治視覺符號充滿了象征和隱喻的政治意味。
2 特朗普和拜登競選海報的多模態隱喻的對比分析
為了確保分析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本文選擇由特朗普官方競選團隊所發布的“超人”海報為分析對象,《華盛頓郵報》賦予這張海報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相當不錯的藝術。然而,由于在拜登的競選官網上未能找到相關海報,因此筆者選取了拜登在2020年11月3日選舉日在推特上所發布的一張海報作為研究對象。這兩張海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能夠體現出兩位候選人所要傳達給選民的核心政治意識。接下來筆者試圖通過視覺語法理論框架對兩張海報進行闡述,力圖清晰地還原這些視覺符號所要表達的象征意義。
2.1 再現意義
在視覺語法框架理論中,再現意義被區分為敘事再現和概念再現兩大類,其中敘事再現展示了發展中的行動和事件,變化的過程,瞬息間的空間安排,而概念再現則更加穩定,時間因素減少,更為概括性,如在類別、結構或意義方面。敘事再現又可進一步分為行動過程、反應過程、言語和心理過程及轉換過程;而概念再現也可再細分為分類、分析以及象征過程。很明顯,在特朗普的海報中握拳的手連接形成了矢量,并且是由特朗普作為動作者本身所指向的方向所構成的,所以它屬于敘事再現中的行動過程。我國學者王一鳴在研究特朗普的人格特質時曾提到特朗普有著一種強烈的信仰——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很多糟糕的、危險的事情,而自己將是那個拯救者,會讓美國重新變得偉大起來。這種救世主的形象符合美國的英雄主義文化,尤其在基督教福音派白人群體當中極具吸引力。
拜登的競選海報也屬于敘事再現而非概念再現,但與特朗普海報所不同的是拜登的海報屬于不及物的反應過程。循著拜登手指引的方向,看著他那極具親和力的笑容的確會讓選民產生一種認同感和舒適感,其中這個手勢與右邊的文字形成互文關系,“改變從你開始”這句短語把“you”特地放大,結合上下文語境淺層含義可理解為我需要你的投票,更深層的含義則是我們一起創造未來為美國的靈魂而戰。此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作為手段情景的墨鏡在這里也具有一定的敘事意義,很多人都很熟悉特朗普最為經典的紅帽子,但很少注意到拜登的墨鏡。該墨鏡為Aviators(飛行員墨鏡),媒體評論員比克認為:“該墨鏡早已作為他政治形象中的組成部分,這讓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冷靜、強硬的領導者。”
2.2 互動意義
視覺語法中的互動意義可以探討圖像中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圖像設計者的交際目的以及圖像解讀者本身對圖像內容的介入程度。主要是通過二級指標中的接觸、社會距離、情態、視角四個要素來實現。
(1)接觸。接觸指的是圖像中的參與者與觀看者之間的目光接觸,有目光接觸的為“索取”類圖像,即透過圖像中參與者的目光似乎在向觀看者索取什么,從而與他們建立起(想象中)的關系;無目光接觸的則為“提供”類圖像,即向觀看者提供某種信息。特朗普的海報與觀看者之間存在目光接觸故屬于“索取”類圖像,而拜登的海報中,作為參與者的拜登目光直視遠方并未與觀看者之間有任何目光接觸,所以屬于“提供”類海報。
(2)社會距離。在日常互動中,與他人的距離似乎在暗示著某種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在圖像的參與者與觀看者之間的距離亦是如此。這種距離主要是取決于圖像中參與者的框架尺寸,即影視學中對拍攝物從特寫到遠景的鏡頭取景。在特朗普的海報中,取景范圍為中景(人物膝蓋以上部分的畫面)屬于視覺語法理論中的社會近距離的范疇,在觀者的視線中,中景既使得特朗普的神情、狀貌清晰可見,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再現出超人的經典形體動作,表明海報想要突出特朗普的超人形象,讓觀者能夠從特朗普身上感受到英雄本色。在拜登的競選海報中只顯示出肩部以上的人物畫像,這屬于個人近距離的范疇,在海報中,拜登露出自信的微笑以及微微抬高的下頜,目光看向手指向的遠方,這些細微的動作所要展現的是一個睿智自信且非常有親和力的領導人形象。
(3)情態。情態一詞源是指在語言學中語言陳述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在圖像分析中情態的高低則取決于圖像的色彩、色調、照明、亮度、再現的細節等表達手段所使用的程度,同在功能語法中一樣,情態可以分成高中低三類。特朗普和拜登的海報都屬于高情態的海報,海報中都十分清晰地再現人物的細節。其次海報的色彩層次分明、對比強烈,例如在特朗普的海報中,紅色是共和黨的象征色代表了這次共和黨依然能夠沖破枷鎖和困境(黑白色)再次成為執政黨。而在拜登的海報中,象征著民主黨的藍色作為背景底色,同樣象征性地隱喻民主黨才是那個最有底氣和自信能夠領導美國人民的政黨。總的來說這兩張高情態海報都給予觀看者一種真實感和可信度。
(4)態度。“態度”指的是觀看者與圖像參與者產生的權勢關系,一般是由視角所決定的。在特朗普的海報中,參與者是從垂直視角的高角度進行描繪,使特朗普的上方拳頭的放大效果極大地增強了視覺沖擊力,使得人物更加富有立體感和生命力,令觀看者記憶深刻。在拜登的競選海報中創造者采取低視角的拍攝手法試圖凸顯拜登的領導氣質和強大氣場,無意間使得觀者對其產生敬仰和崇拜之情。
2.3 構圖意義
構圖意義類似于功能語法中的組篇意義, 指的是圖像的再現意義和互動意義相聯系組成有意義的整體的方式。克瑞斯和凡·勒文提出可以通過信息值、顯著性和取景三個資源來實現構圖意義。由于在兩張圖片中未見明顯的分割線條和框線,因此取景維度暫不做分析。
信息值主要是依據各個元素在圖像中所放置的位置來辨別。在左右結構當中放置在左邊的信息通常是已知的或顯而易見的,而放置在右邊的信息則代表是新的可討論或未解決的;在上下結構當中自然也有一定的隱含意義,放置在上方的信息通常是“理想的”,而置于下方的則是“真實的”;在中心—邊緣結構中,自然處于中心位置的元素信息值最高。特朗普這張海報主要包含了和中心—邊緣結構和上下—結構,特朗普的超人形象被置于海報最中心,大約占據海報2/3的位置,信息值聚焦于特朗普的超人形象。在上方的結構中,特朗普2020年的競選口號“讓美國保持偉大”(Keep America Great!),處于海報的最頂端位置,這說明該信息是“理想的”。而下方是“2020年”象征著競選當年。在拜登的海報中則是由左—右結構組成,左邊放置著拜登的肖像則意味著民主黨來競爭總統職位的候選人是拜登,在右邊文本部分描述的是“改變從你開始”作為選民期待的新信息,隱喻選民要想改變美國現狀關鍵在于給拜登投票。
顯著性指的是元素吸引觀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可通過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相對尺寸、色調值的對比(或色彩)、鮮明度的不同等來實現。在拜登的海報中,運用美國國旗的三種顏色(紅白藍)作為海報的組成顏色具有愛國意義的象征,其中紅色象征勇氣,白色象征真理,藍色象征正義。整個海報的象征意義就是隱喻選民要在正義之上懷揣勇氣投出那正確地具有真理意義的一票。
總的來說,兩張海報中的視覺符合聚合產生“合力”都清晰的建構出候選人的形象,特朗普的海報屬于非常明顯的構成性視覺隱喻,喻體(超人)和本體(特朗普)同時在場,這一置換很容易讓選民將特朗普視為拯救美國復興美利堅的超人;而拜登的海報則與奧巴馬的“希望”海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整張海報都在暗示選民拜登的當選能引領美國走向希望擺脫目前的困境,所以這張海報屬于概念性的視覺隱喻,此張海報最終的目的是在呼吁選民為拜登投票,為美國的未來投票!
3 結語
通過對這兩張競選海報的分析,其視覺設計表現出候選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需求,也折射出當下的選舉現狀、政黨制度、美國文化等方面。具體來說,兩張所反映的主導思想都是關于應對當下美國政治危機如何處理的實質內涵,特朗普的海報更具象地將自己喻為超人,將自己視為美國的救世主,而拜登的海報也在暗示著選民給自己投票必會帶來改變和希望,所以本質上這兩張海報所要表達的核心政治意識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視覺時代的背景下,競選海報作為一種多模態的視覺說服藝術在營銷總統傳播政黨觀念加強選民互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引用
[1] Geise 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Visu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Election Posters[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
[2] 陳世華,劉晶.政治傳播中的視覺修辭流變[J].國際新聞界,2017,39(9):71-87.
[3] 胡圣煒.從社會符號學角度對征兵海報的視覺分析[J].外語研究,2008(4):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