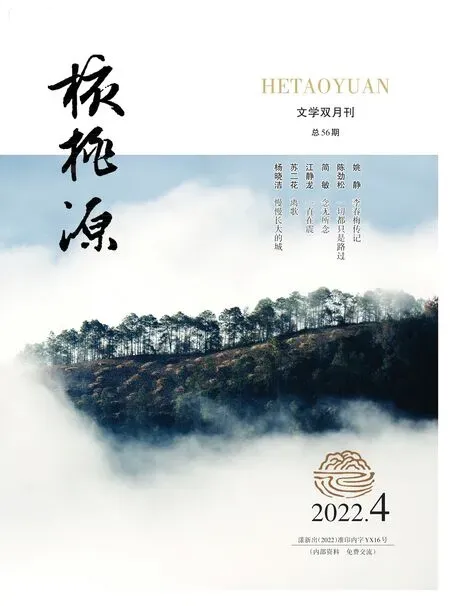撫今追昔憶師恩
——回憶羅秉英老師
楊純柱
羅秉英老師
一
光陰似箭,如白駒過隙,轉眼我退休將近一年時間了。一天清理書房,竟翻到一本2005年9月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頓時思緒紛涌,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在云南大學讀書的時代。
羅秉英是我的大學老師,教中國古代史。《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匯集了秉英老師主要的學術論文。翻開這本書,秉英老師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眼前。
記得我們云南大學八四級歷史系一百多名(包括歷史專業和檔案專業)新生,擠在云南大學一幢老建筑一樓一間光線有點幽暗的大教室里,等著上進入大學的第一節課。
上課鈴聲響起,只見一位面容清癯、身材修長、腰板挺得筆直的中年老師,夾著講義稿,健步走進教室。他面帶親切的微笑,開口的第一句話是:“同學們好!”同學們愣了一下,才慌忙起立稀稀啦啦地回應道:“老師好!”第二次他上課也是如此,直到第三四次上課時,大家才適應了他先向學生問好的習慣,他一句“同學們好”話音剛落,大家就整齊響亮地回答:“老師好!”這就是秉英老師鐫刻在我們腦海里與眾不同的印象。其他老師來上課的順序是班長喊起立、敬禮,老師還禮,然后坐下。
秉英老師,為廣東興寧市人,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雖然來云南工作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紀,鄉音依然十分濃郁。他操著一口粵鄉客家普通話,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要請同學們原諒:一是他講課的過程中,有抽煙的習慣,多次想改,都沒有改掉這個不良的習慣,因為不抽煙,他的思路便打不開,講授就不流暢,就會顯得干巴巴的,枯燥無味。二是他的普通話不好,同學們聽起來會很費勁。他努力學習普通話多年,仍然沒有多少改善,因而很無奈。
當講課開始,秉英老師這口粵鄉客家普通話,初聽的時候,果然有些吃力,漸漸適應了,卻別有一種親切的韻味和吸引人的磁性。秉英老師的課堂向來以秩序井然為人稱道,有人將其歸功于他對學生嚴格要求的緣故,我則以為主要是他人格魅力和授課的感染力使然。
秉英老師的課講得無疑是最棒的。他的講授深入淺出、簡約曉暢、條分縷析、重點突出,而且又非常生動活潑,風趣詼諧。不少同學都說,聽秉英老師的課,可謂如坐春風,是一種讓人甘之如飴的輕松愉快的精神享受。我們的班主任張躍老師多次告誡同學說,秉英老師的課史料豐富、觀點新穎、前后連貫、邏輯性強,完整記錄下來就是一篇篇好文章。我想秉英老師的課堂,之所以精彩迭起,給人獲益良多,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不僅僅是他有博古通今,涉獵廣泛的知識儲備,也不完全得益于其獨具匠心的“上掛下聯,左顧右盼”的講授藝術,更在于他對教學工作的認真負責,對每一堂課都傾心盡力地忘我投入的結果。由此可見,他備課是十分扎實充分的。
惟有如此,秉英老師才能如此得心應手,舉重若輕,游刃有余地進行旁征博引的講授。其凝結在其中的汗水和辛勞,則是難以與外人道的。可惜當年的我并不太懂得,當我明白這種教學的酸甜苦辣和獲得成功背后是需要用成噸的汗水來換取時,已是我大學畢業走上教學崗位的多年之后了。
二
母校的銀杏葉又黃了。2008年那個多雨的7月,告別母校二十年的我,繼畢業十周年同學聚會后,再次返回母校。在畢業二十周年同學聚會的座談會上,我又見到了秉英老師,他依然是一臉親切的笑容,這是我畢業后,第一次見到秉英老師。二十年的寒來暑往,年近八十高齡的秉英老師已然滿頭霜雪,但他和藹的面容,溫潤的笑意,閃爍著慈愛而睿智光芒的目光,在我多少有些滄桑意味的眼睛里,仍然一如當年給人以溫暖親切和真摯友善。大概是由于自己走出校門后的境遇不太好,工作和學習都乏善可陳,深感有些無顏面對秉英老師。我沒有勇氣走上前向秉英老師鞠一個躬,問一聲老師好,我只是靜靜坐在座談會的后排,遠遠地注目著坐在大圓桌對面的這位平易近人的讓我十分感念的師長,默默表達著我心里對他的由衷敬重與祝福。
秉英老師是我所遇到的最優秀的老師之一,更是我今生今世最感念的老師。早在學生時代,我就覺得秉英老師品性高潔,學養深厚,身上散發著一種恬淡通達、平和儒雅之氣。但這還只是秉英老師外在的魅力,更難得的是秉英老師熱愛學生,視學生為平等的朋友,尤其是他急切地欲將自己讀書治學的“金針”度予學生的那種古道熱腸的迫切愿望,在眾多老師中,他的這種精神最突出,最令人感動,也是最使人難忘。
其實,有的老師學問不可謂不好,亦能“講”善“授”,與學生卻很難親近起來。究其原因,可能就是這些名師,只重視“授人以魚”,盡管他們課講得有聲有色,精彩紛呈,可頂多就是贏得學生們的仰慕而已,而并沒有贏得學生由衷的愛戴和感念。秉英老師則將“教書”與“育人”都當仁不讓地肩負起來,“魚漁兼授”,既兢兢業業“教書”,更不遺余力地“育人”。為了將剛跨入大學校園的新生盡快引領上讀書治學途徑,秉英老師在重視傳播知識的同時,更重視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為了“廣開自學門路”和盡可能地培養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講臺上的秉英老師,除了以身示范教學生怎樣讀書、怎樣查閱資料和做資料卡片,怎樣發現問題和尋根究底地進行學術探索外,還不時穿插一些自己讀書做學問的心得體會,以及從事學術研究的艱辛和樂趣。
秉英老師不止一次地強調說,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和富有新意。創新雖然有時需要靈感的火花點燃,更多的則需要殫精竭慮的苦苦思索,只有廢寢忘食地日思夜想,才會獲得“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秉英老師告訴我們他自己在思考學術問題的時候,常常吃飯會想、走路會想,躺在床上也會想,有時想得過于專注和投入,眼睛往往呆呆盯住一個地方,久久都不會移動,直到夾著的煙卷燒著手指皮肉,才驀然驚覺。為此,妻子曾不止一次地同他鬧過小誤會,質問他的心思究竟跑哪兒去啦。
秉英老師還經常拿自己治學道路上曲折坎坷的經歷鼓勵同學們,寫文章投稿要不怕失敗和不畏挫折。他說,自己讀大學的時候,就喜歡寫文章投稿,盡管屢投不中,仍然毫不氣餒地寫,從不間斷地投。當年的編輯極端負責任,自己十分固執地一稿一稿地投,人家不厭其煩地一次一次地將其稿子閱后退回,自己投出去的稿子,就如同放飛的信鴿,不久后又如期飛了回來。每個星期都會收到一兩次退稿,以至于聽到班上負責傳遞信件的同學一叫自己的名字,就本能地想到肯定又是退稿。后來,他想了一個辦法,在每篇稿子末都特別注明:“稿子不用,請直接丟入廢紙簍,千萬別再費心退回”,才避免了經常收到退稿信件的尷尬。
三
有一次,秉英老師把我叫到他家里仔細詢問了我的情況,又同我漫無邊際地聊了一陣天。當得知我是來自大理點蒼山西坡一個小山村的白族大學生,求學經歷又比較坎坷曲折:上大學之前,在農村放過牛羊,在部隊當過兵,還當過筑路民工時,便熱情地勉勵我要倍加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汲取知識營養,認真深造自己,同時鼓勵我要經常提筆練習寫作。秉英老師說,文科生不就是鍛煉一張嘴、一支筆嘛,而筆頭只有愈寫才愈健,正如刀子愈磨才會愈鋒利。
送我出門的時候,秉英老師還一再囑咐我,今后不論他教不教我們班的課程,學習上遇到什么問題都歡迎我隨時去找他。他還再三囑咐我:最好每一個學期至少寫兩篇以上文章拿給他,他會幫我看一下,指導一下。
遺憾的是,我并沒有很好地把握和珍惜這個難得的學習機遇,以至荒廢了大量美好的時光。特別是除老師布置的不得不完成的作業外,我大概也只在秉英老師和我談話后不久,心血來潮地寫過一篇文章呈送他評閱。多年后,偶然買到秉英老師的《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之后,我方知道,此事曾被秉英老師寫入其文章《〈中國古代史〉引導學生自學活動的三個環節》,發表于《云南高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上。他在文章中寫道:“楊純柱同學(少數民族)利用國慶放假,寫了一篇題為《也是一管之見——談談我對歷史的一點看法》的文章,二千八百余字,提出的問題頗有見解。”
不分春夏秋冬,都在焚膏繼晷地“筆耕舌耘”的秉英老師,在云大校園幽靜的書齋里和三尺講臺上度過了大半生的歲月。自幼酷愛寫作的他,走上教學和學術研究崗位后,在教學之余終身筆耕不輟,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學術論文并出版了幾本學術專著,在學術上亦可謂建樹頗豐。
不過比較起來,我覺得秉英老師的主要精力和貢獻還在教書育人領域。在這個什么都靠“炒作”和“包裝”的浮躁年代,秉英老師這種只會整天埋頭于書齋和講臺,老老實實讀書做學問和教書育人,做人做事從來都很低調的不事張揚的學者,自然與時下四處泛濫成災的“大師”頭銜無緣。也許秉英老師算不上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但他卻絕對是他的學生心目中最好的、最值得尊敬的老師。尤其是對于我,從秉英老師身上,不只學到了知識,更學會了怎樣讀書和做人。慚愧的是這么多年來,由于自己的資質太愚鈍和生性太懶惰,別說奢談做學問,就連讀書、教書都差強人意,甚至由于自己對形式主義的厭倦和不耐煩情緒,從而秧及我對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工作往往敷衍了事“蒙混過關”,真有愧于恩師的親切教誨和殷殷期望。
四
秉英老師生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他教我們的時候已是五十有五的人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重點高等學府,勤勤懇懇耕耘了四分之一世紀,教學成績突出、學術成果顯著的秉英老師,當時的職稱還僅僅只是一個講師,理論上只屬于中級知識分子,按那個年代只有縣團級以上職務領導干部和副教授以上職稱的高級知識分子才能享受乘坐飛機和火車軟臥待遇的規定,秉英老師赴成都、北京等外地出差或參加學術活動,都只能擠長途火車硬座。但是秉英老師并未顯出心浮氣躁,更沒有在課堂上講過一言半句怪話和發過什么牢騷。
秉英老師給人的印象和感覺總是那么的從容平和、安祥寧靜、淡泊超脫。在我走上工作崗位后,每當我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遇著不應有的挫折,心中憤憤不平的時候,只要一想起一生淡泊名利的秉英老師那種心無旁鶩,盡心盡力地“筆耕舌耘”,其他“一無所求,別無所爭”的平和心態和仁者風范,我瞬間便怒火頓熄,心氣和順了。僅從這一點上,我覺得秉英老師對我的潛移默化,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的。
最后,還想多說兩句的是大約五年前從林超民老師朋友圈得知秉英老師已經駕鶴西去。我第一時間將此消息轉到大學同學微信群,同學們都紛紛留言表示深切悼念和無限緬懷。其字里行間無不充滿對秉英老師的款款深情和由衷感念。一位同學說:“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很多已經記憶模糊、褪色,羅老師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恍如昨日。”另一位同學說:“帶著客家鄉音的普通話,始終洋溢著真誠笑容的臉龐,數十年教書育人,嚴謹治學,成就斐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還有一個同學說:“羅老師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師,認真負責、學識淵博。羅老師,天堂安好!”諸如此類留言,不勝枚舉。
秉英老師的公子羅青,并不是我們這屆八四級歷史系的同學,但他與我們班的同學比較親近,就作為唯一例外被拉入我們同學群。羅青讀了大家的懷念文字發帖說:“謝謝大家!家父于2017年11月2日中午離開的,已經入土為安!按照家父遺愿不發卜告,不舉行儀式,所以沒有告知大家,也想著給大家留個念想,實在不好意思!再次謝謝大家!”羅青同學的通報讓我們再次深受感動。可以說,作為謙謙君子的秉英老師的這一臨終遺愿,以及他家人對其身后事非常低調的處理方式,可謂一如當年秉英老師的做人風范和謙和淡泊形象。
秉英老師,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我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