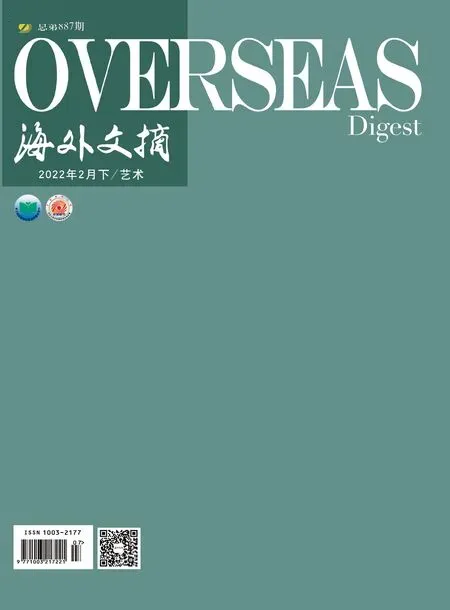儒學看文學
——以福澤諭吉的詩歌為線索
□王雨辰/文
對于身處近世時期的大部分思想家來說,儒學的價值觀是他們衡量事物的最主要的價值標準,漢文學是他們所承認的唯一的正統文學。但是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顯然是站在“近代”的角度來審視、理解和評判文學的,這樣的做法犯了脫離歷史語境的兵家大忌。然而,恰恰是福澤諭吉這樣獨特的文學視角給當時一潭死水的日本文壇注入了新鮮活力。本文將結合福澤諭吉的西學背景和他對中國儒學的理解,以其所作思想詩為切入口,探討福澤諭吉思想的演變與本質。
1 福澤諭吉的詩歌
諭吉對中國詩歌的正式創作始于明治九年(1876年)。那年夏天,根據諭吉的全集,諭吉開始寫詩,回憶起學習漢學的舊時光,買了一本詩歌參考書。他的中國詩歌主要有律詩和絕句兩種形式。以下是對諭吉絕句詩的賞析,并對其思想內容進行分析。
詩1: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修習問學唯尚實,明辨獨立言行一。
根據福澤諭吉的觀點,上天并沒有給予那些在上面的人更長的生命,也沒有給予那些在下面的人更短的生命,也就是說,對于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現實生活中智者與愚者、貧者與富者、貴者與卑者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識的存在,而知識的存在是由學習而非學習造成的。因此,人生來就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勤奮的知識、豐富的知識才能富貴。這種知識不是一般的空洞知識,而是指能夠幫助人們生活、身體的知識。他學習了8國語言,練習寫作和記賬,學習算盤,主張學習地理、物理、歷史、經濟、自我修養和外語。福澤諭吉認為對于國家而言,實施教育文明政策是國家能夠獨立自主、堅強不屈的保障。除了提供普及教育,他還提倡教育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和國家認同感。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人喜歡暴政,憎恨仁愛,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愿意受到外國的欺凌。借助有效的教育手段,把這種樸素的民族意識提高到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詩2:倡文明之實,建文明國家。使硝鐵生煙,抗列國來犯。
日本在崛起前也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而且日本最初危機感很強。早在1837年時,日本德川幕府的統治者德川齊昭就曾說過,日本將是西方打擊的一個目標,因為中國太大,朝鮮又太小,而英國炮艦打日本正好。但英國炮艦沒到日本來,卻敲開中國大門。這就是鴉片戰爭。對于中國發生的一切,日本也很擔心。所以福澤諭吉說,日本不斷向中國學習,連危機意識都學來了。不過日本在19世紀也有危機感。這就很好體現在上詩中。
而為了自強以抵御侵略,福澤認為, 每一個愛國的日本人所持的立場便是推進日本的文明進程。所謂文明,一般是指人的身體安樂、道德高尚。而區分一個國家或社會文明的標志便是看:這個社會的一切事業是否納入一定的規范之內;
人民是否朝氣蓬勃而不囿于舊習;國民是否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需仰仗他人的恩賜;是否敦品勵學,不茍安于目前的小康;工商業是否發達。而就一個國家而言,文明主要包括兩種文明:外在文明與內在文明。前者主要指有關衣服、飲食、器械、居室、政 令、法律等方面的進步程度;后者主要指精神方面的東西,即滲透于全國人民之間,表現于各種事物之中的社會風氣。而當時的日本,僅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精神。
詩3:霧中真相有幾分,萬事無窮亦無言。老翁多言君勿怪,不過人間萬事中。
這首晚年的《傅翁白華》也是諭吉的作品,比青年時期的作品更為世故,也不那么專橫跋扈。這首詩反映了他晚年的人生觀,即“人生如夢”四個字。第一句“霧中真相有幾分”一方面表明人的存在狀態既是真實的又是空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諭吉的基本思維方式,即避免“過分強調”片面性。他曾經指出,日本人在考慮問題時有“偏重量輕”的問題,這種病被它稱為“溺水的誘惑”。最典型的例子是酒店老板被認為酒量很好,小吃店老板被誤認為滴酒不沾。諭吉說,改變這種狀況的方法是建立一種言論自由的世界。
通過以上三首漢詩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諭吉創作的中國詩歌既不是巧妙的文字,也不是生動有趣的人工作品,更不是純粹的寄情山水。這些詩歌清楚地表達了諭吉對日本社會和西方權力社會混亂的不滿。與此同時,我們可以感受到諭吉對西方實學和西方文明的堅定信念,正是這種信念激發了諭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帶領國家致富的愿望,激發了一個強國的決心,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好。
2 儒學無用論的背后
福澤諭吉寫詩,不取材于中國傳統,而大力提倡西方文化,并認為儒學為“無可取的學問”。但其實這樣的觀點是有極強主觀色彩而有失偏頗的。福澤在言論和行動上對儒學的排斥原因何在?從其著作《文明論概略》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第一,福澤認為在儒學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缺乏自由言論的風潮。福澤認為在中國社會只有在周朝末葉尚存一些自由言論的風潮。
第二,福澤認為儒學主要講道德,而儒家主張的道德不僅無法適應變化發展的社會,而且道德是無形的東西,可以偽裝。這個世上會有“偽善者”的出現,但不會有“偽智者”。
其實,在江戶后期,“扇子學校”(由每個家族建立的子弟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數量大大增加。武士在四書五經教育上獲益良多,商人和經濟實力雄厚的農民在私立學校學習儒學,用通俗的語言將神、儒家、佛和道德信學融合在一起,受到普通百姓的歡迎。儒家思想開始成為“大眾”知識。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異校禁書”。
為了遏制當時的鋪張浪費,貫徹重農抑商的方針,實行思想控制,幕府將軍命令直屬的學府(后稱昌平坂學問所)只教授朱熹學說,禁止教授外來學問。這項禁令的意義有限。像所有的禁令一樣,人們總是愿意以兩面派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禁令。據說,當時日本的大儒沙依賽在值班時教學生朱子,在下班時教學生陽明主義。在他88歲去世的時候,他的門徒已經增加到3000人,其中一些是著名的人物,如渡辺華山、中村正直等。他們借助儒家的知識框架和世界觀來理解現代西方文明,試圖解決當時日本在西方世界沖擊下面臨的各種問題。
所有經歷過明治維新的人都學習過儒家思想。這是日本歷史上唯一一個幾乎每個人都接受儒家教育的時期。即使是批判儒家的福澤諭吉也讀過11遍《左傳》。
日本儒家單一行(1622-1685)在他的著作《神圣教會記》中提到:“詩人所向往的地方,他的話語會動,古詩的自然韻律也會動。他的志氣或挽救諷刺,或評多義,或善景,或自鳴得意,或說本屆政府的德行,所以,六義自然存在其中。后來,研究詩歌,巧妙的詞語和趣味,其詞語都是虛假和荒誕的。因此,詩人是世界上最悠閑的人,娛樂和宴請的媒介也就失去了。”
單一行的這段話同時向我們揭示了兩個重要事實。
第一,江戶時期的日本社會,出現了很多詩人,并且寫就了大量詩歌,但很多都是寄情山水、訴諸風情。雖說如此,受儒家文化影響,還是有部分詩歌沿襲了儒家“入世”傳統,揭露了社會現實。
第二,雖然儒學傳入日本的形式和重點與中國明顯不同,但“治世”的核心是一以貫之的。儒家詩歌的初衷是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把文學與人們心靈、社會狀況,特別是國家政局聯系起來,因此這種文學作品既有審美趣道,又不缺乏哲學高度。
行文至此,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福澤諭吉主張詩文要擺脫中國傳統,盡快融入西學體系,但是福澤諭吉本身的思想就是在儒學的環境中養成的,并且他身上的批判的精神也是儒學中的應有之義。或許有人會問,文學為何要為政治服務?文學為何要承載厚重的思想內涵?要在各種思想間選邊站隊?文學不可以成為單純的文學嗎?這種想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實則不然。因為任何“主觀性”一旦脫離客體對象就無法確立。擺脫歷史、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與凈化后的文學不是“獨立”,而是一種“無關”、一種脫節的逃避。而在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時,我們不能忽視儒家的重要命題,即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3 “文道合一”,“詩理相結”
文學與道學的關系是歷代思想家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如柳宗元主張文學應以道為本,韓愈主張文學應以古為本,歐陽詢主張文學應陶之以道,周敦頤主張以道載文,邵雍主張文學是道學的直觀表現。朱熹在周敦頤的影響下,主張“道”與“文”的一致性,堅決反對“文”與“道”二分的思想。他曾經說過,“如果你認為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文本,而不重新考慮其推理的對與錯,那么道就是道,文本也就是文本。有些東西偏離了道,所以它對于道路來說是不夠的,對于道來說是不是足夠的呢?如果道不合適,也不存在,那么文本就是說教。只有文本和道可以相一致。否則,我們兩個都會失去。”
其次,朱熹雖然強調文學與道學的一致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文道”之間沒有關系。他認為,與“文”相比,“道”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和主導地位。顯然,朱熹認為“道”是文學的基礎,文學只能由“道”構成,“道”是日常事物的原則。許多人批評朱熹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和抽象的思維,但事實并非如此。朱熹理論中的“理”只是指它為何如此的原因和如此存在的原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們應該有的存在狀態,同時它們必須遵守某些規律。政治、社會和個人都有其應有的狀態,人們可以通過“審視事物”來獲得這種應有的狀態。朱熹說:“很多人認為這個道理是一個暫停的事實。大學不說精細的原則,只說材料,是事情上的重要人物所理解的,從而方見本質。所謂的本質不應該出現在事物中。”既然理性不是空洞的,如果沒有理性,那么文學就不可能是一個空洞的學習,一個無用的學習。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心中的“真理”,詩歌等文學作品才能成為經典。
不可否認,朱熹希望用“尊”來維持心態,從而達到“明心、明義”的境界。這表明,朱熹的思維方式,詩歌的內容取決于主體心中是否有“理、義、道、體”。“詩義結合”和“文德結合”的思想,不僅反映了朱熹重視文學,也表明了文學離不開宋明理學的指導這一重要事實。
4 有關“文學”概念的思考
當我們思考“文學”時,我們應該在歷史地、辯證地、唯物地分析“文學”的語境。例如,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如俳諧、歌舞伎、浮世繪、薰落本等都可以被稱為文學,但當我們回到江戶時代,我們發現當時的思想家可能已經將文學排除在“文學”的范疇之外。大載臺春(1680-1747)在他的作品《獨白》中將歌舞伎、純玻璃作為“淫樂”的“戲”,為君子所鄙視。對于現代大多數日本思想家來說,儒家價值觀是他們衡量事物的最重要標準,中國文學是他們唯一認可的正統文學。事實上,福澤諭吉作為啟蒙思想家,清楚地從一個“現代”的角度來看待、理解和辨析文學,但這種方法違反了文學的禁忌,脫離了歷史語境。
日本學者中村彥對日本現代文學進行了分類,具有一定的學習意義。中村認為“在現代世界的普遍意識中,所有的文學都按照自己的階級分為兩類。一個是傳統的文學群體,即從中國引進的日本和歌和中國詩歌。二是中世紀末期萌芽的現代形態,開足玻璃、歌舞伎、假草、上吉草子等新文人。現代人稱后者為俗文,前者為雅文學。”
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日本現代文學分為四類:(1)意識形態文學;(2)寄情山水文學;(3)娛樂大眾文學;(4)教育功能文學。
所謂意識形態文學,就是探索 “道”與實現“理”的文學作品,他們以傳統儒家為終極目標。寄情山水文學主要是指中國詩歌,娛樂大眾文學大致可以說是“戲劇”,教育功能文學就是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主張文明開化的文學。其中,前三類文學與最后一類文學并非相互獨立,而是相互聯系。四類文學是存在著交錯的有機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