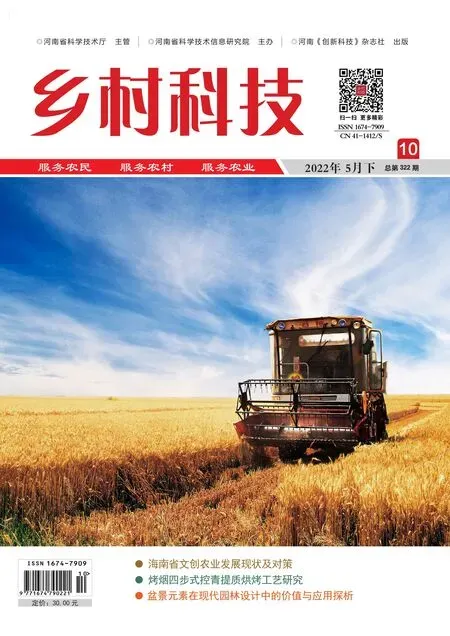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路徑
任佳嘉
(武漢工程大學,湖北 武漢 430205)
0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并相應地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布局。2021年4月,中共中央審議通過《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為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謀篇布局。基層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點工程。隨著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農村基層涌現出不少亟待解決的治理問題,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任重而道遠。梳理新時代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理論依據和實踐邏輯,在認清基層治理重要性的基礎上,結合農村具體實際探求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路徑,助力鄉村振興和民族復興。
1 新時代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理論依據和實踐邏輯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腳踏實地、艱苦奮斗,使中國農村窮困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許多社會問題不斷凸顯,特別是在農村基層,各種深層次社會矛盾沖突集中暴露,給基層治理能力、體制機制帶來了全新挑戰,急需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辟除榛莽。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根植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有其特定的實踐邏輯,體現了中國特色基層治理理念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許。
1.1 新時代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理論依據
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新時代回應“實現什么樣的治理”這一核心問題的現實思考,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突破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困局的關鍵舉措。因此,相關管理部門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基層社會治理中馬克思主義國家論的理論維度。
1.1.1 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認為,私有制條件下必然出現按照不同利益集團劃分且矛盾不可調和的各對抗階級,由此產生國家以緩和階級沖突。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需要注意的是,國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消滅沖突,實質是統治階級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組織形式。在階級社會中,國家表現為“公共權力”并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社會權力服從于國家權力,社會主體無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開始向社會復歸,無產階級逐漸掌握政權,社會主體大量參與“公共權力”,人民享有一定的權力,但未到達人的解放的“彼岸世界”,同時,國家的統治職能被弱化,治理和服務職能不斷擴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實現了對社會的復歸,完全成為服務性質的機構,人民能夠當家做主行使自己的權利,人類最終獲得自由和全面發展,實現徹底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基于此,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其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過程,極大程度上促進了人的解放。
1.1.2 馬克思主義國家與社會關系論。國家治理現代化在于社會治理現代化。關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也有不少研究,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體、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和黑格爾的倫理精神。但是,他們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無法指導現實世界進行變革。馬克思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從資本社會的物質基礎出發,尖銳地指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論證了階級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關系。一方面,國家是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工具。階級把人與人區分開來,一個或幾個階級結成聯盟獲得統治特權并對其他一切階級進行剝削,一旦統治階級掌握特權,國家就會成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統治階級合法地運用強制性國家機器使一切被統治階級服從自己的意愿并對其施加影響,也就是說,國家使統治階級的特權合法化;當統治階級對國家具有絕對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后,維護“普遍利益”的行政機構將無止境地追求“特殊利益”,“人民公仆”名存實亡。另一方面,市民社會是階級國家的基礎,國家終將回歸社會,二者實現統一。第一,市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同時是階級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市民社會中現實存在的、帶有個人利益的自然人和階級國家中虛幻抽象的、帶有政治屬性的人所指為同一人;第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和家庭的天然基礎構成了政治國家,為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直接來源;第三,市民社會決定著階級國家的存在及發展,無論階級國家如何變化,在市民社會的發展內部總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迫使階級國家朝著適應自己的方向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唯心派的根本區別。馬克思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顛覆了以往人們對國家與社會本質的認知,科學地指出了市民社會決定階級國家,二者不可跨越,最終趨向統一,奠定了社會本位基礎,指明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
1.2 新時代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實踐邏輯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治國安民重在基層。新時代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回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主體思想,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需要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需要。
1.2.1 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需要。人民至上是黨百年奮斗的經驗總結。中國共產黨歷來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基層社會治理關乎人民的生活質量,是影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指標之一。人民是基層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和成果享有者。一方面,人民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體力量,群眾參與基層社會事務,發揮主人翁意識,為構建社會治理新局面發光發熱;另一方面,基層社會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統一。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人人有責”強調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匯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使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激發基層治理的內生動力;“人人盡責”強調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在權責清晰的基礎上主動擔當、積極作為,凝聚起“中國之治”的磅礴力量;“人人享有”強調基層社會治理最終是為了人民,共享治理成果、實現安居樂業。這也是社會治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生動體現。
1.2.2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需要。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一方面,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改進治理方式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質要求。一直以來,農村基層都是社會治理的薄弱地帶,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改變這一局面。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三農”工作,并提出“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村基層治理體系更加完善”。這些規劃為實現鄉村振興筑牢了上層建筑,也為基層社會治理明確了方向和目標。因此,加強和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是實現鄉村振興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有效的基層社會治理反過來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加快轉變治理理念,提高治理效能,有利于推動基層治理高質量發展。所謂“基層治理有效”是指國家權力作用于基層治理過程,實現政策、方針落地開花。實踐證明,農村基層治理觀念落后、治理方式單一、治理結構失衡必然導致各項政策、制度的消解,嚴重制約鄉村振興的推進。因此,擺脫基層社會治理的現實困境能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保駕護航。
1.2.3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需要。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于完善制度體系、提高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二者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一方面,制度往往起著長遠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對于國家治理,要以根本制度為保障,以基本制度為支撐,以具體制度為補充。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要推動具體制度法治化、高效化和透明化,以此堅持基本制度、鞏固根本制度,最終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有效的治理能力能極大地發揮制度的效能,體現制度的優越性。縱觀世界社會主義500多年的歷史,在如何提高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能力上沒有道路可循。中國共產黨“摸著石頭過河”,逐漸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道路,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是,相比于人民的期待、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需要及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要想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靠制度,靠國家在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質干部隊伍。當前,國家不斷強調治理重心要下沉到基層社區,提高基層干部隊伍制度執行能力,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完善基層治理體制機制,更牢靠地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2 鄉村振興背景下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路徑
2020年,我國實現全面脫貧,夯實了農村發展的經濟基礎,但是與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還存在較大差距。實現新時代新目標,需要從戰略高度把握農村基層治理發展規律,從實踐角度對治理方式進行創新和總結,堅持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良性互動。筆者主要從以下3方面探討提升農村基層治理效能的路徑。
2.1 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
馬克思、列寧等思想家認為,共產黨作為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物,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中起著領導核心的作用。同樣,社會治理現代化也離不開黨的引領作用。基層黨組織作為聯系黨中央與基層的“最后一公里”,起著貫徹中央部署、凝聚基層力量、穩定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基層治理,狠抓黨建是關鍵。首先,明確角色定位,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者、協調者作用,在加強基層黨支部政治建設的同時,抓好頂層設計,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了解村民所需所想所急所盼,做好基層治理的戰略規劃,在實踐中將黨中央關于基層治理相關發展目標落實落細。其次,改進領導方式,完善黨組織的政治引領作用,加快基層黨組織由傳統的管理向現代化的治理轉變,牢記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把黨建與村民的需求結合在一起;吸納村民的合理訴求,并積極尋求解決路徑,吸引思想先進的優秀村民入黨,壯大群眾基礎;充分發揚基層黨組織的黨內民主,保障黨員干部的民主權利,密切與廣大村民的溝通與聯系,營造“六又”黨內政治生態環境局面。最后,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嚴明黨員干部政治紀律,使黨史學習教育常學常新,做到自省、自責、自查、自改,加強干群“魚水關系”,贏得群眾的信任;通過業務培訓,提升基層干部隊伍辦實事的能力,增強其與時俱進的意識,有效利用黨校、實踐教育基地等機構,更新治理方式方法,增強辦事底蘊和能力;嚴格干部考核,創新干部選用辦法,暢通人才流動渠道,加強村干部后備儲備,使基層治理隊伍擁有源源不斷的活力和生命力。
2.2 盤活農村“三治”體系,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
探索農村基層治理路徑,構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系統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全國廣大基層干部、村民長期不懈地探索。農村基層治理是一個涉及多種元素的動態過程,其治理主體均為村民。基于此,應從以下3方面著手促進“三治”融合,在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中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
2.2.1 創新農村自治模式,激發自治內生動力。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制度,在保障村民基本權益、激發農村內生活力、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村民自治是實現“三治合一”的核心環節,是我國基層治理的創新形式,是基層民主政治的集中體現。實現村民自治需要匯集村民的智慧和力量,依據村民實際需求,在合法的基礎上建立翔實、可操作的自治規則,創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路徑。一方面要賦予鄉村自治主體一定的活動空間,激發自治內生活力。基層組織是社會治理中上下聯動的重要層級,是引導廣大基層干部發揮作用的基本單位。因此,其要練就“過硬本領”,不斷提升在農民中的話語權;建立村委會事務清單,在減負降壓的基礎上推動村民訴求與政府政策的有效銜接,形成村民、村委會、政府間的良性互動。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宗族鄉賢、治理精英在自治中的表達權,做政府和村民的“黏合劑”。另一方面,要推動建立農村自治社區。農村社區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配套工程,是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基層政權的重要舉措。農村社區打破了原有封閉、單一的治理方式,為社區村民提供了均等化公共服務,實現了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創新,通過治理下沉推動農村城鎮化發展。
2.2.2 加強法治普及教育,使群眾懂法守法用法。法治通過法律條文條例形式協調各方利益,是農村基層治理的“硬道理”。將法治觸角延伸到農村事務的方方面面,能保障自治的有效實施,彌補鄉規民約的不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也在基層。因此,建設法治農村至關重要。
首先,加強普法教育,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把法治教育與村民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通過手機、電視、廣播等媒介,運用案例解讀、警示教育、普法宣傳等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使法治觀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導村民樹立學法的意識,擴大普法覆蓋面。
其次,建設一支具有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的基層干部隊伍。基層干部要主動提升自身法治素養,提高帶頭模范守法自覺性,面對村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能用法律知識及時化解,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實現法治裝頭腦、化行動、落實踐。
再次,構建農村村莊治安防控體系。廣大農村地區要積極落實平安農村建設,加強治安防范安全教育,建立人口全覆蓋模式的動態監測網,做到早預防、早發現、早治理,提高村民的安全感。
最后,加快農村相關領域立法進程。加大基層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基層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法律規范力度。同時,加強基層法治宣傳、培訓、教育體系化建設,培養村民維護法律權威和依法參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理念,使懂法守法用法成為共識。通過硬性約束和軟性宣傳進一步提高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2.2.3 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營造向上向善的淳樸民風。中國乃禮儀之邦,歷來重視德治的教化作用。農村德治建設要從德法并重的傳統中汲取治理智慧,把村規民約與當代社會主義道德相結合,發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不斷推動農村文化建設,改善農村落后的精神面貌。第一,要樹立道德典型,引領村莊風尚。不斷完善村規民約,形成新時代的道德規范;樹立榜樣,轉變村民的落后思維;發揮鄉賢以點帶面的領頭羊作用。第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農村人居環境包括居住條件、生態環境和文化生活。實現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雙管齊下,建設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和文化生活日益多元的新農村、新社區。第三,形成具有特色的農村社區文化。文化建設并不是整齊劃一,而是要在博采眾長中傳承文化底蘊。人是文化建設中最活躍的因素,因此,要充分發揮廣大村民的主觀能動性和主動參與性,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嵌入基層農村基層治理的全過程,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鄉規民約,倡導以和為貴、尊老愛幼、助人為樂等傳統美德和優良家風,形成滿足社區發展需要的特色文化,增強村民對社區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3 結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我黨在新時代立足于“三農”、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部署,體現了我黨的初心使命,實現了馬克思社會治理思想與中國城鄉發展實際的有機結合。以鄉村振興戰略為總體背景,以馬克思社會治理思想為重要指導,探究新時代創新農村基層治理的實現路徑具有的理論意義和時代意義。實現鄉村振興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繼續秉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和“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