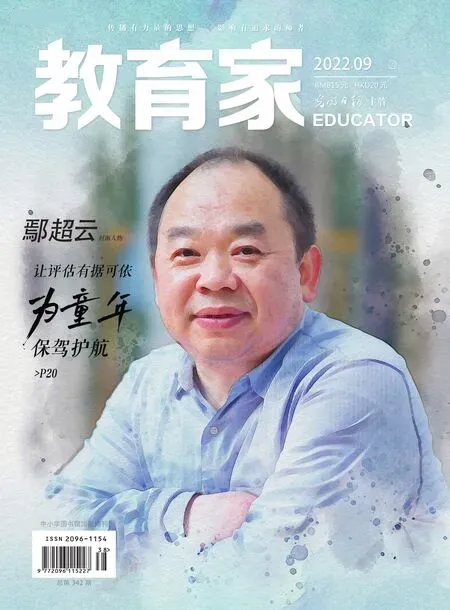“假而不休”不能成為教師減負的盲區
喬雪峰 |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
社會各行業日趨“內卷”的形勢下,教師暑期可帶薪休假常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在許多人眼中,教師的暑假是長達兩個月的休息時間,可自主安排日程。然而實際情形中,“假而不休”常成為教師暑期的真實形態。暑期雖然并未安排教學任務,可備課、教研、培訓、行政事務等工作安排強度往往并不小。特別是“雙減”政策落地之后,暑期托管服務、課后服務的準備工作進一步填充了教師暑假日程表中為數不多的彈性時間。對部分教師來說,暑期儼然變成了工作的“第三學期”。
“雙減”政策致力于滿足人民群眾對“上好學”的愿望,對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和課后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重新界定了教師工作內容和邊界,引發教師工作形態的調整和轉型。更多的教師主動走出“舒適區”,投身到轉型性變革之中,長時間加班、高強度投入、節假日堅守成為教師工作的常態。“假而不休”之下,教師用于自我恢復的過渡期越來越短。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投入導致教師常年處于負荷過載狀態,產生負面情感體驗。長遠來看,其職業韌性將受到不可逆的損傷,對教師職業認同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引發教師的離職。因此,我們需要探究“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產生機制,分析如何營造支持性政策環境和學校環境協助教師減負增能。
“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產生機制

壓力反應是當事人面對工作任務的自然感知,伴隨工作任務而產生,亦隨著任務的完成而消失。適當水平的壓力感有助于當事人調動時間、精力等相關資源,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可是,當工作要求過高或者時間配給不足時,所產生的壓力反應超出當事人的心理承受閾值,壓力感會轉化為工作負擔,引發緊張、焦慮、沮喪等負面情感體驗。“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面臨著重大的轉型調整,由此觸發工作負擔的產生機制。教師工作負擔并非來自單一的壓力源,而是多種壓力累積的結果。
首先,“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理念、工作模式和教學方式面臨轉型,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引發教師的焦慮感。“雙減”政策將學校教育場景從課堂教學延展到課前、課中、課后、家庭等方方面面,對教師課堂教學、作業管理、課后服務課程提出新的要求。在課堂教學方面,要求教師將學校作為課堂教學主陣地,讓學生在校內實現優質學習,不再依賴校外學科類培訓;在作業管理方面,要求作業減量提質,壓減作業總量和作業時長,加強作業完成指導;在課后服務方面,要求開足開齊課后服務課程,滿足學生“五育并舉”的發展需要。面對諸多要求,教師需要轉變教育觀念,重新審視甚至顛覆過往慣常的工作模式,構建與政策情境相匹配的工作模式。然而,工作模式的更迭并非一蹴而就。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期,教師工作的開展面臨著不確定性,導致教師失去了控制感,產生了對未知的發展前景的焦慮。
其次,“雙減”政策產生的任務增量尚未嵌入教師工作體系之中,加劇了教師工作的碎片化傾向。教師工作涉及教學、備課、批改作業、教研進修、家校溝通、行政事務等多種類型的任務。對于教師而言,工作任務之間的正向關聯度越高,越能夠形成良性交互。基于一定的主線將不同類型的工作任務連接起來,使其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往往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雙減”政策之下,課后服務作為新增模塊出現在教師工作中,教師有一定的陌生感。課后服務工作處于摸索階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思路和操作流程。同時,課后服務模塊與其他類型工作任務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厘清,尚未形成聯動機制。由是,課后服務常被作為獨立的任務模塊加以對待,產生額外的任務增量,加劇了教師的壓力反應。
第三,教師對時間的支配能力下降,引發“時間饑荒”。“雙減”政策的任務安排打亂了教師慣常的工作節奏,額外的工作量擠壓了教師可支配時間。為了完成工作任務安排,教師工作的時間密度和時間總量隨之增加,導致教師工作負荷增加甚至過載。同時,課后服務與其他類型的工作在時間安排上產生一定的交疊,引發時間沖突。特別是對于備課、教科研等需要連續沉浸式投入的工作類型而言,時間沖突導致教師工作進程被額外的工作任務或者臨時性的工作通知頻繁打斷,教師不得不采取多任務并行的處理方式。多任務并行處理不僅加大了教師的工作強度,而且任務之間需要頻繁切換,使得教師難以專注地投入,產生焦慮感。
基于上述多種壓力源的累積,高負荷成為學期內教師工作常態,且有蔓延至暑期之勢。暑期作為兩個學期之間的緩沖區,有助于消減教師學期內累積的壓力,恢復教師對工作壓力的抗性。然而,緩沖區的消失,導致教師的壓力抗性受到損耗,面對紛沓而至的工作壓力逐漸不支。
“雙減”政策下如何為教師減負增能
“雙減”政策下為教師減負增能,需要對教師壓力反應的強度進行調控,使工作任務產生的壓力處于教師可承受閾值之內。閾值之內的壓力反應,有助于教師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生動力,促進教師高質量完成工作,同時避免觸發負面的工作負擔機制。
首先,主動響應“雙減”政策要求,從全局視野出發看待“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的新常態。全局視野有助于幫助教師建立長遠發展愿景,跳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將國家發展戰略轉化為組織和個體發展愿景注入行動。在長遠發展愿景的指引之下,教師即便處于較高水平的壓力之下,亦能夠將壓力轉化為行動動力。為此,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可以組織安排“雙減”政策的實踐詮釋和解讀,將抽象的政策話語具象化為教學實踐話語,加固、加密國家政策與教師工作的內在連接。“雙減”政策的實踐詮釋有助于提升教師工作轉型的意義感和認同感,改善教師的工作體驗,促進壓力的正向轉化。
其次,營造高挑戰與高支持并存的工作場域,促使教師在大變局環境下開拓新局。教師在“外接式”進修培訓中提升專業素養成效有限,在高挑戰與高支持并存的真實教育場景中通過解決教學工作的問題才能突破“天花板”,獲得持續提升。其中,挑戰指向教師尚未具備的能力和素養,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支持則是為達到發展目標所配備的資源、條件、平臺、機制等條件。高挑戰和高支持的同向作用有助于營造教師發展所需的承托性環境,協助教師跳出“舒適圈”,將挑戰性壓力轉化為主動發展行動。為此,教育行政部門可發展針對工作挑戰的靶向支持,推進信息技術與“雙減”教育教學場景的深度融合應用,引入校外優質資源,強化家校社協同育人。學校可針對校內教師的切實訴求,做好課后服務的保障工作,為教師提供所需的資源和專業支持,解決教師的后顧之憂。
第三,基于整體意識和統籌思維,開展工作時間的系統性整合。系統層面的轉型性變革需要重組系統內部要素連接,形成合力,驅動變革向前。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可以對教師工作時間進行整體性規劃,利用任務壓減、整合聯動、留白管理等多種手段做好時間規劃安排,暢通時間管理“微循環”,提升教師對時間的掌控感。任務壓減方面,教育行政部門應壓減不必要的督查、檢查、評比、考核等事項,嚴控事務性工作的時間占用。整合聯動方面,可統籌安排周期性事務,合并同類事項,建立清單式任務序列,涉及跨學科、跨年級、跨校的任務可聯合組團開展。留白管理方面,學校可統籌安排教師的到校離校時間,探索AB崗制度、彈性上下班制度,為教師保留適當的可自由支配的彈性時間。而暑期作為教師工作的戰略性留白期,需合理預留教師休假時間,促進教師在高壓下的韌性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