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記憶、療治創傷與生態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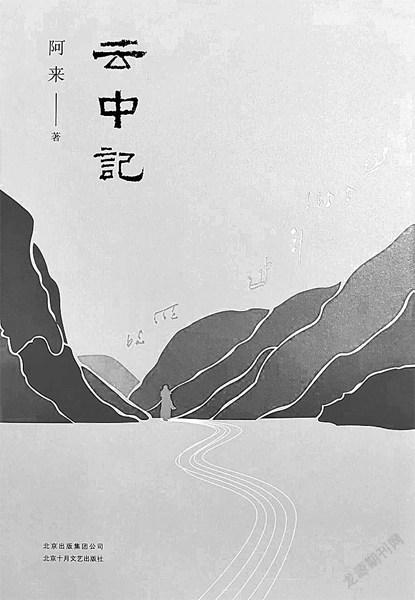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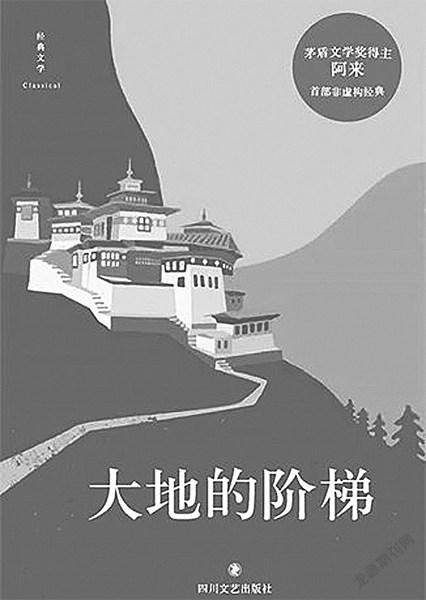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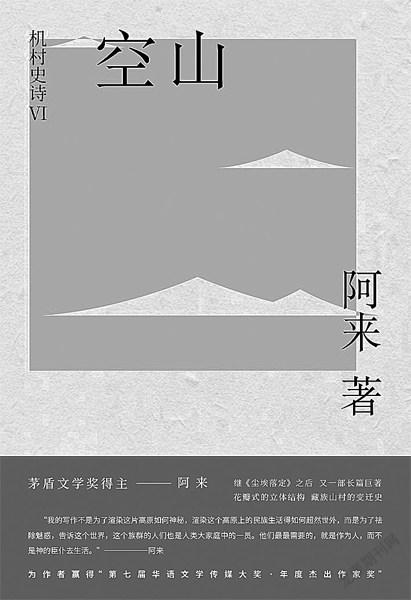
一
如果從迄今為止的寫作歷程來判斷,說藏族作家阿來是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具有鮮明生態意識的作家之一,應該是可以成立的。這有他的《大地的階梯》(2001)、《成都物候記》(2012)①以及其他大量地理生態散文,還有長篇小說《空山》六卷本②(2004—2008)和《云中記》(2019)等作品為證。后者在2021年度獲“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評委會授予的“年度杰出作家獎”,以褒獎阿來“延續了一種由邊地與少數族群出發而通達全球視野與普遍共識的開闊寫作,書寫了萬物并生不悖,文明和諧共處”③所取得的成就。
這種生態意識的形成,首先來自作家個體的切身體驗。阿來的出生地四川馬爾康縣馬塘村本來處于一片茂密的白樺林中,滿坡的林子曾是童年阿來采藥和嬉戲的天堂,“但我沒有能夠與這片美麗的樹林度完整個少年時代”,白樺林在20世紀60年代因城市建設需要被采伐殆盡,“古村豈止是失去了這些白樺,我們還失去了四季交替時的美麗,失去了春天樹林中的花草與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動物。從此,一到夏天,失去庇護的山體被雨水直接沖刷。泥石流年年從當年的泉眼那里暴發,沖下山坡阻斷交通”,但事情遠沒有停止,“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飄滿了大樹的尸體”④。這當然是四十年之后阿來的回憶和審視,已經帶上明顯的生態批判眼光,這里所記錄的兒時經驗本身,也并沒有在阿來創作的一開始就成為其核心主題。我們從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所看到的,是阿來對于康巴藏族歷史的傳奇式敘事,他當時在敘事藝術上的針對性,主要是為“逃脫那時中國文壇上關于歷史題材小說、家族小說,或者說是所謂‘史詩小說的規范”,要“在這僵死的規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尋我自己的敘事與抒發上的成功”⑤。這種對“邊地”藏族敘事的史詩性追求,也是阿來寫作獨創性因素中貫穿至今的重要內涵之一,從《塵埃落定》到“機村史詩”六部曲,正好是四川阿壩嘉絨藏族地區20世紀歷史變遷的投影。
阿來的生態意識的真正喚醒,應該也是感受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文壇的生態思潮的結果。隨著中國大規模市場經濟活動的開展,一時間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不斷出現,客觀上迫使中國作家開始認真對待生態問題。1999年是中國生態文學發展的一個特殊年份。這年10月在海南召開的“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是中國生態文學發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來自美國、法國、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和學者與會,帶來了經濟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生態批判思潮,他們反思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在生態問題上可能存在的盲點,呼吁重視生態問題,質疑無視生態的所謂“成功”,“喚醒對草木蟲魚悲情的感受”⑥。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壇生態意識的廣泛覺醒,對現代化與現代文明的生態批判進入一個高潮,韓少功、張煒、蔣子丹、葉廣芩、賈平凹、于堅、遲子建、雪漠、陳應松等作家先后都創作出具有明確生態意識的作品。就在同一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發起組織了名為“走進西藏”的“文化創作出版活動”⑦,阿來是首批受邀的七位作家之一。雖說這是一次由媒體事先策劃的行旅寫作活動,后來也被視為“媒體策劃與批評”的一個典型案例⑧,其策劃重點在于對邊疆區域文化的考察、探險與記錄,但阿來并沒有完全按發起方的預定路線與方式行事,而是把旅行與寫作的重點放在故鄉四川阿壩的嘉絨藏族聚居區,自稱是“預謀已久”的意圖。他“更多的將不是發現,而是回憶,我個人的回憶,藏民族中一個叫作嘉絨的部族的集體回憶”⑨。這里不得不提及阿來本人復雜的族裔和文化身份:阿來雖然自認屬于藏族中幾乎最為邊緣的嘉絨支系,但事實上又是藏回混血——母親是虔誠藏族佛教徒,父親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阿來早年生活在藏語山村,通藏語方言而不會藏文讀寫,接受漢語學校教育并以漢語寫作。由此可知,作家阿來對于語言、文化與族群身份具有天然的敏感。
正是1999年的這次故地重游,使阿來得以重溫早年記憶,并逐步獲得批判性的審視眼光。這種回憶與審視,至少包含了兩種精神指向:第一是指向四川阿壩地區這一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阿來對那些來自域外他者的西藏想象,始終保持一種警醒與批判,不論是神秘詩意意象,還是“邊地少數民族”想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阿來所質疑的那種“西藏是一個形容詞化了的存在”⑩。它們首先排除了具體的歷史性;其次,又把西藏想象為一個整體而忽略了其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對于阿來的故土而言,那就是阿壩地區的嘉絨支系差異性和特殊性。第二是指向川西北這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生態處境。阿來對方圓八萬多平方公里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理,有一個精確的描述:“這個地帶在現在的地理描述中應該是青藏高原東北部黃河第一彎上的若爾蓋草原,和草原東邊一直向四川盆地逐級而下的岷山山脈和邛崍山脈的腹地。”11這西北部的草原和東南部的山地一起,就構成了從四川盆地到世界屋脊這一“大地階梯”的過渡地帶。
這兩個精神指向對應了阿來的兩種觀察視角:一則是包含了特定的政治、歷史、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人文視角;一則是在東亞大陸板塊整體中的地理視角。兩者的結合就構成了阿來的人文地理學視野。而阿來在20世紀末的那次故地重游所激發起來的生態意識,正是基于這一人文地理學(或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這也是他的生態觀念和生態書寫區別于同時代其他中國作家的明顯特點。從這種觀念與視野基本形成而言,作為非虛構文體的《大地的階梯》是阿來寫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標志。我認為,書中的這段文字是上述審視眼光的典型表述:
從四川盆地邊緣縱深向青藏高原邊緣的階梯形群山達兩三百公里是一個巨大傷痕。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痕。雖然這個傷痕地帶也曾有過民族間的沖突與一些戰爭,但這些沖突與戰爭大多發生在冷兵器時代,還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態災難。這個傷痕的造成,就是進入現代史的近百年間,人類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設的名義,以大多數人的幸福與生存的名義,無休止索取的結果。12
作為隱喻的大地傷痕,既對應著人類沖突的歷史創傷,也對應著自然所經受的人類中心主義所帶來的生態災難,人文與地理、歷史與現實的多種因素在這段批判性文字中交集。自此以后,阿來的虛構性寫作也在史詩敘述的架構中增添了一種明顯的、富于特點的生態視野,這在隨后問世的“機村史詩”六部曲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尤以《天火》與《荒蕪》為最。不過,這種觀念與視野的形成,如何轉化為虛構寫作中的創造性,需要作家在敘述和表達上的持續探索和嘗試。
對阿來而言,文學傳統中的自然書寫是首先需要反思和揚棄的對象。他對漢語文學傳統中大量自然書寫,取一種批評態度,認為中國古典詩文中的自然,已被過分人格化,花鳥魚蟲、梅蘭竹菊、豺狼虎豹,在一代代文人筆下,都已演化為隱喻、象征或者意境,如丁香的愁、蓮花的潔,其象征意義已經固化,相應的自然意義則日漸萎縮和退化,并極言在“我們的抒情文學傳統中,自然是消失和不存在的”。阿來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斷或許因其偏激會引來爭議,但他提出應該像梅特林克、普里什文、契訶夫和屠格涅夫那樣,“把自然和人當作同樣的生命來看待”13,“把自己融入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14的主張,至少體現了其對文學的自然書寫方式的自覺,并在外來文學中獲得了某種方向性的參照與啟迪。
不過,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建構性的探索與創造本身。在《大地的階梯》后記中,阿來曾這樣放話:“我堅信,在我下一部長篇創作中,這種融入的意義將用更藝術化的方式得到體現。”15這里所說的“下一部”,會是指哪一部作品呢?如果按照寫作時間,可以認為阿來所指的是《空山》即“機村史詩”系列,批評家張學昕就是這樣認為的16。但阿來的藝術嘗試與探索的路并沒有終止,在其迄今為止的長篇小說中,《云中記》更應該是他理想中的“下一部”。
二
長篇小說《云中記》以2008年“5·12汶川地震”為背景,講述四川阿壩嘉絨藏族村寨云中村的災難遭遇及其災后重建故事。阿來本無意把它寫成一部生態小說,作品的題記之一就是“獻給5·12地震中的死難者、消失的城鎮與村莊”17,“歌頌生命,甚至死亡”才是這部地震題材小說的本意18。那場震驚中外的大地震發生在阿來的故鄉,他又是救災過程的親歷者和參與者,書寫這一重大又親歷的事件本是順理成章的,但阿來卻遲遲不愿下筆,而要等到大地震十周年之時才開始動筆。這十年間,他相繼出版了《瞻對》(2014)、《蘑菇圈》(2015)、《河上柏影》(2016)和《三只蟲草》(2016)等幾部作品,但所寫都不是那場地震。因為阿來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在新聞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有關災害中的慘烈、悲情、救助等大量細節,每時每刻都在即時傳遞,而作為一個作家的文學書寫,除了作為親歷者呈現災難場景、敘述刻骨銘心的悲情外,又能在其中增加點什么?如何能使文學之光不被現實所吞沒呢?
對于阿來,長達十年之久的情感控制、經驗反芻和動機醞釀,是為了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對于這個題材的表達方式,這個方式就是《云中記》所呈現的以“一個人,一個村莊”為核心,“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19。一個人“就是祭師阿巴”,一個村莊“就是位于岷江岸邊半山腰,海拔2800米的一片臺地上的嘉絨藏族村寨云中村”,它在“5·12汶川地震”中淪為廢墟,并處于震后山體的斷裂帶下,五年后又與山體平臺一起,轟然墜入岷江。這樣,在地震發生十周年之際,阿來終于找到了針對這場地震的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其中寫嘉絨藏族苯教的最后一個祭師,如何完成他的志業,祭奠一個傾塌了五年的村莊,回顧她的歷史,超度她的靈魂,最后與她一起消亡。全書的敘述籠罩在一種濃重的悲愴氛圍中,就像小說題記之二所顯示的基調那樣:“向莫扎特致敬/寫作本書時/我心中總回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如此,作家阿來的“一個年復一年壓在心頭的沉重記憶,終于找到一個方式讓內心的晦暗照見了光芒”20。
《云中記》的故事是從大地震五周年之際展開的:汶川地震后,云中村的幸存者全部內遷到四川平原腹地,村民們在移民村過上了新的生活,種茶、打工、開民族風味的山菜館等,但重大傷亡和家園傾毀所帶來的深刻心理創傷仍難平復,村里的藏族祭師阿巴一直惦記著死難者的亡靈和自己的職責。在地震五周年即將到來之際,阿巴不顧次生地質災害的危險,在兩匹馬的陪伴下,毅然只身上山,回到隨時有墜塌危險的云中村廢墟,以嘉絨苯教的儀式,為天地山川、草木屋宇與人畜亡靈祭祀超度,并執意與云中村共存亡,最后同村莊一起墜落而下。
小說的敘事,也以上述情節為線索,以時間為章節標識而依次展開21,敘述阿巴在地震五周年祭的三天之前,獨自上山返回云中村廢墟,從準備和實施祭祀,到隨后幾個月的獨自守候,最后隨云中村一起墜落的經過。在這樣的敘事結構中,阿來并沒有正面展開地震發生時的驚恐一幕,也沒有正面呈現震后的慘烈與救援中的悲痛無奈、奮不顧身和守望相助的具體場面與情節,即不以現在時態連續展開災難敘述。所有關于大地震的發生、震后救援與重建的大量場景與細節,都是穿插在阿巴的祭祀招魂儀式中展開,以主人公意識回閃及對話等方式交錯呈現。這種敘述結構在時間維度上的回溯,既指向“5·12汶川地震”及震后救災這一核心事件,也指向震后五年間當地村民對嚴重心理創傷的修復和災區的重建;在相反的方向上,更指向云中村的震前歷史,乃至追溯到族裔遷徙傳說與起源神話。這就使作者得以從地震大事件的正面敘述中掙脫出來,獲得表達上的某種自由空間:不僅可以確定一個特定的敘述角度,還可借此呈現和表達時空上更寬廣、意蘊上更復雜的主題,其中也包括這部小說在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意義上所體現的意涵。
如前所述,阿來本無意于把這部地震小說寫成一部生態小說。雖然文本中也涉及了許多有關生態問題的場景和情節,如過度放牧致使草地荒漠化、濫挖蘭草導致資源枯竭、對野生保護動物的捕獵、盲目建造水電站導致泥石流災害,等等。這些當然是生態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內容,但并非《云中記》這部地震小說敘事的關鍵構成,它們與地震這一核心情節并不具有必然關系,事實上作者也沒有對此費太多的筆墨。
本來,生態主義所關注的焦點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反思與批判人類如何在文明進程中不加限制地向自然攫取,由此導致自然生態的系統崩潰、資源枯竭、災害頻發等嚴重后果,由此調整當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但地震是天災,其根本起因即地殼運動與人類行為和意愿本來并無關聯22。如果說生態主義意在追究生態惡化進程中人類所應該承擔的責任,那么,面對地殼板塊運動所導致的地震,人類似乎只能被動地接受它的降臨,包括對生命的毀滅、對生態的破壞。如此,關于地震天災的敘事似乎只能歸于宗教宿命主題,或如道家哲學所謂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無情”,人類對之只能無可奈何。但如果擴大問題域,答案就不會那么簡單眀了:如果說地震的發生并非起因于人類也非人類可以控制,那么地震災害包括它的次生災害給不同時空、不同文明程度、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類群體所帶來的后果則是不同的;如果引入文化人類學和人文地理學的視野,則有可能揭示特定地震帶與特定的族群、宗教與文化之間的具體歷史關聯。由此還可進一步追問:在一場特定自然災害爆發與次生災害的后續發生過程中,相應于不同的預防、救災和重建的手段與機制,同等程度和相似類型的災害對不同社群的身體與心理、生產與生活所造成的傷害,其方式與程度有沒有、有何種差異?這種差異的具體成因如何?《云中記》正是在這一維度提供了想象和進一步闡發的空間。
小說敘述的“5·12汶川地震”處于中國四大地震帶之一的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震帶上,是印度板塊大陸嵌入并擠壓的結果。阿來借筆下瓦約鄉鄉長仁欽的分析,向讀者呈現了這一視角:
世界地理板塊,印度次大陸從南邊沖過來,使得青藏高原高高隆起。這股力量一路往東,瓦約鄉所在的岷江河谷這些高聳又破碎的山地,就是這股持續不斷的力量壓迫的結果。這力量在地下積蓄,過百十年就爆發一回。那在地下暗黑處運行的力量只顧造成新的地貌,卻對地面上的人間悲劇毫無同情。23
從地震學角度看,這種地殼運動并不起因于生活于地表的蕓蕓眾生,但這片土地為什么由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人群依附其上?為什么處于青藏高原東部邊界的山巒皺褶地帶的阿壩地區,恰好祖祖輩輩生活著嘉絨藏族?阿來通過祭師阿巴對云中村歷史由近及遠的回憶,追溯了嘉絨藏族古老的族群遷徙歷史,使這一人文地理學意義上的問題得以生動形象地呈現。在這里,具體而獨特的地理、民族、宗教、文化與歷史相互疊加,作為天災的地震也與特定的人群和生活方式相互交織。而與地震相關又遠遠超出地震的生態系統的種種遭遇,也就在這多重交織中才可以全部顯現。這其中就包括了生態批評通常所關注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維度。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即使相對于地震這樣的天災敘事,也不必然與生態問題無關,而同樣可以呈現其生態批判的意義。
因此,盡管阿來不是刻意將《云中記》寫成一部反映生態問題的小說,但其生態意識使他能把小說所要思考的生死問題置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系統中,置于現代文明進程所遭逢的種種問題中去認識。正如小說另一則題記所示:“大地震動/只是構造地理/并非與人為敵//大地震動/人民蒙難/因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無處可去。”24阿來所思考的有關生命的意義、靈魂的有無、族群與認同、信仰與科學、儀式與療治的關系等問題,不僅屬于人類自身,也屬于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大自然,在這個意義上,《云中記》就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作品。
三
在“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給阿來的頒獎詞中,“邊地與少數族群”這一關鍵詞,對《云中記》的描述雖然并不完整,但也反映了該作在當代漢語文學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作品給漢語讀者帶來最深印象的,或許不是所敘述的“5·12汶川地震”這一著名事件本身,而是在災難背景下所呈現的主人公阿巴這位藏族苯教祭師形象,阿巴所施行的古老祭祀儀式及其感染力,以及借助阿巴所上溯的嘉絨族裔歷史與古老傳說。
《云中記》祭師阿巴所信奉的是藏地苯教中最傳統的一支25。由于它根植于藏族原始文化之中,因而對藏文化特性及傳統有著深遠影響。阿來在小說中所描述的是在藏地最為原始、行將消亡的宗教傳統,選擇一個祭師阿巴作為主人公,顯然有著復雜的寓意,阿巴與“阿壩”諧音,也透露了這一消息。而今天作為阿壩行政中心的“馬爾康”這個地名,也是源于15世紀之前當地曾建起的一座規模宏大的苯教寺院。
在藏族聚居區,其古老而悠久的宗教觀念和儀軌行為,已經完全內化于藏族民眾的共同生活習性之中。今天藏族人的習俗和生活方式中,有許多也是古象雄時期留傳下來的,比如轉神山、拜神湖、插風馬旗、插五彩經幡、刻石頭經文、放置瑪尼堆、打卦、算命、轉經等習俗都有苯教遺俗的影子。小說《云中記》中“第七天”一章中阿巴所吟誦的阿吾塔毗的傳說26,就對應了這一最為古老的神話傳統。阿來選擇藏文化的這一脈傳統作為小說主要呈現的對象,顯見其追溯自身文化血脈的宏愿。其實,阿來在這方面的準備,長篇紀實散文《大地的階梯》就已經有系統的呈現。
兒時的阿巴只在黑夜里和山野無人處(在磨坊憩息)偶爾看到父親的一些祭祀動作。改革開放后,政府為拯救民間文化遺產,說服阿巴擔當起祖輩的職業并將他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但阿巴作為祭師最起碼的一套祭祀儀式規程,還是在當地政府組織的“非遺傳承人”培訓班上,由鄰村的一位佛教喇嘛來傳授的,這位喇嘛顯然在信仰上不認同、甚至瞧不起阿巴的苯教,聲稱“你們的阿吾塔毗不可能同時是金剛手菩薩”,只能作為金剛手菩薩的陪侍27。而阿巴一開始也并不接受這一神職身份:“呀!怎么可能!一個人聽過《不怕鬼的故事》那本書里的全部故事,上過農業中學,當過云中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發電員,現在怎么成了一個祭師?”28他是在被動地接受“非遺傳承人”這一名號,為配合當地政府開發旅游資源而主持起祭山儀式后,才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知識、信仰和祭山儀式之間的內在關系,慢慢尋得苯教祭師身份感。
真正使阿巴領悟苯教傳統的是云中村的老喇嘛的臨終傳授29。阿來在小說中設置的這位老喇嘛,是作為祭師阿巴的精神導師形象出現的。他的身份雖然是個佛教喇嘛,但實際上卻是苯教的傳人。小說里喇嘛出場時就已經是一副老態,似乎已到了生命的盡頭,他牙齒脫盡,幾乎不吃飯、不喝水、不說話,每天呆坐于門前的蘋果樹下。但這個形象正是傳統蟄伏待機的象征:苯教古老傳統借助于佛教的面目和喇嘛的軀殼保存下來,等待著它真正的傳人。已經有了苯教祭師身份的阿巴,對這位同村的老喇嘛的態度,也逐漸從不在意變為好奇與疑惑。只是有一天老喇嘛突然喝令阿巴跪下,在兜頭一盆冷水之后,再給阿巴一番面授機宜。從此阿巴神清氣爽,眼睛明亮。而喇嘛之后則又至死閉口不語了。我不知道阿來筆下這一段情節,是有苯教傳說的原型依據,還是阿來的想象虛擬,但它不僅生動,富于傳奇色彩,而且形象地寄寓了阿來呈現藏地古老文化傳統的用心。
從人物塑造角度看,老喇嘛醍醐灌頂式的“棒喝”或“點化”,是阿巴精神成長歷程的一次突變。但作者并沒有直接呈現人物內心變化過程,而是給予如上所述的傳奇性敘述。與此形成對照的另一次精神突變,就是他親歷并目睹的陡然降臨的大地震,災難的慘烈場景給云中村人所帶來的重大心理震懾、刻骨的生死傷痛和普遍的精神迷惘。在災后重建和移居的五年里,阿巴反復追問著生死的價值、靈魂的有無和神靈的意義。作者并沒有明確地告知,阿巴這個云中村曾經的“文化人”和“第一個發電員”最后有沒有真正信奉古老的傳統,他對有沒有靈魂似乎仍存有一絲保留,但他對自己作為一個祭師的身份與責任顯然有了深深的認同。他對地震后一起來到移民安置地的云中村人說:“你們在這里好好過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師,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顧鬼魂。我不要他們在田野里飄來飄去,卻找不到一個活人給他們安慰。”30在另一處,小說以敘述人口吻這樣陳述:“但愿這個世界上沒有鬼魂。但是……如果萬一有的話,那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太可憐了。作為一個祭師,他本是應該相信鬼魂的。他說,那么我就必須回去了。你們要在這里好好生活。我要去照顧云中村的鬼魂。”31正是災難的突然降臨,逼迫著阿巴完成了作為祭師的身份認同,又獨自返回云中村廢墟,為那里所有自然與生命遺存一一施祭,并陪伴古村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從而踐行了作為最后一個祭師的使命。
四
作為自然災害題材小說,《云中記》雖然將災難發生的慘烈場景和抗震救災的過程以五周年之后片段性回溯的敘述方式加以克制性呈現,讀者仍能借此想象當年舉國救難、全民賑災、守望相助的感人情景。對于阿來這樣成熟的作家來說,這樣的場面與基調的展現與敘述把控,是讀者意料之中的。但阿來在災難敘述的同時顯現了另一個特質,即伴隨這種基調的對于所謂“災民心態”32的種種表現與“表演”的刻畫與批判,這種清醒的批判意識既針對大地震這一災難場景中的某些特定行為,也指向現代文明與后現代技術所引發的一系列“異化”現象。它們包括對災難的商品化消費、表演,乃至唯利是圖的行為。如央金姑娘災后的舞蹈直播,祥巴策劃的乘熱氣球觀看云中村廢墟的旅游項目,以及其他一些對死亡與痛苦的麻木心態,等等。總之,在阿來的敘述中,災難所引發的驚恐與創痛、救難賑災的悲憫與感人,并沒有淹沒其對“災民心態”的審視與批判。這種批判意識的獲得和呈現,一方面是之前的“史詩性”寫作追求的某種延續與變奏,另一方面也是他將這一重大題材的寫作沖動克制、延宕了十年之久的一個回報。
而這種批判理性在作品敘事中的呈現,正與原始苯教傳統及祭師阿巴的形象有關。在作品中,這種原始信仰傳統中對生靈萬物一視同仁、對善惡的包容與超越,與阿來所謂的“災民心態”形成一種精神價值上的鮮明對照。需要指出的是,阿來的這番用心,并不是真要為古老宗教振衰起敝,更非宣揚具體的宗教教義。正如劉大先所說的,“自始至終,敘述者與敘述對象都沒有確認災難死者的鬼魂或亡靈的真正存在,他們只是阿巴情感與幻想之物,而非某種超驗的實體性存在,這與文學史上那些鬼怪幽靈判然不同……因而也并沒有產生恐懼、異類、神秘之感,而是與生者的認知和創造有關”33。但作者以阿壩地區這一亞歐大陸板塊(《大地的階梯》)的皺褶地帶,同時也是歷史文化中處于多重邊緣區域的災難故事,和行將消逝的民間宗教祭師形象,作為小說的核心敘事場景、線索和主要人物形象,意在呈現一種古老文化與精神傳統的象征。它為漢語讀者呈現藏地精神文化傳統的悠久、豐厚與多元,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多元文化與平等觀念,以及對社會文化生態平衡與和諧的祈愿。
這種原始信仰傳統也為文學作品引入了一種萬物有靈的生動的敘述視野。這樣的傳統崇奉天地、日月、星宿、雷電、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獸、神鬼精靈和自然物。由法師進行占卜、祈禱、禳解、咒術、祭祀及各種特殊儀軌加以表現,有著薩滿時期古老信仰的一般特征。從文化發展進程來說,這種泛靈信仰是人類最初對自然萬物的朦朧認識的表現。這一萬物有靈世界,在《云中記》的敘述中,通過祭師阿巴的視角和他主持的祭祀儀式而一一展開。一年一度由全村男女共同參與的“朝山節”是祭奠山神,它是祖先阿吾塔毗的化身;為村頭的神樹——老柏樹行儀作法,它的最后枯死是地震的前兆;震后重返云中村,阿巴為每家每戶焚香祈禱,為每一位遇難的亡靈招魂超度,無論男女老幼、良善或頑惡、大度或吝嗇;在阿巴眼里,山林的大小動物,田野的一草一木,村里的石碉、磨坊、塌屋、殘墻、柴垛子、水池子,乃至水里的綠藻們,都是有生命有靈魂的存在,都可以傾聽與對話。在這個泛靈世界里,更有如遇難于巨石下的阿巴妹妹(仁欽母親)顯靈于鳶尾花這樣的動人情節,它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手段,而是整個泛神世界的有機組成。阿來本無意于將《云中記》這部地震題材小說寫成一部生態文學作品,但在追溯本土古老信仰傳統,呈現泛神觀念和通靈視界的同時,也許是無心插柳,恰好為當下人與自然關系這一生態命題及其文學表現,提供了一種激發和運用傳統文化資源的有效途徑和生動的作品,體現了作者對文學生態功能多樣性的追求。
《云中記》這部經作者十年醞釀的作品,為書寫“5·12汶川地震”這場災難找到了一種獨特的形式。他選擇了以“一個人”(祭師阿巴)——“一個村莊”(云中村)為基本敘事架構,激發并表現了一個族群的文化傳統記憶,將作者、敘述人、人物及其文化原型之間的多層次關系,熔鑄到一個悲劇性的形式結構中,從而使作家本人的書寫行為與祭師阿巴形象的祭祀行為,形成互為映襯和隱喻的關系,也使文學言語行為與語言(文本)結構相互耦合,共同體現了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話語的施為功能。同時,《云中記》還在文學功能的多元化發掘和神話原型敘事開拓的向度上,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富于啟發性的文本。它以一個災難敘事,為恢復文學對創傷心理的療治功能,克服文學因現代分化所導致的功能單一傾向,做出一次成功嘗試,因而在媒介與文化融合的當代語境中預示了一種新的文學可能34;它還為發掘與轉化中國豐富的神話原型資源,在文化人類學意義上開拓中國當代文學的題材和路徑,從而在更加開闊多元、更具文化縱深的意義上,想象、呈現與闡發中國文學的世界性,為同世界文學的其他偉大傳統間展開有效的對話,呈現了一個成功案例。
【注釋】
①此書有三個版本:《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花重錦官城·成都物候記》(成都時代出版社,2018)和《成都物候記》(“阿來散文集”之一,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②《空山》六卷本系列,又稱“機村史詩”六部曲,包括《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
③“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由十月雜志社組織,首屆獎項于2021年9月4日在貴州綏陽頒發,評選范圍為2019—2020年度發表作品。見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90061。
④⑨11121415阿來:《大地的階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第55-56、338-339、13、58、343、343頁。
⑤阿來:《世界:不止一副面孔》,載《看見》,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第207頁。
⑥白爾木:《人與昆蟲的共同命運——99海南“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紀要》,《新東方》1999年第6期。
⑦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由新聞出版機構組織的考察與寫作活動一度成為文化熱點。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劃“解讀中國民族文化萬里行”,于1999年組織的扎西達娃等7位作家“走進西藏”、2000年組織賈平凹等9位作家“游牧新疆”,隨后出版“解讀中國系列叢書”;此外,2000年,鷺江出版社策劃名為“極地沉思”的考察寫作活動,組織葛劍雄等6位人文學者赴南極考察寫作。
⑧宋炳輝:《文學媒質的變化與當代文學的轉型》,《文藝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
⑩阿來:《西藏是一個形容詞》,《青年作家》2001年第1期。
13阿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與書寫》,《科普創作》2020年第3期。
16張學昕:《孤獨“機村”的存在維度——阿來〈空山〉論》,《當代文壇》2010年第2期。
17阿來:《云中記》題記之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18192032阿來:《不止是苦難,還是生命的頌歌——有關〈云中記〉的一些閑話》,《長篇小說選刊》2019年第2期。
21小說共12章,章節標題依次為: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六天、第七天、第一月……第六月、那一天。
22地震一般分為天然地震和人工地震。人工地震當然與人類活動相關,可以納入生態問題討論。這里所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地震,即天然地震中的構造地震。
23262728293031阿來:《云中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第339、162-164、172、79、174-180、46、58頁。
24阿來:《云中記》題記之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25苯教是古代西藏地區盛行的一種原始宗教,又稱“苯波教”。“苯”的本意為反復念誦,“苯波”(Bon-po)則是反復念誦者,原是藏族在遠古時期專門從事宗教活動的巫師稱謂,爾后逐漸演化為這種宗教的名稱。
3334劉大先:《作為記憶、儀式與治療的文學——以阿來〈云中記〉為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3期。
(宋炳輝,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