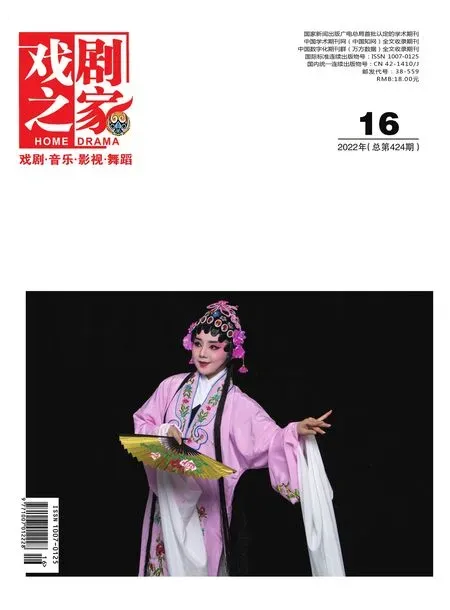流落的歸所
——區域劃分對舞臺呈現的意義
鄭家樂
(山東藝術學院 山東 濟南 250300)
在戲劇藝術中,各流派藝術家對于演出區域的問題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本質還是與舞臺美術的功能與特性相對應。也就是說,戲劇藝術的綜合性使得區域問題無法拋開舞臺美術功能與特性問題而獨立探討,即與演員、導演協作展示戲劇演出的內涵。這便意味著戲劇藝術的綜合性使得更多的新時代舞臺美術家傾向于將“演出場所設計”的重點放在“舞臺區域設計”方面,各藝術家對“區域的劃分”同樣包含對舞臺空間的理解。
一、圍合空間的變體
戲劇演出是建立在演出場所、高度精煉現實實體因素的藝術創作,在中國大眾審美情趣的推演下,“舞臺”逐漸成為適應國人傳統審美體驗的演出場所,觀眾與舞臺在“距離”的調節下彼此相交融。“舞臺”立于觀眾之外,觀演關系不再與觀眾客體融合,而著力追求與觀眾情感上的共鳴,無論舞臺空間內部結構繁雜或簡樸,“圍合”始終是舞臺本身所具有的藝術化特征。區域的劃分本質上是對舞臺空間的劃分,充滿圍合的空間中,區域也將不自覺地擁有“圍合之意”。
(一)服裝的圍合——服裝配合演員調度劃分舞臺空間區域
舞臺美術各部門藝術創作中,對空間的把控似乎并不是服裝部門應展現的本質性藝術特質,但戲劇演出是“實體真人”所構筑的演出,演員在舞臺上自覺或非自覺地充當起詮釋戲劇藝術核心思想的工作,其自身與舞臺演出造型因素的結合無可避免地起到一定程度的“焦點”作用。而演出伊始,觀眾因“服裝”注意到演員,演員首先面向觀眾的也是“服裝”。服裝造型的夸張、顏色的亮麗,都會引導觀眾給予演員更多的關注,某種層次上講,演員因為服裝才得以成為“焦點”。在演員履行調度而對某一區域進行圍合的過程中,身著在演員身上的服裝在更高層面上伴隨演員的行動去劃分舞臺區域。
2019 年杭州大劇院上映了由里馬斯·圖米納斯執導的《浮士德》,在浮士德變年輕的一幕中,浮士德的扮演者經歷了3 次服裝的變化:老年浮士德身著黑色長袍頭戴高頂帽,在舞臺兩側巫女的簇擁下,圍繞魔鬼旋轉一周,又進入舞臺主體物旋轉的“方盒”;此時舞臺左側身著破爛的巫女帶道具“鐵桶”上場,巫女們將半裸上身的浮士德從主體物中拉出,并將頭按入位于舞臺左側的桶中,燈光暗淡,巫女們身披具有銅片的服裝集中在浮士德周圍運動,提供金屬碰撞聲的同時形成一道“墻”,浮士德周圍形成“區域”,與魔鬼的扮演者所處的舞臺右側形成對比,當浮士德從桶中抬頭,伴隨白色頂光轉為黃紅色頂光,浮士德變為了年輕人;在巫女的歡呼中浮士德回到“方盒”,以一身淺色西裝出現并再次圍繞魔鬼旋轉一周,巫女跟隨浮士德身后旋轉一周并四散逃開,舞臺區域再次回歸一個整體。巫女的介入將原本統一的舞臺打散為“區域”,伴隨巫女的調度,舞臺組合、圍合成為兩塊相較區別的區域,巫女身著的銅片服飾、浮士德的“半裸服裝”都使得觀眾約定俗成地認為,舞臺劃分為兩塊適應于浮士德、魔鬼的專屬區域。同時,浮士德扮演者先后兩次圍繞魔鬼的旋轉無不暗示著老年浮士德經過舞臺左側的洗禮后以年輕的姿態回歸到了舞臺右側(故事情節),而身著特殊服裝的巫女緊隨其后正是加強了“左側區域融合回右側區域”的暗示。
(二)隔透的延伸——用三維造型物劃分二維平面區域
“隔與透”本應屬于對區域劃分的藝術創作方法,但卻具有更深層次的藝術價值取向,即在二維平面上用三維立體造型來劃分區域。在此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二維平面”僅僅代表最低層面“臺框”所處的舞臺空間,即“臺框的圍合空間區域”,在鏡框式舞臺中,臺框區域處在一個二維平面空間,舞臺臺板上發生的一切戲劇活動經過臺框的限定,似乎成為了一幅由臺框裝裱的二維平面“畫作”。觀眾只能從舞臺正面欣賞戲劇演出,舞臺上三維造型景物的使用或演員的行動與調度一定程度上劃分著二維“畫作”的區域。而戲劇藝術真正區別于架上繪畫的關鍵,正在于“舞臺是運動的”,運動的舞臺盡管在某種意義上能產生與欣賞二維“畫作”相似的審美體驗,但“運動”勢必包含藝術家對三維立體思維的建構,對“隔透”的運用更是其他二維藝術所無法觸及的層面。
2002 年中國國家話劇院上映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女兵洗澡一幕中,舞臺上方緩慢落下一塊“樹林板”作為遮擋物,女兵在歡笑中進入樹林板與背景中間區域,隨著時間的流逝,女兵間談笑聲逐漸衰弱乃至消失,燈光暗淡并從原本黃色泛光過渡為藍白色頂光,其中幾位女兵們雙手合十舉過頭頂做沐浴狀,但由于“臺框”的作用,此時的行動更是女兵們的精神象征——向戰爭“祈禱”以求安穩,在情感上替女兵們表達了一種“平靜的虔誠”。“樹林板”作為三維立體造型物劃分了三維舞臺空間,但同時劃分著二維“畫作”的空間區域,觀眾能夠將演員雙手合十舉過頭頂這一洗澡動作體會為“祈禱”,并不是單純由于樹林板分割了三維舞臺空間區域,而恰恰在于樹林板將二維平面分割成了具有“前后空間感”的區域;同時演員躲在樹林板后組織動作,使得樹林板劃分出了舞臺前區的一部分區域從而產生二維空間意義上的“距離”(距離正是樹林板劃分出的前區這一小段),這段區域或距離在三維立體空間中微乎其微,但在“臺框”限定的二維“畫作”內卻形成恰到好處的“構圖美感”。空間、構圖都試圖達到“二維畫作”的水準,觀眾在視覺審美舒適的狀態下自然能夠參與、體會演員動作內涵。從舞臺區域劃分的向度來理解“樹林板”,它作為戲劇演出中的“隔”物,“隔”住了區域卻將人情氛圍從樹林板后區“透”向樹林板前區觀眾,似是“隔中有透”,但若立于更高層面來理解“隔透”,定會探尋到區域劃分多半表現出的“透中有隔”:觀眾落座于觀眾席的瞬間實則就進入一種“情感空間”,一塊三維“隔”物將人情擠壓進觀眾席,觀眾通過二維畫面而意識到情感的涌入,這種通過“實體物”完成“三維與二維的隔”和“觀眾與情感的透”,正是舞臺美術乃至戲劇藝術所追尋的“藝術感”。
二、區域劃分的功能性
為講好戲劇故事,導演、演員運用自身藝術特性進行藝術創作,舞臺美術運用對區域的劃分與演員、導演配合共同演繹戲劇“故事”。“區域劃分”屬于舞臺美術藝術特殊的舞臺呈現方式,透過舞臺美術對區域劃分的藝術性表現,體現出的“時空、氣氛的功能”適應于舞臺美術更大范圍的功能與特性。“彰顯獨特并為戲劇整體性創作奉獻”是舞臺美術功能從整體宏觀的尺度去觀察的結果,“區域劃分”在此類表述的理論基礎上,創造出“協同各部門講故事”的新型功用。
(一)體現布景的中性特質——借助區域表現靈活多變的演出空間
現當代中國戲劇演出實踐呈現出“多元、中性化”,觀眾需引用自身對生活經驗的想象與體驗,來參與、欣賞戲劇,而伴隨舞臺始終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成為舞臺美術家無法規避的問題。“舞臺是演出場所”的立論將藝術家“對舞臺空間的理解”推出了“逼真場所”的限制,以“概括化的總體視覺形象”而展開的舞臺空間呈現出“中性”特征。中性布景所營造的舞臺空間恰如其分地滿足舞臺美術對“區域”個性化表達的需求,不同區域所產生的“空間”能夠以非生活邏輯而共生于舞臺之上,不同位置可以表達不同人、不同事件,并配合導演、演員完成更高質量的“故事呈現”。
2001 年中央實驗話劇院上映由田沁鑫執導的話劇《狂飆》日本戲劇一幕中,歌舞伎身著亮麗服飾跪立于舞臺右側,田漢自歌舞伎后側緩慢運動至舞臺左側空間,歌舞伎存在于“戲”里,與田漢本不屬于同一時空,因此舞臺燈光給歌舞伎一束白色頂光,給田漢一束白色側光,二者區域因燈光而被劃分明確,“現實時空與戲中時空”共存于舞臺。田漢的登場使得原本只是“戲中人”的歌舞伎表演化為了與田漢精神世界共鳴的依附物,同時田漢身著藍色素色外衣與歌舞伎彩色和服形成暗示,配合演員所處區域的不同使得觀眾能夠清晰明白田漢對“彩色生命”的向往。而后燈光伴隨音響隱約照射出舞臺后區的“黑衣人”,他們在田漢與歌舞伎發生情感交流的時刻念著“歷史時間軸”,舞臺被劃分為三塊區域并象征三種不同的時空區域,更充分全面地向觀眾講好“歌舞伎因暗殺失敗而跪立于舞臺”的故事。在后半場“皇帝”出現的一幕中,皇帝、大臣等人位于舞臺右側展開一系列行動,同時左側飾演老百姓的演員上場,舞臺被劃分為左右兩部分區域并且空間也分為“皇宮時空與農村百姓時空”兩部分,右側區域的皇帝每發布一項詔書政策,都會影響左側區域老百姓的生活,故事“皇帝昏庸導致民不聊生”在舞臺劃分出的兩種區域、空間的交流中更為直觀。
(二)完善事件的表達——區域劃分表達人物情感并塑造氣氛
藝術化的區域劃分手法必將尊重對戲劇藝術本質的理解,而戲劇藝術是“展現人情感的藝術”,舞臺美術對戲劇整體性演出有著“氛圍塑造”的功能,區域的劃分應“自覺而非自然”的符合區域內人物情感特征,情感的外化與區域本身所蘊含的“組合節奏感”促使舞臺氣氛的形成。跌宕的舞臺事件使得舞臺作為演出場所需要不同區域的聯合協作,而具有情感化的區域能夠引起與觀眾在心理層面的共鳴,借助觀眾想象從而完成事件所表達的意義。區域劃分在與事件、人物情感所聯系的過程中主動地完成戲劇氛圍、人物氣氛的塑造,從而在更高層次完成“故事呈現”。
2019 年杭州國際戲劇節上演的《神魚》,全劇因極簡樸素的布景結構,使得演出中充斥大量對區域的劃分與使用。在屠夫、金掌柜、書生、守魚人協商處理神魚一幕中,金掌柜居于魚缸偏右區位,書生居于魚缸偏左區位,屠夫夾在兩人身后,而守魚人則默默坐于舞臺右下區位看三人爭吵,在金掌柜拿出紙質“賣魚契”并嘲笑二人愚笨時,屠夫被書生教唆將契約奪回并撕碎從而引出下一事件“金掌柜怒斥神魚惹惱守魚人”。屠夫生性粗魯、不識文字,因此站于舞臺偏后區域不被二人待見,而屠夫因憤怒從舞臺中后區沖向中前區一把奪過“契約”并其撕毀時,書生的本性優柔寡斷,見“契約撕毀”便故作震驚在魚缸左側走“曲線踱步”,金掌柜則呆立于原本所在的區域。“屠夫的魯莽、書生的狡猾、金掌柜的咄咄逼人”,人物性格與情感在聯系事件的區域劃分、運動中得以展現。而當金掌柜將悶氣發在神魚身上時,位于舞臺右下區位的守魚人站起并大聲呵斥,走向三人所處的舞臺中區,舞臺區域從四塊獨立區域轉化為兩塊區域,即憤怒的守魚人所在區域與驚慌的三人所在區域。守魚人從舞臺后區黑暗中拖出三袋魚食,并揚言將神魚贈與吃魚食最多的那位,舞臺燈光逐步暗淡,一場幾近癲狂的心理時空即將呈現在舞臺之上。原本具有“人物情感特性”的區域由于守魚人的介入不再獨立,事件發生轉變的時刻區域劃分也表現出“重組”,觀眾在兩種情感不同的區域空間中品味出區域內人物所自帶而成的氣氛與力場,而在進入心理時空的瞬間,舞臺氛圍進入了高峰,觀眾不再淺顯地僅從視覺層面去理解舞臺上發生的行動,而從主觀想象、參與的層面去體驗戲劇人物。舞臺美術層面的“區域劃分”在觀眾無意識的條件下配合事件、演員行動、導演調度完善了“人情味的故事”,塑造戲劇人物情感并創造舞臺美術獨具藝術特色的氣氛。
綜上所述,區域劃分的作用固然存在爭議,而各大藝術流派、藝術家所認同的功能性顯然是現當代戲劇藝術演出創作的前提,但對于演出區域、空間等問題的研究并不能止步于此。區域作為戲劇藝術家“靈魂”的歸所,在完成戲劇本質表達的基礎上,自然在尋找能夠“安放精神”的歸宿,同樣對于欣賞戲劇演出的觀眾而言又何嘗不在演出場所中探尋這種區域呢?區域的作用遠不止以上所探討的方面,觀眾視角中的區域也許并不存在所謂“圍合、時空、情感”的作用,觀眾來到劇場看一部演出實質是將自己托付于“非現實的、假定的”戲劇情境,在各部門協調合作的演出場所中品味人生百態,離開劇場的同時拾起自己“存放”在劇場外“現實世界的缺點”。演出場所中的區域似乎成為了觀眾、演員、導演、劇作家等人的“寄托點”,是一種包含所有寄托的“流落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