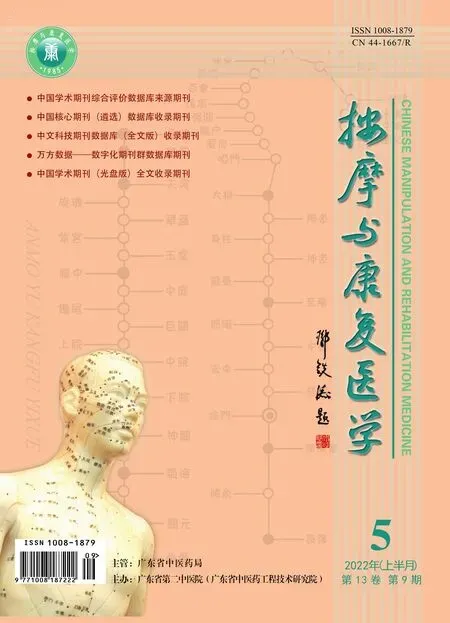李希辨治間質性肺病的臨床經驗
林 雄,李 希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福建福州 350003)
間質性肺病是一組主要累及肺間質和肺泡腔,以彌漫性肺泡炎癥和間質纖維化為主要病理生理表現的疾病,包括200 多種急慢性肺部疾病,如結締組織相關性間質性肺病、肉芽腫性間質性肺病、特發性間質性肺炎、過敏性肺炎等,不同類型的間質性肺病患者其臨床表現不完全一致,多為隱匿起病,臨床上以進行性呼吸困難、胸痛和喘鳴、持續性干咳等為主要表現,肺功能檢查可見限制性通氣功能障礙、彌散功能下降等[1]。間質性肺病的病因至今尚未完全明確,對診斷及治療均存在挑戰。李希老師是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呼吸病專家、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肺部疾病的中西醫結合臨床診療工作,筆者有幸跟師隨診,受益良多,本文對李師中醫藥診治間質性肺病的臨床經驗進行總結,現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
間質性肺病在祖國傳統醫學中并未有能與其完全相對應的病名[2],各醫家根據其患者如干咳、進行性呼吸困難等臨床表現的不同及其不同的發病機制,大致可將其歸為“咳嗽”、“喘證”、“肺痹”、“肺痿”等范疇[3]。李師認為“肺痹”的病機特點可多見于間質性肺病中早期,主要病機在于肺絡瘀阻不通;“肺痿”的病機特點多見疾病后期,多為肺津不足,肺葉痿弱不用。
“肺痹”的論述首見于《黃帝內經》《,素問·痹論》“肺痹者,煩滿喘而嘔”指出肺痹的主要表現為胸膈滿悶,氣喘而欲嘔。對肺痹的病因也有相關的表述,如“皮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肺”,認為肺痹主要在于肺外合皮毛,皮表反復感邪,邪氣由此入里,內閉于肺,壅塞肺氣,痹阻肺絡,日久而成;同時,《黃帝內經》也指出痹證病因多為風寒濕三邪相合而成。后世醫家也對肺痹的成因有相關論述,如《癥因脈治》曾載:“肺痹之成因,或形寒飲冷,……肺氣受損,而肺痹之癥作矣。”指出“肺痹”可由寒熱不調、飲食不節、情志不暢等因素造成肺氣損傷而引發,肺為嬌臟,不耐外邪,外邪反復侵襲而致肺氣受損,故成此病。陳士鐸《辨證錄》言“肺痹之成于氣虛”則認為主要病機在于肺氣虛弱,故易感受外邪,邪氣阻滯經絡,氣血凝滯,久而成肺痹。
“肺痿”病名首見于《金匱要略》,其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重亡津液,故得之。”指出肺痿可因發汗太過、或嘔吐、或下利太過又失治誤治等情況,致使津液進一步耗傷,總述其病因主要在于津液虧耗,肺失濡養而成,并辨其病,將之分為虛寒肺痿、虛熱肺痿兩種證。《金匱要略》“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則提出虛寒肺痿的病機為肺氣虛冷,胸中陽氣痿弱不振,以致肺氣宣降無權,水道失于通調,水津不能四布,留而為飲,停蓄于肺,故見口吐清稀涎沫而不渴[4],治用甘草干姜湯;而描述虛熱肺痿“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認為其病機在于津液虧耗,肺津不足,肺失于濡養,不能通調水道,脾氣升清之津液不能輸布,停留肺中,熱邪煎熬,煉液成痰,治以麥門冬湯。
現代中醫認為,本病的病位在肺,并與脾腎二臟聯系緊密,其病因多為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不節、他病失治誤治等因素,以致脾胃虛弱、腎精虧虛,損及肺臟,氣血循行受阻,以致氣滯血瘀、損傷脈絡,肺臟失于陽氣溫煦、肺葉痿弱不用,而成此病[5]。間質性肺病臨床發展早中期多以邪實為主,外感于邪,肺氣不利,水液停滯,日久化熱,煉液成痰,痰熱互結,組織經脈,血行不暢,停而成瘀,痰、熱、瘀三者互結于內,阻滯經絡,損傷肺氣,屬“肺痹”范疇。疾病的后期則以本虛為主,久病耗傷正氣,肺臟絡虛不榮,氣血不充,肺氣虛衰,肺葉痿弱不振,屬“肺痿”范疇[6]。李師認為肺為嬌臟,若外邪反復侵襲,肺氣受損,久則肺氣虧虛;肺為水之上源,肺虛則津液無以輸布,留為痰飲,壅積于肺,郁而化熱;宗氣虛衰,無力鼓動氣血則成血瘀。痰、瘀、熱互結阻絡,發病日久則正氣耗傷,終至肺失濡養,肺葉焦痿不用而發病。痰、瘀、熱為內在因素,外感六淫之邪為誘因,二者互相作用,則易使病情遷延不愈,反復發作。
2 治療經驗
李師治療間質性肺病的總原則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在臨床的診療過程中,李師根據疾病所處的不同階段對標本各有側重,治本則注重扶正固本、益氣健脾、補益肺腎,治標則注重如活血祛痰、化瘀通絡。此外,李師在面對間質性肺病發生、發展所處的不同病程的不同特點,將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優化選擇,中西醫結合,各取所長,將現代研究成果與中醫辨證施治相融合。
2.1 辨證分期 在辨證論治的過程中,李師主張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先辨病期,再析病因,分清正邪主次、虛實標本。在臨床治療中,李師指出要抓住同一患者在疾病不同發展階段的標本緩急,注重不同患者的病情特點,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方案。李師認為,間質性肺病根據其辨證特點,常可分為早中期、后期兩個階段。疾病的早中期常因感受外邪所致,如《素問·風論》所說“風者,百病之長也”,風邪易兼夾它邪,多以寒、熱、濕等邪兼夾而為病,邪氣雜至郁閉肺氣,氣機不暢,瘀血內停,久致肺氣虛損,肺失宣降,則見胸悶、胸痛、氣喘等癥。疾病后期病機為本虛標實,以肺脾腎三臟虛損為主,夾雜痰瘀。肺葉痿弱不振,總以本虛為主,依據其寒熱偏頗分為虛寒或虛熱,故治療上則以扶正為主,補益肺腎,益氣健脾;兼以祛邪,清肺化痰,活血祛瘀,再據其寒熱加減。
2.2 活血化瘀,清肺化痰 李師認為間質性肺病早中期偏于“肺痹”,其遷延不愈,反復發作的重要因素在于痰、瘀、熱等毒邪互結于內,痹阻肺絡。故臨床治療中李師善用活血祛瘀通絡、理氣清肺化痰等治法,使肺氣得以恢復宣發肅降之功能,肺氣復利,邪去則正安。常用桃仁、紅花、丹參、川芎、雞血藤等活血化瘀、去瘀生新;痰熱互結者,常用瓜蔞、浙貝母、竹茹、蘆根等以清熱化痰。
2.3 益氣健脾,滋補肺腎 李師認為,從間質性肺病的整個疾病發生發展的過程看,貫穿始終的病機在于正氣不足,尤其是肺脾腎三臟虛損。其病后期偏于“肺痿”,故扶正為治療之要,如《醫宗必讀》所云:“脾為生痰之源,肺為儲痰之器。”又如《類證治裁》指出“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根。”從痰與氣的角度來說,肺脾腎三臟的聯系更為緊密,故在臨床間質性肺病的后期的治療過程中,李師多注重扶助正氣,補益肺腎、益氣健脾以固本,多以都氣丸、玉屏風散、參苓白術散等為底方,以達到培土生金,金水相生的目的。常用茯苓、白術、陳皮、半夏等健脾理氣,以絕痰源;肺腎陽虛者,常選擇巴戟天、杜仲、補骨脂等溫藥以溫補肺腎;肺腎陰虛者,配伍北沙參、麥冬、蜜紫菀等潤藥以養陰生津。
3 醫案舉隅
患者王某,女性,61 歲。2015 年1 月24 日初診:主訴:反復咳嗽10余年,伴氣促1年。患者10余年前無明顯誘因開始出現咳嗽咳痰,痰少色白質粘,不易咳出,無明顯氣促,時有低熱,乏力,周身酸痛,伴面部及軀干鱗屑,曾于外院診斷為“系統性紅斑狼瘡”,平素規律口服“甲潑尼龍8mg qd 早、甲潑尼龍4mg qn”,常眼干、口干。1年前出現氣促,活動后加重,無咯血,無盜汗。外院胸部CT 檢查提示“雙肺炎性病變并支氣管擴張,SLE 累及肺部表現?”,平素長期規律家庭氧療。辰下:發熱,咳嗽咳痰,痰多色黃質粘,不易咳出,呼吸稍促,動則氣促加重,胸悶胸痛,納呆,二便尚調;舌質紫暗,苔黃膩,脈滑數。西醫診斷:結締組織病相關性間質性肺疾病;中醫診斷:肺痹,證屬痰熱瘀結證。治法:清熱化痰,活血散瘀。予自擬方加減:茯苓15g、法半夏9g、桔梗9g、炒萊菔子15g、浙貝母9g、甘草片3g、紫蘇子9g、黃芪15g、白芥子12g、丹參9g、金蕎麥15g、麥冬9g、天花粉15g、枇杷葉15g、陳皮12g、桃仁9g、路路通15g、蘆根15g,7劑,日1劑,水煎,分兩次服。
二診:2015 年2 月3 日,患者胸悶氣促較前減輕,咳嗽較前改善,痰量減少,胸脅疼痛減輕,但仍覺疲乏,伴四肢酸軟,口干眼干,納可,寐一般,二便調;舌暗紅,苔白稍膩,脈滑。加強化痰降氣之力,并兼顧脾腎,予前方去蘆根,加黃芪至25g、蜜紫菀15g、巴戟天15g,14劑,日1劑,水煎,分兩次服。
三診:2015 年2 月17 日,經治療,患者諸癥皆緩,苔膩明顯減輕,舌色轉紅。繼續予以上方中藥治療,鞏固療效,此后患者間斷李師門診中藥治療半年,隨訪發作期較前明顯減少,偶有咳嗽咳痰,胸部CT 顯示肺間質纖維化范圍無明顯進展。
按語:間質性肺病是指以肺泡壁為主并包括肺泡周圍肺間質病變的一組非感染性、非腫瘤性的疾病群。目前西藥治療效果一般,且副作用較大,患者費用負擔較重。李師認為,間質性肺病病情反復發作,纏綿難愈,多因肺臟虛弱,外邪侵襲,皮痹日久而致肺絡氣血瘀阻。患者初診時以咳嗽痰黃、胸悶胸痛、氣促,乏力等為主要癥狀,舌紫暗,苔黃膩,脈滑數也為痰熱互結、氣滯血瘀之象。辨病屬肺痹,故治以清熱化痰、行滯散瘀。經治療后患者胸悶、胸痛、氣促癥狀改善,結合舌脈等辨證可歸屬于緩解期,遂逐漸增強補肺溫腎之功。治療中兼顧祛邪與扶正,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為治則,各個時期各有側重,藥切病證,臨床療效較好。
4 總結
間質性肺病包含多種急慢性肺部疾病,且多為隱匿發病,病情的發展與轉歸變化多端,臨床表現也不盡相同。李師臨證時根據其特征,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早中期偏于“肺痹”,故多注重祛瘀清肺化痰;后期偏于“肺痿”故以扶正治本為主,注重補益肺脾腎三臟。標本虛實雖各有偏重,但二者貫穿疾病始終,辨證時抓住虛實主次、輕重緩急,方能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