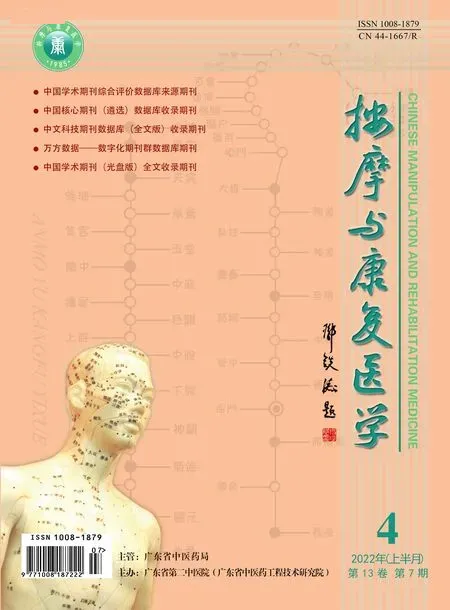銀翹散異病同治驗案舉隅*
葛開發,梁永林,單 帥,馬肖慧,姚小強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甘肅蘭州 730000)
銀翹散出自《溫病條辨》[1],篇中曰:“太陰風溫、溫熱、溫疫、冬溫,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但熱不惡寒而渴者,辛涼平劑銀翹散主之。”臨床多用于感冒及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及肺炎等呼吸道疾病[2-3]。中醫認識和治療疾病講究辨證論治,異病同治是辨證論治中的一大特色。異病同治以病機為著力點,對于相同病機引起的不同疾病采用同一治療方法。筆者在跟師期間,恩師姚小強主任醫師強調“辯病機,用經方,隨癥立方,隨證用藥,惟變所適”診療思路診治面部疾病,今以銀翹散加減治療面部疾病案例進行分享,以供臨床參考。
1 面神經麻痹
王某,女,31歲,2021年3月2日初診。主訴:口眼歪斜1周;現病史:1周前因感冒出現咽喉疼痛,鼻流黃涕,繼之出現右側口眼輕微歪斜,患者未予重視,之后逐漸加重,遂就診于我院門診。刻下癥見:右側口眼歪斜,左鼻唇溝變淺,鼓腮漏風,閉目不行,漏口水,伴咽喉腫痛,咳嗽、咳痰,色黃質粘,不易咳出,口渴心煩;納食可,睡眠可,大小便正常,舌質紅,苔黃膩,脈滑數。中醫診斷:面癱病,證型:風熱襲表兼夾陰虛,脈絡痹阻;西醫診斷:面神經麻痹;治宜疏風解表、滋陰活血通絡,處方如下:連翹12g、銀花12g、苦桔梗9g、薄荷15g、竹葉12g、生甘草6g、荊芥9g、淡豆豉9g、牛蒡子9g、僵蠶9g、柴胡9g、山藥20g,5劑,水煎200mL,早晚分服,每日1劑。
二診(3月9日):右側仍口眼歪斜,鼓腮輕微漏風,閉目較前改善,偶有漏口水,偶有咳嗽,無咳痰,無咽喉腫痛,大便不成形,舌淡紅,苔微黃,脈滑;調整處方:連翹9g、銀花9g、苦桔梗6g、薄荷9g、竹葉6g、生甘草6g、荊芥9g、淡豆豉9g、僵蠶6g、柴胡9g、山藥20g、石斛12g,10劑,水煎200mL,早晚分服,每日1劑。
三診(3月23日):口眼歪斜基本消失,余癥狀完全消失,為鞏固療效,守前方5劑,2周后隨訪,患者完全康復。
按:患者中年女性,工作壓力大,因天氣變化出現感冒,之后出現面癱,祖國醫學認為其病多由正氣不足,脈絡空虛,衛外不固,風邪乘虛入中經絡,導致氣血痹阻,經筋脈絡失于濡養,以致肌肉縱緩[4]。患者久勞耗傷氣血,陽氣虛弱,風邪乘之,上攻于頭面,以致面部筋脈痹阻,陰精不能濡養筋脈,出現口眼歪斜、鼻唇溝變淺等癥。姚師四診合參后,給予銀翹散加減,理由有:一病位在面部,“諸陽之會,皆在于面”,面部筋脈陽氣妄動,出現筋絡痹阻;二病性,患者為感冒后出現,表證未解,風熱證象為根本,此病由外風引動內風夾雜所致,當應疏風解表,風去絡自通。方中在銀翹散基礎上加僵蠶通絡熄風、祛風化痰;柴胡和解表里,發揮少陽樞機之功;予山藥顧護脾胃,石斛滋胃陰。
2 面肌痙攣
陳某,男,42歲,2021年3月5日初診,主訴:左側眼瞼抽搐跳動10余天。現病史:患者10天因受風出現咽喉疼痛,繼而出現左側眼瞼抽搐跳動,自行口含胖大海,咽喉疼痛明顯緩解,但眼瞼抽搐跳動未見改善,遂就診于我科門診。刻下癥見:左側眼瞼抽搐跳動,食納尚可,二便正常,形體微胖,舌淡紅有齒痕,舌苔白膩,脈浮。中醫診斷:面風,中醫證候:風熱襲表,兼夾痰熱痹阻;西醫診斷:面肌痙攣;治宜疏風解表、清熱化痰通絡,處方如下:連翹12g、銀花12g、苦桔梗9g、薄荷15g、竹葉12g、生甘草6g、荊芥9g、蘆根9g、牛蒡子9g、全蝎6g、半夏9g、山藥20g,5劑,水煎200mL,早晚分服,每日1劑。
二診(3月12日):患者自感眼瞼抽搐跳動頻次減少,大便稀,舌淡紅有齒痕,舌苔白,脈浮;調整處方:連翹6g、銀花10g、苦桔梗9g、薄荷9g、竹葉9g、生甘草6g、荊芥9g、蘆根9g、牛蒡子9g、全蝎6g、半夏9g、山藥20g、黃芪30g,5劑,水煎200mL,早晚分服,每日1劑。
三診(3月19日):癥狀基本消失,為鞏固療效,囑患者口服補中益氣丸。
按:現代醫學認為,面肌痙攣由橋小腦角區血管壓迫面神經根部引起,依據癥狀表現,中醫稱為“面風”、“顫證”。姚師在治療該病上強調風邪侵襲腦絡,本例患者中年男性,體型偏胖,發病是由風熱夾痰侵襲面部,擾動氣機紊亂,致筋脈抽搐跳動;而肌肉的抽搐、角弓反張均為風性動搖不定的特征。故本病治宜疏風解表、化痰通絡,方用銀翹散加減,用全蝎不用僵蠶,乃取其性善走竄特點,既平息肝風,又搜風通絡,用半夏燥濕化痰,山藥補脾養胃。
3 討論
面神經麻痹和面肌痙攣均屬于面部疾病,中醫有“巔頂之上,惟風可到”之學說,《太平圣惠方》曰“夫頭面風者,由體虛之人,陽脈為風所乘也,諸陽之經,皆上走于頭面”,故面部疾病多從風邪而論,尚有內外之分。外風為六淫之首,四季皆能傷人,經肌表而入者,多始于經絡,正虛邪盛則內傳臟腑。內風系自內而生,多由臟腑功能失調所致,與心、肝、脾、腎有關,與肝最為密切。前期課題組就風象病作出闡釋,以風之特性(如:風象開泄,風象動變)“象”釋其機體病理狀態謂“風象”病[5],本病亦屬于此病范疇。《類經》云:“風者,天地之陽氣也。”風無外形,實為天之陽氣與人之陽氣互相和諧交融,無論哪一方出現陰陽失衡時,均會引機體發病。頭面部為天,同氣相求,風邪侵襲頭面,便會引起面部筋脈的阻滯或氣機逆亂,從而出現肌肉松弛、面部表情肌癱瘓、前額皺紋消失、眼裂擴大抑或抽搐、跳動等癥。
姚師認為在眾多病因、病位、病性、病理變化中,尤需注意兩點,即“風”與“陽”。在面部疾病進展中,風陽既是基本外因,又是病理因素,亦是病性與病位的概括。面部神經麻痹主要是筋脈阻滯,面筋痙攣主要是陽氣妄動,肌肉抽搐。因此在治療上,面部神經麻痹貴在“通”,面筋痙攣貴在“靜”。外風時常夾雜內風,用藥則以風藥為主,用穴則可選用風穴。本文兩例病案,皆是風熱襲表后出現的癥狀,表證未解,外風入里,擾動內風,繼而出現面部疾病。姚師以銀翹散為底方,隨癥加減,療效顯著。
正如《傷寒論》中言:“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臨床運用銀翹散當應以風熱襲表為主旨,謹守病機,異病同治,通過證癥結合,適宜加減,必當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