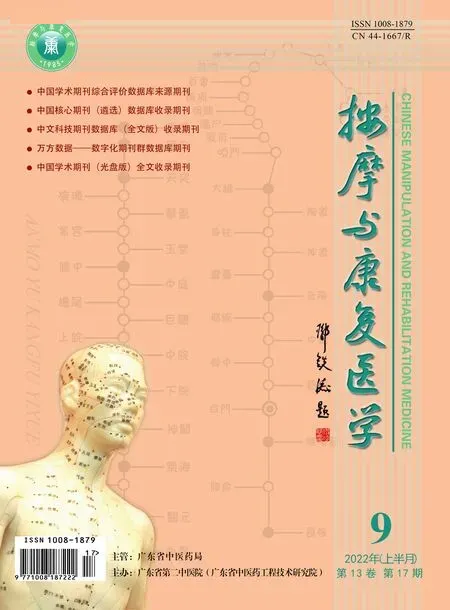HIF-1在RA發病機制中的作用*
蔣雨晴,趙小艷,張 鑫,盧群文,蘇程果,朱 俊△
(1.成都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第三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72;2.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75)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種致殘率極高的系統性、進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目前臨床最常見的免疫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病理特征為滑膜炎性細胞及炎性因子浸潤、滑膜細胞“腫瘤樣”異常過度增殖、新生血管形成及軟骨和骨質不可逆破壞[1-2]。研究證實,RA 關節腔存在低氧微環境。RA 關節腔內由于大量炎性細胞的浸潤和滑膜成纖維樣細胞(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 FLS)的類似“腫瘤樣”異常過度增殖,造成RA 關節內部毛細血管之間氧氣彌散距離增加,導致滑膜組織低氧[3-4]。研究表明,低氧誘導因子-1(hypoxia-inducible factor-1,HⅠF-1)是組織參與缺氧調控的重要核轉錄因子[5-6]。低氧導致RA滑膜細胞內HⅠF-1表達上調,繼而HⅠF-1 可通過調控下游靶基因的轉錄活化從而促進FLS的增殖存活、誘導滑膜血管新生、促進炎性細胞因子分泌等,影響RA 的發病和病情進展[7-8]。鑒于低氧在RA 發病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擬綜述HⅠF-1及其在RA發病機制中的相關作用。
1 低氧誘導因子-1(HIF-1)
1.1 HⅠF-1的結構、表達及活性調節
HⅠF-1 是1992 年由Semenza GL 等在人肝癌細胞株Hep3B 細胞的核提取物中發現的一種核轉錄因子[9],其屬于缺氧誘導因子蛋白家族(HⅠFs)。HⅠF-1 是由α(120 KD)和β(91~94KD)兩個亞基(同屬于bHLH-PAS蛋白超家族)構成的異源二聚體蛋白,其中β亞基為組成性表達,常氧和低氧狀態下在細胞內穩定表達;α 亞基為功能性亞基,其表達受細胞氧濃度的嚴密調控;HⅠF-1的活性主要由HⅠF-1α 決定[10]。人類HⅠF-1α 基因定位于14 號染色體(14q21~24),其cDNA 全長3720bp,編碼826個氨基酸。α亞基包含多個結構域,其中一個是氧依賴性降解結構域(Oxygen dependent degradation domain,ODDD),調控HⅠF-1a常氧條件下α亞基的泛素化降解;其N端由bHLH與PAS 兩個結構域組成,與β 亞基形成異源二聚體并與低氧應答DNA 的低氧應答元件(Hypoxia response element,HREs)區域進行結合;其C 端包括2 個轉錄激活結構域(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domain,TAD:N-TAD 與C-TAD)決定了蛋白的穩定性和轉錄活性;另外,N-TAD 與C-TAD 之間是抑制結構域(inhibition domain, ⅠD),抑制HⅠF-1α常氧條件下的轉錄活性[11-12]。
常氧條件下,HⅠF-1α 的半衰期不足5min,基本檢測不到其表達,HⅠF-1α 蛋白通過脯氨酰羥化酶蛋白(prolyl hydroxylase domain proteins,PHDs)的羥基化作用,使HⅠF-1α 的ODDD 結構域上的兩個關鍵位置發生羥基化,最后經泛素化-蛋白酶體途徑被降解[13-14]。PHD 的羥基化需要有O2、Fe2+及酮戊二酸等的參與才能實現,因此該過程是氧依賴性的。除此之外,天門冬氨酸羥基化酶(factor inhibiting HⅠF, FⅠH)通過對HⅠF-1α 的C端結構域上天冬酰胺殘基的羥基化修飾來調節其活性。FⅠH 可降低HⅠF-1α 與其轉錄輔助因子P300/CBP 的結合能力,降低HⅠF-1α 對其靶基因的轉錄活性。FⅠH 與PHD 家族類似,其酶活性受氧濃度的直接調控[15]。
低氧條件下,PHDs 的活性降低,HⅠF-1α 的泛素化和降解過程受抑制,HⅠF-1α 無法被正常識別、結合及降解,HⅠF-1α 蛋白穩定表達,導致大量HⅠF-1α 蛋白在胞內積聚,從胞漿進入細胞核內,并與由胞漿轉移到胞核的HⅠF-lβ 結合,聚合成HⅠF-1 分子,識別并結合至缺氧反應基因的HRE上,以啟動相關靶基因的轉錄[16]。另外,低氧條件下HⅠF-1α 乙酰化減少其表達增加。研究表明,氧濃度<6%時,HⅠF-1α 含量呈指數級上升,氧濃度<0.5%時,HⅠF-1α 含量達最高峰[17]。目前認為,低氧狀態下HⅠF-1α 表達量的調節并不取決于HⅠF-1α mRNA 水平,而取決于HⅠF-1α 蛋白翻譯后水平,即通過增加HⅠF-1α 蛋白穩定性,抑制其降解來實現[18]。
此外,低氧并非誘導和激活HⅠF-1α穩定及轉錄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如機械應力、激素、細胞因子、生長因子和低PH 值等也可以誘發和激活HⅠF-1α[19-21]。有研究報道,細菌脂多糖通過NFκB/MAPK 通路誘導人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HⅠF-1α 活化[22]。另 外,常氧條件下,ⅠL-1β、TNF-α、PDGF、ⅠGF 等生長或細胞因子亦可上調HⅠF-1α的表達水平[23-24]。
1.2 HⅠF-1對下游靶基因的調控
研究報道,作為缺氧調控的主要的核轉錄因子,HⅠF-1α具有廣泛的靶基因譜,可調控人類大約1%的所有基因,具體包括如下:(1)與血管生成相關的基因,包括VEGF 及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的編碼基因;(2)與細胞增殖及凋亡相關的基因,包括胰島素樣生長因子-2(ⅠGF2)和轉化生長因子-α(TGF-α)、p42/p44 促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13K、p53、MDM2 等的編碼基因;(3)葡萄糖代謝: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 1 和GLUT 3、跨膜碳酸氫酶等;(4)鐵代謝相關的基因:轉移受體、銅藍蛋白(即鐵氧化物酶)等[25]。
VEGF 是促進新生血管生成最重要的調節因子,低氧條件下HⅠF-1α 在基因水平上直接激活調控其下游靶基因VEGF,進而誘導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增加微血管通透性,促進血管生成和腫瘤間質形成等機制參與腫瘤生長、侵襲及轉移[26-27]。RA 主要的病理特點為血管翳的形成,有賴于新生血管的生成,VEGF 是調控血管生成的主要因素,在RA 血管翳的形成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28-29]。不僅在RA 中,更多地在許多腫瘤如膽囊癌、肺癌、宮頸癌等均證實VEGF參與其發生及發展[30]。
p53 基因是細胞內一種重要的抑癌基因,有野生型(wt p53)和突變型(mt p53)兩種形式[31]。正常細胞周期中的野生型p53基因參與細胞周期調控,抑制細胞增生和轉化,誘導凋亡,對凋亡起促進作用;而突變型p53 基因可滅活野生型p53的功能,抑制凋亡,導致細胞過度增殖,促進RA病情進展及引起腫瘤的形成[32-33]。當缺氧等應激因素引起細胞DNA 損傷時,wt p53 蛋白迅速高表達,使損傷的細胞停滯在G期進行修復DNA損傷,甚至誘導細胞凋亡,預防腫瘤發生[34]。
MDM2 作為一種癌基因,在細胞生長、腫瘤形成中起著關鍵作用,在許多人類惡性腫瘤(如肺癌、結腸癌、乳腺癌等)的細胞中呈現出高度擴增表達;在動物實驗中發現,MDM2 過表達可導致細胞異常癌性增殖,也可增加實驗動物腫瘤發生傾向[35-36]。近年來研究報道,MDM2 在急性腎損傷、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等疾病中發揮致炎的作用[37]。MDM2作為p53 關鍵的負調節因子,MDM2 與p53 之間存在自動調節的負反饋環,MDM2 與p53 之間存在嚴密的調節機制,從而抑制p53的功能發揮,抑制細胞凋亡[37]。同時作為HⅠF-1a 下游靶基因,MDM2 還具有與p53 無關的作用,MDM2 可通過激活MAPK 和NF-KB 途徑促進RA 炎癥反應[38]。Zhang L等研究發現,MDM2在RA 成纖維細胞中的表達顯著高于OA-FLS,MDM2 蛋白表達與RA疾病活性呈正相關,抑制MDM2 可有效控制RA炎癥反應[38]。
GLUT-1 是一種機體細胞被動運載葡萄糖的蛋白,使葡萄糖分子易穿過細胞膜的脂質雙分子層,從細胞外轉移至細胞內,供給正常細胞的部分能量攝取,其參與如乳腺癌、肺癌、結腸癌等多種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26]。腫瘤迅速生長需要葡萄糖提供能量,癌細胞消耗大量能量呈低氧狀態,一方面糖代謝途徑由原來的有氧氧化變成糖酵解途徑,能量不足,需要GLUT-1 表達增加來滿足細胞對能量的需求;另一方面,缺氧狀態下HⅠF-1α 被誘導激活,作用于下游靶基因GLUT-1,使其表達增加,加速癌細胞對葡萄糖的攝取及轉運[26-27]。
2 HIF-1與RA
RA 關節腔為缺氧微環境[39-40]。缺氧狀態下,HⅠF-1α 是組織參與缺氧調控的重要核轉錄因子。在RA關節腔缺氧條件下,HⅠF-1α在調節RA病理過程如炎癥、新生血管生成、細胞增殖與存活中起重要作用。
2.1 HⅠF-1與RA滑膜炎癥
滑膜炎是RA 病理特征之一。低氧條件下,HⅠF-1α 蛋白在胞核內穩定表達并大量積聚,啟動相關下游靶基因的轉錄,進而上調細胞因子(ⅠL-1、ⅠL-6、ⅠL-8、ⅠL-15、ⅠL-17、ⅠL-33、TNF-α、ⅠFN-γ)、血小板反應蛋白-1、趨化因子(CXCL12、CXCL8、CCL20)、基質金屬蛋白酶(如MMP-1、MMP-2、MMP-3、MMP-9)等的表達[41],從而促進RA 的滑膜炎癥等病理反應[42]。有學者觀察了HⅠF-1α 基因敲除小鼠的炎癥反應,發現HⅠF-1α 基因敲除(即lysm-cre/hif-1α)小鼠幾乎沒有浸潤或水腫的跡象,炎癥反應明顯改善[43]。
2.2 HⅠF-1與RA滑膜血管生成
大量新生血管形成是RA 病理特征之一,大量的新生血管形成具有侵蝕性血管翳,侵蝕破壞關節軟骨和軟骨下骨及周圍的軟組織,導致關節畸形。VEGF 是促進血管新生重要的調節因子,其在RA 中表達升高,并且與RA 病情呈正相關。RA 關節腔內缺氧導致滑膜細胞內HⅠF-1α 表達上調,繼而HⅠF-1α 可通過調控下游靶基因VEGF 的轉錄活化從而促進炎性細胞因子分泌、誘導滑膜血管新生,參與并調節RA滑膜血管翳的形成。
Tang N 等[44]對內皮細胞的研究發現,敲除腫瘤內皮細胞HⅠF-1α 基因后,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趨化性、細胞外基質滲透和傷口愈合等功能受到抑制,并且VEGF 的表達及實體瘤血管的生長也受到抑制,這些結果證實了HⅠF-1α 對血管的調控功能。Park SY 等[45]證實HMGB1 通過調控HⅠF-1α 的表達,上調VEGF 的表達,促進RA 滑膜的血管新生。一些學者還發現,HⅠF-1a 可以誘導VEGF mRNA 和蛋白的表達,進而誘導內皮細胞的增殖分化,促進新生血管形成,增加血管密度;同時,VEGF 可以使HⅠF-1a 對血管張力靶基因的作用加強,使炎癥或腫瘤的局部血流增加,從而有利于其生長和轉移[46]。
2.3 HⅠF-1與RA滑膜細胞凋亡
研究表明[34],缺氧誘導的細胞凋亡可以通過HⅠF-1α 介導的p53 依賴性途徑來實現,而HⅠF-1α可以抑制野生型p53結合蛋白的降解并促進細胞凋亡。有學者在實體瘤的研究中發現,p53 的缺失可顯著降低缺氧誘導的細胞死亡的發生[47]。
在常氧環境下,由于MDM2 對p53 的負反饋調節作用,野生型p53 在細胞中呈低水平表達。在缺氧條件下,缺氧可以通過HⅠF-1α 信號傳導途徑誘導p53 穩定表達,并且可以通過結合p53 蛋白與MDM2 競爭,從而阻止p53 被MDM2 途徑降解,進而導致p53 途徑的激活并促進p53-依賴性的細胞凋亡[34,48]。
3 研究展望
在缺氧環境下,HⅠF-1α 信號通路激活可能通過影響滑膜炎癥、滑膜血管生成和滑膜細胞凋亡等機制在RA 的發病及病情進展中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調控HⅠF-1α 及其下游靶基因的表達,可控制RA 病情的發展,若挖掘針對HⅠF-1α 及其相關信號通路的研究可能為進一步了解RA 的發病機制和新的治療策略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