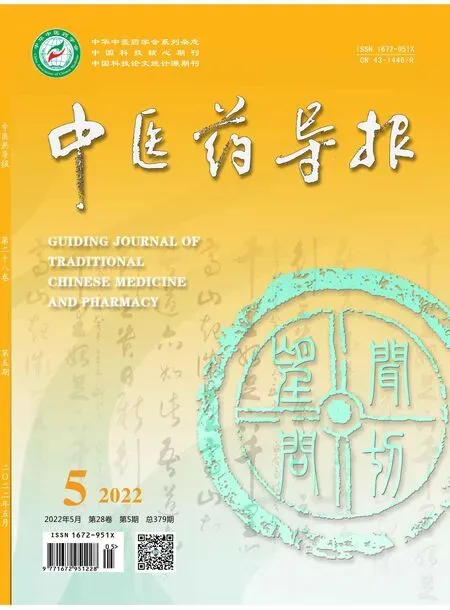基于“初病濕熱在經”探討解毒通利方治療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思路*
蔡媛媛,張達坤,蔡敏,程亞偉,林道斌,楊永和
(海南省中醫院,海南 海口 570203)
我國屬于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virus,HBV)感染的高發地區,同時慢性乙型肝炎亦是引起我國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的主要病因之一。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是特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臟纖維化,是由于乙型肝炎病毒侵入人體,誘發肝細胞炎癥壞死,進而導致肝內結締組織的異常增生而形成的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1]。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本質是慢性乙型肝炎進程中一種肝組織損傷過度修復反應,是纖維增生與分解不平衡的結果。肝纖維化(hepatic fibrosis,HF)的發生機制不僅涉及細胞凋亡、細胞信號轉導通路的介導、細胞因子,還涉及肝星狀細胞的激活、細胞外基質的沉積等多種復雜因素。故如不及時治療,HF進一步向乙型肝炎后肝硬化,甚至肝癌發展,最終造成患者死亡[2]。作為肝硬化的基礎和必經階段,HF是關鍵的治療時期,所以延緩、阻斷或逆轉HF的發展成為治療乙型肝炎相關性肝病的關鍵。雖然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可以逆轉已達成共識,目前西醫主要通過病因治療——抗病毒、保肝護肝及抗HF治療,從而延緩慢性乙型肝炎向肝纖維化進展的進程[3],但效果不確切,且不良反應較多。
而隨著中醫藥在HF領域的深入研究,中醫的治療優勢逐漸凸顯。中醫藥不僅對其有著較好的防治效果,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轉肝纖維化[4-6]。清熱利濕法是中醫抗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代表性治法之一。解毒通利方是蔡敏教授創制的清熱利濕法的代表方。筆者主要基于“初病濕熱在經”理論,探討解毒通利方從清熱利濕角度治療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理論依據。
1 中醫對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認識
在中醫古籍中并無“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病名記載。根據其表現,其歸屬于中醫學中“肝積”“脅痛”“黃疸”“癥瘕”“肝著”等范疇。
多數醫家認為,乙型肝炎后肝纖維化是由于機體感染疫毒或外感濕熱,邪毒羈留不去。邪毒首先侵襲肝臟,進而影響脾臟,而后至腎臟,以致與氣血津液搏結,肝絡瘀阻從而發為此病。由于濕邪其性黏滯,與熱邪相合則膠結難解,濕熱膠著所以肝病纏綿難愈,日久導致正氣為之所傷,進而演變為濕、熱、毒、瘀、虛互結的復雜病理局面。由此可見,濕熱疫毒作為乙型肝炎的基本病因,也是演變為乙型肝炎后肝纖維化的基本病因,而濕、熱、毒、瘀、虛是其基本病理因素[7]。因此,乙型肝炎后肝纖維化的病理過程是動態演變的,即由實而虛,由表及里,由氣入血,由輕到重,并可沿“濕-熱-毒-瘀-虛”演變。
另外,HBV引起的肝臟持續慢性炎癥是形成乙型肝炎后肝纖維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發現,肝炎活動期的患者大多同時存在肝纖維化,因此,慢性乙型肝炎活動的過程就是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進展的過程。而濕熱作為慢性乙型肝炎始動因素,貫穿于大多數乙型肝炎的全過程。其間濕熱是大多數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始發病因和持續因素,而濕熱毒邪沒有除盡則是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不斷加重的重要原因。所以清除濕熱疫毒這一致病因子,對于防治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具有重要意義。
2 基于“初病濕熱在經”應用解毒通利方治療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
多數學者認為,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治療應從瘀、虛階段論治。而蔡敏教授則認為,由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持續的發展過程和不良結局,提前干預和及時治療更加重要。中醫藥防治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以治未病為首則,應在辨病和辨證的基礎上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所以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治療應從濕熱階段論治,將治療端口前移,清熱利濕才能取得較好的治療效果。
清熱利濕法治療本病是蔡敏教授根據《臨證指南醫案》中“初病濕熱在經,久則瘀熱入絡”[8]的觀點總結而成。“初病在經,久病入絡,以經主氣,絡主血。”[8]“經”是相對“絡”而言。疾病初期,濕熱邪毒侵襲,侵犯人體,其初起病情多較為輕淺,此為在經在氣;但濕性黏滯,病情多纏綿,而濕熱膠結、蘊蒸日久則化熱化瘀、瘀熱互結,一旦傷血入絡,疾病則會日趨嚴重,此為在絡在血。故而經病在氣為輕為淺,絡病在血為重為深。濕熱是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起始因素,當濕熱在氣分階段未解,日久導致氣機凝滯,并逐漸深入血分,影響血運,絡脈瘀堵而出現瘀血之征。氣屬無形,血為有形,經氣的損傷階段多為氣機失調導致功能性損傷,而傷及血分則出現器質性病變。所以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發生發展可以認為是由“濕熱”導致“瘀血”,“經病”進展至“絡病”的過程。
HF的病理基礎是肝血竇的毛細血管化。肝血竇屬于血管的終末分支,不僅分支細微、窗孔動態開放,而且數量巨大。HF的基本病理表現為活化的肝星狀細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s)異常增殖,造成匯管區的細胞外基質沉積,以膠原纖維等為主的結締組織增多。纖維結締組織增多后,會形成從匯管區向小葉內延伸的細小條索和菲薄間隔。在肝血管(肝動脈、門靜脈與肝靜脈)之間,纖維間隔中所存的血管可以建立血液分流,從而導致供應肝實質的血液減少。之后肝血竇內皮細胞窗孔數目會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內皮下基底膜逐漸形成,而出現肝血竇毛細血管化。肝血竇毛細血管化后,會影響肝臟微循環,使肝細胞出現缺血、變性、壞死;而肝內微循環遭到破壞,又會進一步影響血流,從而導致肝硬化[9]。
由此可見,“慢性肝炎-肝纖維化-肝硬化”的進展過程與慢性乙型肝炎進程的“濕熱在經-濕熱化瘀-瘀熱入絡”的規律一致,故而可認為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過程即是濕熱之邪久病入絡的過程。
目前也有研究表明,濕熱纏綿可以視為肝纖維化的關鍵病機之一。如占凱[10]通過肝臟瞬時彈性掃描儀檢測HF患者的肝硬度與濕熱證的相關性,發現濕熱明顯的患者,肝臟組織硬度和臨床癥狀較為嚴重,反之則較輕。彭杰等[11]通過肝組織病理檢測評估肝纖維化程度與濕熱證型的關系發現,濕熱證與肝纖維化分級呈正相關。
因此,“初病濕熱在經”可作為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病因病機發展的切入點。針對濕熱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發病中的重要作用,應重視清熱利濕法的早期應用,以防止“濕熱化瘀”及“久病入絡”,及時截斷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進程,從而阻止或延緩肝硬化的發生和發展。
目前也有多項研究提示運用清熱利濕法能緩解肝纖維化程度。如茍娟等[12]運用葛根芩連湯聯合恩替卡韋治療濕熱證HBV肝硬化患者,發現加用葛根芩連湯不僅能明顯改善肝功能,并可抑制血清中肝纖維化指標。李慧文等[13]研究發現王氏連樸飲加味能明顯減少小鼠肝臟纖維組織增生而達到抗肝纖維化的作用。
3 解毒通利方的組方分析及臨床藥理機制
3.1 解毒通利方的組方分析 解毒通利方是蔡敏教授創制的清熱利濕法的代表方。方藥組成:茵陳15~60 g,大黃10~30 g(后下),山梔子15~20 g,雞骨草15~30 g,田基黃15~30 g,鳳尾草10~20 g,葉下珠10~20 g,白花蛇舌草10~20 g,雞內金10~15 g,神曲10~15 g,丹參15~30 g,甘草5~10 g[14]。綿茵陳為該方的君藥,是治療肝病濕熱證的要藥,可清熱祛濕,解毒退黃;大黃為臣藥,既入氣分,還入血分,可瀉下攻積,清熱解毒,利膽保肝,助茵陳使濕熱從大便而出,此外大黃還可活血行瘀;山梔子為臣藥,有清熱涼血之功,不僅可入胃蕩滌熱邪下行,還配伍茵陳走表利便,以助消解瘀熱。蔡敏教授善用南藥、黎藥,故在方中運用了雞骨草、田基黃、鳳尾草、葉下珠、白花蛇舌草等藥物,均為增主藥清熱利濕解毒之力;肝病患者多肝氣過旺,肝氣橫逆犯胃則多有納差等消化道癥狀,從治未病角度,“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故在方中加入神曲、雞內金補土,以求補脾胃之本虛,助脾胃之運化;丹參可活血化瘀涼血;甘草調和諸藥。全方共奏清熱利濕、化瘀解毒、通利二便及血脈的作用,故名解毒通利方[14]。
臨床可根據濕熱程度,在解毒通利方的基礎上酌情增加溪黃草、半邊蓮、半枝蓮等清熱利濕解毒之品;根據瘀血程度,增加赤芍、牡丹皮、紅花等活血之品;根據疼痛程度及部位,酌情增加青皮、大腹皮、延胡索等行氣止痛之品。
3.2 解毒通利方的臨床藥理機制 解毒通利方源自《傷寒論》之茵陳蒿湯。現代藥理研究提示,綿茵陳的保肝作用主要通過減少炎癥因子的產生、抗氧化應激并增強肝臟的解毒功能來體現[15]。大黃可以通過促進膽管舒張來改善膽汁淤積,并且能夠改善肝臟微循環;另外大黃還可通過加快腸蠕動來促進排便,從而抑制膽紅素的腸-肝循環而達到退黃的作用[16]。山梔子可減輕肝臟的炎癥反應,促進肝細胞再生并改善微循環,并促進膽囊的收縮[17]。雞骨草、田基黃、白花蛇舌草、鳳尾草、葉下珠均有清熱利濕解毒的作用,可通過抗炎、抗氧化、保護肝臟、調節免疫等功能發揮抗肝纖維化的作用[18-22]。其中葉下珠在體內或體外均具有抑制HBV的作用,并可減輕肝組織纖維化程度進而保護肝臟[21]。神曲、雞內金可調整腸胃功能[23-24]。丹參中丹參酮ⅡA可以有效清除肝臟缺血期的氧自由基,通過改善肝細胞缺血而改善肝臟循環、促進肝臟再生,并可以抑制纖維細胞增殖和分泌,減少膠原纖維形成和纖維增生,從而達到抗纖維化的作用[25]。甘草有明顯的抗乙型肝炎病毒及抗炎作用,作用機制與其含有大量的甘草酸有關[26]。
目前,茵陳蒿湯的抗肝纖維化作用已得到證實[27]。王晶等[28]研究發現茵陳蒿湯可改善多種因素導致的肝臟損傷,不僅能減輕肝臟炎癥,還可抗肝纖維化、預防肝硬化的形成。茵陳蒿湯能減輕肝臟炎癥,調節膽紅素代謝,抗氧化反應,從而調節肝細胞凋亡,抑制HSCs的活動。楊慶宇等[29]研究發現茵陳蒿湯可改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肝功能,降低肝纖維化指標及肝臟硬度,從而達到干擾肝纖維化形成的作用。研究表明,清熱利濕藥物多有抗炎、保肝、退黃、抗氧化、解毒等作用,清熱利濕法可減輕肝臟的炎癥,進而減緩肝纖維化的進程[30-32]。
解毒通利方以清熱利濕為核心作用,兼以調氣行血,健脾扶正。組方兼顧了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過程中“濕-熱-毒-瘀-虛”的動態演變過程。解毒通利方不僅可有效改善肝功能[14],還可改善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患者血清肝纖維化各項指標。網絡藥理學研究顯示,解毒通利方抗肝纖維化的關鍵信號通路為PI3K/Akt信號通路,該通路可能通過抑制HSCs的增殖,達到抗肝纖維化的作用[33]。
4 驗案舉隅
4.1 病案1 患者,男,45歲。就診時間:2016年2月17日。因“肝區不適間作13年,加重2個月”就診。患者13年前發現乙肝表面抗原(HBsAg)陽性,當時肝功能正常,平素偶有肝區不適,未處理。既往嗜酒,因肝區不適已戒酒2個月。在當地醫院查肝功能顯示,總膽紅素:31.6μmol/L,直接膽紅素:20.7 μmol/L。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定量陰性。現癥見:肝區不適,生氣時加重,甚至夜不能寐,口干、口苦,身熱,食欲稍差,大便硬結,小便黃赤,舌質紅稍暗淡,苔黃膩,脈弦略滑。B超檢查顯示:肝臟實質回聲增粗,脾臟稍大。Fibroscan檢查提示,肝臟硬度:13.8 kPa,脂肪度:171 dB/m。結果提示“重度肝纖維化”。西醫診斷:(1)慢性乙型肝炎;(2)肝纖維化。中醫診斷:肝著,辨證:濕熱內蘊證,擬方解毒通利方加減。處方:茵陳15 g,大黃10 g(后下),山梔子10 g,柴胡15 g,枳實15 g,白芍15 g,雞骨草15 g,田基黃15 g,鳳尾草15 g,白花蛇舌草15 g,丹參20 g,雞內金10 g,神曲10 g,甘草10 g。7劑,水煎服,1劑/d。囑調暢情志,飲食清淡,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忌辛辣刺激食物。
2診:2016年2月25日,癥狀明顯減輕,肝區不適癥狀明顯減少,發作以夜間明顯,口干、口苦減輕,夜間睡眠可,胃納改善,大便稍爛,每日1~2次,小便黃。舌質紅稍暗淡,苔黃微膩,脈弦略滑。前方去大黃,丹參改為30 g,加赤芍15 g。7劑,水煎服,1劑/d。調養方法如前。
3診:2016年3月5日,患者肝區不適癥狀基本消失,偶有口干、口苦,納眠可,小便淡黃,大便正常。舌質紅稍暗淡,苔薄黃微膩,脈弦略滑。當地醫院復查肝功能基本正常。2診方繼續服用14劑,配合復方鱉甲煎丸(武漢中聯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口服,3 g/次,3次/d,服用3個月。
2016年7月13日,Fibroscan檢查顯示,肝臟硬度:9.8 kPa,脂肪度:162 dB/m。結果提示“中度肝纖維化”。隨訪1個月,癥狀無反復。
按語:四診合參,本案患者診斷為肝著(濕熱內蘊證)。患者感受濕熱疫毒,加上平素嗜食肥甘及酒水等濕熱之品,日久濕熱內蘊,影響肝之疏泄、脾胃之運化,出現右脅肝區不適、納差等癥狀;口干、口苦、身熱、大便硬結、小便黃赤亦為濕熱蘊于內之象。故治療給予解毒通利方加減。方中茵陳為君藥,清熱利濕退黃;大黃清熱解毒,瀉下攻熱結,助茵陳使濕熱從大便而出;山梔子清熱涼血,入胃蕩滌熱邪下行,還配伍茵陳走表利便,以助消解瘀熱;柴胡入肝以疏肝氣,條達肝木;枳實散結,入于脾胃可導滯消積,入于肝可散肝之郁結;芍藥柔肝,防止柴胡、枳實疏泄太過;雞骨草、田基黃、鳳尾草、白花蛇舌草增強君藥清熱利濕解毒之力;神曲、雞內金補土以求補脾胃之本虛,助脾胃之運化,改善納差等癥狀;患者脅痛至夜不能寐,多有瘀血停留,丹參可活血化瘀、涼血安神;甘草調和諸藥,并且芍藥與甘草同用有芍藥甘草湯之意,可酸甘化陰,緩急止痛。2診時患者癥狀改善,大便稍爛,可減大黃,脅痛仍以夜間明顯,故增加丹參用量,并加赤芍以增活血涼血之力。其后癥狀基本消失后,給予鱉甲煎丸扶正祛瘀鞏固療效。
4.2 病案2 患者,男,33歲,就診時間:2020年8月11日。因“右脅不適3個月余,尿黃半個月”就診。患者既往乙型肝炎病史多年,未發病。近3個月熬夜較多后,自覺右脅不適,半個月前連續飲酒后,自覺尿黃,遂于2020年8月10日于澄邁縣老城鎮中心衛生院就診,總膽紅素:96.6 μmol/L↑,直接膽紅素:59.4 μmol/L↑,間接膽紅素:37.2 μmol/L↑,谷草轉氨酶(AST):271 U/L↑,谷丙轉氨酶(ALT):238 U/L。HBsAg(+),HBcAg(+)。現癥見:精神疲倦,右脅不適,身目黃染、尿黃,腹脹,乏力,少許惡心,噯氣,口干口苦,納差,眠欠佳,大便干結,量少,每日2~3次。舌暗紅,苔黃膩,脈弦滑。2020年8月11日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定量:7.46×105Copies/mL。肝纖維化四項顯示,Ⅲ型前膠原N端肽:22.38ng/mL↑,Ⅳ型膠原:193.30 ng/mL↑。Fibroscan檢查顯示,肝臟硬度:10.7 kPa,脂肪度:261 dB/m。結果提示“中度肝纖維化,中度脂肪肝”。胸部CT平掃+腹部CT平掃:(1)右肺上葉小肺大皰形成;(2)脂肪肝;(3)脾臟稍大飽滿,請結合臨床;(4)膽胰雙腎CT平掃未見異常。西醫診斷:(1)慢性乙型活動性肝炎;(2)肝纖維化;(3)脂肪肝。中醫診斷:肝著,辨證:濕熱內蘊證。擬方解毒通利方加減。處方:茵陳30 g,大黃15 g(后下),山梔子15 g,雞骨草30 g,田基黃30 g,鳳尾草15 g,葉下珠15 g,白花蛇舌草15 g,雞內金15 g,神曲15 g,丹參30 g,甘草10 g。7劑,水煎服,1劑/d。配合恩替卡韋(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口服,0.5 g/次,1次/d;甘草酸二銨(江蘇正大天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口服,150 mg/次,3次/d。囑嚴格戒酒,飲食清淡,勿熬夜勞累,忌辛辣刺激食物。
2診:2020年8月18日,患者精神明顯好轉,右脅不適減輕,身目黃染改善,無明顯腹脹,乏力感消失,無惡心,少許噯氣,口干口苦緩解,胃納改善,睡眠一般,小便黃,大便爛,每日2~3次。舌暗紅,苔薄黃微膩,脈弦略滑。當地復查肝功能,總膽紅素:52.3 μmol/L↑,直接膽紅素:32.9 μmol/L↑,間接膽紅素:19.4 μmol/L↑,AST:72 U/L↑,ALT:103 U/L。前方減大黃為10 g,減雞骨草、田基黃為15 g。7劑,水煎服,1劑/d。余用藥及調養方法如前。
3診:2020年8月26日,患者精神良好,無右脅不適,無身目黃染,無噯氣,無口干口苦,胃納可,睡眠一般,小便淡黃,大便稍爛,每日1~2次。舌暗紅,苔薄黃,脈弦略滑。當地醫院復查肝功能,總膽紅素:27.5 μmol/L↑,直接膽紅素:20.1 μmol/L↑,ALT:51U/L。本院復查肝纖維化四項,Ⅳ型膠原:167.30ng/mL↑。前方改大黃為酒大黃5 g。14劑,水煎服,1劑/d。余用藥及調養方法如前。
2020年9月16日當地醫院復查肝功能恢復正常。Fibroscan檢查顯示,肝臟硬度:8.3 kPa,脂肪度:257 dB/m。提示“輕度肝纖維化,中度脂肪肝”。囑患者長期服用抗病毒藥,并控制體質量,注意休息。此后隨訪病情無反復。
按語:四診合參,本案患者診斷為肝著(濕熱內蘊證)。患者平素飲食不節,加上酒毒所傷,并感受疫毒,蘊結于中焦,脾胃運化失常,濕熱交蒸于肝膽,肝失疏泄,不通則痛,故見右脅不適;膽汁不循常道,浸淫肌膚、熏蒸頭目、下注膀胱,故見身、目、小便俱黃;濕邪為陰邪,阻遏氣機,故見腹脹、乏力、納差;肝氣犯胃,胃氣上逆,故見惡心欲嘔。舌暗紅,苔黃膩,脈弦滑皆為濕熱內蘊之征。治療給予解毒通利方加減。方中茵陳清熱利濕退黃;大黃清熱利濕,通腑解毒,使濕熱從大便而出;山梔子清熱利濕,使濕熱從小便而走;雞骨草、田基黃、白花蛇舌草、鳳尾草、葉下珠增強清熱利濕解毒的作用;神曲、雞內金健脾和胃,改善消化道癥狀;丹參活血化瘀,改善肝臟循環,以退瘀黃;甘草調和諸藥。2診時患者癥狀緩解,指標改善,但大便次數較多,故調整清熱利濕藥物劑量,以防苦寒傷陰。3診時患者癥狀基本消失,肝纖維化指標輕度異常,故改大黃為酒大黃,取酒大黃可退瘀黃之效。
5 結 語
辨證施治是運用清熱利濕法抗乙型肝炎后肝纖維化的基本原則,并且應觀察患者用藥過程中的反應,顧護脾胃及陰液,通過體質調節,清熱利濕,改善肝臟炎癥以達到抗肝纖維化的目的。此外注意保養,飲食節制、生活規律、情緒管理,都有助于病情向愈。
基于“初病濕熱在經”理論,運用解毒通利方,從清熱利濕角度辨治慢性乙型肝炎肝纖維化,可以為中醫的規范治療、精準治療提供一個新的思路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