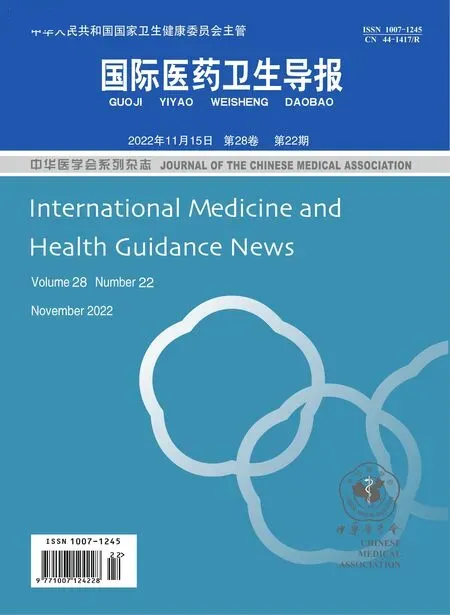不同照護模式對腦卒中恢復期患者心理狀況及生活質量的影響
王慧 申瀟竹 伏兵
1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附屬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院科教處,連云港 222023;2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附屬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院老年醫學科,連云港 222006;3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附屬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內科,連云港 222023
隨著我國老齡化現象的日益嚴重,老年人腦卒中的發病率逐年上升[1]。腦卒中后常遺留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缺損癥狀、心理障礙,嚴重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腦卒中患者的康復目標在于恢復言語、認知、肌力等神經功能缺損癥狀,恢復日常生活能力,力爭重返家庭和社會[2-4]。腦卒中后1~3個月是卒中患者康復的關鍵時期[5],對于此類患者,連云港地區的多數老年患者居家照護,部分患者選擇機構照護,研究表明不同的照護模式對腦卒中患者的康復會產生一定的影響[6]。不同照護模式對老年腦卒中恢復期的影響目前國內研究較少。本研究旨在通過對不同照護模式下連云港地區老年腦卒中患者心理狀況、日常生活質量等方面的觀察,評估不同照護模式的優勢和不足,為進一步改善老年腦卒中患者恢復期的心理狀況及生活質量提供方向。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本研究納入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腦卒中患者,采取電話回訪、上門回訪、返院復診回訪等方式,回訪腦卒中后1~3 個月的老年患者。納入標準:(1)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8》[7]中缺血性卒中診斷標準,頭顱CT/MRI 等影像學確診;(2)年齡>60 歲;(3)腦卒中后 1~3 個月。排除標準:(1)伴有心肺功能衰竭者;(2)伴有嚴重肝腎功能異常者;(3)伴有惡性腫瘤者;(4)伴有精神性疾病者;(5)伴有凝血功能障礙、血液系統疾病者。預期接受回訪老年患者500 例,實際完成有效回訪314 例,其中電話回訪189 例,上門回訪42 例,返院復診回訪83 例。從出院后到回訪期間居住環境為家中,由家屬或護工照料視為居家照護組,共 169 例,男 88 例、女 81 例;居住環境為照護機構(包括連云港市多家養老機構、社會福利院),由醫護人員或護工照護,視為機構照護,共 145 例,男 70 例、女 75 例。兩組患者及家屬均知情同意。
本研究經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號:2019-021)。
2、方法
評估方法:采用一般問卷調查法。所有問卷調查均由經過培訓的評估醫師采用統一指導語,評估前與患者及照料者溝通消除其顧慮,在照料者協助下完成調查表。心理狀態評估:采用國內外具有較好信度、效度的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和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生活質量評估:(1)生活狀態。采用腦卒中影響量表(SIS)中評估生活狀態的8個方面[8]:患者的力氣、移動能力、日常生活能力、感覺和情感控制力、手功能、交流和閱讀能力、記憶和思維能力、參與能力,共59 個條目,評價標準是每個條目的選項分數為1~5 分,統計整理患者得分經公式把各方面的得分換算成100分制,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質量越高。(2)不良風險事件評估[9]。重點觀察墜積性肺炎、跌倒性骨折、中重度貧血、下肢靜脈血栓形成、肺栓塞、壓瘡、燙傷、自殘、管路脫落、擅自出行安全隱患等方面。
3、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5.0 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表示,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MI)、卒中類型、肢體障礙、失能狀況、每天臥床時間、留置導尿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城鎮居民選擇機構照護服務的比例為53.7%(109/203),顯著高于農村居民的32.4%(36/11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一般資料比較[例(%)]
2、HAMA、HAMD評分比較
居家照護組HAMA、HAMD 評分均低于機構照護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HAMA、HAMD評分比較(分,)

表2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HAMA、HAMD評分比較(分,)
注:HAMA為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D為漢密爾頓抑郁量表
組別居家照護組機構照護組t值P值抑郁12.15±4.85 17.65±5.88 9.082<0.001例數169 145焦慮10.35±2.62 15.81±5.22 11.957<0.001
3、日常生活能力
機構照護組日常生活能力、記憶思維能力評分均高于居家照護組,感覺和情感控制力、參與能力、手功能評分均低于居家照護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老年患者在交流和閱讀能力、力氣、移動能力評分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比較(分,)

表3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比較(分,)
組別居家照護組機構照護組t值P值例數169 145日常生活能力44.43±10.21 58.98±7.09 14.431<0.001感覺和情感控制力40.91±6.65 32.98±4.23 13.370<0.001記憶思維能力67.62±9.58 78.19±7.85 10.582<0.001交流和閱讀能力85.01±8.56 85.70±5.09 0.850 0.396參與能力20.96±3.56 12.67±5.74 15.603<0.001力氣71.89±8.13 73.42±9.53 1.535 0.125手功能51.85±6.02 49.62±3.68 3.881<0.001移動能力63.13±6.51 62.98±8.37 0.178 0.858
4、不良風險事件比較
機構照護組墜積性肺炎、壓瘡、管路脫落發生率均明顯低于居家照護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跌倒性骨折、中重度貧血、下肢靜脈血栓形成、肺栓塞、燙傷、自殘率、擅自出行安全隱患(失聯8 h 以上/迷路)人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兩組老年腦卒中患者不良風險事件比較(例)
討 論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腦卒中發病率、患病率日益增多。如此龐大的老年腦卒中人群的照護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10-11]。連云港地區的機構照護得到了快速發展。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養老機構,均為老年人照護,特別是不同程度失能老人照護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老年卒中患者常遺留肢體活動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和精神行為異常,嚴重者可出現行動困難、二便失禁、癡呆等,生活難以自理,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12-13]。腦卒中恢復期的康復越來越受到重視,有效的康復訓練及專業照護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精神心理狀態具有良好的效果[14-16]。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選擇居家照護還是機構照護,腦卒中后患者在年齡、性別、BMI、卒中類型、肢體障礙、失能狀況、每天臥床時間、留置導尿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由此可見,上述臨床特征并不是腦卒中患者選擇照護模式的主要依據。城鎮居民選取機構照護的比例較農村居民明顯增高。考慮可能與城鎮腦卒中老人子女多為工作時間固定的上班族,而農村子女上班族占比低;城鎮居民有醫療保險占比、人均收入支持者高于農村居民;城鎮平均子女數量少于農村等原因有關[17-18]老人。因此城鎮腦卒中老人選取機構照護比例高,而農村腦卒中老人選擇居家照護更多。
本研究顯示,腦卒中老人在恢復期HAMA、HAMD 評分均高于正常值,這提示兩組患者均存在一定的焦慮、抑郁狀態,與Medeiros 等[19]研究結果一致。心理干預和身體機能康復一樣,影響腦卒中患者的康復療效。改善患者精神心理狀態,有助于患者配合治療、提高療效,有助于患者更好回歸家庭、社會作用很大[20-21]。本研究發現,居家照護組HAMA、HAMD 評分均明顯低于機構照護組,這表明機構照護在對腦卒中老人精神心理方面的干預不及居家照護,機構照護人員專業性遠強于患者家人,在愛心、耐心等方面不及患者家人,因而,機構照護者需要在提升患者精神心理建設方面下功夫。
近年來,腦卒中的延續照護在我國蓬勃發展,腦卒中患者從醫院到院外,應得到醫院制定的出院計劃、回歸家庭或社會后的持續隨訪與指導,確保患者在不同場所得到連續的協作性照護[22-23]。腦卒中后日常康復訓練包括坐起訓練、平衡訓練、站起訓練、步行訓練、上下樓梯訓練、日常生活訓練等,便于在居家環境及機構中進行[24-25]。本研究發現,兩組腦卒中老人在交流和閱讀能力、力氣、移動能力評分等方面無明顯差異。日常生活能力評分顯示,機構照護組日常生活能力、記憶思維能力評分均高于居家照護組,感覺和情感控制力、參與能力、手功能評分均低于居家照護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居家照護環境,腦卒中老人熟悉且有溫情感,可能更有利于患者感覺和情感、參與能力等方面的恢復。
本研究發現,兩組不良風險事件比較,機構照護組墜積性肺炎、壓瘡、管路脫落發生率明顯低于居家照護組,兩組在下肢靜脈血栓形成、肺栓塞、燙傷、自殘、擅自出行安全隱患(失聯8 h 以上/迷路)人數無明顯差異。隨著照護機構的執業發展,照護水平不斷提高,制度化的管理,使壓瘡、管路脫落、摔倒等患者安全事件得到更多的重視并在日常照護中盡可能避免。而居家照護者,尤其是對新發腦卒中缺乏經驗的家庭,護理常識欠缺,翻身、拍背、日常護理不能規律持續進行等因素,腦卒中患者在恢復期出現墜積性肺炎、壓瘡、管路脫落等不良事件更常見[26-28]。
綜上所述,機構照護在城鎮居民中比例較高,在焦慮、抑郁等心理狀態等方面劣于居家照護。在日常生活能力方面,機構照護組感覺和情感控制力、參與能力、手功能評分方面均低于居家照護組,日常生活能力、記憶思維能力評分及避免墜積性肺炎、壓瘡、管路脫落發生率方面優于居家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