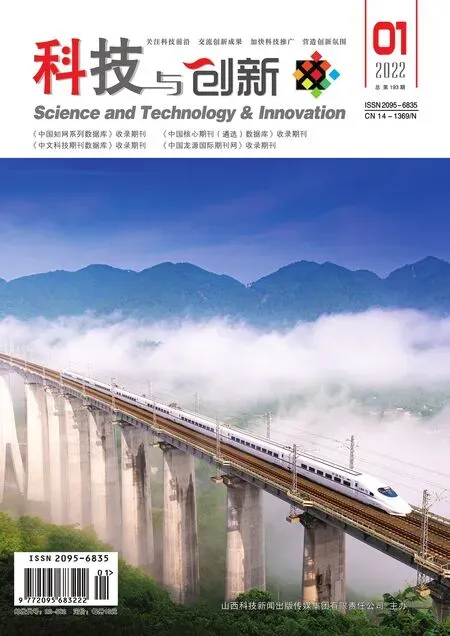基于數字技術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播
——以敦煌莫高窟為例
杜若飛
(武漢理工大學,湖北 武漢430070)
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成就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屬于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精神,通過物質與非物質的方式流傳至今。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提出,在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繁榮發展過程中,文化興盛發揮著基礎作用,通過文化的繁榮,可以加快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傳統文化依然有著突出的價值。通過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播,不但能充分發揮中國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優勢,還有助于文化遺產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完成,與此同時還要對其經濟與觀賞價值作出考量,以進一步增強中國知識產權競爭能力,為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獲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從而提高國際影響力。隨著現代科技文明的高速發展,文化遺產的傳承模式逐漸由口頭、文字等向數字化轉變,文化遺產數字化的保護與傳播方式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如何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保護與傳播優秀的文化遺產,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們所面臨的的新課題。
1 文化遺產數字化概述
1.1 涵義
文化遺產數字化,具體是指運用數字技術,比如數字采集、數字存儲、數字傳播等,使得文化遺產發生轉變,或者將文化遺產復原成數字形態,促使其轉變為可再生資源,實現文化遺產共享[1]。對此,要轉變思路,站在新的視角對文化遺產進行解讀,創新保護方式,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滿足新時代需求。在數字技術的應用下,將文化遺產轉化為數字形態,便于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利用,從而提高文化產品的質量,為人們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將文化遺產永久保存起來,在保護文化遺產的基礎上重現和利用文化遺產,將文化遺產的價值充分體現出來,體現人們對文化遺產的擁有權,進而更好地守望中國文化遺產。
1.2 類型
中國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是運用信息技術使文化載體發生改變,進而改變文化存儲、傳播等方式[2]。有學者將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分為數字化保護、數字化虛擬博物館、數字化圖案設計系統等類型。另外,還有學者指出,文化遺產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存在多個知識點,比如數字記錄、虛擬遺產等,從全局視角研究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播,應當在數字技術的輔助下,重視數字內容管理,從整體上規劃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方案,加強數字化服務體系建設。
1.3 技術支持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網絡信息技術越來越發達,相應的多媒體等技術取得了高速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可以使用的技術更加先進,出現了精度非常高的數字化技術。該技術是多種智能技術的匯集,包括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在優良的計算機網絡環境下,積極研發相關輔助系統,為中國文化遺產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從而保障文化遺產的健康穩定發展,為后期的開發與利用提供重要依據。根據現有文化遺產的文字、聲音等信息,通過數字化檢索、建立數字化博物館等方式,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播工作的順利開展。當今時代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情況下,特別是數字攝影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能夠為文化遺產數字化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撐,促使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與傳播。
1.4 優勢與不足
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中國文化信息實現了大量復制,而且提高了信息傳送速度。數字化時代,文化遺產數字化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①有利于保存和記錄民族傳統文化[3]。通過影像將民族傳統文化記錄下來,實際上是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方式。通過數字技術記錄與保存文化對象,能夠為后期的分析研究提供便利。②有利于展示和傳播文化遺產。隨著時代變遷,由于缺乏有效的保存與傳播方法,一些傳統工藝失傳。應用數字技術可以將傳統工藝清晰地展示出來并且傳播出去。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必須要認識到數字技術的不足,認識到其對文化生態和文化多樣性的損害,如果對數字技術使用不當,極有可能造成文化遺產傳播中,削弱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甚至導致文化扭曲等。
2 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現狀
受歷史變遷和社會活動的影響,許多文化遺產由于人為破壞和歲月侵蝕而陷入保護困境。進入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得到了更多的來自政府部門與學界的普遍重視,文物保護理念逐漸延伸到社會大眾的日常環境與經濟生活當中。雖然現在國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正在大力開展,保護力度與進度都得到了持續的強化,然而,在新時期背景下,關于文化遺產的傳播工作方面,依然存在著一些缺陷與不足之處,主要包括時代的變遷帶來信息傳播途徑的多樣性與傳統文化遺產傳播形式單一的矛盾,全球化信息輸入造成的傳統文化遺產被迫與全球文化進行橫向比較的矛盾,城鄉建設規劃與文化遺產地域保護之間的矛盾,政府資金投入有限與大量的文化遺產亟待保護之間的矛盾,部分文物保存要求的技術手段復雜與現代科技仍不夠發達之間的矛盾等。
3 基于數字技術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播
3.1 文化遺產數字化
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是一種新途徑,即通過虛擬現實技術(VR)、增強現實技術(AR)、三維信息捕捉等信息技術,促使文化遺產能夠和相關的文本、聲音、三維數據等信息關聯起來,客觀記錄有關內容,并開展數字化處理工作,促使其朝著二進制轉換,利用計算機算法運算、總結、編碼之后以新的媒介重現,可進而將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打破,確保信息交互工作的完成。在此基礎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組織了“世界的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項目,旨在用最合適的手段來保護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使得它們能夠最大限度地被盡可能多的人利用[4]。為了加快文化遺產數字化步伐,中國于1996年開始建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工作已經進入良好發展階段,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作也在逐步推進中。“十一五”期間,中國將文化遺產數字化列入國家發展“863”計劃和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用以攻克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的核心技術、公益技術和共性技術的問題。
3.2 文化遺產與數字技術融合的優勢
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展示并非傳統意義上對展示信息的復制和粘貼,而是從一種新的角度進行詮釋和解讀,數字化展示手段與傳統展示手段相比有著諸多因素上的優勢和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傳統展示的展示環境主要為博物館、美術館等室內展廳或一定范圍的室外空間,數字化展示環境為手機、電腦、平板等設備。②傳統展示方式一般為依托展柜的文物實體展示,并輔有圖文影音,數字化展示大多依托互聯網、全息投影或虛擬游覽等。③傳統展示的時間周期受博物館開閉館時間、社會環境等限制,展覽更新較慢;數字化展示可以實現線上24 h不間斷展覽,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展覽更新速度快。④傳統展示的思路常常根據館藏文物的類別、年代等歷史信息按序陳列,思路上呈現出敘事性和線性的特點;數字化展示提供個性化服務,能夠根據用戶興趣按主題定制,思路上呈現出發散性和非線性的特點。⑤傳統展示的受眾范圍主要為到訪的普通觀眾、相關領域的科研學者及從業人員;數字化展示面向社會全體,涵蓋各行各業對文化遺產感興趣的人。⑥傳統展示缺乏交互體驗,多數為隔著玻璃展柜欣賞,無沉浸感,體驗差;數字化展示的交互手段多樣,沉浸感強、參觀體驗豐富。⑦傳統展示的不確定因素較多,一些文物保存難度大、易損壞、安全性低;數字化展示通過建立數字化文檔,永久儲存數據、安全性高。⑧傳統展示無共享性,不可復制,不可二次加工;數字化展示可復制,可二次加工,易于通過互聯網進行館際收藏和信息共享。⑨傳統展示的傳播渠道較為單一,范圍受限,速度較慢;數字化展示通過微信、微博、互聯網等大眾媒體進行傳播,范圍廣、速度快。⑩傳統展示的展示效益受時間、地域和技術手段等因素限制,不能展示館藏內全部文物及相關內容;數字化展示不受時空限制,能夠根據不同人群的需求來展示大量的信息內容。
總的來說,數字化展示不僅能夠拓寬信息呈現的層次,打破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性,拉進社會大眾與文化遺產之間的距離,更是以一種寓教于樂、極具趣味性的方式對大眾起到了教育和傳播意義。
4 基于數字技術的敦煌莫高窟保護應用
公元366年開始了敦煌莫高窟的建設工作,在悠久的中國古代史中,凝聚了彩塑、壁畫、建筑和各個朝代的文化風俗,是國際上最大規模的佛教圣地,也是中國乃至世界藝術史上熠熠生輝的明珠,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世界文化藝術交流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莫高窟內有735個洞窟,2 000余座彩塑和4萬余平方米的壁畫,其藝術寶庫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歷代藝術家在繼承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積極汲取優良的外來文化并再創作,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莫高窟文化。因此,莫高窟內所保存的大量文字和圖像資源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藝術風格以及當時人們的生活生產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在其中,藏經洞內的經書涵蓋了古代政治、法制、宗教信仰、文學、軍事、民俗等領域的文字和圖像資源,無疑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寶庫。始通于公元前2世紀的絲綢之路見證著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其中敦煌是絲路上的重要站點,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地位。隨著文化交流的深入,佛教文化傳入中國,開始與中華傳統文化相交融、發展,絲綢之路沿線的石窟文化,就是對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秦以后、宋元以前,莫高窟不斷發展;元朝后期,敦煌成為邊塞游牧之地,莫高窟日漸冷落荒蕪;晚清時,政府腐敗無能,藏經洞文物慘遭西方列強劫掠;進入20世紀,張大千等學者積極探索敦煌文化,意在喚起敦煌藝術的生命力;1961年,在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中,將莫高窟劃入進來;1987年,其被收錄至“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現如今,敦煌莫高窟的藝術價值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關注。然而,利用傳統方式保護和開發敦煌莫高窟仍面臨著許多的困難,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通過二維、虛擬現實技術等數字化手段保護和傳播敦煌文化實現了新的突破。
4.1 “數字敦煌”
“數字敦煌”是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與傳播的成功案例之一[5]。20世紀90年代,敦煌研究院開始研究利用數字技術保護敦煌文化,“數字敦煌”概念首次被提出,即通過廣泛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資源,永久保存石窟藝術,實現保護與傳承并舉。經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多年的探索,“數字敦煌”項目初步建成,敦煌瑰寶借助數字技術手段和傳播形式走出敦煌,走向了全國,面向著世界。在“數字敦煌”中,系統整理并存儲了敦煌石窟以及有關的文物,將獲取到的圖片、三維等各種數據整合,開展了敦煌文化數字資源庫的建設工作,實現了智能化與多樣化的統一,并借助互聯網面全球資源共享,建立起數字資產管理系統與數字資源科學保障體系。
目前推出的“數字敦煌”線上平臺設有雙語版本,向世界展示了橫跨10個朝代的30個洞窟和4 430 m2的壁畫。自上線以來,“數字敦煌”累計訪問量達700萬余次,訪問國家超10多個。線上的展示方式使人們可以足不出戶了解石窟藝術,領略敦煌的奧妙,為廣大敦煌文化愛好者創造了一個學習和交流的平臺。然而在當下,文化遺產線上平臺的發展仍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其一便是運用數字技術進行開發的線上平臺仍處于初步階段,以“數字敦煌”為例,目前仍有大批洞窟和壁畫亟待修繕及修繕后的數字化處理、錄入、重現,這個過程漫長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其二是文化遺產類的線上平臺受眾相對局限,主要為文化遺產相關從業人員、文化藝術愛好者等,而優秀的文化遺產需要社會全體的廣泛重視,如何使人們更自覺地去了解文化遺產線上平臺,關注文化遺產發展狀況,是相關工作者急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4.2 基于華為AR地圖的數字化敦煌展示
增強現實技術在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建設中同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實現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增強現實技術根植于虛擬現實技術,而又超越了虛擬現實,最終實現的是對物理世界的立體化增強,強調部分虛擬,即疊加在真實環境之中,與虛擬信息同步顯示。
在華為AR地圖中,其建設工作以華為河圖(Cyberverse)為基礎,意在建立一個“地球級的、可持續發展的”數字新世界。在該地圖中,一些重要的技術得到了普遍的運用,比如3D地圖、高精度空間運算、虛實遮擋融合繪制等,在真實世界之上疊加了數字世界,其核心體驗包含實景導覽、AR人機互動等。在華為AR地圖中,真實世界和數字世界沒有界限,真實世界成為信息呈現的面板,各類實時訊息被疊加在用戶當前所處的現實環境中。
敦煌研究院和華為AR地圖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針對敦煌莫高窟開展了相關的數據整理與掃描活動,依托厘米級空間識別技術,制作完成了數字莫高窟,基本將實景環境重現,實現了敦煌壁畫、洞窟的三維空間模型與客觀環境的融合。華為AR地圖提供十足的沉浸感,內置專業的全系講解,如覆蓋全展區的AR引導,在幫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敦煌文化的同時還會隨著參展路線展示不同的敦煌壁畫元素,如九色鹿、飛天等。
利用互動體驗的形式,在游覽莫高窟的過程中,游玩者可以深入了解各座洞窟的細節、傾聽一段久遠的訴說,與敦煌文化一起跨越千年,見證華夏文明的璀璨絢麗。科技給敦煌莫高窟帶來了全新的活力和感知力,促使敦煌記憶變得更加真實。
5 結語
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播中,數字技術無疑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利用數字技術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是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除科技層面外,還應當立足于文化戰略視角,強化開展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活動,運用各項信息資源,高度重視公共和文化屬性,將人文事業和科技導向緊密聯系起來,推動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