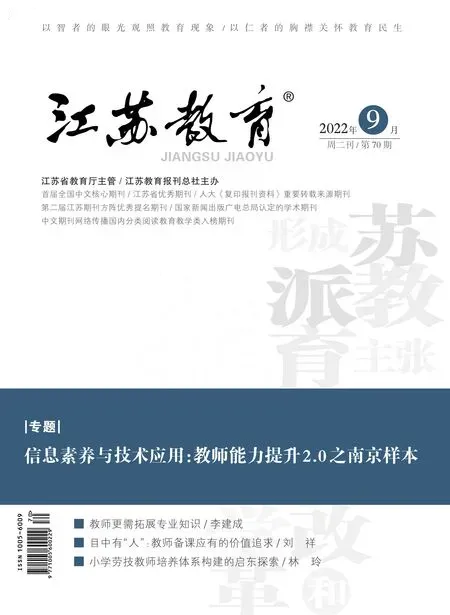追尋教育的三重境界
王亦晴
有幸擔任李吉林老師的助手,一做就是15年,我見證了她不懈追求的教育生涯的三重境界:教書—育人—立說。它們既相互交融,又呈現(xiàn)螺旋上升之勢,昭示了一條每個教師都可以行走其間進而獲得職業(yè)價值感的道路。
以研究之眼,看向教學的深處
有青年教師來找李老師備課時,李老師常常讓我一起聽。她不會立即發(fā)表對教學設(shè)計的意見,而是同大家認真地分析教材,理清教學目標、重點和難點。她始終秉持基于學生、立足教材、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贊成青年教師為了讓課堂出彩而急于創(chuàng)設(shè)一個有趣的情境。于她而言,教學是一個需要遵循客觀規(guī)律,需要有大量的經(jīng)驗支撐,并且需要不斷尋找新的、更適切的方法的過程。
受李老師影響,我也不斷改變看待教學的眼光,去琢磨、追問每一個設(shè)計背后的道理。《蜜蜂》是一篇科學小品文,具有探究性特點,我想結(jié)合情境讓學生擔當“小小研究員”,激發(fā)他們的學習熱情,通過合作探究推動學習進程。然而,學生在小組合作中,理清實驗經(jīng)過、提煉實驗步驟所需的時間大大超過預期;在小組合作演示時,組內(nèi)的分工也不夠合理,影響了演示的效果。學著李老師那樣,我客觀地觀察學生、審視課堂,自覺地進行反思,并做了較大調(diào)整:對于三年級學生來說,“實驗過程”不必過于細化,改用按實驗順序擺放提示卡片的方式,既節(jié)省了時間,又為后面的演示做了鋪墊。演示部分則改為一位學生邊演示、邊講解,在進一步明晰實驗過程的同時,結(jié)合情境進行語言表達。于是,學生很快就達成學習目標,過程也更為清晰、流暢。這又觸發(fā)我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任何一種新的、好的教學方法對于不同年齡段、不同基礎(chǔ)的學生來說,實施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只有在大量實踐中努力把握適用情形的細微差別,教學才能更加科學而準確。教學方法“萬變不離其宗”,“宗”既是核心學科知識和能力,也是兒童的特點及其學習基礎(chǔ),如此設(shè)計相關(guān)訓練,方能行之有效。
用研究的眼光看教學,它不再是照本宣科的重復性勞動,而是以“工匠精神”和專業(yè)態(tài)度去打磨一項技藝。李老師爐火純青的教學藝術(shù),源于真實教學場景中無數(shù)表象所匯聚而成的直覺,是長期執(zhí)著鉆研、積智成慧的結(jié)果。
以樹人之心,拓展教育的寬度
李老師不把自己定義為“教語文的老師”,而是始終懷抱著“樹人”的信念,她堅信每一位大腦健全的兒童都潛藏著智慧。她說:“兒童身上有著一種沉睡的力量,我們要把它喚醒。我們要把他教得聰明起來,還要培養(yǎng)他的精神世界,使他成為‘人’。教育說到底,是‘人’的教育。”在李老師的教育“地圖”中,學習、研究的“疆域”十分廣闊。眼中有“人”的教育教學,也必然在達成學科教學目標的基礎(chǔ)上,較好地兼顧、滲透著情感、態(tài)度、審美、價值觀等培育目標,實現(xiàn)教學與育人的統(tǒng)整。
我也學著李老師那樣,嘗試用更深遠的視角來看待教學的意義,努力把學生教得更聰明、更靈活。執(zhí)教《在牛肚子里旅行》時,我原想用簡易卡通圖表現(xiàn)“牛的四個胃”,讓學生能輕松地根據(jù)課文內(nèi)容畫出“紅頭”在牛肚子里的運動過程。轉(zhuǎn)念一想,未來的他們需要有科學探究的精神,如果能借此機會看一看“牛肚子里的世界”簡明示意圖,他們則會發(fā)現(xiàn),四個胃室并不像想象中那樣連成一條直線,而是相互交錯,“紅頭”的旅行線路也會變得像“走迷宮”那樣奇妙……培養(yǎng)科學家不是我們的任務(wù),為學生涵育科學精神卻是應(yīng)有的擔當。
學生果然對這幅示意圖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爭著要來畫“紅頭”的運動線路,能夠?qū)φ照n文講解得準確清晰。甚至有學生提出疑問:“‘青頭’說只有第四個胃才是管消化的,‘紅頭’經(jīng)過了第一個胃和第二個胃,那第三個胃有什么用?”我欣喜于學生有了如此主動的、探索性的思考。真正的學習不就是從大量的信息中去理解、過濾、篩選,進而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和尋求答案嗎?把兒童的認識和思維帶入一個更靈動、自由的天地里,讓我看到了教育的可為之處是如此寬廣。
以超越之志,探尋教育的遠方
肖川教授說,教育家能夠代表他所在的時代,具有原創(chuàng)性地回答教育理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提出富有解釋力的理論命題或者概念,其實踐探索影響了同時代人的教育行為,改變?nèi)藗儗Υ逃那楦小B(tài)度和評價。李老師就是這樣的教育家。從理論角度看,她創(chuàng)造性地把握了“情境”這一核心概念,從民族文化中汲取智慧,將中國古代文論的“情境”“意境”滲透到自身教育教學實踐和教育思想體系中,又與西方的情境認知理論遙相呼應(yīng)。李老師說:“要把實踐的感受不斷地取舍、提煉,在反思中產(chǎn)生頓悟。”她把實踐探索得到的點滴認識用寫隨筆、寫論文的方式積累起來,探尋其中的規(guī)律。久而久之,零星的想法變得愈發(fā)有條理;在不知不覺中,對教育教學本質(zhì)的認識水平和理論概括能力逐步提高了,不斷實現(xiàn)著跨越式發(fā)展。
李老師的教育主張不是只從書中得來的理論,而是從長期實踐中反思、歸納和建構(gòu)起來的。她以自己獨有的話語方式去“立說”,建立起情境教育理論體系,架起實踐與理論之間的橋梁,讓廣大一線教師看到如何憑借情境將教書與育人有機地融合起來。李吉林老師的“教書—育人—立說”三重境界可以鼓舞更多的教師去追尋“自己心中的教育高峰”,使自身職業(yè)價值得以不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