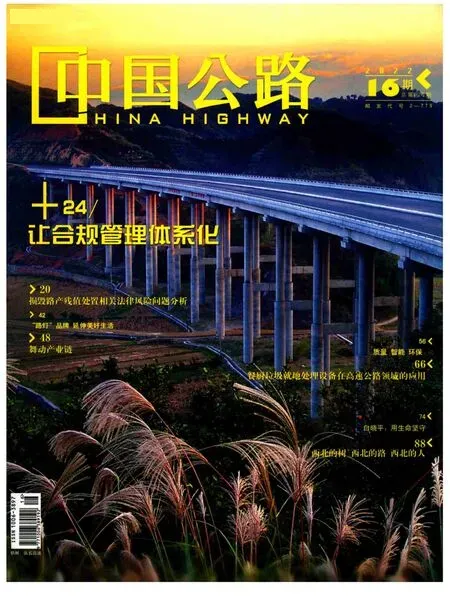調整思維 走出執法協作困境
文 浮塵
成天一針見血,
自認快意恩仇。
苦心尋章摘句,
風雨中猶清醒。
所謂生民立命,
過眼便成浮塵。
文章若能濟世,
應問懸壺之人。
協作內容
前文通過力量對比差異分析了執法部門在協作過程中遭遇的被動處境,隸屬改革遺留問題,它的消化需要時間,但執法協作是以行業為主的改革方案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執法協作必然在遺留問題的影響下進行。比如:你們需要的協作,具體內容有哪些,能列個清單嗎?這是一位領導在協作辦法討論時拋出的“靈魂拷問”。如果不知道,談什么協作?如果知道而思考不深,拿出來也是貽笑大方。這里試舉四方面內容。
辦案協作
辦案過程中,雙方可圍繞嫌疑線索移交(核實)、軟件協作交互、行業信息通報、行政許可內容及技術鑒定、設備調用、支撐證據等方面開展協作。在行政強制的查封、扣押、代履行等方面,也可在場所、機械、設施、設備、人力等方面開展協作。
檢查協作
分家前,行業檢查和執法檢查本為一體,一次檢查結果可多渠道共享。改革后,執法信息來源渠道依然包括行業檢查、通報等。因此,聯合檢查、行業檢查、數據分析成果共享均可作為執法協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普法協作
在一體化的法律設計中,行業部門與執法機構均有普法義務。充分利用行業宣傳體系相對健全、預算資金相對寬裕的優勢,開展聯合普法,可有效提升普法集約化程度,提高普法覆蓋面,節約社會資源。
其他協作
包括行政許可過程、事中事后監管、借用人員管理等。
總之,協作是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中多數能實現互利共贏。當前,阻礙協作推進的主要原因,是雙方的精力更多用于零和博弈,很少朝協同共贏的方向去思考。以辦案協作為例,行業似乎付出較多,但執法也幫忙凈化了環境,何況行業的這些付出,還可從許可協作和事中事后監管中得到補償。再如檢查協作、普法協作,都是一舉兩得、雙方受益的事情,思維一轉換,爭議和計較就會減少很多。
談判籌碼
從共贏層面厘清問題,只是在談判思路上找到了突破,分家時帶來的“先天缺陷”,仍然沒有解決。要在談判中取得主動,必須分析“以小博大”的籌碼,盤點可以團結的對象,才可能爭取失衡補償。
首要籌碼 三定方案
合作博弈三條原則中,三定方案是基礎,需要實際工作與支撐匹配,裁判員不偏不倚。在強弱對比明顯的非對稱博弈中,事先確定的標準,是對改革思路的最佳體現,是實質賦權的直接佐證,是合作談判的首要籌碼,也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底線。對此,應對策略是團結人事部門一起鎖定三定方案,厘清改革主要思路,避免因混淆造成的一團漿糊,讓談判無據可依,被莫名帶入對方的知識語境成就被動。
次要籌碼 資源匹配
事權、財權、財力是行權的三要素。改革落地中的諸多困惑,主要集中在財力和事權不匹配。表現為上級要求越來越高,保障差距越拉越大,這可成為談判的第二籌碼。原因是外部補償不能到位時,“對內挖潛”就名正言順。主要理由是資源分配不均,行業分家時的“多吃多占”應在榮辱與共的集體語境中得到補償(例如,行業與執法一體時,執法經費預算與行業預算一體,分家后,這部分費用并未隨職能的剝離而“財隨事走”,新成立的執法單位面臨財政預算逐年壓縮的困惑)。這里,最關鍵是讓主管部門意識到,在法律一體化的語境中分離的改革,解決爭議是持久而漫長的過程,過渡期間,讓實力相對占優的一方承擔更多,是最佳應對策略。第二籌碼的團結對象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門中的法規處(科、股),他們具有行業監督指導責任,與執法隊伍一榮俱榮。
第三籌碼 過程糾結
拋開改革思路、方案的問題不談,改革后半篇的最大癥結在于:改革思路不能一以貫之,造成“穿新鞋走老路”,耽誤工作落地。按照改革設計最大限度維持行業完整性的方案,以行業為主的改革方案中,行政檢查更多地應由行業以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名義實施(實際上,執法檢查也只是行政檢查的真子集),執法案件以流轉型為主,執法機構僅負責案件辦理。第三籌碼的團結對象是行業主管部門中對應的業務處室,因其身負“雙重角色”,最清楚改革后各方的承受能力和權力運作。
第四籌碼 團結對象
目前,執法部門分擔了原屬于交通行政主管部門職責范圍的工作,這一點應讓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部門領導盡快知悉。以省級執法為例,按照“整合分散在行業部門中的執法門類”的思路,本輪改革集中的是公路路政、水路運政、工程質監及水運領域執法。而基本建設程序、市場信用和行政許可執法,這類原來在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執法,未被劃入綜合執法改革內容。三定方案中,之所以要將“承擔省級執法事項”的表述放在最后,實際上是以集中的四類執法事項作為定語,構建以剝離職能為中心的工作語境。這樣一來,省級執法部門承擔的建設程序、市場信用和行政許可執法,其實是在為行政權力集中后的省級主管部門分憂。
以上四種籌碼是外部分析的結果,靈活用于協作談判,可以排除額外干擾,聚焦最終目標,更好地爭取工作主動。當然,這需要談判智慧、工作制度和治理能力作為保障。
未來走勢
談判對象錯位
按照“行政權力向行業主管部門集中、行政處罰向執法機構集中”的制度設計,行政權力和執法工作分家后,協作雙方應為行政和執法,怎么談協作的對象變成了行業和執法呢?其實,這才是協作爭議的源頭——談判主體錯位。行政權力集中,行業主管部門需要重新適應、歸位。傳統“以上級領導簽字代替履職,以任務分解代替管理”的工作思路,在行政權力集中到行業主管部門后,已不合時宜。上級部門用好時勢權力的基礎,是從根源上取得下級的同意權力。因此,適應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以上率下的切實行動。改變固定思維模式和既有工作方法,主動革自己的命,遇事多“下深水”,切實做大格局,才能在改革后以理服人,推動工作落地。
談判最終出路
從一體化制度設計中強行分離的行業和執法,還在零和博弈的思路中斗法,其根源是主管部門喪失權威后未主動歸位。錯位的協作談判造成雙方聚焦于有限資源的零和博弈,“節流”的思路限制了“開源”的空間。要走出協作困境,除了需要兩部門力同心外,還需要行業主管部門適時轉換角色,主動參與,“下深水”示范。
例如,執法保障,特別是新機構資金保障的專項爭取問題;行權事項目錄、首次輕微違法承諾免罰范圍問題;盡職免責內容落地和容錯機制建設,以及改革中一些職責的留白由誰承擔等問題,都不能停留在寫一篇調研報告了事的認識上。主管部門“下深水”,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可以深入催生執法協作的內生動力,促成協作從“節流”向“開源”轉變,從業內零和博弈向業間資源匹配轉變,從而將隊伍帶向一個新的起點。
執法當自強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協作談判僅是權宜之計,執法機構必須向獨立履職的方向努力,這是執法存在最為重要的價值,也是具備“獨立人格”的必經之路。為此,縱橫向的調研與溝通協作必須盡快提上議事日程;一些地方客觀存在的、特定專業執法“跛腳”的問題,也必須引起足夠重視;一些法定術語趨于寬泛、模糊的定義等,必須盡快明確;無論難度再大,開發全國統一的執法系統,必須持續推進……簡而言之,執法自強需要面對的還有很多,路還特別漫長。
在涉及非對稱態勢的零和博弈中,牽頭部門缺位時,“節流”“對抗”的思維占據了主導地位,錯位的談判雙方對“開源”“雙贏”的思考不夠,造成協作嫌隙。執法協作在爭議中較量,其主觀原因是思維適應不了新的改革定位;客觀原因是主管部門垂范不夠,未能及時發現并消除的“模糊地帶”,讓爭議有了發酵空間。這是職能型組織架構的缺點被放大的典型案例,深入總結這一情況,有利于為后期改革提供借鑒,這個咱們下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