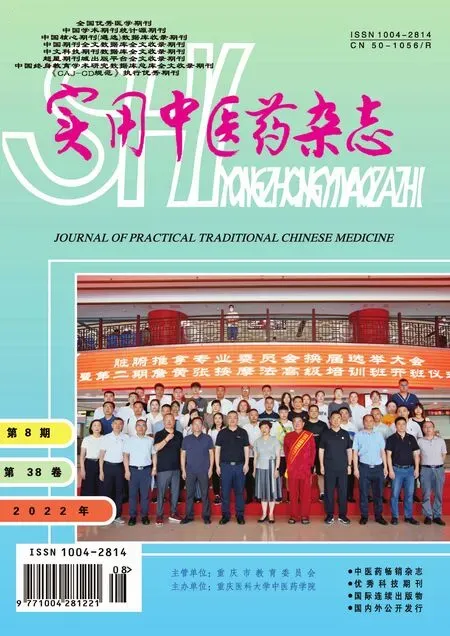從少陽病論治灼口綜合征臨床體會
郭智寬,翟紅印,張 勇,崔文哲
(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中醫科,河南 鄭州 450052)
灼口綜合征(burning mouth syndrome,BMS)是一種常見的口腔黏膜疾病,是以口腔及舌部為主要發病部位,以燒灼樣疼痛為主要表現,同時可有口干或其他味覺改變的一種綜合征,常不伴有明顯的臨床損害體征,也無特征性的組織病理改變[1]。據國外報道BMS的患病率在0.7%~8%,在女性中特別是中老年女性中發病率較高,女性是男性發病人數的7倍[2]。目前對灼口綜合征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治療多采用去除可能的誘因(假牙、齲齒等)、補充B族維生素及抗焦慮、抑郁治療[3]。我們據胡希恕經方理論認為其符合六經辨證中的少陽病,并依據此理論指導治療取得滿意療效,介紹如下。
1 中醫認識
中醫雖無灼口綜合征的病名,但歷代醫家不乏舌痛的描述,如《黃帝內經·靈樞》中就有“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的記載,《證治準繩·雜病·第八冊·舌》中也說“若恚怒過度,寒熱口苦,而舌腫痛”。《備急千金要方》舌論第三中說:“多食甘則舌根痛而外發落,……若臟熱則舌生瘡引唇揭赤”。所以本病屬中醫“舌痛”范疇。
2 治療進展
辨證分型上多以臟腑辨證為主。如彭于治等[4]認為更年期婦女所患灼口綜合征多屬腎虛所致“形衰精虧”,給予左歸丸加減以滋腎補陰治療。劉艷等[5]認為灼口綜合征的病機關鍵于脾胃損傷、心火上炎,治療應從心脾論治,以溫陽健脾、行氣導滯、清瀉心火為治則,選用黃芪建中湯合導赤散治療。李馨蘭[6]則認為依據《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載“心主舌”,灼口綜合征治療應以清痰熱、開心竅的方劑為主。吳迎濤等[7]認為腎陰虧虛,心火亢盛為灼口綜合征的主要病機,用連梅湯加味治療效果滿意。朱建華[8]認為本病病位在腎,病機為陰陽失調、氣血失和,采用自擬灼口飲治療。熊連珠等[9]認為BMS因各種因素傷及肝腎,導致虛火循經上炎,或肝氣失于疏泄,肝郁化火,耗陰,陰不制陽,火熱內生,而灼傷舌體,自擬滋陰降火方治療。
3 從少陽論治
胡希恕教授為我國近現代杰出的經方家,中醫臨床家,其提出的《傷寒論》的六經來自八綱的理論得到了中日兩國研究經方學者的廣泛認可[10-11]。
《傷寒論》第263條少陽病提綱曰:“少陽之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第264條曰:“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據此胡希恕教授認為少陽病屬于半表半里的陽熱性疾病,既不在體表,也不在胃腸消化道,而是胸腹腔間一切臟器均屬于半表半里的范疇。如果熱邪郁積在半表半里,邪氣既不能出表,也不能入里,只能上循孔道行至耳鼻口咽而發病,以至五官孔竅出現陽性熱性癥狀[11]。《靈樞·經脈》曰:“脾足太陰之脈,……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是動則病舌本強,……舌本痛”;“腎足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干,咽腫上氣,嗌干及痛”;“手少陰之別,……循經入于心中,系舌本”;“肝足厥陰……其支者,從目系下頰里,筋者聚于陰氣,環口唇”。又曰:“厥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而脈絡于舌本也”;《素問·金匱真言論》謂:“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所以心、肝、脾、腎諸臟皆與舌與口的感覺密切相關。同時結合胡希恕教授六經理論中少陽病的病位位于胸腹腔間,故不論中醫心、肝、脾、腎出現病變導致的舌痛均可以從少陽論治。
4 病案舉例
患者,女,47歲,2021年3月27日初診。1個月余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舌面、口腔灼熱、疼痛,吃涼東西時明顯,饑餓時消失,伴有咽干不適,右脅肋部輕微脹痛,納谷不香,睡眠可,大便干,3~4天1次,小便正常,舌淡紅苔薄黃,脈弦。中醫診斷為舌痛,少陽陽明合病。藥用北柴胡12g,黃芩12g,白芍12g,黨參20g,法半夏9g,枳實12g,大黃10g,生石膏30g,生姜5g,大棗10g。7劑,水煎早晚分服。二診,舌面、口腔灼熱感消失大半,大便已通暢,仍存在咽部不適,舌苔、脈象同前。上方加厚樸10g,紫蘇葉8g。繼服10劑,諸癥消失。再給予原方7劑鞏固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