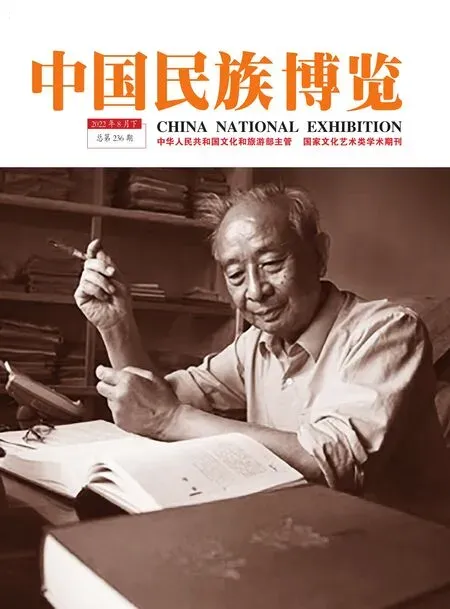高師西方音樂(lè)史教學(xué)中歌劇鑒賞思維培養(yǎng)的幾點(diǎn)思考
——以歌劇《茶花女》為例
姚 穎
( 濱州學(xué)院,山東 濱州 256600)
高師音樂(lè)學(xué)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在中共中央全面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新時(shí)代學(xué)校美育工作的進(jìn)程中,承擔(dān)著中小學(xué)音樂(lè)師資培養(yǎng)的重要任務(wù)。“西方音樂(lè)史與作品欣賞”是高師音樂(lè)學(xué)專業(yè)的核心課程,內(nèi)容以西方藝術(shù)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歷程為線索并輔以相關(guān)作品鑒賞,其也是中小學(xué)音樂(lè)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歌劇(opera)作為用音樂(lè)展開(kāi)戲劇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是西方音樂(lè)史中復(fù)調(diào)音樂(lè)體系向主調(diào)音樂(lè)體系過(guò)渡的里程碑,是貴族文化走向大眾文化的藝術(shù)體裁。它的發(fā)展凝結(jié)著西方音樂(lè)戲劇藝術(shù)審美上的變化,它承載的復(fù)雜思想感情反映出重大的社會(huì)性、哲理性問(wèn)題,是人們的思想情操、道德面貌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體現(xiàn)。因此,歌劇對(duì)音樂(lè)學(xué)專業(yè)學(xué)生藝術(shù)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道德情操的塑造以及在未來(lái)進(jìn)入中小學(xué)承擔(dān)起美育工作,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學(xué)生對(duì)歌劇的認(rèn)知尚處于了解歌劇故事、看過(guò)幾部經(jīng)典作品、會(huì)唱幾首詠嘆調(diào)淺嘗輒止的狀態(tài)。因此,本文從音樂(lè)學(xué)專業(yè)素養(yǎng)、能力與中小學(xué)藝術(shù)教育需求對(duì)接的角度入手,以歌劇《茶花女》為例,談?wù)剬?duì)學(xué)生歌劇鑒賞思維能力培養(yǎng)的幾點(diǎn)思考。
一、梳理歌劇相關(guān)背景材料
在鑒賞歌劇之前,梳理歌劇創(chuàng)作的相關(guān)背景資料、歌劇故事梗概,從人文的視角走進(jìn)歌劇,是鑒賞前必要的基礎(chǔ)工作。
歌劇《茶花女》(La traviata)由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作曲,弗朗奇斯科·瑪利亞·皮亞韋(Francesco Maria Piave)編劇,1853年3月于意大利威尼斯芬尼斯歌劇院首演的一部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歌劇。它是世界歌劇史上上座率最高的經(jīng)典作品之一,也是我國(guó)上演的第一部西洋歌劇。
該作品取材于亞歷山大·小仲馬(法語(yǔ):Alexandre Dumas fils)在1848年出版的同名長(zhǎng)篇小說(shuō)及1849年改編的話劇,故事講述了巴黎上流社會(huì)交際花瑪格麗特·戈蒂埃(Marguerite Gautier)與青年阿爾芒·杜瓦爾(Armand Duval)之間曲折凄婉的愛(ài)情故事。據(jù)說(shuō)故事的原型是小仲馬與大約在1844年結(jié)識(shí)的瑪麗·迪普萊西(真名阿爾豐西娜·普萊西)的一段真實(shí)愛(ài)情經(jīng)歷。威爾第深受小說(shuō)和話劇感染,決定將其改編成歌劇,這是歌劇史上第一次以風(fēng)塵女子為主角的大膽嘗試。歌劇的腳本在小說(shuō)和話劇基礎(chǔ)上將原有五幕縮減為三幕,主人公的名字也由瑪格麗特改為薇奧莉塔·瓦蕾莉(Violetta Valery),阿爾芒改為阿爾弗萊德·亞芒(Alfredo Germont)。簡(jiǎn)潔的故事情節(jié)聚焦在女主角薇奧莉塔身上,突出了情節(jié)發(fā)展與沖突中薇奧莉塔的心理狀態(tài)。
二、歌劇《茶花女》音樂(lè)戲劇性分析
美國(guó)音樂(lè)學(xué)家科爾曼(Joseph Kerman)認(rèn)為歌劇首先、而且主要是“戲”——通過(guò)動(dòng)作和事件展現(xiàn)人的沖突、感情和思想。在這一過(guò)程中,音樂(lè)承擔(dān)著最重要的表現(xiàn)職責(zé)。并強(qiáng)調(diào)歌劇腳本應(yīng)是被音樂(lè)所重新詮釋后的結(jié)果。美國(guó)音樂(lè)批評(píng)家愛(ài)德華·T.科恩(Edward T.Corn)也強(qiáng)調(diào):“每一個(gè)重要的戲劇動(dòng)作都必須在某處被轉(zhuǎn)譯成音樂(lè)的表述。……它必須作為音樂(lè)被聽(tīng)到。”[1]因此,歌劇中音樂(lè)承載著戲劇。從音樂(lè)和戲劇的視角走進(jìn)歌劇是培養(yǎng)學(xué)生歌劇思維的重要途徑。
(一)音樂(lè)主題的戲劇性暗示
歌劇《茶花女》使用音樂(lè)主題增強(qiáng)全劇的戲劇性。
1.前奏曲
歌劇的序曲或前奏曲經(jīng)歷了從其最初提示歌劇即將開(kāi)始,到逐漸承擔(dān)戲劇功能(如莫扎特《唐璜》序曲采用奏鳴曲式結(jié)構(gòu)很好地詮釋了唐璜的性格;歌劇《命運(yùn)之力》的序曲是全劇情節(jié)的概況)的發(fā)展過(guò)程。《茶花女》的前奏曲如同一個(gè)未卜先知的水晶球,在大幕拉開(kāi)之前就揭示了故事的結(jié)局。
前奏曲由兩個(gè)主題組成。第一主題“悲劇主題”(譜例1)。以半音、半音下行旋律為主,調(diào)性從b小調(diào)轉(zhuǎn)到e小調(diào)又轉(zhuǎn)到C大調(diào)、B大調(diào),調(diào)性不穩(wěn)定。這個(gè)主題在第三幕的前奏曲再現(xiàn)并充分發(fā)展,小提琴嘆息般纖弱的音色描繪出已身患疾病的薇奧莉塔孱弱、悲戚的形象,預(yù)示了主人公悲劇命運(yùn)的結(jié)局。

譜例 1
第二主題(譜例2)是該劇的核心主題。E大調(diào),下行旋律,結(jié)構(gòu)方整,具有歌唱性。抒情優(yōu)美、略帶傷感色彩。由于該主題旋律與第二幕薇奧莉塔與阿爾弗雷德分手時(shí)的旋律(譜例3)基本相同,故將該主題稱為“告別主題”。

譜例 2

譜例 3
這個(gè)主題變化衍生出第一幕中阿爾弗雷德向薇奧莉塔示愛(ài)的“愛(ài)情主題” (詠嘆調(diào)《幸福的一天》Un di felice eterea)。(譜例4)

譜例 4
“告別”主題衍生出的“愛(ài)情主題”已經(jīng)暗示了薇奧列與阿爾弗雷德的情感走向。
前奏曲兩個(gè)主題預(yù)示了該劇女主人公失去愛(ài)情香消玉殞的人生悲劇。
2.詠嘆調(diào)
詠嘆調(diào)中也使用了音樂(lè)主題來(lái)加強(qiáng)故事的戲劇性。
第一幕阿爾弗萊德與薇奧莉塔的二重唱《幸福的一天》中,阿爾弗萊德向薇奧莉塔表白:“大約在一年前,你在我面前走過(guò),自此那天起,我愛(ài)上了你,這愛(ài)情無(wú)處不在,簡(jiǎn)直跟宇宙同呼吸……”[2]這是“愛(ài)情主題”(譜例4)第一次正式出現(xiàn)。之后,這個(gè)主題在詠嘆調(diào)《啊!夢(mèng)中的人兒》(Ah,fors’è lui che l’anima)中再現(xiàn),由薇奧莉塔唱出,她重復(fù)了阿爾弗萊德的話“這愛(ài)情無(wú)處不在,簡(jiǎn)直跟宇宙同呼吸……”,表現(xiàn)出薇奧莉塔對(duì)愛(ài)的心動(dòng)、憧憬與渴望。緊接著,“愛(ài)情主題”又在薇奧莉塔的一段卡巴萊塔《及時(shí)行樂(lè)》(Sempre libera degg’io)中以阿爾弗萊德愛(ài)情誓言的情景閃回形式穿插在薇奧莉塔激烈而興奮的情感矛盾中,并反復(fù)再現(xiàn),以此來(lái)強(qiáng)化愛(ài)情誓言。此時(shí)的“愛(ài)情主題”已經(jīng)像一顆愛(ài)情種子種在了薇奧莉塔心里,每當(dāng)她產(chǎn)生對(duì)愛(ài)的游移、不確定,“愛(ài)情主題”便會(huì)在她的腦海中浮現(xiàn),她甚至想用歇斯底里的聲音掩蓋住對(duì)阿爾弗萊德愛(ài)的向往,但已經(jīng)無(wú)法控制,直到在糾結(jié)中筋疲力盡。
“愛(ài)情主題”的三次出現(xiàn),從愛(ài)的表白—心動(dòng)渴望—掙扎中接受,描繪出薇奧莉塔面對(duì)愛(ài)情復(fù)雜、糾結(jié)的心路歷程。
由此可見(jiàn),音樂(lè)主題猶如隱藏的戲劇標(biāo)簽,在塑造人物的同時(shí)暗示了歌劇的戲劇走向。
(二)歌劇片段戲劇性分析
戲劇,是動(dòng)作的藝術(shù)。動(dòng)作包括內(nèi)部動(dòng)作和外部動(dòng)作。內(nèi)部動(dòng)作是引發(fā)外部動(dòng)作的內(nèi)在動(dòng)因,內(nèi)部動(dòng)作的變化往往是外部事件影響內(nèi)心誘發(fā)矛盾所引起的,這也是引發(fā)戲劇動(dòng)作發(fā)展的根本動(dòng)因。[3]對(duì)話,作為戲劇動(dòng)作的一種方式,體現(xiàn)出人物潛在的意愿,并且對(duì)談話的另一方具有一定的沖擊力或影響力,使雙方的關(guān)系有所變化、發(fā)展,是劇情發(fā)展的組成部分。[4]歌劇《茶花女》采用了傳統(tǒng)分段式音樂(lè)戲劇結(jié)構(gòu),戲劇動(dòng)作(對(duì)話)則是通過(guò)音樂(lè)來(lái)表達(dá)的。
如圖表1、2、3所示,是該劇第二幕第一場(chǎng)阿爾弗萊德的父親喬治·亞芒(Giorgio Germont)拜訪薇奧莉塔并勸其與阿爾弗萊德分手的戲劇場(chǎng)景。兩人三個(gè)回合的角力由喬治引發(fā)以戲劇性對(duì)話展開(kāi),黑色代表喬治,紫色代表薇奧莉塔,橙色代表內(nèi)部動(dòng)作對(duì)外部動(dòng)作的影響,紅色代表兩人的矛盾沖突。音樂(lè)上由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組成。

圖 1

圖 2

圖 3
由圖1至圖3可知,在喬治與薇奧莉塔第一回合博弈中,不論是先從氣勢(shì)上壓倒對(duì)方還是斥責(zé)她貪圖享受侵占他兒子的遺產(chǎn),都沒(méi)有成功拆散兩人。但喬治卻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了薇奧莉塔的弱點(diǎn):善良的本心和對(duì)阿爾弗萊德勝過(guò)生命的愛(ài)。于是在接下來(lái)的第二回合從善良出發(fā)對(duì)薇奧莉塔進(jìn)行道德綁架,遭拒絕;第三回合則從愛(ài)出發(fā),分析阿爾弗萊德對(duì)她的愛(ài)并不可靠,直擊薇奧莉塔內(nèi)心最不能承受的痛處,致使薇奧莉塔徹底崩潰,放棄這段被視為人生唯一希望的愛(ài)情。從戲劇節(jié)奏上看,每一個(gè)回合都有兩人激烈的爭(zhēng)執(zhí)、對(duì)抗,但激烈程度各有不同。第一回合來(lái)勢(shì)兇猛,但殺傷力最小;第二回合最激烈,兩人對(duì)抗性最強(qiáng),不分勝負(fù);第三回合喬治抓住機(jī)會(huì)猛擊薇奧莉塔的痛處,這一回合最為痛心。另外,三個(gè)回合中非常巧妙地安排了兩次節(jié)奏的停頓。第一次是第一回合結(jié)束后,喬治不甘失敗思考著接下來(lái)與薇奧莉塔博弈的策略,這次停頓看上去是喬治夸贊薇奧莉塔以緩和兩人的關(guān)系,實(shí)則是在思考下一步博弈的關(guān)鍵點(diǎn)。第二次是第二回合兩人僵持不下,喬治放緩的戲劇節(jié)奏,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幫薇奧莉塔分析現(xiàn)狀。這三個(gè)回合塑造出薇奧莉塔善良和為愛(ài)癡狂的形象,同時(shí)也刻畫出喬治既有作為父親慈善的一面,又有為了維護(hù)家族榮譽(yù)不惜傷害薇奧莉塔的精明與偽善的形象。由此可見(jiàn)作曲家威爾第在創(chuàng)作上對(duì)人物心理層次細(xì)膩的把握。
三、歌劇《茶花女》版本分析
我國(guó)著名音樂(lè)學(xué)家陶辛教授曾這樣說(shuō)道:“歌劇在當(dāng)下,既是一種以音樂(lè)為主體的供人‘聽(tīng)賞’的古老經(jīng)典藝術(shù)形式,又是一種有著較為復(fù)雜的意義生成機(jī)能的現(xiàn)代性乃至先鋒性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形式。”2010年我國(guó)國(guó)家大劇院邀請(qǐng)海寧·布洛克豪斯(Henning Brockhaus)導(dǎo)演對(duì)這部作品進(jìn)行了現(xiàn)實(shí)與抽象相結(jié)合新嘗試,為觀眾呈現(xiàn)出一部充滿魔幻的、亦幻亦真的佳作。
(一)多種敘事方法的使用
序曲音樂(lè)奏響,舞臺(tái)上巨幅鏡面緩緩打開(kāi),如同呈現(xiàn)在觀眾眼前的一封巨大“信”被打開(kāi),隨著序曲的第二部分奏出,阿爾弗萊德手拿他與薇奧萊塔的信若有所思地踱步而上,此時(shí)鏡面被燈光折射,透視出薇奧莉塔去世后的遺物拍賣現(xiàn)場(chǎng)……故事采用倒敘的方式,以阿爾弗萊德的回憶展開(kāi),引領(lǐng)觀眾走進(jìn)一個(gè)塵封已久的故事。由于鏡面打開(kāi)與舞臺(tái)成45度角,舞臺(tái)邊緣的部分并未投影在鏡面中,阿爾弗萊德在鏡面的反射區(qū)與未反射區(qū)的移動(dòng),如同自己在現(xiàn)實(shí)與過(guò)去的回憶中穿梭,承擔(dān)著故事的講述人和劇中人物的雙重角色。
這一版本中還使用了電影蒙太奇閃回的敘事手法。第二幕喬治撫慰?jī)鹤映鹆恕稄钠樟_文察的海上》(Di Provenza il mar),此時(shí)地面上出現(xiàn)了一個(gè)“照片墻”,阿爾弗萊德在父親的吟唱中躺在“照片墻”上并由鏡面反射出來(lái),那一幅幅照片就像往日的回憶在阿爾弗萊德的腦海中閃回。
(二)舞美的獨(dú)特設(shè)計(jì)
在這一版本中,舞美設(shè)計(jì)是一大亮點(diǎn)。
首先,歌劇開(kāi)始前幕布上一朵白色的茶花靜靜地從花心開(kāi)始慢慢地暈染成紅色,這一妙筆不僅是在強(qiáng)調(diào)故事將圍繞女主人公茶花女薇奧莉塔展開(kāi),更重要的是茶花女一個(gè)月30中有25天戴白色茶花,5天戴紅色茶花,戴紅色茶花時(shí)她并不接客。薇奧莉塔與阿爾弗萊德相遇時(shí)正好戴了紅色茶花,這也表明兩人的關(guān)系,阿爾弗萊德并不是薇奧莉塔的恩客。
其次,不得不提的就是那副長(zhǎng)22米、寬12米的巨幅鏡面。它將西方歌劇的寫實(shí)與中國(guó)審美的寫意相結(jié)合,為觀眾營(yíng)造出一種虛實(shí)結(jié)合的夢(mèng)幻情境;舞臺(tái)與傾斜45度的鏡面給觀眾呈現(xiàn)出舞臺(tái)鏡面反射區(qū)、無(wú)反射區(qū)、舞臺(tái)本身的三重戲劇空間,如同觀看一部由阿爾弗萊德講述的劇中劇,它打破已有版本“四堵墻”戲劇敘事模式。特別是歌劇第三幕結(jié)束時(shí),鏡面打開(kāi)成90度,觀眾也被反射進(jìn)鏡面成了劇中的角色,一時(shí)間不知是觀眾入了戲,還是夢(mèng)境照進(jìn)了現(xiàn)實(shí)。
最后,平鋪在舞臺(tái)地面的畫幕。共六幅,是巨幅鏡面反射的重要內(nèi)容,營(yíng)造出故事發(fā)生的物質(zhì)空間和心理空間。如第一幕那如油畫般精致絢麗的畫幕迅速將觀眾代入到19世紀(jì)茶花女生活的奢靡舞會(huì)中,而第二幕的小雛菊則營(yíng)造出角色的心理空間。每一次場(chǎng)景的轉(zhuǎn)換都會(huì)將地幕撕開(kāi),仿佛看到了阿爾弗萊德在回憶與薇奧莉塔美好過(guò)往時(shí)內(nèi)心撕裂的疼痛。
歌劇《茶花女》自1852年創(chuàng)作以來(lái)的一個(gè)半世紀(jì)里,音樂(lè)家和導(dǎo)演用不同的方式、視角詮釋著這部作品。雖然故事本身、角色、音樂(lè)都遵循著威爾第原有的創(chuàng)作藍(lán)本,但每一次復(fù)排都在為這個(gè)作品制造新的意義使其更具時(shí)代感,更符合當(dāng)下的審美。
綜上所述,通過(guò)對(duì)歌劇《茶花女》背景資料的梳理、音樂(lè)戲劇性分析以及版本分析可知,在高師西方音樂(lè)史歌劇教學(xué)中除了了解歌劇故事及相關(guān)背景資料外,更重要的是從戲劇動(dòng)作入手對(duì)歌劇的戲劇結(jié)構(gòu)、音樂(lè)的戲劇性、舞美的戲劇性表達(dá)等方面引導(dǎo)、培養(yǎng)學(xué)生從多維視角融合的角度鑒賞歌劇的美,已達(dá)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美育目標(biāo)。